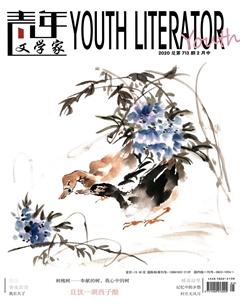叶燮意境论
作者简介:潘佳伟(1996-),女,汉族,浙江湖州人,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小学语文。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05-0-02
概要:
清初著名诗论家叶燮构建了一套自己的诗歌意境创作论。他认为,为文以至极便是达到“冥漠恍惚之境”。要达到这种境界有两个前提,一是诗人在诗歌流变中有所变与不变,二是诗人能拥有托以万物的胸襟来触类起兴。有了这兩个前提后,诗人便能以在我的“才、胆、识、力”构筑在物的“理、事、情”。
1.情思涌动,极致婉转——诗歌意境的“冥漠恍惚”
意境,作为中国古典文论的核心范畴,埋养于各派文艺家的意识田地间。从《尚书.尧典》的“诗言志,歌咏言”到王昌龄论述“诗之三境”时所言“三曰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再到王国维赞称“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有意境而已”,数千年间无数文论家集毕生心血诠释何为“意境”。叶燮是明末清初文论大家,集毕生智慧于《原诗》,其文学本原论、正变论、创作论、批评论已成中国古典文论的显学一支,为世人所重视。本文将着力阐释叶燮诗论中“意”与“境”之思,展现其不同于以往诗论家重理论建构而轻实践架构之处。
叶燮在《原诗》里没有论述过多对于意境的见解,但他在对诗歌追源溯本时所强调的踵事增华(即继续前人的事业并使之更加完善美好)和以主体的“才、胆、识、力”衡于客体的“理、事、情”之论都表达了为文以至极并构筑完善意境的看法。叶燮推崇诗文达到“冥漠恍惚之境”,即诗歌韵味细腻婉转、情思涌动、感人所感。而要拥有这种极致之境,作者既需要在诗歌流变中拥有不落俗的“胸襟”来领会日月星辰之美,又需要懂得构筑诗歌“理、事、情”的层次。叶燮提出“诗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1],有了“胸襟”,诗即使寥寥数语,也能仿若俯观宇宙万物,生死至痛尽显,意境也便显现出来。简而言之,叶燮认为一首诗能达到“冥漠恍惚之境”有两个前提,一是诗人在诗歌流变中有所变与不变,二是诗人能拥有托以万物的胸襟来触类起兴。有了这两个前提后,诗人便能以在我的“才、胆、识、力”构筑在物的“理、事、情”。“意境”至叶燮处焕发出独特的“审美”韵味空间,诗之境与世事相关,与情思相关,与行文技巧相关。我们常说没有经历的作家无法完成伟大的作品,叶燮反复强调的也正是这种“经历”。
2.踵事增华,触物起兴——对诗人能力的要求
2.1 变与不变的能力
叶燮在《原诗》中首先肯定诗歌是在不断流变的,只有诸如苏轼之集大成者,“其境界能开辟古今之所未有”[2],天地日月,生死离别均投注笔端。 他强调诗歌一方面有源必有流,有本必达末,另一方面强调因流而溯源,循本以返末。不能不谈诗歌的流变,也不能不谈诗歌的不变。《原诗》开篇便指出诗始于《诗经》,到汉颇具规模。诗有其“道”,每时每日都处于变化之中,历经数代,也确有一代之盛衰。但非前代之诗必盛,后代之诗必衰。因此叶燮对以李梦阳、李攀龙为代表“复古派”持批判态度,认为他们既不谈诗歌流变的循环往复,又不论作者才识的高低,仅生硬地取法盛唐,未免过于牵强。
叶燮“时有变而诗因之”的文学发展观肯定了公安派、竟陵派反复古斗争的功绩,但又指出了他们抛弃古代优良的风雅传统,忽视了文学发展的历史继承性。文学发展是奔腾向前的,也是相继相承的。一方面,叶燮认为“学诗者,不可忽略古人”,从诗百首到盛唐之音都有其可继承性;另一方面,叶燮认为诗歌发展有不变的“体”,所谓“体”就是指儒家思想所推崇的诗教—温柔敦厚。这两点也是叶燮所强调的不变之处。
那么诗人如何才能在变与不变中把握自己的品格,叶燮认为应该做好两点:1.诗歌的审美意味和诗人的独特情趣也不可被抛弃,诗之所以为诗,必有它的文学韵味。2.诗的变化是循序渐进的,诗人的境界也不是一蹴而就的,灵感也许起于智者,但后世之人可以求其精华,不断钻研,达到自己的极致之境。
叶燮的这一观点,在宗白华先生的《美学散步》中也可一探。他说:“适我无非新,是艺术家对世界的感受。光景常新,是一切伟大作品的烙印……李、杜的天才,不忘转益多诗”[3]。文学是极具传承性的艺术形式,作家间往往相互影响,相互批评。没有《诗经》的风雅颂,谈何中国文学;没有柏拉图,谈何尼采;没有《源氏物语》,谈何川端康。因此,一位诗人要拥有不一般的作品,一首诗要拥有不一般的意境,离不开前人的遗赠。
2.2托万物,以起兴
踵事增华,却未有感而发,原因是缺少触发点。叶燮称“原夫作诗者之肇端而有事乎此也,必先有所触以兴起其意,而后措诸辞、属为句、敷之而为章。”[4]当诗人被所闻所见所触发时,必当能感怀到古人的内在情感,这种情感劈空而起,萦绕于心,诗人作诗时采撷一页,化为一片景,一桩事。叶燮并非论述“兴会”的第一人,《宋书·谢灵运传论》便有关于“兴会”的明确表述,但他的兴会论有其独特之处。首先,“起兴”的前提是诗人非凡的胸襟。叶燮称“诗之基,其人之胸襟也。”[5]诗歌的基础,在于诗人的胸襟,只有历经沉浮的广阔胸襟,才能随遇发生,随生即盛。所以叶燮格外推崇杜甫,赞扬他的诗随境迁,思君王、忧祸乱、悲时日、念友朋,概欢愉、忧愁、离合、今昔之感。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艺术家所表现的意境是主观的生命体悟与客观的天然气象的交融互渗。艺术作品是美的,其美来自艺术家心灵之美。一位诗人,能见明月而思乡,一定曾徜徉于皎洁的月光下,也曾徘徊于异乡的小道中;领略过自然之美,也必定体悟过人生之痛。其二,在以非凡的胸襟触物起兴后,诗人所感悟的必是“真”的情感。叶燮并非如竟陵派一般空谈“真心”,他推崇的“真”一方面来自诗人的品尝人生后造就的广阔胸襟,一方面来自感知人间疾苦的善心。“欲其诗之工而可传,则非就诗以求诗者也”,就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