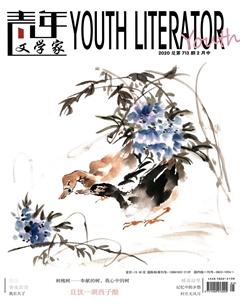浅析“活着”的意味
摘 要:活着是一个哲学问题,引发着人类对其所持有的生命的反思。人更多的对苦难的看法是将之克服,与之斗争。一个人或许一生也不曾认真思考活着的意义。如果人一开始就没有清晰地认识活着到底是什么,活着本身就是怎样的,那么在面对困难时表现出的往往都是抱怨、沮丧、后退。而如果懂得活着本身的样子,人对苦难的态度大概就不是一味地反抗了。余华《活着》中所传递的活着的意味值得深究,研究《活着》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通过研究《活着》来体味活着。
关键词:活着;福贵;苦难;承受;乐观
作者简介:逄会卿(1998.9-),女,汉族,安丘县人,现就读于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2017级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本科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05-0-02
引言: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说余华是一位颠覆大师。《活着》既写出了人活着的原因的共通性,也道出了活着的颠覆性意义。最具有颠覆性的是对活着方式的新变。这就构成了人类对活着这个伟大命题的探讨。活着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活着?人如何活着?余华通过书写主人公福贵的一生带给我们这些问题的答案。
一、“活着”是什么
余华这本书的名字叫《活着》,“活着”是什么呢?
首先,活着意味着生命的存在。活着是中国人的一种最朴素的生存愿望,也是人类最基本的一种生存要求。[1] [P112]活着是和死亡相对应的一种存在方式,用一个同义词解释就是“生”。无论是生还是活着,它所涵盖的意义都是非常宽广的。虽然活着与死亡相对,但是活着不仅意味着自身生命的存在,也意味着会见证别人的生死,因而活着并非和“死亡”毫无关联。小说主人公福贵活着意味着福贵生命的存在,同时,他在活着的过程中见证着身边人的生死,像家珍的死,苦根的生等。
其次,活着是一个受难的过程。“活着”的背后洋溢着一种对生命的感恩,也折射出一种对命运的自然承受。这种承受反映在主人公福贵身上主要表现为对苦难的承受。贫困的生活,炮队一劫,父母、家珍、有庆、凤霞、二喜、龙二、春生、苦根等人的相继离世……都是福贵生命中的苦难,福贵的一生也都在经受着这些断断续续的苦难。
活着意味着在生命中受难。而对于福贵而言,活着更像是一个见证死亡的过程。他的苦难大致都来自 “死亡”,只不过这个死亡是他人的死亡,是他对别人死亡的见证。而见证他人死亡之所以成为他的苦难,是因为这种死亡代表着亲人的离去,意味着這种离去带给它的孤单和冷清。
二、为什么“活着”
“活着”是一个受难的过程,福贵活着经历了数不清的苦难,其中有些苦难真的太难以承受。既然活着如此之艰难,那主人公福贵为什么还要活着?
首先,是个人生存的欲望。人会死,一是自然规律或意外疾病等外在因素所致,二是自身因素所致,即人缺乏生存欲望,主动选择死亡。前者是被动的,后者是主动的。如果没有外在因素的干预,自身也愿意活着,那么人就不会死。家珍、有庆、凤霞、二喜等人活着的时间较短,出于意外,出于疾病,都是不可控的。不是他们不想活,只是他们都被动死亡了。唯一由于自身缺乏生存欲望而死的只有春生一人。春生自己想死,所以活不了。与身边的人相比,福贵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没有因为疾病或者意外去世,没有外力来决定他的生死,其生死基本可以说是掌握在他个人手中的。在没有外力的情况下,想放弃活着,就只能自身主动选择死亡。反之,如果一个人没有被动死亡的情况,却依然活着,那只能说明这个人想要活着。福贵是想要活着的,即便苦难重重。福贵去城里为母亲请郎中的过程中遇上了国民党,当连长用枪顶着福贵的胸膛时,福贵自己叙述说:“我的两条腿拼命哆嗦”。龙二被枪毙后,福贵“摸摸自己的脸,又摸摸自己的胳膊,都好好的,我想自己是该死却没死,我从沙场上捡了一条命回来,到了家龙二又成了我的替死鬼,我家的祖坟埋对了地方。”在死亡面前的恐惧与软弱,逃脱死亡后的庆幸虚惊中可见:福贵也是恐惧死亡、向往生命的。
其次,是感情的支撑。如果福贵的一生,始终只有苦难的存在,没有任何温暖的感情,那福贵还能否活着呢?我们或许无法给这个问题确定一个答案。或许福贵真的可以活下去,抑或不能。但是活着时感受过的温情和美好,必然会成为他活着的一个因素。活着是有温暖的,于是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就会对拥有过的温暖感到不舍。福贵能够活着是有很强大的感情支撑的。福贵的父亲在福贵败光家产后,将家中的一百多亩地和房子都抵押了。当福贵还清债务回到家中时,他只道:“这就好,这就好”,没有太多的怨言,没有厉声的斥责。福贵的母亲,弯下身体求家珍的父亲,只求家珍能留在徐家。而不离不弃的家珍,心灵手巧的凤霞,活泼懂事的有庆,三好女婿二喜……那些来到福贵生命中的给予过他深厚情感体验的人们,都是支撑福贵活着的强大精神力量。厄运、苦难或许永远都驱之不散,可也要为片刻的欢愉和永恒的爱而活着。人世间的温情,或许不会成为一个人活着的决定因素,但至少是一个组成因素,是人在主动选择死亡时,还会愿意活着的一个筹码。
再次,是苦难的可承受性以及对苦难的习惯。苦难是能够克服的,并不是过不去的。生命是不绝望的,因为人只要活着,就什么都可以承受。人可以承受巨大的苦难,因而人就不必非死不可。主人公福贵经历过许多苦难:败光家产、进入炮队、生活贫困,最大的苦难是身边的亲人一个接一个离开他。终其一生,苦难已是家常便饭,他拥有了比别人更多的死去的理由,也就是苦难,可是他依然可以活着。余华自己也认为:“福贵是属于承受了太多苦难之后,与苦难已经不可分离了,所以他不需要有其他的诸如反抗之类的想法。”[1] [P118]一发也可承千斤,福贵就像那一根头发,承受起了千斤的苦难。苦难是可承受的,接连不断的苦难也早已让福贵习惯了面对苦难,因而苦难变得没那么苦、那么难了,因而死亡不是唯一的路子,因而活着也是可以的。
最后,活着不为了任何别的,只是为了活着而活着。余华说:“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活着只是为了生命本身而活,即使过程和结果都不如人意,即使拼尽全力也没把生活过好,即使耗尽毕生精力也未能与世间抗衡,即使如此,我们依然要活着。因为,活着本身或许真的与活得好不好、值不值等任何评价标准无关,活着只与活着本身有关,为了活着而活着。
福贵活着的理由,又何尝不是我们活着的原因。
三、怎么“活着”
既然选择了活着,那更重要的是要懂得怎么活着。面对广阔的人生,随时可能发生变化的人生,苦难与欢笑并存的生活,我们选择了存在,我们到底该如何存在?对于这个问题,福贵和余华都有他的答案。余华成功为福贵找到了一条缓解苦难的有效途径——忍耐,这使得整部小说的叙述都因着这种宽阔的忍耐,变得沉郁、悲痛而坚定,没有血泪的控诉,没有撕心裂肺的尖叫,甚至都没有愤怒,有的只是福贵在生活中磨练出来的无边无际的忍耐包容着一切,以致更大的苦难来临,福贵也能将它消解于自己的忍耐之中。[2] [P35]福贵自始至终都没有给“我”明确的答案。但从福贵晚年真诚的叙述中,读者可以领悟。福贵用他一生的经历告诉我们:乐观且温情地受难,平静而宽容地活着。生命是不绝望的,保持乐观,永存温情。在这里,生命更像是自己的朋友,活着则是与生命友好地相处。本书所传递的“活着”的方式不是呐喊着去“扼住命运的咽喉”,和命运拼个你死我活。不是来势汹汹的一场搏斗,不是进攻、喊叫。而是“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是不畏惧、不抗拒、不谢幕、不庆祝、不欢呼,以最平静的态度和自己的命运相处。
余华说:小说的主人公福贵有着对苦难异于常人的承受能力和乐观态度,他的一生经历了自己的大起大落,经历了身边的人失而复得和最终一个个离他而去,当最终他世界上的亲人一个不剩的时候,他也变成了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他的生活再也不会有亲人逝去的苦难了。他买了一头牛陪伴他,把它当成自己死去的亲人们,他的一生正如他唱到的那样——“少年去游荡,中年想掘藏,老年做和尚”。能够在经受了一生的苦难之后还能将之带以温情地全部叙述,如果这都不算乐观、难得,那么怎么才算呢?
需要指出的是,第一,这种乐观绝不是无知觉的或者麻木的。福贵对于苦难的降临不是没有反应的,不是毫无感觉的,只是他受住了所有的难,并将之视作活着的方式。第二,乐观也并不是福贵专属的。乐观还属于家珍,属于凤霞,属于苦根,属于书中的所有人。乐观更是贯彻于整本书中的。第三,乐观的来源是多样化的。年轻时候的福贵嫖赌放纵,那时他面对生活也是一种乐观态度,但是这种乐观来自他对生活的不在意,来自生活的安稳富足。福贵父亲去世后,他扛起了养家的责任,努力生活。这个时期他的乐观来自对情感的发现,他变得珍惜夫妻之情和长幼之情。福贵被拉近炮队,那段日子里他的乐观是被迫的,是出于对生命的渴望而又心有余、力不足,即为了活下去的一丝希望而不得不乐观起来。
故事的最后,炊烟升起,霞光四射。女人吆喝孩子,男人挑着粪桶。田野宁静,霞光退去,土地袒露。这样的风景便是生活的全貌:炊烟袅袅,宁静安详。万物平静地变化,人生也是如此。如福贵的一生,多变又无声;似福贵的心态,平静且安详。土地是宽广的,其胸膛也是宽广的,它所召唤的恐怕不单单是渐行渐远的福贵与老牛,更是人对生命的豁达与包容。
结语:
活着代表生命,代表受难。活着需要理由,抑或不需要理由,只是为活着而活着。《活着》给予人类一种新的对生命的看法,乐观忍受,平静受難,年轻时坦然接受,年老后真诚回忆。它折射出对生命的感恩,与命运共进退、同生死的价值观,这是余华写出的“活着”的方式。还有更多活着的方式和意义等待着被探讨,而在多种方式中,我们选择的是哪一种,取决于我们的生命观和哪一种相契合。不难看出,福贵活着的原因中也有我们活着的原因,福贵活着的方式在现实中多多少少也是存在着的,而从小说中概括出的活着的定义,不仅仅出自对福贵一生的总结,更是对整个人类存活的普遍概括。因而“活着”的意味不是单单出自对福贵这个人物的提炼,更是对社会人生中 “活着”这个命题的观察与反思。活着本身是一个十分宽泛的命题,对于它的研究,应是无休止的。
参考文献:
[1]洪治纲.余华评传[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
[2]吴义勤.余华研究资料[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