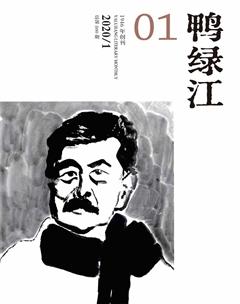被压抑的“小我”情感
一枚戒指,伴随着男女双方在婚礼上的海誓山盟牢牢地环扣在对方的无名指上,它既是以爱相守的浪漫契约,也是天长地久的美好期许。然而我们将一枚金戒指还原至解放战争时期的价值生成背景中,便会发现这枚戒指远远超脱于男女之间定情信物的意义,当其被放置革命战争语境的小说之中,有时也可能成为革命化的一种修辞。
《金戒指》是周立波创作于1947年5月的一篇短篇小说,当时正值国共双方战争胶着时期,而小说中的时间背景定位在1944年前后抗战时期。《金戒指》的创作显然是符合这种战争氛围的。它撷取了浩瀚的革命战争中一个普通侦察兵的日常片段,在一场由金戒指引起的风波中,人物通过内在的革命意识的进化获得了精神上的成长。小说中,主人公张海是一个带有英雄主义色彩的革命青年战士。他机智灵敏、有勇有谋,深受司令员和战士们的一致好评。他的妻子张叔贤是村上的纺纱小组长,也是一个劳动女英雄的形象。关于二人的结合,小说中这样写道:“驻扎绥德时,有三个姑娘同时看上他(张海),他却以侦察员惯有的锐利的眼光和迅速的行动,爱上了她们之中适合于自己的一个,和她结婚了。” ①在解放区文学时期,这种革命对爱情、婚姻的介入已不同于20年代末“革命加恋爱”的文学现象,相比于后者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浪漫蒂克”情调,前者则是在宏大的革命意识主导下,以崇高的革命理想与革命情怀作为精神旨归的一种叙事形态。
然而夹杂在革命过程中的这一段婚恋,之所以用《金戒指》来命名,是因为在小说中,这枚戒指既是婚姻的信物,也是革命的修辞,甚至是革命高于婚姻的隐喻。张海对于这枚戒指的几次“取”与“舍”,构成了故事的叙事链条——当新婚之夜,妻子将戒指戴在他的手上,他此后一刻未曾摘下,这是对两人爱情与婚姻的执守;当女老板深夜持刀闯入张海住处,企图偷走戒指时,对于戒指的保护既有对于妻子和婚姻的守护,也有作为一名侦察兵的天生敏感与革命正义;当他发现带有侦察记录与地形图的笔记本落在旅店,立刻折返,女老板提出用金戒指交换笔记本,他用侦察员惯有的果决将戒指摘下,同意了女老板的交换条件,此时革命事业与革命情怀已经战胜了个人的“小我”情感;当他从女老板手里取回笔记本,并“解决”了女老板,继续赶路时,又再次折返要取回戒指,枪声暴露了他的行踪,在与敌人对战后,只剩一颗子弹时,经过复杂的心理活动之后,张海选择将枪口对准自己:“他低下头,看见了平常戴着金戒指的左手无名指上的白色的环痕,想起他的妻,心里有一阵酸楚。他又想起了司令政委对他的器重和青睐……他想,要做毛主席的好学生,活要活的光荣,死要死的漂亮,人生百岁也是死,何处黄土不埋人呢?想到这里,他不再有酸楚,只觉得兴奋,他举起枪来,对准自己的右边的太阳穴,他扣动了枪机。”在这个短暂的心理斗争过程中,为革命事业自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几乎在转瞬间就取代了丢失戒指的失落,张海决定宁可自己结束生命,也不愿受敌人“屈辱”的枪子,这体现着在他身上高度凝练着的、作为一名革命战士的思想自觉。这位年轻的战士也并没有在这次风波中牺牲。而关于这枚金戒指最耐人寻味的情节,大概是在经历了这一次死里逃生之后,张海意识到“他的妻送给他的金戒指,几乎使他贻误了公事”,于是将妻子赠予的爱情信物上交给了党组织,作了党费。在这里,金戒指完成了由个人私有到集体所有的价值升华,实现了生活日常对革命大业的自觉融入与皈依,由此获得了超越其本身的、更深广的革命意义。
在解放区时期的“革命伦理”中,有利于推动革命进步的一切思维模式、行为方式被高悬于至高无上的地位。革命性成为压倒一切的强势力量。而婚恋书写作为私人化情感的一种文本呈现,在倡导无“私”、忘“我”的时代语境中是不合时宜的。即便如《金戒指》一般,在革命书写中夹杂个人情感的渗入,其中婚恋书写的真正目的与功能,也是在于突出革命事业的崇高与历史前进的必然。革命价值体系中的个人情感言说要通过自觉实践与革命进程形成同构的关系。革命的“暴风骤雨”将个人情感书写的边界框定在革命历史的逻辑体系之内,“小我”的情情爱爱裹挟着时代的热烈与革命的激情,融入浩大的革命洪流,变成了豪迈、激昂的革命图景中的点缀。
我们无法否认公式化、概念化的婚恋书写在革命战争时期话语实践中的现实斗争意义。它将家庭内部结构的和谐、稳定与外部新政权的催生、引导相勾连。一方面,革命成为男女双方互生情愫的大环境,无产阶级新政权为青年男女提供了广阔的恋爱机会与场所,在革命事业中催生的爱情与革命本身构成了不可分割的亲密关系;另一方面,男女双方因共同的革命理想与组织、集体力量的加持,而在革命事业中加深对彼此以及新政权的情感认同,构成推动革命历史向前的反作用力。与此同时,解放区小说中的婚恋模式与“十七年”时期小说中革命对于爱情价值观的“改造”之间有着一定的内在延续关系,在此意义上,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应和不仅在当时促进了革命事业广泛而深入的发展,更是为新中国成立之后文学发展的方向提供了某种范式,或者说一种发展路向。
解放区文学作为中国共产党为创立现代化国家所设的一方文艺田地,其中的文艺思想与样态天然地带有现实功利主义色彩。在五四時期倡导思想解放、婚恋自由的时代大潮下,延至40年代,无论从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还是康濯的《我的两家房东》等等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一代新人在婚恋方面具有了自主选择权。然而悖反的是,一代“新人”挣脱了“父母之言、媒妁之约”的枷锁后,仿佛不自知地将个人婚恋问题又与革命进程相捆绑,个人的情感属性被夹套进入火热的政治话语体系内。在此过程中个人意义上的选择与“解放”其实还是有限度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有限度的自由以及婚恋选择的另一种“依附”已经走向了五四时期思想启蒙的对立面。特殊的时代诉求下,在解放区文学作品中,我们甚少看到一个既有强势又有弱点、完整意义上的“人”,“小我”内心丰富的情感与丰满的人性被革命战争滚滚向前的车轮轧平、拍扁,此间强大的革命话语挤压了个人情感的空间。在社会整体的解放高蹈于个人的思想解放之时,革命话语缝隙中的私人情感以一种屈居于革命情怀之下的姿态被压制在历史的“褶皱”之中。
然而无论是五四时期个体的相对自由,还是解放区时期趋于革命的情感倾向,都是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这种历史的选择便在“话语讲述的年代”与“讲述话语的年代”的重合中形成封闭的阐释空间,由此便带来了时代规约中的意义与局限。
从一篇《金戒指》,我们可以透视时代整体性的价值取向与社会氛围。固然,这也代表了创作主体的价值立场与文学追求。作家周立波以终身坚守左翼、顺应历史主流的姿态塑造了一个斗志顽强、忠贞不渝的革命战士“跳皮鬼”形象,但《金戒指》这个故事正如作家本人的创作一样,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使命所赋予的局限。亲历战场的革命战士叠加在文艺创作者之上的双重身份为周立波提供了观察革命、表现战争的独特视角。在作家的文化潜意识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了无产阶级政权领导下不可动摇的话语秩序。“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方向的指引在周立波的作品中得到了诠释。从“亭子间”到“左联”,再至解放区,再至“十七年”时期乃至“文革”时期,直至生命结束,结合周立波“跨时代”的人生经验与精神历程,我们不能忽视作家试图在“农村题材小说”中坚守“乡土”启蒙的努力,也正因如此,周立波在启蒙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文艺战士”双重立场的纠葛中凸显了自身独特的文学史意义。我们更无须置疑作家这种内在的、虔诚的创作心理与价值立场,当我们用历史性的眼光重新审视此文乃至解放区时期“小我”情感被遮蔽的革命化范式,其时代意义确有之;但当我们过滤掉时代动因下主流意识形态的濡染,从文学揭示人性的复杂与人类的永恒性角度来看,这种“削足适履”式的书写,局限亦有之。
【责任编辑】 铁菁妤
作者简介:
薛冰,辽宁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19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