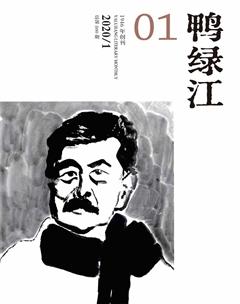万事可行
1
宋娇影怎么也没想到,会在民政局里遇到那对中年夫妇。男人咋咋呼呼地打着电话,嗓门儿很高。女人浑身疲软,目光茫然空洞,似乎看着身旁的男人,却又好像穿过男人,落在虚无的半空。
办完手续,中年男人将绿色的离婚证书举在眼前看了看,塞进手包。女人面无表情,机械地点头或者摇头,机械地接过绿色小本。宋娇影的心情就是从那一刻开始糟糕起来。她想,离婚证是绿色的可真有意思。股市里红色是涨,绿色是跌。婚姻和股市一样,都是赌,运气好,一红到底。运气差,半道儿跌了,幸福也跟着七零八落。待她和杨卫东领了红色结婚证,走出民政局的大门,远远地看到那对中年人在无声地撕扯。
谁也没看清女人是从哪里变出一把刀来,也没人能说清楚女人是如何把刀刺向男人的。也许是预谋,或者只是碰巧,从男人的下体插了进去。女人刺了一刀便松开手,面色苍白,嘴角抽搐。刀在男人的体内插着,粉色的刀柄垂在两腿之间。男人挓挲着手,石化了般一动不动,既不去拔刀,也没有报警,只是一声比一声悲怆地号叫着。
那时刚过了十点钟,太阳斜挂在天空上。
2
作为目击证人,宋娇影和杨卫东双双被请进派出所,和几个看热闹的人一起接受警察的询问,又在笔录上按了红手印。这是宋娇影第一次按手印。若干年前,在她就学的城市博物馆看展览,看到一张典妻的卖身契:泛黄的纸张上,行文从右至左,工整的小楷,冷静地落笔提笔,由上而下,笔锋处处透着看惯了世事的超然,行文最后一个鲜红手印,胎记一般长在她的记忆里。她并没有刻意记着这件事,却在今天按下手印的瞬间,想了起来。她抬起食指,按在印泥上,又照着警察的指点在自己的名字上按下手印。她的名字挨着他的,两个红色的手印也自然地挨在一起。
实际上他们已经同居了半年多。宋娇影骨子里还是有些传统,觉得如果没有那一纸婚书,就算是一起住了一辈子,也算不得是夫妻。
“頂多算是姘居。”宋娇影说。
“我们还算不上姘居。”杨卫东把她搂在怀里。刚亲热过,心里亲近得没什么界线,话说得软,逗趣儿似的。
“那还是把证领了吧。”宋娇影赤裸的后背靠在杨卫东怀里,头抵着他的下巴,一只手握着他揽在自己腰上的手,一下一下轻拍着小腹。
“我们农村不兴领证,谁家娶媳妇儿,亲戚里道地都请来,摆几桌酒席,就算是结婚了。”
“不领证儿?”
“不领。酒席多实惠,相当于昭告天下。”
那天之后,宋娇影就开始张罗着领证的事儿。现在人人都讲究个仪式感,她也要把婚姻的仪式一个细节不落地履行全了,酒席要摆,证也要领,既要昭告天下,又要立此为据。
领结婚证的日子,像是婚礼的一次预演,因此也是千挑万选。宋娇影捧着日历头儿翻了四五天,哪天宜嫁娶,哪天忌纳采,初一十五肯定不行,还得和星座的运势合上。
“这么一弄,好像也没什么日子可选了。”杨卫东说。
“不用你管。”宋娇影现学现用查了好一通星盘,却还是没整明白,正烦躁着。
“要我说,随便挑个日子,去把证领了就行。”杨卫东大大咧咧地说。心里却想着另一回事:男人的脑回路和女人的果然不一样。男人在意的是和谁结婚。女人在意的却是些没用的细枝末节。
“我认认真真地活着,为什么要随便选个日子?”宋娇影的心绪起伏不定,仿佛提前进入了更年期,一时间是有了着落的释然,一时间又疑疑惑惑。
“只是领个证——”杨卫东想说“只是领个证而已”,看到宋娇影的脸色不对,及时把“而已”两个字吞到了肚子里。
终于千挑万选出了一个日子,皇历上写着“万事可行”。虽然最终宋娇影还是没有弄明白星盘是怎么回事,但是也没法儿去在意了。如果一定要选个中西皆吉的日子,大概今年是选不出了,只能紧着中国的规矩来——万事可行——那就这天吧。
宋娇影万万没想到,领结婚证的地方,也是办理离婚手续的地方。她在吃惊之余,不由得心里咯噔了一下,这是个暗示吗?在这个“万事可行”的日子里,生活在向她暗示什么?
3
从派出所出来,宋娇影闷着头往前走,很长一段时间不说话。
“去哪儿?”杨卫东追上来。
“饿了。”宋娇影瞅他一眼,口气生硬别扭,像是跟谁呕气似的。杨卫东心里也不舒服,想说句话调侃一下,搜肠刮肚半天,觉得说什么都没心情。
“那就去吃饭吧,我也饿了……想吃什么?”杨卫东说。
宋娇影甩了甩身子,说:“山葵。”
“山葵”是鸭绿江边的日本料理,最有名的炙烤三文鱼寿司,热火燎过的痕迹,含在嘴里嫩嫩的,像是初恋时的吻。杨卫东不是宋娇影的初恋,宋娇影也不是杨卫东的初恋。经过朋友的朋友介绍认识后,不温不火地处了小半年。骤然升温是在年底。宋娇影说同事介绍了一个日本料理馆子,很好吃。杨卫东不喜欢日本料理排排场场却并不实惠的样子,却也没拂她的意,说:“好,我请你吃山葵。”
“炙烤三文鱼是它家的招牌。”宋娇影说。
“你喜欢吃就再来一份。”杨卫东没吃出什么特别来。
宋娇影吃了三份炙烤三文鱼。还要点第四份,杨卫东拦着她说:“你不是说这个味道像初恋时的吻吗,吻多了光剩口水味儿了。”
“你舍不得钱呀?”宋娇影说。
“怕你吃伤着。我小时候吃猪油拌饭就吃伤着了。”杨卫东说。
“借口。”宋娇影撇撇嘴。
“真的。吃伤着就再也不想吃了。留个缝儿,下次再来。”杨卫东说。
走出山葵,在夜色里逆着鸭绿江往上游走。正在涨潮,江里的冰排跟着潮水往上涌。天上是半拉月亮,将满未满的上悬月。宋娇影的身子随着江水的节奏,一下一下撞着杨卫东。后来,就在杨卫东的单人床上把两个人撞成了一个人。
出租车司机按着宋娇影的指点开到“山葵”,看到的却是一家韩国馆子。以为是走错了地方,杨卫东让出租车司机继续往前开,一直开到五道河桥也没寻见“山葵”的踪迹。江边的路是单行线,只好调转车头驶入反方向的车道再绕回来。这样绕着圈子走了两三趟,确定“山葵”是不见了——要么搬迁,要么倒闭。总之,在原址上是寻不出它来了。
宋娇影眼神迷惘起来了:“怎么会?”
接下来,宋娇影便开始执着起来。她点开手机里的地图,输入“山葵”两个字,循着导航让出租车司机往坝岗街开,由近及远,一处又一处地找山葵。第一家山葵饭店是东北家常菜馆,第二家山葵是隐藏在胡同里的小吃部,第三家在遥远的城东头,“山葵”的牌子斑驳而孤独,周围的墙上写着一个又一个“拆”字,圈在红漆画的不规则的圆里。
从派出所出来时,路过一家花店,杨卫东不顾宋娇影的反对,进去买了束红玫瑰。十九朵,挤挤挨挨地围成一个小圆圈,周边点缀着几枝白色的勿忘我。花上喷了香水,艳俗的香气张扬着四处乱窜。
山葵日料遍寻不见,在寻找的途中又把红玫瑰落在了车上。等到杨卫东感觉到手上少了些什么的时候,出租车已经绝尘而去。
4
五月天气,已经有些热了,下午一两点钟太阳正毒,外套和长袖的衣裳就有些穿不住。特意穿的白衬衫,清爽干净的白到此时已经有些发蔫,透着疲惫和乏力,乍一看,像是业务不景气的保险公司推销员,又像是偷偷跑出来约会的银行柜员。
请了半天假,现在已经过去大半天,午饭还没吃上。谁也不想说话了,也不知道说什么。
手机里的地图再导不出新的“山葵”,他们俩从一个又一个“拆”字里穿行出来,半天寻不到一辆出租车。宋娇影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身子一倾,倾到杨卫东的肩上。他扶住她的身子,顺势握住她的手。她挣脱了一下,他握得更紧。她回过头来看他,从他的脸上看到了陌生的东西,仿佛眼前这个人不是杨卫东,不是法律意义上可以称其为丈夫的人。好像她认识并同居了半年多如今领了一纸婚书即将耳鬓厮磨一辈子的男人是另外一个人。眼前这个人是钝的。不是生了锈的惰怠,而是有所克制的细水长流。他不抗拒,也不妥协。人人都在抗拒自己的生活,对一切不满意,总是不甘心已经拥有的,以为还可以更好。还应该更好。而他似乎总是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
她的目光爬过他的眼睛、他的额头、他浓密而短促的黑发,望向天空。天空是明亮赤诚的蓝,没有一丝云彩。道路两旁的高楼仿佛形象各异的水泥柱子顶向天空,让人生出许多的错觉,仿佛头顶上那一片蓝是楼尖支撑起的布料子。
杨卫东的思绪飘在远方。比天空还远的远方。他的眼睛也跟着缥缈起来,似乎浮着一层迷惘的雾,犹疑的,不确定的,还有——抗拒什么似的狠劲儿。待他把思绪收回来时,目光像上了锁似的扣在宋娇影的脸上。他说不上是不是爱她,再说,爱不爱的又能怎么样?有时候想想,爱情就像个笑话。在爱情里的人,全都没有智商。说一些傻话,做一些傻事。爱情是未成年人的游戏,婚姻是成年人的结盟,是两个人的统一战线,共同抵抗生活的磨损和残酷。所以他选择了宋娇影。她身上的烟火气和不经意间散发着的俗气,让他的心里很踏实。
5
“吃点儿东西吧。”杨卫东攥了攥宋娇影的手。
路边一家正在试营业的西餐厅,门前摆了两排竹子编的花篮,花篮里是红的粉的康乃馨,还有黄的橙的扶郎花。杨卫东牵着宋娇影的手,踩着铺在两排花篮间的劣质红地毯,进了迎门处供奉着财神关老爷的玛格丽特西餐厅。早已过了午饭时间,餐厅内食客不多,三五个人零星分布在不同的角落,像是着意落下的棋子,布成一个互不干扰却又浑然一体的格局。
“两位请点餐,今天有赠品。”样貌俊秀的服务生穿着崭新的店服,把精美的菜单递向杨卫东。
“赠送什么?”宋娇影伸手接了菜单,捧在胸前,问道。
“点一份牛排,送一份意粉。菜单上三种意粉任选其一。”
“随便点哪份牛排都行?”
“是。”
宋娇影点了一份西冷牛排,赠送的意粉选了肉酱意粉。服务生送来两杯温热的白开水,宋娇影的心绪被白开水中漂浮着的淡淡的柠檬香气抚慰。她在心里轻轻叹息一声。
“你能一辈子对我好吗?”宋娇影手捧着杯子,低着头,问了一句自己都觉得傻的话。
“我努力。”杨卫东说。
“努力——什么意思?”宋娇影抬头,盯着他的眼睛。这不是她想要的答案。她想要个承诺式的、带有仪式感的话。可是,她心里也清楚,他是个不大会说浪漫话的人,虽然说的话都是实情,却也难免让人有些不快。
“我们证儿都领了。”杨卫东说。
“证领了也不能说明什么。”宋娇影又想起了在民政局里遇见的那对中年夫妻,“结婚证是红的,离婚证居然是绿的,绿的——”
“是呀,绿的。”杨卫东感叹。
宋娇影的心情在起起伏伏间归于平静。是呀,结婚证已经领了,契约在手,接下来,是两个人如何履行契约——一念至此,她的心纠结着疼了一下。那个绿色的本本儿不也是个契约吗?
“我这辈子从此交给你了。你不能对我不好。”宋娇影有些矫情却又不失真情的流露。
“我也一样。咱们俩是互托终身。”杨卫东说。
服务生送来了肉酱意粉。意粉煮过了头,粘在一起,和肉酱一拌,像是搅作一团的炸酱面。西冷牛排半生不熟,离“八分熟”还差了三四分。宋娇影在心里默念着“左叉右刀”,尽可能优雅地切下一小块牛排,举在眼前盯着看了半天,却怎么也狠不下心来把渗着血丝的红色肉块儿送进嘴里。
后台换了曲子,餐厅里飘荡起“男孩地带”的歌曲《无论如何》。来自爱尔兰的五人男子组合,略带乡村音乐的演唱风格,像是久别重逢的老友,在耳边轻轻地诉说着别后的一切。思念。彷徨。坚持。迷惘。“No matter what the end is/My life began with you”(无论结局如何,我的生命从你开始),这句誓言般的歌词经过沙哑忧伤的嗓音演绎,竟有了天荒地老的味道。
6
玛格丽特西餐廳现在只剩下杨卫东和宋娇影,像是要终老一生似的面对面坐在餐厅近窗的位置。牛排和意面早已吃完,配送的水果沙拉也吃得见底,宋娇影执意留下一玫红色的灯笼果在盘底。免费的柠檬水喝了两瓶,宋娇影又点了一杯“玛格丽特咖啡”,两人一人一口慢慢啜饮。
“走么?”杨卫东把咖啡推向宋娇影。咖啡快要见底了,但上面漂浮着的心形奶油基本保持着完好的形状。
“嗯。”宋娇影捧着咖啡杯,点了点头,却没动。半晌,道:“结婚证呢?”
“在我这儿。”
“给我看看。”
一式两份鲜红的证书并排摆在桌子上。宋娇影拿起左面的那本,打开来。里面是两个人的彩色结婚照,红色背景,纯白衬衫,肩膀挨着肩膀,“感觉会到天老地荒似的”——这是宋娇影说的。她并不是浪漫的人,他们也早已经过了说甜言蜜语的年龄。言来语往间都是去了粉饰的实在话。因此,当她脱口而出这句话时,自己的内心是感动的。
放下左面的结婚证,宋娇影又拿起右面的结婚证端详。然后,皱了眉头,把两本结婚证摊在眼前,再然后就是一声惊叫。
“错了!”宋娇影喊道,人也跟着站了起来。
服务生惊慌地奔过来,手里擎着点餐器,看一眼餐桌再看一眼点餐器。
“小姐,没错。”服务生说。
宋娇影看也不看他一眼,抓起两本结婚证,翻开封皮,翻到贴着两人合影的那页。为了让杨卫东看得清楚,恨不能塞到他的眼睛里去似的直勾勾地递过去。
“你看——!”宋娇影说。
“看什么?”杨卫东接过结婚证,瞄了一眼,没看出什么不妥。
“仔细看!”宋娇影指着两本结婚证下面执证人一栏,道:“看名字!”
杨卫东盯着名字看了一个来回,终于看出特别来,执证人不是“宋娇影”,而是“宋骄影”,娇嫩的“娇”错成了骄傲的“骄”。
“今天到底是个什么日子?”宋娇影气恼得眼睛里含了泪,“工作人员太不负责了。”
“不用他们负责,我们自己负责就好。”杨卫东抱着她的肩,下巴抵着她的头,劝慰道。
就这样,杨卫东和宋娇影揣起写错了名字的结婚证走出玛格丽特西餐厅。七拐八拐拐到了鸭绿江边,一回身,兀地瞥见山葵日本料理的牌匾挂在道路对面崭新的建筑上。江水正在退潮,一波一波的浪向江心处退去,没在江水里的亲水台阶露了出来,黑色的滩涂露了出来,西斜的太阳投影在江水里,跟着水波一晃一晃。宋娇影盯着碧蓝的江水,想起若干年前,有一个人曾经对她说,江心里藏着许多木排,上游发大水的时候,会把那些沉在江心里的木排顶上来。
“除了木排还有什么?”她问。
被问的人想了想,说:“谁知道呢。”
【责任编辑】 陈昌平
作者简介:
贾颖,1971年正月出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居辽宁丹东。著有長篇儿童文学《阿满》,儿童文学作品集《我的同桌叫太阳》。作品曾获冰心儿童文学奖,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