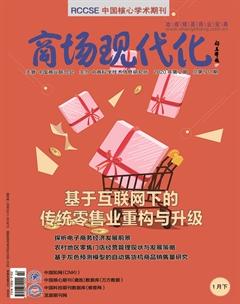电子商务平台上“刷单炒信”行为的刑法规制
杨梦凡
摘 要: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带动了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提高了人民的生活质量。但在电商平台上所形成的“刷单炒信”行为滥用,破坏了电子商务蓬勃发展的动力——信用评价机制,侵害了多种法益,为电子商务的长期发展带来了挑战。因此,实践中有必要对该行为适用统一、合理、有效的刑法规制手段。目前,实践和理论层面提出的方案较多,从文义解释和司法解释的层面出发,非法经营罪不宜适用;从体系解释和类推解释的角度出发,虚假广告罪不宜适用;唯有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可以适用,不仅是因为“刷单炒信”行为符合该罪的构成要件,而且该罪的适用还可以对行为的发生起到预防之效用。
关键词:刷单炒信;非法经营罪;虚假广告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刑法解释
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商务部2018年出具的《中国电子商务报告2018-2019》,2018年中国电子商务交易规模高达31.63万亿元,其中网上零售额超过9万亿元,同比增长23.9%;电子商务相关就业人员达4700万人;中国继续保持世界最大网络零售市场地位。该报告同时指出,电子商务在壮大数字经济,共建“一带一路”、助力乡村振兴,带动创新创业等方面均发挥了积极作用。可见,电子商务发展势头迅猛,继续承担着国民经济发展的强大源动力,并且牵涉大量就业人口,正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①而信用评价机制是维持电子商务健康蓬勃发展的基本动力,如果这一评价机制丧失效能,整个电子商务的环境将会迅速恶化。
“刷单炒信”行为正是依托信用评价机制在电商交易中的显著地位,在电子商务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其行为模式具体为,个人、法人或其他非法人组织通过频繁虚假交易,滥用电商平台中的信用评价机制,获取不正当利益。该行为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本质上是一种不正当竞争的行为。目前,“刷单炒信”行为包含正向刷单炒信②和反向刷单炒信③两种行为模式的分类得到普遍认可。但由于反向刷单炒信行为在实践中出现的较少,且部分理论与正向刷单炒信重合,因此不对其做重点讨论;④其次,“刷单炒信”行为逐渐表现出专门化的特点,由发单者(电商平台商家)、刷单平台、刷单者三方各司其职,共同完成。但实践中,由于发单者和刷单者数量较多、违法金额较少的特点,往往无法达到刑法规制中“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另基于“法不责众”的刑事政策考量⑤,通常不对该二者对其进行刑法上的规制。⑥
由于“刷单炒信”行为对电商交易的消极影响巨大,阻碍了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行和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且理论上有关于“刷单炒信”行为的刑法规制观点较多,实践中也未能形成統一的规制模式,因此,笔者将从该行为所侵害的法益出发,探讨该行为应当如何为刑法所规制,以期在实务中对该行为的规制日渐统一,从而有效遏制该行为的发生。
二、行为所侵害的法益
其一,“刷单炒信”行为的手段直接侵犯了电商平台的信用评价机制,影响了平台的正常经营活动,侵害了电商平台的合法权益;其二,“刷单炒信”行为的结果侵害了消费者对商家信誉、商品销售情况、商品评价的知情权,会使消费者在电商平台选择商品时获取虚假的信用信息,从而可能做出错误的决定,造成损失;其三,行为的结果同时破坏了电商平台上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本质上是一种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侵害了相对市场中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三、刑法规制路径
1.新设新罪名的否定
我国刑法目前并没有特别针对这类违法行为设置独立的构成要件。⑦有学者建议,鉴于“刷单炒信”行为侵害多方主体合法利益,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最优方案应为直接在刑法中增设“破坏网络市场信用评价罪”。⑧还有学者主张在未来的刑法修正案中增设诸如“妨害信用罪”或“背信罪”等条款⑨。但笔者认为,不宜新设特别罪名。
首先,虽然“刷单炒信”行为具有法益侵害性,但该行为大多系被动引发,即需要发单者作出“刷单”邀请后才可启动,不具有危害的自主性,新设罪名予以规制有失公允;其次,目前刑法体系下的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完全可以涵盖该行为,且即便在没有实害结果出现的情况下也可以对其进行刑法规制,较好地起到了预防的作用。综上,并无独立设置特别罪名的必要和条件。
2.非法经营罪的否定
随着“刷单入刑第一案”⑩的宣判,对于刷单炒信行为,实践中大多效仿“第一案”,以非法经营罪对刷单平台论处。通过分析各法院的判决理由,法院对于非法经营罪的认定或基于刑法第225条的规定,或基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的规定。笔者认为,无论基于刑法条文的规定,还是司法解释的规定,都不宜将刷单炒信行为认定为非法经营罪。
第一,对于非法经营罪条文中“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的规定,根据同类解释的原则,其应当与本条所明确列举的三种非法经营行为具有相当性,即该罪的法益侵害不能泛化为对市场秩序的扰乱,而是应当限缩理解为对国家经营许可制度的破坏。而对于“刷单炒信”的行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和《电子商务法》第17条中均规定其为“虚构网络交易”的行为,并不涉及“经营许可制度”。因此,从兜底条款的解释出发,将“刷单炒信”行为认定为非法经营行为是不合理的。
第二,《解释》第7条设置的初衷实际上是希望通过非法经营罪来规制网络上非常猖獗的“删帖”和“发帖”服务,即俗称的网络“水军”。其规制的依据在于,该类行为破坏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第4条所确立的“国家对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的许可制度”。但正如上述,“刷单炒信”行为与经营许可制度并不相关,且刷单平台组织刷单的行为,属于制造虚假信息,与该解释中“明知是虚假信息而予以发布”的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并不相同。因此,该解释对于“刷单炒信”行为的规制上不存在适用空间。
3.虚假广告罪的否定
考虑到“刷单炒信”行为所具有的严重的法益侵害性,有学者提出“刷单炒信”行为属于利用广告对商品或服务作虚假宣传的行为的观点,以期通过虚假广告罪对该行为进行规制。但笔者认为,这一规制手段违背了体系解释和扩大解释的解释理论,不宜适用。
其一,持该主张的学者大多依据2017年11月4日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印证上述判断。立法机关明确指出,这一关于虚假宣传的立法修订就是为了打击刷单炒信的行为。但同时,该法第20条亦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法第八条规定,属于发布虚假广告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的规定处罚。可见,立法者对于虚假交易行为和虚假广告行为仍持区分的态度,虽然二者在外观上均表现为虚假宣传,但其行为的模式并不相同。《刑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上处于同一位阶,如若以虚假广告罪对刷单炒信行为进行刑法规制,将导致两法对同一行为的性质认定不一致,违背了体系解释的内容,造成法律适用的混乱。
其二,将“虚假宣传行为”解释为“广告行为”时采用了类推解释的方法,而非扩大解释。两种解释方法的重要区别在于解释结果是否在语义可能的范围内。显然,“刷单炒信”并非在广告的语义范围之内,而之所以将其认定为广告是因为二者都对消费者产生了宣传的后果。因此,仅仅从行为后果相同而将其做同一性质的解释并不合理,属于类推解释的适用。
4.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适用
《刑法》第287条之一的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是《刑法修正案(九)》新增加的罪名,其规定了三种行为模式。“刷单炒信”行为符合第一种行为模式,即=设立用于实施诈骗、传授犯罪方法、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管制物品等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通讯群组,可以适用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对其予以规制。
其一,“刷单炒信”行为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所明令禁止的违法行为,属于本条规定的违法犯罪活动;其次,刷单平台对“刷单炒信”工作的宣传、组织和分工大多依赖于网站或通讯群组的设立,因此,“刷單炒信”行为符合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构成要件。
其二,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立法初衷在于对网络犯罪的预备行为进行提前规制。网络犯罪通常借助网络跨地域进行,由不特定人在短时间内共同实施,受害人往往分布各地,难于一一查办,所以立法者防范于未然地将网络犯罪的预备行为加以提早处罚。也就是说,如果适用该罪,以“刷单炒信”为目的而建立网站或通讯群组的行为,即便没有实害结果的出现,一旦达到了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也可以对其予以刑法规制,从而起到预防的效用。
四、结语
“刷单炒信”行为破坏了电子商务平台上的信用评价机制,影响了电子商务的长期发展,在行为达到“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后对其予以准确、合理的刑法规制是正当且必要的。但与此同时,亦不能忽视对行为的民法和经济法规制,于此,才能确实、完整地保障消费者、电商平台和其他经营者的合法利益,还电商平台一个合法有序的经营环境。
注释:
①王华伟:《刷单炒信的刑法适用与解释理念》,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8年第6期,第6页。
②正向刷单炒信行为是指,电子商务平台上的商家通过虚构交易或好评的方式,提升自己店铺的信誉值,从而促成更多交易机会,谋取不当利益的行为。
③反向刷单炒信是指,一方卖家出于打击竞争对手的目的,通过为竞争对手恶意刷单,使对方遭受平台降低评级的处罚,从而导致其被电商平台认定为从事虚假交易而受到信誉降级处罚的行为。
④下文所称“刷单炒信”均指正向刷单炒信行为。
⑤王华伟:《刷单炒信的刑法适用与解释理念》,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8年第6期,第7页。
⑥下文所涉及的各项罪名的犯罪对象均为刷单平台。
⑦张明楷:《网络时代的刑法理念——以刑法的谦抑性为中心》,载《人民检察》2014年第9期,第8页。
⑧孙道萃:《可增设破坏网络市场信用评价罪规制刷单行为》,载《检察日报》2017年9月6日第03版。
⑨李世阳:《不妨强化对信用的刑罚保护》,载《法制日报》2017年6月22日,第7版。
⑩参见http://www.sohu.com/a/150450934_362042,访问日期2020年2月28日。
以营利为目的,通过信息网络有偿提供删除信息服务,或者明知是虚假信息,通过信息网络有偿提供发布信息等服务,扰乱市场秩序,达到相应数额标准的,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王安异:《虚构网络交易行为入罪新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17条规定为依据的分析》载《法商研究》,2019年第36卷,55页。
张向东:《网络非法经营犯罪若干问题辨析》,载《法律适用》2014年第2期,第58页。
王华伟:《刷单炒信的刑法适用与解释理念》,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8年第6期,第11页。
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经营者不得通过组织虚假交易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参见http://www.gov.cn/xinwen/2017-11/07/content_5237723.htm,“新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获通过相关部门负责人回答记者提问”,访问日期2020年1月19日。
周光权:《刑法总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4-45页。
臧铁伟、李寿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00-2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