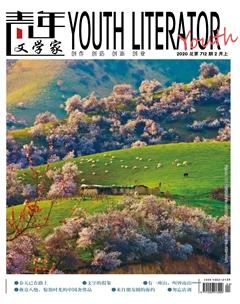《万历十五年》的出版故事
在有关30年的阅读记忆中,《万历十五年》是极其重要的一本。这不仅是因为它在近30年时间里长销不衰,更因为它影响了吴思、李亚平、杨念群、李勇(十年砍柴)等几代学人。近日,中华书局、三联书店以及学界相关人员,梳理了本书一波三折的出版过程,以及它在学界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书稿命运:“原则上接受出版” 不签约就出书
1979年5月23日,身为中华书局古代史编辑室副主任的傅璇琮,收到了著名画家黄苗子写给他的一封信,信中说道:“美国纽约纽普兹州立大学中国历史教授黄仁宇先生,托我把他的著作《万历十五年》转交中华书局,希望在国内出版。”
收到书稿后,傅璇琮马上予以细致审读,发现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他很快写了一份审稿意见,认为书名虽说是《万历十五年》,实际是论述明代中期的社会情况,着眼点比较广。但是,当时中华书局的一位领导提出,何必要出一个外国人的书,并要求傅璇琮“婉拒”。
同样是在1979年,年过花甲的黄仁宇已经失去了他在纽约纽普兹州立大学连续十年的教职。而《万历十五年》的英文版出版也几经波折。1976年,黄仁宇完成了本书初稿。根据黄仁宇在《黄河青山》中的回忆,本书处于学术性著作和商业性著作之间,几家出版社都不愿出版。出版社认为,这书既不像断代史,也不像学术论文,又缺乏分析与解剖,实在是不伦不类,也不愿承印。直到1979年,耶鲁大学出版社才答应出版。至于英文本其后被若干大学采用为教科书,则是以后的事情。
而1979年的时候,中国改革开放不久。按照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的弟子潘振平的说法,中国的影射史学此时已经是穷途末路了,而新的史学方法还未出现。由于文化开放程度不够,中华书局对于外籍华人作者的书稿以及不同寻常的表述有这种顾虑实属正常。就连傅璇琮也怕肯定得太过分,出问题。因此,他又“鸡蛋里挑骨头”,提出了幾点批评意见,并提出建议,请别的同志“再审阅一遍,共同商量一下”。之后,就由古代史编辑室的另一副主任魏连科再审一次,两人最后联名提出“原则上接受出版”的报告。
其后,时任中华书局总编辑的赵守俨在中华书局发稿单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至此,《万历十五年》在中国的出版一锤定音。中华书局版《万历十五年》后来的编辑徐卫东感慨道:“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才从十年内乱里走出来,那时候的眼光没有现在这么开放,处于一个比较封闭的环境,而且此书的作者又是外籍华人,所以在当时出版这本书真是比较大胆的举动了。”
由于当时的中国出版界版权意识淡薄,因此,中华书局与黄仁宇并未签署出版协议。直到1995年,双方才签署了一个期限为10年的出版协议。
出版过程:书信来往无数 古文专家润色
黄仁宇写作《万历十五年》的时候,最初是用英文写的,书名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后来,又由他自己翻译成了中文。由于30多年的国外生活,黄仁宇对中文已经有些生疏了,他寄来的中文稿里有很多语法不规范的地方,谴词造句上难免有不少难懂之处。中华书局编辑部在征求黄苗子的同意后,请来了傅璇琮大学时代的同窗好友,当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工作的古典文学专家沈玉成帮忙给稿子润色。
编辑部当时的意见是“尽量地按照作者的行文规则进行润色,不进行较大删改”。沈玉成每修改完一章就交给编辑部,再由编辑转寄给黄仁宇,黄仁宇修改认可后再寄回来,就这样反反复复,一章一章地润色修改。在来往了许多书信后,直到1981年6月,《万历十五年》中文版才基本定稿。黄仁宇对沈玉成的修改稿是满意的,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提到:“幸经润色修改,本书与读者见面时,文字方面已较原稿流畅远甚。”
从结果来看,《万历十五年》能在读者中引起较好反响,沈玉成先生“润色书稿”功不可没。中华书局严肃认真的编辑,连1997年三联书店版《万历十五年》的责任编辑,现为三联书店副总编辑的潘振平都很赞许:“仔细比较黄仁宇先生的著作可以发现,《万历十五年》的文字很典雅,与黄仁宇先生其他著作的文字很不一样。沈玉成先生早年被誉为‘才子,他后来跟我谈起过在本书文字上所下的工夫。中华书局确实在这本书的编辑上下了很大工夫。”
至今,中华书局的档案里还保存了当时很多改稿的书信。在书稿来回修改的过程中,黄仁宇与傅璇琮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但是作为《万历十五年》的作者和编者,两人直到十多年后,才第一次见面。
1982年,《万历十五年》正式出版,由黄仁宇的老友廖沫沙题笺,印在封面。为了表达对中华书局和沈玉成的感谢,黄仁宇提出自己不要稿费,同时将稿费的三分之一交给沈玉成,但沈玉成却执意不收。后来,黄仁宇在一封来信中写道,“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百业待兴,还有很多学者的书等着要出版,我倒希望你们寄些样书给我,我可以送给海外的学者和留学生朋友。”黄仁宇同时又表示,样书数量不必过多,怕“印数不敷分配”。于是编辑部就把稿费折成230多本样书寄给他,除去这些样书,稿费还剩了780多元,黄仁宇坚持不要。当年十月,黄仁宇在收到中华书局编辑部寄出的样书后,立刻于10月11日致函感谢中华书局编辑部,称“拙稿蒙贵局发行与国内人士见面为数十年海外人士攻读的一大快事,应向诸先生致谢。”
当时,黄仁宇有一位妹妹在广西桂林工作,黄苗子曾问是否能给予一部分稿费,黄仁宇说可以考虑,但在信中说:“但如贵局愿付与少量报酬,笔者亦不阻挡,只是人民币三十元、五十元之间则已至矣尽矣,再多一分即与鄙意相违,亦陷笔者于不诚。”
学界反响:两种范式之外 历史写作新途
《万历十五年》于1982年出版后,初版首印2.75万册很快销售一空。这样的成绩给了黄仁宇一些安慰,而本书在史学界所产生的冲击和影响,则更是黄仁宇始料未及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明史专家刘志琴回忆,“《万历十五年》出版是在史学著作发行普遍不佳的情况下,闯出来的一匹黑马。怎样评价这本书一度成为明史学界颇有争议的话题。”刘志琴还记得,“《理论信息报》在80年代曾经刊载,在作家中进行‘最近读什么书的调查,有6个作家列出近期阅读的书目,各人都不相同,连当时在文学界最走红的刘再复作品,也只有一个人次,惟一的例外是《万历十五年》,同时出现在两个作家的书目中。”
此时,正在华东师大求学的潘振平也读到了《万历十五年》,他回忆说,“我们原来的历史写作都是苏联教科书似的,从定义出发,过滤掉了历史中比较鲜活的那部分人性,事件的展开……变成了完全是一种论述性的东西。而黄先生让大家知道,至少有这么一种历史叙述方式。他的落脚点是中国怎样从一个传统社会转变成现代社会。这个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关心的问题。”
学者吴思第一次读到《万历十五年》是1986年。他在阅读过程中,情不自禁地惊叹:历史竟然可以这样写!而让他感到惊奇的原因在于“我们那个时候见过的历史写作只有两种,一种是范文澜式的,另一种是《史记》和《资治通鉴》式样的。黄仁宇的史学著作对于那个时代进入很深,读完之后有一种让人在那个时代活了一遍,走了一遭,认识了很多活人之感。总之,有全面的好感,带来耳目一新的新鲜空气。”等后来有了积累之后再看《万历十五年》,读明史,他终于发现黄仁宇绕来绕去一直想说明白却没有说明白的东西,这就是让他一举成名的“潜规则”。
《万历十五年》影响的还有吴思的同学李亚平。他在1983年读了《万历十五年》,“老实说我当时没看懂,我不明白老先生想说什么,后来,又一次重读《万历十五年》,有一种用棒子在脑袋上敲一下的感觉,敲醒了的感觉。每次读完之后都会有新的感受。”及至后来因写作《帝国政界往事》一炮而红,不少读者还指出他受到了黄仁宇的影响,而李亚平对此表示,“如果你觉得我学黄仁宇学得很像的话,那是我的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