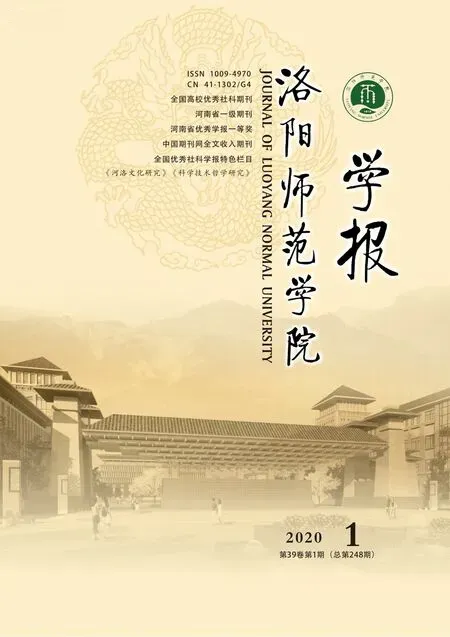论毛、郑对《诗经》的强制阐释
——以《邶风·静女》为例
张昌红
(洛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洛阳 471934)
“强制阐释”是指“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1]5。这种现象不但存在于中国当代学者对西方文艺理论的接受领域,也存在于传统文本阐释中。张江认为“主观预设”是强制阐释的基本特征之一: “论者主观意向在前,前置明确立场,无视文本原生含义,强制裁定文本意义和价值。”[1]5也就是说在文本阐释以前,阐释者已经确定了立场,并以这个立场为准则,考量和衡定文本。在这个立场面前,文本是第二位的,是张扬立场的证词,一切阐释都围绕立场,立场决定阐释。
回顾《诗经》研究历程,我们不难发现,至少存在两种立场的强制阐释。一是以毛亨、毛苌《毛诗故训传》(下简称《毛传》)为代表的“诗教”立场,认为《诗经》承担着“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社会政治作用[2]12; 二是以朱熹《诗集传》为代表的“理教”立场, 将《诗经》作为理学的教科书,通过《诗经》中的善恶美丑来警戒人们的不正当欲望与行为。尤以前者的影响为大。然而并不是《诗经》中的每一首诗都具有明显的教化意义,也并不是每一首诗本身具有的意义正好与被赋予它的教化意义相匹配。现以《诗经·邶风·静女》为例做一剖析。其诗曰: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1)《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4—207页。下引《静女》小序、诗歌文本及其笺疏文字皆在该书第204页至第207页,不再注出。《毛诗序》之《静女》小序曰: “刺时也。卫君无道,夫人无德。”在这里,阐释者的“前在立场”就是其对该诗主旨的看法。《毛传》、《郑笺》(郑玄《毛诗传笺》)受《静女》小序影响,认为该诗主旨是讽谏卫君得贞静达礼之女以替代今夫人。朱熹《诗集传》则从男女交往礼节的角度出发,认为是“淫奔期会”之诗。[3]23虽然朱熹的阐释仍存在“前在”看法,但毕竟摆脱了小序的影响。毛、郑则相反,为了迎合小序的说法而不惜改变《静女》文本大多数词语的训诂,甚至改经以就注(2)《静女》诗句“彤管有炜,说怿女美”,郑玄笺曰: “‘说怿’当作‘说释’。赤管炜炜然,女史以之说释妃妾之德,美之。”将“怿”改成了“释”来解释。,是典型的强制阐释。
“静女”二字《毛传》解释为“贞静也。女德贞静而有法度,乃可说也”,是说这位女子守女德、有法度,堪为君主之配。显然,为了支持《静女》小序,毛氏采取了增字为释的办法。实际上,“静女”意为漂亮女子。《说文》曰: “静,审也。《上林赋》‘靓妆’,张揖注曰: ‘谓粉白黛黑也。’按,靓者,静字之假借。采色详审得其宜谓之静……人心审度得宜,一言一事必求理义之必然,则虽繁劳之极而无纷乱,亦曰静。引伸假借之义也。”[4]215所以,静女是指“采色详审得其宜”的女子,即肤色、面色及服饰搭配均恰到好处的漂亮女子,跟安静无关。《郑风·女曰鸡鸣》的“琴瑟在御,莫不静好”句,可为反证。[2]345既然琴瑟在御,怎么可以安静?所以这个“静”就是“人心审度得宜”,是“采色详审得其宜”意义的引申,是和谐之义。《静女》第一章的“姝”字、第二章的“娈”字,与标题照应,亦皆为漂亮之义。
“城隅”是指城墙的角落,偏僻之地。《诗集传》释为“幽僻之处”[3]23,颇为得之,然《毛传》《郑笺》却将其解释为高于常处的城角,“以言高而不可逾”,形容女子“自防如城隅”之贞德,是有意将“城之隅”当成“城隅”解释了。这种解释与《静女》小序相符,却与诗意不合。既然是男女约会,就应选择僻静之地,高高的城墙拐角处不但不僻静,反倒更易被发现,有失人之常理。
《毛传》释“爱而不见,搔首踟蹰”为“志往而行正”。《郑笺》云“志往谓踟蹰,行正谓爱之而不往见。” 意为男子想见又不想即刻见,犹豫是否符合礼仪法度。然而这里的“爱”《齐诗》作“僾”、《鲁诗》作“薆”[5],并无喜爱之义。《说文·人部》: “僾,仿佛也。”[4]370《尔雅·释言》: “薆,隐也。”[6]75与“仿佛”义相近。薆、僾,古字通用。所以“爱而不见”意为隐藏起来,不与人相见,其主语不是诗中的男子,而是诗中的女子。男子与女子相约在城隅相见,男子到了,女子却藏了起来,不出来与男子相见。首章短短几句就写出了女子调皮、活泼的性格。所谓“搔首踟蹰”,其主语应是男子。男子准时赴约,到了约定地点却见不到女子。他感到很尴尬,不确定本次约会是否能成功,是继续留下来等她,还是转身离开,一时犹豫不定。

《毛传》释“牧”为“田官”,与诗意不谐。《郑笺》曰: “自牧田归荑,其信美而异者,可以供祭祀,犹贞女在窈窕之处,媒氏达之,可以配人君。”尽管此句诗意与后妃之德相距甚远,郑玄还是通过增字为释及比兴联想手法使二者发生了联系,强制阐释行为非常明显。《尔雅·释地》曰: “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林外谓之垧。”[6]218所以,“牧”的正确意思是指郊外。《毛传》释“荑”为“茅之始生也。本之于荑,取其有始有终”。如此解释,也是为了与“后妃之德”相谐。事实上,荑为草木初生之嫩芽,并非专指茅之始生。《管子·度地》曰: “草木荑,生可食。”[10]荑是百姓寻常所见之物,本没有什么深意。男女从最初在城隅见面,到女子正式送彤管为礼物,再到女子从郊外回来顺便送点自己采的草木嫩芽给男子,表明二人的交往从拘谨、犹豫发展到了郑重其事,直至简易平和。他们的关系更亲密了,相互之间更信任了,交往也更频繁、随意了。然而,《毛传》受小序所限,对“荑”字的解释偏重于“茅之始生”之“始”字以及茅的祭祀之用,对理解《静女》真正诗意来说是多余的。
《毛传》释“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为“非为其徒说美色而已。美其人能遗我法则”。可理解为: 我并不是只喜欢美女的漂亮颜色,还喜欢美女堪配人君且能依既定法则来掌管后宫。《郑笺》修正为“遗我以贤妃也”,意为我不只喜欢女子的美色,还对能得到贤妃以奉人君之事感到高兴。这里的“美”意为喜欢,是动词,与美人之“美”意义不同。可见直到《静女》一诗的末尾,毛、郑仍在围绕“女史彤管之法”作阐释,并没有顾及这次女子所赠不是“彤管”而是“荑”的事实。毛、郑把本来并不复杂的诗意解释得十分繁琐,是强制阐释的必然结果。其实此句可简单解释为: 不是因为嫩芽本身有多美,而是因为它是自己喜欢的人所赠,所以我才觉得它美。正是因为女子所赠为寻常之物,而“我”却认为非常漂亮且与众不同,才突出了两人的恋人关系。
“十五国风”源于民间,不排除有“缘事而发”的刺时之作,但大多数是先民的自由歌唱,未必有明确的美刺对象。然而,朝廷通过采诗、献诗等途径,对这些诗进行集中、整理后经常在不同场合和乐演唱。作为中华礼乐文明的一部分,这些诗在配乐演奏时往往被赋予一定的教化功能。这样,这些来自民间的质朴的歌谣就逐渐具有了美刺价值,每一首诗被赋予的或“美”或“刺”的教化内涵就成了其原有诗意之外的另一标签。《诗经》各篇前的“小序”正是对每首诗诗教指向的固化。不可否认,在诗教盛行的春秋中后期,一首诗的教化涵义往往比其原有诗意更为重要。《毛诗序》之“小序”所点明某一诗歌的教化主题很容易成为该首诗歌被再次阐释时的“前在立场”,从而导致阐释者对该诗文本的强制阐释。《毛传》之所以释“静女”为贞静之女,是为了使其与“后妃之德”相配,所谓“贞”就是要求女子做到不失身、不改嫁,终身忠于一位男子。《静女》小序谓“夫人无德”,从撰序者角度来看,正是讽刺卫宣公夫人不贞不德。卫宣公夫人本是太子伋(急)之妻,宣公纳之,而后又听其言,设计伏杀太子伋。(4)《左传·桓公十六年》曰: “卫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属诸右公子。为之娶于齐,而美,公取之。生寿及朔,属寿于左公子。夷姜缢。宣姜与公子朔构急子。公使诸齐,使盗待诸莘,将杀之。寿子告之,使行。不可,曰: ‘弃父之命,恶用子矣!有无父之国则可也。’及行,饮以酒。寿子载其旌以先,盗杀之。急子至,曰: ‘我之求也,此何罪?请杀我乎!’又杀之。”《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9页。朱熹之所以释“静女”为闲雅女子,是突出其清闲贞顺、端庄稳重、言语得当、动静有法等品德,以合乎其封建理学标准对女子的要求。
毛、郑所依之《毛诗序·小序》其实并非一人一时之作,而是前人写成后,后人有所增益。前人所写相对于所序诗歌之本意来说,已经是出于诗教目的的附加,后人增益的内容于所序诗歌本意来说,就更是相距甚远,甚至毫无关系了。《四库全书·诗序》提要曰: “今参考诸说,定序首二语为毛苌以前经师所传,以下续申之词为毛苌以下弟子所附。”[11]下举数例: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则志在于女功之事,躬俭节用,服浣濯之衣,尊敬师傅,则可以归安父母,化天下以妇道也。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则男女以正,婚姻以时,国无鳏民也。
《采蘩》,夫人不失职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则不失职矣。

《凯风》,美孝子也。卫之淫风流行,虽有七子之母,犹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尽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尔。(5)以上各篇序文均引自《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分别是第36页、第54页、第77页、第85页、第157页。

崔述《读风偶识》曰: “《邶》《墉》《卫》风三十九篇,玩其词意,考其时势,惟《墉风》自《柏舟》外皆春秋时事,而《邶》《卫》二国风多似春秋以前所作。《淇澳》《硕人》不待言矣,其余诸篇皆与《春秋》经、传所载卫国之事无所关涉,且《邶风》十九篇而‘毖彼泉水,亦流于淇’在第十四篇中。《卫风》仅十篇,而言‘淇’者四,至第九篇犹云‘在彼淇梁’,其无渡河以前之诗明甚。考卫渡河之日,在鲁闵公二年,上距春秋之初仅六十年,然则其诗在春秋以前者多矣。故序虽以春秋中事附会之,而委曲牵强,卒不能合也。”[12]可见《静女》小序所谓“刺时”之“时”也并非指春秋卫宣公之时。总之,毛、郑以此小序为主旨来解说《静女》诗意,是以强加给文本的含义来证实“前在立场”的强制阐释。
在《诗经》中,同一首诗歌在不同时期,甚至同一时期的不同场合所承担的教化作用也许并不相同,所以人们对其主题的理解与阐释也可能有多种。譬如作为《诗经》首篇的《关雎》,就有娱乐嘉宾、以色喻礼、讽刺周康王好色耽政、歌颂后妃之德、表达男女恋情、渴求贤才等主题。(6)西周及春秋时期,上流社会在举行燕礼、乡饮酒礼的时候,一般要演奏《关雎》作为合乐,因《关雎》中有“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等诗句,正好表达了宴会主人娱乐嘉宾之意。“以色喻礼”是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提出的观点。该观点以琴瑟的和谐来比喻男女的和谐,认为《关雎》是一首歌唱婚配的篇章。“讽刺周康王好色晏朝”是汉初今文三家《诗》的观点。“歌颂后妃之德”是古文《毛诗》的观点。五四以后,学者一般认为《关雎》是一首爱情诗。然而,阐释不是没有边界。不管阐释者对某首诗歌的主题做何种理解,他都必须以文本为依据,并且在做文本阐释时一定不能改变对词语本来含义的训诂,一旦改变了词语的正常训诂,那就是不当甚至错误的阐释了。我们今天阅读《诗经》,应理性地对待《毛诗序·小序》,既要合理利用,又要避免受其过度影响,以免导致对文本或词语产生不恰当的理解。对于“诗教”,我们更应该辩证地看待。如果抱有通过《诗经》中的有关篇章去了解先民生活的目的,那读者就应该尽可能地把加在《诗经》每首诗歌本意之上的教化外衣去掉,去直接聆听先民们的心声; 如果借由《诗经》各篇章的历代不同解释来做思想史、社会史等方面的研究,那么以诗教、理教等教化目的为出发点的强制阐释显然是重要的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