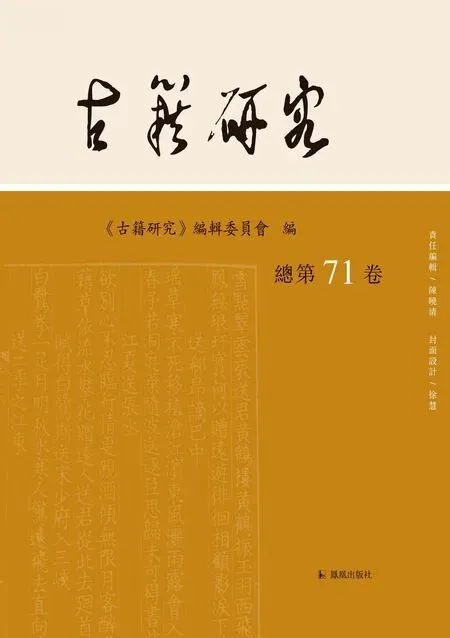閻若璩未刊書劄十一通輯釋*
宣燕華
關鍵詞:閻若璩;潛邱劄記;上海圖書館;佚文;書劄
閻若璩(1636—1704,山西太原人,寄籍江蘇山陽)是清代樸學開山時期最重要的學者之一,除最著名的《尚書古文疏證》一書外,其筆記體著作《潛邱劄記》亦久負盛名,《四庫全書簡明目録》稱其“與顧炎武《日知録》方軌並騖,未决誰先”(1)(清)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簡明目録》,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483頁。。通行的乾隆十年眷西堂刻本《潛邱劄記》卷五,收閻若璩書劄173通,内容大體皆爲論學談藝,對於研究閻若璩及清初學術皆有重要價值。現藏上海圖書館的拜經樓舊藏抄本《潛邱劄記》七卷,其内容形成於刻本之前,且較刻本多出詩19首、雜文8篇及書信11通,具有極高的版本和校勘價值。其中的書信11通,在抄本中是完全連續的,且皆爲言之有物的論學之文,其未刊入刻本很可能是無意的遺漏而非有意的删削,是此抄本所見佚文中最有價值的一部分。11通書劄皆列於《與戴唐器(2)(清)戴晟(1659—1735),字西洮,又字晦夫、唐器,江蘇山陽人,師從黄宗羲,有《寤硯齋集》。書》目下,對應眷西堂刻本的位置爲卷五頁五十三“李商隱與陶進士書”條與頁五十四“虹考去後”條之間。今輯録並略作考釋如下,以供學者之研究。
一
吴草廬序王荆公文,以唐宋文人有七家,小蘇不預焉(3)(元)吴澄(1249—1333),《臨川王文公集序》云“合唐宋之文,可稱者僅七人”,分别爲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洵、蘇軾、曾鞏和王安石。,可見元尚未有八家之目。萬曆中南豐刻曾集云:“世藏先生《隆平集》數十卷,别無副本,未敢示人,即豐人士亦不知先生復有是書,雅欲手寫,傳之好事,以困公車未能。”(4)(明)寧瑞鯉《重刻曾南豐先生文集序》。可見今尚有此書,在其裔孫家也。連閲宋、金、元天文及曆志證成。《疏證》中及曆法者,頗爲絶學,蓋知曆者不知《胤征》僞書,紛紛附會,日食至不可言。弟以爲僞,再參以曆法,虚空粉碎矣。
按:此劄涉及閻若璩對《尚書古文疏證》中曆法部分的自我評價,認爲以曆法證僞是自己的一大發明,反過來又可以糾正曆法學者對古文《尚書》的附會之失。具體見《尚書古文疏證》卷六上第八十一條“言以曆法推仲康日食《胤征》都不合”。
二
錢宗伯學第一,詩次之,文又次之。今人以爲文勝其詩者,非也。顧處士學第一,詩次之,不在能文之列。徐昭法以爲今之作者,此胡説也。黄徵君學第一,文次之,不在能詩之列。今人以爲文勝其學者,亦非。(5)以上分别指錢謙益(1582—1664)、顧炎武(1613—1682)、黄宗羲(1610—1695)。徐昭法爲徐枋(1622—1694),江蘇長洲人,有《居易堂集》。聖人復起,不易吾言。吾兄具眼人也,楊序果從小杜《李賀序》脱胎(6)楊序指楊萬里《石湖先生大資參政范公文集序》,見《誠齋集》卷八十二;杜序指杜牧《李賀集序》,見《樊川文集》卷十。,但不及杜文之有意味,豈唐宋人之别耶?豈廷秀原不及牧之,非關時代邪?放翁却佳,似勝廷秀。《宋史》本傳“堰在松陽、遂昌之間,激漢水溉田”(7)《宋史》卷三百八十六《范成大傳》。,此處那得有漢水,應是溪字之訛。三顧于此等不能辨,仍其訛舛,此昌黎以詩人爲餘事,韋蘇州以“讀書事已晚,把筆學題詩”自命也。然《序》以黄衣屬健步,不知何典故,知否?戰國時黑衣,晋時白衣,皆吏之衣也,或宋不同在此。學問真無窮無盡也,可勝浩嘆不盡。
按:此劄評騭清初三家錢、顧、黄的詩文和學術成就,並指出了與時人評價之不同。閻氏認爲三人最突出的成就皆不在詩文,而在學術。他在《潛邱劄記》中屢屢表達對三人學問的拳拳服膺之情,例如在另一通寫給戴唐器的信中説道“生平所心摹手追者,錢也,顧也,黄也,黄指太冲先生,顧指寧人先生”(8)《潛邱劄記》卷五,閻氏眷西堂刻本。,在《南雷黄氏哀辭》中又寫道:“博而能精,上下五百年,縱横一萬里,僅僅得三人焉,曰錢牧齋宗伯也,顧亭林處士也,及先生而三。”(9)《潛邱劄記》卷四上,閻氏眷西堂刻本。閻氏將錢、顧、黄三人視爲清初學術界的巨擘,而並不看重他們的文學地位,認爲時人的普遍看法不甚恰當,這對我們認識當時的學界和文壇格局具有很大的參考價值,同時也有助于我們理解閻若璩的學術宗旨和淵源。
三
張東海名弼,字汝弼,華亭人,成化丙戌進士,官南安府知府,詳牧齋《列朝詩集》丙之四,可檢看也。但牧齋原本稱其弘治丙戌進士,弟一見疑之。孝宗十八年,始戊申,終乙丑,安得有丙戌紀年。嘗記羅一峰爲成化二年丙戌狀元,弘治其成化之訛乎?且陳白沙以成化十八年辟召至京,道出南安,正張東海爲太守,賦詩往復,有《玉枕山詩話》盛傳于世,安得弘治方成進士?故敢放筆改正。所謂觀天下書未遍,不得妄下雌黄。弟觀書遍天下,豈尚有疑於中,而輟筆不下乎?弟嘗自謂:話到即覺,境到即悟,書籍不得而欺我,實海内絶學。黄先生(10)指黄宗羲。亦有不及閻生處,况他人乎?
按:此劄提供了閻氏考據和校勘的一個實例,以“觀書遍天下”的自負“放筆”理校,正是閻氏學術的一個鮮明特徵。
四
《史記》《漢書》俱作咸,注,咸一作函,自然咸字爲是,《文選》安知非傳寫之訛增偏旁?(11)司馬相如《難蜀父老》中的一句,《史記》、《漢書》作“上咸五,下登三”,《文選》作“上减五,下登三”。雖然,就减字解,亦無不可,古人所謂兩義並通者是也。以《史》《漢》正《選》,或尚可,竟以《文選》正《史》《漢》,斷斷不可,惟高明者知之。如運籌帷幄之中,《漢書》語也,《史記》作帷帳,豈得謂《史記》非耶?各有所出耳。一飯之德,見《范雎傳》,若大丈夫勿顧一飯之恩,又出《唐書·劉從諫傳》,豈得謂恩字無本耶?文憲(12)(明)宋濂(1310—1381),謚文憲。雖朱子一派,其實純乎禪,錢牧齋以爲當入從祀(13)見錢謙益《牧齋有學集》卷四十九《書趙太史魯游稿後》。,非矣。連考陽明之入從祀,廷議不許,申時行密揭神宗,取中旨而行,醜矣醜矣!念臺先生(14)(明)劉宗周(1578—1645),字起東,號念臺,浙江山陰人,有《劉蕺山集》。曾議薛文清(15)(明)薛瑄(1389—1464),謚文清,理學巨儒。在内閣,不能救于謙之死,精嚴之至。此等議論,可配聖經,見《雒閩源流録》(16)見《雒閩源流録》卷三薛瑄條。,此書不可不覓一部藏之。
按:此條可見閻若璩對于宋明理學的態度。《雒閩源流録》中的相關文字,閻若璩曾全加手録,見今《潛邱劄記》眷西堂刻本卷一頁六十六—六十七。
五
《顧命》明是“兑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安得有“兑弓和矢”之文?近方覺□□(筆者按:原文空兩格,當爲震川,指歸有光)先生文用事亦多誤處,如《洪範傳》“大事先筮而後卜,晋侯得阪泉之兆僖二十五年,趙鞅遇水適火哀九年,又筮之是也”(17)見《震川集》卷一。。如此則當云先卜而後筮,《左傳》可考,何得誤以先筮而後卜耶?吾兄于此等可考《尚書》《左傳》,以見弟非謬,而于學問亦思過半矣。王圻《續文獻通考》于二十四考補一考曰謚法,即取王元美《古今謚法考》全全登載。遍查元臣謚,無潘昂霄,此自有故,元美止按《元史》列傳有謚者録出,潘既無傳,安從考其謚,只好兩載,以出自子孫爲近是耳。
按:歸有光在閻氏心中的地位與錢謙益頗有相似處,即于文學成就之外更看重其學術造詣,此則雖爲批評,却仍可見其服膺。歸氏對清初學術的影響至今仍没有得到恰當的估計,閻氏的相關表述是我們考察此問題的重要參照。
六
昨述李退庵侍郎(18)(清)李敬(1620—1665),字聖一,號退庵,江蘇六合人,有《退庵集》。對汪苕文(19)(清)汪琬(1624—1691),字苕文,號鈍翁,江蘇長洲人,有《堯峰文鈔》。云,《菁菁者莪》之什,什字用不得,此篇名在《彤弓》之什内,查《毛詩注疏》、朱子《詩集傳》皆可見。駁人者乃爲人所駁乎?真可一笑。雲九(20)當爲秦文淵,通天文曆法,有《秦氏七政全書》。兄枉過,將寒食畢竟在何日,出《月令廣義》所載异説,令其折衷,反復良久,方得表裏洞達,吾兄可切記。曰中曆自漢至明,寒食在清明前二日,如清明係丙寅,寒食則甲子是也。西曆愈精,寒食在清明前一日,如清明係丙寅,寒食則乙丑是也。老弟蓄意數十年,今方一口説盡。《元史·河源附録》,“至元十七年,都實窮河源,還並圖其城傳位置以聞。其後翰林學士潘昂霄從都實之弟闊闊出得其説,撰爲《河源志》。臨川朱思本又從八里吉思家得帝師所藏梵字圖書,而以華文譯之,與昂霄所志互有詳略。今取二家之書,考定其説,有不同者,附注于下”,潘昂霄見《元史》僅此。愚嘗謂元有二絶,郭守敬曆法也,都實河源也,皆出世祖至元十七年一年間。可笑王守溪不信,真夏蟲不可以語冰。
按:閻氏所謂二絶,其實也代表了他本人的兩個重要學術方向——地理學和曆法學,這兩種實學色彩非常濃厚的專門之學,實際也是乾嘉學術的重要組成部分,從這一學術取向的承繼也可以看出閻氏在清代學術史上的地位。
七
顧景範(21)顧祖禹(1631—1692),字景範,江蘇無錫人,有《讀史方輿紀要》。地學得其大,黄子鴻(22)黄儀(1636—?),字子鴻,江蘇常熟人,有《紉蘭集》。得其細。□□(筆者按,原文爲兩空格)未遇江夏南雷先生(23)指黄宗羲。,《水經》已被渠攻駁無完膚,每駁每絶倒也。所説某上人既爲遵王(24)錢曾(1629—1701),字遵王,江蘇常熟人,從學於族曾祖錢謙益。高第弟子,則牧齋之再傳門人,今聞出南雷先生門,得其緒餘者,無不可喜可愕,况虞山乎?施虞山學問似未討論,不可不兼攝之。嘉靖時詩,時天水胡纘宗出獄,謝榛貽之詩曰“白首全生逢聖主,春山何意見騷人”,又玉峰王永祚之子詩曰“無恙此山色,相思只酒人”。遵王改句似從此偷來(25)可能指錢曾《莪匪樓成詩以自賀八首》其三“但覺窗中山窈窕,不論床下客何如”一句。此詩作于康熙十二年(1673),詳見謝正光:《錢遵王詩集箋校》(增訂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7年,第225頁。,真盗狐白手也。弟欲一面某上人,問牧齋遺事一二,竟不可得而把臂矣。元祐黨籍碑,鮮于綽乃鮮于侁之子,字子駿,東坡最交好,不獨司馬、范、吕三家爲父子,南雷先生又一逗漏矣。雖然,此不見《宋史》,黄僅據《宋史》,未博極群書也,恐此等輸却牧齋一籌。安得趁其一息尚存,縮地告之,使後生可畏,來者難誣。
按:此則可見閻氏推重牧齋更甚于南雷。閻氏的批評針對的是黄宗羲《陳定生先生墓志銘》中“元祐黨人,唯司馬光、司馬康、范純仁、范正平、吕公著、吕希仁父子名在黨籍,而先生之父子實似之”(26)見(清)黄宗羲著,陳乃乾編:《黄梨洲文集》,中華書局,2009年,第184頁。一句。此劄當與《潛邱劄記》卷五頁二十八—二十九《與戴唐器書》“歸讀《陳處士墓表》”一劄參觀,二劄皆論及黄氏《陳定生先生墓志銘》一文中的錯誤,當約略爲一時所作。
八
《傳是樓記》(27)(清)汪琬《傳是樓記》,見《堯峰文鈔》卷二十三。,“經則傳注義疏之書附焉”,此句不通之甚,《易》《書》《春秋》等雖有專刻正文本,畢竟算不得,經豈有舍傳注義疏者哉?當改曰“經則義注、讖緯、小學之書附焉”。細讀《隋·經籍》《唐·藝文》及《通考·經籍考》,方知此句之妙也。《御書閣記》(28)(清)汪琬《御書閣記》,見《堯峰文鈔》卷二十三。,“冬十月戊午,越二日庚申”,此句亦不合經。《召誥》“三月丙午朏,越三日戊申,越三日庚戌”,皆連本日數,則越二日庚申,當改曰越三日庚申。唯《武成》“丁未祀于周廟,越三日庚戌”,離本日數,此僞書之顯露破綻者,詳見《疏證》(29)見《尚書古文疏證》卷四第五十三條“言《武成》癸亥甲子不冠以二月非書法”按語第一則。。《傳是樓記》前云“子孫未必能世富、世寶、世享娱樂”,即司馬温公之唾餘,後云“讀而不行,與弗讀同”,又老生之常談也。試取牧齋《千頃齋藏書記》(30)(清)錢謙益《黄氏千頃齋藏書記》,見《牧齋有學集》卷二十六。,《有學集》删節了,非原本;黄先生《天一閣藏書記》(31)(清)黄宗羲《天一閣藏書記》,見《南雷文定》卷二。如數家珍,歷歷指諸掌,不千百倍于鈍翁乎?鈍翁自喜文集多説經,牧翁不及我,弟獨議其經學不深。如云自唐世盛行毛、鄭,而齊、魯、韓三家遂亡(32)(清)汪琬《詩説序》,見《堯峰文鈔》卷二十六。,何异説夢?殊未讀《隋·經籍志》乎?亦知高子遺書之妙(33)(清)汪琬《重刻高子遺書後序》,見《堯峰文鈔》卷二十七。高攀龍著。,難得難得。蓋文章家多不尚理學也。《徐圃臣集序》(34)(清)汪琬《徐圃臣集序》,見《堯峰文鈔》卷二十八。佳絶,三記有法不待言,豈有鈍翁而無法者哉?弟則終以爲遜侯朝宗、魏叔子(35)時汪琬古文與侯方域、魏禧齊名,有“國初三家”之稱。。且姑存此論,他年垂七十再案此言,何如?每遭此輒欲發憤讀書忘言,願先助我。
按:此則評論汪鈍翁文章,多譏談。蓋閻氏與汪氏夙怨甚深,故多相互嗤毁。而汪氏對于閻氏極推崇之錢牧齋多所詆訶,如《讀初學記》一文云 “夫理學固非牧齋所知。姑以文字言之,集中如《天臺泐法師靈异記》《萬尊師》《徐霞客》諸傳,駁不經,曾郢書燕説之不若。尚未能望見班馬藩籬,况敢攀六經乎”(36)(清)汪琬《讀初學集》,見《鈍翁類稿》卷五十。,或許也是招致閻氏以彼之道還施彼身的原因。但閻氏所論汪琬不深于經學,則堪稱的評,鈍翁亦恐不能自辯。從閻氏所論也可看出,當時已將汪琬、侯方域和魏禧三人並稱。
九
黄先生《庚戌集自序》末云,“先聖庚戌生,朱子庚戌生,余亦庚戌生,論者以謂朱子發明先聖之道,似非偶然”(37)見《南雷文定》卷一。,妙妙。今日讀宋景濂門人□□(筆者注:原文空兩格,當爲林静)曰:“吾夫子與朱子生同庚戌,今潛溪先生之生亦於是歲。人謂聖賢之出,鍾靈降秀,爲世禎祥,天之所畀信乎?其不偶也。”(38)見《雒閩源流録》卷一。若黄先生更將景濂之生補出,在朱子後,己之前,豈不更妙?或曰:“我先生直繼朱子,豈屬潛溪?”非也。此考之不博,無高明勝己之人告之耳,告則未有不欣受者。
按:閻氏自負高明過于黄宗羲,在私人書信中顯露無疑。戴晟爲南雷及門弟子,閻氏屢在信中直言批評其師,或許是想通過戴氏轉致黄氏之耳。黄宗羲曾爲閻氏《尚書古文疏證》四卷本作序,但二人終身未曾晤面。南雷死後,閻氏方因戴氏兄弟之介而執弟子禮于靈前,詳見《南雷黄氏哀辭》。
十
輿圖偶一披覽,具茨山在陽關之外,怪哉,不可解矣。按《莊子·徐無鬼》篇,黄帝將見大隗音委乎具茨之山,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司馬彪注,山在滎陽密縣東,今名秦隗山,即《明一統志》山在新鄭縣西南四十里是也。考之《水經注》,潩音亦水出密縣大騩音貴山,即具茨山。黄帝登具茨之山,升於洪堤上,受神芝圖於黄蓋童子,即是山也。又考之《國語》,主芣音浮騩又音委而食溱洧,韋昭注,芣騩,山名,在密縣,此大隗之訛。又證以《統志》,襄城在開封府許州西南九十里,與新鄭縣相近,豈得遠在异域?且從來説具茨者止此一處,不比黄帝問道于空同,《史記》注一在平凉府,一在肅州衛,有二處也。安得見江夏父子(39)不詳何人,可能指黄宗羲、黄百家。而面質之?若以此子呶呶,以後有刻不與之看,則大繆矣。《初學記》有虹入君子之室則吉等語,即以此本假我。蓋《詩》《禮》《爾雅》所載虹事,盡披覽矣,豈容獨遺却此耶?舊城有虹入其灶屋,此不祥也。有來叩我考此,答之:末二句定、哀之微辭,非實語。朱子《詩傳》蝃蝀倏然成質,似有血氣之類,奇絶。
按:刻本《與戴唐器書》有“虹考”一條,抄本在下條之下,合此條可見閻氏與友人商量考證的原委經過。
十一
詩人、文人、學人,斷分三種,此何待言?其年(40)(清)陳維崧(1625—1682),字其年,號迦陵,江蘇宜興人,有《湖海樓詩》《湖海樓詞》《迦陵文集》等。亡友止嫻詞章,苕文便兼學問。有文人之詩,實自少陵始,加以昌黎、樂天,益又甚焉。詩人之詩,則高、岑、王、孟是也,界畫甚明。分舊雨、鬥新晴十四字,酷似坡公也,不甚似老杜,然真絶調矣。字書:示,告也,又呈也。雖字含二義,其實杜詩于先輩及同輩皆曰呈,子侄方曰示,此兄指摘最確。弟欲聞其姓名字,願告我。郝京山(41)(明)郝敬(1558—1639),字仲輿,號楚望,湖北京山人。《草堂集》《談經》各爲一書,王三原(42)(明)王恕(1416—1508),字宗貫,號介庵,晚號石渠,陝西三原人。《石渠意見》並《續意見》若干卷,錢牧齋稱之;李騰芳《説莊》、萬廷言《經世要略》、于慎行《讀史漫録》(43)皆明人。李騰芳(1572—1633),湖南湘潭人;萬廷言(1522—1566),江西南昌人;于慎行(1545—1608),山東東阿人。,並梁公狄(44)(清)梁以樟(1608—1665),字公狄,直隸清苑人,有《梁鷦林先生全書》。稱之;何喬新(45)(明)何喬新(1427—1502),江西廣昌人。《宋元臆見》,孫北海(46)(清)孫承澤(1594—1676),號北海,順天大興人,有《春明夢餘録》、《研山齋集》等。稱之;切記隨時覓之,勝《玉堂才調集》(47)(清)于朋舉編,刊于康熙十四年(1675)。遠矣。近來方知《八大家文鈔》(48)(明)茅坤編:《唐宋八大家文鈔》。好不通,黄《答張爾公書》(49)(清)黄宗羲:《答張爾公論茅鹿門批評八家書》,見《南雷文定》卷三。張自烈(1597—1673),字爾公,江西宜春人。駁正不盡。《韓文起》(50)(清)林雲銘編:《韓文起》。尤不通,然有一二解釋,真足解頤。以知坊本俗刻,亦不可放過。欲與吾兄談者甚多,奈何奈何。
按:此劄論及明人著述,可以考見清初學界對明代學術的接受情况,其中郝氏、王氏著作被閻若璩稱引頗多。儘管現在的學術史叙述中清學和明學似乎關係甚微,但從閻氏這樣的清初學者的著作中却可以發現,明人著述仍然是他們極重要的學術資源。
以上11通書信,所論包括詩文、曆法、地理、文字考證等方面,涉及人物包括錢謙益、顧炎武、黄宗羲、汪琬、顧祖禹、黄儀、錢曾等,内容豐富,具有較高的研究參考價值。此外,抄本中《張孺人行略》一篇佚文,是閻氏爲亡妻所作,對于閻氏生平的研究亦有較大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