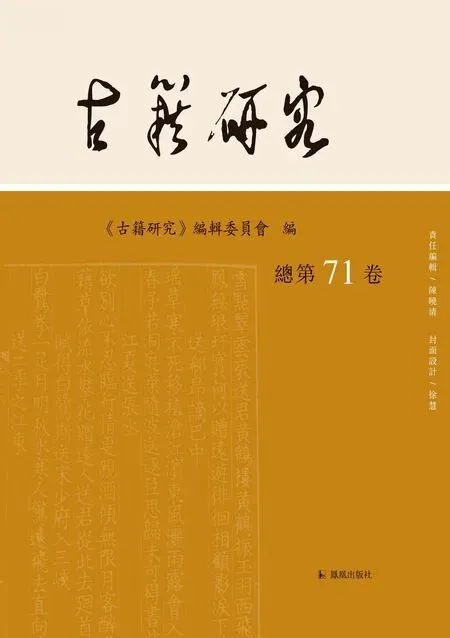翁方綱時文理論探微*
——以《復初齋時文》《帖經舉隅》爲中心
李文韜
關鍵詞:復初齋時文;帖經舉隅;翁方綱;經術;學人之時文
翁方綱(1733—1818),字正三,又字叙彝。號覃溪,又號忠叙、彝齋、蘇齋。其家先世福建莆田人,十世祖官北京,始入籍順天,是以翁方綱爲順天府直隸大興人。翁方綱於乾隆十七年(1752)中二甲進士,欽點翰林院庶吉士。乾隆三十八年(1773),任《四庫全書》纂修官。又一生以文學清華之職,多次出任鄉、會試考官以及地方學政。嘉慶二十三年(1818)卒,年八十六。翁氏生平精心積學,著述宏博,主要撰有《復初齋文集》三十五卷、《石洲詩話》八卷、《杜詩附記》二十卷、《粤東金石略》九卷等(1)相關著述可參見沈津所撰《翁方綱年譜》(臺北:“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出版社,2002)以及段慧子博士論文《翁方綱著作研究》(2011)。翁氏的時文著作,據梁章钜《制義叢話》載:“翁方綱……有《復初齋時文》。”孫殿起《販書偶記》載:“《帖經舉隅》三卷,北平翁方綱撰,無刻書年月,約乾隆間以自寫本精刻。”可知翁氏時文代表性著作爲此二種。,於經學、詩學、書學、金石學、評點等均有涉及。
作爲乾嘉之際學術界的代表人物,翁方綱在經學、詩學、書學以及金石學方面的著述一直都受到關注,但他所撰時文以及時文理論却鮮有受到矚目。結合其官宦生平來看,翁氏曾一任江西學政,三任廣東學政,一任山東學政,壯年精力多付諸此。其中“校士”是其作爲學政的主要職責,時文理論則是他校士的主要工具。因此,從時文角度進行研究,對完善當今學界關於翁方綱的整體研究無疑是十分有必要的。
一、 《復初齋時文》《帖經舉隅》版本述略
綜觀明清兩代有關時文批評與理論的成書,大致有兩種形態:一是時文選集的評點,此類以《可儀堂一百二十名家制義》《欽定四書文》爲代表;一是時文理論的專書,而在時文理論專書中,有一類專論時文作法,有一類則是專論時文各題的題解,後一類書最貼近《四書》原典,最具經學之性質。翁方綱的時文理論主要保存在《復初齋時文》和《帖經舉隅》兩書中。《復初齋時文》爲其自選時文集,各文均有夾批和文後總評,屬於評點類時文集;《帖經舉隅》除了包含字説、碑銘法帖的筆記外,其主體部分是有關《四書》各題的題解以及對時文的討論等。
《復初齋時文》現存哈佛本、上圖本兩種,其中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本爲《復初齋時文》與《帖經舉隅》的合刻本。哈佛本《復初齋時文》全書不分卷,共兩册,每半葉九行,行二十四字,白口,無魚尾,四周雙邊。版心上書口刻“復初齋時文”,下方書葉次,第一册首葉首行下鈐朱文“哈佛漢和圖書館珍藏印”。對該藏本的基本信息,館記説道:“九行, 二四字”、“Published:[China] : [publisher not identified], [1787?]”。館記對於其刊刻年限未能下斷語,沈津先生於《年譜》中將該時文集認定爲“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自刻本”,依據的是該書葉首處翁方綱的自序,翁氏自記道:“乾隆五十二年六月望日大興翁方綱自序。”此時翁方綱正擔任江西學政,五十四年(1789)九月方奉旨調回京師。再結合文本内證,文集中的《西江文體論》等篇章亦能證明該文集當是在江西時所作。因此,《復初齋時文》的刊刻時間當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六月至五十四年九月之間。
上海圖書館藏《復初齋時文》共一册。板式上,每半葉九行,行二十四字,白口,無魚尾,四周雙邊。版心上書口刻“復初齋時文”,下方刻葉次,上圖本於册首葉序目下鈐朱文“上海圖書館藏”。該書舊爲民國王培孫所藏,扉頁有小記,叙述得書始末,並於翁方綱自序之後鈐有朱印“王培孫紀念物”。
内容方面,兩藏本均以翁方綱自序居首,先目録後正文,每篇時文題目均空兩字起刻,正文部分均頂格起刻,篇尾的評點則整體空一字起刻。依哈佛本目録所載,時文當爲四十篇,哈佛本實際缺九篇,分别爲《女得人焉爾乎》《古之道也爾愛其羊》《赤之適齊也》《明日》《天油然作雲》《王使人矙夫子》《誠不以富,亦祗以異,其斯之謂與》《子路從而後 子見夫子乎》《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一節》,上圖本則篇目結構完整,以上圖本作爲對校本,便能將缺失的九篇補齊。此外,時文集中還附有《西江文體論》一文,論述江西文人爲文之風貌。
通過對照兩本,可以發現除葉次有所顛倒、脱落外,兩本於板式、同篇目下的内容了無差異,這種高度一致顯示出了這兩藏本實爲同套板片所印。舉例來説,查閲哈佛本,發現在題爲《先王有不忍人之心猶其有四體也(其一)》(seq.49)、《先王有不忍人之心猶其有四體也(其二)》(seq.50)的時文中,兩題的右上側,即該頁之右欄均有斷口。上圖本(61a、63a)在相同位置亦有相同斷口。又如哈佛本(seq.53)右上角邊口明顯斷裂,上圖本(66a)亦出現相同情况。再從文字漫漶現象來看,文字漫漶雖然有很大部分原因是由於後期保存所致,但如果是板片自身的缺陷,依然能很清楚地辨認。哈佛本(seq.77)中,原文爲“中間扼要争奇……以此圭臬士林”,其中“間扼”與“臬”明顯是屬於刻板問題導致的文字缺損,結合上圖本(88b)對照,可以看到相同問題。上述哈佛本與上圖本所呈現出高度一致的斷口與文字缺損等異常狀况,在兩本中數見,在此僅列舉其顯著者。這樣的情况既非有意爲之,又不是保存不善所致,再結合二者在板式、同篇目下内容的高度相似性,可以斷定二者爲同一套板片印刷而成。
《帖經舉隅》版本有三種,除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本外,中國國家圖書館亦藏有《帖經舉隅》三卷本、《帖經舉隅》四卷本。由於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所藏《帖經舉隅》與《復初齋時文》是合刻本,二者刊刻體例相同,且《帖經舉隅》文本中亦有屢次提到“江西”的相關文字,可推論《復初齋時文》與《帖經舉隅》應是爲了同一目的而同時刊刻,哈佛合刻本應是初行本,其他單行本應是後來析出,對初行本進行相關增補和删節,上圖本《復初齋時文》便是如此。
哈佛本《帖經舉隅》是三卷本,書册封面左側題識爲“翁覃谿帖經舉隅”,右側題爲“歷代碑帖考”。每半葉九行,行二十四字,白口,無魚尾,四周雙邊。版心上書口刻“帖經舉隅”,下方書葉次,藏本於每卷首葉首行下鈐朱文“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哈佛本《帖經舉隅》主體部分爲關於《四書》的題解,每卷中主要以“論《××××》題”的形式來闡發對某題的見解,其中有涉及大題如《中庸第二十五章》全節、《大學之道》四節等,亦有涉及小題如《入雲》之類。全書無序無目録,卷一共有十四篇題解。卷二有六篇題解和一篇《制義江西五家論》,此外還附有歐陽修、曾鞏、黄庭堅三人詩文選目,以及《書法舉隅》卷上、下,其中《書法舉隅》上卷論字,下卷論碑銘法帖。卷三有題解八篇以及《文體論》(上、下)、《讀書養氣説》三篇論説文。
國圖《帖經舉隅》兩藏本作爲單行本與哈佛合刻本有所區别。國圖所藏《帖經舉隅》三卷本在刊刻字體上就與哈佛本明顯不同,應是另一塊雕版,但全書在整體内容、文字排版格式上無較大差異,只是在卷三處增加一篇題解(論《子曰孟子曰》題)和兩篇論説文(《論杜詩“前輩飛騰入”句》《杜詩“熟精文選理”“理”字説》)。國圖藏《帖經舉隅》四卷本在刊刻字體、文字排版格式上與哈佛本相同,但内容發生了重大變化,除了删除哈佛本卷二處歐陽修、曾鞏、黄庭堅三人詩文選目外,還增加了卷四,其中包括一篇《詳詩髓論》以及六篇題解。綜而觀之,無論是《帖經舉隅》國圖三卷本、四卷本,還是前述上海圖書館所藏的《復初齋時文》,所增補的部分在論述風格上始終與全書文風保持統一,應是翁氏在初行本中未收録的文字,於後來的單行本中進行了增補。
以上時文兩種是翁方綱集中論述時文的著作,通過時文創作、時文題解以及相關論説等,向我們展現了成熟的時文理論體系。
二、 先河後海,或原或委——從經學到時文的思考理路
從明末至清末,時文家陸續對時文風格進行總結,或作階段性的劃分,或作種類上的判定,這無疑是基於時文曲折發展的客觀現實。時文風格的多樣化,其實意味着士子對時文理解的多元性。如錢謙益所指出:“有舉子之時文,有才子之時文,有理學之時文。”(2)(清)錢謙益:《牧齋有學集》,錢仲聯標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508頁。牧齋結合明代時文的發展,認爲在風格種類上可分爲三種,舉子之時文是其中的正宗。牧齋無疑是以行文風格、行文邏輯來作判定標準,但評價仍有一定局限,如認爲舉子之時文應當在“本經術、通訓故”的同時,摒棄時文機法;又如理學之時文的提出,則主要是顧及當時陽明心學的影響,而别立此一支。
從時文創作的行文風格、邏輯出發,我們認爲,將翁方綱的時文稱之爲學人之時文是不爲過的。學人之時文,既是在牧齋“舉子之時文”基礎上的修正,也彰顯出翁方綱作爲清代學人的個人特點。《清史稿》稱:“方綱精研經術,嘗謂考訂之學,以衷於義理爲主……所爲詩,自諸經注疏,以及史傳之考訂,金石文字之爬梳,皆貫徹洋溢其中。”(3)趙爾巽等:《清史稿·文苑二 翁方綱》卷四八五列傳二七二,中華書局,2003年,第13395頁。翁方綱精研經典,作文、作詩均宗於六經。雖然錢鍾書先生對翁方綱“學人之詩”(4)錢鍾書:《談藝録》“學人之詩”條,三聯書店,2013年,第462頁。評價不高,認爲翁氏乏詩才,却仍好以經籍潤飾詩篇。但其學人特質對時文寫作却極爲重要,如袁枚所説:“時文者,學人之言而爲言。”(5)(清)袁枚:《小倉山房詩文集》,周本淳標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771頁。士子學習時文,所學之人應上至孔孟,下逮周、程、張、朱,具體到時文寫作之中,援引經籍更是加分項。南橘北枳,翁方綱的學人特質在作詩範圍内顯得“水土不服”,但天然契合於時文領域。
學人之時文,本質上是以經學爲本,這裏包含了兩層含義:一是在具體寫作層面,士子在時文寫作中援引經典;一是在個人學習的價值取捨層面,士子應當宗於經典義理。當然,前者無疑是後者的自然流露。以經學爲本的基本邏輯始終貫徹在翁方綱的時文創作中。事實上,《復初齋時文》與《帖經舉隅》析以爲二,是由於内容的側重不同,兩書主旨却是統一的。翁方綱時文持論亦不離經典,因爲經學是時文的根柢,它决定着時文的深度與價值。
探賾學人之時文的具體内容,首先無疑要説明經典在翁方綱心中的地位。《復初齋詩集》卷三十三至三十八收録翁方綱督學江西時所作詩,單行本名爲《穀園集》,序言中説道:“是秋奉命視學江西,取夙昔瓣香山谷、道園二先生詩之義以名是卷。”(6)(清)翁方綱:《復初齋詩集》,清嘉慶刻本,卷三十三。以下詩句均引自該本,不再另出注。詩集名稱就暗含着翁方綱的價值取向。詩集以《發南昌述懷》十六首最爲重要,翁方綱以組詩的形式將督學三年的感悟進行了整體的回顧,前七首詩作主要表述個人主張,後九首則重在描繪江西風土。
在此不妨以《其五》詩爲例:
草廬及道園,文章皆理學。夫豈才筆騁,務與歐曾角。半山急用世,成就或醇駁。當其始學時,本亦勤切琢。士方茅屋居,往往見甚卓。履之乃知艱,境苦不自覺。正要翻覆看,方信志行確。平易初何害,質厚乃完璞。近人學三魏,格調襲煩數。端從肄經始,此事須商榷。
雖然從談藝的角度上看,這首律詩或許不入詩人法眼,但從研究個人思想的角度看,却爲研究其崇經主張提供了重要的論據。從該段表述中能發現,翁方綱例舉虞集、王安石等江西先賢,實則是以軒輊江西諸家的方式來表明自己的崇經主張。翁方綱無比推崇吴澄、虞集等江西理學家,原因便在於理學與經學關係密切。詩句中强調的“端從肄經始”,其實也是“以古人爲師,以質厚爲本”(7)(清)翁方綱:《漁陽先生精華録序》,《復初齋文集》卷三,道光丙申刻,光緒丁丑李彦章校,7a。的另一種表達。將經學視作學問的起點,這表明只有經學才被翁方綱視作第一流的學問。
《穀園集》帶來的還有文本之外的信息,翁方綱任職學政期間極力推重經典,與其學政身份以及個人治學理念密不可分。具體來看,首先是官方規章對學政履職的要求。乾隆三十八年(1773),《欽定學政全書》由禮部尚書素爾訥主持纂修而成,是書對學政的諸項職責進行了詳盡的規定,比如“崇尚實學”“厘正文體”“書坊禁例”等,在官方標準的規定下,學政無論是衡文課士,還是赴學宫講學,都必須積極履行官方要求。從翁方綱的履職結果來看,“在江西任内奏報歲試情形,申嚴月課一摺,約束武生一摺,申嚴場規、核實經古學一摺。皆蒙御批嘉獎並敕諭各省學政照依辦理”(8)(清)翁方綱撰,英和校訂:《家事略記》,清嘉慶刻本,46b。,所作所爲無不呼應崇實學以正文體的規章,可見翁方綱也是順應官方話語,作爲朝廷課士標準的代言人。其次是時代經學風氣與個人崇經心態的綰合。翁方綱推崇經學既是由於個人的治學傾嚮,也是當時學術界主流價值觀的體現。乾隆朝開始逐漸扭轉前朝推崇理學的風氣,並加以對實學的重視。結合翁方綱任職廣東學政的治學旨趣、四庫館臣的學術經歷等,可以發現他的治學路綫與時代大潮有着天然的契合。綜而觀之,無論是《欽定學政全書》的要求,還是自上而下的崇經觀念,都是中央話語與主流價值的體現。而翁方綱的治學旨趣、學政主張與時代主流相輔相成,其思想訴諸時文層面,必然是對經學旨歸的深化。
其次,論及從經學到時文的思考理路時,翁方綱主要採取兩種論述方式進行展開。一是從義理的闡釋角度找尋關聯。時文無疑與經典關係密切,甚至可以説是由經典直接推動而生。因此,他指出:“爲經學者當先從事於注疏,而後及於師儒百家之説。爲時文者當先研極於經傳,而後及於藝林流别之派。”(9)(清)翁方綱:《制藝江西五家論》,《帖經舉隅》卷二,清乾隆刻本,11a。一是從文體的發展歷程而論。時文是一種後起的文體,需要將時文與其他文體等而視之,按時間先後逐漸梳理出經學與時文的聯繫。結合其時文集進行細緻考索,便能發現他也站在文體的發展歷史的角度上,爲時文尋根溯源——以經典爲綱,構建起了文體發展的譜系。
《復初齋時文》中的《西江文體論》詳細闡明了從經學到時文的思考理路。翁方綱在《西江文體論》中品評了諸多人物,既有如馬端臨、鄱陽四洪等以學術聞名的大家,又包括羅萬藻、艾南英等時文名家。涉及的文人、文體看似繁多,在翁方綱眼裏其實都能用經典進行統攝。該文開篇談道:
古今文,未有不出於《周易》“有物”“有序”二言者。然物有本末,而序有原委,故吾嘗舉《禮》經之語以論文,曰:“先河後海,或原或委。” 此即摯虞《流别》之義也。(10)(清)翁方綱:《復初齋時文》,清乾隆刻本,86a。
“先河後海,或原或委”,出自《禮記·學記》,意味着爲學、爲文要探清源流。翁方綱隨後從經學(包括理學)、史學、詩學等方面進行了論述,認爲後起的文體均發端於經典。比如在古文方面,翁方綱由虞集追溯到曾鞏等宋代古文大家,認爲“經術之氣必以南豐爲至焉。南豐之文,蓋出於班孟堅,而孟堅所次劉向、匡衡、李尋、翼奉諸人,皆經術之文也”(11)《復初齋時文》, 87a。所謂的“經術之文”,正指向了文之起源。
蘇齋以逆推的手法描述了文體發展的歷程,並確立了文章的正統。這種正統指的並不是某種文體,也不是某種具體的創作手法,而是一種融匯在文章創作中的觀念。何惺庵對此作出了評價:
“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聖賢文章,從心寫出,故文便是道。”至哉紫陽之言!……此所謂載道之文。願承學者,毋徒奉爲制藝律也。(12)《復初齋時文》, 87b。
“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語出《朱子語類·論文》。翁方綱持論不悖朱熹,在於他認同朱熹鑽研經典義理的態度。朱熹曾批評這樣一種寫作現象:“今人作文,皆不足爲文。大抵專務節字,更易新好生面辭語。至説義理處,又不肯分曉。”(13)(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論文(上)》,中華書局,1999年,第3318頁。翁方綱亦曾批評捨本逐末的時文寫作現象,“(士人)即帖括依經爲之,而亦好用奇字僻事,忘其初入家塾之舊業,則逐末而失其本者衆也。”(14)(清)翁方綱:《樹蘭齋時文序》,《復初齋文集》卷四,道光丙申刻,光緒丁丑李彦章校,23a。由此,“先河後海,或原或委”的觀念便更爲清晰,只有沉潛經文,時文方有根柢。從文體發展來看,時文雖然産生較晚,却是依附六經而生。時文的義理與經典相通,以文載道,以時文彰顯經學的價值,這也是時文應有之義。
三、 文氣·機法·詞章:翁方綱時文持論的多維性
先經傳後時文的思考理路,無疑爲翁方綱時文理論的形成提供了嚴密的邏輯基礎。具體到時文理論層面中,翁方綱則將其精髓進行了深入的闡釋,也向讀者展現了其時文理論的系統框架。
(一) 沉潛經術,涵養文氣
以氣論文一説,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是個令人矚目的命題,時至今日依然有值得討論的空間,如郭紹虞先生就以分階段的形式分析術語内涵的流變(15)郭紹虞:《照隅室古典文學論集》,《中國文學批評史上之“神”、“氣”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46頁。,有的學者則從文學創作的内在心理和外在形式探討了文氣(16)熊湘:《古代文論範疇“氣”與“脉”之關係探賾》,《文藝理論研究》2013年第4期。。雖然在文學史的主流書寫中,有關文氣的論述鮮有涉及時文領域。但當我們對明清别集、文話等相關材料進行梳理時,能明顯發現“文氣”一詞既廣泛運用於古文理論處,也是論述時文的重要術語,以下兹舉數例。
湯賓尹論制義時指出:“杜牧之論文以氣爲主,蓋氣和則文平,氣充則文暢,氣壯則文雄,氣清則文貴,氣豪爽則文逸宕,然此不可旦夕計效也。”(17)(明)湯賓尹:《湯睡庵太史論定一見能文》,見《稀見明人文話二十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874頁。萬曆時黄汝亨也談道:“文之有氣,如人身之有血脉,壅則病矣……心清學術端,則爲醇正之氣,躁心淺見,則爲浮邪之氣,其需於氣則一。”(18)(明)武之望撰,陸翀之輯:《新刻官板舉業卮言》,見《稀見明人文話二十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14頁。艾南英在針砭明季時文更是指出:“古之至文未有不以氣爲主者,氣有斷續而章法亡矣。氣之斷續非不能文者犯之,文而巧俊者犯之也。”(19)(明)艾南英:《陳興公湖上草序》,《天傭子集》,《明别集叢刊》第五輯,清康熙張符驤淳如堂刻本,第178頁。針對明季時文悖理程朱傳注、一味追求奇詭的現象,艾南英認爲要以“渾樸之氣行乎其間”,以此來拯救萎靡文風。清初吕留良論述時文時也談道:“文以氣爲主,有氣方能曲……文無遒蕩迤演之氣,囚瑣媕娿,皆行尸坐魄耳。”(20)(清)吕留良:《吕晚村先生論文匯鈔》,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477頁。以上四家,前二者是論述文、氣間的聯繫,後二者則是針對文風不振的現狀,强調氣對於作文的重要性。
與艾南英、吕留良境况相似,翁方綱在論述時文中提出“養氣”一説,也是針對時文寫作的積弊。《讀書養氣説》談道:“使者來視江右學政,屢言文之積敝,而文之所以敝未之剖析也……則姑舉蘇子叙歐陽文所説者,曰‘論卑氣弱’而已。夫論之卑,氣之弱,非一日之病也,積漸使之然也。”(21)(清)翁方綱:《帖經舉隅》卷三,清乾隆刻本,17b。點出了正是由於文氣極弱,才導致時文格調不高的結果。而如果認爲改善機法便能提高文氣,則又是取徑失當,是“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則其病益以滋蔓,而治之而益難”,如果没有從根本上作改變而徒飾浮詞,所作文章依然顯得空泛。如何從根本上培養自身文氣?《讀書養氣説》進一步點出:“必沉潛善下者,而後論可望其勿卑,必静虚善養者,而後氣可期其勿弱……今日之俄頃,他日之積久也,今日之小得,他日之大成也。江西士人,今日之病,蓋在於不讀書,而其所以病,在於心不能入。”(22)《帖經舉隅》卷三, 17b。翁方綱以批判的口吻説出解决之道,認爲只有沉潛經典才能有所提高。
時文創作有其特殊性,唯有將經典爛熟於胸,才能在風簷寸晷中回憶起題目的前後文本,也唯有平素涵養文氣,才能在考場中厚積而薄發。翁方綱於《復張瘦同論聯句書》中談道:“今日讀書考證之學其多且難,已倍於古人,而説經訂史之文,又不可闌入詩句,既不欲多涉議論,又不欲沾滯文字,又不欲空拈風雲花月,則將如何而可乎?其必有深潛博厚之氣,獨出於古人之所已得與古人之所未言者。”(23)(清)翁方綱:《復張瘦同論聯句書》,《復初齋文集》卷十一,道光丙申刻,光緒丁丑李彦章校,26a。時文何嘗不是一種“説經之文”,同樣的道理,學子只有培養自身的“深潛博厚之氣”,才能對經義進行深切的闡發。在《貴溪畢生時文序》中,翁方綱更以“清粹之氣”“江山精氣耿耿”來稱讚深究經術之人所撰寫的時文,對該類文章的品格表示高度的讚揚。通過沉潛經術,涵養文氣找到了具體的操作方式,也從抽象的理論轉化爲具象的寫作指導、評價標準。
(二) 根柢經術,機法並行
談及時文創作,往往離不開時文機法,時文家對機法的態度有褒有貶,這離不開他們所處的時代環境。比如在明末清初時文家眼中,機法始終是一個敏感的詞匯。王夫之曾談道:“無法無脉,不復成文字,特世所謂‘成弘法脉’者。”王船山極力駁斥文章成法,認爲“有皎然《詩式》而後無詩,有八大家文鈔而後無文”(24)(清)王夫之:《姜齋詩話》,舒蕪點校,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第169頁。。明季陳龍正也提到:“若脉、法二言,惟可神會。文安有脉?題至則脉隨之;文安有法?意至則法隨之。謂文之至者,法、脉自具可耳,謂以法、脉成大家,何其隔歟?”(25)(明)陳龍正:《幾亭外書》,《叢書集成續編》第173册,上海書店,1994年,4b。艾南英指出:“今之爲制舉業法者,非國初制也,而士皆去彼取此,曰:‘是今日有司之法度也。’”(26)(明)艾南英:《萬永師近藝序》,《天傭子集》,《明别集叢刊》第五輯,清康熙張符驤淳如堂刻本,第162頁。清初吕留良亦説道:“法脉出落,不可不講。然無蒼秀氣骨,而著意於此,以爲老練,其老練處正是惡俗處。”(27)(清)吕留良:《吕晚村先生論文匯鈔》,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475頁。明季制義文風大壞,王夫之、陳龍正、艾南英、吕晚村等人均針對時文悖離程朱的現狀提出批評,無論是使用文法、以巧取勝,還是雜入百家雜説、六朝偶語,亦或爲坊間俗見蠱惑、隨意作文,都只是這期間文風大壞的一個側面。在這裏,機法只是作爲標靶,時文家往往超出一般性的文學層面而進一步進行針砭,力圖聯繫文風、士習乃至國運三者進行更深層次的解讀。
時運交移,清乾隆朝時局穩定,《復初齋時文》《帖經舉隅》的編選初衷是作爲時文寫作指導用書。翁方綱在《蔣春農文集序》談道:“予嘗謂爲文必根柢經籍,博綜考訂,非以空言機法爲也。”這既是對他崇經觀念的説明,也反映出他對作文機法的重視。對於身處考場的士子來説,要想在諸多限定條件下完成品質尚佳的作品,就不能不牽涉時文寫作機法。
時文寫作首在認題,這其中既包含了對題目所含義理的理解,也包括該以怎樣的論文框架進行論述,這種論調在明清兩代時文大家的論述中屢見不鮮,翁方綱亦是如此,《送張肖蘇之汝陽序》中就談道:“時文之法,在於審題,題得而理定,理定而法生焉,其但務古調以震駭於人者,猶之浮詞也。”(28)(清)翁方綱:《送張肖蘇之汝陽序》卷十二,《復初齋文集》,道光丙申刻,光緒丁丑李彦章校,10b。如果審題不清,只想以詞氣打動考官,也只是一篇不合格的制義文章。
要達到審題清晰,首先要能辨認題目所含之義理,否則會出現義理謬誤的硬傷;其次,則是因題而定法,也即用什麽樣的行文邏輯來闡釋題理,或用考證而行文,或從虚字找實字以行文等等,機法不一,但均是由題而來。《帖經舉隅》集中探討了時文題解,大題、小題、長題等都有所闡發。在這之中,尤以截搭題難做,也極易認錯題目而誤用吊、伏等機法。翁方綱在《論〈陳其宗器,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題》中,就對認錯題目而亂用機法明確指出批評:
法必從理生,而理從題出,五載以來,使者日久諄諄與學人研切經義,冀其深心體認古人語言意味……至於二節、三節之書,中間抽截出題者,總須相其理脉神致,斷不可鈎棘字句,挑剔一二字以爲清題位。致如搭題之吊、渡、挽者,則將混長題、搭題爲一例,俱目爲機巧串合之法,此則大有關於學術之淳漓,文體之正衰。(29)《帖經舉隅》卷一,8a。
是題出於《中庸·第十九章》,乍看是一個典型的搭題,翁方綱認爲雖然按例屬於截搭題,但題句神理完整,士子依然可以按文勢而説下,只是在“其聯合機致之處,又必運以古文之波瀾意度”,也即在過文處,用一二散語作過接,而不是單純因題目的形制而仿效機法。同時,翁方綱又對坊間時文空言機法而導致審題謬誤的弊端進行了批評,如“‘春秋’二節分時祭、祫祭之説,久經前人駁正……而俗塾教師,舉眼但見題句,遂乃認爲時祭,又因下節有‘群昭群穆’句,認爲祫祭。訛以傳訛,所以學者皆不知體味古書神氣,不善會古人語言,因陋就簡而莫之省。”(30)《帖經舉隅》卷一,7a。時文要闡發的義理必須緊緊圍繞所出之試題,翁方綱在全書中多次强調,“文從法生,法從理生,理從題出,全在虚心涵泳”“每勸士子作文,先須研求義理,而理即在題中,不煩外索,其舍此而空言機法者,皆大誤也”“渾然天成之法度,未有不從題理中出者也”等等,足見其用心良苦。
如艾南英指出:“道一而已,而法則有二焉。有行文之法,有御題之法。”(31)(清)戴名世:《己卯行書小題序》,《南山集》,《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41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第99頁。除前述認題定法之外,在行文之法方面,翁方綱又提出“前偏後伍、伍承彌縫”的行文機法。“前偏後伍、伍承彌縫”一詞出自《左傳·桓公五年》,原指兩軍對壘時的佈陣之法,杜注:“《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爲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缺漏也。五人爲伍。此蓋魚麗陣法。”楊伯峻先生進一步説明:“伍之左右在於承偏之隙而彌縫缺漏。”(32)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第一册,中華書局,1981年,第105頁。通過這種方式,車陣與步兵融合成一個更緊密的整體,以兵法喻文法,翁方綱以此來形容時文的整體佈局。如在《論〈入雲〉二字題》中談道:“‘然’字意已到下節,而‘弗與共之’三叠仍完繳上節,此則前偏後伍、伍承彌縫之大章法。”(33)《帖經舉隅》卷一,10b。是題出自《孟子·萬章》,原文較長不録,但翁方綱使用這條術語的指向性已然十分清晰,即在該題下,對題前一些字句的闡釋要能暗示到題後,而對題後字句的解讀要能照應到題前,前後勾連,渾然一體。
這種做法在截搭題中也時常用到,如《君子易事而難説也。説之不以道,不説也》一題,作爲一個典型的上全下偏題,翁方綱所作之時文便行以前偏後伍、伍承彌縫的機法。在該篇時文中,先在承題中承接“難説”,則將題中“不説也”牽連而出,而在後之八比中,則是按題理娓娓道來,先説易事之因,難説之由,進而以過文點出“道而已矣”,整篇時文如夾批所言“通篇直如一句”。雖然在該題時文的作法中,直接按題理順序説下亦可,但顯得較爲平衍,如果用這種魚麗之法,則能讓文章平地起波瀾,頗有古文神氣。
以上不過略舉翁氏時文機法之兩例,時文機法由來已久,明代時文家已是創制頗多,但其實一本萬殊,首先是要認清題中義理,之後再因題定法。翁方綱不摒棄機法觀念,正是建立在他堅守經典義理的基礎上,如此作文,文氣多歸於醇實,也是時文寫作之正脉。
(三) 篤守經術,不悖詞章
對於時文的理解,翁方綱並不是偏執一隅。《吴懷舟時文序》中談道:“有義理之學,有考訂之學,有詞章之學,三者不可强而兼也,况舉業文乎。然果以其人之真氣貫徹而出之,則三者一原耳……然吾有以語吴生者,研理者喜深入而疏於博綜,嗜博者又多騁奇秘而遺坦途,是二者厥失均也。”(34)(清)翁方綱:《吴懷舟時文序》,《復初齋文集》卷四,道光丙申刻,光緒丁丑李彦章校,20b。又如《蛾術集序》中所説:“士生今日經學昌明之際,皆知以通經學古爲本務,而考訂詁訓之事與詞章之事未可判爲二途。”(35)(清)翁方綱:《蛾術集序》,《復初齋文集》卷四,道光丙申刻,光緒丁丑李彦章校,17b。在此,翁方綱將義理、考證、詞章三者視爲寫好時文的重要標準,偏廢其一都有所抱憾。
進一步來看,在翁方綱調和漢、宋學説的持論之下,考訂又是爲義理服務。《附録與程魚門平錢、戴二君議論舊艸》是翁方綱論述漢、宋學的重要文章,所作背景便是錢載與戴震——兩位宋、漢學代表産生了激烈的衝突。文中説道:“訓詁名物豈可目爲破碎,學者正宜細究考訂詁訓,然後能講義理也。宋儒恃其義理明白,遂輕忽《爾雅》《説文》,不幾漸流於空談耶?况宋儒每有執後世文字慣用之義,輒定爲詁訓者,是尤蔑古之弊,大不可也……故吾勸通知者深以考訂爲務,而考訂必以義理爲主。”(36)(清)翁方綱:《附録與程魚門平錢、戴二君議論舊艸》卷七,《復初齋文集》,道光丙申刻,光緒丁丑李彦章校,20b。可見,考證與義理都是爲了發明經義,流於瑣碎或漸入空談都是失當的。認識到這點,回歸翁方綱的時文持論中,便能發現義理、考證、詞章三者其實轉化成了篤守經術、不悖詞章,經義闡釋與文章詞氣應當並駕齊驅。
具體到時文的詞章之説,翁方綱則將其與古文的散體文風聯繫起來。他指出:“今如教人爲時文,則必篤守傳注之人以爲之師,精研史漢唐宋諸家義法之人以爲之師,則雖一帖括,而漸可以得爲文之本矣。”(37)(清)翁方綱:《擬師説(二)》,《復初齋文集》卷十,道光丙申刻,光緒丁丑李彦章校,8a。篤守經術的同時,又要研習古文義法,如此方能得到“爲文之本”。在《論〈孔子之去齊至遲遲吾行也〉題》中他又談道:“此必平日深悟古文章法,而後知之,所以每勸學者必多讀古文,而後精於時文之法也。”始終强調熟讀古文的重要性。事實上,無論是煉字遣詞,還是對文章結構的整體佈局,古文都有可兹借鑒之處,這在文論家眼中已是共識。(38)限於篇幅,兹不從明清文話中羅列例證。關於時文借鑒古文的論調,當代學者也有相同見解,如吴承學《中國古代文體形態研究》“明代八股文”一章、蔣寅《科舉陰影中的明清文學生態》等。
在這裏又牽涉時文創作中一個重要領域——以古文爲時文。正如雷鋐所言:“文必根於經,達於史,浸淫於唐宋大家,而濬導於濂洛關閩之學脉,則言之有物,皆一心之貫注……以古文、時文爲二道,非知者言。”(39)(清)王步青:雷鋐所作《序》,《己山先生文集》,清乾隆刻本,1b—2a。表明古文、時文未可斷然區分。事實上,用古文作時文,自明代歸、唐二人以來已是屢見不鮮,但是採取這種做法,對於學力深厚的士子來説固然可以,對於不深究經典的人來説,却只是習得皮毛。鑒於當時慣用散體來代替八比做法的風氣,翁方綱於《文體論》中給予了較爲明確的説明,對古文散體保持着一種謹慎的鼓勵態度,《文體論(上)》談道:
至於散行者,特文中之一體,必其平日服習古籍,真氣充塞,而後偶一爲之。然亦必具有史漢韓柳諸家氣味格律而後可,如其氣稍弱則不敢,議稍卑則不敢,詞稍平則不敢,蓋散行之難,百倍於對比也。乃近日坊間時文選本,不知始自何人,忽倡爲化板爲活之説,有於起講下省去提比直作一段者,甚至於提比下不作中二比,直用一段散行,而後以兩後比足之者。嘻!其有害於文體豈細哉!夫文以載道,而法從理生,時文名曰經義,是爲聖經而作,代孔孟立言,其事綦重。若以古文格律論之,尚在記、序、論、説之上,其托體如是之尊,而顧可以翻新之説誤之乎?”(40)(清)翁方綱:《文體論(上)》,《帖經舉隅》卷三,清乾隆刻本,14a。
是説高度評價了時文在諸文體中的地位,作爲解經之作,其重要程度甚至超過了記、序、論、説——這些古文家闡發個人思想的重要文體。同時也表示出掌握古文散體寫作的困難性,古文寫作是展現個人才思的一種方式,但是又極易落入空發議論,失之輕弱的境地,只有深切理會經義,才能駕馭散行古文。在《復初齋時文》中,翁方綱便有文章是純用古文散行來闡發義理,如《古之道也爾愛其羊》,全文雖用散體,却結構嚴密,足見翁氏亦是在踐行着這種篤守經術、兼重散體的時文寫作觀念。
四、 刊落險怪:對江西時文的批評
翁方綱一生以文學清華之職,多次出任鄉、會試考官和地方學政,《復初齋時文》《帖經舉隅》兩種時文著作,便是他於乾隆五十一年(1786)出任江西學政時所編著。通常來看,衡文課士是學政的常規職能,學政以圖書實物的形式將個人所認定的時文正格展示出來,則又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但歷史事實往往是復雜的而並非單綫度的,一件事實的出現可能是多種元素的合力,翁方綱的兩部時文著作同樣也是如此。當我們將視野放寬,便能發現翁方綱在督學江西期間將其時文理論以圖書的形式刊出,既是多年來時文思考的總結,也具備極强的現實針對性,與此時江西時文風尚有着莫大的關聯。
明代以來,衆多江西士子登瀛洲、入館閣,科名之風盛於江西。明代成弘時丘濬談道:“國朝文運,盛於江西,開國之四年,策士以問,即得掄魁於金溪……會試天下士,裒然居首者,分宜人也。”(41)(明)黄佐:《翰林記》,傅璿琮、施純德編《翰學三書》,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76頁。至如明季,由於江西五家的出現,更是讓江西成爲時文創作、時文批評一大重鎮。艾千子自謂:“予與陳大士、羅文止三人者起而振之,以《易》《詩》《書》《禮》《樂》之言代《語》《孟》之文,以古雅深醇之詞洗里巷之習,一時後輩從風丕變。”(42)(明)艾南英:《王子鞏觀生草序》,《天傭子集》,《明别集叢刊》第五輯,清康熙張符驤淳如堂刻本,第174頁。足見江西五家對當時制義文風的影響。進入清代,江西五家的影響依舊存在,既有稱頌五家者,又有批評五家者。如袁枚談道:“金正希、陳大士與江西五家,可稱時文之聖者。”(43)(清)袁枚:《隨園詩話》卷八,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第267頁。而在同一時期,澎湖通判胡建偉則談道:“惟有一種艱深怪僻者,以妄誕爲新,以判道爲超脱,何異病入膏肓……凡此者,皆托名江西派一説以誤之。夫江西五子之文,或意在筆先,或神遊題外,自成一家機杼,然按之題位、題理,依照一絲不亂,此文之所以可貴而可傳也。今人既無此本領,但剽竊險怪字句。”(44)胡建偉:《文石書院學約》,見鄧洪波主編:《中國書院學規》,中西書局,2011年,第1753頁。而在翁方綱調任江西後,於時文集、詩文集中多次談到江西時文的特徵,其中的春秋褒貶也頗能反映出個人的微妙心態。這其中最顯著的例證莫過於《制藝江西五家論》,翁方綱在該篇中專門討論籠罩在江西五家陰影之下的江西時文風氣,他指出:“今日江西士習文體,漸入於浮膚矣,所以審其弊而救正之者,果必以五家歟?夫經訓之文,以和平怡愉爲主,而五家之文,幽者,峭者,險而肆者,各詣其極而惟變所適也……吾又懼學人不善用之,而惟才力之是騁矣。”(45)(清)翁方綱:《制藝江西五家論》,《帖經舉隅》卷二,清乾隆刻本,10b。在此,翁方綱站在學人之時文的立場上,批判性地看待江西五家。江西五家在此被立爲標靶,不僅是因爲其幽峭險肆的時文風格與經訓之文相悖,翁方綱更對在江西五家影響下,士子唯才是騁而落入險怪的文風表示不滿。
如吴承學先生指出:“地域的文化氛圍和傳統,無疑對本地域的作家起着强烈直接的影響。所以同一地域的作家容易産生相近的審美理想。”(46)吴承學:《江山之助——中國古代文學地域風格論初探》,《文學評論》1990年第2期。在時文方面,由於明末江西五家珠玉在前,江西士子習文常常仿效,却又容易走上彎路,艾南英早已意識到這點,他認爲:“而四家之中亦有樂其纖詭靈俊,偶一爲之者,則於所謂辭又有不盡純焉,雖力追古文者,時時非之。”(47)(明)艾南英:《四家合作摘謬序》,《天傭子集》,《明别集叢刊》第五輯,清康熙張符驤淳如堂刻本,第170頁。晚清夏曾佑回溯時文流變時,也指出:“金壇六子爲一派,出於明之西江五子,其文高曠幽眇……及陋者爲之,則趑趄囁嚅,語多不辭。”(48)夏曾佑:《夏曾佑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4頁。“高曠幽眇”的風格本身就與“清真雅正”的標準相去甚遠,更何况如有才力不及者作文,則斯爲下矣。有鑒於此,翁方綱便專門撰以《制藝江西五家論》等文進行批判,離任之際,又在《發南昌述懷·其六》詩再作補充:
時文體屢變,前輩稱五家。後來紛摹擬,踵事何陋耶。臨川陳與章,純瑜粹無瑕。觀者但驚絶,異彩揚天葩。文之淡彌旨,咀腴擷其華。彼哉貌襲取,一瞬千里差。從此問歐曾,若海由津涯。士病氣亦驕,奚以洗淫哇。所視夙夜養,豈在礱斫加。漸使胸有書,庶望思無邪。
結合前引詩作,可以發現《發南昌述懷》十六首實則作爲一面鏡子,既表明翁方綱對江西險怪文風的批評,更將其學人之時文的主張折射出來。不難看出,至少在乾隆朝後期,明末江西五家依然在時文領域極具影響力,五家的時文以及時文選集甚是爲江西士子看重,但江西五家“纖詭靈俊”“高曠幽眇”的文風實則是“鄭聲”,並非“雅樂”。江西士子“貌襲”該種文風,只會是南轅北轍。面對這種境况,翁方綱試圖將這種向心力進行扭轉,在詩集中多處談到“崇實學”(《南昌學宫摹刻漢石經殘字歌》)、“貴於經術”(《題盱江書院壁》)。又在時文集中多次批評士子不鑽研經典原文,徒飾浮華,要求士子的注意力從江西五家的時文回到六經原文,沉潛經術,以古雅爲宗。既正面提出學人之時文的主張,又對險怪的江西時文風尚提出批評。
《復初齋時文》《帖經舉隅》是翁方綱學人之時文觀念的體現。借助於兩書,翁方綱將其長久以來關於學人之時文的思考進行了系統總結。同時,如王步青所言:“文之盛者,大都義法謹嚴,體氣深厚,而其衰者,率由蹈虚摭寔,兩家輾轉,於浮靡姿媚之相,尋而爲大雅所屏棄。”(49)(清)王步青:《題程墨所見集八》,《己山先生别集》卷二,清乾隆刻本,10b。由於“浮靡姿媚”的江西時文風尚恰好站在“體氣深厚”的學人之時文的對立面,在正、反兩個因素促使下,翁方綱便有心以圖書的形式推出他所認定的時文正格,以學政的名義將時文理論進行廣泛的展示,期望江西制義文風得以改善。
從《欽定學政全書》的規定來看,圖書刊刻對於學政來説,是一項非常規的職責,但刊刻著述依然有着典範性意義,如翁方綱督學廣東時刊刻的《粤東金石録》、阮元督學浙江時刊刻《經籍纂詁》等,既表明了學政的治學興趣、態度,也對當時士子的讀書、作文等起指導作用。從刊刻結果來看,我們看到,《復初齋時文》與《帖經舉隅》版本的更迭,内容的增删,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時文集在士子群體中良好的接受情况。刊刻時文既是對翁方綱的時文理論的認同與發揚,也將江西時文傳統進一步進行了延續。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圖書刊刻)甚至建立起了提學名宦與地方文脉之間的親密聯繫。”(50)葉曄:《提學制度與明中葉復古文學的央地互動》,《文學遺産》2017年第5期。這兩部時文也使得翁方綱在江西時文文脉的傳承中佔據了一席之位。兩部刊刻的時文,對於江西時文觀念的洗禮,無疑是影響深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