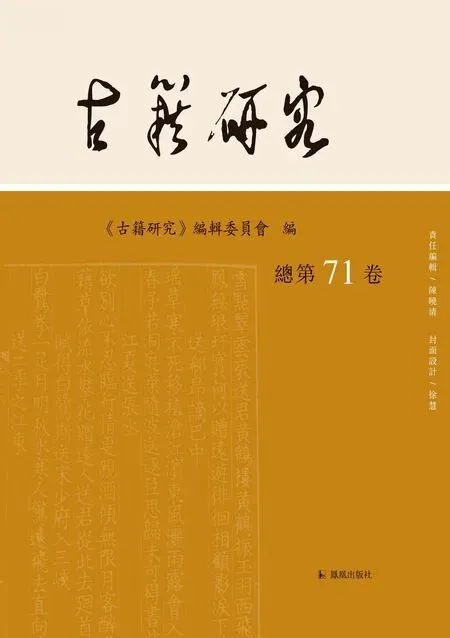《韓昌黎文集校注》校點錯訛舉隅*
吴欽根
關鍵詞:《韓昌黎文集校注》;校點;錯訛
韓文至宋代而大盛,學者非韓不學(1)(宋)歐陽修撰,洪本健校箋:《歐陽修詩文集校箋·外集》,卷二十三《記舊本韓文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927頁。,由此而衍生的韓集注本亦不勝枚舉,有所謂“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韓”之説(2)杜詩有黄希、黄鶴補注《黄氏補千家集注杜工部詩史》,徐居仁編次《集千家注分類杜工部詩》,韓文有魏仲舉《新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 》等。。而在這些名目繁多的韓集注本中,又以方崧卿、朱熹校理本最爲通行,此後王伯大《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廖瑩中世堂本《昌黎先生集》等均屬此一系統。至明代,徐時泰復用世堂本翻雕,以朱子校本考異爲主,而删取諸家要語,附注其下,即所謂東雅堂本。此本因刻印精良,最爲通行於後世。陳景雲《韓集點勘》、王元啓《讀韓記疑》、方成珪《韓集箋正》等均以此爲底本。馬氏此本亦以東雅堂本爲底本,朱筆細字,博取諸家校語、評點,書於行間眉上。其中評點以桐城派諸大家,如方苞、姚範、劉大櫆、姚鼐、曾國藩、張裕釗等爲主,大部分屬内部批本的過録,至爲寶貴;而校理則廣泛吸收了沈欽韓、陳景雲、方成珪等諸家成果,沈氏《韓集補注》更爲初注稿本,多數校語爲刻本《補注》所未收(3)沈欽韓《韓集補注》有光緒十七年(1891)廣雅書局刻本,收録於《叢書集成續編》第100册。又沈氏批本見存者,有國家圖書館藏東雅堂本《昌黎先生集》、南京圖書館藏《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韋力私藏秀野草堂本《昌黎先生詩集注》等。,可謂徵引繁富。此本1957年由古典文學出版社首次斷句印行,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出版了首個分段標點本,2014年再版,是現今最爲流行的韓集注本之一。然由於徵引上的博贍,加上韓文本身文辭奥博,以及校語多出手書等原因,錯訛之處在所不免。今筆者一以明徐氏東雅堂原刊本(簡稱徐本)爲據,參以廖瑩中世堂本《昌黎先生集》(簡稱廖本)、方崧卿《韓集舉正》(簡稱《舉正》)、朱子《韓文考異》(簡稱《考異》)、宋蜀刻本《昌黎先生文集》(簡稱宋蜀本)、魏仲舉《新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簡稱魏本)、王伯大《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簡稱王本)諸本,互爲比勘,其不能無疑者,爲之詳加羅列,以就正于大方之家。
1. 或從閣杭苑作可,云可人,見禮記鄭注曰:“此人可也。”(頁32)
按:標點有誤,當作:“或從閣、杭、《苑》作‘可’云,‘可人’,見《禮記》鄭注,曰:‘此人可也。’”
2. 孫樵又與王霖書曰:玉川子《月蝕詩》、楊司城《華山賦》、韓吏部《進學解》、馬常侍《清河壁記》,莫不拔地倚天。(頁50)
按:徐本無“楊司城《華山賦》”“馬常侍《清河壁記》”十三字,當是校註者據《孫樵集》卷二《與王霖秀才書》一文增補。且馬當作馮,馮常侍即馮宿。馮宿,字拱之,東陽人,敬宗朝嘗官左散騎常侍,新舊《唐書》均有傳。《清河壁記》今不存,《文苑英華》卷八百二十五、《唐文粹》卷七十四載有其《蘭溪縣靈隱寺東峰新亭記》一文。
3. “顯”,或作“白”,《舊史》四句皆無“而”字。(頁54)
按:“白”,徐本作“洎”。陳景雲《韓集點勘》云:“按:‘泊’字與‘顯’字義絶不相近,恐是‘白’之誤,‘白’作‘泊’,後又轉訛爲‘洎’耳。”(4)(清)陳景雲:《韓集點勘》,卷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075册,第557頁。馬氏蓋據此校改。考《莊子》卷九《寓言》:“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郭象注云:“洎,及也。”(5)(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卷九,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下册,第946頁。則“不洎於衆”即“不及於衆”,義近於“不顯於衆”,不得言絶不相近。宋蜀本及《考異》正作“洎”,又《册府元龜》卷七百七十所載亦作“洎”,均可爲證,不煩校改。
4. 《太玄經》亦曰:山川褊庳而禍高。(頁54)
按:“褊”當作“福”,魏本、廖本同。《四部叢刊》景明翻宋本《太玄經》亦作“福”。是。
5. 沈欽韓曰:司馬彪注《莊子》云:豕橐,一名岑,其根如猪矢。(頁55)
按:“岑”當作“苓”。司馬彪《莊子注》早亡,沈氏所引當出於他書。考《太平御覽》卷九百八十六藥部六“猪苓”條所引司馬彪注文正作“苓”。“岑”爲“苓”之形誤。
6. 頸,或作頜。(頁58)
按:頜,徐本作領,魏本、廖本及《考異》同。所屬正文爲“朝夕舉踵引頸”,或作“領”者,所謂引領而望也。
7. 呶,音饒。(頁63)
按:饒,徐本作“鐃”,魏本、廖本及《四部叢刊》景元本王伯大《朱文公校韓昌黎先生集》(簡稱王本)同。當是形近而誤。
8. 何焯曰:《潛夫論》本傳著其五篇:曰《浮侈》、曰《實貢》、曰《貴忠》、曰《愛日》、曰《述赦》。(頁66)
按:《潛夫論》後當讀斷。意謂《後漢書》本傳載其《潛夫論》中五篇也,見《後漢書》卷四十九。
9. 方又云:康駢《劇談録》謂公此文因元稹而發,董彦遠謂賀死元和中,使稹爲禮部亦不相及争名,蓋當時同試者。(頁67—頁68)
按:“使稹爲禮部”以下標點有誤,當斷爲“使稹爲禮部,亦不相及,争名蓋當時同試者”,方文從字順。所謂“不相及”者,元稹爲禮部在長慶初,賀已故去久矣。
10. 安或作知云,此以教葉僑與囂,《車牽》詩用韻如此。(頁76)
按:“云”字當屬下讀。《考異》云:“安或作知,方云此以……”,可知“云”以下爲方崧卿語。書中類此者尚多,如“‘遲’,諸本作‘違’,今從閣杭蜀苑云。《新史》與《文粹》作‘依違’,以意改也。”(頁136);“‘以吾’,或作‘以餘’。今從閣蜀本云,除下文‘江湖予樂也’一語,餘並作‘吾’。”(頁153);“‘移族從’以下八字,閣杭本如此云。頔世雄朔易……”(頁165);“‘於古’,閣作‘於吾’云,或作聞,而無邪字。”(頁277);“‘洛師’,或作‘洛陽’。‘及鄭’,或作‘反鄭’云。此序疑作‘於鄭’。”(頁280);“‘階’下一本複出‘即客’二字云,《文粹》亦有即字,則知古本誠然也。”(頁297)等。均當正之。
11. “若干”,或作“著干”。“獻”下或有“之”字。今按:“‘著干篇’雖古語,然施之於此,似不相入。”(頁77)
按:兩“著干”字當作“著于”。“著于”見於秦漢典籍如《晏子春秋》《史記》《漢書》等頗夥,故云古語。徐本及《考異》均作“著于”,當正之。
12. “敵以”,或作“敵已”。《國語》,“自敵以下則有讎”。注“敵體也”,今人多用“敵已”字者,非。(頁78)
按:兩“已”字,諸本或作“已”、或作“巳”,刻本於此三字多混刻,疑當作“己”,《考異》正作“己”。“敵己”見於《列子》,所謂“天下之敵己者,一人而已。”(6)楊伯俊:《列子集釋》,卷五《湯問篇》,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193頁。朱子亦屢用之,如《朱子語類》卷一百一云:“明仲甚畏仁仲議論,明仲亦自信不及,先生云人不可不遇敵己之人。”(7)(宋)朱熹撰,黎靖德編次,王星賢校點:《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第7册,第2582頁。又卷一百七云:“先生于父母墳墓所托之鄉人,必加禮,或曰敵己以上拜之。”(8)《朱子語類》,第2674頁。另宋杜范《回丞相劄子》亦云:“温詞曲論,開曉諄諄,若施之敵己者。”(9)(宋)杜範:《清獻集》,卷十五,《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175册,第732頁。又《宋史》卷三百七十二《沈與求傳》云:“與求歷御史三院,知無不言,前後幾四百奏。其言切直,自敵己已下,有不能堪者。”(10)(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第33册,第11542頁。另柳宗元《先太夫人河東縣君歸祔志》亦云:“尊己者敬之如臣事君,下己者慈之如母畜子,敵己者友之如兄弟,無不得志者也。”(11)(唐)柳宗元撰,吴文治等校點:《柳宗元集》,卷十三,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1册,第326頁。韓柳同時,且所言語意相近。均可爲作“己”之證。
13. 今鄧州有淅水縣,以淅水得名。(頁94)
按:上“水”字,徐本作“江”, 廖本、王本同。《舉正》《考異》作“川”,魏本引樊汝霖説亦作“川”,無作“水”者。考《宋史》卷八十五《地理志》鄧州下有淅川縣,又宋歐陽忞《輿地廣記》云:“淅川縣,本後漢南鄉縣,魏置南鄉郡,晋改爲順陽郡,後魏復爲南鄉郡,又分置淅川縣,後周省之。隋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置淅陽郡,其後淅陽及南鄉縣皆廢焉。五代時復置淅川縣,屬鄧州。”(12)(宋)歐陽忞撰,李勇先、王小紅校注:《輿地廣記》,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74頁。知作“川”字爲是。
14. 《舊唐·禮儀志》云:田再思議曰:改葬之服。鄭玄服緦三月。(頁128)
按:徐本“三月”後有“注云訖葬而除”六字,今不知何故而删去。考《舊唐書》卷二十七《禮儀七》云“改葬之服,鄭云‘服緦三月’,王云‘訖葬而除’。”則此處“玄”當作“云”,“服緦三月”乃鄭玄注《儀禮》之文。又《唐文粹》卷四十二載田再思《服母齊衰三年議》正作“云”。當據改。
15. 退之以貞元五年後來京師,至是十五年矣。(頁157)
按:“後”徐本作“復”,魏本、廖本同。韓愈初至京師在貞元二年,不得云於貞元五年後方來。本書卷二《上兵部李侍郎書》“凡二十年矣”注即云:“退之以貞元二年入京師,至此二十年矣。”(頁161),作“後”者,當是形近而誤。
16. 謹,或作謂。(頁158)
按:“謂”徐本作“請”,《舉正》《考異》、王本、廖本同。當是形近而誤,當據改。
17. 唐德宗以後,方鎮多制樂舞以獻……雄健壯妙,號爲文武順聖樂。(頁165)
按:“文”徐本作“孫”,魏本、廖本同。考李肇《唐國史補》卷下云:“于司空頔因韋太尉奉聖樂,亦撰順聖樂以進,每宴必使奏之,其曲將半,行綴皆伏,獨一卒舞於其中,幕客韋綬笑曰:‘何用窮兵獨舞’。言雖詼諧,一時亦有謂也。頔又令女妓爲六佾舞,聲態壯妙,號孫武順聖樂。”(13)(唐)李肇:《唐國史補》,卷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59頁。注文所引或出於此。又王讜《唐語林》卷三、《新唐書》卷二十二《禮樂志》及王應麟《玉海》卷一百五均作“孫”,作“文”者蓋因正文有“文武順聖樂辭”而改。當以“孫”字爲正。
18.夫馬之智不賢於夷吾,農之能不聖于尼父,然且云爾者,聖賢之能多,農馬之知專故也。(頁166)
按:“多”字下不當讀斷。“多”字古有讚揚、讚美之義,管子“釋老馬”,孔子使問老農,即以農、馬之知各有所專而“多”之也。
19. 日或作由,仁鈞以讒流愛州。(頁311)
按:“由南”不詞,《舉正》《考異》及宋蜀本、王本均作“山”,當從。愛州地處嶺南,猶山南也。“由”蓋“山”之形誤。
20.申叔字子重,年二十一舉進士。(頁341)
按:“二十一”當作“二十二”。考柳宗元《亡友故秘書省校書郎獨孤君墓碣》云:“君諱申叔,字子重,年二十二舉進士。”(14)《柳宗元集》,第277頁。又魏本、廖本正作“二十二”,當從。
21. 元和元年四月,以兵部侍郎李異爲度支鹽鐵轉運使。(頁415)
按:“李異”徐本作“李巽”,魏本及廖本同。考《唐會要》卷八十八《鹽鐵使》條云:“元和元年四月,兵部侍郎李巽充諸道鹽鐵使。”(15)(宋)王溥撰,牛繼青校證:《唐會要校證》,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年,下册,第1378頁。又《册府元龜》卷四百八十三《邦計部》同。
22. “道易”上或有“其次曰序”。(頁416)
按:“序”徐本作“字”,《考異》及魏本、王本、廖本同,當從。則此處當斷爲“‘道易’上或有‘其次曰’字。”
23. 建字杓真。(頁418)
按:“真”徐本作“直”,魏本、廖本同。考白居易《白氏長慶集》卷二十四《有唐善人墓碑》云:“唐有山人曰李公,公名建,字杓直,隴西人。”(16)(唐)白居易撰,朱金城箋注:《白居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6册,第2676頁。又有《贈杓直》《秋日懷杓直》等詩。《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五《李遜傳》亦作“直”。當正之。
24. 《舊史·畢誠傳》乃稱吏部。(頁425)
按:“誠”當是“諴”字之形誤。畢諴,《舊唐書》卷一百七十七、《新唐書》卷一百八十三均有傳。
25. 後琳客死源朔間。(頁457)
按:“客死源”徐本作“死客河”,魏本、廖本同,是。檢本書卷六《唐故檢校尚書左僕射右龍武君統軍劉公墓志銘》云:“琳死,脱身亡,沉浮河朔之間。”(頁507)此亦與正文“終琳之已,還卧民里”(頁456)相應。又《新唐書》卷一百七十《劉昌裔傳》正作“子琳死,客河朔間。”(17)(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第16册,第5166頁。是客河朔間者乃劉昌裔。此處文字、標點多所訛誤,當正之。
26. 九月丙午,中官季建章坐受啓賄。(頁471)
按:“季”當作“李”,魏本、王本、廖本均作“李”。檢《册府元龜》卷一百五十三《帝王部·明罰二》云:“辛酉,罰國子司業韋纁等一十四人各一月俸,以其不赴曲江之宴也。是月,中官李建章坐受桂州觀察房啓之賄,杖一百,處死。”(18)(宋)王欽若等編纂,周勳初等校訂:《册府元龜》,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年,第2册,第1710頁。可見“季”乃“李”之形誤,當正之。
27. 元和元年四月,應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中第四第,爲右拾遺。(頁502)
按:“中第四第”不詞,徐本作“中第三”,下另有“辛酉”二字。考《舊唐書》卷一百六十八本傳云:“元和初應制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入第四等,拜左拾遺。”(19)(後晋)劉昫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第13册,第4381頁。又《唐大詔令集》卷一百六《政事》:“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第三次等元稹、韋惇,第四等獨孤鬱、白居易、曹景伯、韋慶復。”(20)(宋)宋敏求:《唐大詔令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544頁。是郁乃第四等,徐本誤。今云“中第四”,乃馬氏所校改,則後一“第”字應是“等”字之誤。
28. 斥,或作許,或作訢。(頁520)
按:“訢”徐本作“訴”,《考異》及魏本、王本、廖本同。方成珪《韓集箋正》卷九云:“《舉正》所謂閣本作‘訴’。‘訢’當是‘訴’字之誤,然亦未詳其義。”(21)(清)方成珪:《韓集箋正》,《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310册,第647頁。《孟子·盡心上》云:“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注云:“訢,與欣同。”(22)(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卷十三,北京:中華書局,第360頁。是訢乃喜義,用於此處,文義、語氣均不契合,作“訴”爲是。
29. 《月令》“盲食至”,注“疾風也”。(頁543)
按:“食”徐本作“風”,是。《禮記注疏》云:“盲風至,鴻雁來,玄鳥歸,群鳥食羞。注云:盲風,疾風也。正義曰:盲風,疾風者,皇氏云:秦人謂疾風爲盲風。”(卷十六)可見其誤。
30. 陳景雲曰:舟中樹兩旗,設寓焉以迎神:此嶺外祀神舊俗,見南宋臨邛韓本注。(頁552)
按:“焉”徐本作“馬”。考魏本引朱廷玉注語云:“湖湘土人云:柳人迎神,其俗以一船兩旗,置木馬偶人于舟,作樂而導之登岸,而趨於廟。”(23)《新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卷三十一,《中華再造善本》影宋慶元六年魏仲舉家塾刻本。又《漢書》卷二十五上《郊祀志》云:“詔有司增雍五畤路車各一乘,駕被具。西畤、畦畤寓車各一乘,寓馬四匹,駕被具。”(24)(漢)班固撰,(唐)顔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4册,第1212頁。又卷二十五下云:“以木寓馬代駒,寓馬代獨行,過親祠,乃用駒。”(25)(漢)班固撰,(唐)顔師古注:《漢書》,第4册,第1246頁。是漢郊祀禮已有所謂“木寓馬”“寓馬”迎神之説。則“焉”爲“馬”之誤可以無疑。
31. 續純絢綰繒紘縉絳縑。(頁580)
按:“繒”徐本作“繪”,魏本、廖本同。考劉禹錫《劉夢得文集》卷二十九《唐故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使福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贈左散騎常侍薛公神道碑》云:“公諱謇,字某,曾祖寶胤,以名家子且有學行,歷尚書郎、雍州司馬、邠州刺史。王父繪,有俊材,刺三郡:金、密、綿,皆以治聞,累績至銀青光禄大夫,封龍門侯。”(26)(唐)劉禹錫撰,瞿蜕園箋證:《劉禹錫集箋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上册,第71頁。是薛謇之父名“繪”,“繒”字誤。
32. 長慶元年正月,戢自湖南觀察又爲少府監。(頁594)
按:“又”當作“入”。所屬正文云:“公之薨,戢自湖南入爲少府監。”可見其誤。
33. 凉武昭王名暠,字玄感。(頁614)
按:“感”當作“盛”,諸本均作“盛”。《魏書》卷九十九本傳云:“李暠,字玄盛,小字長生。”(27)(北齊)魏收:《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第6册,第2202頁。《晋書》卷八十七《凉武昭王傳》同。可證其誤。
34. 朱居靖公《秀水閑居録》云。(頁639)
按:“居”當作“忠”。朱忠靖即朱勝非,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卷十一云:“《秀水閑居録》三卷,丞相汝南朱勝非藏一撰,寓居宜春時作。秀水者,袁州水名也。”(28)(宋)陳振孫撰,徐小蠻、顧美華點校:《直齋書録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42頁。又《宋史》卷三百六十二本傳云:“朱勝非,字藏一,蔡州人。……謚忠靖。”(29)(元)脱脱等:《宋史》,第32册,第11315—11319頁。可見作“居”者誤也,當正之。
35. 縛盧從史,收澤潞等五州。注:五洲,澤、潞、邢、洛、磁。(頁681)
按:“洛”徐本作“洺”,廖本同。檢《舊唐書》卷一百七十七《盧鈞傳》、卷一百七十八《王徽傳》、卷一百九十《唐次傳》,均以澤、潞、邢、洺、磁五州連稱。五州于唐皆屬河東道,《元和郡縣志》卷十五“洺州”條云:“《禹貢》冀州之域。春秋時赤狄之地,後屬晋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按曲梁,即今州理地也。七國時屬趙,趙敬侯始都邯鄲,至幽王遷,爲秦所滅,秦兼天下,是爲邯鄲郡。漢武帝置平干國,宣帝改曰廣平。自漢至晋,或爲國,或爲郡。永嘉末,石勒據有其地,石氏滅,又屬慕容雋,至子暐滅,又屬苻堅,後慕容垂得山東,其地復屬焉。周武帝建德六年於郡置洺州,以水爲名。隋大業三年罷州爲永安郡,武德元年又改爲洺州,兼置總管。二年陷於竇建德,四年討平,又爲建德舊將劉黑闥所陷,尋討平之。六年罷總管,復爲洺州。”(30)(唐)李吉甫撰,賀次君注解:《元和郡縣圖志》,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上册,第430頁。洛州屬河南道,或改稱東都,與澤、潞等州不相連屬,作“洺”爲是。
36. “歉,或作歎。”(頁780)
按:“歎”徐本作“暵”,《考異》及王本、廖本均作“暵”,是。《説文》:“暵,乾也。耕暴田曰暵。”與旱義同。《周禮》云:“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卷三《地官司徒》)是“旱暵”連言之例。作“歎”無理,當正之。
除以上所舉之外,尚有一些明顯屬於排印時出現的錯訛,如將“入”誤作“人”,將“土”誤作“士”“士”誤作“土”,將“土”誤作“上”,將“上”誤作“人”,將“凡”誤作“幾”,將“宇”誤作“字”,將“於”誤作“子”,將“子”誤作“予”,將“干”誤作“千”,將“水”誤作“氷”,將“注”誤作“窪”,將“讙”誤作“謹”,“瀠”誤作“溁”等(31)如頁738注五“於,或作子”,“子”當作“于”;頁552注一“蕉下或有‘葉’字,或有‘予’字”,“予”當作“子”;頁697正文“葬華陰縣東若千里”,“千”當作“干”;頁287正文“白金氷銀丹砂石英鐘乳橘柚之包”,“氷”當作“水”;頁562注一三“補窪”,“窪”當作“注”;頁294正文“謹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謹”當作“讙”;頁565注七“補注:何焯曰:溁洄曲折,不可一覽而盡”,“溁”當作“瀠”。,所在多有。其中又有文句竄亂者,如“會周平齊,改爲《關東風俗傳》,更廣見聞,勒成卅載卒於卷以上之”“兢撰《梁》《齊》《周史》各十卷,《陳史》五卷,《隋史》二十卷。天寶八恒王傅。《舊唐書·吴兢傳》云云”(頁745)兩句,前句“載卒於”三字當在下句“天寶八”之下。其他標點上的細微錯誤亦不勝枚舉。(32)如頁145注四“國子、太學、四門、律、書、算,爲六館”,“算”字後的頓號不當有;頁173注四“補注:沈欽韓曰:按‘載’之訓,‘則’也”,“訓”字後不當斷;頁179注文“‘之’‘爲’‘耳’三字,或作‘爲之耳’”,當標作“‘之爲耳’三字,或作‘爲之耳’”;頁184注六“或無‘兩之’字”,“兩”字不當引;頁201注八“‘吾下’或無‘豈’字”,“下”字不當屬内;頁259注文“方從閣本作‘咸而’,屬上句”,“而”字不當引;頁259注文“方從閣杭本‘光翔’下皆有‘兮’字”,“光”、“翔”本分屬兩句,不當合引。當作“方從閣杭本‘光’、‘翔’下皆有兮字。”頁294注一“或作‘集’,或云‘卒業’。字見《漢·楚元王傳》。” “卒業”後不當讀斷;頁525注一一“……李季卿黜陟江淮,奏皋節行,改著作郎復,不起。”“復”字當屬下讀;頁769注文“或無‘日’字‘於’,一作‘于’”,“字”後當斷不斷。其他多有,不備舉。當然,這些在校點過程中産生的訛誤,完全不影響此書的經典性。今將其疏漏之處舉出,但有望於此書之日臻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