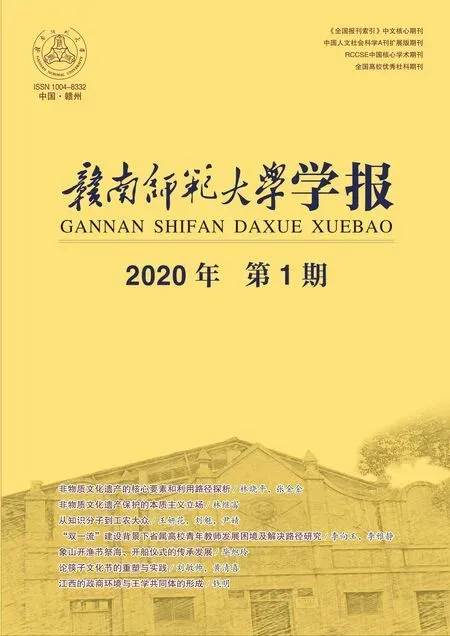女性符号与性别叙事
——新世纪以来客家影视剧女性形象研究*
刘丽芸,张 文
(赣南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江西 赣州 341000)
进入新世纪以来,客家族群文化建构的形式越来越多样化,其中以影像为媒介建构族群记忆与历史的主题获得广泛关注,期间涌现了大量的客家题材影视剧。据不完全统计,从2000年至今,客家题材的影视剧有几千多种,包括在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都出现了一些反响较大的作品,如中国大陆地区的《围屋里的女人》《土楼里的女人》《客海往事》《白鹭谣》《等郎妹》,中国香港的《客家女人》以及台湾地区的《一八九五乙未》《插天山之歌》等。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些影视剧大都以客家女性为叙事主体,客家女性这一类型形象,往往与客家族群文化中的“大地之母”紧密相连。[1]在某种意义上,客家族群文化的主体建构,正是通过客家女性故事的讲述,重新连缀起传统客家文化与现代客家族群,完成其形式上的客家族群历史建构。客家女性作为叙事的主体,被赋予具有独特意义的“大地之母”形象,在完成历史叙事的同时,充当了某种可以跨越的社会功能角色,最终成为一种符号化的空洞能指。
一、客家女性形象类别
在客家族群文化的历史脉络中,客家女人是极为特殊的类型形象。在众多的客家文艺作品中,最常出现的原型,便是“大地之母”的母亲形象。“大地之母”有着坚韧不拔、吃苦耐劳及顽强不屈的精神品质,而背后联系的是客家族群迁徙、生存环境恶劣的早期族群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大地之母”近乎某种“原型形象”,呈现着客家族群中女性的族群功能角色。客家族群大规模的迁徙移民历史,要求客家女性与客家男人一样,翻山越岭、跋山涉水,因此客家女性不缠足,成为客家传统农业生活的主要劳动力,而客家男人大都外出打拼,漂洋过海谋生,传统社会家庭的“男主外、女主内”这一结构在客家族群中往往变为客家女性既主内又主外的族群结构模式,传统衡量客家女性美德的“家头教尾、田头地尾、灶头锅尾、针头线尾”四项妇功恰是对这一家庭结构模式的最好注脚。由此可见,在传统族群意义上的“大地之母”——客家女性,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可穿行的空间或场域,既包括了“女织”的家庭内部的女性功能,也担当了“男耕”的社会功能,其性别角色并未进行严格意义上的差异性。“大地之母”作为描述客家女性形象及族群文化的“原型”,在客家文化的历史书写中不断被诠释。随着客家影视剧在新世纪以来的新兴与发展,“大地之母”作为客家女性的形象标签,亦演变成极为特殊的类型。
文本选取传播影响较大且具有代表性的几部影视剧女性形象——《白鹭谣》中的玉秀莲、《等郎妹》中的闰月、《客家女人》中的姊妹花梁美田、梁美行以及《插天山之歌》中的奔妹。之所以选取这4部作品,一方面是由于它们具有较强的地域特征,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全球范围内主要的几个典型的客家区域:江西赣州、福建龙岩、广东梅州及香港、台湾地区。另一方面是这些作品以客家女性作为故事的第一主角,塑造了较有影响力的客家女性形象。同时,这些客家女性及影视剧均产生了较大影响,传播范围较广。《白鹭谣》是中国大陆第一部正面描写客家人的大型电视剧,《等郎妹》囊括了2008年长春电影节等7个大奖,《客家女人》由香港HDTV版制作,在豆瓣评分中保持8.0的较高成绩。《插天山之歌》是由台湾本土女导演黄玉珊的一部客家方言电影,具有台湾客家的本土体验与情感。
以上4部来自不同地域的客家影视剧无疑均是以客家女性为故事中的第一女主角,由客家族群文化历史中的“大地之母”作为原型,在新世纪以来的历史脉络中,呈现出了不同的类型形象。
一是传统压抑性。以《等郎妹》中的闰月为典型。学者戴锦华曾指出:“在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史上,关于女性和妇女的话语或多或少是两幅女性镜像间的徘徊:作为秦香莲——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旧女子与弱者和花木兰——僭越男权社会的女性规范,和男人一样投身大时代,共赴国难,报效国家的女英雄。”[2]秦香莲式的被奴役、被损害且在苦难中压抑自我的传统女性,经常在历史话语中被称为“旧式女子”。《等郎妹》中的闰月与被压抑被损害的“旧式女子”形象不谋而合:故事发生的背景放置于解放前,客家山区的畸形婚俗——年幼女孩嫁到没有男孩的家中,苦苦等待婆婆为自己生一个丈夫。以闰月为代表的客家旧式女子,年幼被送往封闭的客家土楼做等郎妹,经历了一生悲剧命运的沉浮之后,最终选择了坚守土楼,等待丈夫的归来。灰蓝色调的传统客家服饰以及封闭的土楼空间营造了传统客家压抑的氛围,闰月被压抑与被损害的客家旧式女性形象与影片格调相契合,成为了旧式客家婚俗的经典标签。
二是花木兰型。以《白鹭谣》中的玉秀莲为典型。在客家族群的历史书写中,客家女性除了作为旧女人——被压抑与被伤害的符号象征,便是作为花木兰式的巾帼英雄。《白鹭谣》中的玉秀莲堪称典型。玉秀莲虽然没有如花木兰般女扮男装替父从军,但是依然遵循的是一个花木兰式的女性故事:在家族中男性羸弱或缺席的情况下,女性扮演男性角色,承担起男性的社会功能。玉秀莲经历千万磨难终于成为钟氏家族的女性掌门人,其聪颖与坚韧也成为客家族群历史与精神的有效认同符号。
三是现代自我型。以《客家女人》中的梁美行为典型。现代都市剧《客家女人》(《来生不做香港人》)则不再拘泥于客家历史故事的讲述,而是把客家女性作为叙事的第一主体,放置于当下,梁美行的外表已然成为都市摩登女郎——一个拥有知识美貌且特立独行的女子,而与之相对比的便是依然恪守传统的典型客家女子——姐姐梁美田。非常有意味的是,这位外表现代且个性自我的摩登客家女的现实遭遇却困难重重,经历无数误解、考验与磨难,最终与代表传统客家女性的姐姐和好,在某种意义上象征着被传统客家文化所认同。
四是自然之子型。以《插天山之歌》中的奔妹为典型。台湾本土导演黄玉珊导演的《插天山之歌》,根据客籍小说家钟肇政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同样是讲述台湾客家族群历史,与前面3部作品所不同的是,客家女性并非是绝对意义上的叙事主体,而是讲述抗日客籍青年陆志骧回归台湾客家本土,并获得客家本土女性奔妹的救助并最终成长的故事。奔妹作为故事中的客家女性,故事女主角,同样承担了拯救者的角色——“美救英雄”。陆志骧的抗日计划失败,遭遇追捕的凶险之境,在深山中获得奔妹的救助,并最终收获了爱情。一改客家女性被压抑的悲情,奔妹更多的是客家本土、山林之母的象征。
二、叙事策略:女性符号与族群认同
关于历史尤其是客家族群历史的叙述,始终是客家影视剧影像系列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世纪以来的特定语境中,追溯族群历史,宣扬族群文化成为客家影视剧历史叙事的重要表现主题。作为一个具有族群意识的强化手段,无疑与我们所处的时代情境与社会现实有着密切关联。面对全球化的现实语境以及转型期中国急剧的社会变更,地域性、本土文化面临着被吞噬的危机与困境。与此同时,社会变迁中所面对的拜金、欲望与生存,这些带来的是身份焦虑。在某种程度上,为了摆脱族群、自我的危机与焦虑,影视剧一个重要的叙事策略,就是不约而同地把这种危机与焦虑转移到女性角色身上。正如劳拉穆尔维提出的视觉快感理论,在影像中“看”的视觉快感始终指向男性对女性的凝视,影像视觉充满性别意识,银幕中男性(观众)向女性投去欲望的目光,使得女性化为景观,影像叙事的主体——女性被建构为他者,或者说在影像历史叙事的策略中,女性作为叙事主体,实际意义上是被他者化为不同的形象,而这些他者化的性别叙事,充当了符号化的族群景观文化,同时承载了族群历史叙事与文化认同。
(一)文本分析一:《白鹭谣》与《等郎妹》
《白鹭谣》与《等郎妹》,一部为热播电视剧,一部为获奖无数的数字电影,其中的相同显而易见,都以客家女性为叙事主体,完成客家族群叙事,所不同的是,一个是客家巾帼英雄的奋斗史,一个是被压抑的“秦香莲”式的传统客家女,客家女性在镜头中被展现,女性并非主体而是被符号化为表象或者景观,观照族群历史,通过女性符号认同建构统一的自我与族群认同。
在数字电影《等郎妹》中,空间场景是20世纪20年代的客家山区,电影利用造型色彩传达了禁闭的意象。
黛青的影调定下了影片压抑的主题,特写镜头中的黄豆与圆形土楼外屋砌满小而圆的石子路形成呼应,俯拍镜头中年幼的闰月走进土楼,喻示了她此生的命运。影片的大多故事场景均选择在夜里发生,深蓝而近黑的夜色里,小闰月出逃;新婚刚过,丈夫思焕要下南洋,闰月虽不舍,但依然承担起近乎母亲的角色给丈夫送行,远景中思焕走出土楼渐行渐远,近景中闰月被桎梏在土楼封闭的小屋,唯独一扇小窗和一盏昏暗的油灯,能驻足、远望、悲伤与痛哭;影片中唯一的一抹亮红便是闰月即将收获爱情要与春生完婚之时,近景特写的大红盖头巾点亮了蓝灰压抑的土楼空间,但一封近乎遥遥无期的信却再次将闰月重新放置于土楼,重新经历漫长的岁月摧残与等待,在近景特写镜头背影中,身着客家蓝衫,头戴客家首饰的新婚女子闰月,主动将这些一一褪去,空间场景再次放置于黑夜,在狭窄幽暗的房间里,闰月点起油灯,细数起那象征等待的黄豆,与片头强烈呼应。
作为族群历史的书写,整部影片的造型以福建客家大围屋为重要造型元素,封闭的围屋、浓墨黑色的瓦顶、结实的石子地板成为影片非常重要的视觉元素,导演郑华在谈到以客家围屋为拍摄环境时,提到封闭的造型空间,目的在于“与人物命运紧密相连,给予了象征关系。”[3]闰月的命运与客家围屋紧紧联系在一起,从小闰月要在黑夜里出逃,到成年后逐渐接受围屋既有的规定与惩罚,到最后,在一封丈夫思焕可能活着的书信下,闰月自觉地接受族规,将婚嫁取消,甘愿在油灯下重蹈等郎妹的凄苦命运。闰月作为一个受压抑的传统客家女性承担了历史叙事的“他者”身份,正是闰月与封闭围屋融为一体的过程,展现着闰月从一个受害者身份到一个传承者身份的转变,除了小闰月从被迫跪搓衣板到主动跪搓衣板这一细节之外,最具有象征性的便是片头与片尾油灯下等郎妹数豆子的特写镜头,而影片的结尾将历史的空间拉回到现代,当围屋已经成为族群历史景观,供游客观光欣赏的时候,老年闰月则与围屋融为一体,成为被展览的活化石。特写镜头下老闰月数着粒粒黄豆,符号化为族群历史中的畸形景观。把影片主题定义为对客家族群旧制度等郎妹的反思不免浅显,因为在新世纪探讨一个20世纪初就探讨过的话题,难免陈旧。闰月对客家族群文化从反抗到认同,一方面迎合了观众(或者说男性观众)对封闭山区客家女子的猎奇心理,而更深层面上,闰月被符号化为旧式客家女性,闰月数黄豆,与封闭的客家围屋一起,被符号化为族群历史的一道景观。
《白鹭谣》在建构族群历史文化的过程中,同样以客家女性作为第一主角和叙事主体。与《等郎妹》所不同的是,一改“秦香莲”悲苦命运的“景观”化。《白鹭谣》中的客家女性变为坚韧强大的“花木兰”,在丈夫死亡,家公病逝以及家族男性羸弱不堪的情境下,作为钟氏家族的小妾——客家女玉秀莲,挺身而出,承担起家族男人的身份与重担,经历了重重磨难,最终重振了赣南具有客家代表性的钟氏家族。女性表象与爱情故事成为故事的前半段叙事,建构起窥视情境。作为钟家顶梁柱钟正义与客家贫女玉秀莲的曲折爱情故事,但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别有意味的是故事的下半段,当丈夫死亡,玉秀莲承担起家族的使命之时,同时也捐弃了自己的性别身份。前半段作为钟正义小妾的玉秀莲,聪明美丽,后半段作为钟氏家族掌门人的玉秀莲,担当了抚养遗腹子,振兴家族的使命,坚韧刚毅,同时具备了全能的救赎力量,但在性别身份转变的同时,玉秀莲必须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丧夫、守寡、历经重重困境与磨难,最终获取了钟氏家族掌门人——男性的社会功能角色。玉秀莲并未获得自由穿行的性别自由,故事的后半段秀莲仅仅是角色身份的转变,女性表象渐次成为单一扮演:出演与族群历史建构意义对应的单薄符号。
(二)文本分析二:《客家女人》与《插天山之歌》
《客家女人》是由香港电视台制作的热播电视剧,《插天山之歌》则是由台湾本土导演黄玉珊执导的客家方言电影。两部客籍题材作品分置于具有特殊历史政治的场域空间,客家女性作为叙事主体,符号化的文化景观依然呈现,性别与文化政治则呈现出更多的地域文化认同。
《客家女人》中的客家姐妹梁美行、梁美田,像绝大多数影视剧中的姊妹花一样,按身份地位悬殊、性格迥异、矛盾丛生最后大团圆结局的叙事路径来开展故事情节。与一般家庭情节剧所不同的是,故事的叙事有较大的历史政治时空的跨越,一是1960年代的中国大陆;二是1980年代后的香港。由于分隔两地的姊妹花在不同政治时空的不同境遇,也形成了不同的社会身份地位。梁美行作为留在大陆的姐姐,身上有更多传统客家女性的印记:勤劳、质朴、大度。而逃亡香港并在现代都市生存下来的妹妹梁美田则和姐姐相反。从妆容上看妹妹梁美田干练美丽,姐姐梁美行朴实无华;着装上妹妹大都为都市职业装、时尚休闲装,姐姐衣着相对朴实、乡土气息浓;妹妹完成学业,跻身高级白领,姐姐文化程度低,基本无业,但后来因为家乡被开发,变得富有;在性格特征上妹妹独立进取,姐姐温柔体贴;而妹妹在道德、家庭观念上相信爱情、坚持自我,姐姐关爱他人、敢于牺牲、忠于爱情、重视亲情。
客家姐妹的造型、身份地位、性格特征及道德价值观念的对比,姊妹花形成了一种具有客家女性视觉符号的女性符码,姐姐与妹妹的诸多对比形成一种视觉形象、社会特征、道德价值多层次的参照与镜像关系。
作为视觉形象,姐姐代表着传统客家女性形象,身体和观念都融入到家庭生活之中,在故事中作为一个失去主体性的虚化形象存在于族群文化的历史叙事中,而妹妹作为一个新客家女性,视觉形象上的变化、干练时尚的华美装束使得其女性身体符号更具魅力。在性别叙事中,姐妹俩的形象对比通过图像与符号,传达出身体的更深层次的文化意义与内涵。由于时代政治的因素,姐姐与妹妹在1960年代成长的过程中呈现不同的际遇,姐姐留守在客家本土,失去了接受教育的机会,而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又重新给予了姐姐金钱乃至社会地位,作为传统的客家妇女,姐姐并未因此而改变,她身上保留了一切观念上的客家女性应该具备的性格特征:勤劳、质朴乃至隐忍。一个丧失主体被压抑的客家女性符号,不仅是传统客家族群文化的符号象征,同时也是进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客家本土的文化象征。而妹妹成长于远离客家本土的异乡——香港,接受教育,成为知识分子、都市高级白领与独立时尚的客家女性。妹妹梁美田独立进取、坚持自我的性格与道德观念可以看出女性更多的自我呈现。然而与此相悖的是,妹妹梁美田并未成为新时期现代客家女性的身体表征与文化象征。故事中姐妹俩的乡土情结始终是一对异己的矛盾冲突贯穿始终,在相互的情感纠葛与冲突中,亲情血浓于水,矛盾的最终化解是妹妹的传统回归与对姐姐的认同,妹妹与传统客家文化的差异性最终由叛逆到回归的认同得以抹除。姊妹花的团圆不仅意味着异乡客家对本土客家的认同与传承。同时,姊妹花分别所代表的中国香港与中国大陆,也随着妹妹梁美田的回归与认同,传递出香港回归与认同祖国大陆文化的时代政治意味。由此,两个具有着女性符号意义的客家女性,通过对比与认同的镜像关系,传递出由客家女性身体所代表的时代、政治乃至族群文化意义。
相比中国香港书写客家族群历史的时代政治意义,中国台湾在新世纪以来的客家影像叙事中则呈现出更多对在地文化的建构。
20世纪90年代,随着台湾政治格局中的“政党轮替”和“经济衰退”,台湾电影也因政府辅导金政策出现危机。随着一大批六七十年代的健康写实主义导演的去世,80年代兴起的新电影运动也接近尾声,台湾电影的一个重要时代也宣告结束。[4]电影的本土危机直至2008年获得新的转机,《海角七号》在2008年的票房与口碑双丰收,以及其前后《插天山之歌》《一九八五》《艋舺》《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等似乎预示着台湾后新电影时代的到来,而这一系列电影的一个重要的共同特征,就是对台湾本土生活的表现,以在地生活作为电影的主要内容,语言呈现多元交融之势,不同的族群和原住民的历史再次成为电影表现的题材。
《插天山之歌》由黄玉珊2007年独立制片,此片改编自钟肇政小说《台湾人三部曲》。《插天山之歌》故事发生的背景是在“二战”末期。日本加强内部弹压,对台湾进行严密的思想管制之际,客家青年、知识分子陆志骧因在日本留学期间参加了反日组织,潜逃回台湾,后遭遇日本特务通缉,陆隐蔽于插天山,结识了客家女性奔妹,并产生爱情,最后在奔妹的帮助下陆志骧坚持到抗日战争胜利。[5]与之前几部客家影视剧所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的客家女子——奔妹并不是故事的叙事主体,也非故事真正的主角,但却是导演黄玉珊重点刻画的一个客家女性角色。与黄玉珊执导的多部影片相似的是,虽然男性是故事的第一主人公,但女性却形象鲜明且充满力量。如果说《插天山之歌》叙述了客家男子陆志骧的个人成长,那么这个助其成长并给予其生活力量的便是台湾客家本土女性奔妹。导演给予奔妹的客家女性形象及族群文化思考,更多地带着对台湾本土与客家族群的历史反思。
在影片中,客家女子奔妹被导演赋予客家“自然之子”的形象特征,赋予奔妹独立、个性且充满力量的女性意象。在这场“美救英雄”的性别叙事中,导演在影片的前半段采用纪实性影像风格来表现大历史背景下所受日本殖民统治的压抑与痛苦,故事没有编排剧烈的矛盾冲突,而是用安静潜藏的力量来孕育客家人内心深处所受到统治阶级的压抑与痛苦。
整个故事采用实景拍摄,取景于客家美浓山区,服装美工方面力图还原年代感,演员也是由职业演员与非职业演员(客籍)共同演出,完全真实的表演虽略感生涩,但恰好与人物性格相吻合。同时影片还插入了大量婚嫁、过年等客家习俗,采用客家语、闽南语与日语相交错的语言对白,营造了真实的台湾客家本土人文与历史地理环境。
奔妹在整部影片中着装古朴,具有历史年代的客家女子风貌。大量的固定长镜头描写奔妹与陆志骧劳动的场面,喻示着奔妹作为“大地之母”的性格力量。影片有大量女性劳动的场景盛赞奔妹作为客家女性劳动生存的本领,如挑柴、采茶、田间劳作使得奔妹具有着客家女性应有的勤劳、坚强且极具生命力。第一次劳动场面,陆志骧不胜劳作,从后山上跌伤,奔妹将其救起并为其治疗伤口,故事场景设置在客家山林,烟雾缭绕的背景氛围喻示着两人浪漫的爱情由此萌生,中近景镜头让观众对奔妹采集草药,为志镶包扎伤口等举动印象深刻,从而也隐喻着奔妹是山林的主人,奔妹在客家乡土的生活当中对陆志骧起着主导与引领的作用。与此同时,作为客家山林主导的奔妹,具有独立个性且勇敢追求自我。陆志骧第一次见奔妹,正是奔妹从山林间砍柴归来,志镶对奔妹一见钟情,想帮助其挑担,却遭遇奔妹的拒绝,但志镶的爱国之举却让奔妹深深佩服,同时又同情他的现实困境,奔妹的性格力量更多从救助陆志骧的叙事情节中得以展现。最终,当陆志骧从压抑的噩梦中走出,勇敢面对日本殖民者的缉捕之时,奔妹也自觉且勇敢地承担起家庭责任,继续扎根于客家山林,哺育孩子,坚强地活下去。
黄玉珊用纪实性的影像风格塑造了一个具有客家“自然之子”的女性奔妹,呈现了“包容、坚强与康健”的“大地之母”的母土特征,同时赋予奔妹独立自我的个性特征。奔妹健全的“自然之子”的客家女性形象,在影片中承担起“美救英雄”的叙事模式,客家青年男子陆志骧最终在奔妹的救助与力量感召下成熟成长,奔妹的客家女性形象,成为台湾客家本土族群历史叙事与文化认同的有效符号。同时,也呈现导演极具主观性的族群文化叙事与历史反思。
三、结语
正如拉康所言,女性图像与女性符号的表达永远离不开女性身体的呈现。新世纪以来的客家影像的历史叙事与建构,客家女性成为历史叙述的主体,成为文化景观的符号,借由女性形象的视觉符码,身体承载了历史叙事与文化认同的双重功能。在中国大陆,客家影像中的女性形象呈现出传统压抑与性别僭越的性别特征,客家女性并非主体而是被符号化为表象或者景观,观照族群历史,通过女性符号认同建构统一的自我与族群认同。由于中国香港特殊的时代政治背景,女性符号意义的客家女性,通过对比与认同的镜像关系,传递出由客家女性身体所代表的时代、政治乃至族群文化意义。而在中国台湾,客家影像中的女性形象的符号化与性别叙事中,“大地之母”成为台湾客家本土族群历史叙事与文化认同的有效符号,同时也呈现极具主观性的族群文化叙事与历史反思。
综上所述,两岸三地不同的政治形态与地域文化在客家女性形象塑造中均呈现女性图像化、女性符号化的影像特征,由景观所代表的女性身体被赋予了特定的社会功能,性别叙事的背后是族群历史建构,女性符号承载的是族群文化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