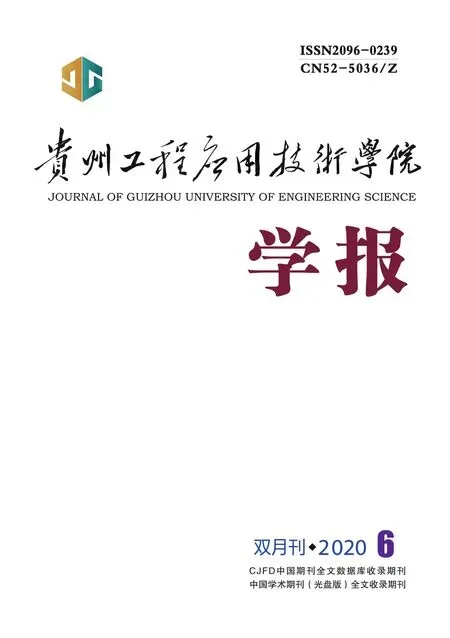伦理关系的突变
——《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中的恐惧问题
李丽红
(凯里学院国际教育学院,贵州 凯里 556011)
海明威著名短篇小说《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以下简称《麦》)的标题富有深意,它是指麦康伯在第二次狩猎时突破第一次狩猎时的恐惧心理,获得了超乎寻常的勇气,雄性激素的复活不仅使他敢于近距离面对受伤后凶猛的野牛,而且也为他能够以新的角色和姿态重新占据生活中的位置筑牢了基础,所以这一时刻的麦康伯是幸福的。但是他的幸福又是短促的,他妻子玛格丽特有意无意(对他而言)打进他头颅的那颗子弹,结束了他短促的幸福生活。
问题是,他的幸福生活是否在妨碍别人的幸福生活?当他们夫妻之间相对固定的伦理关系将要发生突变的时候,玛格丽特感到了无法把握生活的恐惧。换句话说,麦康伯的幸福生活即将深刻地影响她的幸福生活,而在她看来,属于她的幸福生活绝不能像麦康伯的幸福生活那样短促。这是“一篇有关开化了的女人的精彩寓言,这个女人鄙视没有勇气和进取心的男人,而一旦男人献出一点勇气和进取心,女人就会竭力将其毁掉”[1]。
一、麦康伯的恐惧
麦康伯第一次狩猎时,狮子受伤跑进野草丛中,他们开始搜寻。小说是这样描写的:“麦康伯靠近威尔逊,他那支来复枪准备着射击;他们刚跨进野草丛,麦康伯就听到被血哽住的咳嗽似的咕噜,看到野草丛里有东西呼的扑出来。接下来,他知道,他逃啦;发疯似地慌慌张张逃到空地上,向小河边逃去。”[2]26也就是说,面对受伤狮子的反扑,他吓破了胆,落荒而逃。这丑陋的一幕没有逃过他妻子的眼睛。小说前半部都在围绕他的恐惧行为及由此而造成的后果来展开,而构成小说前半部的恐惧,又是小说后半部他突破恐惧心理的铺垫,所以他的恐惧当然是小说的主题。
麦康伯猎杀狮子时的恐惧是他懦弱性格的集中体现。事实上他面对狮子落荒而逃只是他本性的一次折射,因为他并不是看到拼死反击的凶狠的狮子才感到恐惧的,头天晚上一直到要出发前,他都因那头狮子的吼声而心烦意乱。“这种情况是昨天夜晚开始的,那时候他醒过来,听到河上游不知什么地方有狮子的吼叫。吼声深沉,结尾有点象咕噜咕噜的咳嗽声,听上去好象它就在帐篷外面;弗朗西斯·麦康伯夜晚醒来,听到这声音,他感到害怕。他能够听到他妻子平静的呼吸,她睡着了。他没有人可以告诉,感到害怕,也没有人同他一起害怕。”[2]15他不仅害怕,甚至因没有人同他一起害怕而在孤独中感到了充满绝望的无助。一个要去猎杀狮子的人,还没有见到狮子就因它的吼声感到害怕,可以说,在出发前他与狮子之间就已分出了胜负。狮子受伤躲进野草丛后,他提出让黑人进去寻找,或者用火把狮子熏出来,他不敢再次面对狮子,他的恐惧从夜晚以来就一直在缠绕他。
正是这种懦弱的性格,才使他在与妻子的相处中多次容忍她的不忠,而他又是一位善良的人(海明威在创作谈中说他“是个善良的傻瓜”)[3],“如果他同女人打交道比较有办法,她也许会开始担心,怕他另外去娶一位美丽的妻子,但是她对他了解得很清楚,压根儿用不着为这事担心”[2]29。他有钱,她漂亮,这样的结构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均衡的,但是,他懦弱的性格使他处在了不平等关系中弱势的位置。
麦康伯猎杀狮子时的恐惧也是他最终能够突破恐惧的原因。他的恐惧被众人看在眼里,他羞愧难当,并要求威尔逊不要在外面传播他的丑闻,他甚至可怜兮兮地说“我像一只兔子似的逃跑”,这一切开始使他在心里主动放弃了作为雇主的那份至高无上的权力。小说的开头是这样描写他与妻子、白人猎手威尔逊之间关于饮料的对话的:
“你要酸橙汁呢,还是柠檬汽水?”麦康伯问。
“我要一杯兑酸橙汁的杜松子酒。”罗伯特·威尔逊告诉他。
“我也要一杯兑酸橙汁的杜松子酒。我需要喝点儿酒。”麦康伯的妻子说。
“我想这玩意儿正合适。”麦康伯同意说:“告诉他调三杯兑酸橙汁的杜松子酒。”[2]4
这是麦康伯面对狮子撒腿逃跑后中午聚餐时的场景。他问是喝酸橙汁呢还是柠檬汽水,这里只有两个选择,但威尔逊却提出了另外一个兑酸橙汁的杜松子酒的选项,而麦康伯的妻子不假思索就赞同了威尔逊的选择。威尔逊是一个属于非洲大陆的白人猎手,他的职业是陪同有钱的欧美白人打猎。他的身份夹杂在土著黑人与欧美白人之间;他是白人,指挥着一群土著黑人,自己却又要靠领取欧美白人的薪水生活;尽管在人格方面他与雇主是平等的,但相对于欧美白人来说他仍然是下层人物。现在,正是这个下层人物主导了饮料的选择,而麦康伯在威尔逊与自己妻子达成统一战线的时候,竟然妥协地回答:这玩意儿正合适。看似漫不经心的几句对话,揭示出了他在主动遗忘作为雇主应该具有的选择权,甚至做出决定的那份权力。
最终刺激麦康伯,让他突破恐惧心理的是,他妻子居然在当天晚上睡到了威尔逊的帐篷里。第一次狩猎之后的晚上他被梦中的那头狮子惊醒,发现妻子并不在帐篷里。等妻子回来后,他们之间有一段对话:
两个钟头以后,他的妻子走进帐篷,撩起蚊帐,舒适地爬上床。
“你上哪儿去?”麦康伯在黑暗中问。
“唷!”她说:“你醒了吗?”
“你上哪儿去了?”
“我刚才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你干的好事,真该死。”
“你要我说什么呢,亲爱的?”
“你上哪儿去了?”
“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这倒是这种事的一件新鲜名称。你是一条骚母狗。”
“唔,你是一个胆小鬼。”
……
“你只要有机可乘,真是一刻也不等啊,对不?”
“请别跟我说啦。我很困,亲爱的。”
“我要说。”
“那么,别缠我,因为我快要睡着了。”接着,她确实睡着了。[2]30-31
她真的睡着了。玛格丽特不是第一次背叛麦康伯,但是这里的不同在于,两个帐篷相隔不远,而她是从自己身边溜走的;另外,她私通的对象刚巧是亲眼目睹自己逃跑,又在关键时候杀死狮子的那个身份低微的人。在他感到寒冷和空虚的恐惧时,妻子不仅没有安慰他相反在公然侮辱他,他当然无法容忍这种明目张胆的背叛,然而却没有在妻子和威尔逊面前发作。这有两个原因:一是他懦弱的性格;二是他没有找到机会。因为这毕竟不仅仅是他和妻子的关系问题,而是他作为男人应当找回尊严的问题,是他在今后的生活中该以怎样的姿态站稳位置的问题,所以,他在寻找恰当的机会来重塑自己。这个机会就是第二次狩猎,他们去猎杀野牛。
有一次扯闲篇时,吴小哥问,古家庄那两个水湾是不是还在?我说在啊,那个种着芦苇的水湾已经种了苘麻,到了夏天便开出黄色的小花,香味浓浓的,说不出的清香。吴小哥不愉快地问,咋会成了苘麻,我记得整个水湾都长着芦苇,夏天还有苇喳。
二、麦康伯与玛格丽特伦理关系的变化
对惜字如金的海明威来说,小说对麦康伯和他妻子之间关系的描写可以算是较为详尽了。“总的说来,他们被认为是一对幸福的夫妻,他们就是属于尽管经常谣传要散伙,但是从来没有实现的那类夫妻;……他们有健全的结合基础。玛戈(玛格丽特的昵称)长得太漂亮了,麦康伯舍不得与她离婚;麦康伯太有钱了,玛戈也不愿离开他。”[2]29聂珍钊先生说:“文学的性质是伦理学的。”[4]麦康伯与玛格丽特之间的夫妻关系当然是一种伦理关系,这种伦理关系体现了美国上流社会的一种价值取向,即物质是人与人之间联系的主要媒介;有钱和漂亮都不属于精神层面,但是它们之间无法分离的状态仍然体现了“健全的结合基础”,也就是说,他们之间的伦理关系是相对固定的。
麦康伯第二次出发去猎杀野牛时,受伤的野牛逃进灌木丛,他们端着猎枪顺着血迹去查看野牛,这样的情形与第一次去猎杀狮子时非常类似,甚至危险都一样,但是,面对同样危及生命的第二次行动,他的心理却发生了变化。“麦康伯感到一种他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抑制不住的和莫名其妙的快活。”他对威尔逊说:“你知道,我发生了变化。”“我感到完全不一样。”接下来小说描写了麦康伯猎杀受伤野牛的行为:
那条野牛庞大的身子眼看就要扑到他身上,他仔细瞄准着,又开了一枪;他的来复枪差不多同那颗伸出了鼻子冲上来的牛脑袋一样高低了;他看得见那双恶狠狠的小眼睛;接着那颗脑袋开始搭拉下来。[2]47
面对麦康伯的变化,威尔逊与玛格丽特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反应。威尔逊异常高兴,他说:“但是现在他喜欢这个麦康伯了。……嘿,这可是一件好得要命的事。”威尔逊与麦康伯只是一种雇佣关系,很可能打猎结束后一辈子不会再见面,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固定的而是临时的,也就是麦康伯无论懦弱还是勇敢,他对威尔逊都不构成任何威胁;而威尔逊作为一位无所畏惧的猎人,他的内心更认同坚强、勇敢这类品质,更认同麦康伯完成获得真正男人身份的仪式。所以他说:“麦康伯终于长大成人了。……有了这东西,他就变成了一个男人。”
玛格丽特则是另一种反应。她对追逐受伤野牛的最先感受是厌恶,而这种感受实际上是面对两难选择时的一种表现。因为如果麦康伯再次逃跑,那只是在增加她对他懦弱的厌恶;而一旦换一种方式,即麦康伯英勇无比,她又因无法接受他的变化而感到厌恶。当麦康伯表现出极度兴奋的时候,“他妻子一句话也不说,神情古怪地看着他”轻蔑地说:
“你变得勇敢得很,突然变得勇敢得很。”但是她的轻蔑是没有把握的。她非常害怕一件事情。麦康伯哈哈大笑,这是非常自然的衷心大笑。“你知道我变了。”他说:“我真的变了。”
“是不是迟了一点呢?”玛戈沉痛地说。因为过去多少年来她是尽了最大的努力的;现在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弄成这个样子不是一个人的过错。
“对我来说,一点儿不迟。”麦康伯说。[2]44-45
玛格丽特不相信丈夫会变得勇敢,但又没有把握;她很清楚地认识到,今天他们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是客观存在的,但是那不是自己的错,因为她做过努力,所以责任应归咎于丈夫的懦弱。“她非常害怕一件事”那就是麦康伯真的发生变化,变得勇敢了。她的恐惧来自于他们之间关系的根基很可能发生不可扭转的变化。我们知道,他们之间的伦理关系是较为稳固的,但现在很可能会陷入“伦理混乱”之中。《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术语解释”中是这样解释“伦理混乱的”:
伦理混乱即伦理秩序、伦理身份的混乱或伦理秩序、伦理身份改变所导致的伦理困境。……把人同兽区别开来的本质特征就是人具有伦理意识,这种伦理意识最初表现为对建立在血缘和亲属关系上的伦理身份的确认,进而建立伦理秩序。由于身份是同道德规范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身份的改变就容易导致伦理混乱,引起冲突。[5]
当然,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看,伦理身份的混乱或改变是指明确的身份出现了混乱或发生了改变。例如,聂珍钊先生曾说:“《哈姆雷特》中克劳迪斯身份的改变,从而导致哈姆雷特复仇的伦理障碍,最终酿成悲剧。”[5]这里的克劳迪斯身份的改变是因为他娶了哈姆雷特的母亲,而从伦理的角度讲,哈姆雷特不能向继父复仇。在《麦》中,即使麦康伯身上真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与玛格丽特的夫妻身份也不会改变,丈夫还是丈夫,妻子还是妻子,不过,我们这里所说的“伦理混乱”中的身份改变,是指内在角色的变化,或者说,是指他们之间关系中谁将处于主导地位的变化。当然,最大的变化是夫妻关系的坍塌。
麦康伯真的脱胎换骨了,面对迎面猛冲过来的野牛,他直挺挺地站着对着它的鼻子开枪。他与野牛最后的距离还不到两码。而此时的玛格丽特“眼看公牛的犄角要冲到麦康伯的身上,就用那支6.5口径的曼利切向那头野牛开了一枪,谁知道却打中了她丈夫的颅底骨上面约摸两寸高、稍微偏向一边的地方”[2]47。很有意味的是,海明威描写了麦康伯对遭受这一枪的感受:
他感到突然有一道白热的、亮得叫人睁不开眼的闪电在他的头脑里爆炸,这就是他的一切感觉。[2]47
三、玛格丽特的恐惧
《麦》提供给读者或研究者最大的悬念是,玛格丽特是否是在有意地向丈夫开枪。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品为什么能够引起这样的悬念。引起悬念是因为小说揭示了玛格丽特的厌恶,并从麦康伯的实际转变中,表现了她真实存在的恐惧。她的恐惧才是小说真正的压倒性主题。导致玛格丽特恐惧的原因有两点,一是麦康伯性格的突变,二是她与威尔逊的关系。
导致她恐惧的原因首先是麦康伯性格的突变。前面说过,玛格丽特的恐惧来自于他们之间的伦理关系陷入了“伦理混乱”中,小说有一段常被人们忽视的关于他们之间关系的描写:“再说,他宽宏大量,如果说,这不是他的致命弱点,那么,就是他最大的优点了。”[2]29对妻子的放荡行为表现出宽宏大量,是麦康伯性格懦弱的突出表现,但对乱性的妻子而言,这当然就是他最大的优点了。玛格丽特睡进威尔逊帐篷的第二天早上,小说描写到了他的“宽宏大量”(懦弱):
天还没亮,他们三个人全坐在桌子旁吃早饭了;弗朗西斯·麦康伯发现,在他憎恨的许多人当中,他最最憎恨是罗伯特·威尔逊。
“睡得好吗?”威尔逊一边在烟斗里装烟丝,一边用喉音问。
“你睡得好吗?”
“好极啦!”这个白种猎人告诉他。
你这畜生,麦康伯想,你这神气活现的畜生。
原来她进去的时候把他闹醒了,威尔逊想,用没有表情的、冷静的眼光望着他们两人。[2]31
妻子当面背叛自己,麦康伯无法不憎恨威尔逊,但他也只能在心里骂他是畜生。他有钱她漂亮,本身平衡的关系在他的宽宏大量面前显出了他的弱势地位,所以,他离不开妻子的真正原因,除了她的漂亮之外,更多的是他自身的懦弱。现在,当麦康伯突然突破恐惧心理,表现出真正男子汉气质的时候,他不能离开妻子的基石就动摇了。麦康伯不仅很有钱,而且也长得很帅(“他被人认为长得漂亮”),一旦这样的男人获得刚毅的性格——她又是那么的放荡,玛格丽特就无法掌控自己的丈夫了。伦理关系的突变,即人物内在角色孰重孰轻的转化,导致了她的恐惧,并构成了小说独具特色的开放式结尾。事实上,通过威尔逊的眼光,作者已在小说开始不久就提到了她的恐惧:“她们变得冷酷以后,她们的男人就得软下来,要不然,就会精神崩溃。”精神崩溃就是她恐惧的最终体现。
导致她恐惧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她与威尔逊的关系。她与威尔逊私通不仅因为她原本就是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而且也因为他在与麦康伯的对比中显出了男人的本色,甚至于在与他的私通中获得了羞辱胆小鬼丈夫的快感。她公开与他调情(她在打猎的车上双手放在他肩上,他扭头时她亲了亲他的嘴),肆无忌惮地到他的帐篷鬼混(面对丈夫质问她为什么又干这种事时,她柔情蜜意地说:唔,现在又干了),这一切都表明她完全无视丈夫的感受,她与威尔逊的私通在丈夫胆小懦弱的面前似乎充满了正当理由。但是,胆小懦弱的麦康伯突然变得像威尔逊一样显出了男人本色,这就把她私通的正当性消解了。她看着威尔逊,他与昨天一模一样,当时她头一回发现他的本领有多大。但是她现在看到了弗朗西斯·麦康伯身上发生了变化。[2]44她头一回发现他的本领有多大,既可以指他猎杀狮子的勇气和本领,也可以指他在男女性关系方面的出色表现。她为什么会注意观察威尔逊有没有变化呢?这是因为麦康伯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在麦康伯变成真正男人的时候,她与威尔逊“光明正大”的偷情就变成了她与麦康伯保持正常夫妻关系的障碍。上述描写中的“威尔逊没有变化”一句很奇怪,威尔逊当然没有变化,但这句话暴露了她的心理,即她与他之间的私通关系是无法改变的,而麦康伯却改变了;如果不是私通行为构成了夫妻关系继续存在的障碍,那就是麦康伯的变化构成了她继续与别人私通的障碍。
总的来看,玛格丽特的恐惧是在他们仨人的言行中产生的,是一种拒绝理性梳理的心理变化;她的恐惧即精神崩溃,是她自身也无法掌控的,所以,麦康伯毙命的悲剧就无法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