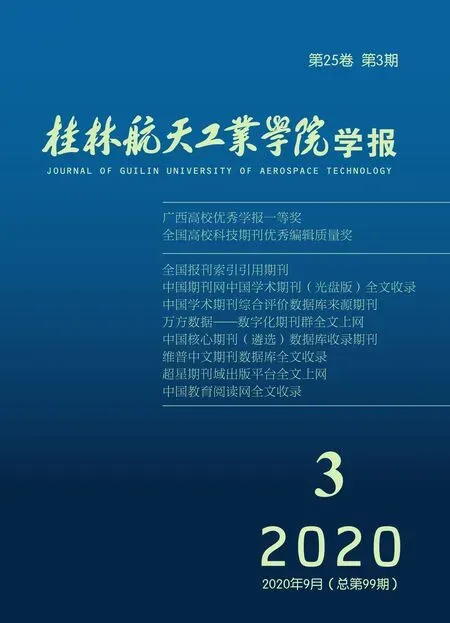艾丽丝·门罗日常生活中的哥特式书写*
张芳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外语外贸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艾丽丝·门罗(Alice Munro, 1931—) 是加拿大最负盛名的短篇小说家,她将大量的哥特手法运用到创作实践中,并加以个性化处理,融入了加拿大偏远小镇独特的社会、经济、历史和文化营造的地域色彩,被视为加拿大南安大略哥特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作品没有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也鲜少歇斯底里的呐喊和呓语,通篇都是对日常琐事喋喋不休和极为写实的描述。看似平淡无奇、细碎繁杂,仿佛女人们家长里短的闲话,但熟悉、平静的生活表象之下,却暗流汹涌,充满了哥特的气息,诉说着生活的黑色,形成了独特的“门罗式哥特风格”。与强调暴力、 血腥和恐怖场面的早期哥特小说不同,门罗更执着于去捕捉南安大略小镇居民,尤其是小镇女人们的生命瞬间,用犀利的笔锋去敲开小镇古板生活的裂隙,窥探潜藏其下的隐秘。读她的小说,就好像在研读自己和邻居们的人生,不经意间,一切变得面目全非。那些曾经熟悉无比的生活日常,在作者不动声色的叙述中渐次变得陌生和诡异,让人心惊顿悟:哥特无处不在。
1 人性“黑洞”
哥特文学被视为“黑色浪漫主义”,其黑色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在情节上,它浓墨重彩地渲染暴力与恐怖;在主题上,它不像一般浪漫主义那样从正面表达其理想的社会、政治和道德观念,而主要是通过揭示社会、政治、宗教和道德上的邪恶,揭示人性中的阴暗来进行深入的探索,特别是道德上的探索”[1]。极具“黑色性”的暴力死亡情节便成了哥特作品中经典的元素。
在门罗的创作中,哥特式暴力遍布于生活的每个角落,也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如影随形的死亡阴影是人物内心“恶”的释放,也是人性最阴暗恐怖的欲望的展现。但是死亡本身并非门罗关注的焦点,对于死亡的血腥,作者向来不做刻意的渲染,着墨甚至几近吝啬。门罗的成名和处女作《快乐影子之舞》收录了一个短篇,题名为《死亡时刻》,但作者却避开了对死亡事件本身的描述,通篇对死亡时刻的提及仅有寥寥几个字“他死了,就是死了,他确实死了!”[2]124余下的一切均留给读者去自行想象。无独有偶,在另一部短篇《孩子的游戏 》(出自短篇小说集《幸福过了头》)中,作者对死亡事件也语焉不详。死亡时刻在女主人公马琳支离破碎的回忆中闪烁其词,“要是说那时候,阴沉的云彩渐渐散了……或许是我们手掌下那块橡胶不再挣扎的时候——太阳出来了”[3]257。整个死亡场面被描写得冷静而客观,不带任何评判。即使在门罗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死亡故事《多维的世界》中,父弑子的场面也写得极为克制简略,采用白描的手法寥寥数语,未加血腥的渲染和刻意的煽情,血腥刺激几近于无。“季米特洛在自己的婴儿床里,婴儿床倒在走道上。芭芭拉躺在床边的地板上,似乎是掉下了床,或者是被拽下了床。沙沙在厨房门边上——看起来他想逃,只有他的喉咙上有伤口。其他的孩子,是用枕头干的。”[3]19
尽管门罗的死亡叙事避开了强烈的感官刺激,可是当读者细读这些文本,将整个碎片化的叙事重新整理,品出其中层层隐埋的真相,寒意就会直击人心,让人禁不住倒吸一口气,产生英国女作家安·拉德克利夫(Ann Radcliff,1826)所说的“心理恐怖”。 安·拉德克利夫认为哥特式小说实际上可以区分为“心理恐怖”和“本体恐怖”两个类型。前者以“恐惧”(terror)为目的,作品中很少或几乎不出现超现实主义的幽灵,而只是通过充满悬念的“未知物”存在,暗示可能发生的凶险,从而“扩充灵魂,使各种功能警醒到生活的高程度”;而后者以“恐怖”(horror)为目的,通过赤裸裸的超现实主义的暴力、凶杀等描述,刺激人的感官,使灵魂凝聚、冻结,甚至湮灭[4]。门罗作品中的死亡叙事重在呈现人物的隐秘心理,通过对死亡事件不动声色、似是而非的讲述,让原本简单的故事情节充满了诡异、神秘和恐怖的氛围,达到骇人听闻的效果,让人在唏嘘感叹的同时又发人深思,震撼心灵。
在门罗笔下,死亡来得如此诡异,又如此莫名。《孩子的游戏 》的女主人公马琳只有十岁,她和密友沙琳在一次游泳课上将邻居维尔娜的头按在水里致其溺水身亡,起因仅仅出于孩子“排他”的偏见。邻居维尔娜是个有智障的孩子,马琳将其视为“异类”,对她产生了不明的敌意和病态的恐惧,并莫名地把她“妖魔化”成长着“蛇一般的头颅”的哥特式怪物。无论维尔娜如何示好,马琳对她的憎恶和恐惧只增不减,最后甚至将其臆想成了自己的“迫害者”。尽管两位稚童起初并没有谋杀的计划,但当时机来临时,排除异己的本性让她们瞬间动了杀机,酿成了最终的惨案。更令人心惊的是,施暴后的两个当事人“并没有罪恶感”,眼睛里还“充满了喜悦的神采”[3]257。 通过对两位少女杀人犯的塑造,门罗将儿童内心深处潜在的动物本性展露无遗。
《死亡时刻》同样讲述的是一个孩子的死亡事件:十八个月大的小婴儿本尼因为长姐照顾不当,被意外烫伤不治身亡。作者对整个死亡时刻的描述是极简式的,她将大量的笔墨聚焦于事故之后各种人物的反应和表现,借此来探讨人性的微妙幽暗之处。事故发生后,父亲喝得酩酊大醉借酒来逃避责任;母亲伤心欲绝地尖叫:“不要让我看见她,我不会忘记我的儿子的”,将所有过错归咎于只有九岁的大女儿帕特里夏身上,并拒绝让她参加本尼的葬礼;邻居们挂着“仪式化的悲伤、同情的面具”,说着“仪式化的安慰”[3]119。虽热心帮忙,却难掩对这家人的轻视;弟弟乔治“胜利一般”地挑衅姐姐:“他死了,就是死了,他确实死了!…就是她的错!”只有帕特里夏强自镇定,“似乎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过”[3]126,独自默默地吞噬着苦涩的滋味。父母们只顾着自己的伤心,弟妹们完全不懂事,邻居把这当作谈资,没有人真正关心过小小的帕特里夏承受了怎样的心理压力,在如常生活的若无其事之后有着怎样的伤心、委屈、愧疚和恐惧。众人的漠视最终让这个原本有着极高音乐和表演天赋的小姑娘走入了疯癫。《多维的世界》则探讨了婚姻关系中的家庭暴力问题。劳埃德因妻子未经他的许可买了降价面条而争吵,导致妻子离家出走。暴怒下的男人毫不手软地杀死了自己的三个孩子,以此来惩处越界的妻子。这种疯狂暴力的发泄,是男性霸权意识不断强化,直至走向极端、偏执后的必然结果。
门罗的死亡故事体现了作者一贯的“于无声处听惊雷”的风格,始于平淡而终于震撼。语言精练,情节简单,通过拼图式的讲述打造哥特式的叙事迷宫,制造扑朔迷离的诡异氛围,营造一波三折的哥特悬念,揭示人类变化莫测、复杂阴暗的心灵状态,探讨关于人类潜在暴力的伦理问题。借助哥特叙事的强烈震撼力,唤起了人们对那些看似无比“正常”的生活下面冲涌着的暗流的深度关注,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和感染力,深化了作品的主题。
2 暴君“城堡”
禁锢与隔绝是哥特小说中另一普遍表现的主题。从哥特小说诞生伊始,女性因男性的欲望被禁锢与隔绝的故事就一直在上演。《奥特朗托城堡》中的哥特恶棍曼弗雷德不顾乱伦禁忌,拘禁亡子的未婚妻伊莎贝拉为自己延续子嗣;纯洁善良的爱弥丽被觊觎其财产的姑父莽托尼囚禁在群山之间的尤道弗孤堡里;疯癫的伯莎被绑缚于桑菲尔德庄园暗无天日的阁楼中;与世隔绝的呼啸山庄成了伊莎贝拉的婚姻牢笼。在女性哥特视阈下,这些“作品中普遍存在的一些密闭空间意象,例如幽暗的古堡、神秘的老宅等,……象征着禁锢女性自我的父权社会”[5],充斥着男性对女性的暴力压制和强权胁迫以及女性心理上难以言说的恐惧和压抑。现代女性哥特小说已跳出传统哥特小说的框架,故事的发生地不再是魅影重重、遥远的中世纪古堡,而是当下的现实环境,家宅之地已经替代哥特式的城堡和荒芜破败的修道院成为禁锢女性的主要空间隐喻。
传统的父权观念主张“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要求女性必须以家庭为中心,满足于操持家务和相夫教子的性别角色,做个服从、服务于男性的“好女儿”“好妻子”和“好母亲”。 家庭被视为女性命定的归宿,狭小、封闭的家庭空间也因此成了女性遭受禁锢和隔绝的一个重要象征。作为一名女性作家,门罗始终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在父权社会中苦苦挣扎的普通女性。她的许多作品围绕家庭这一空间来探寻女性的生存境况,展现女性在男权思想压制下的哥特式的生活图景,书写女性“被禁闭在‘女性化’的角色、被禁闭在父权中心的屋子之中的种种感受,以及她们试图逃离那些角色或者屋子的强烈的欲望”[6]400。
在门罗的创作中,厨房空间被赋予了丰富的性别隐喻。偏于家中一隅的厨房,是女性接受规训的专属空间,其边缘、角落的位置象征着女性在家中从属的地位。于是,《男孩和女孩》中的女主人公将厨房视为哥特式的女性世界,极力想要摆脱。故事中的女主人公是个没有名字的小女孩,小小年纪便隐约认识到男女生存空间和社会地位的差异。日复一日在厨房操劳忙碌的母亲很少出现在家门之外。尽管为家庭付出了很多,自身的价值却得不到认可和尊重。在狭小的空间里做着“分内之事”的她永远只是男权文化空间中一抹模糊的背影,扮演着“他者”的角色,默默无闻,无足轻重。母亲黯淡无光的生活让年幼的女主人公对自己的未来日子产生了一种焦虑和恐惧,她本能地想要逃离母亲所属的那个禁锢和规训女性的厨房空间,进入父亲所代表的那个自由和充满尊严的“男性世界”。 于是,她对逼她做家务的母亲极为反感,将其视为“敌人”。对父亲她则充满了仰慕,渴望成为他的帮手。她以为,只要她能够逃离厨房这一幽闭的空间,确保自己作为父亲助手这一角色,就可以重新定义自己的性别角色,摆脱被禁闭在家庭藩篱之中的命运。然而,在一个“任何超出性别定势的追求不仅仅是错误的,而且是遭禁忌的”[7]的文化环境中,小女孩的抗争显得可笑而无力。在众人的合力压制和思想灌输下,女主人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社会的规约,回归了女性的世界。
在性别空间里,家庭虽然被视为女性既定的活动场所,但是在这个私人的空间里女性只有操劳的职责,却没有支配的权利,空间的控制权仍牢牢掌握在男性的手中,女性的一切行为都受制于男性家长所制定的“生活规则”。因此,家于女性而言是没有实体的“全景敞视监狱”,处处为男性所监视和操控。《庇护所》中道恩姨妈的家便是这样一个“全景敞视监狱”, 家里的一切尽在贾斯珀姨父的掌握之中,“房子是他的,菜单要由他来定,广播和电视节目要由他来选。即使他在隔壁坐诊,或者出诊,一切也必须时刻准备着得到他的许可”[8]104。在这个父权制的监禁框架中,姨妈只是奉命行事的“管事”,没有任何的话语权,每日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努力让自己的丈夫满意、争取他的欢心”[9]33。吃饭得姨夫先拿叉子,饭菜的口味得问过他的意见,获准微笑的时候就立刻微笑。偶尔没让丈夫称心,姨父难看的脸色、冰冷的目光、不留情面的斥责就是对她最大的惩罚,让她惴惴不安,痛悔不已。有一次,因饭菜不合口味,贾斯珀姨父一句“我不喜欢”,就让姨妈瞬间“笑容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紧绷的嘴唇和英勇的自我控制”[8]33。新搬来的邻居邀请他们夫妇俩去家里喝茶,缺少社交生活的道恩姨妈没有拒绝的经验,贾斯珀姨父虽然最后如约去了邻居家,但却没有原谅姨妈接受邀请这个莽撞的错误。也许是压抑了太久,隐忍多年的姨妈竟然更进一步违抗了丈夫的旨意。趁姨父参加县医生年度大会时偷偷回请邻居和不受姨父待见的姐姐以及一些音乐家来家里做客,甚至兴奋地忘了丈夫回家的时间,贾斯珀姨父的震怒是可想而知的。丈夫在客人面前不留情面的指桑骂槐第一次让姨妈深刻认识到“男人的家就是他的城堡”[8]36,他才是这个空间主宰者,绝不容许女性任何一点挑衅。
一些经过女权思想洗礼的知识女性,想要走出家庭去寻找自我的空间,却发现想要逃离父权社会所圈定的家庭空间是那样的艰难。《办公室》的女主人公是个跟门罗一样有着写作梦想的年轻妻子,渴望暂时逃离困陷自己的家庭琐事,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可以身心独处,不受打扰地专注写作。然而,偌大的花园房子却容不下她的书桌。孩子、丈夫和家务时刻提醒着她作为贤妻良母的职责,要将她逼回“家中天使”的角色。不甘于埋没于琐碎家庭生活的女主人公向丈夫提出租一间办公室来写作。尽管她征得了丈夫的同意,走出了家门,如愿租到了一间办公室,可是却无法“冲进社会的‘铁门’”[10]。在这个本该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间里,年轻的女作家依然没有逃脱男性窥探和注视的目光,走出男性控制的阴影。房东麦利先生是那个时代男权文化的典型代表,看不惯一个女人将丈夫和孩子抛在一边,“把自己的时间花在咔嗒咔嗒的打字上”[2]91,也不能容忍一个女人拥有一个秘密的空间,将男性排除在外。于是,他以强势的姿态想要进入这个空间,将其置于自己的监控之下。他时不时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敲开办公室的大门窥探作家的动向,并试图将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她。大到写作的主题,小到房间的小摆设,喋喋不休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或直接强行送来。甚至还趁女主人公回家后,私自进入办公室偷看她的写作稿件。一气之下,女主人公不再出于礼貌打开大门招待麦利先生。被拒门外的房东感觉自己的男性权威受到了挑战,于是频频在办公室的门上贴上内容越来越恶毒的便条,给她安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女主人公的置之不理进一步激怒了他,让他彻底失去了理智,诬陷她在盥洗室涂画淫秽图案,名声受辱的女作家最终不得不忍痛放弃这间女性自我的空间,重回家庭。
3 双重“自我”
莫尔(C.D.Moore)认为“典型的女性哥特女主角兼具天使和魔鬼两个身份, 通常魔鬼的自己被深藏,而天使的自己呈现在大众面前。 因为在父权条款下,天使的自己更受欢迎”[11]17。在父权社会中,“天使自我”是社会对女性的期望,也是女人对自己角色定位的镜像认同;“魔鬼自己”则是不为社会规范所接受的第二个自我,是另一个会受到社会驱逐的黑暗 “异己”。在父权社会中,女性为了求得生活的安宁常常不得不屈服于外界的力量,压抑“魔鬼自我”,选择扮演那个顺从的“家庭天使”,如《呼啸山庄》中的凯瑟琳、《吕蓓卡》中的吕蓓卡。
这种“双重性”的自我冲突在艾丽丝﹒门罗本人身上也可以找到。年轻时的门罗醉心写作,但是在她所生活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加拿大,女人的命运就是相夫教子,操持家务, 女性的写作抱负如同鸡肋一般,并不为社会所认可,反而会招致人们的嘲讽,认为她逾越了女人的本分。因此,门罗不得不隐藏起她的作家梦想,将创作的追求转入地下,开始了分裂的“双重生活”——忙忙碌碌操持家务的贤妻良母式和利用家务间隙时间躲躲藏藏写作的作家生活。这种挣扎于“天使自我”与“魔鬼自我”分裂之间的生活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门罗的故事中。
《女孩与女人们的生活》中的女主人公黛尔的母亲艾迪是一个经过女权主义洗礼,对知识充满狂热崇拜,拒绝接受男性社会对女性性别角色的定义,积极争取自我发展的空间,具有自强自立意识的“新女性”。她忙于上街售卖百科全书,给报社写信,并因此疏忽了家务活,被亲戚和邻居们视为“不守本分”的主妇,荒诞可笑的怪人,受到了众人的侧目和社会的耻笑。母亲的遭遇告诉黛尔:在小镇旧固的环境中,任何逾越或违抗性别角色规范的行为都会招致人们的挞斥,贬低自己的道德价值和社会价值。在黛尔看来,母亲这种公然的反抗是不明智而危险的行为,也是不懂得保护自己的表现,并为之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被整个小镇社会孤立和抛弃在外。因此,尽管她意识到自己在很多方面其实和母亲很相似,比如对知识的热爱,对写作的热衷,对“秩序和完整,错综复杂的城市生活”[12]的向往,但聪明的她却像女性哥特女主角们一样地将自我的这一面隐藏起来,做个表面上循规蹈矩平常的“好女孩”。母亲可以看作是黛尔隐藏在心灵深处的另一个自我,一个不敢言明的黑暗“异己”。 她对自己这个他性“异己”的掩盖实际上是对自我完整性的一种保护,也是在父权制下存活的一个聪明的选择。只有通过表里不一的策略,藏在公开的“天使”面具背后,掩饰男性文化所不容的“非女性”自我,女性才能在父权社会存活下去,秘密地寻求女性的自我定义。
在门罗的小说文本中,歌特已然变脸。多年来,她植根于加拿大安大略西南小镇的日常生活,描摹小镇女性在琐碎庸常的生活之中苦苦挣扎的人生百态,挖掘隐匿在现实之下的“黑洞”,呈现庸常生活背后的黑色暗流,展现出南安大略独有的哥特景致。其作品缺少传统哥特小说的要素,如遥远的年代、幽深的古堡、邪恶的幽灵等,她所关注的是当下生活中的哥特式体验。 哥特式的梦魇不再是来自于超自然的鬼怪幽灵,而是潜藏在平和的生活日常之中。这些平日里被理性所掩盖和隔离的生活“异常”可能是隐秘内心难以言说的欲望,也可能是游离在道德边缘的恶意,蛰伏在人们的内心深处,等待时机,借由一些荒诞离奇的偶然事件,以最猝不及防的方式爆发出来,催化出极大的破坏力量。利用哥特这一表现人类黑暗心理的有力工具,门罗揭示了人性中那些不经意间展现的“日常之恶”,剖析了人类内心深处长期被压抑和掩盖的非理性部分,透视出平和生活表象之下的黑色,体现了哥特文学创作的精神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