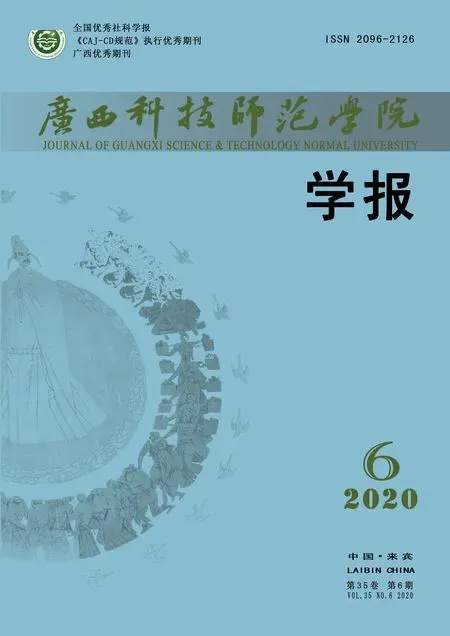论《水浒传》网络小说改编者的民间姿态
曹 金 合
(洛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河南洛阳 471934)
当《水浒传》①本文出现的《水浒传》,均指施耐庵所著的《水浒传》。展现的“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民间自由状态遇到以自由为核心理念的网络媒介载体的时候,题材和媒介的双重自由为摆脱壁垒森严的信息控制权和话语表达权的网民获得了欲望宣泄的权力。不少网民在网上冲浪时将传统的社会分工以及不容质疑和违反的规则与制度抛到九霄云外;现实生活中久遭压抑的生命个体按照主体哲学和江湖社会学的原则,在赛博空间里播撒和延异出的匪夷所思、脑洞大开的艺术符码对层级分明的文化意蕴予以颠覆和消解。因此,“过去被认为坚不可摧的文化概念如同经历了其后果不可估量的地震一样动摇了”[1]。对照施耐庵的《水浒传》表达的忠义、英雄、庙堂等大传统和尽孝、帮派、江湖等小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水浒传》网络小说改编者更倾向于以“我”为中心的小传统,遵循“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自由表达的本然原则,淋漓尽致地展示欲望化和低俗化的民间文化抒写模式。立足于现实的英雄退位、众神狂欢的无名时代的话语表述语境,网络改编者采取戏仿、讽刺性模拟的改编策略使古典的《水浒传》有了现代新生境地。在此过程中,“一方面,强调个人感受与经验的主体性地位,最终达到突出主体创造性的目标;另一方面,通过诙谐文本的哈哈镜,对生活进行复制、重组、夸张、变形,改变它的常态,凸现它那不易于为人们所注意的一面,达到解构生活的同时建构生活的民间精神目标”[2]。这是摹本在秉承解构与建构的和而不同的原则之后,形成的富有个性创新色彩的艺术结晶,使每个人的个性意识都在或长或短的文本编写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如果我们没有看到这种有感而发的抒写目的背后体现的改编者的创新意识和伦理诉求,就无法理解大传统与小传统、正统文化与异端文化、国家观念与个人观念、狂欢解构与潜在建构的二元对立中体现的民间姿态。
借助网络的匿名性、开放性、自由性的媒介特征,地位卑微的改编者把自己内心的情感与欲望附着于《水浒传》中某个人物形象身上,对原文本人物的出身、身份、地位、脾性和气质采取“脱冕”和“加冕”的狂欢化方式颠倒一切,“把一切高级的、精神性的、理想的和抽象的东西转移到整个不可分割的物质—肉体层面、大地和身体的层面”[3]。这样,高贵与卑贱的颠倒、英雄与小人的含混、物质与精神的转换、动机与目的的错位,就成为小人物表达自身隐秘欲望的形象载体。日记体小说对高大上的英雄人物的隐私、心理和情感进行披露;穿越小说对小人物偶然进入异空间、满足“我为英雄”的意淫进行描摹;大话小说对英雄和凡人的喋喋不休的一腔废话进行尽情展示。这些只不过是作为小人物的改编者在“压抑—反弹”的心理机制下,“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来做狂欢化的白日梦而已。
一、日记体小说:改编者的欲望暴露
由于日记体小说中的叙述者“我”可以将内心最隐秘的人性意识、情感心理和欲望诉求借助鲜活的情节和细节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可以不顾忌现实社会中传统的伦理道德与人际规范的规训和惩罚,因此许多惊世骇俗的言论和为当时僵化保守的世俗社会难以容忍的叛逆行为都可以非常轻易地以“我”为载体来表露。从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鲁迅的《狂人日记》,到庐隐的《丽石的日记》、周作人的《真的疯人日记》、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从中国作家何顺学的《陈小西日记》、林日暖的《第三本日记》,到外国的多丽丝·莱辛的《好邻居日记》、奥斯卡·帕尼查的《来自一只狗的日记》、井上靖的《淀殿日记》、卡夫卡的《地堡日记》和果戈里的《狂人日记》等,这些日记小说表达的思想观念虽不同,却同时暴露出古今中外、身份各异的创作主体对日记文体的情有独钟。网络改编者也对用日记表达自己情感和思想的文体形式非常感兴趣,但并不是像鲁迅、丁玲、卡夫卡、果戈里等经典作家那样表达十分严肃的思想主题,而是为了充分满足“本我”的快乐需求和“自我”的现实欲望,这就是他们典型的叙事姿态。因此,他们在打破创作资质认证的最低标准、消除了浅薄幼稚的涂鸦之作“出场”的焦虑之后,表达自己“小狗”叫唤般的最得心应手的载体工具就是日记体小说。改编者看中的就是第一人称限制视角诉说的真实性、亲切感和代入感,更能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解构方式将英雄人物拉下神坛。所以,以《水浒传》中的英雄人物为参照的对象,网络改编者在日记体小说中让大名鼎鼎的英雄人物自曝其短、自揭其丑,在英雄人物隐秘心理的“脱冕化”与外在行为的“加冕化”的矛盾冲突中获得狂欢的感受。
以日记体的形式解构《水浒传》中最有噱头意味和心口不一的卑劣心态的英雄人物就成为“码农”们的拿手好戏,也是宣泄他们物欲和情欲的最佳艺术载体。仓土的《李逵日记》、王小枪的《孙二娘日记》之所以分别选择黑旋风李逵和母夜叉孙二娘作为解构英雄意蕴的符号,是因为李逵直率莽撞的性格和孙二娘“巾帼不让须眉”的英雄气质有太多被遮蔽的疑点。因此,改编者采取逆推法,反其道而行之就可以让原本习焉不察的人物的烟火气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也可以在能指与所指的错位、高尚与卑劣的漶漫、口是与心非的对比中体会码字的快感。在《李逵日记》里,李逵对领导者们官场沉浮的细致观察,简直就是一部当代妙趣横生的官场现形记。《孙二娘日记》倒是按照日记体的形式,从“1101 年 正月二十 多云”记到“1103年 十一月二十 多云转晴”,近三年的日记全是欲望化的日常生活琐事。《水浒传》中那个不解风情的孙二娘,在日记小说中却成了款款情深而又多愁善感的女子。何明敏的《宋江日记——及时雨的“飞升”传奇》与张志玲的《宋江日记——我的处世心经与管理心法》,都不约而同地选择“及时雨”宋江作为颠覆和消解的靶子,这主要是因为《水浒传》中一把手宋江的为国尽忠、为父尽孝、兄友弟恭、朋友义气的高风亮节太让人生疑。网友采取佛头著粪的亵渎意识和颠覆神圣的时髦作派,对原著中高不可攀的首领宋江予以贬低化、权术化和欲望化,就成为情理之中的事情。日记假借宋江自我道白的揭秘方式,将一个微不足道的郓城衙司充分运用权术扬长避短,最终成为众人仰慕、震动朝廷的草莽枭雄的形象刻画得活灵活现。
如果改编者仅仅以《水浒传》中的英雄人物作为自己表露心迹和展示姿态的对象的话,就必然受前文本的人物性格、生活环境、交际模式和兴趣爱好等复杂的历史文化语境的影响和限制,也不能随心所欲地编造自己最喜欢的情节,来与叙事者“我”的性格气质充分融合,以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为了解决第一人称叙事与前文本的语境限制带来的矛盾冲突,张苡陌的《水浒日记》干脆编造了一个与《水浒传》中的混江龙李俊同名同姓却没有任何关系的农村毕业生李俊作为第一人称叙事者,顺便将人物生活的环境设置为与水泊梁山没有丝毫关联的水浒书院。小说通过大宋国立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李俊的视角进行叙事,以嬉笑怒骂的文笔精心描绘了一幅水浒社会的复杂绚丽的浮世绘。改编者在对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的世俗生活的琐屑描绘中,诠释一种“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北岛的《宣告》)的卑微诉求。
二、穿越小说:改编者的英雄梦
《水浒传》中的英雄人物身上体现出的急公好义、扶危济困、打抱不平、勇敢豪爽、洒脱无私等优秀品质,成为改编者潜藏于内心深处的英雄崇拜情结。著名学者张炯指出:“文学艺术里的正面人物和英雄形象不但体现了一定的社会理想,还体现一定的道德信仰和行为规范,而且还往往表现一定的时代精神乃至民族精神。因而这样的人物形象也往往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偶像和楷模,具有巨大的精神影响力和精神凝聚力。”[4]正是前文本塑造得栩栩如生、令人无限敬仰的英雄人物的道德品质,成为改编者“影响的焦虑”的最根本的原因,无论英雄人物的个性意识,还是表现人物形象的艺术技巧,都成为后来者难以逾越的大山。因此,借助虚拟的网络时空形成的穿越小说的文体模式,改编者就可以在充满神秘感、好奇感、不确定性和陌生化的异空间中,获得超脱现实束缚的无限自由的想象力。其实,从改编者不厌其烦地采用穿越小说这种通俗化和大众化的文体形式表现的心理诉求来说,“‘穿越时空’这样的文学母题,使人类在文学想象中实现了对自身既定时空规定性局限的超越,体味到最大的精神自由和快乐”[5]。改编者对现实中熟悉的时空关系的打破,体现出其对异时空中如何进行自我确证的本体论问题的思索,反映的是依附于英雄人物身上改变历史走向和人物命运的白日梦的冲动。改编者在运用当代的思维、知识和文化描绘古代水泊梁山的各路英雄逆天改命的惊人壮举中,得到如电影《私人订制》中书店小老板扮演英雄那样的快乐。
这些形形色色的满足小人物英雄欲望的穿越小说,其中一部是一剑飘红的《梁山好汉混迹现代黑帮》。该小说以一阵闪电作为跨越异空间的媒介,将水泊梁山的宋江、李逵、武松、鲁智深等好汉穿越到现代都市社会,让这些好汉纵横现代黑帮社会。这是一部没有另外虚拟一个带有改编者情感色彩或代入角色的英雄的穿越小说。其他穿越小说里的主人公,都因偶然的机缘穿越到古代,充分运用现代人的智慧,在对整个局势的宏观把握、战争的策略、攻心的计谋、驭人的权术等方面展露才华,在众星捧月般的恭维氛围中得到现实生活中得不到他人重视的匮乏心理的补偿。从不受待见的小人物到叱咤疆场的风云人物、从底层的草根到高层的领袖、从卑微的处境到高贵的身份、从唯唯诺诺的行为处事风格到一剑封喉的豪爽果敢,都体现出改编者根深蒂固的英雄情结。恩泽仔仔的《煞星再降之梁山好汉》中的现代中学生陈昕贤和月神鐮刀的《极品梁山》中遭受恶霸欺凌的懦弱孩子宋姜,都转世为人上人“宋江”,确实是改编者遵循心理备受屈辱后的“压抑—反弹”机制做的一个补偿情感慰藉的白日梦。比如在《极品梁山》里,生活在现实社会的宋姜沉迷于梁山世界、醉侠世界、武侠世界和玄幻世界的幻想中不能自拔,是因为他追求没有世俗的浮躁喧嚣、没有人际关系的尔虞我诈、也没有恶人横行霸道的虚拟世界的生活。这种自在、自由和快乐的生活无法在冷冰冰的残酷现实中得到实现,就只好借助奇幻和玄幻的方式,穿越到异空间中去当梁山众好汉的首领宋江。主人公收服神行太保、调戏李师师、仗义助林冲、智救林娘子、大破十三杀阵、梁山排坐次、登极称帝,带领天下最优秀的锻造师、神医、剑术大师、神箭手、机关师纵横江湖,体会到了首领意志和计谋实现带来的名利双收的生平快慰。在水月双城的《夜水浒》中,心理备受压抑的公务员劭青云,在夜间化身为晁天王与宋江斗智斗勇,在众英雄面前树立自己的领袖威信。这与月神鐮刀的改编策略如出一辙。只不过水月双城采用主人公“庄周梦蝶”式进入自由自在的梁山世界,恰好是对改编者处于现实生活中左右掣肘、无法实现自己宏大人生抱负的心灵折射。叙事者通过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鲜明对比,暴露出备受压抑和委屈的草根阶层渴望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梦想姿态。
既然是穿越到一个不受现实生活的法律道德和人际关系规约异质世界,为了自己自由的梦想尽情飞翔,也就没有必要把梁山好汉的活动时空设置在大宋的疆域上,也没有必要将穿越到异王朝的代言人附着于梁山好汉的身上,成为一个受原文本的英雄人物的性格、气质和心态影响的半自由人。所以,绝大多数采纳穿越文体的改编者就无中生有地塑造出一个拥有现代人智慧,却又统领众好汉建功立业的领导者角色作为自己梦想的化身。昊龙在《梦回梁山当天王》里的梦想的脚步迈得还不是很大,只是让李剑穿越到水浒世界,成为晁盖的儿子晁春。作者采用这种无中生有的把戏,尽管可以凭借现代已知历史的智慧对原文本中晁盖和宋江的地位、命运以及众好汉因招安导致的悲惨结局进行改写,但代言人晁春生活受梁山的地域环境、血缘关系和伦理道德的影响与制约是无法改变的,原文本中某些情节脉络对虚拟的化身的为人处事的掣肘也是不言而喻的。既然这样,那么选择一个玄幻世界或者一个异代王朝作为实现自由梦想的空间载体,就是备受改编者青睐的事情。空间的改变、朝代的嬗变、人物的幻变完全打破了原文本逻辑情节的铺排,这样梁山好汉的空洞的能指与游戏的所指形成的虚拟叙事,更能将改编者的自由心态暴露无遗。因此,被划过的夜的《梁山好汉逐鹿三国》中的戒色与苏行无期的《梁山好汉闯东汉》中的刘浩,都穿越到烽烟四起的三国时代,为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横空出世创造出最有利的条件。如苏行无期虚构文弱书生刘浩魂穿三国,率领卢俊义、林冲、关胜等将领,采纳军师吴用、公孙胜、朱武等人出奇制胜的谋略,对三国时期群龙割据的曹操、刘备、吕布、袁绍等进行挞伐,终于实现一统三国、成就霸业的梦想,这也不过是改编者心目中难以释怀的“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侠义梦而已。可能有的改编者觉得将众梁山好汉的活动空间和身世背景挪到三国还是要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不能大踏步地在虚拟空间中畅快遨游,于是干脆在新造的异世王朝中提供穿越者带领众好汉施展才华的舞台空间。禽时的《梁山好汉之异世王朝》描绘了一个农村普通中学的高三学生江堤穿越到天武大陆的世界,以《梁山英雄宝典》为介质,用自己的血液唤醒梁山好汉,在天城江家和星魂学院的异度空间中伏妖降魔。
三、“大话体小说”:改编者的话语狂欢
《水浒传》网络改编者跨专业、跨行业的玩票性质的业余抒写,其实正是现实生活中小人物没有话语权、内心憋屈却又无处发泄的“苦闷的象征”。现实生活中隐形的等级观念、处事标准和交际潜规则都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难以忍受的,他们迫切地希望借助幽默的笑声颠覆高雅与低俗、严肃与滑稽、正统与异端、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壁垒森严的界限。这种以水浒英雄为载体,玩弄文字游戏、调侃僵化的教条模式、嬉笑虚伪的道德观念的“无厘头”式的改编“充满了两重性的笑,充满了对一切神圣物的亵渎和歪曲,充满了不敬和猥亵,充满了同一切人一切事的随意不拘的交往”[6]。通过“上半身”与“下半身”的颠倒错位,改编者将小人物打破话语门槛的狂欢精神和炫耀话语权的姿态展示了出来。正如对梁山好汉林冲世俗性和欲望性的改编而闻名的网红写手稻壳所认为的那样,他的《流氓的歌舞》一举成名“最简单的原因,就是因为里边还有一些幽默感吧。有人对我说,看这篇东西,从头笑到尾。我这个人比较随便,也比较喜欢开玩笑,所以写小说也不喜欢板起面孔来,小说首先应该具有娱乐性,必须让人看”[7]。也就是说,个人受压抑后产生改编的目的和动机不是严肃作家的那种“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宏大叙事母题引起的欲望和冲动,而是不受外在条件拘束的个性自由和码字的幽默快乐,这是他们更为看重的情感诉求。此时,借助水浒好汉的外壳突显文学的娱乐功能就是小人物话语狂欢的目的所在。
福柯所说的“话语即权力”的哲学内涵,不经意之间成为受《大话西游》之类的大话文艺影响的水浒改编者无厘头式话语表述的重要依据。他们就是要通过语义逻辑链条的断裂,取得话语自由狂欢的审美效果。对这种借助古典名著改编为由,宣泄胸中不平之块垒的心态,著名学者陶东风主要从话语秩序的角度予以分析,他认为:“大话文艺的基本文体特征,是用戏拟、拼贴、混杂等方式对传统或现存的经典话语秩序以及这种话语秩序背后支撑的美学秩序、道德秩序、文化秩序等进行戏弄和颠覆。”[8]所以,在大话体水浒小说中,产生最大影响效果的是林长治、肥羊、段武军等人塑造的人物的无厘头口语带来的解颐幽默的搞笑段子。他们对经典话语秩序的戏仿、颠覆和消解,无疑表明了改编者民间化的狂欢姿态。其中,林长治的《缺钙水浒》《Q 版梁山好汉》,肥羊的《大话水浒》,都走的是对话体搞笑的路子,区别仅在于林长治的水浒改编的文体形式是标准的戏剧体,肥羊则是加入了一点叙事的成分。改编者的目的就如林长治所说的:大家看《Q 版梁山好汉》时就当作像是在看《猫和老鼠》那样动画片就行了。以《缺钙水浒》为例,钙质的匮乏意味着原作中的首领、军师、英雄等都得了扶不起的软骨症。该小说里无论是“老婆长得太俊,老公就得受罪”“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章节对民间段子的借用,还是“九纹龙村中耍威风”“宋江杀婆惜的全过程”章节对原作内容面目全非的改写,突出的都是作者(号称“周星星”的林长治)对周星驰《大话西游》的模仿与创新。小说中人物在彼此的对话中穿插的现代话语与古典语境的错位而产生的无处不在的幽默感,正是拥有话语权的小人物最想达到的炫技效果。段武军的《麻辣水浒》小说里的麻辣味道,是对周星驰无厘头话语的模仿。例如,小贪官县太爷因东窗事发,被高太尉严刑处死以儆效尤,临刑前感叹:“唉,曾经有一堆真正的金叶子摆在我的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的时候才追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让我对金子说最后一句话,我会说——我爱你。如果让我给这种爱加一个期限的话,我希望是——一万年。”这一段显然是对《大话西游》中耳熟能详的那一段“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的戏仿,用正话反说的方式把贪官污吏搜刮民脂民膏的卑鄙目的和贪得无厌的丑恶嘴脸暴露出来。与此同时,时空的跨越对接也使得改编者借此机会宣泄着被压抑的愤懑,在对色厉内荏的贪官的蔑视和假真情的颠覆中享受破坏的快感。这样,母本与子本的机制观念和话语动机的同源性就决定了他们话语姿态的同一性。
网络改编的以《水浒传》为摹本的“大话体小说”,除主要以人物对语的无厘头引起狂欢的审美效果来表明作者的叙事姿态以外,改编者还以隐含作者的身份,通过对风马牛不相及的情节结构的铺排,或者是对原著情节意蕴的逻辑颠覆的叙事话语来表明创作的意图和目的。例如:杨西奇的《大话水泊梁山》与别样冷寒冰的《胡同水浒传》都是采取逆向思维的方式,以原著中的好汉作为解构的对象。改编者不相信有所谓的有情无欲的柏拉图之恋,也大胆质疑青春年少的英雄都是清心寡欲,所以对原著中人物的性格、气质、思想、情感等个性意识进行大胆改变。例如:《胡同水浒传》里,李逵本是一个饱受欺骗和歧视的老实巴交的农民,后靠打家劫舍赚的钱开了家公司,成为颇有名气、驰骋商场的李总,实现了华丽转身。作者作这样的改编,就是为了颠覆和消解原文本中“视金钱如粪土”的英雄好汉形象。在物质与精神、低俗与高尚、真实与伪装、俗人与英雄的二项对立中,运用后现代主义的思维方式对后项的解构,显示出改编者旗帜鲜明的民间价值观念。在这方面,meng13die的《大话青白》和宁财神的《在路上之金莲冲浪》,在借鉴后现代话语的边缘姿态向以传统经典文本为中心的正统典范发起冲击的时候,采用的解构的叙事策略和情节结构的路径也有所不同。meng13die采用的是经典文本杂糅的方式,将《水浒传》融合《白蛇传》《封神演义》《西游记》,把燕青、林冲、公孙胜等梁山好汉与小青、白娘子、法海、狐女苏妲己、白骨精等角色混杂在一起。宁财神采用的是“冰糖葫芦”式结构,把原著中生性风流、丢掉卿卿性命的潘金莲改编为多情善感的文艺青年,以她刻骨铭心的爱情经历串联起与武大、西门庆、陈经济、应伯爵、武松之间的爱恨情仇。meng13die 的小说对人物心态、气质与命运的改变,尤其是对金莲与武松两位颇具文艺范的青年惺惺相惜的真挚爱情的描绘,无疑是对原著仇敌关系的快意叫板。情节、结构、人物关系的乱点鸳鸯谱呈现出来的“无厘头”式的话语狂欢,也典型地体现了改编者有意识的民间边缘姿态的站位。
四、结语:对改编者极端化姿态的反思
由于“互联网对文学的传播首先从‘物质、时间、空间’三位一体上打破了传统文学传播模式,然后又从‘迟延、在场、踪迹’的逐项延伸中消解纸介作品和口头文学的单线传播理念,实现了文学传播方式的根本革命”[9],所以,获得赛博技术与思想意志双重自由的网络写手,又在《水浒传》表现的江湖自由的伦理意识推动下,自然更加肆无忌惮地挥霍自由的本初内涵。但自由毕竟是一把既指向他者又指向自身的双刃剑,偏执的自由姿态也会在解构经典的过程中把改编者逼向花样翻新的死胡同。无论是改编者的学历背景、身份教养、知识经验有多大的差距,只要是以匿名者的身份投入到水浒网络改编的游戏和狂欢的自由氛围中,都不可避免地站在民间的立场上尽情地挥霍太轻松得来的低门槛的入门券,这就形成了同质化的带有普遍性的改编症候。
第一,极端油滑的改编策略。鲁迅在小说集《故事新编》的序言中提到“油滑是创作的大敌”。水浒改编者在自由的创作环境中,对词语古今杂糅的滥用,小丑式的信口开河、插科打诨,都深陷油滑的泥潭中不能自拔。小说人物三句话不离外文,成为某些大话小说的典型徽标。在肥羊的《大话水浒》里,旺才晒太阳的感觉就像享受“毒品带来的HAPPY 一样”,回答问话时“I see?”“NO 看头啊”“SAY 吧”“don’t worry 拉”“再给你chance”;在林长治的《缺钙水浒》中,王进的母亲满口“八嘎”“有油的没有”“房钱的不付”;在王小枪的《孙二娘日记》中,孙二娘的口头禅“真TMD 笨”“Chinese 功夫”,老头儿的“NO!去十字坡”,叙述人的“摆了一个很酷的POSE”;在老了的《水浒十一年》中,大臣和皇帝满口“恁”“鳖孙”“中!中!中!”“老美”;等等。这些英语、仿日语、网络用语和方言的杂糅,早已失去了语言革命的意义。对“语言是存在的家园”的本体论的忘却,是对改编者极端自由姿态的莫大讽刺!
第二,抖包袱的俗套戏仿。网络信息的爆炸化和海量化意味着改编者如果不以读者的眼球经济为自己创作鹄的的话,即使是颇有见地的改编,也会在网络媒介遵循的“劣币驱逐良币”的原则下淹没在碎片化的海洋里。因此,水浒改编者只能剑走偏锋,采取抖包袱、炫机灵的俗套戏仿的方式,在互文本提供的笑料叠加中达到娱人并自娱的目的。《李逵日记》的作者仓土的自白就代表了改编者的共同心态:“本想娱乐下自己,却意外开心了观众”,写作时“无牵无挂,信马由缰,指点人物全凭一己之好恶,酣畅于笔,痛快于心”[10]前言。所以,每一个改编者在选择哪一个情节片段作为刻画人物的性格、表现人物的情感命运、加快或延缓故事进展的速度、突出或弱化表达的思想主题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出奇制胜的谋略以及如何挠到读者痒痒肉的笑点和泪点。由于网络时代信息的迅捷性、普泛性和体验的同质化带来的审美疲劳之感,只有在大众传媒中留下刻骨铭心印象的笑料信息,才能作为引起阅读快感的重要媒介吸引读者的眼球。因此,水浒改编者从电影、春晚、流行歌曲、坊间段子中得到抖包袱的灵感,让人物在不合时宜的氛围中笑料迭出,就成为他们自由戏仿的典型姿态。例如:老了在《水浒十一年》中根据梁山好汉的出身、身份和职业安排的一场娱乐活动,让阮氏三兄弟演唱《渔家傲》,让杜迁、宋万说对口相声《我是黑社会》,让公孙胜现场表演魔术,让朱贵和刘唐表演小品《黑店》,这些显然是借鉴和戏仿春晚的娱乐模式。肥羊在《大话水浒》中让王婆对旺才的劝告:“你不崇拜它我不怪你,可是你不能阻挡我们崇拜它嘛,虽然崇拜也可以放在心里,不一定要讲出来。但是我相信听过我的讲解,你也一定会拜倒在它的脚下,亲吻,叩拜。来,让我从头给你讲解,这个就要从前朝的时候开始叙述。”这显然是对电影《大话西游》中喋喋不休的唐僧劝说徒儿悟空的戏仿。王小枪在《孙二娘日记》中让武松的夫子自道:“当里个当,当里个当,闲言碎语不要讲,听我表表山东的打虎英雄武二郎!”这段从外在形式到表现内容都是对山东快板的模仿。宁财神在《在路上之金莲冲浪》中让西门庆伴之以山东快书的调头对潘金莲的深情表白:“金莲金莲我爱你,就象耗子爱玉米,金莲金莲我恨你,就象居委会恨小痞……”这段是对流行歌曲《老鼠爱大米》的戏仿。这些水浒网络改编小说里,段子的目不暇接、环环相扣,包袱的层层展开、孔雀开屏,都是对流行且俗套的东西的戏仿。当改编者深陷在段子手的温柔乡里自鸣得意的时候,恰恰忘记的是与流俗共舞的文化快餐必将与流俗一同偕亡的发展规律,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