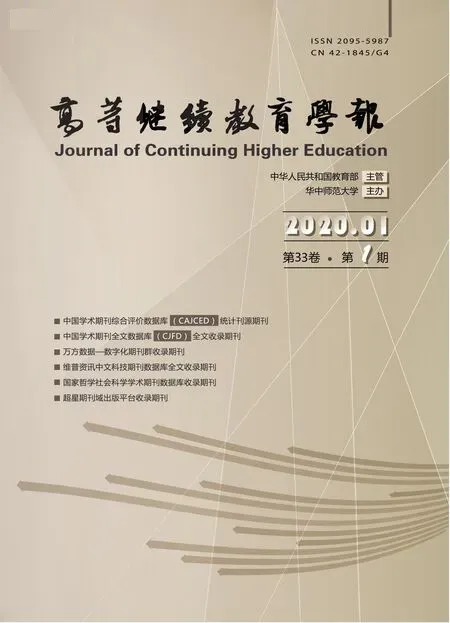何谓“终身职业教育”
——兼与周永平、石伟平先生商榷
汤广全
(龙岩学院 师范教育学院,福建 龙岩 3640012)
一、问题的提出
10年前,笔者在江西科技师范大学职业教育研究所工作时,在从事职业教育原理教学与研究的间隙,有感于职业教育学界创造“终身职业教育”一词及其不当诠释,重新阅读、思考了相关概念,最终在《成人教育》2009年第5期上发表拙文《“终身职业教育”刍议》,[1]初步厘清了相关概念,化解了心中的疑问。2012年,笔者离开原单位后主要致力于普通教育研究,对职业教育基本概念的关注相对就较少了。前不久,偶读周永平、石伟平两位先生的作品《论“终身职业教育”》(下文简称周文),笔者油然而生“往昔”与“顾念”。
周文指称“终身职业教育”概念的使用并无不当,且详细论述了“终身职业教育”的必要性及“终身职业教育”的实现路径。[2]文中不可避免地提及笔者当年那篇回应职业教育学界“抛砖引玉”的拙文,这再次引起了笔者的进一步深思:何谓“终身职业教育”,“终身职业教育”之说当否,“终身职业教育”是否符合逻辑,它到底意味着什么。本文旨在追问何谓“终身教育”“终身职业教育”及其语义分析,阐明“终身职业教育”在逻辑上不能自圆其说,“终身职业教育”概念的厘清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二、何谓终身教育
在解析“终身职业教育”之前,须先把脉“终身教育”的内涵;而欲理解“终身教育”,需先弄清“终身”与“教育”各自的内涵。
(一)终身
终,形声字,源自“将丝线扎紧,象征结束”。本义是末了、结束,跟“始”相对,引申为极限、停止、尽头等;再后来引申出从头到尾、永久等。[3]身,象形字,象人之形,本义是人的躯体的总称,引申为人的生命或一生。[4]终、身二字合为一体,即为合成词。所谓终身,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理解,即一生、一辈子。[5]
(二)教育
所谓教育,有广义、狭义之分,按中国学界的理解,狭义的教育,主要是指学校教育,即教育者根据一定社会或阶级的需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或学习者)的身心施加影响,把他们培养成为一定社会或阶级所需要的人的活动。[6]这个界定侧重社会视角下的个体培养。广义而言,按照西方学界的理解,教育是人们尝试性地持续在任何一方面改善他(她)人的心理素质结构,或者保留其心理素质结构中有价值的内容,或者避免不良心理素质形成的行动。简言之,教育是人们尝试性地在任何一方面提升他(她)人人格的行动。[7]这个界定撇开了具体社会,抽象地从普遍的视角谈论个体人格的培养。
综合而论,不论广义还是狭义,教育都有其共性,即提升受教育者或学习者的素养、健全其人格的一种活动。这种活动的长久持续,莫过于“终身教育”一词指称的内涵了。
(三)终身教育
所谓终身教育,即“贯穿于个体生命的教育”。它包括学前教育、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大学后继续教育及各类成人教育,旨在“维持和改善个体的发展与社会生活质量,以适应社会急剧变化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需要”。[8]职业教育就是其一。也就是说,终身教育具有两个维度的特质:一是从其外延角度而言,它是贯穿人生始终的一种教育形态,具有“时间的延展性”;二是就其内涵而论,终身教育不是单一或纯粹的教育形态,它更多的是一种教育观念和教育理论,它囊括了所有现有的教育形态的教育过程。[9]实质上,上述终身教育的第二种特质可理解为一种空间上的包容。综合而论,终身教育是时间上与空间上的融合,呈现出一定的时空张力,远远超越了传统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及社会教育乃至自我教育等。很大程度上,终身教育内涵的界定更接近于终身学习,即活到老、学到老,没有止境,直至生命终结。
三、何谓“终身职业教育”
“终身教育”与“终身职业教育”有什么内在关系,需要厘清。欲剖析“终身职业教育”,必先理解“职业”及“职业教育”的内涵。
(一)职业
按现代汉语词典的理解,所谓职业,有两个义项:一是指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所从事的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工作;二是指专业的、非业余的。[5]本文持第一个义项,旨在表明个体为谋取主要生活来源的工作而事先或同时致力于提升自身素质、健全自身人格的活动。他(她)需要接受职业教育。
(二)职业教育
什么是职业教育,尽管学界仍存在分歧,但笔者仍坚持10年前的基本界定,并略作修改,即以谋生为导向的一种传授知识与技能,以使个体身、心两方面都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完善,且能获得生活来源的社会活动。如前所述,职业教育是终身教育的一部分。那么,它又与“终身职业教育”有何关联?
(三)“终身职业教育”
什么是“终身职业教育”?国内学界对“终身职业教育”的解释,即倾向于把“终身教育”与“职业教育”简单化地组合起来,也即认为职业教育贯穿于个体的一生,既不会随着职业的变更或工种的转换而停止,又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或个体生命的衰弱而中断。[1]有人可能会辩说,职业教育只有成为扩展到每个人整个的职业生涯的终身职业教育,才能使其更好地迎接知识信息时代大潮的挑战。[10]笔者丝毫不否认,职业教育可以扩展到“每个人整个的职业生涯”,以力倡有识之士所言的“在职业教育中全面贯彻并充分体现终身教育思想、终身学习精神,在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的框架下来理解现代职业教育”。[11]但是,“职业生涯”并非等同于个体的一生,它只是人生的一部分,人生的一个阶段,而非全部。既然如此,就有必要从逻辑上进一步剖析“终身职业教育”内涵的失当。
四、“终身职业教育”内涵失当的逻辑分析
“终身职业教育”的内涵在逻辑上不能自恰,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层面,即时间上难以趋同、空间上不能合流、论据上不能相融。
(一)时间上难以趋同
如果说终身教育等同于“终身职业教育”,无异于认为二者之间在时间上趋同,即认为终身教育贯穿于人的一生,职业教育亦然,即职业教育具有“活到老、学到老”的特质。尽管职业教育是终身教育的一部分,可以面向终身考量,即“为每个社会成员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提供相应的服务”。[12]问题在于:一旦二者在时间上趋同,那就意味着终身教育、职业教育及“终身职业教育”三者的内涵在时间上趋于一致,而这在语义上是不合逻辑的,也是不可能的,兹不赘述。
(二)空间上不能合流
如果说终身教育等同于“终身职业教育”,那就等于承认终身教育与职业教育能够合为一体,即终身教育包含各级各类教育,职业教育也然。问题的关键是,终身教育凸显的是各级各类教育,而职业教育原本只是教育的一部分,即个体在人生某个阶段为谋生或获取主要生活来源而接受知识、技能的传授。显然,指称终身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内涵在空间上趋于合流,同样在语义的逻辑上是说不通的。
(三)论证上不能自恰
“终身职业教育”的内涵不仅在时、空上不合逻辑,而且在“摆事实、讲道理”的论述过程中也背离逻辑。周文在论证“终身职业教育”一说的合理性时,提出了两个论据:
一是“焦点”论据,即认为职业文化环境对职业教育理解的着眼点不一样,即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来说,“职业的概念”是终身的,“一个老木匠,没有严格的职业资格认证,职业身份和职业伴随他生命的终了,学徒制教育形式和教育生涯也伴随他生命的终了”。[2]这个论据有两点值得商榷:第一,即便“职业的概念”是终身的,也并不必然意味着“职业教育”是终身的。也就是说,对于老木匠而言,他的职业可能“伴随他的生命的终了”(注意,这里是“可能”,而不是“必然”),但并不意味着他的职业教育“伴随他的生命的终了”。退一步而言,即便是“必然”,也不能得出“学徒制教育形式和教育生涯也伴随他生命的终了”。这是因为就老木匠与学徒而言,前者是教育者,后者是受教育者或学习者;随着老木匠(教育者)生命的终了,学徒(受教育者或学习者)在前者那里的教育生涯也终止了,而后者的生命并未终止。此外,我们这里谈论终身教育主要是着眼于现当代社会而非传统社会,即中国传统社会虽有终身教育理念的萌芽,但并未“落地生根”,终身教育理念的正式提出是现当代社会发生的事情。
二是“立场”论据。周文直接引用了《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中的汉译中文原典来作为自己的证据,即“最初,终身(笔者注:周文引文是“终身职业”四字,而非“终身”二字)教育只不过是应用于一种较旧的教育实践即成人教育(并不是指夜校)的一个新术语。后来,逐步地把这种教育思想应用于职业教育,随后又涉及到在(笔者注:周文引文中没有“到在”)整个教育活动范围内发展个性的各方面,即智力的、情绪的、美感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修养。最后,到现在,终身教育这个概念,从个人和社会的观点来看,已经包括整个教育过程了。”[13]显然,引文强调的是终身教育贯穿个体的一生,而非“终身职业教育”或“职业教育”伴随个体一辈子。遗憾的是,比照《学会生存》汉译中文同一时间的版本,原文并无“终身职业教育”(即周文引文中第五、第六个字“职业”在原中文译本中根本不存在),只有“终身教育”。也就是说,周文的这个“立场”论据缺少论证力量。缘此,一旦周文“终身职业教育”概念的逻辑成了问题,它详细论述的“终身职业教育”的必要性及“终身职业教育”的实现路径也就成了空中楼阁。
因此,“终身职业教育”的称谓在时间与空间上难以相融,论证的理据也难以自圆其说。
五、“终身职业教育”概念厘清的意义
“终身职业教育”概念在学界流布10多年,产生了一定的学术影响,厘清它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一)认识论意义
众所周知,概念是一种基本的思维形式,虽然附带有人的主观能动性,投射出人的意识具有一定的创造性,但它毕竟首先奠基于认识对象之上,然后才能“反映客观事物的一般的、本质的特征”。[5]也就是说,人在认识对象时,在反映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时,在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时,不能过度“概括”“提炼”或“推演”认识对象或客观事物具有普遍性的共同特点,更不能一厢情愿,想当然。否则,过犹不及,物极必反,适得其反。无疑,“终身职业教育”的辨析就具有这样的认识论个案价值。
而且,作为一种观念,“终身职业教育”只存在于部分人的头脑中,并非准确地反映认识对象或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忠实抽象与逻辑推演,而是偏颇的阐释,是失真的论析。也就是说,“终身职业教育”这一概念在逻辑上是不能自恰的,因而是概念世界的“多余者”。它是人为地附加在终身教育内涵上的一层外在关系,是“毫无用处的画蛇添足,与逻辑学和科学的原则是相矛盾的”。[14]厘清“终身职业教育”的悖谬具有“若无必要,切勿增加”[15]的“思维经济”意义。
(二)价值观意义
教育的重要职责在于“传授价值观和道德”[16]。也就是说,任何教育都具有立德树人的价值取向,职业教育也不例外。通常情况下,小学生可以进行职业意识启蒙,老年人在体力与精力尚可的境遇下也可接受适度的职业教育、职业培训,但是对于幼儿进行职业教育等相关活动既没必要,也不符合其个体生理与心理发展特征。同时,对于离休或生计无忧的老人,职业教育既无必要,也不符合普通社会的价值取向;即使对于生计困难或者耄耋之年的老者,家庭或社会都有义务帮助他(她)解决生计,或助其享有社会基本的福利,也不一定非得对其进行职业教育或相关职业培训,否则现代社会该有的人道担当就要受到质疑,职业教育的人性关怀也一并受到威胁。此外,即便是那种没有一技之长、生计没有着落且大脑极度受损、正常学习极其困难的年轻人,也不可能接受职业教育或相关职业培训,他(她)所在的家庭、社区有义务,有责任化解其衣食之忧。显然,如果“终身职业教育”在语义上能够成立,就必然违背职业教育自身人性关怀的情感操守,也必然违背现代社会所秉持的基本的人道立场。
六、结语
正如刘诗能先生所言:“无论从职业生命周期、职业生涯发展,还是从‘终身职业教育’与‘终身教育’的扦格来看,终身职业教育理论都很难自圆其说。”[11]有鉴于此,笔者仍然坚持近10年前对“终身职业教育”的判断,即它是对“终身教育”内涵简单化的推演,是对“职业教育”内涵进行的似是而非的扩展,名不副实,口惠而实不至。(感谢唐老师为拙文提出的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