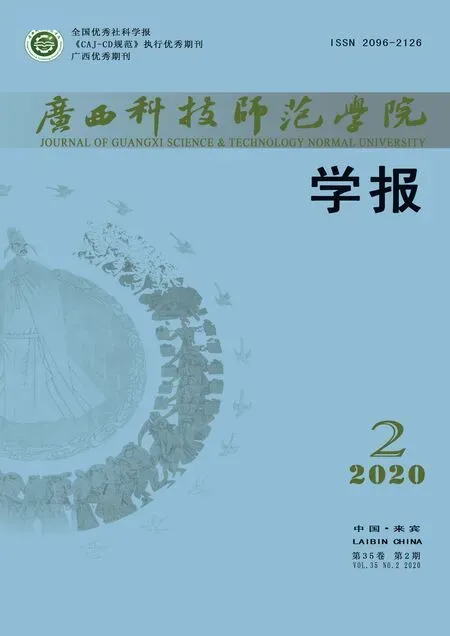柳宗元《河间传》的批评与研究
刘 城
(广西教育学院文学院,广西南宁 530023)
唐代古文大家柳宗元所作小说《河间传》,叙写女子“河间”如何从一个“有贤操”之德的女子堕落成荡妇的过程。她原本“独养姑,谨甚,未尝言门外事。又礼敬夫宾友之相与为肺腑者”①关于《河间传》的原文,皆引自尹占华、韩文奇,《柳宗元集校注》,中华书局,2013年版,此后不另注。,且“恶群戚之乱尨,羞与为类”。但在家族恶少的多番设计引诱之下,被一“貌美阴大者”强暴,并从此变得纵欲淫乱。与奸夫设计害死丈夫,“居一岁,所淫者衰,益厌,乃出之。召长安无赖男子,晨夜交于门”,后“又为酒垆西南隅,己居楼上……凡来饮酒,大鼻者,少且壮者,美颜色者,善为酒戏者,皆上与合。且合且窥。恐失一男子也”,如此十年之后,“河间”“病髓竭而死”。其臭名之昭著,连那些“戚里为邪行者”都不愿提及。
历来研究柳文者,多不重此篇,认为其行文不似与柳宗元之作,更因该文语涉淫秽之辞,甚至有人指其为伪作②如清人马位于《秋窗随笔》云:“《河间传》一篇,托辞比喻何苦。持论至此,伤忠厚之道。编之集外,宜矣。恐是后来文士伪作。”。但也正因为此文的特殊,古往今来也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与批评。
一、主旨探究:讽喻、影射与寄托
自北宋始,《河间传》逐渐进入世人的视野且颇受关注,相关的批评也随之增多,其中最为学者关注的是对《河间传》主旨的深究与蠡测。
首先,世人多不把《河间传》当成是一篇纯粹写女子堕落的小说,而是多目之为一篇暗含讽喻、影射及寄托的作品,对该文背后所蕴藏的深意颇感兴趣,试图深挖其真正的主旨。
北宋胡寅(1098—1156 年)可谓是开此风气之人。胡寅的《致堂读史管见》似乎是目前现存最早对《河间传》进行评论的著作,其卷二十四云:
或谓宪宗用法太严,而人才难得,岂应以一眚终弃,是不然。梦得、子厚之附伾、文也,盖有变易储贰之密谋,未及为而败。……子厚至托讽淫妇人有始无卒者,以诋宪宗。二人者,既失身匪人,不知创艾,乃以笔墨语言,深自文饰,上及君父,以成小人之过,则其免于大戮,已为深幸,摈废没齿,非不幸也。[1]
他认为柳宗元此文“托讽淫妇人有始无卒者,以诋宪宗”,文中暗含托寓讽刺之处。此论一出,影响甚远,后世许多评论由此衍生而出,只是暗讽影射的对象有所差异罢了。
何焯(1661—1722 年)在《义门读书记》卷三七批注“河间命邑臣告其夫召鬼祝诅”一句时说:
《汉书》: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此云“邑臣”,岂其公主耶?[2]
认为河间或许指代的是公主。
陆以湉(1801—1865年)《冷庐杂识·河间妇传》曰:
柳子厚《河间妇传》遣词猥亵,昔人曾讥之。然其文固有为而作。其记游戏之所,一则曰浮屠,再则曰浮屠,可知佛庐之贻害甚烈,二妇人之喜入庙者,可以警矣。[3]
则认为《河间传》指责“佛庐之贻害甚烈”,警戒妇女慎入佛寺。
另外,南宋人王正德(生卒年不详)《余师录》卷三引李朴《书柳子厚集》云:“至若河间传、李赤事以讥切当世,属意明白,而卒自蹈其弊,岂所谓工于词人而拙于用己耶?”[4]胡次焱(生卒年不详)也说:“读柳子《河间传》知邪之得以败正。”[5]二人虽未做具体阐述,但可知他们也认为该文有寄托讽喻之意。
其次,论者除指明《河间传》暗含讥讽之意外,还多藉此文批评柳宗元之为人。
如上所引胡寅之文可知,他实不满柳宗元自“失身匪人”之后,“不知创艾,乃以笔墨语言,深自文饰,上及君父,以成小人之过”,这种行为“免于大戮,已为深幸”,而遭致贬谪摈废,却是罪有应得。
明人刘定之(1409—1469 年)曾论韩愈和柳宗元之优劣,认为“以文言,柳差肩于韩”,但“以人言”则“韩阳淑”,柳“阴慝”,“如冰炭异冷热、薰犹殊芳臭矣”。又云:
退之怀忠事主,辟邪宗圣,固有本原。其称子厚,谓斥不久,其文必不能传于后如今无疑,盖惟称其文而已。其阿附伾、文,胡致堂谓忌宪宗在储位,有更易密谋,未及为而败;后又托河间淫妇无卒者以诋宪宗,得免于大戮为幸。由是言之,文虽美,而若斯过恶,固非可湔涤者也。[6]
刘定之赞同胡寅之论,且云柳宗元其文学成就颇可称道,但就为人而言“若斯过恶”而不可取。
除此之外,还有学者借《河间传》阐发士人要修身养性之论。
南宋罗大经(1196—1252年后)在《鹤林玉露》云:
全州士人滕处厚贻书魏鹤山云:“汉人谓士修于家而坏于天子之庭。夫能坏于天子之庭者,必其未尝修之于家者也。”可谓至论。然余观柳子厚《河间传》,非不修于家也,及窃视持已者甚美,左右为不善者,已更得适意,鼻息咈然。则虽欲不坏于天子之庭,得乎?要之不坏于天子之庭,乃特立独行者也,若夫中人,虽修于家,其不坏于天子之庭者,鲜矣。[7]
罗大经此言论士人修身养性之不易,品行易坏而难以维持。关于此,明代海瑞更进一步阐发:
昔人谓士非不脩之家也。至应举入官,耽利禄慕荣途,患得患失靡所不至,不能不坏焉。夫如柳子《河间传》,则士脩之始,坏之终,间亦有之然。大槩不美之士,不必献身天子之庭,然后人可得而知之,讲之不明,守之不固,穷居之所以自脩自养,有彰彰然著者。[8]
海瑞此处就勉励士人应当要坚持自修自养,避免为功名利禄所诱而自毁名节。
与罗大经同时而稍后的黄震(1213—1280 年)在《黄氏日钞》则云:
《河间传》志贞妇一败于强暴,以计杀其夫,卒狂乱以死。子厚借以明恩之难恃。愚以为士之砥节砺行,终不免移于富贵利欲者多矣,正当引以自戒,而不必计其恩之可恃否也。[9]
黄震亦是借《河间传》来警示士人要能抵御富贵利欲的诱惑,砥节砺行。清代蒋之翘辑注《柳河东集》外集卷二云:
《河间传》,文小有致耳。其摹写贞、淫两截,焯焯如观。此正为士之不终其守者戒也。子厚乃特以明恩之难恃,则所谓讽一而劝百者,是不可以已矣乎?[10]
其所论承自黄震,而“讽一劝百”之说又源自南宋李季可。
二、文学批评:师承、因袭与文辞
在深究《河间传》所蕴含的政治讽喻、道德修持等寓意之外,不少学者还从为文的角度来评说《河间传》。
首先,不少学者从文章写作的师承、因袭摹写切入,探讨《河间传》的师承及因袭之处。
王楙(1151—1213 年)在《野客丛书》卷二○《河间传意》云:
客或讥原涉曰:“子本吏二千石之世,结发自修,以行丧推财礼让为名,正复雠取仇,犹不失仁义,何故遂自放纵,为轻侠之徒乎?”涉应曰:“子独不见家人寡妇邪?始自约敕之时,意乃慕宋伯姬及陈孝妇,不幸一为盗贼所污,遂行淫佚,知其非礼,然不能自还,吾犹此矣。”仆谓此柳子厚《河间传》之意也。《史记·吕不韦传》述太后云云,《河间传》又用其语,古人作文,要必有祖,虽秽杂之语,不可无所自也。[11]
《野客丛书》乃王楙精心结撰之作,在考证经史百家之时钩隐抉微,骚人墨客,佚人佚事均多有留意。他考证《河间传》之文用了班固《汉书》原涉传记之意,语句有祖《史记》之处。考《汉书》卷九十二《游侠传》,其叙原涉其人其事云:
先是,涉季父为茂陵秦氏所杀,涉居谷口半岁所,自劾去官,欲报仇。谷口豪桀为杀秦氏,亡命岁余,逢赦出。郡国诸豪及长安、五陵诸为气节者皆归慕之。涉遂倾身与相待,人无贤不肖阗门,在所闾里尽满客。或讥涉曰:“子本吏二千石之世,结发自修,以行丧推财礼让为名,正复雠取仇,犹不失仁义,何故遂自放纵,为轻侠之徒乎?”涉应曰:“子独不见家人寡妇邪?始自约敕之时,意乃慕宋伯姬及陈孝妇,不幸一为盗贼所污,遂行淫失,知其非礼,然不能自还。吾犹此矣!”[12]
司马迁《史记》卷八十五则载:
庄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为王,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时时窃私通吕不韦。不韦家僮万人。
……
始皇帝益壮,太后淫不止。吕不韦恐觉祸及己,乃私求大阴人嫪毐以为舍人,时纵倡乐,使毐以其阴关桐轮而行,令太后闻之,以啗太后。太后闻,果欲私得之。吕不韦乃进嫪毐,诈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韦又阴谓太后曰:“可事诈腐,则得给事中。”太后乃阴厚赐主腐者吏,诈论之,拔其须眉为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与通,绝爱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诈卜当避时,徙宫居雍。嫪毐常从,赏赐甚厚,事皆决於嫪毐。嫪毐家僮数千人,诸客求宦为嫪毐舍人千余人。[13]
王楙认为原涉所举一些慕伯姬及陈孝妇的“家人寡妇”,“不幸一为盗贼所污,遂行淫失”,此行事经历与河间多有相似。而《河间传》所亦颇类《史记》述太后事,且语句也有祖《史记·吕不韦传》之处。最后,王楙以此总结:“古人作文,要必有祖,虽秽杂之语,不可无所自也。”可见,他论《河间传》,是从文人创作的师承角度而言。
稍后的戴埴(1238年进士)于《鼠璞》卷下云:
柳子厚,文坛之雄师,世谓以作《河间传》不入馆阁。然亦有所本,《汉书·原涉传》涉曰:“子独不见家人寡妇耶?始自约敕之时,意乃慕宋伯姬及陈孝妇,不幸壹为盗贼所污,遂行淫行,知其非礼,然不能自还,吾犹此矣”。其意正相类。[14]
所言与王楙并无二致。
同时代的俞文豹(约1240 年前后在世)在《吹剑录》云:
原涉云:“家人寡妇,始自约敕时,意慕宋伯姬为人,不幸为盗贼所污,遂行淫失,虽知其非,而不能改。”柳子厚《河间传》亦此意也。如涉所云,自足以劝戒,何必极状其淫荡之丑?又《捕蛇者说》即苛政猛于虎之谓,《礼记》以八十言尽之,子厚乃以六百字。文日盛,质日衰,可以观世变矣。[15]
认为柳文为文亦有师承前人之意而加以扩充之举。但俞文豹似不满柳宗元极状河间其淫荡之丑,并认为世人之文辞日盛,而世道却日衰,以文变可观世变。
清人钱大昕(1728—1804 年)、光聪谐(1781—1858 年)、平步青(1832—1896 年)也认为《河间传》本于《原涉传》,或用《史记》之《吕不韦》之语③参看(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一六,光聪谐《有不为斋随笔》辛部,平步青《霞外攟屑》卷七上。。
清人袁枚(1716-1798 年)曾有一长段议论,指出韩愈和柳宗元为文亦有摹仿而未能尽去之处,其中说道:
古人作文摹仿痕迹未化,虽韩、柳不免。……《河间妇人传》先贞后乱,仿《游侠传》原涉曰:“寡妇一朝被污,从此放纵”云云。”[16]
此虽未脱前人之论,但袁枚却明确置之于文章师承背景下来探讨《河间传》对前人作品的摹写问题。
其次,不少学者颇不满该文文辞之污,多有声讨之论。南宋李季可(生平不详)《松窗百说·柳宗元》云:
柳宗元作《河间传》,足以讽一劝百。其言淫污之甚,吁可怪也。岂夫子自道乎?
黔驴、永鼠,轻薄子常藉以骂曰“技止此尔”,则其言岂有益哉![17]
此论柳宗元所作之文辞,本有讽喻之意,但其却收到“讽一劝百”的反面效果,有害于世人。正如柳宗元之《三戒》,原为讥刺时政,但其辞却为“轻薄子”所藉以骂人。故李季可颇反感这类文字,感慨道:“其岂有益于世?”
明人方鹏(1470 年—?)于《韩柳文章大家》一文云:
古今人称文章大家,必曰韩柳,然柳非韩匹也。韩之文主乎理,而气未尝不充;柳之文主乎气,而于理则或激之太高,拘之太迫。奇古峭厉则有之,而春容隽永之味则不足,其甚者,《天说》是也;其鄙亵不足传者,《河间传》是也。传中数语,虽稍知义理者犹耻之,而谓宗工硕儒为之乎?读之污齿颊,书之累毫楮,删而去之可也。[18]
认为《河间传》文辞“鄙亵不足传”,“可删而去之”。陈师(嘉靖年间人)亦有相似语:
夫文者,载道之器,然则无关于理道得谓之文乎?古今称文章大家曰韩柳,然柳岂能与韩匹哉?韩之文主乎理,而气未尝不充;柳之文主乎气,而于理则不能无,忒奇崛峭厉则有之,春容隽永则未也。其甚者,《天说》是也;其鄙亵不足传者,《河间传》是也。能文之士所不屑言而谓宗工硕儒为之乎?胡氏曰:“《河间传》寓言耳。盖以讥宪宗也,则其罪益大矣。”[19]
陈师之论几乎出自方鹏而稍加变化而已,二人都视《河间传》为“亵不足传者”。
王锡爵(1534—1611 年)《王荆石先生批评柳文》云:“腥秽满前,岂关世训?”[20]孙传能《剡溪漫笔》卷五在论及“文字作秽媟语,自是斯言之玷”时说道:“柳子厚《河间传》文亦近秽,虽借以寄刺,何乃为此淫丑之词!”[21]
清人钱大昕也认为“而词太秽亵。此等文不作可也”[22]。
三、当代研究:新方法与新视角
20 世纪以来,《河间传》虽非柳宗元研究的热点,但近三十年也陆续有学者撰写专文加以关注。
首先,如古代批评家一般,当代学者对《河间传》真正所映射之人及事也极为在意,发表了各具特色的看法,其中,有数篇是学者颇有针对性的商榷论文。
唐代文史研究名家卞孝萱先生有《〈谪龙说〉与〈河间传〉新探》[23]一文颇可值得关注,其通过对大量文献的考索与驳难,指出《河间传》的旨意乃是柳宗元在永贞改革失败后,被贬到外地不能直言其满腔的愤懑,只得用曲笔以表达他对唐宪宗对其迫害的不满。该文还对古人关于《河间传》的数种重要观点进行一一辨析与反驳,如《河间传》影射公主说,《河间传》文辞污秽说,警戒妇女勿入佛寺说,等等。论文虽篇幅不长,却可视为《河间传》的研究简史。
卞孝萱先生的文章刊发之后的第二年,金仁以《〈谪龙说〉与〈河间传〉勾沉——兼与卞孝萱先生商榷》[24]一文与卞先生进行商榷,认为河间影射顺宗,河间的丈夫影射王叔文,河间对其丈夫始爱终弃、有始无卒的态度与顺宗对王叔文先爱后恶、有初不终的态度是一致的,而那些勾引、挟持和利诱河间的戚里恶少及淫夫等人,则是暗指当时引诱、要挟和胁迫顺宗的宦官和藩镇等政治势力。稍后,张铁夫撰《柳宗元〈河间传〉考证》[25]一文,分五部分进行论述,但前四部分与金仁的《〈谪龙说〉与〈河间传〉勾沉——兼与卞孝萱先生商榷》关于《河间传》的论述几无差别,只是加了第五部分,即“《河间传》从标题到内容都寓藏着这样一个事实,即顺宗与宦官和藩镇串通一气,合谋害死了王叔文,镇压了永贞革新”,认为“柳宗元在《河间传》中所叙述的河间对其丈夫始爱终弃的态度及戚里恶少和淫夫的诱惑要挟等等,用比喻的方法,形象生动的故事情节,再现了历史上这复杂曲折而又丰富多彩的一幕”。由此可见,金仁应该是张铁夫的笔名,而此文是《〈谪龙说〉与〈河间传〉沉勾——兼与卞孝萱先生商榷》的扩展版。此外,张铁夫还有《〈谪龙说〉与〈河间传〉后探——兼与卡孝萱先生商榷》一文[26],与金仁的《〈谪龙说〉与〈河间传〉勾沉——兼与卞孝萱先生商榷》一文相比,在论点与论据上虽有删减或补充之处,但二文多有相重合之处。由此可见,署名金仁《〈谪龙说〉与〈河间传〉勾沉——兼与卞孝萱先生商榷》、张铁夫《柳宗元〈河间传〉考证》与《〈谪龙说〉与〈河间传〉后探——兼与卡孝萱先生商榷》三文,皆是张铁夫所作,文字基本相同,或稍有补充。
十多年过后,李腾飞发表《也谈〈河间传〉的影射问题——与张铁夫先生商椎》[27],不仅不同意张铁夫所提出的新的影射说,还认为前人所提的各类影射说均是牵强附会、不伦不类。柳宗元作《河间传》并非影射任何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而是在创作小说,其题材的选取,细节的描写,都很符合他传奇小说创作的原则。这一观点力图打破前人的讽刺、影射说,将该文视为一篇柳宗元精心撰构的小说,从而开拓该小说的研究视野。
除此之外,学者在考索《河间传》的影射对象时,还有一些颇为新颖、发前人所未发之处,如沙培铮《浅谈柳学研究的禁区——〈河间传〉》[28]就认为河间影射的是曾与柳宗元在“永贞革新”并肩作战的“八司马”之一程异。而刘瑞明《柳宗元〈河间传〉不是伪作》[29],指出《河间传》实际写一位身端行治、明知深察、聪明睿知的名臣被嫉妒者毁灭的悲剧,是柳宗元的自我哀惋及为自己鸣不平,并非伪作。其于文末还简述了《河间传》的后世影响,认为《水浒传》《金瓶梅》《痴婆子传》等小说中的一些描写均得益于《河间传》。
其次,跳出关于《河间传》讽喻、寄托以及影射说的窠臼,一些学者试图以各种视角来阐扬此文,以期多角度发掘其价值。
通过解析河间的形象,探讨古代两性关系。这方面,海外学者较早做出尝试,代表人物为美国著名的汉学家倪豪士(William H.Nienhauser,Jr.)教授。他在《唐人载籍中之女性性事及性别双重标准初探》[30]一文中,开篇就引述《河间传》作为楔子及讨论的主要文本,但其并非如传统批评一般对该文进行“时事背景的阐释(topical reading)”,而是借此探究唐代小说所描述的两性关系,指出所引唐代文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相信女性及其情欲具有危险性,故要进行抑制。并且得出结论:中国的两性之间,亦即中国人的性爱——指非涉婚姻关系的性行为——几乎是男性占有、独享的专利。至于女子,则只有以“贞洁”与忠实为中心的“道德”而已。而吴昌林、欧阳艳《社会性别理论下的女性形象探析——以唐传奇〈河间传〉为例》[31],认为前人多是把《河间传》当作一篇“载道之文”,而忽视了文中的主要女性——河间妇以及她所体现的社会性别关系。该文从社会性别这一全新视角出发,通过河间这一荡妇形象考察男性中心话语下的女性形象,从而探究唐代社会的性别关系以及所体现的文化意蕴,所言颇可一观。
借河间堕落的过程来剖析人性。魏玉川《论柳宗元〈河间传〉的多元价值》[32]就指出《河间传》乃写一良家女子由贤德而入淫邪的过程,剖示了人性固有的弱点,描绘了一幅“文化酱缸图”,同时也寓涵着“朋友之恩难恃,君臣之际可畏”的人生感慨,且对破解现代社会的人性与道德难题亦不乏借鉴意义。
最后,关注《河间传》在后世的影响与接受。如赵伯陶的《〈聊斋〉丛脞录——说〈河间生〉与〈桓侯〉》[33]实际上是《河间传》创作接受的个案研究。其认为,蒲松龄《聊斋志异》卷四中《河间生》的写作显然受到唐柳宗元《河间传》的启发,形式上模仿柳宗元的《河间传》,但内容却反其道而行之,宣扬“一念之差”在改恶迁善中的重要作用。一“妇”一“生”,皆事出“河间”,不同的是,前者弃善为恶,后者改恶迁善,有关“一念之差”的渲染则是两者异代相通的情感基础。
四、小结
综上所述,《河间传》虽非柳宗元研究的热点,但古往今来,世人对其也颇为关注。自宋代始,论者对该文所影射、讽喻之人之事颇感兴趣,力图发掘其文寄托的政治、道德深意。这种兴趣点一直持续到当今的学术研究。而一些评论家则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探讨《河间传》为文的来源、因袭之处,甚至指责其文辞之污。近十多年来,学术界在研究方法及研究视野上又有了一些新的拓展,如美国著名的汉学家倪豪士教授就采用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视角以期重新认识《河间传》,有些学者则借分析河间的形象探究中国古代的两性关系、性别和道德之关系,还有学者则举实例来论证《河间传》对后世小说创作的影响与接受问题。可见,当今的《河间传》研究,已经跳出了古人批评多深挖其讽喻寄托之意的窠臼,朝着多元化、多角度的方向发展,其不仅可以更好地认识这篇小说,实际上也将会对柳宗元的研究带来一定程度的提升与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