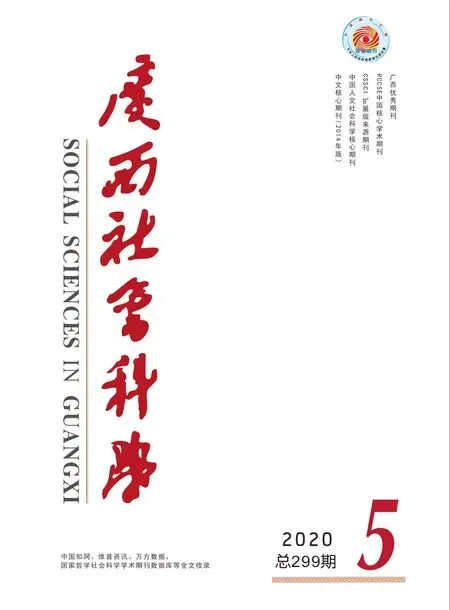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逻辑架构与当代诠释
——基于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本考察
(华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1)
19世纪30到40年代,德国在政治上处于四分五裂状态,各邦中的封建贵族把持国家政权。在经济上农村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城市的手工劳动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当英法等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弊端显露并遭到空想社会主义尖锐批判的时候,德国的资本主义“才刚刚开始”。在思想文化上,整个德国仍然笼罩在黑格尔头脚颠倒的哲学体系下。《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5年秋到1846年5月共同撰写的。他们从德国哲学与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着笔,对唯物史观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并以此为哲学基础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揭示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曾一连用到九个“学习马克思”,其中之一就是要学习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因此,笔者将以《形态》为依托,试着将散落于文本中的“世界历史光点”进行串联,以期能够探寻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逻辑架构。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逻辑架构
(一)在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历史哲学扬弃的基础上形成的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哲学根基
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在其《精神现象学》《哲学全书》《逻辑学》《法哲学原理》等著作中以思辨的哲学建构了庞大的精神体系,因此成为唯心主义的典型代表。而他的世界历史理论除一小部分散见于以上几本著作外,主要还是体现在《历史哲学》(黑格尔晚年在柏林大学开设的讲座课程“历史哲学”的教材)里。在开讲之初,黑格尔就把他的“哲学的历史”与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的“原本的历史”以及效用的历史、专门史、批判史等四种“反思的历史”作了对比,并进一步指出绝对精神对于世界历史的地位与作用。“我们就这样简单地对世界历史作了阐述。宗旨在于表明,整个历史的进程是精神的一种连贯进程,整个历史无非是精神的实现过程,而这种实现过程是由各个国家来完成的;国家就是世界历史在尘世中的实现。真的东西必须一方面在纯粹的思想中,另一方面也在现实中作为客观的、得到发展的体系存在。”[1]显然,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是被嵌入在精神的范畴,而国家实则就是精神发现自己、演绎自己以及最终实现自己的载体。作为世界历史之内蕴的精神是自由的、自足的,其发展是一个辩证的扬弃过程。黑格尔非常推崇东方的“重生”观念,曾用“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比喻来形容精神的运动,曾以太阳渐渐升起时的光明与人的注意力之间的变化来说明世界历史的大概路线。世界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处处可见运动的、矛盾的、量变质变的以及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思维,而这又恰恰成为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合理内核,并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创立作了理论准备。
在《形态》里,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作了根本的扭转,对在黑格尔体系基础上产生的现代“德国意识形态家”们作了彻底的批判。“它(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2]在笔者看来,我们在理解这段文字时,至少有以下几点是应当明确的:第一,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而这里的“个人”是有血有肉的,是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的。第二,现实中的个人为了需求的满足而进行物质生产活动的实践,催促了相互之间的交往以及交往的普遍化,因而得出人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总和。第三,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并非绝对精神、概念、理性,也不是历史事件的简单堆砌,而是人们“能动的生活过程”。不可否认,黑格尔在其著作中也曾对人类欲望与历史发展、个人利益与国家目的以及人的价值与民族精神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了详细论述,并以思辨的逻辑将个人性、主观性与自在自为的普遍实体相结合。但这些没有离开他一开始的立场与预设,即理性统治世界,相应地也统治世界历史。而这与《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实践所得出的“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3]的结论是格格不入的。马克思、恩格斯旗帜鲜明地反对将对意识形态的批判与建构建立在思想层面,而是始终立足人的生产实践与生活实践,始终把人视为世界历史的主体,在对黑格尔头足倒置的历史哲学进行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创立了以唯物史观为哲学根基的世界历史理论。
(二)在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揭示的基础上形成的历史形态划分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演变机制
全部人类的第一个活动就是满足衣食住行这些物质资料的活动,因此,人类必须运用一定的劳动资料(劳动手段)作用于劳动对象,从事生产实践的活动。生产力是人类社会生活和全部历史的基础,具有客观实在性和社会历史性的特点。劳动者、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互相协同,构成生产力的三大要素。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生产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经济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和产品分配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4]因此就二者的关系而言,首先表现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如果说现实的个人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前提的话,那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则是其核心问题。为了阐释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里运用了诸如“生产力”“交往”①《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用的“交往形式”“交往方式”“交往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这些术语,表达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生产关系概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88页。以及“分工”等高频率词。“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5]由此可知,一个民族内部结构之间以及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往活动和生产力发展水平都取决于分工的程度。而分工又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历史发展过程,具体表现为:首先是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引起的城乡对立,继而发展至商业劳动同工业劳动的分离,最后部门内部的分工必然又导致劳动者的分工;种种分工的相互关系又取决于农业劳动、工业劳动和商业劳动的经营方式(也就是生产关系)。因此,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
黑格尔在精神辩证运动的基础上曾将世界历史阶段划分为儿童期的东方社会、青年期的古希腊城邦、成年期的罗马帝国与成熟期的欧洲世界。相应地,马克思、恩格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基础上提出了四种历史形态。
第一种历史形态的所有制是部落所有制。这种形态下的生产力低下,分工与生产很不发达,人们以狩猎、捕鱼、畜牧、耕作为生,“社会结构只限于家庭的扩大……潜在于家庭中的奴隶制,是随着人口和需求的增长,随着战争和交易这种外部交往的扩大而逐渐发展起来的”[6]。
第二种历史形态是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这种形态的主要特点有二,其一,城乡之间的对立,以及后来的一些代表城市利益的国家同另一些代表乡村利益的国家之间的对立;其二,发达的分工促使私有制的发展,继而致使私有财产的集中和平民小农向无产阶级的转化。
第三种历史形态是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在这种形态下,“一方面是土地所有制和束缚于土地所有制的农奴劳动,另一方面是拥有少量资本并支配着帮工劳动的自身劳动”[7],致使狭隘的生产关系、分工较少、城乡对立以及等级森严成为其主要特征。
第四种历史形态是资本的或资产阶级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以腓尼基人以及中世纪玻璃绘画的遭遇为例指出,只有当交往演化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竞争在一切民族之间演化为普遍竞争的时候,才能够保护好原有的生产力。因此,“大工业”“资本”“市场”“殖民”“贸易”“竞争”等词语成为这个历史形态的代言,“它(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8]。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部落所有制、公社所有制、封建所有制的产生、发展、成熟、衰落以及灭亡进行梳理,总结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脱胎于封建制度的内在规律,并成功牵引“世界历史”的出场。
(三)在对资本主义“异化”现象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形成的共产主义愿景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终极目标
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形态》里对共产主义社会形态中人的日常生活作了非常美好的设想。“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者批判者。”[9]这段文字通俗易懂,反映出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的向往,同时也反衬出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现象的深恶痛绝。资本主义的“异化”指的是工业资本的集中和普遍竞争迫使所有的个人都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下的物质力量和强制力量。比如喜剧大师卓别林在电影《摩登时代》里拧螺丝的精彩片段就形象地展现了这种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的现象。
而对于如何消灭异化,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里则运用了“革命”“解放”等词语。革命的终极任务就是“把人类的大多数变成完全‘没有财产的’人,同时这些人又同现存的有钱有教养的世界相对立”[10],而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又成为革命的现实推动力。生产力不仅能够把致力于“争取必需品斗争”的人们从极端贫困的状态下解放出来,还能够推动普遍交往、世界历史的实现,从而也就实现了“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11]。共产主义运动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和各个民族之间普遍交往的基础上,陷入绝境的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在后来发表的《共产党宣言》里曾用辛辣的笔锋撇开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的种种责难,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2]。相比于《形态》中的部落所有制共同体、古典古代的共同体、封建结构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这里的“联合体”指的是真正的共同体。因此笔者认为,“共同体”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演变轨迹是一致的。世界历史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历经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共产主义是其终极目标。
综上,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真正内涵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整体性的宏大叙事,以人的物质生产实践为基础,所展示出的由人与人、群体与群体、民族与民族、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以及国家与地区之间的普遍交往所推动的历史从区域性向世界性的转变过程。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诠释
尽管《形态》距今已有170多年的历史,但其中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仍然具有极大的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所以今天我们研读这部经典,既要有历史感,即还原到当时的历史情境探求其精神实质;亦要有时代感,即站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上谋求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当前,国内外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革,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以战略思维和全球视野,多次强调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笔者认为,统筹好两个大局需要妥善处理好两对关系,一是国内发展与改革开放的关系;二是中国自身发展与世界共同发展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在国内继续推进改革开放,致力于打造全面开放的新格局;另一方面在国际上努力构建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一)改革开放——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践行
首先,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当代的改革开放提供了理论支持。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东方大国,曾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遥遥领先于西方国家。但从世界历史的发展逻辑来看,农耕文明语境下的古代中国与海洋文明语境下的西方所走出的道路是大不相同的。农耕文明相对比较封闭,而海洋文明相对较开放。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制是古代中国的主旋律,并一直绵延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1840年到1949年,是中国的近代史,也是“百年屈辱史”。学界很多专家学者均从不同的视角分析近代以来中国落后的原因,虽众说纷纭,但有两点是认可度极高的,即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中国长期以来的闭关锁国。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作出“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判断,也就是说,一个国家要么主动进入世界历史进程,要么被动进入世界历史进程。如果说英国的大炮使近代中国被动卷入世界历史进程的话,那么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则是中国主动加入世界历史进程的见证。因此,改革开放与闭关锁国是两个相互对立的思维体系: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提供了思想资源,而晚清时期的闭关锁国则是与其背道而驰的。
其次,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妥善处理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内在要求。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了世界历史的演进。不可否认,世界历史是由资产阶级开辟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3]。在生产力的推动下,资本主义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率先走向工业化、现代化道路。资产阶级的贪婪性和资本的逐利性推动并主导了一轮又一轮的全球化浪潮,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4]。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仍占据主导地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应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进一步加强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合作,继续发展生产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可能建立在落后的生产力之上。社会主义历经的百年沧桑告诉我们,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既可表现为战争与革命,亦可表现为合作与发展。因此,中国的改革开放在牢牢把握社会主义这一大方向的前提下应妥善处理好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这就要求在全球化语境中的改革开放既要充分利用资本,又不能被资本驾驭。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驾驭资本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这一历史形态只是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环,换言之,资本主义只是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共产主义才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未来图景。
截止到2020年,改革开放已走过了42年的风雨历程。波澜壮阔的40多年,使中国实现了由“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华丽蜕变。显然,改革开放已走到了“不惑之年”,下一步将何去何从?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的“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15]充分表明了新时代中国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无论是增设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还是在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行示范区,都彰显了中国积极走向世界、积极推动全球化进程的大国担当。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新时代表达
当今世界局势风云诡谲、变幻莫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变得敏感复杂,国际性的问题层出不穷:在政治上,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有所抬头;在经济上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肆意横行;在文化上“文明冲突论”“普世价值”沉渣泛起。面对这种局面,201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的《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演讲中,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16]。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公开提出的“命运共同体”思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秉持“兼济天下”这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对“世界之问”的积极回应,彰显了中国情怀和中国智慧。其后,在2015年的巴黎气候变化大会、2016年秘鲁APEC峰会、2017年日内瓦总部主旨演讲以及同年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总书记又多次提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也使这一思想理念实现了从“提出→深化→成熟→进一步推进”的逐步升级与日臻完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新时代表达: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理论来源,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又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首先,以唯物史观为哲学基础,对人的价值的肯定以及对人类前途与命运的极大关注成为二者共同的理论旨趣。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之上,充分肯定了人、人类实践以及在此基础之上产生的分工、交往、生产力等诸要素的客观实在性;最后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其终极目标。当今,生态危机、国际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全球性问题使得人类日益成为一个利益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基于诸多“世界问题”的出现才提出的。而这些与地球村上每个人的利益都紧密相连的世界性问题的解决,仅凭一个人、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列宁曾说:“世界历史是一个整体,而各个民族是它的‘器官’。”[17]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一个整体,每一个个人是其组成部分;而人与人之间又是以一定的结构形式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合力推动“共同体”的运动、变化与发展。正如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中的诸多“平行四边形”所产生的合力一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推进亦是合力的结果,而非单个人、单个国家的意志。
其次,对阶级局限性的突破和对“西方中心论”的超越是二者的理论契合点。在马克思那里,世界历史是由资产阶级开辟的,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8]。文艺复兴、新航线的开辟以及工业革命是资产阶级挣脱封建堡垒的动力之源。资本的逐利性促使其到处安家落户,一切民族都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过程也是其对内残酷剥削和对外征服、奴役、掠夺与杀戮的过程。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里用了“虚幻的共同体”一词来说明资本主义所开辟的世界历史形态,而寻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真正共同体”才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旨归。马克思关注的是全人类的解放,而不仅仅局限于某一阶级、某一民族或者某一群体。近代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确立,欧美传统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倚仗其经济优势,强行向其他国家和地区推行西方的价值观。以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为典型代表的“西方中心论”在全球肆意横行。纵观人类历史长河,对话与交流是异质文化间的发展趋势和规律。比如,在17世纪,法国人弗朗索瓦·贝尼耶翻译的《论语导读》曾在欧洲大陆引起久远激荡;再如,在19世纪,德国人库尔茨和肖特就曾译介过中国盛唐时期的李白诗歌,并在异质文化中激起共鸣与关注。“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19],习近平总书记在亚洲文明交流大会上的主旨演讲既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思想,又为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语境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文基础的构建指明了方向。
最后,加强政党自身建设,着力构建使命型政党是二者共同的内在规定。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带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华丽蜕变。在中国道路的开辟过程中,无论是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始终非常注重党的自身建设。今天,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新方位上,中国共产党将“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20]镌刻在自己的旗帜上,彰显了党的人民情怀、民族情怀和世界情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面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带领本国人民所取得的成功;一面则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将通过自身实践所探索到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分享给世界各国。概言之,中国共产党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者,同时也是积极践行者与推动者。
三、结语
世界历史思想就像一个又一个闪光点,星罗棋布地分布在《形态》中;试着将其进行串联,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便会自成体系、跃然纸上。这一理论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当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而且还跨越170多年的“时间距离”,极大地指导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德国哲学家、诠释学大师伽达默尔在其代表作《真理与方法》一书中指出:“重要的问题在于把时间距离看成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可能性。时间距离不是一个张着大口的大沟,而是由习俗和传统的连续性所填满,正是由于这种连续性,一切传承物才向我们呈现出来。”[21]也就是说,在对待“时间距离”的问题上,我们应该将着眼点定位在时间的连续性上,而不是间断性上。无疑,《形态》是属于伽达默尔概念里的“习俗与传统”的。每一个时代都必须按照自己的方式诠释历史传承下来的文本,以实现“视域融合”。笔者希望,通过对《形态》文本的诠释,一方面能够讲清楚马克思、恩格斯所处时代下的世界历史理论,另一方面能以新时代中国在发展实践过程中积累的新经验、得到的新启示以及探索到的新规律进一步完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经典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