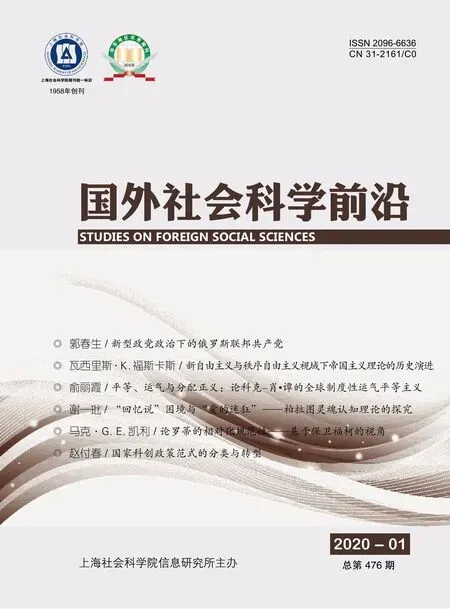“回忆说”困境与“爱的迷狂”
——柏拉图灵魂认知理论的探究 *
谢一玭
内容提要 | 柏拉图通过“灵魂回忆”来沟通理念世界和现实世界,因此,“灵魂回忆说”是“理念论”的主要认识路径。然而,这条认识道路有着它自身无法跨越的逻辑障碍:灵魂自身具有非统一性或者说二元性(在世灵魂与纯粹灵魂),对真理(或者纯粹灵魂)的认知要么死后才能获得,要么只能凭借在世灵魂不纯粹的理性推理功能获得一种意见,而不是知识。面对这个难题,柏拉图在中晚期著作《会饮》《斐德罗》中,提出了另外一条认知道路——爱的认识道路。爱欲沟通“有知”和“无知”,是在世灵魂不断朝向神圣灵魂的涌动性、生长性力量。而在爱欲的巅峰状态即“爱的迷狂”中,二分的灵魂才能实现真正的统一,对理念的认识才是可能的。尽管这条认知路径对于柏拉图来说具有逻辑自洽性,且具有现实经验基础,但遗留了更大的问题。
柏拉图是一个理念主义者,对于柏拉图来说,最重要的是对理念的认识,现实的经验知识是次要的、从属的。那么,问题也就在这里,生活在经验世界的人如何认识理念世界)的理念,这两个世界是如何打通的?而柏拉图对此最为成熟的理论是“灵魂回忆说”,企图以灵魂为桥梁,通过区分在世灵魂和纯粹灵魂,强调在世灵魂对纯粹灵魂状态的回归来试图沟通这两个世界,尤其是进入到理念世界认识理念。然而,在《斐多》中,这种回归和沟通只能在死后实现,这个答案本身对于一个现实世界的人来说具有致命的逻辑缺陷。而《理想国》对此进行修正,提出“灵魂转向”,虽然更具有操作性和可实施性,但是也只能获得逻辑推演的“真意见”,而不是理念知识。本文试图说明,“回忆说”的问题在于灵魂的二元论,二分的灵魂本身就具有无法跨越的鸿沟,因此,这种灵魂观之下的对理念的认识也是不可能的。后期柏拉图重新修正灵魂观念,把灵魂看作是一个整体,即对于一个人来说,生存具有整体性,并不仅仅是理性认知。同时,灵魂具有自动性,灵魂的自动性保证了灵魂的不朽,因此,灵魂兼具神圣性和在世性。且灵魂自身具有朝向神圣性涌动的内在动力机制即爱欲,爱欲是灵魂自动性的表达,是沟通在世灵魂和神圣灵魂的桥梁,1在世灵魂和神圣灵魂是同一个体灵魂的两个性质。也是沟通经验世界和理念世界的桥梁。在“爱的迷狂”中,即在爱欲的巅峰状态中,柏拉图把灵魂整合为一,同时也实现了对于理念认识的可能性。
然而,“爱的迷狂”也留下了很多的问题,迷狂到底是一种什么状态,是否具有量化的标准以及可操作性?这种迷狂和巫术、神秘主义的界限又在哪里,是否和柏拉图的理性认知理论相悖?那么爱的迷狂作为不同于灵魂回忆说的另外一条认知路径,是否行得通?本文试着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和回应。
一、“回忆说”困境:灵魂概念的非统一性
在《斐多》中,灵魂能够作为认识主体的前提是灵魂不朽。灵魂不朽意味着灵魂在死后能够继续存在。这里柏拉图突出的并不是个体灵魂的长生不老,而是要说明存在这样一种“普遍的灵魂”,它是一种永恒不朽的精神性力量,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普遍的理性。而与普遍的理性相联系的是普遍必然的知识,也即理念知识。只有普遍的理性才能认识普遍必然知识,而普遍必然的知识也只能由普遍的理性去认知。这个认知的过程是通过“看”(Θεάoμαι/ θεωρέιται)1本文所有涉及柏拉图原著的作品采用本杰明·乔伊特(Benjamin Jowett)英译本和伊昂内斯·伯纳特(Ioannes Burnet)的希腊本。参阅本杰明·乔伊特:《柏拉图著作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Ioannes Burnet(ed.), Platonis opera, vol.II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09.这个动作完成的,即灵魂与事物直接的接触。这个“看”,不是理性的把握,而是一种注视,一种理智的观看,这一过程在《斐德罗》中也有类似的描述。并且,这种灵魂之眼的观看能够滋养灵魂自身。2《斐多》66d7的 Καθαρως(纯粹无污的)和83b4的όρα(看)也用来表示看到理念本身或者美本身。《理想国》《会饮》都有类似的表达,比如善理念和美本身等。在灵魂的“普遍性”“纯粹性”的角度上,认知主体和认知对象才能联系起来。这也是《斐多》主要强调的认知路径。
然而,现实情况是,灵魂并不全都是纯粹的,灵魂有现世和纯粹之分。如果说只有纯粹灵魂才有认识知识的可能,那么知识只能在死后得到。那么处于无知状态的在世生活如何能够进行呢?对此,在《斐多》中柏拉图的解决思路是:练习死亡。在世生活不能做到身体和灵魂的完全分离,因此是不可能获得知识的,人,尤其是哲学家的希望或方向是,尽可能接近灵魂和身体相分离的状态。也即尽量不受肉体的奴役,不为感官所迷惑,以独善其身的方式尽量保持自身的纯粹性,为死后做准备。
当然,这是一种极端的生活方式,是哲学家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渴望完全占有理念的生活方式。对于普通人的生活,柏拉图承认“真意见”的价值。真意见即意味着对于理念世界的部分占有,“在指导正当行动方面并不亚于知识。”3参阅《美诺》97c。但是真意见要“捆牢”,把部分占有的理念留在灵魂里,这个“捆牢”指的就是“灵魂回忆”,即用推理的方式追索出理念的原因,这样才能把真意见变成知识。4参阅《美诺》98a。由此看出,柏拉图肯定现实生活对于知识的获取和认知,尽管是妥协之后的肯定。“灵魂回忆”是在世生活中唯一可能的认识路径。
然而,这条路径也存在很多问题:在灵魂还未进入到肉体之前的状态中,灵魂能够获得所有的理念知识吗?还是每一世都有所不同?而灵魂所能获得的理念知识也需要每一世的积累,是一个由少积多的过程?并且,每个纯粹灵魂的状态都类似吗,还是有所区分?如果纯粹灵魂没有区别,那么在世灵魂的区别来自哪里?而这关涉到认识是否具有普遍性和统一性的问题。假如回忆说成立,那么在一世能够全部回忆完,还是需要累世积累?即便是能够回忆,那回忆的知识和与纯粹的理念相遇的知识是否一致,是不是完整的再现?这牵涉到认识的有效性问题。还有另外一个麻烦的问题是,一个人在世所获得意见是否会影响灵魂与身体分离时对纯粹理念的认知,也即人死后,这些活着时候的体验和知识是否会清零。
这些问题在《斐多》中并没有得到解答,“灵魂回忆”的认知道路充满了各种漏洞。究其背后的原因,在于灵魂概念本身的非统一性。灵魂被割裂为在世灵魂和纯粹灵魂,分别作为认知的主体和认知的客体,且是一个不纯粹不完美的主体认识一个完美的对象。这在逻辑上就是行不通的。但无论如何,《斐多》奠定了柏拉图知识论的基础,其他对话,比如《会饮》《理想国》《斐德罗》的认识路径都与《斐多》一脉相承。即对于理念知识的认知其实就是对灵魂自身纯粹性的认知,因此,灵魂认知道路重点强调灵魂的净化、灵魂的回归。
顺着这一思路,《理想国》提出“灵魂转向”,即“灵魂转向自身”,去认识灵魂本身的真理性(纯粹性)。可以说,“灵魂转向”是对“灵魂回忆”的一种更为具体的路径阐释。不过不同于《斐多》,在这里,在世灵魂不再是消极被动、独善其身,而是强调其理性功能的最大发挥。而这个过程在“线喻”中生动表现出来,即从想象到信念再到理智和理性的转变过程。1参阅《理想国》510-511。“灵魂转向”不像回忆说是不确定的零散的认识,它具有实操性,有一系列的课程。通过几何算术、天文学,最后到辩证法,一步步实现灵魂的净化或者理性的上升。到了最高的 “辩证法”阶段,它是唯一的“不用假设而一直能够上升到第一原理本身”的方法。2参阅《理想国》533c-d。
这一理性思考功能之所以在《斐多》中没有得到重视,是因为理性功能是灵魂在不纯粹的状态下(灵魂与肉体混合,也即在世的状态),作为一个人的一部分或者说一个器官功能的发挥。它不是灵魂的最佳状态。因此,灵魂的理性思考功能无法实现对于理念真正的认知。虽然从自身理性出发,从个人经验出发,可以说更具有现实性,但它的问题在于,它是从具体到抽象、从个别到种属的一种归纳过程。这种归纳终归还是现实经验,它和理念认识有着本质区别,同时我们也无法论证如何从这种经验跳跃到理念知识上。尽管柏拉图高扬“辩证法”的纯粹性和无条件性,以及认识知识的可能性,但他无法通过他的认知道路给出证明。我们在《理想国》中也看到柏拉图承认这一点:对于最高的“善理念”的知识并不可得。3参阅《理想国》533a。
《理想国》所提出“灵魂转向”,更多指的是一个方法或是一个态度,它并没有解决认识的可能性问题。而其原因仍旧是“灵魂回忆说”本身的理论缺陷,即灵魂缺乏统一性。只不过“灵魂转向”比“灵魂回忆”对于在世灵魂的分析更为具体,灵魂三分更为强调其理性认知功能,强调灵魂自身的和谐与统一,但是这仍旧是在现实层面的谈论。在逻辑上,二分的世界无法打通。灵魂的认识论问题,同时也是理念论自身的问题,理念是一种纯粹的哲学范畴,具有强烈的“彼岸”世界的性质,但同时柏拉图又用理念来说明感性事物,企图建立两个世界的连接,即所谓的“拯救现象”。如何建立这两个世界的关联?知识论(本体论)问题是与认识论问题相关的。
然而,这里是否还有另外的路径呢?柏拉图在晚期作品中继续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他重新定义灵魂,以灵魂自身的统一性作为灵魂的本质规定,试图通过建立灵魂概念本身的一致性,来解决理念的认识论问题。接下来,我们以《斐德罗》的灵魂观作为典型来进行分析。
二、灵魂概念的修正:灵魂的自动与不朽
在《斐德罗》中,柏拉图说:“灵魂是永远运动的,永远运动的东西就是不朽的。”4参阅《斐德罗》245c5。如何在永恒的运动和永恒的存在之间建立关联,柏拉图这里有两个论证:
首先,运动即意味着有生命,无生命的存在是不能运动的。而永远在运动中,也意味着永远活着,也即是不朽。什么事物能够永远在运动中?只有自动者。因为它不是靠外力推动,不会因为外力消失而停止运动,运动的源头在于自身。灵魂就是这样的存在,自动者因此也是不朽者。这是柏拉图的第一个论证。
柏拉图的第二个论证是,自动者是其他运动产生的源头。其他运动都是由自动者产生的,因此是有时间性,有开始也有终结。然而,自动者作为源头,其本身是没有开始的,如果源头有开端,那么源头就不成其为源头了。它也没有终结,因为如果它被消灭,其他事物也就不存在了。所以灵魂作为自动者既没有出生,也没有死亡,是不朽的。
可以说,第一个论证的原则是有生命存在的生存原则——活着就是运动,第二个论证是“本源”原则,灵魂的本性是自动,是第一因,是万物的本源。1柏拉图的灵魂不朽的论证,可以看出毕达哥拉斯学派观点的痕迹。亚里士多德引用毕达哥拉斯学派阿尔克莽(Alcmaeon)关于不朽的观点:“灵魂的不朽是因为类似不朽的天体(比如太阳、月亮、星星、整个天体),之所以不朽是因为它总是在运动中,因为一切神圣的东西在于持续的运动。”(《动物志》1.2 405a29)。“灵魂在永恒运动中是一种自我运动的物质,因为这个原因(自动),灵魂是不朽的,也是神圣的。” (Aetius iv 2,2)把自动性归于灵魂,从而证明它的不朽,亚里士多德认为这一点来源于阿尔克莽。而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观点也得到了A. E. 泰勒(A. E. Taylor)的肯定,但R. 哈克福斯(R.Нackforth)则认为如果本质上把它看作是阿尔克莽的观点,就忽略了柏拉图对他的发展,柏拉图只是借用了他“运动”的概念。关于二者的详细讨论,参阅:A. E. Taylor, Plato: The Man and His Work, Trowbridge and London: Redwood Press Limited, 1969,p. 184. R. Нackforth, Plato’s Phaedrus, London, Cambridge, 1952.通过运动(创立与感觉世界的联系)来论证灵魂不朽的方式,2参阅《斐德罗》245d-e和《法篇》896a。与《斐多》中灵魂通过认知(以理念为对象)来达到不朽的方式不同。3艾瑞克·J. 罗伯茨(Eric J. Roberts)认为,柏拉图达到灵魂不朽主要有两种方式,分别对应于灵魂的两种功能:认知功能和运动功能。具体参阅:Eric J. Roberts, Plato’s View of the Soul, Mind, vol. 14, 1905, p. 372, p. 375。而泰勒也同意这种划分,并认为柏拉图之所以没有在《斐多》中提到灵魂的运动的功能,并不是没有考虑到这一点,而是为了在没有分歧的前提下去探讨灵魂不朽问题。参阅A. E. Taylor, Plato: The Man and His Work, Trowbridge and London: Redwood Press Limited,1969, p. 184.《斐多》对灵魂不朽的证明是建立在理念论的基础上,代表灵魂的是灵魂的普遍理性部分,也即纯粹部分,灵魂的不朽也只能通过这部分把握了实在(oν或oντι)才能达到。这是灵魂通过认知功能达到不朽。而在《斐德罗》中,通过运动达到不朽,灵魂是作为宇宙的万物生成和运动的原因。此时的灵魂概念不是在心理学意义上谈论的,即作为与肉体相对应的精神性的部分,而具有宇宙论意义,是支持宇宙形成、运行背后的动力。《蒂迈欧篇》中也持相似的看法:人的灵魂结构是作为宇宙的一个结构。这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和身体对立的、纯粹精神性的结构是不一样的。
通过灵魂的自动性来标志灵魂,来论证灵魂不朽,这是柏拉图新的灵魂概念。灵魂的自动性是灵魂的本质,但这个本质不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因为灵魂没有质料。毋宁说灵魂的自动就是灵魂本身,二者是等同的。因此,灵魂并不是可见的实体,而是一种类似于位格的存在,体现为一种创生的、属生的、主宰性的力量。它所具有的这种创生性力量,使它与感觉世界,尤其是身体建立了牢固的关系。灵魂进入身体虽然是因为灵魂的堕落,但灵魂的地位仍旧高于肉体,它主宰着肉体,给予肉体以生命。因此在一个存在体中,灵魂占主导地位,而不是如《斐多》中所描述的,灵魂是被动地避免受肉体的影响。在《斐德罗》中,纯粹灵魂的主动性是不言而喻的,灵魂在天上去追随神,努力观看真理的草原,而堕落后的灵魂的自动性也被明确地阐释出来,这就是“爱欲”(Eros)。1“爱欲”的希腊文是Eros,它区别于“欲”(epithumia)。“爱欲”强调这种“爱”的向善力量与“欲”向下堕落力量的结合。在《理想国》的灵魂学中,爱欲只限制在灵魂的欲望层面,被等同于欲望,真正重新确立欲望的地位是在《会饮》和《斐德罗》中,但这个欲望是经过爱的培养和训练的。也即爱被引入了欲望,欲望成了爱欲,爱为欲正名。可以说,灵魂的自动性保证了在世灵魂和纯粹灵魂的统一,也即灵魂概念自身的统一性。
柏拉图把灵魂概念发展为一种自动性的力量来论证灵魂不朽,并从这个逻辑前提去说明现实,阐释在世灵魂的状态。这种思路和“灵魂回忆说”并无二样。首先,这里都存在一个循环论证。“灵魂回忆说”中,回忆以灵魂的先在为前提,而灵魂的先在是由回忆的论证得出。在灵魂的自动论证中,也是从灵魂不朽的内涵出发提出灵魂具有自动性,反过来,又通过自动性去论证灵魂不朽。其次,这都是一种逻辑假设。在这种方法论中,“假定有这样一些东西,如美本身、好本身、大本身之类”,2参阅《斐多》100b3。然后一步一步推演,即“先认定另外一个你觉得高一级的最好的说法,做出说明的根据,这样一层一层往上攀登,直到找出合适的为止”。3参阅《斐多》101d3-7。这种陷在逻辑概念中的论证方法,可以说是柏拉图认识论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
然而与“灵魂回忆说”不同的是,在《斐德罗》中柏拉图并没有仅仅停留在一个逻辑假设的灵魂概念上,这一概念仅仅是前提,他从现实经验出发去论证这一概念的合理性以及探索一种抽象知识的可能性。从个人的具体现实出发去探索理念世界,在《理想国》中表现为“灵魂转向”的功夫,但这并不是人人都能做的,至于谁能够做到,且做到多大程度上也很难讲。这只是柏拉图对于哲学家、理想教育的一种想象。这仍旧是一种“理想的”的经验,而不是基于真正的现实。《斐德罗》所要寻找的是一种更具普遍性的经验,人人都有的经验,而对此的证明就是“爱欲”。爱欲是一种本能,根植在人的本性中,不局限在某类人中。同时,爱欲遍及灵魂的三个部分(理智、激情和欲望),爱欲除了有对理念的热爱,也有对于荣誉、肉体的满足的追求。它是一个更为完整的概念。爱欲不是灵魂单一理智功能的发挥,因此它不是通过灵魂的一个部分去认识灵魂的整体,而是表现为对于灵魂整体的回归,朝向它的一种涌动、生长的力量。而这种朝向灵魂整体(神圣性)的特征,给予“爱欲”实现真理性认识的可能性。
爱欲作为一种力量和运动,方向性在爱欲中就显得格外重要。不同的方向,导致不同的爱欲层级,也导向不同的认知路径和认知结果。如果朝向肉欲的满足,那么爱欲就表现为对性的沉溺,是一种低级的爱欲;而如果朝向的是美本身和善本身,爱欲就表现为对哲学的爱,是相对高级的爱欲。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并不是所有的爱欲都能导向对纯粹灵魂的回归?或者爱欲认识论仍旧是某些人的认识道路?对此,柏拉图持否定态度。柏拉图把爱欲看作是一种创生的力量,在所有的爱欲背后是一种渴望不朽的表达,朝向不朽的行动。4参阅《会饮》206b。在这一点上,表面上相互对立冲突的爱欲之间具有一致性。只不过普通人所认为的不朽,在柏拉图看来,并不是真正的不朽。不管是身体层面生育子女,还是在灵魂层面孕育精神子女,比如工匠制作,政治家立法以及诗人创造,都只不过是在时空层面上的延续,这种生命仍旧是可朽的。真正的不朽类似神的不朽,也即超越时空的至善,只有进入到可知世界中,人才能达到真正的永恒和不朽。而柏拉图所做的工作是利用人人都具有的不朽的渴望,引导人认识且转向真正的不朽,也即引向哲学,引向善。
总之,爱欲是在世灵魂自动性的表达,自动性保证了灵魂概念本身的统一性,这是柏拉图对早中期作品灵魂观的修正。并且,这种统一性的论证不仅仅停留在逻辑演绎或者逻辑假设中,而是基于生活体验,基于普遍的人性,立足于伦理生活的探索。柏拉图试图把普遍的本能性的爱欲引导向善,实现对理念知识的认识,这是另外一条打通二分世界的探索,但它能否实现上述目的呢?能否解决“回忆说”的困境呢?我们在下一节中重点分析这一点。
三、困境的出路:从“爱欲”到“迷狂”?
爱欲是一种“居间”1“居间”的意识被沃格林称为“非事实”性(non-fact)存在的人类现状。的实践,这是因为爱欲本质上是“缺失和丰盈的一体”,它“居于两者之间”,使得“整体自身自己就连成一气”。2参阅《会饮》203b-204a。柏拉图把它比作一个精灵,它使神人之间有了来往和交流。哲学的爱欲是将有死的人和不死的知识联系起来的努力。虽然人的灵魂居于有死者之中,但是它的目的是不朽。它欲求自己所缺乏的,这个所缺乏的永远不能被满足,所以对于不朽永远处于一种追求的状态中。也即在爱欲的追求过程中,人对于至善永远有着一种敞开的态度,这是一种基于对自我处境的认识,不断超越自我处境的过程。如此,“爱智慧”中的“智慧”才能被人“占有”,但这里的“智慧”不是全知意义、本源意义上的,而是一种“关于有知的和无知的”居间的智慧,一种在人的生活中“知道自己知道什么和不知道什么”的自我实践知识。3参阅《卡尔米德》171d-172b。更为确切地说,是“真意见”。
因此,我们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爱欲采取的并非真理之路,而是居间的“真意见”之路。4具体参阅罗兴刚:《柏拉图的第三条路线——“爱欲”作为“真意见”的“居间”教诲》,《理论月刊》2012年第10期。而“真意见”在柏拉图早期的著作(比如《美诺》)中也稍有涉及,并不新鲜。但不同的是,柏拉图对于爱欲如何达致“真意见”有着具体的分析,主要体现在《会饮》和《斐德罗》中。
在《会饮》中,这条认识路径被形容为“爱的阶梯”,从美的形体开始,到美的心灵再到美的行为和制度,到美的知识,最终达到美本身。这样一条道路具有明确的阶段性,以及可参照性,而最终对于美本身的认识是一个顺理成章的过程。这让我们想到《理想国》的“线喻”,爱的阶梯是否直插真理的云霄,这一点让人怀疑,且这种认识路径是否就是一个可以不断攀升的阶梯,也同样是没有经过论证的。每一个阶段,比如对美的形体的认识、美的心灵的认识,分别属于不同的层级,这些层级之间是否就有沟通的路径,是否就是跨一脚的问题,同样令人质疑。在这种几乎是直线式的认识路径下,它还是呈现出了较强的理智意味。这让人怀疑这种攀登的动力不是来自欲望、本能性的,而是理智。在爱的阶梯中,柏拉图想要把爱欲引导向最高的智慧,倘若人不想被引导向上怎么办?即便是人人都愿意向上,未必都能够实现这个目的,因为这条爱的阶梯之路并不容易,和“辩证法”的上升之路一样,都是极少数人才能得到的。
鉴于此,柏拉图发现自下而上的探索是比较困难的。不管是理性认知还是爱的阶梯,它都属于在世的经验,和彼世无法建立关联。两个世界仍旧是割裂的、分离的。爱欲虽然居于两个世界之间,但主要是作为在世生活的动力、道路,它携带着此世的重量而难以飞升。那么,如果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给予,是不是才有沟通的可能性?是否只有当神圣性主动去连接下界,而下界能够开放地接受,才有认识的可能?在《斐德罗》中,柏拉图对这种可能性进行了探索,并将之形容为“灵魂的迷狂”。
灵魂的迷狂有四种,包括先知的迷狂、仪式中的迷狂、诗神凭附的迷狂和爱的迷狂。前三种迷狂来自于传统,而第四种迷狂来自于个人。通过引入这些迷狂状态,柏拉图想去类比灵魂获得理念知识的一种可能性状态。拿爱的迷狂来说,人在热恋状态中,看到对方是完美的,不是说对方真的没有缺点,而就是觉得美。理性有参与,也起作用,但感受并没有被压制。在那种爱恋中,一个人体验到一种美好,它远远超越现实的美,超越对方的美貌,是一种出神的状态。因此,如果灵魂和理念在一起,就像灵魂回到了家,用《斐德罗》的表达就是:见到了自己所跟随的神,见到真正的美本身。这种状态和爱的迷狂状态有可比性,从中推导出这种状态,在感受性上是说得通的。那么,到底“爱的迷狂”是什么样的呢?柏拉图在《斐德罗》如此描述道:
当他凝视的时候,寒颤就经过自然的转变,变成一种从未体验过的高热,浑身发汗。因为他从眼睛接受到美的放射体,因它而发热,他的羽翼也因它而受到滋润,感到了热力,羽翼在久经闭塞而不能生长之后又苏醒过来了。这种放射体陆续灌注营养品进来,羽管就涨大起来,从根向外生展,布满了灵魂的胸脯——在过去,灵魂本是周身长着羽毛的。在这过程中,灵魂遍体沸腾跳动,正如婴儿出齿时牙根感觉又疼又痒,灵魂初生羽翼时,也沸腾发烧,又疼又痒。
它一部分注进他身体里面,一部分在他装满之后又流出来了。像一阵风或是一个声音碰到平滑而坚硬的东西就往回窜,窜回原出发点一样,那从美出发的情波也窜回那美少年,由天然的渠道——他的眼睛——流到他的灵魂。到了灵魂,把它注满了,它的羽翼就得到滋润,开始发出新羽毛,这样一来,爱人的灵魂也和情人一样装满爱情了。1《斐德罗》251c-e。中文译文参阅朱光潜:《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127页。另,英文版本参阅:《柏拉图著作集》第4卷,本杰明·乔伊特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1页。
我们看到,柏拉图用诗意的浪漫的文学性的语言描述灵魂马车如何奔向美的对象,这种“爱的迷狂”状态,和他一贯的写作风格大不相同。我们也可以对此分析道,因为迷狂无法言说,它不是可以用理性分析的。那这种状态就是所谓的灵魂认识到真理的状态吗?迷狂是否反对知识,反对理性,如何调和迷狂——作为诗的状态和柏拉图一贯的理性主义的立场?对此,我们需要对“迷狂”这种诗意的状态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在《斐德罗》中,柏拉图按照掌握真理的多寡把人分作九等。第一等是哲学家或“热爱智慧的人”(philosophos),“爱美的人”(philokalos)或称之为诗人,“缪斯的追随者”(mousikos)或称之为“爱者”、“爱恋者”。2参阅《斐德罗》248d。哲学家与“爱美的人”或“缪斯的追随者”相提并论,那意味着哲学家不仅爱智慧,而且爱美,并且不能不通晓缪斯的艺术(mousike)。在这里,最好的哲学家和最好的诗人并不构成矛盾。当然,在柏拉图这里,“缪斯的艺术”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模仿的艺术或者诗艺。接下来我们看到,诗人或者被柏拉图所称的模仿艺术家只能算是第六等人。在此,柏拉图区分了mousikos 和一般意义上的poietikos。
缪斯是诗乐和知识的象征。英语的music(音乐)和museum(博物馆)都出自希腊词Mousa(缪斯)。在《克拉底鲁》里,柏拉图打算从词义学的角度去解释缪斯的来源,认为缪斯姐妹们所以取这个名字,是因为她们从事了对广义上的哲学或学问的探索(mosthai)。3在《克拉底鲁》406a、《会饮》205中,柏拉图认为mosthai(探索)是mousike(音乐、诗)的词源。在古希腊人的神学观中,缪斯姐妹们不仅是诗、音乐、舞蹈之神(参阅《会饮197a》),而且至少从公元前5世纪起,还监管天文哲学和一切研习活动。诗乐和哲学同源。在《斐德罗》中,柏拉图把哲学家的工作和生活看作是对缪斯姐妹中最年长的两位,即卡莉娥佩和乌拉尼娅的尊崇,因为她们讴歌的主题是天体和所有关于神和人的故事,她们的诗歌是最崇高的乐章。缪斯的艺术(mousike)可以含带“学问”甚至“哲学”之义,缪斯不仅激发人们诗的想象,而且还促使人们从事包含哲学意义的探索。因此,诗歌和哲学在“通神”(受缪斯神的激发)的意义上是一致的。1参阅《斐德罗》259d。从这一点上,我们也能够很好的理解:为什么苏格拉底在睡梦中接受神谕,要他“实践和护理缪斯的艺术”(《斐多》60e6-7),以及究竟在什么层次上,柏拉图反对诗人、诗歌(《理想国》第10卷相关论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诗人不同于我们寻常所理解的只通晓某种诗歌技艺或仅仅只会模仿、毫无思考能力的人。
而缪斯所催发的灵感是一种“通神”状态,这种状态被柏拉图描述为“迷狂”。诗歌中的灵感状态是由缪斯神激发而来,优秀的诗人和艺术家不能仅仅满足于所掌握的技艺(poietikos),因为技艺只能指导通行的做法,并不能让人出类拔萃。“因为清醒者的工作不能进入艺术的殿堂,不能成为迷狂者的对手。”2参阅《斐德罗》245a。当神赐的迷狂使人处于精神恍惚的状态时,艺术家或诗人可能产生超乎寻常的艺术感觉。比如当斐德罗称赞苏格拉底的谈话中所表现出来的“超乎寻常的辩才”时,苏格拉底答道:“这里有神的显灵。”3参阅《斐德罗》238c-d。
尽管柏拉图把哲学家和诗人都看作是“缪斯的追随者”,尽管他在《斐德罗》中有意识地淡化了诗人和哲学家的界限,但他还是认为诗人的迷狂低于哲学家的迷狂。在柏拉图看来,诗人的迷狂尽管令人羡慕,但还不是mania(狂迷)的最佳表现形式。只有迷狂的哲学家才能自觉接受神的指引,接近真正的善和美。诗人的迷狂缺乏一种积极主动的力量,这种力量要体现为“追随”缪斯,献身于缪斯艺术,成为缪斯所喜爱的“随从”。因此,哲学家的迷狂即爱的迷狂是四种迷狂中最好的一种,是迷狂的最佳表现形式,只有哲学家才是缪斯艺术真正的实践者和追寻者。
哲学家的迷狂是爱的迷狂,靠爱来实现。虽然低层次的爱主要针对物质层面上的人或物,但是真正的爱是不会长期停留于此,它会从物质层面升华到对精神美的追求。并且,这个真正的爱或高级的爱,超越于一般意义上的理性,它不受世俗化理性的制约,而体现为一种对神的信念和高层次上的直觉感知。在这种状态中,人进入到一种灵感状态,感到“通神”的美好,实现一种对世俗观念的超常理解。而这种理解是普通的理性所达不到的。这就是“爱的迷狂”状态。
但是,迷狂并不是常规意义上的无知,它的这种非思考状态是一种灵感,或者通神的状态。这一点(诗人所处的灵感状态)在《伊安》中被当作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加以描述。4参阅《伊安》534d、e。因此,《斐德罗》中,诗人的迷狂并不是一个弱点,反而是一种福分。神赐的迷狂甚至比受人尊崇的节制(sophrosune)更可贵。《理想国》推崇的三个阶层的美德即“节制”“勇敢”“智慧”,由于它们不是神赐之物,所以尽管它们比迷狂多一点凡俗的理性,但少一些通神的灵秀。而通过迷狂,人们可以接收到“最美好的信息”。5参阅《斐德罗》244a。
虽然柏拉图强调迷狂的重要,但是他从未明述或暗示过可以用迷狂取代知识。很明显,人不可能一直处于通神的状态中,但可以处于理性的、有知识的状态中。与上述三种迷狂相比,爱的迷狂之所以是最好的,还因为爱包含了知识。爱处于有知和无知之间,人与神之间,因此,它既是人的感觉,又是驱使感觉的神力。爱不仅不排斥知识,而且还欢迎知识的参与,因为知识有助于人把握爱的真谛,使人在追求和实践“爱”的过程中不致迷失方向。在《斐德罗》结尾,苏格拉底请斐德罗传达缪斯的一条信息:给荷马和其他诗人,给梭伦和其他立法者,给卢西亚和其他讲稿撰写人——倘若他们知晓真理,指出自己的作品是无用的废物,那么,他们就可以获得“哲学家”的美名,以取代原有的称呼,即诗人、立法者和诗歌撰写人。1参阅《斐德罗》278b-e。诗人所缺乏的就是哲学家这种辨析的本领,排斥知识的文字只能误导人的思考,因此,诗人应该把文字或者语言的力量用于对“真理”和“美”的彰显上。
总体来讲,前三种迷狂完全拿掉了人的主体性,人只能被动接受,等待神灵附体。尽管在基督教的神启、先知思路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这种思路的力量所在。但是,柏拉图作为一个理性认识论者,对此是无法接受的。但与此同时,迷狂不是人自身所能创造的状态,它需要神圣性力量(爱的对象中的神性)的参与,在这两种力量的交汇中,人能够回忆起神圣的理念世界,从而看到(behold)2参阅《斐德罗》247c6-e4。“看”(έωρακυία)在《斐多》中有所提及,这是理智之眼的看,是对推理的补充。在《会饮》中更是提到这种爱的最高点的看。自己。这种“看”是一种注视,是对自身纯净无污染部分的观看,而这个观看同时也是与理念的相遇。这样一种看,完全不同于理性的把握,更为确切地说,它是灵魂的自我回归。这种灵魂之眼的观看之所以能够认识到真理,就在于真理本身就存在于个体灵魂中,只不过由于肉体的遮蔽,灵魂之眼无法观看罢了。
在理性认识论中,人囿于自己一定的理性观念、概念体系,终究无法摆脱某种经验或某种理解框架,在这种状态中,理性无法突破自身,也无法继续扩展,这也是我们所说的理性的有限性,只能待在此岸世界。然而在爱中,人面对一个具有神性的他者(爱人),这种情感本身就带来一种开放、理解、接受的倾向。3关于情感认识论,参阅谢文郁:《语言、情感与生存——宗教哲学的方法论问题》,《宗教与哲学》第三辑,2014年。在这种情感的倾向中,恋爱中的双方,尤其是爱者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解构先前的固化思维、思维定式,能够吸收不一样的感受、理解和价值观,从而扩展理性的认知。尤其是在“迷狂”状态中,它不仅仅是一种情感上的、感受上的体验,更能够解构人的某种理性认知。而在爱的这种状态延续中,不仅仅有解构的参与,还有新的理解力的加入,这叫做建构。在这种不断解构建构过程中,“迷狂”作为一种认识方式或是认识理论才是有效的。
“迷狂”是一种飞跃,从此岸到彼岸的飞跃。迷狂的状态也是两个世界的分界点。爱欲作为一种非理性的情感状态,帮助理性实现跨越,理性不再是一种静止的规范(共相),而成了一种能动的自我超越性。这种自我超越,使得掺杂了感官印象的理性进入到纯粹的领域。因此,“迷狂”与其说是非理性的,还不如说是超理性的。迷狂在柏拉图看来,实现了理性的最大化或者说理性的“辩证法”。逻辑上“迷狂说”解决了“回忆说”两个世界割裂、无法统一的问题。然而,它却遗留了更大的问题。
爱的迷狂具有不可验证性,既不可验伪,也不可验真。就不可验伪来说,爱的迷狂是柏拉图认识论的闭环,它从逻辑上和现实经验的角度,解决了“回忆说”认识论的困境,论证了获得理念知识的可能。这是一个自洽的体系,后人也有很多这样的路数。即对非理性力量的重视,从非理性的力量出发去探究认识的可能性,这个论证还是很有力量。我们也从中看到柏拉图自身学说的丰富性,他不是我们所以为的一个严苛的理性主义者,他同样非常重视非理性的力量。柏拉图不仅重视智慧,还重视爱本身。爱不仅仅是现代哲学的问题和关注点,它可以追溯到柏拉图,
但对不可验真来说,这里遗留了很多问题。爱的迷狂跟哲学还是相差太远。迷狂跟巫术、神灵附体、喝多了酒、梦境有什么区别?如果想对迷狂状态进行验证,也仅仅只能拿外在的标准,比如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快乐的不同的精神表征,因为迷狂本身就是一种私人化的体验性和感受性,缺乏公共交流的基础和途径。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很难说它就是一种认识,或者说可以达到共识的认识。缺乏义理思辨的认知是否具有有效性和普遍性,这个是现代社会,尤其是科学主义所强烈质疑的东西。“迷狂”没有一种可量化的标准,因此,很难重复这样一条认识路径。如果不能够清晰知道如何达到迷狂,迷狂最终只能落入一种偶然的意外的体验罢了。
迷狂是一种认识状态,柏拉图通过对这个状态的过度描述,希望能够解决世界二分的问题。柏拉图试图论证爱欲是一条可以实践的认识道路,而《斐德罗》所强调的爱的迷狂状态是对这条道路可行性的一个证明。在爱的迷狂状态中,人才能和真理在一起,直面真理的丰富和全知。这条认识道路不同于理性认知道路,但也不是全然非理性的,它更多呈现为理性和非理性的张力。这个张力问题永存于人类本性中,认识论问题必须要面对理性与非理性的张力问题。而后人对柏拉图认识论的发展,也无非就是对这个张力问题的不同解决思路。可以说,虽然遗留了问题,但通过理性和爱欲达到对真理的认识,柏拉图在这方面所做的探究,不管对于后人还是整个哲学史,都影响巨大。
——读《图像与爱欲:马奈的绘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