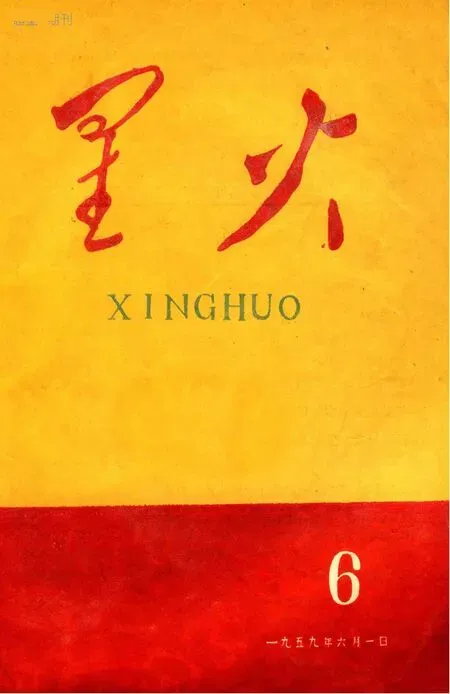那极小的部分
○ 贾志红
一
高新区道路两旁的香樟树并不高大,树干不过碗口粗,一看便知道它们的年龄是符合高新这个区域的。树虽然小,叶子却毫不敷衍这片南方的红土地,它们长势茂密、彼此交织,只允许阳光星星点点地漏下,像洒落地面的碎银。而细细密密的小果实,隐蔽于枝叶间,如绿珍珠一样与叶子相爱相守。
我初到南昌是在一个七月,香樟树让这个南方城市的盛夏有着碧绿的浓阴。但七月的浓阴带给南昌的不是清凉而是密不透风的闷热。其实炎热于我而言是一种熟悉的感觉,在奉调来南昌前我刚刚结束在西非四个年头的工作,那片土地终年被赤道的太阳炙烤,四十摄氏度以上的气温是家常便饭。但是南昌的闷热与西非的燥热有些差别,它仿佛是凝滞不动的。香樟树的浓绿加深了这种凝滞感。
我喜欢香樟树,就像喜欢东北的白桦和西北的胡杨。喜欢,这种情感的生发是没有由头的,似乎也不需要什么由头。抬头看看天空、俯首瞅瞅大地,就怜惜着这大地之上的植物了。而越是在气候不完全尽如人意的地方,植物就越发令人崇敬。用美或不美、有益或无益来打量植物是浅陋的,就像一位诗人所说:在神的庄园里,人无权评论植物。它们不似人或其他动物,不喜欢某个地方可以抬脚就走,它们和脚下的土地签订了生死同盟,活着装扮土地,死了进入土地。仅凭着这份执着的契约精神,就让我对植物产生足够的敬意。
初始,我不认识香樟树,抬眼细细看着这陌生的树,问一位清洁工大姐,这是什么树?我的北方口音极好地为我的提问做了解释。大姐咧着嘴笑我,慢悠悠地说,这是香樟树。她的南昌普通话语调轻快,有掩饰不住的喜爱之情,像喊叫自家的二丫头。我听懂了。
接下来的两个晚上,我在住处的周边游走。陌生之地,我不敢走得太远,看着表,选定一条道快步走二十分钟后再折身返回。高新区的工厂多,夜晚少人,植物繁密,暗香阵阵。我有时候寻着香味走,仿佛想找到它的源头,不过气味这东西总是虚幻,在似与不似之间迷惑着人。我曾经寻着一种特别的香味一直找,边找边琢磨那味道,熟悉却又很遥远。等到我终于站在一家烟草工厂的大门口时,不禁莞尔一笑,烟叫作香烟大概是有道理的吧。有时候选定的某条小道太短,不到预定的时间它就到了尽头,如小河流汇入一条更大的主流。华灯闪烁处,一条小路惶惶然失去了自己,也或许是欣欣然终于追上了主流,谁知道呢?谁能看透一条路的心?我便止步,在香樟树的浓阴里往回走,又从繁杂的花香中辨识出水的气息,湿湿的、微腥的,从同一个方向漫延过来。我知道那是艾溪湖。
李静专程来看我,在我到达南昌的第三天,她从江西西部的一个地级市新余坐火车来南昌。普通火车需要两个小时,高铁只要半小时。李静坐普通火车,新余的高铁站远离市区,从她家去高铁站的时间远远多于她在高铁上的时间。南昌的高铁站也是如此,远远地躲在城市的边缘,高冷地遥望着拥挤不堪的老火车站。我们在电话里说,坐普通火车呀,普通火车更划算。
我去火车站接李静。我前天才刚刚从这个通道里走出来,跻身陌生的城市、融进陌生的人流,今天便又跑来接人,俨然已是这城市、这人流中的一员。我已经吃了两三天南昌饭菜了,呼吸间有了辣椒的气息,像一小股火,灼着我的鼻腔和牙龈。尽管我每次都会和饭店的服务员说,不要放辣椒啊,但是菜依然是辣的。我边吃边呵呵地哈着气,鼻涕眼泪流了一脸。服务员小哥儿歉意地看着我,不好意思地说,锅是辣的、锅是辣的呀。
倚着栏杆等李静,突然觉得接人这个事儿让我对南昌有了最初的归属感,我像个主人一样,在这个城市有落脚的地方,能接待朋友了。尽管我不过是早来了两三天,也才刚刚弄清楚5路车是从高新区直达火车站的,虽然它的行车路线弯弯绕绕,比出租车要花费多得多的时间,但是,在一座城市会坐公交车出行,难道不是更有主人的气象么?况且价格又便宜,叮叮当当地在车上晃悠一个半小时,才需要投币一元钱。
此前,我没有见过李静,但是我并不担心认不出她,实在不行的话,她还可以认出我,我们见过彼此的照片,多年的网络交往令我们像邻家姐妹般熟稔。不出所料,她认出了我,她说,你和照片一模一样。她又何尝不是如此,只不过我眼睛近视,没有率先认出她。我领着她上了5路公交车,挑了临窗的座位坐好,回我住的酒店。那时,我住在分公司附近的锦江之星快捷酒店,这家酒店是分公司的协议酒店,奉总公司调令而来却又没有租到房子的外地员工都暂时住在这里。我和李静是首次见面,此前我们在一个文学网站里互相点评对方的文章并成为朋友。我承认阅读其实都带有窥探对方隐私的意向,但是矜持和所谓的修养又让我们从不开口打探对方,彼此只是从文章的缝隙间漏下的一言半语中去猜想远方那个人的生活。而见了面就不一样了。在七楼的一个临湖的标间里,我们聊了一个晚上。工作、写作、家庭、生活。李静翻着我正读着的一本书,是杜拉斯的《情人》,书和这个黏稠而芳香的夏夜的氛围很搭,和临湖的房间也很搭,甚至也配这暧昧的灯光。本来灯光是明亮的,但是坏了一盏灯,便恰好有了我想要的效果。
不过我看出李静的嘴角微微上翘了一下,她是一家事业单位的宣教部长,我曾经戏称她是马列主义老太太。她的服饰和发型从来都是一丝不苟的,衣服是稳重的颜色,头发梳理得纹丝不乱,在脑后挽个发髻,像宋庆龄的发型。她说话也是严肃的,令我联想到工作中的李部长。我猜想她大概不会读杜拉斯吧,《情人》这类书是不会进入一个宣教部长的书架的。她手里翻着书,嘴角带着意味深长的微笑,我几乎担心她责怪我不看好书,想把书拿过来,藏起来,像藏住一个真正的情人。她却出人意料地说,回头她也想看看这本书。
女人间的聊天,什么都能说,远的、近的、她的、我的,别人的……后来,直到眼睛都睁不开了,我们才终于沉沉睡去。
那晚的长谈没有艾溪湖的波浪声来伴奏,只有空调很卖力的送风的声音,或许其他的季节会有吧,安静的、开窗的时候便能听到湖水的动静?那个夏夜,门窗紧闭,湖水过于平静,香樟树的浓阴也锁住了艾溪湖,它顺从、乖巧,像所有被城市圈养的湖泊一样。
那会儿,我还没有走近过艾溪湖,还不知道我将在南昌一待就是五年,而这五年,艾溪湖成了我在这座城市生活过的一个见证。当然,除了湖,还有人也是见证。比如吴琼、李静。接来下,我的另一个主人公吴琼要出场了,是李静徐徐拉开了大幕。她用一个呵欠结束了长聊,最后说了一句,咱们明天去见吴琼吧。而后,轻微的鼾声便均匀响起。
二
我和吴琼的相知源于黑夜,虽然我们是在一个明艳的夏日首次见面。但是我们的确是在一篇名为《黑夜怀想》的文章中相识的。
那篇文章其实更像一篇私密的日记,回忆青春往事,有密集的迷茫弥漫在浓稠的黑夜中。我在那篇文中,用梦游者的笔调写一些夜晚,写我在黑夜中和母亲相拥而坐,母亲盼着刚刚逝去的父亲的灵魂能借助黑夜的遮掩回到家里来再和她说些什么,或许能交代一些没有来得及说出的事情。母亲相信人死后灵魂依然存在,而鬼魂和人的交流必须在黑夜完成。我在那些黑夜中恐惧得浑身发抖也兴奋得眼神明亮。最终,当然没有什么鬼魂,清晨一如既往地从窗口跳进屋来。清晨像个神,它救了我,其实也救了我的母亲。
吴琼在这篇文章的后面写下了大段的留言,她说,黑夜到来,万物寂静,在白昼渺小的事物都在黑夜被无限放大,模糊的事物也逐渐清晰,放大和清晰便于修补,人需要黑夜是因为需要一个修补的时间,像兽躲在一个地方检查伤口,肌肤的、内脏的,乃至心灵的,缝补、抹平,而后不动声色地迎接下一个黎明。黑夜给人喘息身体和平衡内心的机会。
时间久远,我已不能完整记忆留言的全部词句。但是这个以“于是”为笔名的人令我记忆深刻。我觉得吴琼既是黑夜的进入者又是黑夜的旁观者,那是一个黑夜清醒者的独白。我知道她一直在和顽固的失眠搏斗,她见证一个个黑夜由淡渐浓、再由浓变淡,直至融化在新鲜的白昼里。
坐在吴琼家的沙发上,我们仨一起回忆那个把我们联系起来的文学网站。其实那个文学网站还在,不用回忆,鼠标一点就能到达。但是,网站改版升级了,再也找不到旧版的内容,它像一个搬入新居的家庭,把旧家具、旧饰品一股脑扔了。到处新崭崭的,光亮得晃人眼,恍如陌生之地。也或许,那些旧物没有被扔掉,只是放进了一间储藏室,落了锁,也落了灰尘,我们找不到了?
吴琼的手腕上戴着一个玉石的镯子,发出晶莹润泽的光。女人间聊天的话题总是跳跃不定,前一刻还在说着黑夜啊、迷茫啊等等形而上的问题,下一刻就衣食住行、五谷杂粮了,那是现实的、可触摸的话题,透着生活的温度和欢乐的细节。聊起镯子,她说她本是不喜欢戴首饰的,但是发生了一件事之后,她便喜欢了,尤其喜欢玉镯。
我心里自是一惊,我猜想,她必有一只镯子在某个时刻、在毫无预兆的时候,碎过或是遗失。女人大多热爱首饰,总有那么一两件被格外寄予深意,我亦然。我曾经有一条绿松石手链,在一个毫无预兆的时间、在我不经意的一个挥手动作之后,飞离我的手腕,再也没有找回,而此前它是碎过一颗珠子的。传说每一种宝石上都住着一位神,这类神大概都是微神吧,没有过于强大的法力,动不动就先把自己弄碎了。微神的职责是护佑在人类中同属弱者的女人,女人戴珠宝首饰是和微神惺惺相惜,我们需要微神的提示和护佑。碎是警醒,消失便是微神披挂上阵去降妖捉怪了吧。而这一去不回又反过来令女人如此心碎。
果然,吴琼讲起了那只玉镯。本是放在包里的,并没有佩戴,包挂在门后面,不记得那只包是否坠落过,在打开包取东西时,发现那只玉镯竟然断裂了。吴琼相信那是一种暗示,或者是有什么意外被那只玉镯默默地抵挡了。我亦信,这是神和人之间的密语,神提醒人时时注意自己的修行来免除灾难的降临。这无声的密语,或许只有女人才懂。曾经有一个男人说,这是你们女人的神经质。我斜了他一眼,懒得接他的话。他哪里懂得,他那么高大风光,恨不得去征服全世界,而微神,在低处,他看不见。
三
一周之后,我搬离宾馆,租住了一间临艾溪湖的公寓。在一栋大楼的20层,我站在落地大窗前看着夜晚的灯火。湖泊已经被夜色遮盖,横跨艾溪湖的大桥彩灯闪烁,像一条彩虹降落人间。
这间公寓让我在南昌有了踏实感,它小而安静,足以安放我工作之外的身心。或许是楼层太高了,即使安静的夜晚,我打开临湖的窗子,依然听不到湖水的任何动静,风声、水声、风掠过湖水的声音,统统都没有。没有动静的湖总是给人虚假的感觉,像孩子怀里的布娃娃,不哭也不闹。城市里的湖或许就是孩子怀里的布偶。
其实,这间公寓主要用于安放我的睡眠,我醒着的时候大多都是在办公室里的,或者在艾溪湖边走路。我就职的单位是一家央企,担任财务部的主管意味着数据和报表是我的日常,加班成为常态。而不容易获批的年休假,我把它们统统送给了远方的旅行。有一天上午,我回公寓取忘在床头的材料,打开门,站在门口愣住了。我发现公寓的上午,阳光竟然这么好,大落地窗像一个取景框,天空、湖泊尽收其中。窗子朝着东南方,阳光打在湖水上的碎影都清晰可见。而我,几乎没有留意过公寓竟然有这样明媚的上午,那些为数不多的在公寓度过的上午,或许是懒在床上补觉,或许是忙着其他的事情,唯独不曾看一看这扇临湖的窗。它只在这一刻最美,时辰过了就过了。而另一个上午它或许又是另一番美,不会复制。美从来不去抄袭,不抄袭别人也不抄袭自己。
我买了几盆绿植放在阳台上,滴水观音长势很旺,绿萝和吊兰看起来弱一些,不过,没有关系,卖花的大姐说了,傻子都能养活绿萝和吊兰。
又去超市买了几件炊具,不太复杂,不过是刀具、案板、锅,三个碟子和三个碗,为什么是三个?不是更少或更多?那是因为我心里想着在这间公寓里招待李静和吴琼。还有三只高脚酒杯,没准儿什么时候我们情之所至时想喝上一瓶红酒呢。
时间这东西改变着一切却也固化了许多事物。比如说习惯。
初次沿着艾溪湖徒步的时候我不知道绕湖一圈是12.6公里,可能是沿途的景致过于漂亮,荷塘、长廊、曲径应有尽有,不知不觉我就绕着长形的湖走了一圈。在近处才觉得艾溪湖不是孩子怀里的布娃娃,它会哭会闹会踢腾。水浪拍打堤岸,运送鱼的船突突突地在湖里行驶,散发着浓重的腥味。隔一段距离就会有一个写着禁止钓鱼的牌子竖立在堤岸上。这才是湖泊应该有的样子。湖堤上的植物中,香樟树不再唱主角,其他任何树都不是主角,根本就没有主角,桂树、橘树、柚子树、杨梅树、山茶树等等群分天下。杜英树在七月底开出了花,白白的像一串串风铃。多亏它开花了,它不开花的时候,我把它当成了香樟树。花叶间有几片红色的叶子,像经了霜一样。我更喜欢杜英的另一个名字:杜氏木兰。如旧时深闺中的女子。走在湖边看见它,我喊一声:嗨,木兰你开花了。花期好像还挺长,什么时候落的,我没有记住,想必它落花的时候不似开花那般热闹。过于安静的事物不容易被人记住。有些花就不会安安静静地落,比如山茶花,它凋落的样子令人心惊。看着好好的一朵花,没有衰败的痕迹,却整朵地坠落了,花瓣不散,从花茎处断裂,像走至悬崖的女子,决绝地往下跳,扑通扑通地,能听见声响。香消玉殒地躺在地上了,又不甘心,朵朵睁着眼睛。
后来,绕艾溪湖徒步成了我的习惯,每周三次或者更多。下班之后,直接去湖边,按顺时针的方向走。走着走着天就黑了,不过我并不害怕,大部分路段都有路灯,人也不算很少。但是有些时候也是害怕的,比如说七月半的中元节。先是惊诧这一天湖堤上锻炼的人怎么如此少,接着就看到了路边一圈圈的灰烬或正在燃着的火焰,忽明忽暗,青烟缭绕。一位大姐行色匆匆,她诡秘地冲着我说,赶紧回家吧,今晚不要在外面走路。
到了十月,满城桂花香,湿热已经从这个城市撤离,南昌迎来了气候宜人的秋天。我在南昌度过第二个中秋节的时候,收到一个远方妹妹寄来的月饼,她和我同名同姓,偶然的机会让我们彼此知晓了对方的存在。她在信里写到,月饼是老字号的、提前预定的、限量版的。我专门去湖堤上偷采了一枝桂花来配这限量版的月饼。偷花回来的路上遇到一个老人家提醒我,这是丹桂,他说,你要偷就偷金桂,又香又好看啊。插好桂花,又想了想,还有什么东西能配得上远道而来的月饼,铺上那块从印度背回来的真丝地毯吧,红的底色配黄灿灿的月饼,恰好呢。便搬一把椅子垫脚,从吊柜里取出地毯。想起当初在印度的斋普尔买这块地毯时,挑挑拣拣了很久,店里的伙计有些跛脚,他一次次帮我调换,流着汗,从仓库搬出搬进,并无不耐烦的神情,直到我满意,他也开心地笑。只是没有月光,厚厚的云层挡住了月亮。想起母亲说过的谚语: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把这句话写在便签上了,贴墙上,留到正月十五,看看是否灵验。有一年应验了,只是正月十五下的不是雪,是雨。南昌少雪,我在南昌待了五年,只见过一次雪。
另一个秋天,我与李静和吴琼约着去了一趟武功山,去看芭茅草。我们露营、疯玩,也冻得发抖。那天碰巧是我的生日,吴琼记得,她心细,给我带了特别的月饼,盛在小盒子里,比生日蛋糕还精致。深夜,我们钻出帐篷,手拉手下到半山坡去上厕所;黎明,又一起上到山顶去等待日出。
在南昌的日子一直就这么过着,不加班的时候,熬一碗粥、熏一支香、斟一杯酒,洗洗衣裳浇浇花。滴水观音居然被我养得开了花,绿萝和吊兰依着卖花大姐的话,跟着我这个傻子也长得越来越旺了。它们的要求实在不高,不过是想起来的时候的一碗水。
有一些不好的消息传来,好在这些消息传到我这里的时候,最不好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它们正在朝着好的方向变化。李静做了一个手术,甲状腺方面的,她没让我知道,我知道的时候,她已经出院了。吴琼那段时间遭到恶人陷害,身体又出了一些状况。我打她的电话,一直是关机状态。随后我就不打了,我知道她需要安静。她正在一个漫漫黑夜中修补自己。天总有亮的时候。
闲暇时,我摆弄我的瓶瓶罐罐。在一个地方住久了就有了一些瓶瓶罐罐。有一个蓝色的小碗是我从土耳其带回来的,用来放珍珠胸针正好。小碗和胸针都挺便宜,都是在偏远地方的集市上淘来的,但都是我喜欢的物件,跟着我走了很远的路来到南昌。喜欢便是无价。还有一个盛着撒哈拉沙子的小瓶子,是好友从摩洛哥带回来送给我的。她常去摩洛哥,她沉迷那些蓝色小镇、黄色小镇、粉色小镇,哦,还有卡萨布兰卡,那里有一个经典的瑞克咖啡馆,咖啡馆里有永远不落幕的爱情故事。
有时候,我站在窗前往艾溪湖的对岸望,那里有一座高新区的地标性建筑,最高的第44层将是分公司的新办公室,但愿我在高处办公亦能看得更远。或许能看到火炬四路和京东大道交叉口那儿,新开的那家瓦罐汤店何时能有炖好的莲藕排骨汤。那家店的汤味道极好,尤其是莲藕排骨汤,好像也是限量版似的,总是不够多。我曾经给店小伙儿留下电话,说若是有了莲藕炖排骨汤就给我打电话。这个电话从来没有响过,人家生意忙得不得了,哪里还会记得一个常常喝不上汤的人在惦记着一罐莲藕排骨汤。
我的花花草草长势越发好了。滴水观音已经在开它的第三朵花,绿萝的藤蔓一直垂到了书架的底部,吊兰的枝条上也绽出许多小花。它们在挽留我么?它们是怎么察觉我想离开南昌的心思的呢?
等我终于有机会在我的小公寓里与李静、吴琼喝上一杯红酒的时候,我离开南昌的想法已经很坚定了。是我远方的儿子的一张照片促使我下定决心离开。我的少年背着鲜花走在奥克兰清晨的阳光下,他说能背着他的花花一直走下去该有多好。我的心突然就动了一下。一直走下去。是要一直走下去。
那天晚上,下着小雨,我拉开了窗帘,艾溪湖上的桥依然彩灯闪烁。三只高脚酒杯终于聚齐,宝石红的液体注入它们的腹中,像血液回归人体。大灯跳了好几次,灯管老化了,也或许是它太兴奋了,我的小公寓从来没有来过这么多人。
她们的身体都是刚刚康复,还有着静养后的虚胖。我们聊着一些琐琐碎碎,聊什么是生活,聊我们该过怎样的生活。我们心里都有一个模具,那个模具叫美好。我们把自己的日子放进这个模具里,卡进这个形状里,看看是否吻合。吻合了就叫美好,不吻合呢?更多的时候是不吻合的,但是我们依然过着自己的日子。
我说,琼,我把我的花花草草托付给你,你是它们的干妈了啊。琼就站起身,去看花盆的大小,说,嗯,得拿个大箱子来装。她还喜欢桌上花瓶里的几支干荷,李静也喜欢。那晚的干荷配这场没有菜的晚宴,实在是很协调。
后来我们又聊起了红酒,她俩本来就不擅饮,我说你们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别喝了,沾沾嘴巴就行。一瓶酒,打开了,只有我是真喝,便喝多了,有些醉意。
这是一款澳洲BIN407,清澈明艳的宝石红,略带淡紫色。是朋友送的,朋友说这款酒适合我。我在这个夜晚,饮完这瓶2012年的赤霞珠。口感厚实而完整,单宁稳定,回味绵长。当初朋友说这款酒适合我,是因为她知道我多年来过着无法定居的生活,而这款酒不必有太长的陈放期,新世界的酒大多适宜产后即饮,BIN407也不例外。日子在漂泊中匆匆,我换城市、换居所,而这款品性结实的酒,真的是最适合我的。品性结实,算是对漂泊的一种支撑吧。
有些人嗜酒是喜欢酒精的刺激,而有些人爱酒,却是除去乙醇和水,在极小的部分里品味丰富的层次和巨大的差异。这极小的部分只占酒体的百分之二,却富含酯类和醇类物质。这些物质,对该类酒的口感和香气有着最重要的影响。
这是我看过的关于酒的最精彩的一段话。
那极小的部分决定了酒的品质。
宛如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