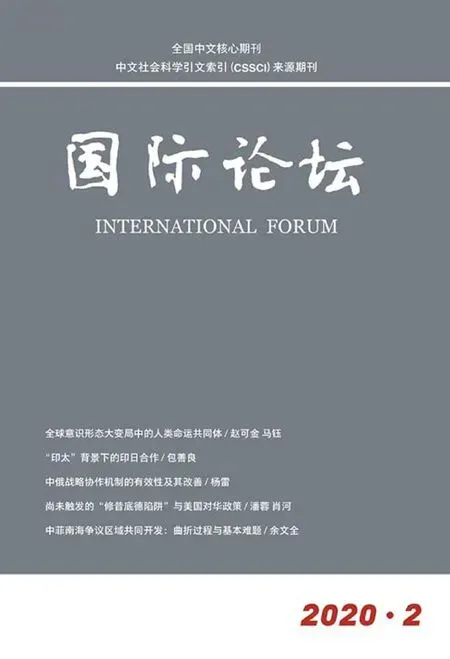中菲南海争议区域共同开发:曲折过程与基本难题*
余文全
【内容提要】共同开发是中国积极提倡并推动的为解决南海部分岛礁、海域的领土所有权、管辖权争议而选择的临时措施。其中,中菲在礼乐滩的共同开发合作最引人注目。本文在回顾了中菲并不顺利的共同开发历程后发现,共同开发争议区域的油气资源,是一个兼具经济、政治属性而非纯商业属性的合作行为。划定作业区域、管理共同开发、协商利益分配是共同开发面临的三个基本难题,而与之直接相关的议题分别是:领土所有权、管辖权、经济利益。在共同开发中,虽然经济利益赋予了中菲合作的物质基础,但领土所有权、管辖权矛盾却从根本上制约着共同开发的推进。三个基本难题相互独立却统一于共同开发之中,共同构成了共同开发的行为逻辑。每个难题所对应的议题都有其特定属性,对共同开发过程形成或制约或促进的不同作用。
中国积极推动的共同开发,是缓解南海声索国激烈争夺资源以及为最终解决领土争端创造条件的务实举措。但是,共同开发提出三十多年以来,并未在中国与其他南海声索国之间取得广泛的实质进展。比如,越南几乎没有表现出与中国共同开发的意愿,而马来西亚显示出了一定的合作意愿,但实际合作相当有限。不过,菲律宾与之不同,不仅态度积极,而且努力采取行动。由此,在南海争议区域共同开发整体情况不理想的背景下,尽管中菲共同开发进程并不顺利,但仍然备受关注。探讨中菲共同开发,不仅有助于厘清中菲共同开发的行为逻辑及困难,而且为理解中越、中马等声索国未在共同开发上取得突破,提供了有效的分析“棱镜”。
中菲已有两次并不成功的共同开发经历。既有研究对此的解释一般有:菲律宾国内法律的限制;①祁怀高:《当前中菲南海共同开发的制约瓶颈与应对思考》,《太平洋学报》2019年第 3 期,第 1—9 页。菲律宾国内反对派力量强大;②李忠林:《菲律宾杜特尔特政府的南海政策及前景》,《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6 期,第57—65 页。美国的干扰;③李金明:《中菲南海油气资源“共同开发”的可行性研究》,《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5 期,第72 页。菲律宾对中国的信任度不高。④洁来:《中菲成立南海油气合作委员会“共同开发”仍存四大障碍》,多维网,2019年8月31日,http://news.dwnews.com/global/news/2019-08-30/60147372.html。这些分析都将关注点聚焦在与共同开发密切相关的外部因素上,而非“共同开发”这一行为本身。中菲共同开发难以取得突破,不仅有上述客观的外部因素,而且有“共同开发”在实施过程中本身存在的难题。这种难题比外部因素对共同开发产生的作用更大,但往往容易被忽视。一般而言,争议区域共同开发面临三个基本难题。第一,在哪儿开发?第二,如何开发?第三,成本怎样担利润如何分?这三个基本难题对应的具体议题分别是:划定争议区域、管理共同开发、协商利益分配。每项议题在共同开发过程中都存在不同的困难。具体而言,争议区域领土所有权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造成共同开发的前提陷入两难境地;争议区域管辖权的排他性与共存性导致共同开发的管理矛盾重重;利益共享是共同开发的物质基础,但不是推动共同开发的决定性因素。
一、中菲南海共同开发的历程:“蜻蜓点水”式合作
共同开发(Joint Development)是两个及以上的国家在主张重叠的区域,为联合勘探或开发油气资源而达成的临时性政府间安排。这为领土争端国在彻底解决领土争议前进行划界问题谈判,创造了友好对话的氛围。①祁怀高等:《南海共同开发六国学者共同研究报告》,第3 页,http://www.iis.fudan.edu.cn/_upload/article/files/9f/21/992faf20465fae26c23ccce1ecc6/182e8776-45a6-4117-9906-b9797198a881.pdf。2017年7月,在中菲外长谈及南海共同开发时,菲律宾外长艾伦·彼得·卡耶塔诺(Alan Peter Cayetano)表示,早在1986年,邓小平和时任菲律宾副总统萨尔瓦多·劳雷尔(Salvafdor H.Laurel)就已对中菲南海共同开发作出了决定。但31年过去了,中菲仍未取得突破性进展,也未迈出实质性步伐。②袁梦晨、王羽:《中菲两国外长谈南海“共同开发”》,新华网,2017年7月25日,http://www.xinhuanet.com/2017-07/25/c_1121379270.htm。从邓小平提出“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至今,中菲已经有两次不成功的共同开发经历,目前正在努力推动第三次合作。
(一)半途而废的勘探前研究合作
2004年9月,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简称“中海油”,CNOOC)与菲律宾国家石油公司(PNOC)在北京签署《联合海洋勘探谅解备忘录》。时任菲律宾总统格洛丽亚·马卡帕加尔·阿罗约(Gloria Macapagal Arroyo)出席签字仪式。她表示,此项协议旨在研究中菲都宣称拥有主权的南海地区的石油潜力,是纯粹的收集、处理、分析地震数据工作,是勘探前的研究,不是钻探或开发。2005年3月,越南油气总公司加入合作,中、菲、越签署《在南海协议区三方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三方表示,协议表达了三方共同研究南海潜在石油资源的意愿,是勘探前的准备工作。《三方协议》合作期三年。2008年3月,菲方表示《三方协议》不符合菲律宾宪法,侵犯了菲国家主权,不再续签第二期合同。③李金明:《中菲南海油气资源“共同开发”的可行性研究》,《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5 期,第72—74 页。中菲第一次合作破产。
(二)不了了之的试探性合作
2011年中菲礼乐滩对峙后,菲律宾单方面开发礼乐滩受阻,遂寻求与中国合作。2012年5月,菲律宾菲利克斯矿业公司(Philex Mining Corporation)董事长彭泽仁来华,寻求与“中海油”在礼乐滩联合开发油气。有媒体问彭泽仁,在礼乐滩地区,中国侵犯了菲律宾“领土”,菲利克斯公司是否还愿意与中国企业合作。彭泽仁表示,菲利克斯公司应当同中国企业对话,这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案。④周旭:《菲公司寻求同中企合作,共同开发礼乐滩资源》,环球网,2012年5月8日,http://mil.huanqiu.com/observation/2012-05/2698776.html?agt=15425。5月7日,菲利克斯董事长邦义礼南(Pangilinan)向贝尼尼奥·阿基诺三世(Benigno Aquino III)提交一份报告,介绍了中菲关于南海油气合作的会谈情况,称中方积极看待菲方提出的建议。阿基诺指出,礼乐滩是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协议必须符合菲律宾法律。后来,菲律宾政府要求在合作协议中加入“开垦条款”,即中方承认菲方为开发区域的所有者,中国拒绝接受,中菲第二次合作再次搁浅。
(三)小心翼翼的联合勘探合作
2016年罗德里戈·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执政后,中菲关系得以改善,两国共同开发南海油气再次提上日程。2017年1月,中菲建立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BCM),重申以和平方式解决领土和管辖权争议。①千帆:《中菲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启动》,中国青年网,2017年5月20日,http://news.youth.cn/jsxw/201705/t20170520_9823113.htm。2018年2月,中菲召开BCM第二次会议。针对涉及主权争议的海域,两国探讨了联合勘探油气与开发合作。同年10月,BCM 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在不影响两国各自关于主权、主权权利、管辖权立场的前提下,双方探讨了海上油气联合勘探与开发合作。11月20日,习近平主席对菲律宾进行国事访问,中菲签署《关于油气开发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2019年8月,杜特尔特访华。根据之前签署的文件,中菲成立“油气合作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和“企业间工作组”,以推动共同开发取得实质性进展。菲律宾驻华大使乔斯·罗马纳(Jose Romana)表示,“工作组”由参与合作的两国公司高管组成,“委员会”由两国外交部、能源部门的官员组成。根据合作协议,菲中油气分配方案为60 : 40,即菲方占六成,中方占四成。罗马纳强调,合作目标是达成一个商业协议,②“China,PH to Form Committees for Joint Gas Exploration Talks,”ABS-CBN News,Aug 30,2019,https://news.abs-cbn.com/business/08/30/19/china-ph-to-form-committees-for-joint-gas-exploration-talks.利益分享方案有利于菲律宾,但这只是显示出中国政府愿意“灵活”,不意味着中国默许菲律宾在南海的权利,因为联合勘探必须符合两国的法律。③《菲中成立“委员会”和“工作组”推动油气共同开发取得实质进展》,菲律宾世界日报网,2019年8月30日,https://worldnews.net.ph/post/105436。
二、共同开发的两难前提:争议区域所有权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启动共同开发的前提是确定作业区域,但在争议区域,当事国对此却很难达成一致。确定作业区域必先划定争议区域。这意味着当事国对主张重叠的海域,在其主权归属未得到解决前,要先承认的确存在主权归属争议,也就是争议海域的领土所有权是不确定的。在现实中,当事国往往将本国主张的海域视为非争议区,即便声索的海域存在重叠,也坚持本国才是声索区域的主权拥有者。
(一)共同开发的前提:划定争议区域
为解决南海主权和管辖权争议,中国提出在争议海域共同开发的倡议。在考察共同开发前,先了解其具体含义。根据邓小平在1986、1988年先后对菲律宾副总统劳雷尔和总统阿基诺(Aquino)阐述的共同开发主张,可以明确其基本含义:第一,主权属我;第二,搁置争议,是在不具备彻底解决领土争议的条件下,暂时不谈主权归属,而不是放弃主权要求;第三,在有争议的区域共同开发,其目的是通过合作增进相互了解,为最终合理解决主权的归属问题创造条件。①《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外交部网站,2000年11月7日,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 674904/wjs_674919/2159_674923/t8958.shtml。
可以看出,中菲在争议海域共同开发油气,实际上是为两国最终解决争议海域的主权归属创造条件。似乎共同开发与主权归属,不仅敏感度不同,而且还能相互独立。实际上,二者只是表面上敏感程度不同、相互独立。2012年中菲尝试在礼乐滩合作,菲律宾加入“开垦协议”最终致使合作失败。看起来是“开垦协议”这一偶然因素导致中菲共同开发破产,实际上反映了共同开发过程中隐含的深层合作困难。领土争端国要想通过共同开发争议区域的资源,缓解处理争端的对抗性,并为最终解决主权归属创造条件,承认声索区域存在争议是不可避免的前提。中国对此释放了极大善意,但菲律宾坚持认为,本来存在争议的区域却属于菲律宾无争议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②雷筱璐:《仲裁案后中菲海上油气合作主要障碍的国际法分析》,《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8年第5 期,第99 页。这就造成中菲不能明确划定共同开发的区域。由此为共同开发带来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不清楚在哪儿共同开发。
包括中菲在内的其他南海声索国,在共同开发上存在一种倾向:虽然声索区域大量重叠,但都不认为自己的声索区域属于争议区域,共同开发只能在他国的声索区域而不能在本国的声索区域进行。③许浩:《南海油气资源“共同开发”的现实困境与博弈破解》,《东南亚研究》2014年第4 期,第21 页。而且,南海周边国家在实际侵占中国南海岛礁基础上进行资源开发,试图造成实际占有、管理的假象,④李毅:《领土主权取得的“历史性巩固”理论评析》,《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12 期,第11 页。加剧了声索国不愿承认主张重叠的海域为争议区域的倾向。就像阿基诺在中菲礼乐滩对峙后所叫嚣的那样:菲律宾对勒道滩(礼乐滩)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这个地区就像马尼拉的勒道大街一样,是菲律宾的。①李金明:《菲律宾将南海争议提交国际仲裁——一场大国代理人的战争》,《新东方》2014年第1期,第20 页。即便是积极改善中菲关系的杜特尔特,在涉及对争议区域的表态时,也是闪烁其词。当杜特尔特政府被问及中菲共同开发的区块在哪里,其发言人罗克(Roque)表示,有两个区块可供选择,SC57 在“九段线”外,SC72 位于面积为88 万公顷的礼乐滩,在“九段线”内,(但)两个区块都在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内。②Enrico de la Cruz,“Philippines Earmarks Two Sites for Possible Joint Oil Exploration with China,”Reuters,March 2,2018,https:/ / uk.reuters.com/ article/ philippines-china-southchinasea-energy/ phil⁃ ippines-earmarks-two-sites-for-possible-joint-oil-exploration-with -china-idUKL4N1QK4CW.
承认争议海域存在争议是争端国实现共同开发的前提。这首先需要争端国就选择共同开发区块达成一致。但中菲在区块选择上没有形成共识。SC57 相对容易推进开发,但该区块在“九段线”外,不是争议区域的共同开发。SC72 完全在“九段线”内,属于争议区。但中菲对“共同开发”的理解又不一样。中国提倡的共同开发(Joint Development),包括确认争议海域和开发资源;菲律宾认为共同开发(Joint Exploration)是通过联合勘探而非开发以加强务实合作,没有确认争议区域的明显意愿。③康霖、罗传钰:《中菲南海油气资源共同开发:挑战与努力方向》,《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5期,第120 页。由此,位于争议区域的SC72 区块,菲律宾强调的是勘探而非开发,无争议的SC57 才可以共同开发。但是,要真正实现共同开发,争端国必须首先承认,某一海域存在划界争议或某一岛礁存在主权归属争议。④丁洁琼、张丽娜:《南海油气资源共同开发“区块”选择探究》,《中国海商法研究》2015年第2期,第49—50 页。
(二)中菲划定争议区域的两难
推动争议海域共同开发必须首先划定争议区域,争端国并非不明白这一点。争端国之所以很难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以中菲为例,一是两国权利主张的依据不同,造成争议海域的法律性质模糊;二是都担心在确认争议区域过程中,将本该属于自己独享的部分划为了共享区域。
第一,争议区域法律性质模糊。
南海其他争议区域共同开发的成功案例有一个特点:争议海域的法律性质明确。例如,马来西亚和泰国在泰国湾海域存在争议,但两国成功进行了共同开发。这是因为两国的海上争议明确集中在大陆架划界上,争议区域相对容易确定。反观中菲,情况就复杂得多。首先,中国援引历史性权利(historic rights)对整个“九段线”范围内的海域、海床、底土提出主权和管辖权主张。但是,中国没有明确指出享有权利的具体范围。而且,“九段线”的法律性质到底是什么,是“历史性水域”“海上疆域线”,还是“岛屿归属线”?目前没有明确的解释。①李金明:《中国南海疆域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21—238 页。其次,菲律宾等国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南海主张200 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权利。菲律宾认为,中国援引的历史性权利与《公约》相违背,中国在“九段线”内的权利主张也超过了《公约》允许的范围,因此,历史性权利和“九段线”不具有法律效力。②王军敏:《从历史性所有权争端解决制度看仲裁庭对中菲南海争端的管辖权》,《法治研究》2018年第3 期,第130—132 页。如此,虽然南海各争端方的权利主张区域大量重叠交错,但都不愿意承认主张重叠的区域是争议区域。在这种情况下,争议区域的划定非常困难,而选择共同开发区块、实际推动共同开发自然也非常困难。③张丽娜:《南海争议海域油气资源共同开发的困境与出路》,《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 期,第14 页。
第二,领土所有权的确定性与争议区域领土所有权的不确定性。
任何领土和海洋争端,都集中在谁拥有某片有争议的地物及其周围海域这一关键问题上,南海争端也不例外。④Zou KeYuan,“South China Sea Studies in China: Achievements,Constraints and Prospects,”Singapore Year 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Vol.11,2007,p.87.在南海问题上,一般还可以把争端进一步分为两个独立问题:谁拥有相关水域的地物(所有权),谁有权为某种目的而使用该水域(管辖权)。⑤Richard Turcsányi,“The Long Term Perspective of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Policy Paper,2013,p.1.在领土争端中,领土所有权(territorial ownership)比管辖权具有更深刻的矛盾,因为管辖权建立在所有权基础上。中菲共同开发难以取得实质成效,与领土所有权矛盾尖锐密不可分。菲律宾一直把南海争议海域当作自己的专属经济区,是属于菲律宾的“领土”。例如,菲律宾前外长艾伯特·德尔·罗萨里奥(Albert del Rosario)在与中国前驻菲大使王英凡谈论礼乐滩共同开发事宜时表示,菲律宾愿意邀请中国投资者到礼乐滩投资,但前提是中国必须遵守菲律宾法律。罗萨里奥进一步指出,因为礼乐滩是菲律宾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不能被共同开发。①李金明:《中菲南海油气资源“共同开发”的可行性研究》,《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5 期,第77 页。
所有权通常意味着确定性和排他性。在领土争端中这一点体现得尤为明显。领土所有权赋予了某个国家为某一地物的明确拥有者。但在争议海域的共同开发实践中,争端国开展共同开发,意味着领土归属争议在彻底解决前,双方共同拥有争议区域的资源、共同享有争议区域的权利,比如勘探和开采。②Jay Batongbacal,“Philippine-China Joint Development Talks Still at an Impasse,Despite Green Light,”April 13,2018,the Asia Maritime Transparency Initiative,https: // amti.csis.org /philippine-chinajoint-development-impasse/.这就让争议区域的领土所有权具有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也就是说,“共同拥有”本身就与所有权的确定性、排他性相悖。当前中菲正在努力推动共同开发,但仍然没有明确开发的具体区域。中菲将这一任务交由共同开发指导委员会负责协商,并且,两国政府的外交、能源部门高级官员担任联合主席。有观点认为,共同开发的具体位置能在不久的将来划定。③康霖、曹群:《中菲达成南海油气资源共同开发新共识》,《世界知识》2019年第2 期,第31 页。
本文不讨论中菲何时能在划定开发区域上达成共识,而是指出在争议区域明确开发位置,其困难不仅有“法律性质模糊”这一点,而且有所有权的属性难题。划定争议区域涉及的深层议题是,争端方就争议区域的归属要作出明确判断,什么地方归你什么地方归我,必须弄清楚。所有权的这种排他性让共同开发陷入两难:争端国开展共同开发是为了最终解决争议区域的所有权问题,但实际启动共同开发的前提却是,争议区域的所有权需要提前明确。这就像一个“死结”。比如,菲律宾总想着在无争议区域共同开发,而在有争议区域进行有限的联合勘探。为什么这样?因为菲律宾不想在争议区域把认为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割让”出去而使其变为“公共区域”。
由此可知,如果争端国试图利用共同开发争议区域的资源,为解决争议区域的最终归属创造条件,其成效是有限的。这里的成效有限,不是指共同开发这一行为本身不足取,而是指共同开发间接涉及领土主权归属议题,不宜将共同开发视为纯粹的经济行为。因为共同开发争议区域的资源,是经济属性明显但暗含政治属性的复合议题。而且,实际开发常常因其暗含的政治属性而受阻。
目前,中菲关系处于提升期,双方正在努力推动共同开发。在喜见中菲南海合作势头良好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对此保持冷静,不宜对共同开发的前景抱以过高期待,更不宜在未厘清制约共同开发的因素前,就盲目评价共同开发对解决领土争端的积极作用。从中菲南海问题双边磋商和发布的声明文件可以看到,中菲在推动共同开发时,有意避开了共同开发涉及的政治议题。例如,在《中菲关于油气开发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的“有关立场”中,双方这样表述:本谅解备忘录以及双方或双方企业,根据该备忘录进行的所有讨论、谈判和活动都不影响双方各自法律立场。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菲律宾共和国政府关于油气开发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外交部网站,2018年11月27日,https://www.fmprc.gov.cn/nanhai/chn/zcfg/t1616639.htm。在已举行的中菲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会议上,中菲都对油气联合勘探和开发合作作出如下限定:有关合作以不影响两国各自关于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立场为前提。这些限制性的声明,试图将涉及共同开发的争议区域的主权归属、管辖权等政治议题“排除”,以减少影响共同开发的“干扰因素”。
当然,在趁中菲关系提升时顺势推动共同开发的初期,为减少阻力,有意避开共同开发内含的政治议题是可取的。不过,在具体商讨共同开发的细节中,像划定争议区域、明确共同开发区块等议题,就不能不谈。因为这些议题是中菲南海共同开发绕不开的关卡。只有通关了,共同开发才会有实质性进展,共同开发对解决领土争议的促进作用才可能真正发挥出来。
三、共同开发的管理困境:争议区域管辖权的排他与共存
“在哪儿开发”是中菲共同开发必须面对的第一道难关,而“如何开发”即共同开发的管理问题,是中菲不得不面对的第二道难关。开发管理一般涉及开发主体、开发模式、资源管理等具体议题,而这每一项都与中菲各自的国内管辖权息息相关。换言之,共同开发的管理问题是“表”,管辖权是“里”。
(一)共同开发中的管理模式与管辖权
关于争议海域油气共同开发的管理模式,不同学者看法并不一致。有的学者认为有三种模式:联合经营、代理制、超国家管理。②安应民:《论南海争议区域油气资源共同开发的模式选择》,《当代亚太》2011年第6 期,第133—134 页。也有学者认为,根据开发主体在共同开发中发挥的主导作用,可以把开发模式划分为共同机构主导模式、石油公司主导模式。③何海榕:《马泰与马越共同开发案的比较研究》,《太平洋学报》2015年第 12 期,第89—90 页。本文无意对共同开发模式进行分类,而是强调,不论依据什么标准,争议区域的共同开发模式都有一个共同点:开发主体基于授权,代理行使缔约国的权利,开发主体受到授权国政府的监督、管理。其实,共同开发模式的关键,不在于开发主体是谁或者选择何种具体管理模式,而在于当事国政府能授予开发主体何种权利。实际上,开发主体(石油公司、机构等)既是负责开发工作的管理者,又是被授权国政府监督、管理的被管理者。开发主体在共同开发工作中的权限源于当事国的授予,但当事国向开发主体到底授予何种权限,又受制于其国内法律的规定。
中菲在共同开发中就明显受到这一点的影响。根据菲律宾国内法律规定,开发主体作为国家资源勘探、开发的代理人,不能获得等于或大于其委托人的任何权利。即使开发主体是100%的外资实体,并且有权做出有关经营和管理的所有决定,但该开发主体最终仍然要受到菲律宾政府的完全控制和监督,即菲律宾对共同开发享有专属管辖权(Exclusive Jurisdiction)。①Jay Batongbacal,“Philippine-China Joint Development Talks Still at an Impasse,Despite Green Light,”the Asia Maritime Transparency Initiative,April 13,2018,https://amti.csis.org/philippine-chinajoint-development-impasse/.显然,如果中菲企业在争议区域共同开发,那么中国对此是不能接受的。在中国政府颁布的《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中,第一章第二条明确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海、领海、大陆架以及其他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资源管辖海域的石油资源,都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所有。在前款海域内,为开采石油而设置的建筑物、构筑物、作业船舶,以及相应的陆岸油(气)集输终端和基地,都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第一章第三条这样规定: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的一切活动,都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法令和国家的有关规定;参与实施石油作业的企业和个人,都应当受中国法律的约束,接受中国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的检查、监督。②《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的决定》,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11年10月10日,http://www.gov.cn/flfg/2011-10/10/content_1965948.htm。从中菲关于油气开采的法律规定可知,两国都以维护本国的主权为前提,都欲对开采活动实施专属管辖。
(二)共同开发的管理困境:管辖权的排他与共存
实际上,海洋管辖权是国际法赋予主权国家的一项基本权利,国家享有对其所辖海域内的一切人(享有豁免权者除外)、物、事件行使管理和处置的权力。国家对海洋管辖权的行使体现在海洋立法权、执法权、司法权等方面。在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沿海国对自然资源的勘探、开发享有专属管辖权。①高智华:《论实施国家海洋管辖权的若干国际法问题》,《东南学术》2009年第3 期,第94—95 页。
纵观中菲第一次、第二次不成功的合作经历,管辖权矛盾十分突出。2008年,菲律宾议会认为《三方协议》违反了菲律宾1987年《宪法》关于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条款,最终导致合作终止。2012年,菲律宾要求中菲在礼乐滩合作时,中国必须遵守菲律宾法律,承认礼乐滩为菲律宾所有,中国拒绝此要求,第二次合作再次宣告失败。2018年,菲律宾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尼奥·加彪(Antonio Carpio)表示,他不反对中菲共同勘探西菲律宾海,只要联合勘探符合菲律宾宪法。不过,菲律宾《宪法》第12 条第二节规定,国家政府全权控制及管理自然资源的勘探、开发及利用,但允许菲律宾公民或菲律宾人与拥有至少60%股权的公司签订共同生产、合资或生产共享协议。②《加彪不反对菲中共同勘探南海》,菲信网,2018年8月3日,http://www.feixinph.com/local/6354.html。加彪的言外之意是,虽然他不再强力反对中菲共同勘探,但中菲共同开发要受到菲律宾宪法的严格限制。
虽然当前中菲在共同开发上呈现良好势头,但管辖权矛盾并未减弱。只是中菲在小心避开管辖权矛盾。比如,在多次中菲外长会议上,两国反复强调:共同开发不影响也不涉及各自的法律体系。由于认识到伴随而来的政治和法律风险,大多数共同开发协议都使用标准条款,称此类临时的实际行动不会损害或影响缔约方的主张或立场。③Lucio Blanco Pitlo III,“Joint Development in the‘West Philippine Sea’Analysis,”Eurasia Review,21 March 2018,https://www.eurasiareview.com/21032018-joint-development-in-the-west-philippine-seaanalysis/.
但是,中菲在争议区域的共同开发必须要面对管辖权难题,因为这涉及共同开发的管理问题。具体来说,开发主体的选择、开发主体的权利、国家与开发主体的关系、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等具体议题,都牵涉到中菲各自的国内法律体系。而中菲相关的国内法律,又直接关系到两国怎样对共同开发进行管理。简言之,中菲向开发主体(如石油公司)授予何种权利,是管理共同开发的关键。但从中菲关于合作开发油气的相关法律看,双方在授权问题上要达成一致并不容易。例如,菲律宾法律规定,菲政府全权控制、管理自然资源的勘探、开发和利用,对开发主体实施全面控制和监督;相应地,中国法律规定,合作开采油气资源的一切活动,应遵守中国的法律、法令、法规,开发主体应受到中国法律约束,接受中国政府的检查、监督。仅从海洋立法管辖上看,中菲双方的法律都体现出本国应行使专属管辖权。这意味着,中菲在对争议区域的管辖上本质是相互排斥的,但两国在管理油气开发活动时,又需要双方的管辖权形成交集、实现共存。
现实中,管辖权矛盾先于共同开发而存在。不过,共同开发却不能脱离管辖权问题而单独进行。如果是在非争议海域共同开发,那么管辖权只属于资源所有国,此时的开发主体只需遵守授权国的法律规定即可。但在争议区域,管辖权是重叠、冲突的,开发主体到底该适用谁的法律、受谁的管辖,并不清楚。虽然涉及争议的每一方都声称自己拥有管辖权,但这实际上是加剧了管辖权矛盾而非使管辖权更清楚。如此一来,在“如何开发”这一基本问题上,共同开发缺乏可操作的管理条件。
(三)管理共同开发中的管辖权矛盾难以协调
争议海域的共同开发难以推进,一个关键原因是,当事国之间管辖权矛盾大。管辖权属于政治议题,与带有明显经济属性的共同开发似乎是分开的。事实上,在涉及当事国管理共同开发过程中,管辖权问题会自然而然地渗透进来并制约开发行为。这种制约作用的存在有两方面原因:管辖权的排他性、协商共同开发的管理问题是事后调适。
第一,管辖权具有排他性。
管辖权在法学界没有统一的定义,但学界对管辖权的功能却有一致的认识。在主权国家时代,管辖权是国家主权的中心要素,它反映了国家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部管辖事务的原则。在国际关系中,管辖权象征着国家主权,决定着国家主权的权力边界与范围。①宋杰:《我国刑事管辖权规定的反思与重构——从国际关系中管辖权的功能出发》,《法商研究》2015年第4 期,第150 页。由于管辖权划定了国家权力行使的界限,因此,管辖权意味着主权国家行使权力的范围、对象都是清楚、确定的。如果在同一区域,存在不同国家都欲行使管辖权的现象,就会造成每个当事国的权力边界都模糊不清。于是,国家间的管辖权矛盾就产生了。
例如,中菲都对礼乐滩提出主权声索,双方都坚持本国有权管辖礼乐滩。这不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的主权宣示,而是两国都会从国内立法、执法等层面去行使管辖权。在这种情形下,共同开发就面临着严重的管理矛盾。诸如开发主体、资源利用、合作方式等问题,都受到各自国内法律体系的约束,而双方为实现有效管辖,都各自在立法、执法、司法等领域确立了以维护本国主权、利益为目标的标准和界限。如此,共同开发在启动之前,就已受到各当事国管辖权排他性、利己性的限制。
第二,协商共同开发的管理矛盾是事后调适。
管理共同开发的矛盾先于共同开发而存在,此时,当事国遇到的管理矛盾只是已存在的管辖权冲突的表征。国家在行使立法管辖权、执法管辖权的时候,优先考虑的是维护本国的主权、利益,不同国家(比如中菲)管辖权的行使不会自然适配对方,管辖权不会出现天然和谐的局面。所以,当事国一开启共同开发的“阀门”,管辖权矛盾就会乘虚而入。如果当事国要继续推动共同开发,就不得不针对已存在的管辖权冲突进行协调。但是,这种协调是小心谨慎且幅度很小的。由于管辖权是政治敏感议题,各当事国决策者都会因顾忌国内、国际等压力而束手束脚。当事国原本试图以共同开发为手段,逐步推动争议区域管辖权矛盾的解决,但现实却是,共同开发受到争端国管辖权矛盾的严重束缚,本身就难以“大展拳脚”,更不用说以此推动解决争议区域的管辖权矛盾。
在国际上,共同开发油气资源是一项商业行为,实质上是授权国与某一开发主体进行的交易,此时的共同开发管理问题容易处理。但是,争议区域的共同开发不能简单地当作纯商业行为,它是政治、经济等交织的复合议题。如果把非争议区域共同开发具备的经济属性“复制”到争议区域的共同开发中,认为以此就能推动争议区域政治议题如管辖权矛盾的解决,就忽略了共同开发在不同情境中具有不同属性的实情。非争议区域的共同开发只需“在商言商”,而在争议区域的共同开发,却需要“在商先言政”。中菲争议区域共同开发亦是如此。如果争议区域划定后,制约共同开发的管辖权问题应在实际开发之前就予以协商,而不是等共同开发受阻后再去试着协调管辖权矛盾。
四、共同开发的脆弱基础:共享利益的非决定作用
利益共享是声索国在争议区域共同开发油气的物质基础。油气作为战略性资源,对国家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国防巩固等都极为重要。然而,声索国让争议海域的油气发挥其战略价值并非易事。声索国对待争议区域的油气有以下几种策略:不开发、单方面开发、与其他声索国共同开发。①Emily Meierding,“Joint Developmen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Exploring the Prospects of Oil and Gas Cooperation between Rivals,”Energy Research & Social Science,Vol.2,2017,p.66.“不开发”,如果不是受到资金、技术的限制而做出的无奈之举,就是该国决策者太超脱。“单方面开发”,虽然一国可能获得更大的开采量,但很容易招致其他声索国的反对,风险极高。很显然,对一个国家来说,前两种方式都不是最有利的。相较之下,“共同开发”是声索国之间分享资源,各方可分得的“蛋糕”总量比单独开发要小,可经过协商达成一致的开采模式,各方权责分明、利益分配有章可循,开采过程面临的政治、军事风险小。不过,利益共享仅仅是共同开发的必要条件,具备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当事国可以克服其他制约因素而成功实现共同开发。
(一)中菲具有共同开发的物质利益基础
如果不涉及领土争端,油气开发是一项经济活动,属于纯商业范畴。缔约各方按照协议,承担相应成本,分享约定比例的利润。如果涉及领土争端,虽然油气开发内含着政治属性,但其经济属性的一面仍然存在。声索国之间通过签订合作协议,可以开展风险共担、利润共享的合作。2019年8月杜特尔特访华,他表示最感兴趣的议题是菲中在西菲律宾海联合勘探石油。按照中方提议,中菲联合开发的股权分配方案是40 : 60,中方企业占40%,菲方企业占60%。杜特尔特认为,这个分配方案没有问题。总统发言人萨尔瓦多·班尼洛(Salvador Panelo)表示,中菲联合开发油气,可以作为解决两国领土争端的谈判筹码,而且,两国都可以受益,达到双赢局面。②《府:油气协议可作谈判筹码》,菲律宾世界日报网,2019年8月12日,https://worldnews.net.ph/post/104422。
目前,中菲在共同开发上取得一定进展。一些分析者从物质利益层面,对中菲油气开发合作乃至解决领土争议持乐观看法。
首先,菲律宾油气资源短缺,需要寻找新的来源。菲律宾是“东盟”内石油进口率最高的国家。据统计,菲律宾一天的原油消耗量是43.4 万桶,而菲律宾国内只能生产其6%,剩余的全部依赖进口。③许利平:《中菲油气合作为南海树立新典范》,环球网,2019年8月31日,https://www.toutiao.com/a6731110138335199751。到2030年,菲律宾高达30%的电力需求,只能由一个单一的石油平台供应。①Chris Schnabel,“Malampaya Kicks off Gas Production from New Platform,”Rappler,October 5,2015,https://www.rappler.com/business/industries/173-power-and-energy/108205-malampaya-new-offshoreplatform.这些问题迫使菲律宾要么寻找其他替代能源,要么与中国达成协议。②Jay Batongbacal,“Philippine-China Joint Development Talks Still at an Impasse,Despite Green Light,”the Asia Maritime Transparency Initiative,April 13,2018,https://amti.csis.org/philippine-chinajoint-development-impasse/.对菲律宾而言,从财政或资源环境看,弥补国内电力短缺的替代能源很少,而进口液化天然气、建燃煤电厂或核电厂又成本太高,财政难以承担。所以,当中菲两国的能源公司联合采油时,虽然菲律宾无法获得像执行仲裁裁决那样100%的收益,但从商业角度来看,50%总比0%强。如果菲律宾拒绝与中国接触,并推迟勘探南中国海的碳氢化合物资源潜力,它就什么都得不到。③Carlos Santamaria,“Sino-Philippine Joint Developmen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s Political Will Enough?”Asian Politics & Policy,Vol.10,No.2,2018,p.338.
其次,中国具备采油所需的资金、技术条件。海上采油是一项高风险、高技术、高投入的产业。例如,勘探一个中小型油田,仅前期勘探费用一般就高达数千万或上亿元。④李国强:《南海油气资源勘探开发的政策调适》,《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 6 期,第109 页。在南海开采油气,菲律宾没有雄厚的财力支撑,而中国却有能力进行大笔投资。在技术层面,随着2012年中国“蛟龙号”深海载人潜水器下潜深度达7029 米,标志着中国具备了在全球99.8%以上的深海作业的能力。因此,中国在资金雄厚、技术先进的基础上与菲律宾共同开发南海,而且让利菲律宾,意在为未来南海领土争端解决铺垫一种超越主权的方案,这将不同于现有的领土争端解决模式。⑤陆莲:《南海开发菲律宾占六中国占四 习近平通过让利获得什么》,多维网,2019年8月31日,http://news.dwnews.com/global/news/2019-08-30/60147383.html。
(二)利益共享是共同开发的基础却非决定性因素
憧憬中菲共同开发的光明前途并无不可,但分析逻辑不能太跳跃。中菲只要在共同开发中具备了利益共享的物质基础,就真能推动中菲实现共同开发,甚至为解决领土争端开创新模式吗?事实上,利益共享只是中菲乃至任何国家之间进行合作的基础,没有利益,国家当然缺乏合作动机。但是,有利可图只是国际合作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为利益基础与合作行为往往受到其他因素的干预。中菲争议区域共同开发就受到争议区域的所有权和管辖权矛盾的制约。换句话说,中菲争议区域的共同开发不是简单的经济行为,经济利益只是共同开发的合作起点。尽管这种物质利益是合作基础,却非推动共同开发的决定性因素。有观点认为,中菲共同开发可以借鉴功能主义思想,先从低敏感议题领域如海洋环境考察、油气储量探测、油污预防和处理等展开合作,循序渐进,再转向高敏感议题如海洋划界合作。如此,中菲可通过共同开发解决南海资源管辖争端。①祁怀高:《欧洲煤钢联营经验对南海共同开发的启示》,《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10 期,第70—71 页。
从直觉上判断,中菲共同开发具有利益共享的物质基础,好像只要这一基础存在,由低敏感议题到高敏感议题顺势而为,就能取得突破。但是,中菲共同开发是一个政治、经济交叠的复合议题,不是单一的经济议题,用经济利益去考察共同开发的可行性,混淆了非争议和争议区域两种情境下共同开发的区别。而且,低敏感议题领域的合作,虽然有助于密切中菲海上联系,但这种合作并不涉及划定争议区域、明确管辖权等实质难题,即便合作再多,也不会触及核心问题,反而会让真正对共同开发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因敏感而被搁置。久而久之,可能随着其他与共同开发无关的海上合作的增多,呈现出中菲两国南海合作的“虚假繁荣”,让人误以为这种合作状态已经具备解决争议区域共同开发难题的条件。尽管功能主义合作对中菲关系有利,可对解决争议区域共同开发存在的难题而言,只能算是打“擦边球”,其作用相当有限。
低敏感议题领域的成功合作很难“外溢”到高敏感议题领域。不同议题之间不仅有领域之别,更有特定的属性之分。像划定争议区域、明确管辖权这些高敏感议题,具有明显的排他性。而海洋环境保护、测气储量探测等低敏感议题具有共存性,加深这类议题的合作,虽然便于中菲提升关系,但这种合作只限于共存性的议题领域,难以将合作功效外溢到排他性议题领域。不同议题的属性界限分明,而且,往往是高敏感的排他性议题对低敏感的共存性议题影响更大,而不是相反。不过,中菲扩大其他低敏感议题领域的合作,以及利用共同开发的利益基础推动合作,这些努力本身就有价值。因为这既可以增加两国的海上联系,为处理南海争端创造更多协商、沟通的机会,又有助于降低两国处理资源矛盾时的对抗性。
五、结 论
通过分析中菲三次南海共同开发经历可知,争议区域的共同开发存在基本的行为逻辑和制约因素。首先,在哪儿开发。这是共同开发的前提。只有明确了共同开发的具体位置,作业和管理才能实际运行。但是,划定作业区域却困难重重。在主张重叠的区域,中菲都坚持认为该区域属于自己,也就是本国拥有该区域的领土所有权。一旦需要在主张重叠的区域划分出争议区域以便确定共同开发的作业位置,双方难免产生将本属于自己的领土“割让”出去共享的损失感。由此,中菲都把划定争议区域视为高度敏感的政治议题而选择回避,导致关于共同开发的作业区域的具体谈判、协商停滞不前。
其次,怎样开发。这包括选择开发主体、确定合作模式、协商资源利用等一系列具体议题。表面上看这是共同开发的管理问题,实际上直接关系到两国的管辖权。例如,海洋立法、执法管辖权等。由于中菲各自关于海洋管辖的立法、执法、司法等内容,都以优先服务于本国的主权、主权利益等为目的,因此,双方在海洋管辖上不会形成自然和谐的局面。而且,管辖权矛盾先于共同开发而存在,所以,双方遇到的管理共同开发的矛盾,其实是管辖权冲突的延续。虽然管理问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协商,但这对缓解深层的管辖权冲突的作用很有限。因为中菲各自的法律体系、执法章程等内容,不会因协调共同开发中的管理矛盾而得以大幅度调整。
最后,利益共享。这是中菲在南海争议区域推动共同开发的物质基础。正因为共同开发具有经济属性,产生的利益可以按照商业原则进行分配,所以不少分析者对当前中菲共同开发持乐观看法,并认为共同开发可以为中菲领土争端的解决开辟新思路。诚然,共同开发的商业性质的确为中菲合作赋予了物质基础。但是,中菲在争议海域进行的共同开发,是经济与政治交织的复合议题,不是单纯的经济议题,不能与非争议海域的共同开发相混淆。虽然利益共享为中菲共同开发注入了物质利益动力,但这并不足以推动中菲越过领土所有权、管辖权给共同开发制造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