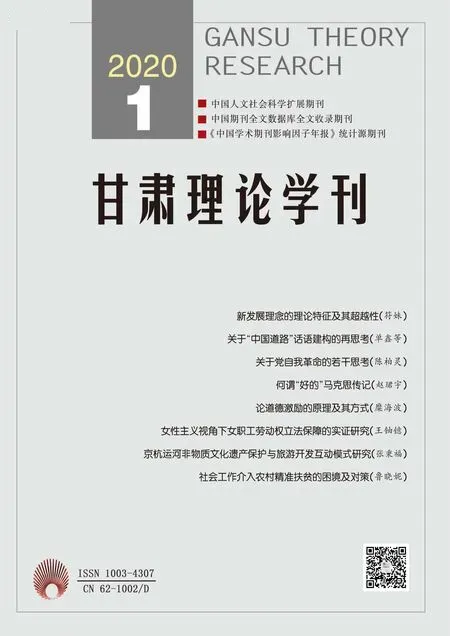《墨子》德性教育思想的内涵与价值取向
张晓立
(山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济南 250014)
一、《墨子》德性教育的思想背景
要探讨《墨子》的教育思想,就需要理解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在战国时代纷扰的社会变动中,先秦诸子均提了自己的教育主张,以解决当时的政治文化等问题。虽然诸子的教育主张不同,但所面临的问题相同,在构建基本的教育理论中存在内在的一致性。
(一)先秦诸子思想的教育主题
先秦诸子所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终结政治秩序崩坏多元价值并存的乱世。面对当时复杂的价值选择,先秦诸子根据所处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提出不同的社会政治理想以及解决方案。孔子所代表的儒家依靠个人主体性道德的完善来维持家国秩序的稳定与和谐,使自周代以来所建立的礼乐文明制度重新获得实现。而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则是从自然主义出发,强调个人的价值实现与美好生活并不依赖于政治秩序,只有构建宽松而又自然的政治环境,不伤害个人生活的独立与自适,才能够保障个人生存的真正实现。墨子所代表的墨家则是从社会交往的现实角度出发,依靠功利主义的价值考量,强调个人生存实现依赖于整个社会共同体的利益实现。这就要求以整个社会的共同利益为价值基础,建立社会共同的价值目标与共同的道德标准,从而实现社会交往的可能,最终达到整体社会“兼爱”的政治理想。而韩非所代表的法家则是从对社会发展的历史性思考上,强调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根本支持在于“耕战”。顺应这种以发展生产和政治统一为时代要求的历史潮流,法家发展出以实现专制统一国家为目的的社会理想,在严苛的统治秩序中要求人民坚持以国家利益为导向进行生产和战争。诸子解决社会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思路虽不一致,但都依赖于各自基本价值观念的实现。而价值观的实现,一方面依靠外在的公权力对个人的宣教与要求,另一方面就是依靠个体的自发价值认同。这两方面的实施无论是显性还是隐性,都依赖于教育。先秦思想家均对教育的重要性加以强调,在他们的著作中,讨论了多种价值倾向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制度设计,而在具体的教育活动中,先秦思想家更是在培养弟子、传播知识上身体力行,实践自己所提出的教育思想。
(二)先秦诸子所提倡的德性教育
先秦诸子对教育的强调,落实在针对理想人格的实现所必需的德性培育之上。德性教育针对的是各学派所设想的理想人格的实现,它并不只是追求那些满足不同学派政治理想诉求的道德素养,更直接目标是培养诸子政治思想的实践者。从这个角度来说,诸子思想中的德性教育不仅包括人格完善上的道德培育,还包括针对相应职责能力的才性培育。基于各自理论,先秦诸子对德性教育的设想方向与实现方式有根本性不同。儒家和道家从对个体生命发展的应当性出发,强调从个体生命的完善与天人和谐的当然角度而提倡德性教育,这种德性教育的实现依靠主体性的价值反思,依靠内省式的生命体验而获得。墨家与法家则是从政治理想实现的应然出发,以培养能够完成专门性职责的人才角度来考虑发展教育,德性教育的出发点是满足社会共同体良好运行的需要。从各自哲学的认识论出发,各家思想对人的教育路径和可能性也存有不同的看法。虽然存在不同意见,区别于现代教育思想的先秦教育思想,从自然与社会的和谐秩序实现出发,更强调对人德性的培养,最终以追求天人合一为目标的德性教育落实在人的全面发展上。
当前,对先秦诸子的教育思想虽有较多讨论,但也存在一定误区,即以现代教育思想中的道德教育来理解先秦诸子的德性教育。这样的理解方式有三个不足。首先,先秦诸子所处时代已然是礼崩乐坏价值多元的时代,不同阶层不同文化区域的人民所持有的基本价值观念乃至生活方式多有不同,先秦诸子各自对什么是理想人格、什么是符合社会需要的道德有不同的理解。同时,先秦诸子所构建的思想理论的基本模式各有特点。在不同的理论构建模式中,教育思想的探讨更具有多元的理论形态。以目前单一趋同的价值观和理论模式去理解先秦诸子的教育思想,这就不符合历史事实。其次是以今解古的问题。学界对道德教育的理解,多是从现代教育思想的范式进行考察,使用的话语体系与基本价值观念都是由现代西方所出,进而用所谓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等现代社会的价值标准去评价先秦诸子的教育思想。且在目前的研究中,先秦诸子思想中那些符合现代价值的道德要求,就被提倡和借鉴;而那些与现代价值不相符的价值诉求则被冠以糟粕之名而被忽视。最后,即使有些研究者,努力从先秦思想观念出发去讨论诸子教育思想,但是受其学术背景以及研究方法的制约,对诸子思想的内在逻辑只停留在表面理解上,简单地将诸子思想进行分类总结,不能将诸子教育思想与其哲学思考进行内在连接,使先秦教育思想的丰富内涵无法获得中国式的理论诠释。所以本文强调依靠对先秦思想的全面理解,从诸子哲学与时代背景出发,将诸子思想中的教育思想归纳为德性教育,并从诸子具体的思想观念中构建德性教育的共通形态,并对《墨子》所提出的德性教育做出理论梳理。
本文对先秦德性教育的定义是,它是共存于先秦思想家所面临时代困境的解答之中的,由天人关系的哲学思考出发,以人的道德与才性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依靠言传身教与自我体认的办法,追求个体生命境界的超越与圆满的教育。这种德性教育可以用孔子之言“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来概括。
二、《墨子》德性教育的职责指向
先秦时期最为流行的思想流派是儒墨道法四家,其中儒墨两派虽有很多共同的问题,但是选择不同的解决进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解决进路是以点带面,依靠对作为道德楷模的君子的培养,使君子将亲人之间的淳朴真诚的情感扩充到整个社会关系中,依靠这种仁爱而将整个社会的秩序构建在家庭秩序的稳定之上。而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学派则是以面带点,认为社会动荡的根源在于无法实现全体社会成员基本生活需要,导致社会成员为争夺生存资源而进行掠夺和战争。《墨子》提出兼爱的社会政治理想,强调对社会利益的合理分配,在利益的合理分配的基础上构建人之间的信任与友善。《墨子》从类似帕森斯的功能结构主义的社会思考上,去设想改变社会分层,实现社会团结,将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实现作为最基础的政治目标。由以上的分析,可见《墨子》以社会共同体为中心的思想构建与儒家的由家及国的思路完全不同,《墨子》对理想人格的培养目标自然也与儒家不同。
从《墨子》整个文本来看,它所设计的君子(1)《墨子》对理想人格的培养有多重的标准,如兼士、兼王、君子、圣人等理想人格形象,分别指向理想人格面对不同社会问题的解决,而要满足的基本职能要求。而“君子”这一理想人格,是对儒家君子思想的继承与改造。君子这一概念,能够集合《墨子》从个体存养乃至匡扶天下的多层人格理想。所以,君子可以当作整个《墨子》思想中理想人格培养的根本目标。而反映在《墨子》的社会政治理想的实现之下,“兼士”则可以看作《墨子》多重理想人格中适应政治实现的一种面向。的道德标准源自维持社会公平、保障社会秩序的理想。《墨子》理想的君子人格指向是满足社会成员的基本利益与社会组织具体功用。理想人格应具有的所有品德,皆是满足社会生活和谐稳定的功利主义需求。所以《墨子》思想中美德教育,就不能以儒家仁爱思想作为研究的标准,而应当从《墨子》独特的“以利为义”的功利主义价值观进行阐述。对《墨子》教育思想中的理想人格培养,不能简单以“道德教育”进行概括。《墨子》所提倡的道德,不是古代延续至今发挥作用的儒家式道德,而是为实现其兼爱社会理想而构建的“兼士之德”。这种“兼士之德”,与古希腊哲学中所讨论的维护城邦政治而培养的“节制”“勇敢”“智慧”等美德,在其指向内涵上是一致的。麦金太尔在考察荷马史诗中古希腊人的善时认为:“一个履行社会指派给他的职责的人,就具有德性。然而,一种职责或角色的德性与另一种职责和角色的德性是完全不同的。国王的德性是治理的才能,武士的德性是勇敢,妻子的德性是忠诚,如此等等。如果一个人具有他的特殊的和专门职责上的德性,他就是善的……‘善’完全在于社会职责的履行,与它相联系的其他概念也显出这个特点。”[1]31-32《墨子》所提倡的兼士之德,更趋向以个体职责完成来讲。“兼士”职责的来源是《墨子》的“兼爱”理想实现的各种物质性需要。《墨子》所规定的实现个体职责而获得的德性,与其他先秦思想家所倡导的道德是不同的。但是,对人如何发展、对人如何获得良好的德性培养的讨论,则是先秦诸子共同的话题。这种共同性得自于中国从先秦时代所开创的以生命为主要课题的哲学,人之生命的调节与完善,落实在个体的德性培养之上。“中国哲学,从它那个通孔所发展出来的主要课题是生命,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的学问,它是以生命为它的对象,主要的用心在于如何来调节我们的生命,来运转我们的生命、安顿我们的生命。……中国人首先重德,德性这个观念首先出现,首出庶物。这个拿康德的话来讲,就是实践理性有优先性,有优越性,优先优越于theoretical reason。”[2]14可以说,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核心问题就在对人的德性培养上,中国古代教育是一种重视生命实现的德性教育,德性教育就是生命教育。本文反对以简单化的“道德教育”来去讨论《墨子》教育思想,应以“德性教育”来定义《墨子》教育思想。
三、“兼相爱”是《墨子》理解德性教育的落脚点
在《墨子》社会政治思想中,对人与人关系的理想状态的设想,是社会成员打破阶层差别而实现互相亲爱。这种亲爱并不是个体性的体验式的情感,它的内在意义更突显在个人对他者的无限性责任,依靠这种无限性责任的实现,整体社会成员才能够建立互信,获得生活与生产上的正常交往,从而能够展开合作与互利。这种对社会成员理想状态的设想,是建立在《墨子》对人的生存权[3]1的深切关注之上的。我们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理解这种对生存权的关切,生存需要是人的各层次需要中最为基础的一层,只有解决这一基础性需要才能够去考虑其他需要的实现。从社会成员对于生存的基础性需要出发,从生存需要的满足必须建立信任与交往出发,《墨子》构建出针对当时历史环境下人民所需要的社会政治理想,设立以兼爱为实现目标的终极理想。而《墨子》在战国时代得到广泛的支持成为显学,也在于其思想对人基本生存状态的极端关切。“兼爱”有其独特的思想体系,与当时的其他诸子思想有明显不同。
在传统对“兼爱”的理解上,多以儒家的“仁爱”比对《墨子》的“兼爱”,但是兼爱与仁爱在使用语境乃至于实现方式均不一致(2)墨子之学虽宗于孔子之学,但是以墨子之学中的重要观点与孔子之学的观点进行比附理解,则有极大的问题。虽然墨子之学对各种问题的讨论,多是从对孔子之学的批判而来,但是对很多概念的理解之上,两者所关注的内容并不是站在同一问题层次,所要解决的问题也并不是来自同一价值源头,如“兼爱”与“仁爱”、“天志”与“性与天道”、“敬鬼神而远之”与“明鬼”。。总的来说,孔子所提倡的仁爱是人之为人的利他性情感。它源于个体对自我生命的理性思考,进而推向对其他社会成员生存状态的关心,即“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它是人区别动物的价值根源,所谓“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论语·学而》);它是个体价值在社会之中实现的基础性依据,“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它可以依靠君子自身的学习和实践而获得实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总的来说,这种仁爱建立在道德主体的挺立之上。“儒家的思想开辟价值之源,挺立道德主体,这方面没有能超过儒家者。”[2]54而《墨子》“兼爱”首先指向的是理想的社会生活秩序。对“兼爱”的理解重心应当放在“兼”字上,“兼,并也”(《说文》)。这个“并”,可理解为现代汉语中的“共同”,即是要满足社会成员的共同性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实现整体社会成员的共同生存。这种共同性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生产和分配,是建立在社会成员的互相交往之上,即所谓“兼相爱,交相利”中的“相”。
既然在社会交往理论中,人必然地要与他者产生联系,那么就需要一个基础性的保障来实现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这种基础性保障就是社会成员所共享的某种价值观念。《墨子》所设计的“兼爱”亦可以看作是《墨子》理想的核心社会价值。在这种价值观念中,爱是社会共同体中个人对他者的天然性责任,所以“兼爱”的实现需要社会成员之间产生互利性的关系,即“兼相爱,交相利”。同时还依靠共同的价值规范在整个社会共同体中发挥作用。“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墨子》强调价值规范需要得到最高统治者的统一和弘扬,从而实现天下的治理。在这个层面上讲,《墨子》的兼爱思想既是从社会交往角度对理想社会形态的设计,又是根据社会交往理论假设所构建出的社会成员基础性道德义务,还是理想社会的主导价值。《墨子》的兼爱思想是针对整个社会秩序的价值性构建,而仁爱则是对个体道德完善的完满追求。《墨子》的兼爱思想,虽然与儒家仁爱有相似性,即强调对社会成员的友爱与帮助,但是其设计的初衷并不是树立个人的道德主体性,而是将个人消解在社会共同体中,它的目的是完成整个社会的秩序性建构。
四、《墨子》外在性价值树立的两个向度
先秦诸子针对各自的社会理想,设计不同的制度去实现,但是归根结底,诸子都强调理想政治的实现依靠核心价值观念在社会中的树立。《墨子》所提倡的价值观的树立主要依靠外在强制性的价值宣教和内在的德性教育。《墨子》从整个社会秩序的整合出发,强调外在的价值提倡作为德性教育的制度性补充与舆论背景。在外在价值的树立上,《墨子》使用两种方式:一是依靠国家强制力树立社会主体价值,从整个社会物质需要的角度,强调秩序稳定和生活节约等系列价值,即《墨子》提出的“尚同”“尚贤”“非攻”“节用”“节葬”。二是利用商周以来所延续的天命鬼神的宗教信仰,依靠“神道设教”,重新对天命与鬼神从功利主义价值哲学上加以诠释,依靠神秘主义和对生命的超越性解释实现价值树立,即《墨子》的“天志”“明鬼”“非命”等思想。
《墨子》从构建社会主体价值的角度,强调“尚同”,即以统治者的意志来归纳统摄被统治者的价值观念,从而使得君民上下同义,使得天下获得价值统一而不混乱。“国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国君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学国君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学国君之善行。”(《墨子·尚同上》)但是在当时政治失序价值混乱的社会背景下,《墨子》所设想的依靠统治者的意志来强制规范社会价值是不可能实现的。《墨子》又从社会共同体的利益满足上,强调国家贫穷混乱的原因是不能任用有能力的贤人。他强调要对贤士“富之贵之,敬之誉之”(《墨子·尚贤上》),用直接的荣誉和财富去吸引天下的贤士。在选拔人才的过程中,强调以才能为标准,“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墨子·尚贤上》)。甚至要打破以往举才只上不下的局面,要求“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墨子·尚贤上》)。从维持社会秩序稳定的角度来思考,《墨子》反对侵略战争,即“非攻”。战争会导致人民的生存难以保障,“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墨子·非攻中》)。战争无论是胜利还是失败,最终都导致社会物质财富的浪费,“弃所不足,而重所有余”(《墨子·非攻中》)。《墨子》也从整个社会稳定的角度,强调对国家物质财富的节约,强调“节用”。“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墨子·辞过》)。君主节约财富,才能够获得天下的治理。“圣人为政一国,一国可倍也;大之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足以倍之。”(《墨子·节用上》)不仅在社会生活中要节用,《墨子》还反对厚葬的习俗,要求在葬礼中节约。“厚葬久丧,重为棺椁,多为衣衾,送死若徒,三年哭泣,扶后起,杖后行,耳无闻,目无见,此足以丧天下。”(《墨子·公孟》)“细计厚葬,为多埋赋之财者也。”(《墨子·节葬下》)厚葬久丧只会带来巨大的浪费,甚至妨碍到正常的社会生产,这与《墨子》所设想的保证社会成员基本生存的政治理想是背道而驰的。
但是,依靠外在政治力量的宣教并不能全面地将兼爱的价值理想在社会大众心中树立。《墨子》接续中国传统思想中“神道设教”的观念,对商周以来所树立的天命与鬼神的宗教观念进行功利主义的价值改造,以求依靠神的惩恶扬善对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产生影响。“祭祀鬼神之事虽然属‘神道设教’,但却非以鬼神信仰为核心,祭祀在于表达思慕之情,忠信爱敬之意,所以荀子将祭祀理解为‘人道’,人道也即是祭祀鬼神之事的文化意义之所在……神道始终没有脱离人道,未曾与人道形成尖锐的对立,反而以人文精神作为本质内涵,则是中国礼义文化之整体所追逐的人道之‘当然’。”[4]25《墨子》首先反对儒家不信鬼神的思想,为自身所提倡的鬼神信仰提供合法性。“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此足以丧天下。”(《墨子·公孟》)在《墨子》看来,不信仰天命鬼神,就会对整个社会的道德价值规范产生危害。因为天具有意志,能够赏善罚恶,辅助兼爱理想的实现,“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墨子·天志上》)如果不对鬼神有所信仰与敬畏,天下便会产生混乱。“皆以疑惑鬼神之有与无之别,不明乎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墨子·明鬼下》)《墨子》所设计的这种功利主义宗教,一方面从外在行为规范上要求社会成员履行社会义务,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谐;另一方面从社会成员个体心理的角度,引导和培育利他的价值观。从思想的构建理路来看,“天志”“明鬼”的设想并不是出于简单迷信,而是《墨子》为解决兼爱理想设计中的道德根源问题而展开的神道设教。“墨子讲天鬼并不是出于虔诚的信仰,而只是为人的行为制订一个外在的标准,所以他的眼光始终停留在现世之中,墨子既没有一种来世的观念,又没有一个彼岸世界的幻想。”[5]118天不仅作为有意志的至上神对社会成员的行为加以干涉,《墨子》还强调天是人间治理的基本制度与法则的来源。在这个角度上讲,天不仅是意志之天,还是价值之天。从社会合理运行的角度,人的行为应当取法于天,“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墨子·法仪》)总的来说,《墨子》所提倡的“天志”“明鬼”,是一套不完整的宗教教化思想。“凡一种文化的教化理念,必落实于某种特定的生活习俗、仪式、礼仪系统方能见其功。宗教之影响信众的精神生活,亦不仅在其教义,更因其显诸实践性的仪轨系统而能与信众的生活相密合。”[6]21
但以上两种以政治与宗教为形式的外在价值树立,在战国特殊的历史时期无法真正解决社会成员价值缺失的问题。只有依靠内在的德性教育,“引发人的内在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的转变”,[6]25才能够将社会的共同价值树立起来,才能够真正培养出实现兼爱理想的有德之兼士。所以在《墨子》的整个兼爱思想中,更重视内在的德性教育在整个社会理想实现中的作用。
五、德性教育的面向
从孔子开始,儒家就强调德性培养是君子人格养成的基础,“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在《墨子》思想中,德性也是理想人格培育的基础与面向,是君子在具体社会活动中的处事原则。“君子战虽有陈,而勇为本焉;丧虽有礼,而哀为本焉;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墨子·修身》)《墨子》所提出的德性树立,既是君子体认个体存在价值、开启道德性自觉的开端,又是君子获得社会认可、明确自己所处社会地位的起点。儒家主要从个人道德主体的自觉讨论,如《论语·颜渊》云:“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述而》载:“我欲仁,斯仁至矣”。《墨子》则是从人的德性来自于社会价值的实现来立论,“是故置本不安者,无务丰末;近者不亲,无务求远;亲戚不附,无务外交”(《墨子·修身》)。君子德性树立的直接动因在于满足君子实现其事业的必要能力特质,实现“为天下兴利除害”的最终理想。
在《墨子》构建统治秩序的设想中,从经验现象的角度强调有德的贤士影响国君的国家治理,《所染》篇用染丝(3)在对《墨子》教育思想的讨论中,多有以染丝说解释《墨子》人性论的。此种说法欠妥。《墨子》的人性论主张并没有在其著作中直接论述,通过对《墨子》全篇的理解,墨子所持的人性论观点应与告子的自然人性论类似。染丝之说只是贤臣对君子直接的德性影响的分析,并不能当作人性论思想的论据支持。这个直观的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丝本无色,但是沾染到不同颜色的染料之后,就会变成不同颜色的丝,“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墨子·所染》)与此同理,国君在治理国家亦受到有德之士的影响。《墨子》中列举历史上数十位君王,说明国家之所以得治,在于君主行事合乎自然之理,而这种合理的治理措施来自于有德之士的影响。“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以其行理也,行理性于染当。故善为君者,劳于论人,而佚于治官。”(《墨子·所染》)《墨子》甚至还将德性感染的理论推向一般的士,“非独国有染也,士亦有染。其友皆好仁义,淳谨畏令,则家日益,身日安,名日荣,处官得其理矣。”(《墨子·所染》)一般的士也会受到有德性的朋友的感染,从而处理好家庭与自身的事务。在《墨子》的整体社会秩序构建中,德性高越的士通过对他人的影响,不仅促进国家的有效治理,还满足周边他人的德性生活实践,所以德性高越的士在《墨子》的理想社会中成为国家得治、个人身名安荣的人才保障,所以培养这种德性之士,推进德性教育成为国家治理的首要要求。
在兼士养成的德性培育中应该着重开展哪些德性的养成?在《墨子》对德性修持的理解中,廉义爱哀的德性修养是兼士的主要培育面向。“君子之道也,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四行者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墨子·修身》)这四种德性要求是从人之为人的最基础的公义道德上讲的,即通过这四种德性的培育,使得君子能够对他者的不同的生存境遇有同情理解,从培育同情心的角度来激发君子对他人的友爱。在《墨子》自然人性论设想中,如果连这种基础的同情心都无法培育,则再高超的德性也不可能获得发展。在这种基础的德性培育之上,《墨子》进一步提倡“志强”与“言信”的实践德性,这种实践德性,旨在解决《墨子》所树立的功利主义价值的实现。《墨子》所设计的“兼爱”社会理想建立在人民的生存利益获得保障之上,这就需要君子能够促进生产发展,满足社会分配公平。这种功利性的需要要求君子之德性有实践性的指向,即能够“志强”,通过立志而学习具体知识,获得解决问题的能力。《墨子》又要求君子能够“言信”,通过个体信用的树立而保障社会成员对君子的信任与服从,从而能够指导社会成员开展社会生产。当然这种志与信的德性培育,并不是君子德性培育的最终目标。君子依靠参与具体问题的解决,不断展开对其个人能力的培养和磨砺,从而实现君子德性的全面培养,实现个体对社会生产与秩序稳定的实际性功用。“故君子力事日强,愿欲日逾,设壮日盛。”(《墨子·修身》)我们可以看到,《墨子》所设计的德性培育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志与信的培养过程中不断反省自己,明察他人。“君子察迩而迩修者也。见不修行,见毁,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修矣。”(《墨子·修身》)《墨子》这种渐进性的培育过程是曲折和艰难的,也是墨子自身行事风格的缩影。“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庄子·天下》)从以上的君子德性培育设计来看,《墨子》设计出基础性道德伦理与实践功用两个德性培育方向,来满足其兼爱理想的现实性需要,而这两种层次的德性培育设计,其价值根源于《墨子》对社会组织常态运行的功利主义思考。
六、《墨子》德性教育的功利主义价值取向
(一)“爱”在“利”中
考察《墨子》全篇思想,言必称利。《墨子》从兼爱理想的设计角度出发,明确社会共同体基本交往依赖于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利益的获取与保障,即“爱”在“利”中。《墨子》从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历史经验主义的角度出发,回顾以往的三代圣王,皆是以利天下万民而得以兼爱天下,“则此言三圣人者,谨其言,慎其行,精其思虑,索天下之隐事遗利,以上事天,则天乡其德;下施之万民,万民被其利,终身无已。”(《墨子·尚贤中》)古代圣王在选贤任能的时候,是以能够对天下有利的标准进行选拔。“故古者圣王唯能审以尚贤使能为政,无异物杂焉,天下皆得其利”(《墨子·尚贤中》),《墨子》认为兼爱理想的实现,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当时乱世中战争厮杀的不和谐关系,是由损人利己的夺利行为所导致。“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墨子·兼爱上》)只有依靠人与人之间的互利关系,社会成员之间的和谐交往才能够正常化。“若我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爱利吾亲乎?意我先从事乎恶贼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乎?即必吾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墨子·兼爱下》)《墨子》从社会交往的正常态势中认为,依靠我对他人的利益上的满足与帮助,他人也会在同一层次对我进行回报。“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墨子·兼爱中》)《墨子》预设在这种利益互相满足中,人的良好交往建立起来,进而可以实现人与人的兼爱。
(二)以利为义
《墨子》非常重视作为社会主体价值的义。在回顾远古社会历史时,《墨子》讨论社会主体价值的出现与稳固的过程。《墨子》认为,古代由于没有统一的价值规范从而产生社会混乱,而统治者出现的根本原因或者根本职责就在于维护天下公义。“明乎民之无正长以一同天下之义,而天下乱也。是故选择天下贤良、圣智、辩慧之人,立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墨子·尚同中》)而后依靠圣王与众贤的推动,从而使得天下之公义得以树立,天下得以稳定和治理。《墨子》进而主张国君选举贤良以义为依据。“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此若言之谓也。”(《墨子·尚贤上》)从天命观的角度,《墨子》认为天下之义来源于高于人世的天。“天下既已治,天子又总天下之义,以尚同于天。”(《墨子·尚同下》)先秦哲学在追寻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根源与理想形态时,均将其推向天所代表的自然秩序,如儒家“知天命”、道家“道法自然”。《墨子》虽然坚持天作为现实价值的至上根源,但是与其他各派思想不同的是,《墨子》所宗的价值来源落实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中。既然兼爱理想的实现在于人们总体利益的满足,社会活动的基本出发点是保障人们的生存利益,社会的最高价值也应当从生存利益的满足上进行讨论,那么作为社会共同体的基本价值——“义”,自然与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的满足相挂钩。《墨子·经上》篇直接将义理解为利的实现:“义,利也”。为了实现对利的满足,《墨子》提出尚贤,是因为“尚贤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墨子·尚贤下》)。尚贤可以运用贤人的智慧与能力,满足天鬼百姓的利益要求,从而获得社会的治理。所以,蕴含在《墨子》德性教育中的价值预设就是以利为义的功利主义价值观。
通过对《墨子》思想的理论梳理,我们可以明确“兼爱”是《墨子》设想的社会政治理想和预设的社会主体价值,“义”是《墨子》设想的社会共同体合理运行的基础性价值原则,“利”是《墨子》构建其价值思想的现实性源头,“天”是《墨子》价值原则的超越性根源和外在保障,而《墨子》最终理想的实现,依赖于政治生活中尚贤和培养“兼士”人才,更依赖于对社会成员的德性培育和实践性引导,即德性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