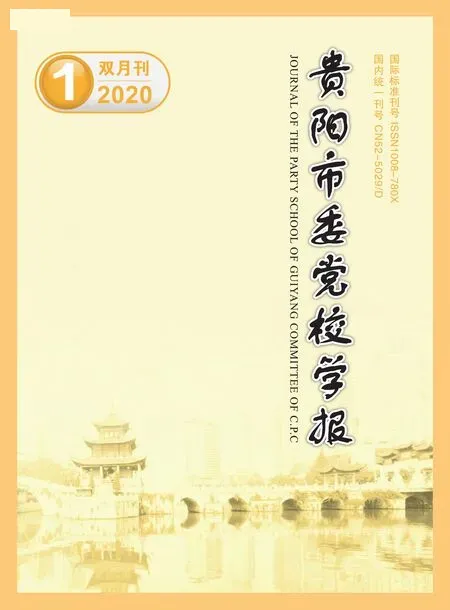文化自信的出场语境与内在逻辑
——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中国转向
杨思远 杨 锦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浙江 杭州 311121)
文化体现着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或内隐或外显”的行为模式与行为理念,反映着该民族改造客观世界、创造现实财富的路径选择与活动规律,让文化发挥最大的力量,就必须坚持文化自信。坚持文化自信就是坚持文化主体对自身文化与价值的深度认同,是对其自身文化生命力、文化感召力与文化影响力的高度自豪与坚定信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在新时代的中国,“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源于鲜活的社会实践,源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创造,拥有着深厚的哲学基础与理论意义,体现着理论与现实的结合、历史与实践的统一。
一、文化自信的出场语境
文化自信始于中华民族对自身内蕴的理性观照,要求客观、批判地认知、观察、理解根植于民族深处的文化基因。近代百年以来中国社会遭遇了千年历史上最大的变迁,中华民族对自身文化的态度经历了由“盲目自大”到“妄自菲薄”的过程,其间,倡导“文化自觉”与“全盘西化”的声音此起彼伏,叫好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本位论”与叫衰中国文化的“全盘西化论”相互交织,但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正视民族文化、重估自身文化价值以实现文化复兴的“文化自信”问题日益得到全社会的关注,因此,文化自信的出场有着深刻的理论与现实语境。
第一,回应中国道路与理论实践的需要。中国追求现代化的道路是一个艰难而曲折的探索过程,通过不断实践与摸索,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发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个实践与探索过程中,要求、呼唤着更深层次的精神力量作为支撑与指引,文化自信问题应运而生。文化的产生、发展必须根植于实践的土壤,而实践的更好发展也离不开文化“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滋养。文化在“自然的人化”这一具体实践中产生,在实践的展开过程中,人们将能动的力量转化为现实的物质性,唤醒出人与生俱来的超生物性思维认识能力与伦理道德能力——知性与理性,而这二者的合一便是人精神思维的实践力与表现力——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文化可以帮助人们实现感性与理性、真与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渗透与交融一致,但其根本还是根植于人的现实实践当中的,“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135-13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就是这样不断地在中国人民的革命、改革与建设的实践当中不断确立、不断坚定的,因而文化自信也就是中国人民对自身实践力量的确证与肯定,并在这种肯定之中又内生出富有创造性与凝聚性的文化力量,又进一步促进实践的发展进步。
文化自信同样给予中国实践以精神信念,回答着中国实践的价值追求。马克思始终关注文化对人的个体性存在与社会的整体性存在的重大影响,他为我们描绘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愿景,规定了解放全人类是每个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而无论是共产主义理想还是对全人类解放的追求,其内在的价值取向都是追求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都是为了实现现实的个人的真正解放,而这种解放的实质核心就在于人类精神层面的解放。由此而看,文化自信首要地就是为了实现最广泛的人民群众的人文关切而存在的,它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来,又高于现实,化生为一种凝聚性精神力量引导、帮助实践的发展,促进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整体风貌的提升。
第二,解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问题的需要。解决现实需要是理论创新与深化的根本动力,马克思认为,“问题却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2]203因此,解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问题,需要文化自信的出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资料的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重大的时代课题与现实难题,发展如何更加均衡普惠、如何更加全面协调、如何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等等都是当前实际的重大需要,而这其中处于关键枢纽地位的便是文化自信问题。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相互促进的结果。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离不开文化软实力的强大推动,更离不开文化自信对全国各族人民的强大凝聚与感召;当前我国发展所遭遇的一系列困难与瓶颈,需要实践创新,同样需要文化自信的驱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是社会交往关系不断交织、不断融合、不断丰富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逐步确立了反映中国实际、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社会上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部分拜物教性质的思想意识,国民精神层面也存在一定的空缺与空虚,这就需要文化自信与解决现实问题的实践产生深度共鸣,在更深层次上解决不良意识形态对我国社会的影响。正如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在其名著《文化与混乱》(Culture and Anarchy)中指出,文化是“世人所思、所表的最好之物”[4]6,可以“使全人类衷心向善”[5]23。因此,坚定文化自信可以帮助社会摆脱拜物教意识,消除非理性与非科学的不良意识,在“守正”的基础上,实现文化的创新与繁荣。
二、唯物史观中国转向的理论探源
树立文化自信,其内在、首要的逻辑意蕴就在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化,这一问题具有深厚的理论背景。马克思从理论根本上探析了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逻辑,从物质经济角度与意识形态角度对其展开了激烈的批判,认为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仿佛是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模式仿佛变为了“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具有)正在实现的趋势”[6]82,但与此同时,他又不断反思与追问:“‘是否存在着不同于资本逻辑规制的现代性道路’的现实可能性”[7],这就是著名的“马克思之问”。实现唯物史观的中国转向,实质也就在于在中国的现实场域内实现对“马克思之问”的彻底回答。回答好这一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化,根本上就在于用中国的文化逻辑去破解西欧逻辑,从而创建中国化的唯物史观。这主要有以下几个规定性:
首先,唯物史观的中国转向要求在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中探析中国历史发展的逻辑脉络。毛泽东指出:“对于物质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就是说,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8]308因此,要考察中国革命的逻辑、中国社会发展的逻辑,就必须要注意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就是要将一般规律运用于本国文化之上,将所谓的“铁的规律”或“超历史的一般必然性”照搬、生套于中国实际是绝对无法行得通的。唯物史观需要在中国语境、中国场域内发挥作用,这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首要前提。
其次,唯物主义的中国转向要求从具体的、现实的中国国情出发掌握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钥匙”。探索中国应该走何种道路,探索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内在逻辑始终是指导现实的理论前提,同样也是唯物史观中国转向的理论表达与实现方式。西方人在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他们的现实场景与实际困难。同样,中国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也有属于自身特点的国情场域,从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时期,从追求民族独立实现“站起来”到追求全面小康实现“富起来”,再到追求民族复兴实现“强起来”,中国的历史任务始终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发生转换。因此,唯物史观的中国逻辑就是关于中国的社会性质及发展道路、演化规律的理论,就是关于在中国社会场域中革命的必然性、革命对象、性质、主体、领导阶级、道路和未来目标的阐释理论。同样,文化自信是中国的文化自信,是反映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的文化自信,产生于中国大地,也必将根植于中国大地。
三、文化自信的二重内生性:唯物史观中国转向的文化维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有机生长,开辟了中华文化观的唯物主义转向,实现了中华文化生命力的蓬勃焕发。毛泽东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为主动。”[9]1516究其原因就在于中国人实现了唯物史观的中国化,将唯物史观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践当中,用中国文化、中国语言、中国方式回答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之问”。在唯物史观中国转向的过程中,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价值方法贯穿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内在蕴藏之中,文化自信内生性地具有了两个方面的维度:
第一,文化自信的内在价值向度就在于其人民主体性。以人为本一直是唯物史观最核心的价值旨趣,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转向首要地就是把人民主体思想贯彻到文化发展和文化实践的各个方面。首先,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转向规定了文化自信的主体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同样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通过其整体性力量,产生出一个推动历史发展的合力,促进文化的产生和发展。而具体的文化内容则又是通过人民群众的批判、吸收最终形成从内心深处到外在行为的高度认同,实现文化自信。其次,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转向规定了文化自信的对象同样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形成文化自信一个重要的方面就在于要让文化发展成果为人民所共享,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文化发展所带来的意趣与幸福感,让他们自己创造出的精神财富为自己所享用,正如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在《乌有乡消息》(News from Nowhere)中所设想的那样,文化将“不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领域。因为文化和创造力已经完全融入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5],他同时指出,“如果我们不能共享艺术,那么艺术跟我们还有什么关系?”[10]139这就点明了文化共享性之重要所在。最后,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转向规定了文化自信的价值目标是实现人民群众的全面发展。文化自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功用就在于它要消除文化的异化状态。在商品经济下,商业社会或“景观社会”(La Société du spectacle)使得“异己的和正在异化的精神文化作品变成了熟悉的商品和服务设施”[11]50,文化逐渐变成了一种单纯商业消费品,丧失了文化的审美向度与批判向度,本应作为文化载体的“景观”,却只是“让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既在场又不在场的世界,一个商品世界,统治着所有被经历的东西”[12]19。因此,文化自信所要实现的就是要让人处在真正文化环境与文化氛围之中,从内心的本真世界中探寻文化的归属感,从自己的文化背景里发现属于自己的文化满足状态,摒弃依靠文化消费所获得的“虚假的欲望满足”,实现全面健康的发展。因此,坚定文化自信,就要坚持人民本位,让人民在真正的优秀文化之中,实现文化渴望之“需要”与文化体悟之“美”的真正统一。
第二,文化自信的内在动力向度就在于其创新性。历史和实践证明,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没有创新,国家和民族就不会富强。当前,中国发展进入新常态,创新驱动越来越展现出其强大的引导力量,特别是文化创新驱动,更凸显出其“基础、深厚、广泛”的重要影响力量。文化创新是历史与现代碰撞、交融的必然要求。面对时代的变迁,要保持文化自信,固步自封地从自身历史中“吃老本”是不可行的,现代性伴随着全球化的趋势变成了一种强大的冲击力,对传统与历史形成了威胁;如何看待现代与传统、外来与本土、现实与历史,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关键所在。坚定文化自信,内在就已经包含着文化创新的内容。实现文化创新,其一要融合世界性于本土性之中,吸收现代性于历史性之内,需要对优秀的外来文化“兼收并蓄、兼容并包”。萨义德指出,“文化与文化总是彼此牵连,谁都不能‘独善其身’。一切文化都是混血的、异质的、独特的、多元的。”[13]29因此,谁都不能切断世界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只能去从中吸取有利于自身文化发展的积极因素,从融合之中完成发展,在交互过程之内实现创新。其二,文化创新还要在接受外来文化的同时,坚守好自己的文化本色。实现文化的多元创新,还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立场,坚守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本位,注重科学理论对文化实践的指导,既要防止发展停滞,失去活力的“文化结石化”,又要防止被迫消融,失去民族特性的“文化虚无主义”。最后,文化创新还要建立与之配合的文化体制机制,帮助实现文化生命力的最大释放。
四、从文化“自在自发”到文化“自信自觉”:唯物史观中国转向的文化表征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实现从文化“自在自发”到文化“自信自觉”的过程,这个过程内在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与中国传统文化观交织、耦合的一系列文化与社会反映,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发展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对立统一,也是中国文化历史发展与道路选择的深层表征。
中国的文化自觉自鸦片战争中国失败始,在重大的文化挫败感、文化倒错感与文化失落感中,知识分子便对中国文化的救亡图存与复兴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这一讨论的针对点就在于中西古今文化之争,产生了“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尖锐对立的两种思想及其转换和引申形态”[14]。 以章太炎为主要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位性,反对变革与现代化发展;而以胡适为主要代表的文化激进主义者,倡导“全盘西化论”,认为必须摒弃中国传统文化的控制,要从中国文化的“质和量”上、根本观念上和文化体用上彻底西化。但无论是“文化保守主义”还是“文化激进主义”都没有认识到中西古今文化的激烈争论背后只不过是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与西方现代的资本主义文化的对立,它们都只讨论了文化研究视野的“地理切入”划归(着眼于中国与西方)还是“历史切入”划归(着眼于传统与现代),都只是实现了在文化外在发展模式上的比较与争论,实质上都缺乏批判、辩证的视角与眼光,不约而同地走向了文化形式主义的错误,虽然一定程度上开启了中国文化的自信自觉之路,但最终还是未能探析出中国文化实现变革与转型的发展方向。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从文化观与价值观上实现了由形式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由此也实现了中国文化由“自在自发”到“自信自觉”的根本转向。
首先,唯物史观进入中国,使得文化观的讨论跳出了“历史切入”划归或“地理切入”划归的表面功夫,文化发展讨论冲破了原有的形式主义问题域,为文化由“自在自发”到“自信自觉”的转变提供了全新的思考模式。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文化观的改造既实现了对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双重批判,也实现了对传统中国文化与资本主义西方文化的双重超越,因而如美国汉学家迈斯纳指出的那样,“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既要否定中国过去的传统,又要否定西方对中国现在的统治,因而出路只能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15]
其次,唯物史观进入中国,没有导致中国文化的传统—现实性断裂,而是使传统文化获得了现代性力量,也使马克思主义文化获得了中国民族文化的滋养。从文化的纵向发展来看,“马克思主义从来不主张割断传统,而是明确宣称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发展的必然结果”[16];从文化的横向发展来看,马克思主义并未否定或取代民族文化的主体性,而只是给中国文化以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帮助中国文化走向一种更加光明、“大同”的道路。因此,从这一层面上来看,文化从“自在自发”到“自信自觉”的转变过程,实质上也就是中国文化实现“否定之否定”的自我蜕变的过程,这一过程即作为“接受主体”的中国文化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汲取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力量作为指导,再从自身历史传统里摘取出具有鲜活生命力的优秀内容,将两者相渗透、相融合,最终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这一过程既是由“一”(传统文化)变“多”(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的裂变过程,也是由“多”(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变“一”(中国文化)的聚变过程。
最后,唯物史观进入中国,实质上是将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最大优势发挥了出来,实现了二者双流合一、“综合创新”[17],最终导致文化“自在自发”向文化“自信自觉”的转变。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传入中国并解决中国的革命、建设与改革问题,一定程度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内在所具有的“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力量性,这种力量能够将中国传统文化论争中长期争执不下的时代问题、民族问题、价值问题、功用问题与继承问题进行统摄,并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解决过去未能解决的问题、干成过去未能干成的事业;同样,马克思主义能回答中国历史与现实之问,还在于中国文化与生俱来的那种充满活力与自信、富有包容性的广阔胸怀,中国文化是积极开放的“生命主体与创造主体”[16],是能够将“他山之石”连接贯通、引为己用的,也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才实现了将马克思主义纳入到自身文化发展过程之中,实现了文化自信的建立。这一过程,便是实现了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关于文化的“综合创新”,张岱年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一定要继承和发扬自己的优良传统,同时汲取西方文化的先进贡献,逐步形成一个新的文化体系。这个新的文化体系,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指导下,以社会主义价值观,来综合中西文化之长,而创新中国文化。它既是传统文化的继续,又高于已有的文化,这就是新文化。”[18]实质上,文化自信的核心要义也就在于此,文化自信是能够既包容各方之所长,又能保持自己特色的“综合创新”的文化,文化自信的形成之路如此,其未来发展也必将如此。
五、小结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传入中国,实现了我们历史观的伟大转向,这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它使“中国人民学会了科学的革命的新文化”,实现了精神上的“伟大胜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精神保障与文化根基,是促进全社会团结凝聚、蓬勃向上的底气与基石。坚定文化自信必须始终把握唯物史观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必须不断从历史纵深面与现实横截面里汲取力量,必须更好地立足于中国现实和“中国语境”,最终为实现中国文化的繁荣兴盛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