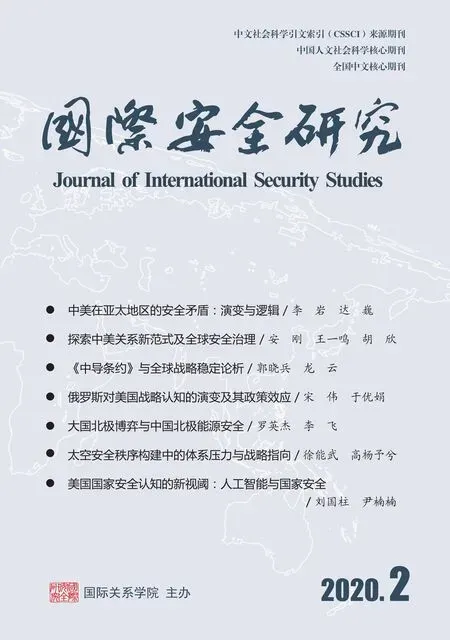大国北极博弈与中国北极能源安全——兼论“冰上丝绸之路”推进路径*
罗英杰 李 飞
安全战略
大国北极博弈与中国北极能源安全——兼论“冰上丝绸之路”推进路径*
罗英杰 李 飞
在“海权论”“无主”“共有”等国际视阈下,北极地区的归属特别是能源资源权益的划分一直悬而未决——特别是在近年来北极环境变迁逐步加快、各国极地活动能力不断增强、全球能源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各国拓宽能源获取渠道的需求已经变得越来越强烈。无论是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北极地区国家,还是以中国为代表的“非北极国家”,都对北极有着较强的能源权益声索以及能源安全维护需求。围绕着北极地区的公共与私有属性界定、开放与排他政策选择、法制与权力标准划分等诸多问题,各国之间展开了全方位的多轮博弈。目前,在各国北极政策“理念一致、目标冲突”的背景下,在北极开展合作特别是能源开发合作也越发困难重重。而对于提倡构建“冰上丝绸之路”的中国来说,要想维护本国在北极的能源安全,就必须借助在北极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的力量,通过分享理念、设置议题、促成合作等多种方式,实现对北极事务的有效介入。这将有助于规避因恶性竞争而带来的战略透支,为增强中国的北极能源开发话语权奠定基础。
北极治理;大国博弈;冰上丝绸之路;能源安全
资源稀缺的日益凸显和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使得世界各国能源获取的渠道由地表转向地下,由温热带转向极地,甚至由地球转向外太空。其中,北极地区丰富的能源、矿产、渔业等资源和巨大的战略价值,使各国,尤其是大国[1]争相单独或联合出台政策主张。在这一过程中,国家身份的不同和战略追求的各异,使得各国在涉及北极事务的协调上存在着巨大而复杂的矛盾。从根本上讲,近几十年来在北极地区展开的“圈地运动”,是各国围绕其公共属性和私有属性的界定问题展开的拉锯战。在这场争夺战中,利益诉求的重合与龃龉,决定了国家间政策的迎合与相悖,而法理与权力的配合或相斥,则映射出国家实力与国际法规之间的复杂辩证关系。
当前,时值“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六年,“冰上丝绸之路”的建设也取得了较大进展。然而,北极地区复杂的博弈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冰上丝绸之路”的开放性和顺利推进。在推动这一包容互利的合作倡议的过程中,作为“非北极国家”[2]的中国不仅面临着与谁合作、如何合作的问题,更要考虑如何应对风险、最大程度保障北极能源的安全乃至未来在北极更为广泛的利益。从某种意义上讲,作为一个“域外”国家,北极能源安全的维护不仅取决于中国以何种方式介入北极事务,也取决于战略和战术两个层面举措的契合程度。当前摆在中国面前的难题是:如何在众多倡议、政策和战略中,在凸显中国政策的开放包容的同时,尽可能避免遭到其他国家或组织的排挤,从而为维护能源安全、拓展能源进口渠道打下基础。
一 北极能源状况与各方的北极能源利益声索
在讨论北极地区的能源状况之前,有必要首先厘清“北极”这一概念。一般来讲,北极地区包括北冰洋、边缘陆地海岸带及岛屿、北极苔原带等,总面积约2 100万平方千米,涉及美国、俄罗斯、加拿大、丹麦(北极圈未穿过丹麦本土但穿过格陵兰岛)、芬兰、瑞典、挪威和冰岛8个环北极国家。[3]美国地质调查局曾对北极地区常规油气勘探的潜力进行了初步评估(主要是欧亚大陆和北美大陆两地内的区块),结果表明:北极地区预计有770万亿~2 990万亿立方英尺的潜在常规天然气和390亿桶液态天然气,其中大部分在俄罗斯境内。在能量等效的基础上,北极地区潜在的石油储量仅为天然气的1/3,总体约有44亿~1 570亿桶潜在石油。[4]其中60%的原油集中在六个区域——仅阿拉斯加平台就占到31%。尽管北极地区的潜在油气资源非常丰富,但目前仍不足以撬动中东地区主导的世界能源格局。北极地区内的油气资源分布极不平衡,80%的能源资源蕴藏于离岸地区:北美大陆板块所蕴藏的潜在石油约占65%,天然气则仅占26%,其余的集中分布在欧亚大陆板块。[5]
北极地区良好的资源开采前景,以及大部分地区主权未定的现状,使其很快成为国际政治经济的角力场。围绕“北极研发”这个核心任务,各国在合作框架内外都展开了争夺。[6]北极能源之争同时存在于北极国家和非北极国家中,但由于先机优势和地缘位置等因素,北极国家的竞争力无疑要强于非北极国家。[7]也正因如此,“域外国家”与“后发国家”才具备更强的动机与更富雄心的政策,去挑战既存的北极权力格局。于是,发生在“现状政策”与“帝国主义政策”之间的钳制与反制,勾勒出北极地区治理的基本图景,也奠定了大国北极政策对冲的基调。本文通过分析美俄等主要大国的北极政策及其内在关联性,解释当前北极博弈态势产生的内在机理。
(一)美国的北极政策与北极能源权益声索
作为没有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大国,美国在北极事务中的存在感相对较弱,当然,在日渐升温的北极事务中,美国也在寻求以法理依据或“双重标准”来谋求自身话语权。
美国的北极政策发轫于里根政府的《美国北极政策》、克林顿政府的《第26号国家安全总统指令》和小布什政府的《第66号国家安全总统指令》及《第25号国土安全总统指令》。2013年5月发布的《北极地区国家战略》是美国首个北极战略性文件,集中体现了奥巴马政府的北极战略理念和思路,[8]它明确指出美国在北极的五大利益:保障国家安全、保证资源与商业自由流通、保护环境、解决原住民需求和加强科研。在奥巴马任期内,美国通过了如《北极路线图》《海岸警卫队北极战略》《国防部北极战略》《国家安全:变化的气候》《跨部门北极研究政策委员会2015年报告》《北极地区的变化、战略行动计划、纲要》《NOAA[9]北极远景与战略》《北极研究计划:2013~2017》。[10]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12月,奥巴马政府还颁布了关于无限期限制在北极和大西洋地区进行油气钻探开发的禁令,但这很快就遭到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反建制派的否定。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并卸任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国,导致其北极政策的国内外实施环境受到消极影响。[11]2017年,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发布《北极必要性:加强美国第四海岸战略》,确定了美国北极事务的六个新目标: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资助和维护极地冰船建设、改善北极基础设施、加强北极国际合作、支持阿拉斯加可持续发展、维持对科学研究的预算支持等,以进一步加强对北极的关注力度。[12]特朗普政府十分重视美国阿拉斯加州及北极海域的资源开发,积极推动北极资源开发以增加就业机会,兑现“美国优先”及振兴实体经济的竞选承诺。[13]
2019年初,特朗普破除奥巴马政府“禁钻令”的计划被联邦法官搁置后,便开始寻求政策转圜,瞄准了军事等突破口,并频繁发布关于北极的政策主张和报告,阐述美国北极行动的必要性和路径,呈现出较强的攻击性色彩。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国防部在2019年6月发布的《2019年国防部北极战略》。该报告明确将“越来越不稳定的”北极视作美战略竞争的关键区域,并提出保持北极战略安全的切入点即:强化北极意识、强化北极行动、强化北极地区基于规则的秩序。[14]另外,该文件还谴责了中俄“挑战”北极地区规则与秩序的努力,特别是批判了俄在北极的强大军事存在与违反国际法的政策与行为。[15]
不可否认的是,美国国防部发布的报告,将注意力更多集中在军事层面,其关键词一般为“战略安全”。但是,作为维护能源利益的强力手段与最后屏障,在特朗普政府维护北极能源利益的手段中,军事手段扮演着“急先锋”的重要角色。这一政策倾向,也从侧面印证了美国在维护北极能源利益上的强硬态度。
(二)俄罗斯的北极政策与北极能源权益声索
俄罗斯被视为北极战略的“先锋者”。[16]2008年发布的《2020年前俄罗斯联邦北极地区国家政策原则及远景规划》,是全球首份关于北极的国家战略;2013年发布的《北极地区发展和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又将北极作为俄罗斯的“战略储备区”。[17]2020年3月普京批准的《2035年前俄罗斯联邦北极地区国家基本政策》强调,到2035年要使北极航线成为有国际竞争力的国家运输动脉。[18]俄罗斯曾以反对非北极国家介入北极事务和“努克标准”(必须承认北极国家在北极的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为由,为非北极国家参与北极事务设置了障碍。[19]但近年来,中俄关系的发展以及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恶化,使其在北极事务上的态度有所调整。根据现行文件精神,俄北极政策的目标可概括为:获取北极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掌控北极地区潜在的具有战略意义的航道,利用北极地区的军事价值,寻求战略纵深。[20]
俄罗斯对北极能源的开发始于1972年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的石油量产,该地能源开发还陆续扩展到其他区域。目前,北极圈内开采出的八成石油和九成天然气均来自俄。2001年年底,俄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申请,要求将北极地区120万平方千米的海域作为专属经济区,但被驳回;2008年7月,梅德韦杰夫颁布法令授权俄联邦政府可直接指定企业开采油气,这也意味着俄天然气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和俄石油公司极有可能垄断北极圈内俄大陆架的能源开采。2014年,联合国承认鄂霍次克海5.2万平方千米为俄大陆架组成部分,这标志着俄在北极的权益声索得到了联合国的支持。
与美国不同的是,俄罗斯由于政治体制等原因,其北极政策具有较强的延续性,从政策出台到落实的周期也比较短。2019年2月底,梅德韦杰夫签署政府令,将拨款8.6875亿卢布,用于“穿越北极-2019”考察活动项下的2019年北极地区科学研究和环境监测工作;[21]在2019年4月举办的“北极-对话区域”国际北极论坛上,普京发表“北极——充满机遇的海洋”的主旨演讲,提及北极社会经济发展、环境保护、提高北极地区居民生活水平以及加强国际合作等,并展示俄罗斯开放合作的姿态。但与此同时,俄罗斯修建军事基地、驻军等强化北极军事存在的行动也在继续。[22]由此可见,俄罗斯对北极能源权益的声索和拓展,呈现出四个特点:以科研为先导、以军事为后盾、以合作为手段、以先占为依托。这种策略组合建立在地缘和军事优势的基础上,并将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俄在北极的地缘和军事优势。
(三)欧盟的北极政策与北极能源权益声索[23]
欧盟虽然是一个区域性国际组织,但其在北极的影响力不容忽视,特别是由于不少成员国如丹麦、瑞典等依托北极立国,欧盟的北极地位不言而喻。当前,欧盟是北极油气资源出口的最大市场,如挪威开采的北极油气的半数以上均销往欧盟。2007年10月,欧盟首次宣示其北极利益诉求;在2008年3月发布的《气候变化与安全》中,欧盟提出了发展整体一致的北极政策以应对北极地缘战略演变的主张;2008 年11月,欧盟发布首份北极政策报告《欧盟与北极地区》,强调其与北极在历史、地理、经济、科学等方面的联系。2012年,欧盟委员会发表《发展中的欧盟北极政策》,强调加大在知识领域对北极的投入,以负责任和可持续的方式开发北极,同时要与北极国家及原住民社群开展定期对话与协商。[24]2016年的《欧盟的北极综合政策》,再次申明其在北极的三大优先领域:应对气候变化环境保护、促进可持续发展、加强国际合作。
从欧盟出台的政策文件可以看出,其北极战略的三大目标分别是:气候变化与生态保护、资源的绿色开发、提升和加强北极治理。[25]然而,欧盟至今都没有形成统一的综合性北极政策,相反,欧盟内部决策机制的复杂多样,束缚了其通过北极政策法案的手脚,使得其往往通过组织框架下少数几国的联合行动来实施具体政策。为贯彻北极政策目标,欧盟更加注重与俄、美、加等北极国家寻求合作与妥协,使这些国家允许其参与北极治理;同时,欧盟对外行动署及海洋与渔业事务总司对不同业务部门的资源加以整合和协调,从而将北极事务纳入具体政策领域之中。[26]
可见,作为庞大的国家联合体,欧盟并未有效统筹各国力量,而是囿于庞大的组织架构,在北极能源争夺中影响微弱、行动迟缓。在这一表象之后,是各国基于自身利益、实力和国际关系等考量做出的盘算。欧盟在北极问题上的组织涣散,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北极地区的权力整合与利益分配进程。鉴于此,欧盟在2019年7月发布的文件中提出,欧盟有关北极的不同政策必须在一个真正的总体战略下进行整合,在北极国际关系中的行动的总体目标应该是在多边和基于规则的外交的基础上,让所有有关方面参与进来,以避免北极合作的分散化。[27]
(四)英德的北极政策与北极能源权益声索
2013年,英国政府发布了第一个北极政策框架。该文件以尊重、合作和适当领导三项原则为基础,阐述了英国的北极政策。由此可见,英国并未因二战后的衰落而放弃其在北极事务中的话语权甚至“领导权”,而是“以变应变”,希望通过协调外力,强化其在北极的影响。此后,英国官方和民间不断以政策和行动强化其在北极的存在感。2018年4月,英国发布名为《超越冰雪——英国北极政策》的报告,总结过去五年英国在北极科学研究、参与北极事务等领域的系列举措,并阐述对相关北极事务的立场,包括:以科研等提升北极的全球影响力,保护北极原住民和环境,通过油气、航道的开发等实现北极地区繁荣。[28]毫无疑问,多年酝酿的“脱欧”将米字旗绑在了高速运转的“离心机”上,导致国内共识和政策难以达成,在很大程度上阻滞了英国北极雄心的实现。因此,可以预见,在未来较长一个时期内,英国并不能通过有效力量来维护其北极的能源权益。
作为欧洲的“领头羊”,德国高度关注北极能源开采对其利益的影响。2013年,德国出台《德国北极政策的基本原则:利用机遇,承担责任》,对其在北极的利益诉求、角色定位以及政策方向进行了重新评估。近年来,虽然德国一直在致力于实现其北极影响力与欧洲影响力相匹配,但由于地理位置等原因,一直所济有限。在2019年8月发布的《北极政策指导方针》中,德国以“对北极自然资源的开发行使环境责任”等为切入点,希望各国遵守有关矿产资源勘探和开采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法规,并凭借其在研究、技术和环境标准方面的专业知识,为北极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等作出贡献;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在北极水域内航行自由,在负责任的前提下以合作解决北极地区相互重叠的主权声索。[29]这份政策指导方针以“环保”为主基调,在能源开发问题上的主张较为保守,凸显出其在北极事务中的低参与度。
目前,英德两个欧洲大国在北极能源声索等问题上,基本处于“目标远大、政策无力”的状态,其对北极事务进程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也乏善可陈。
(五)日韩的北极政策与北极能源权益声索
日本是首个出台北极政策的非北极国家。2012年出台的《北极治理与日本的外交战略》,是日本第一个涉及北极的政策文件。该文件指出,日本的政策重心包括:推进北极的观测、研究及调查活动;推动国际合作;建设北极航道,确保海上运输等。从内容上看,该文件的主体部分还是就日本国家安全而言的“普遍的海洋利益问题”,因此这并不能被称为完整意义上的“北极战略”。 在各国竞相出台北极政策的背景下,2015年10月,《日本的北极政策》应运而生,该政策文件主要针对北极航线的利用和资源的开发,提出了其对于参与北极事务的新主张,这标志着日本北极政策的进一步成熟。日本在诸多利用北极的国家中属于相对边缘化的地位,它对北极能源的声索并不体现在直接开采北极油气资源等方面,而是体现在开发并保障北极海域航道的通航之上。由于日本难以独立开展北极能源开发活动,因此它往往通过与北极国家建立合作关系来实现这一目的,例如尝试与俄罗斯建立政府高层北极会议、开展北极活动[30]并取得了较大进展——当前,俄日在北极海域合作开发液化天然气的项目业已成熟,这对于维护一个资源小国的能源安全来说,无疑具有战略意义。
目前,日本的北极战略呈现出以下四个特征:战略规划综合化、官民融合化、国际合作化和决策机制集权化。[31]从国际层面上讲,由于日本以俄罗斯为主要合作对象,因此作为“边缘地带”国家谋求进入北极开发与治理“核心圈”的尝试,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是否能够突破美日同盟的限制。
与日本类似,在没有广阔大陆和丰富资源作为依托的情况下,韩国的能源获取渠道正逐渐经历从“向西看”到“向北看”的历史性转变,即从之前的中东地区,逐渐转向距离更近、途经国家更少、合作关系更稳定的俄罗斯等北极圈穿过的国家,以降低运输和安全等成本。从2013年朴槿惠政府出台“新北方政策”(New Northern Policy)和《韩国北极政策的总体规划》,到《2015年北极政策执行计划》,再到2017年9月文在寅政府继续扩充“新北方政策”的外延即北极部分,并提出了“九桥战略规划”(9-Bridges)的推进思路,[32]韩国的北极资源开发谋划逐渐落到实处。该规划具备了更强的经济色彩和更为淡化的意识形态色彩,因此也更加接近合作对象俄罗斯的预期。值得注意的是,韩国希望通过韩国电力公司等国企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建设一条贯穿俄、朝、韩的能源输送路线,使其成为远东能源示范项目。当然,这种尝试最终能否成功,除了取决于突破美国对同盟体系束缚的程度之外,还受限于朝鲜半岛局势的演变前景。
(六)其他国家的北极政策与北极能源权益声索
2010年9月22日,于莫斯科召开的第一届“北极国际论坛”,标志着北极五国(美国、加拿大、俄罗斯、挪威和丹麦)机制的诞生,其成立之初的目的是:协调五国在北极的领土之争,但这一“俱乐部式”的高度排他性安排,使北极地区事实上已被此五国所占据,同时也是其他国家(甚至包括另三个北极国家即瑞典、芬兰和冰岛)插手北极事务的阻碍。因此,这一安排遭到了其他国家的强烈反对,由于这一机制内部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其运行也出现了较大问题。
挪威是最具政策影响力的北极国家之一,这与其“早开发、早利用”的历史有关。早在20世纪中叶,挪威就已通过科研等手段实施了北极领土扩张;冷战时期,它将北极政策嵌入国家安全战略中,并于1969年始,指定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开发北海石油资源,加速进入现代工业化国家行列;冷战结束后,挪威开始实施独立的北极政策,并具有涵盖军事、环保、渔业、科研等诸多领域的综合性特征。[33]近十几年来,挪威的北极政策进入强势扩张阶段,举全国之力开发高北地区,其间通过了2005年《北极地区的挑战和机遇》白皮书,2006年《挪威政府的高北战略》(挪威第一个系统全面的北极战略文件),2009年《北方新基石:挪威政府高北战略的下一步行动》[34]等文件。[35]挪威的北极政策特征包括:通过对俄“双轨”政策减轻地缘政治压力;强化科研能力,提升治理参与能力;发展尖端技术,实现油气开发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推动北极多边合作,提升国际政治影响力等。当前,构建与俄罗斯的北极合作关系是挪威北极战略最显著的特点。[36]
加拿大政府起步较晚,2009年7月26日发布的《加拿大北方战略:我们的北方、我们的遗产、我们的未来》,明确了其参与北极事务的四大目标:行使国家主权、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护环境遗产以及改善深化地区治理,该报告成为加拿大北极战略的标志性文件。[37]与美、俄、挪不同的是,加拿大对北极能源资源的开发和争夺热情并不高,一方面是碍于自身技术力量的薄弱和境内北极区能源蕴藏量不高的现实,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兼顾北极原住民的利益。
作为与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北极国家存在领土纠纷的小国,丹麦与加拿大的北极政策目标与实现手段相类似,不同的是,加拿大在某些事务上可以依附美国,而丹麦相对“孤立”,它在北极五国内部事务中的位置也被边缘化,这也为北极五国机制乃至八国机制的内部分裂埋下了隐患。
二 大国的北极博弈与其对中国北极能源利益维护的影响
从各国的北极政策和能源利益声索中,不难看出,能源只是大国争夺北极的众多目标之一,甚至是其北极政策的附属品,但是在近年来全球性能源安全问题日益凸显的背景下,各国形成了“开发-储备-贸易”的综合性能源安全政策惯性。在能源开发前景被普遍看好的北极,从科考活动到船舶航行和资源开采,再到军事演习,大国博弈一直贯穿其中。随着世界能源格局的深度调整与北极地区竞合关系的日益复杂化,北极能源的竞争将呈现愈加白热化的态势。地缘政治经济利益的角逐归根结底是大国之间的权力游戏。对于北极地区来说,大面积主权未定区域的存在,使其成为大国竞相抢占的战略高地。随着参与北极争夺主体的不断增加,大国的北极博弈也日趋激烈,并呈现出三个特点即:军事化持续升级、合作体系日趋复杂、能源开发愈发无序。与此同时,国家之间的冲突也一直贯穿始终,如加拿大与丹麦在汉斯小岛争端中频繁上演的“插旗”闹剧,使得北极地区的风险系数不断升高。
(一)大国的北极博弈特点
多层的国家实力、多元的政策重点与复杂的国家间关系,决定了任何国家都必须通过占领先机、整合力量与分化同盟等方式来谋求比较优势。这将造成三个结果:一是北冰洋沿岸国家希望借助地理位置、历史纽带等优势,通过直接的军事手段或制造争端来谋求对北极领土的永久性占有;二是北冰洋沿岸国家之间、北冰洋沿岸国家与“近北极国家”之间甚至“近北极国家”之间,往往通过抱团扎堆等形式,扩大北极影响力;三是在主权等属性界定尚不明朗的状态下,能源开采的成本较低,这只“无形的手”驱使着各国政企涌入北极,尽可能撬动北极能源开发的格局。如此一来,国家利益维护所提供的动能,助推着大国争相角逐北极领地。
1. 北极的军事化
长期以来,北极地区的军事化角逐以俄罗斯和美国为代表的国家之间展开,各种形式的军备竞赛和军事对峙此起彼伏,从未中断。作为北极地缘政治博弈的主角,俄美的北极关系构成一直是推动北极国家关系发展的主导型力量。[38]对于俄罗斯来说,北极冰层的融化,使战略大后方变成首当其冲的战略“大前门”,将自身直接暴露于北约的射程之内,是对其国家安全的极大挑战。
2001年,俄罗斯提出对北极的领土要求后,引爆了一轮北极领土声索的热潮。相应地,美国、加拿大、丹麦、挪威都组建了北极专门部队并强化在北极的训练和演习。随着北极地区军备竞赛的不断升温,2015年1月,俄北极战略司令部开始执勤,并与其他军兵种进行联合演练。2018年3月,英美举行了“冰原演习”,有效地检验了部队在严寒条件下的实战能力。同年9月底,俄罗斯北极特遣部队抵达科捷利内,进行“世界上最先进的海防导弹系统”——棱堡海防导弹系统的首次试射并获得成功;作为回应,10月,美国航母战斗群以杜鲁门号为旗舰,进入挪威海域参加“三叉戟”军演。这是自1991年小鹰号航母驶入北极圈以来,美国第二次进入俄“后花园”。当然,对于俄罗斯来说,北极军事存在和活动的目的是威慑,为了确保威慑有效,必须竭力避免冲突的发生。因此,俄罗斯在通过武力保障司法的手段谋求北极权益的同时,又借助安全机制的建立来规避冲突。[39]
除了与俄罗斯开展针锋相对的行动之外,美国还将中国视作其实施北极军事战略的“威胁”。2019年5月2日,美国军方出笼《中国军力报告》,臆想中国将扩大在北冰洋的军事存在,并在北极部署核潜艇,以应对核威慑。[40]这是“中国威胁论”的北极版本,也是美国加速提升北极军备的借口所在。
2. 北极合作体系的复杂化
一般来讲,一个国家的利益诉求是多元的,这就决定了其合作对象的选择是多样的。为了尽可能分享合作红利,一个国家往往倾向于与多个国家在多个领域进行合作,由此导致北极地区合作体系呈现出复杂的网络化格局。目前,北极地区存在着多个国际合作与管理体系,并呈现出“碎片化”的态势——一个国家同时参与多个合作体系,但其侧重点和目标却大相径庭。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些合作体系无一例外具有鲜明的“排他性”,即由于利益诉求的多样,导致没有任何一个合作体系或框架协议能够囊括各北极利益攸关方,甚至一些合作体系之间存在近似同盟体系之间的竞争。这是未来北极地区秩序塌陷的一个巨大风险点。
值得注意的是,北极的能源合作并未形成成熟机制,反而一直被情势变迁所左右。目前,除了北极理事会等政府间的合作机制发挥了较为有效的作用之外,北极经济理事会、北极海岸警卫队论坛等涉及经济社会发展、极地安全搜救等重要领域的机制都是独立运行的。[41]也就是说,合作机制的繁杂与主次不分,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国家合作的初衷。从时间上讲,北极合作一般由短期的访问或联合工程来推动,而缺乏战略性的长远布局;从内容上讲,大多数合作都是挂靠在政治和其他合作之下的“附属品”,并未上升到应有的位置。这种合作现状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在北极合作体系中,时间和空间上的复杂交错,使得国家之间因缺乏战略互信而付出巨大的时间和经济成本。
3. 北极能源开发的无序化
为抢占北极能源开发的先机,各国大都采用了联合开发的方式,以充分发挥比较优势,避免因某一块短板而使全局计划被搁置。在联合国有关法律法规和各国间的协议未能解决的范围内,各国往往倾向于以实力为后盾谋求占领先机,而这显然对小国是不利的。为了扭转劣势,小国往往将域外大国拉入己方阵营,以联合开发来维护自身权益。这样一来,北极地区的诸多活动更多具有鲜明的经济导向甚至军事导向。
与军事化相对应的是,北极国家都在竭力发展北极能源资源的开采和利用,而没有考虑可能发生的后果——特别是在主权未定区域。这种盲目抢占先机的短视思维,导致各国在上马大规模能源开采项目之前,并未经过充分的地质勘探、环保论证、技术评估以及市场渠道的调研,相关的保障工作也没有有效跟进。在大规模的资本、设备和人员涌入的情况下,北极地区的能源开发的速度已经远远超出了合理范畴,使本就脆弱的北极生态系统持续超负荷运转,无法有效完成自我修复。此外,无序的能源开发也带来了世界能源市场的供过于求,将使得世界能源贸易格局随之畸形,影响能源价格的稳定性,使一些以能源出口为主要创汇来源的国家特别是中东国家遭受较大损失,并将因此直面较大的国家安全风险。
(二)大国北极博弈对中国维护北极能源利益的负面影响
北极复杂的博弈形势使中国的北极能源利益维护囿于一系列的主客观因素。
其一,由于缺乏地缘与信息优势,中国无法深度融入现有的能源合作体系,也无法及时依据新情况采取相应政策措施。目前,只有北冰洋沿岸国家的实质性行动对北极权力格局形成了较大的影响力与塑造力,特别是一些永久占领性质的行为,如建设永久性的人工设施、派驻军队等。面对复杂的海冰情况、脆弱的生态环境、落后缺乏的补给设施等现实,[42]中国在北极地区所建设的科考设施,远远无法支撑长期的、复杂的北极行动,更无法及时准确搜集相关情报,并对这些情报进行分析研判,达到抓住机遇和规避风险的双重目的,因此会在大国进行北极权力分配或博弈的过程中错失宝贵的参与机会。在维护能源利益的问题上,中国将因位置和信息的不对等而付出较大的机会成本,且这种成本是无法单纯用经济数据来衡量的。在既有的竞合体系基本固化的前提下,中国的融入将意味着现存权利与利益格局的重大变动,且这种权力份额的变动无论是从短期还是长期来讲,都对现有的利益群体极为不利。因此,中国将同时面临既得利益者的排斥与先天的地缘与信息劣势,二者的复合作用将可能形成明显的马太效应,使中国逐步丧失应有的话语权与主动权。
其二,其他国家之间的优势互补,使中国在资金和技术上的优势不再凸显。以日本与韩国为例,从宏观上看,两个国家的北极战略规划较为清晰,且有具体的实施步骤与可靠的伙伴依托,受情势变迁的负面影响较小;从微观上看,二者的海洋产业体系较为健全,都拥有较为先进的海洋技术与丰富的海洋作业经验,能够在复杂的海上条件下实施海上工程建造、能源开采、远洋运输等作业。此外,两国政企出色的融资能力与对海外项目的风险管控能力,决定了其能够在合作机遇到来时,更快达成合作意向并付诸实施,且能够较好地保证后续合作的顺利开展。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虽因庞大的体量而在投资风险抵御能力等方面有着较强优势,但海外能源项目的投资经验缺乏、能源开发技术和经验等优势不足等客观现实,也导致其在“量”而非“质”的竞争中处于相对不利位置。对于在对外能源合作中更多重视经济效益的国家来说,中国的可选性无疑较差。如此一来,中国的比较优势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成了劣势,更容易在招标竞争中出现失利——许多国家出于股权甚至是经济主权和技术引进等方面的考量,更倾向于选择利用技术而非投资。特别是在“中国威胁论”被渲染的背景下,这种规律体现得更为明显。
其三,主要国家和区域组织对北极的利益诉求复杂化,导致中国难以掌握北极能源开发的主导权甚至是话语权。目前,中国在北极事务中的参与深度还远远不够,在北极治理演变的进程中,更多地扮演着“旁观者”的角色。而当前涉北极诸国“各执一词”与“各自为政”的现状,又在客观上削弱了中国作为体系参与者乃至重塑者的能力。撇开北极理事会等北极治理机制的排外性不谈,北冰洋沿岸国家与“域外”国家进行能源合作最主要的目的除了经济利益的获取之外,还有借助权势的考量,即通过利用中国等“域外”国家的经济政治影响力,来弥补自身在北极竞争中话语权的缺失。在这一进程中,中国等“域外”国家所扮演的角色更多的是策略性工具而非战略性伙伴。对于中国来说,在北极地区的复杂博弈形势下,形式上的而非实质上的合作“伙伴”的增多,也呈现出一定的负面效应——特别是在与存在竞争甚至敌对关系的国家同时进行合作的过程中,即使提供了大量公共产品,也将由于难以获得合作对象的信任而游离于话语体系之外。从目前来看,中国北极合作对象的单一性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与各国的北极合作更多停留在意向而非实施层面,这也是国家间政治与经济关系脱节、经济让位于政治的一个典型表现。
三 中国北极政策与能源合作:以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为例
世界能源革命的方兴未艾与能源格局的持续调整,决定了中国在北极的能源合作对象、模式和深度也将随之经历巨大变迁。中国与北极国家的能源合作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以大国为主,兼顾其他小国;二是以经济杠杆和科研合作而非军事手段挖掘能源合作潜力,实现政策对接;三是由声明到政策,再到行动,基本实现梯次推进。这种合作模式的选择,较充分地发挥了中国作为“近北极国家”的后发优势,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恶性竞争。特别是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的理念优势正逐步显现,政策的红利也在逐渐释放。
(一)中国的北极政策
中国对北极的重视和研究由来已久。早在1925年,中国就加入了《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条约》,实现了参与北极事务“零的突破”;1996年,中国成为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成员国,开始参与北极科研活动;1999年7~9月,中国政府组织了对北极地区的首次大规模综合科学考察——极地考察船“雪龙”号首航北极,对北极海洋、大气、生物、地质、渔业和生态环境等进行了综合考察;2004年7月,依据《斯瓦尔巴德条约》,中国在北极建立了第一个科考站“黄河站”。此后,中国在北极或单独或联合他国进行了多次以科考活动为代表的“低政治领域”活动。根据中国官方发布的数据,截至2017年年底,中国在北极地区已成功开展了八次北冰洋科学考察和14个年度的黄河站站基科学考察。[43]总体而言,中国的北极政策一直处于酝酿期和试探期,直到2017年6月,中国在首届联合国海洋可持续发展大会上,提出了构建“蓝色伙伴关系”的倡议,这标志着中国的北极政策主张由一般行动抽象为宏观概念。
2017年6月12日,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中国国家海洋局联合发布《“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提出重点建设“三条蓝色经济通道”的实施方案;[44]2018年1月,中国政府发布的《中国的北极政策》是中国第一部北极政策白皮书。该文件指出,北极治理需要各利益攸关方的参与和贡献,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愿本着“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基本原则抓住北极发展的历史性机遇,积极应对北极变化带来的挑战,共同认识北极、保护北极、利用北极和参与北极治理,积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涉北极合作,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北极的和平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特点在于:坚持科研先导,强调保护环境、主张合理利用、倡导依法治理和国际合作,致力于维护和平、安全、稳定的北极秩序。[45]具体到能源层面,中国则主张对北极油气、地热、风能等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以实现低碳发展。
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所推崇的原则,在政策思维层面给各国的北极合作提供了有益借鉴。“共商、共建、共享”的政策主张,为参与北极能源竞合的诸国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对接而非对冲、对话而非对抗、以双边或多边的政策磨合与优势互补,寻求最佳的利益契合点,进而避免零和博弈的发生。对中国而言,一方面,它将有力驳斥“中国北极威胁论”的荒谬说法,展现中国开放包容的北极能源合作姿态;另一方面,它也体现了中国作为“近北极国家”的合理自我定位以及在北极合作中对“予”与“取”的正确匹配。这既是中国外交智慧的集中展现,也是中国在北极合作中提供的最有价值的公共产品。
近年来,北极在中国能源进口格局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中国主张对北极能源的包容性合理开发利用,在多边磋商而非单边主导机制下进行有效合作,以实现共赢。这种开放合作而非排他对抗、合理开发而非掠夺攫取的政策导向,具有天然的理念优势,也将在众多北极利益攸关国家中取得最大公约数。在没有一个可以很好协调利益、规范行为的多边机制框架的现实境况下,中国北极政策从愿景到现实的转化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下,中国“冰上丝绸之路”的推进,虽然得到了不少北冰洋沿岸国家在原则性声明和协议中的支持,[46]但从落实效果来看,目前成熟的北极能源合作项目仅限于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亚马尔液化天然气(LNG)项目对接。
(二)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愿景与推进路径
中俄两国分别是最大的非北极国家和北极国家之一。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目标下,双方就北极问题存在诸多共同利益——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等北极合作可在纵深发展两国地方合作的同时强化国家层面的合作,并在北极治理等跨区域问题上为两国多边框架下的合作提供机遇。[47]
中俄两国在北极的合作由来已久并不断深化。2013 年,中远集团“永盛”轮获得了俄当局颁发的“极地通行许可证”,并于2015 年7 月再次航行东北航道;2016年,中俄两国进行了首次北极联合科考,对北冰洋俄专属经济区内楚科奇海和东西伯利亚海进行了综合调查。[48]“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如何将它与俄罗斯对北极和与远东地区的开发联系起来成为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近年来,中俄两国也在共同开发能源、开辟北极航道等问题上表现出相当的积极性。“冰上丝绸之路”这一概念一经提出,便得到了俄罗斯的积极响应。中国与俄罗斯在这一框架下开展了多层次、多领域的务实合作,其中已初见成效的是亚马尔液化项目。2017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了将北极海航道与“一带一路”相对接、开发“冰上丝绸之路”等构想,以能源贸易和基础设施建设为纽带,加快推动沿线和相关地区尽快走向发展快车道。[49]当前,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作为两国重点的能源合作项目,也是全球首例极地天然气勘探开发、液化、运输、销售一体化项目,完全建成投产后,预计该项目每年向中国提供约60亿立方米天然气。[50]两国还致力于加强和扩大极地科研和制造以及北极阿尔汉格尔斯克深水港建设和维护项目的合作,以形成具备规模效益的综合产业体系,与能源合作项目互为促进。
2019年6月5日,中俄两国元首决定,将两国关系提升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51]在此种形势下,中俄在“冰上丝绸之路”的合作,不仅成为双方特色议题与战略目标的成功对接,也象征着双边关系的巨大提升,这将有利于开启全球经济治理新模式,并可能重塑区域和全球大国竞合态势与格局。[52]从宏观上看,“冰上丝绸之路”的推进,将使北极国际合作机制的重塑成为可能,[53]在大国的带动下,促进北极合作的进一步深化;从微观上看,中俄的“冰上丝绸之路”合作有助于双方的利益实现——特别是在西方阵营围堵俄罗斯且俄综合实力日渐式微的背景下。
由上可知,“冰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将为巩固俄在北极的主权和存在增添巨大筹码,俄的立场与合作将有力助推“冰上丝绸之路”的深入推进。这种合作对象与内容的单一性,既给渴望“强国兴邦”的普京提供了丰富的外部资源支持,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中国的能源安全风险和北极能源合作协调成本。当前,中国在北极能源合作中的最大伙伴和最具潜力伙伴仍是俄罗斯,对俄来说中国的角色也同样如此,这一状态在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为了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中俄双方都愿意寻求一种以最低的成本来实现最大收益的合作理路,以推进“冰上丝绸之路”。
在 “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框架下,中俄推进“冰上丝绸之路”的建设路径,应包括以下两个维度:
第一,中国应将能源合作项目作为中俄“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抓手。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总体布局中,北向的合作具有对象单一、国家间关系发展稳定、合作基础较为深厚、安全环境良好等固有优势。中国在“冰上丝绸之路”的建设过程中,就可以节省大量协调和对接的成本。为了将这种优势较好地发挥出来,应重点打造“冰上丝绸之路”的大型旗舰项目,以与能源开发相关的配套基建为抓手,推动相关政策文件尽快落地。这种大倡议嵌套重点方向、重点方向嵌套重点工程的模式,将有助于形成较强的示范效应和带动力量,在向其他方向的沿线国家展示中国的实力与诚意的同时,拓展中国的能源进口渠道与交通运输路线,实现重点突破基础上的全面发展。这种策略选择,基于一个战略契合:当前乃至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北极开发环境将稳步向好且北极能源的开发将有增无减;而同样地,中国对能源的需求特别是天然气等清洁能源的需求将大幅增长;与此同时,俄罗斯作为中国在北极地区能源开发的最重要的“支点国家”,在对中国有重大的利益期待的同时,也愿意配合中国的发展战略。
第二,俄方应发挥“北极大国”的绝对优势,为中俄双方北极规划的对接整合资源。“冰上丝绸之路”是中俄两国在北极地区相向而行的重要体现,也是两国优势互补的重要依托。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形势下,作为在北极有着固有领土、军事优势和开发基础的国家,俄罗斯是毫无争议的“北极强国”。以此种实力为依托,在北冰洋沿岸国家范围内构建身份认同、整合优势资源,从而谋求撬动北极地区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成为俄罗斯北极战略实施的重要着力点。当然,作为一个开放型的合作倡议,“冰上丝绸之路”并不排斥其他任何国家的参与,只是在整合意愿、寻求共识的过程中,以俄罗斯为“组织者”或“协调人”,将能够最大限度地消除阻碍两国政策规划对接的阻力,从而形成较为稳定而有效的合作机制。虽然在国际形势和国家利益诉求发生变化的综合作用下,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合作发展并非呈线性,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相互依赖的逐步加深,双方互利友好的政策基调不会发生重大改变,北极地区资源整合的进程都将继续——只是时间与主导权掌握的问题。
四 中国北极能源安全面临的风险与应对
虽然中国自涉足北极以来,与各方都开展了一定合作,但风险与阻力的客观存在,限制了这种合作的深化。例如,作为北极理事会的观察员国,中国在承担诸多责任与义务的同时,却并未相应地享有相关的权利。[54]作为“非北极国家”或“近北极国家”,中国要想在复杂的北极博弈中赢得一席之地,就必须获得其他国家的身份认同——至少是默认,以减轻加入“北极俱乐部”的阻力,成为在北极立法、资源开发、交通运输等方面都享有一定话语权的国家。这就要求中国必须突出自身北极战略的普适性与包容性,在战略调整过程中实现与北极利益攸关方特别是北极国家的政策对接,同时竭力避免或降低战略对冲带来的负面影响。
(一)中国北极能源安全风险
从近年来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实践中可以看出,在“走出去”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属地管辖权和北极“朋友圈”规模的有限,以及历史和现实中规则等“软联通”的相对薄弱,中国的北极能源安全之虞一直存在。在北极能源利益的维护过程中,主导权的缺乏、合作对象与内容的单一、极地立法参与度的低位,是中国亟待破解的难题。
1. 能源开发的主导权之争
中国在北极的国家利益多为共享性利益,需要借助国际平台特别是与北极国家的合作才能实现。[55]由此,中国在北极能源安全战略的实施就逐渐形成一种“粘性”(stickiness),即任何政策主张的提出和实施,都离不开北极国家的支持或默许;任何能源项目的上马,也必然绕不开与北极国家的合作。
在中国的主张中,同南极地区一样,大部分北极地区作为“无主地”,是人类共同拥有的财产,因此所有国家都享有开采的权利。但从俄罗斯近年来采取的行动和发布的声明来看,很显然俄罗斯已经将北极大部分地区作为其“领海”甚至“内海”来进行管辖和开发,而不接受任何国家特别是非北极国家对于北极利益的声索。
俄罗斯参建“冰上丝绸之路”的愿景管理,既取决于俄北极经济的可持续性,也受制于欧亚地缘政治环境。[56]随着中俄能源开发合作的纵深发展,中国将获得更多的来自北方近邻的能源,而中国企业也将在俄罗斯能源开采中获得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这将带来能源的开采权和定价权的敏感问题。对于俄罗斯来说,在短期之内,无法实现与西方之间的关系缓和,特别是在将能源作为一种战略工具来对抗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同盟,那么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是否会出现能源这一武器不再行之有效?而对于中国来说,在参股北极能源开发的情况下,原有的中俄能源输送管线是否面临缩水的局面?且在中国掌握一定股权的情况下,是否存在中国将能源就近出口,而这将“违背”俄罗斯的战略意图?当前,俄罗斯虽然在积极推广国际合作的开发模式,但同时还要保持俄罗斯对北极地区石油和天然气开发及利润的高度控制。[57]
近年来,中国与俄罗斯呈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发展状态,即中国的强势崛起与“领军”意向,相比于俄罗斯勉强支撑的衰落,导致了一种国际地位的“位移”,使俄罗斯产生了不安全感。[58]这种政治上的猜忌,将可能加大俄对于中企参与能源开发的担忧甚至限制。
2. 合作对象与内容较为单一
中国北极能源合作的主要对象是俄罗斯,而中俄北极资源合作很大程度上只能在俄罗斯的主导下进行。[59]在俄罗斯的战略考量中,其与中国在北极开展的合作,是全面开发北极战略的助推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强途径。[60]归根结底,中国与任何国家在北极的能源合作,都是在服从合作对象的国家战略前提下进行的,这使得中国的合作对象与内容较为单一,且优势难以持续。
从合作对象上看,一方面,对象较为单一。北极国家之间存在着复杂的领土声索主张矛盾,这在一定程度上将北极圈的合作体系碎片化。而主权的排他性,使得中国无法同时在有主权矛盾的国家之间寻求合作,如此中国的合作伙伴数量就被限定在一定范围内,甚至可能不得不有所取舍,这将使中国陷入被孤立的窘境。另一方面,目前,中国的北极合作伙伴多为发达国家,中国的比较优势特别是长期的比较优势明显不足。北极国家选择与中国合作的原因,大多是希望通过借助中国的庞大市场、资金、技术等来实现优势互补,但中国的技术和资金优势并非独一无二,且面临技术转让或资金转移的风险。
从合作内容上看,中国与北极国家开展的主要是能源开发、加工合作,而能源贸易等利润较高的合作项目较为缺乏,这就导致成本与收益的匹配问题和市场话语权的掌握问题。有学者指出,在“可持续性”的原则下推动大项目模块化,坚持科学先导和技术支撑是推动中俄北极合作的基本路径。[61]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在北极的科研方面都投入了巨额成本,然而这种状况的长期维持,将使科技投入的边际成本递减,导致有能力开发的国家逐渐增多,而中国逐渐失去竞争优势;而基础设施投资和主权纠纷解决等边际成本的递增,将给中国的收益带来更多不确定性,且这种不确定性更多的是政治和安全层面而非经济层面。
3. 极地立法中话语权较弱甚至被排除在外
虽然中国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但是中国在掌握北极立法权方面力量极为薄弱,特别是在法规的强制执行条件和能力上与其他北极大国有很大差距。这归咎于北极立法的长期混乱,也源于联合国、北极理事会等组织发挥作用的有限性。
例如,俄罗斯对于北极立法就拥有较为突出的主导和执行力。从破冰船强制领航到许可证制度的变化,俄北方海航道法律规定不断变化——从1991年颁布的《北方海航道海路航行规则》,到2013年1月28日正式生效的《关于北方海航道水域商业航运的俄罗斯联邦特别法修正案》——俄对北方海航道定义和破冰船强制领航规则进行了调整,有进一步向国际开放的政策倾向。[62]这从侧面体现了俄对于北极立法的主导能力,而现实也证明了其较强的执行能力。自2019年开始,俄政府采取措施,着手修改1999年颁布的第1102号法令《关于外国军舰和其他国家非商用船只在俄罗斯联邦领海、内水、海军基地、军舰基地以及军港航行和停留规则》,欲对进入北极海航道的外国舰船加强管理,这也使得俄与西方在“航行自由”方面的矛盾更加表面化。[63]
此外,为维护北极地区的生态环境安全和船舶航行安全,国际海事组织(IMO)于2017年1月发布了《极地规则》(),对相关航行标准作出了强制规定。[64]然而,中国在这一规定的制定过程中几乎没有发挥任何影响力。当然,深入参与国际立法、深度融入北极治理体系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将更多受到国际规则的约束,将不得不在很多方面作出妥协。
(二)几点应对建议
笔者认为,要想实现“冰上丝绸之路”的行稳致远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中国北极能源安全,应寻找有力的理论支撑,丰富现有合作模式。相较于其他理论,道义现实主义的理论逻辑更有说服力,即: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中国必须寻求一种建立在二元理论基础上的战略路径,既强调物质力量的作用,也强调主观能动作用。[65]从宏观上讲,道义现实主义并不排斥“王道”而非“霸道”的合作,愿意提供公共产品并允许中小国家搭中国的便车。[66]作为一个在经济上处于较为弱势地位的国家,俄罗斯自然也有强烈的“搭便车”需求。当然,便车的搭乘必然建立在实质性的合作行动的基础之上,特别是让中国同样获益。在推进“冰上丝绸之路”、推动与北极国家能源合作的过程中,要想充分保障中国能源战略安全,不仅应当考量北极的政治军事博弈形势,还应当将北极能源开发的成本-收益纳入决策体系,在维护能源安全的基础上,尽可能降低能源安全护持的成本。
其一,继续推动在联合国框架内完善北极立法。对于中国来说,北极区域合作机制可以为“冰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提供保障与促进,也为北极航行保障、油气资源开发的法律依据、科学合作提供便利。[67]但受地理要素的限制,中国仅仅是北极理事会的观察员国,距离真正加入“北极俱乐部”显然还有一段距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应当将北极的有关概念扩大化,争取在联合国范围内解决北极国家之间的争端和北极立法问题,特别是推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细化和可操作化。不可否认,这一过程将是长期的、渐进的且需要多个国家的支持与配合。对此,有学者基于战略管理学中的“态势分析法”(SWOT)得出结论:中国当前宜采取机遇型战略,借助外部机遇来克服自身劣势,以实现向促进型战略的过渡。[68]
当然,这一立法的合法性与身份认同要想被接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笔者认为,在这一问题上的策略选择应遵循学术-政治或民间-官方的实施路径,即从低政治向高政治领域的逐步过渡,尽可能实现渐进式的融入,以最大程度降低相关国家的戒备和排斥心理。
其二,灵活运用政企结合模式,互为保障。“冰上丝绸之路”的顺利推进必须以政治共识为前提,以经济效益为可持续发展的保障。[69]中国与俄罗斯之间良好的政治关系,为实现能源合作提供了保障。对于俄罗斯来说,最现实的北极利益就是北极圈油气资源开发带来的经济利益和航运利益。[70]中企巨大的实力将使这种利益的实现成为可能。当然,在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中,中企应结合实际调整策略。在一些特殊的情形下,可以发挥企业的优势,如在格陵兰谋求从丹麦“渐进式独立”[71]的窗口期,中国应当更多通过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走出去”的方式,加强与格陵兰的经济关系,较有代表性的是2015年中国俊安公司以独资的形式接受伦敦矿业公司(London Mining)的伊苏华(Isua)铁矿项目。此外,还可以加强科研机构和高校等非官方机构与北极国家的合作,如在《加强国际北极科学合作协定》框架下,深化科研合作,推动形成产学研相结合的模式,发挥多方的综合优势,在破冰抗寒设备制造、天气预报、地质勘探技术装备等方面加强知识累积,保证科学技术先行。[72]
在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应坚持多领域投资、经济与其他效益并重的原则,通过发展北欧国家普遍关注的旅游产业投资与海洋生态产品贸易等,逐步扩展合作领域,特别是能源开发所涉及的交通运输、装备制造等行业,从而形成较为完整的合作产业链,使合作基础更加坚实。此外,还可以通过联合开展搜救行动等,在提升极地活动能力、积累相关经验的同时,更好树立本国政府和企业的形象。
其三,深化与涉北极国家的能源合作,形成辐射状合作体系。当前,中国应继续坚持“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的外交基本方针,在稳定轴心、密集辐射的基础上,借助成熟的合作平台与机制,发展与更多国家的合作。可以说,合作对象与内容都需要扩展。
在合作过程中,更多强调主导权或核心地位的实现,在能源勘探、开采、加工和贸易等各个环节,争取更大的话语权。当然,这要建立在中国阐明立场的基础上,即表明中国不会损害北极国家的领土、航线等主权利益和介入北极国家的纠纷,在北极诸国之间的争端中采取中立立场,以实现合作范围的尽可能扩大,即所谓的“多交朋友”。[73]此外,在合作过程中,应避免同质化倾向,与各国共同建立能源价格调整和保护机制,在面临制裁或国际能源价格出现波动时,能够形成较为稳定的能源开采和贸易量,保证稳定的能源价格,使北极的能源项目能够顺利运转。
在这一过程中,应特别注重与丹麦、挪威等北极国家的合作。在保持与日本、韩国等“近北极国家”基本相同政策主张以减轻这些国家疑虑的同时,应结合中国国情特别是“冰上丝绸之路”相关的政策,制定与各北极岛国之间的专门合作方案。这种方案,既要有共性,也要有个性,即尽可能立足于合作对象的诉求及优势和劣势,使合作更具有针对性与可行性,避免因同质化竞争而遭到排斥或因优势不足而被取代。应充分考虑到合作对象国的利益,特别是利益诉求的变化,比如,在诺瓦泰克公司受到西方制裁的情况下,正是中国资金的注入,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才得以如期顺利开展。[74]从更高层次上讲,除了培育资金优势之外,应当发挥理念与制度优势,以建构更高层次的吸引力,其中的核心要义就是要以求同存异的观念打造北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其四,加大对北极环境的保护力度。中国在推进“冰上丝绸之路”合作的同时,更不应忽视合作对象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社会效益等方面的需求。对于海洋有着天然感情与依赖性的海洋大国来说,其可持续发展的根基之一就在于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为此,在与政府、企业维持良好关系的同时,还应通过环保合作与公益等形式,做好高校、科研机构、非政府组织(NGO)甚至个人等的联系工作,以树立起中国政企的良好形象,减小潜在风险。
中国作为《斯瓦尔巴德条约》等政府间条约的缔约国,在享受条约规定权利的同时,也承担北极环保等义务。2013年,北极理事会通过《北极海洋石油污染预防与应对合作协定》,旨在守住北极生态环境底线。对于北极国家来说,北极环境的变迁,特别是冰面的融化和生物多样性的变化,甚至将会影响其国家安全。而作为非北极国家,保护好北极生态环境,本质上就是对北极国家特别是冰岛等受海平面上升和渔业资源增减影响较大国家的利益的尊重。为此,应开展中俄北极能源走廊海上污染治理等合作,[75]加强同绿色和平组织、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接触与合作,建立北极联合开发、科考等机构,对油类或其他危险物泄漏造成的严重污染、船舶破冰过程产生的噪声、船舶航行排放的污染物、通过船舶的压载水、船舶污底、货物等途径传播的外来物种入侵予以及时有效处理,[76]保证北极地区生态环境系统的健康运转。
环保是一个长期系统工程,对生态环境脆弱的北极来说更是如此。因此,对北极环境的保护应是一笔长线投资,其直接经济效益并不十分可观。在环保等领域,应充分借助合作对象国特别是西欧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经验优势,通过提供资金、资助科研、共建环保企业和项目等方式,在合作对象国树立起良好的公众形象。自然环境的保护是对北极原住民的尊重,也是社会文化习惯的一种表现,因此,应加强对原住民的社会文化调研,把“国之交在于民相亲”落到实处。[77]
五 结论
北极是资源的宝库,也是战略的要冲。近年来,北极环境变迁的逐步加快、各国极地活动能力的不断增强以及全球能源竞争的日益激烈,使北极成为各国关注和争夺的焦点区域。在大国的北极博弈过程中,北极的军事化色彩不断增强、合作体系日趋复杂化,能源开发也逐步陷入无序化。相比于美国、俄罗斯、日本、欧盟等主要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北极战略利益之争,中国以“冰上丝绸之路”为代表的北极政策具有更强包容性,有利于实现中国与北极国家的长期能源战略合作。这得益于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取得一定成果,这也为双方深入开展北极能源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在维护北极能源安全过程中,由于存在着能源开发的主导权之争、合作对象与内容较为单一、极地立法中话语权较弱等不利因素,导致中国的能源安全也面临较大风险。为此,笔者建议应当着重从推动在联合国框架内完善北极立法、灵活运用政企结合模式并互为保障、深化与涉北极国家的能源合作并形成辐射状合作体系、加大北极环保等四个方面开展工作。对于提倡构建“冰上丝绸之路”的中国来说,要想维护本国在北极的能源安全,就必须借助在北极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的力量,通过分享理念、设置议题、促成合作等方式,实现对北极事务的介入。这既有助于规避因恶性竞争带来的战略透支,也将为增强中国的北极能源开发话语权奠定基础。
当下,在大国争相在北极地区进行“圈地运动”的背后,是中国作为“后来者”与“非本土”的身份被接纳的突破困境,特别是在“不结盟”的政策基调主导下,谋求广泛合作的理论建构和开局实现等难题,成为必须跨过的门槛。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方案”——通过打造“冰上丝绸之路”推进包括能源在内的北极合作——是目前解决北极争端的最有效路径之一。毕竟,随着大国力量在北极的集聚、分化与组合,北极问题必将走上一条广泛的全球化治理的道路。[78]这种全球化治理模式将树立开放合作共赢的理念,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以及包容务实的多层次合作,最终实现构建北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1]针对“大国”这一概念,有必要作出三点说明:一是从体量和实力上来看,欧盟作为重要的国家联合体和国际行为体,其影响力应与美俄等其他大国等量齐观;二是本文将在北极圈以内的国家,即在北极领土主权等方面有着重要权益主张的“小国”视作“大国”,如挪威、冰岛等;三是在北极开发中起步较早并在当前对北极事务较为关注的“近北极国家”,也被本文视作“大国”,如韩国等。总而言之,“大国”是基于地缘位置、综合实力和意愿三者综合考量而得出的定义。当然,这一定义并非具有普适性,其原因在于笔者案例选取的倾向性。
[2] 也有论者从宏观概念入手,将中国视为“大北极”国家网络中的成员之一,参见李振福:《大北极国家网络及中国的大北极战略研究》,载《东北亚论坛》2015年第2期,第31-44页。
[3] 卢景美、邵滋军等:《北极圈油气资源潜力分析》,载《资源与产业》2010年第4期,第29-33页。
[4] M. K. Verma, L. P. White, D. L. Gautier, “Engineering and Economics of the USGS Circum-Arctic Oil and Gas Resource Appraisal (CARA) Project,” Open-File Report, 2008, https://pubs. usgs.gov/of/2008/1193/downloads/OF08-1193_508.pdf.
[5] USGS, “The 2008 Circum-Arctic Resource Appraisal,” https://pubs.er.usgs.gov/publication/ pp1824; D. L. Gautier, K. J. Bird, R. R. Charpentier, et al., “Chapter 9 Oil and Gas Resource Potential North of The Arctic Circle,”, Vol. 35, No. 1, 2011, pp. 151-161.
[6]张丽娟、许文:《主要国家北极研发政策分析》,载《全球科技经济瞭望》2017年第3期,第8-13页。
[7]目前,北极地区国际治理模式包括:1996年成立的由北极八国组成的北极理事会、1993年成立的由俄罗斯、丹麦、冰岛、芬兰、瑞典和欧盟委员会组成的巴伦支海欧洲-北极理事会、1990年成立的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等,但这些治理模式显然并未囊括所有的北极利益攸关方。
[8]孙凯:《奥巴马政府的北极政策及其走向》,载《国际论坛》2013年第5期,第55-60页。
[9]NOAA系指美国国家大气与海洋管理局。
[10]参见“Navy Arctic Roadmap,” http://www.navy.mil/navydata/documents/USN_artic_roadmap. pdf; “United States Coast Guard Arctic Strategy,” http://www.uscg.mil/ seniorleadership/DOCS/CG_ Arctic_Strategy.pdf; “Department of Defense Arctic Strategy,” http://www.defense.gov/Portals/1/ Documents/pubs/2013_Arctic_Strategy.pdf; “Findings from Select Federal Reports,” https://www. 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docs/National_Security_Implicati ons_of_Changing_ Climate_Final_ 051915.pdf; “Interagency Arctic Research Policy Committee 2015 Biennial Report,” https://www. 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microsites/ostp/ NSTC/iarpc-biennial-final-2015-low.pdf; “Changing Conditions in the Arctic Strategic Action Plan Full Content Outline,” https://www.whitehouse.gov/sites/ default/files/microsites/ceq/sap_8_arctic_full_content_outline_06-02-11_clean.pdf; “NOAA’s Arctic Vision & Strategy,” http://www.arctic.noaa.gov/docs/NOAAArctic_V_S_2011.pdf; The White House, “Arctic Research Plan,” FY2013-2017, 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microites/ostp/ 2013_arctic_research_ plan.pdf。
[11]杨松霖:《特朗普政府的北极政策:内外环境与发展走向》,载《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8年第1期,第88-101页。
[12]《美专家建议:加强美国第四海岸战略》,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www.cssn.cn/sf/bwsf_lllwz/ 201704/t20170413_3485435.shtml。
[13]杨松霖:《特朗普政府的北极政策》,载《国际研究参考》2018年第1期,第1-9页。
[14] “Report to Congres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rctic Strategy,” https://media.defense.gov/2019/ Jun/06/2002141657/-1/-1/1/2019-DOD-ARCTIC-STRATEGY.PDF.
[15] “New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rctic Strategy Sees Growing Uncertainty and Tension in Region,” https://www.highnorthnews.com/en/new-us-department-defense-arctic-strategy-sees-growing- uncertainty-and-tension-region.
[16]王淑玲、姜重昕、金玺:《北极的战略意义及油气资源开发》,载《中国矿业》2018年第1期,第21页。
[17]刘欢:《中俄北极合作研究》,载《西伯利亚研究》2018年第2期,第38-41页。
[18]《俄罗斯批准北极地区发展政策》,中国新闻网,2020年3月10日,http://www.chinanews. com/gj/2020/03-10/9119644.shtml。
[19]郭培清、孙凯:《北极理事会的“努克标准”和中国的北极参与之路》,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12期,第118-139页。
[20] N. Hong, “Arctic Energy: Pathway to Conflict or Cooperation in the High North?” May 31, 2011, http://www.ensec.org/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id=310:arctic-energy-pathway-to-conflict-or-cooperation-in-the-high-north&Itemid=375; Katarzyna Zysk, “Russia’s Arctic Strategy: Ambitions and Constraints,”Vol. 57, No. 2, 2010, pp. 104-115.
[21]参见《俄罗斯政府拨款“穿越北极-2019”科考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俄罗斯联邦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http://ru.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903/20190302839911.shtml。
[22]《俄罗斯:抓住北极机遇强化军事存在》,中新网,http://www.chinanews.com/gj/2019/ 04-12/8806780.shtml。
[23]同样,作为一个成员高度重合的区域组织,北约也高度关注北极,但更多停留在军事层面。较有代表性的是其于2017年10月发布的报告,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动,包括在北约领土周边的挑衅性军事活动”,强调威慑力和加强北约防御姿态的必要性,并称北约盟国也应该提高北极的局势意识,可以而且应该以非挑衅的方式做到这一点,即无需在北部地区部署军事资产。参见“Nato and Security in The Arctic,” https://www.nato-pa.int/download-file?filename=sites/ default/files/2017-11/2017%20-%20172%20PCTR%2017%20E%20rev.1%20fin%20-%20NATO%20AND%20SECURITY%20IN%20THE%20ARCTIC.pdf。此外,北约还宣称:盟国将作出一致努力,帮助美国在北极以“平衡作用”拒绝俄罗斯人的进入,并阻止其声索国际公认的公海。参见“The NATO Alliance’s Role in Arctic Security,” https://www.maritime-executive.com/editorials/the-nato- alliance-s-role-in-arctic-security。
[24] Kathrin Keil, “The EU in the Arctic ‘Game’ -The Concert of Arctic Actors and the EU’s Newcomer Role,” http://www.ecprnet.eu/databases/conferences/papers/209.pdf; Timo Koivurova, “The Present and Future Competen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in The Arctic,”, Vol. 48,No. 4, 2011, pp. 361-371.
[25]程保志:《欧盟北极政策实践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载《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第87-92页。
[26]程保志:《北极治理与欧美政策实践的新发展》,载《欧洲研究》2013年第6期,第46-50页。
[27] “Walking on Thin Ice: A Balanced Arctic Strategy for the EU,” https://ec.europa.eu/epsc/sites/ epsc/files/epsc_strategic_note_issue31_arctic_strategy.pdf.
[28]参见伊民:《英国发布更新版北极政策框架》,http://www.oceanol.com/jidi/201804/27/ c76554.html。
[29]参见“Germany’s Arctic Policy Guidelines,” https://www.auswaertiges-amt.de/blob/2240002/ eb0b681be9415118ca87bc8e215c0cf4/190821-arktisleitlinien-download-data.pdf。
[30]刘乃忠:《日本北极战略及中国借鉴》,载《南海法学》2017年第6期,第102-107页。
[31]邹鑫:《试析日本北极战略新态势》,载《国际研究参考》2019年第4期,第15-20页。
[32]“九桥战略规划”即韩俄合作的九大领域:天然气、铁路、港湾、电力、北极航道、造船、就业、农业和水产。参见《韩国北方经济合作委员会首开会议确定俄九大领域合作规划》,中韩海洋科学共同研究中心网站,http://www.ckjorc.org/cn/cnindex_newshow.do?id=2676。
[33]赵宁宁:《小国家大格局:挪威北极战略评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7年第3期,第108-121页。
[34]此为2006年战略的更新版本。
[35]廖星宇:《挪威的北极战略》,载《中国海洋报》2014年5月22日,第4版;孙超:《不断演变与发展的挪威北极政策》,载《中国海洋报》2016年10月26日,第4版。
[36]参见陈思静:《北极能源共同开发:现状、特点与中国的参与》,载《资源开发与市场》2018年第8期,第1099-1104页。
[37]唐小松、尹铮:《加拿大北极外交政策及对中国的启示》,载《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第5-11页。
[38]李振福、彭琰:《“冰上丝绸之路”与大北极网络:作用、演化及中国策略》,载《东北亚经济研究》2018年第5期,第9页。
[39] [俄] 弗·费·别切利察:《俄罗斯北极战略的特点及其影响》,赵印译,载《边疆经济与文化》2018年第2期,第19-21页。
[40]陆忠伟:《谁在给北极披战袍?》,载《文汇报》2019年5月11日,第5版。
[41]张耀:《“冰上丝路”能否为北极合作确立新方向?》,载《解放日报》2019年3月28日。
[42]罗英杰:《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成果与挑战》,载《世界知识》2019年第3期,第52-53页。
[43]参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http://www.gov.cn/xinwen/2018-01/26/ content_5260891.htm。
[44]三条蓝色经济通道指:以中国沿海经济带为支撑,连接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经南海向西进入印度洋,衔接中巴、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共建中国-印度洋-非洲-地中海蓝色经济通道;经南海向南进入太平洋,共建中国-大洋洲-南太平洋蓝色经济通道;积极推动共建经北冰洋连接欧洲的蓝色经济通道。参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海洋局联合发布:《“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6/20/c_1121176743.htm。
[45]参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http://www.gov.cn/xinwen/2018-01/26/ content_5260891.htm。
[46]比如:2013年12月,中国-北欧北极研究中心在上海成立。该中心是中国和北欧开展北极研究学术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将围绕北欧北极以及国际北极热点和重大问题,开展北极气候变化、北极资源、航运和经济合作、北极政策与立法等方向的合作研究和国际交流。参见姜巍:《环北极国家基础设施投资机遇与中国策略》,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年第11期,第50-59页。近年来,挪威政府也表达了与中国合作的意向,但主要停留在口头层面和旅游领域;再如,中美在北极领域的合作主要依托在北极理事会的框架之下,且多为科考、航运、气候变化、北极航道等“低政治”领域合作,参见潘敏、徐理灵:《中美北极合作:制度、领域和方式》,载《太平洋学报》2016年第12期,第87-94页。此外,2017年,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芬兰,芬兰总统绍利·尼尼斯托(Sauli Niinisto)表示希望深化双方在经贸投资、创新、环保、北极事务等领域和“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参见《北极开发:中国或牵手芬兰》,欧洲时报网,http://www.oushinet.com/ouzhong/ouzhongnews/20170331/259278.html;孙凯、吴昊:《芬兰北极政策的战略规划与未来走向》,载《国际论坛》2017年第4期,第19-23页。但中国与这些国家正在开展或计划开展的项目多属于“二轨外交”即非官方合作项目。
[47]白佳玉、冯蔚蔚:《以深化新型大国关系为目标的中俄合作发展探究——从“冰上丝绸之路”到“蓝色伙伴关系”》,载《太平洋学报》2019年第4期,第53-63页。
[48]《中俄首次北极联科考圆满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ov.防大学cn/xinwen/2016-10/12/content_5117872.htm。
[49]《丝路基金与诺瓦泰克签署关于俄罗斯亚马尔液化天然气一体化项目的交易协议》,http://www.silkroadfund.com.cn/cnweb/19930/19938/31795/index.html。
[50]刘欢:《中俄北极合作研究》,载《西伯利亚研究》2018年第2期,第38-41页。
[51]《中俄关系将提升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央视网,http://news. cctv.com/2019/06/05/ARTIvYCIJCJiuY7tmd6A6Ecj190605.shtml。
[52]关雪凌、杨博、刘漫与:《“冰上丝绸之路”与中俄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探索》,载《东北亚学刊》2019年第3期,第30-42页。
[53]谢晓光等:《“冰上丝绸之路”建设中北极国际合作机制的重塑》,载《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第13-25页。
[54]郭培清、孙凯:《北极理事会的“努克标准”和中国的北极参与之路》,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12期,第127页。
[55] [俄] 古尔巴诺娃·娜塔丽娅:《21世纪冰上丝绸之路:中俄北极航道战略对接研究》,载《东北亚经济研究》2017年第4期,第83-99页。
[56]肖洋:《俄罗斯参建“冰上丝绸之路”的战略动因与愿景展望》,载《和平与发展》2018年第6期,第107页。
[57]王琦、石莉、万芳芳:《浅析俄罗斯北极战略中的关键因素》,载《极地研究》2013年第2期,第176-184页。
[58]刘德斌:《中俄关系与欧亚变局》,载《东北亚论坛》2017年第2期,第9页。
[59]孙凯、王晨光:《国家利益视角下的中俄北极合作》,载《东北亚论坛》2014年第6期,第26-34页。
[60]赵隆:《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背景、制约因素与可行路径》,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8年第2期,第106-120页。
[61]赵隆:《中俄北极可持续发展合作:挑战与路径》,载《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4期,第49-67页。
[62]张侠:《从破冰船强制领航到许可证制度——俄罗斯北方海航道法律新变化分析》,载《极地研究》2014年第2期,第268-275页。
[63]刘锋:《俄罗斯对外国船只使用北方海航道加强管理》,载《世界知识》2019年第9期。
[64]《在极地水域运营的船舶采用国际安全守则(极地代码)》,http://www.imo.org/en/MediaCentre/HotTopics/polar/Pages/default.aspx。
[65]阎学通、张旗:《道义现实主义与中国的崛起战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4页。
[66]阎学通、张旗:《道义现实主义与中国的崛起战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6页。
[67]夏立平、谢茜:《北极区域合作机制与“冰上丝绸之路”》,载《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第48-59页。
[68]张木进、王晨光:《中国建设“冰上丝绸之路”的战略选择——基于“态势分析法”(SWOT)的分析》,载《和平与发展》2018年第4期,第111-125页。
[69]阮建平:《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冰上丝绸之路”倡议》,载《海洋开发与管理》2017年第11期,第3-9页。
[70]肖洋:《俄罗斯的北极战略与中俄北极合作》,载《当代世界》2015年第11期,第72页。
[71]肖洋:《“冰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支点——格陵兰独立化及其地缘价值》,载《和平与发展》2017年第6期,第108-123页。
[72]杨剑:《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国际环境及应对》,载《学术前沿》2018年第11期,第13-23页。
[73]胡鞍钢、张新、张巍:《开发“一带一路一道(北极航道)”建设的战略内涵与构想》,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第15-22页。
[74]胡丽玲:《冰上丝绸之路视域下中俄北极油气资源开发合作》,载《西伯利亚研究》2018年第4期,第28-32页。
[75]肖洋:《中俄共建“北极能源走廊”:战略支点与推进理路》,载《东北亚论坛》2016年第5期,第109-117页。
[76]李振福等:《中俄北极合作走廊建设构想》,载《东北亚论坛》2017年第1期,第53-63页。
[77]郭培清、宋晗:《“新北方政策”下的韩俄远东——北极合作及对中国启示》,载《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8期,第1-12页。
[78]李振福、彭琰:《“冰上丝绸之路”与大北极网络:作用、演化及中国策略》,载《东北亚经济研究》2018年第5期,第5-20页。
罗英杰,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李飞,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北京邮编:100091)。
10.14093/j.cnki.cn10-1132/d.2020.02.005
D815.5; D81; F416.2; F166.2
A
2095-574X(2020)02-0091-25
2019-06-04】
2020-03-12】
*本文是2019年度国际关系学院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创新科研项目“冰上丝绸之路研究”(项目编号:3262019T58)的阶段性成果。特别感谢《国际安全研究》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深刻、中肯的修改意见。文中错漏之处由笔者负责。
【责任编辑:苏娟】
————不可再生能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