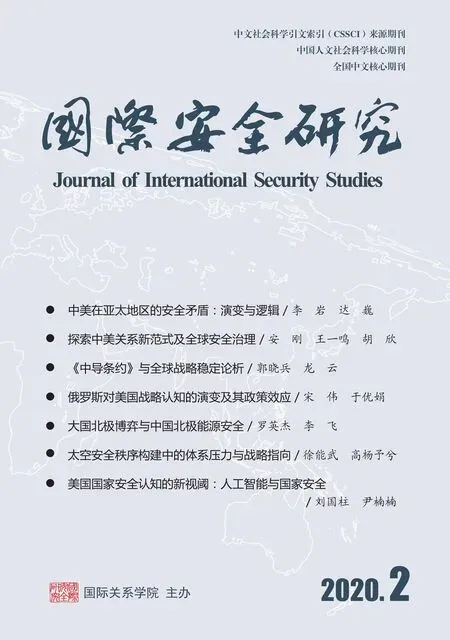探索中美关系新范式及全球安全治理*
安 刚 王一鸣 胡 欣
安全理论
探索中美关系新范式及全球安全治理*
安 刚 王一鸣 胡 欣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对华战略定位出现全方位负面趋向,由“接触”向“规锁”的转型不断加深。作为当今国际体系中的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两国关系正在形成战略竞争日益突出的新态势。中美经贸摩擦的出现和深化表明,经贸合作作为两国关系的传统“压舱石”,在单独应对战略竞争“新态势”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有限。为有效阻止“新态势”向全面对抗与冲突方向演变,中美亟须重新定位、处理和管控彼此关系的“新范式”。包括全球安全治理在内的全球治理架构为中美战略博弈与权势平衡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制度体系。通过明确战略竞争边界、构建对话协调平台,有效借助第三方力量等,中美的理性博弈、积极合作能够得到有效推动,并直接带来全球安全治理在观念、制度、模式等方面的变革。这不仅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愿望,也是全球治理健全发展的需要。但确立“新范式”有待解决的一大问题是,经贸合作作为两国关系“压舱石”的作用已经不稳,需要探索新的“压舱石”,全球安全治理合作在此方面的作用是不够的。未来中美关系的首要特点是战略竞争,新的“压舱石”可以通过权力博弈建立某种相对稳定的机制架构,最终以大国权势平衡的方式来打造。
中美关系;大国竞争;中美关系新范式;全球安全治理
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打着“美国优先”旗号,全面推行保守主义的对外政策,将战略重点从反恐调整至大国竞争,宣告中国为美国首要“战略竞争对手”,出台一系列旨在压制中国崛起势头和发展潜力的措施,挑起一场全方位的博弈,将中美关系推入战略“竞争的新时代”。美国对华政策的这一调整并非始于特朗普政府,根源在于中国的加速崛起及美国面对这一历史性现象所产生的战略焦虑和恐慌。
一 中美关系正在生成新态势
在基辛格看来,国际秩序的重塑问题是对当代政治家的“终极考验”。[1]就已经迈入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而言,这种考验的影响力是巨大的,“类似中美经贸摩擦这样的事件足以生成比毁掉欧洲的世界大战威力更大的重塑效应”,[2]未来国际秩序的稳定性和经济全球化的延续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和美国将如何共存。
(一)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关系是国际体系难以逾越的结构性樊篱
按照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提出的命题:“由于不同社会的发展速度不均衡以及技术突破和组织形式变革对不同社会的优势偏好,世界大国的相对实力并非一成不变”。[3]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以来的国际关系发展史深刻表明,这种大国实力的相对变化、循环往复是推动国际体系更迭、国际秩序变迁和国家间关系调整重塑的主要动力源。按照现实主义理论,国际关系的本质就是国家间争夺权势的斗争,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永续博弈是这一过程的基本样态。[4]在该理论的重要奠基人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看来,国家对权力的无一例外的追逐导致冲突和战争,当守成大国实力下降、新兴大国实力增强时,战争注定爆发。由于每个国家在不同时期内经济增长速率并不总是保持平衡,因而那些实力快速增长的新兴大国寻求与其不断上升的实力相匹配的权力地位和收益分配。[5]历史上,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执着于打破凡尔赛体系,日本处心积虑突围华盛顿体系都是典型案例。按照现实主义理论中最具影响力的结构现实主义观点,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不过是分布在国际关系体系中的两个单元,它们之间的竞逐博弈关系是结构赋予的一种客观必然,国家之所以陷入冲突乃是出于无可奈何的安全困境。“国家无法知道它们是否已经得到了足够的安全,但它们却知道一件事情:一个拥有力量的国家比一个没有力量的国家要更安全”。[6]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爆发的冲突主要源于国家对彼此战略意图不够确定,新兴大国寻求增强自身军事实力也许只是出于防御目的,但这种举动在守成大国看来,却是新兴大国意图颠覆世界秩序和国际体系的开始。在这种意识的指引下,以审慎和节制为特点的战略目标往往会无限扩大,从保持制衡转向追求普遍的霸权,从相对安全转向绝对安全,并最终转向霍布斯式的绝对困境。
在现实主义者眼里,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冲突和战争源自一种深刻的宿命论,只能通过一较高下实现权力的更迭,存在被先验注定的“修昔底德陷阱”。从历史上看也的确如此,例如英西海战、拿破仑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先后使得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树立了各自的战后霸主地位。维也纳体系的失败使得均势论在维护既有国际体系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彻底破灭,新旧势力的历史进退场只能以激烈方式进行。然而历史在今天不可能被简单复制。其一,伴随着全球化体系、国际制度与国际规范的发展,国家间相互依存的层次和程度在不断加深,各政治行为体之间的结构关系深刻交织、极其复杂,无法用简单的敌我二元关系予以说明。其二,成熟的外交和危机处理机制可以更清晰准确地传递政治信息,由错误认知导致的安全困境不一定必然出现。结构现实主义始终相信,只要各国明晰自身维护既有体系的基本意图,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还是能够实现权力和平转移的:“尽管所有革命性的国家都是不满于现状的,但不是所有不满的国家都是革命性的……关键在于准确区分仅仅在现存秩序内寻求变化的、目的有限的修正主义国家和目的在于推翻体系的革命性大国”。[7]其三,核武器以及人工智能军事应用、超高音速武器等的出现使战争的性质发生异变,战争已不再如旧时代那样是权力博弈的唯一工具。当代大国政治更为注重经济文化、盟友体系、国际制度、国际组织等不同层次的影响力构建,战争几乎沦为最后选项。综上,在当今世界的环境里,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如果相互把握得当,是无须通过战争一决高下的,更简单易行的办法是保持欲望的节制审慎和对权力的认同敬畏,通过和平共存、合作治理、互利共赢实现权力的和平合理再分配。
(二)二战后美国对华战略观与安全观的理念嬗变
二战后,美国对华战略观、安全观的理念嬗变完美展现了中美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是如何逐步生成的:
第一阶段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中美建交(1945~1979年)。这一阶段美国对华战略的深层思考从“谁丢失了中国”发展至“新中国是谁”,完成了对中国“体系敌对国”的身份界定。二战甫一结束,美国希望将中国纳入西方民主国家阵营,计划通过扶蒋反共将中国塑造为与苏联对抗的战略前沿。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彻底放弃这一意图,按照美苏结构性对抗的大的战略布局将中国由朋友转变为敌人。冷战初期,中国台湾地区作为美国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自由前哨”存在,中国则被美国视为苏联权势在亚洲“可靠的战略延伸”。这一时期美对华战略观、安全观的核心特征是完全敌视、拒绝接触,中国始终位于美国遏制战略亚洲包围圈核心位置。
第二阶段是从中美建交到冷战结束(1979~1991年)。在美苏冷战对抗最高峰的20世纪70年代,由于越南战争、石油危机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内部瓦解,美国在军事、安全上处于劣势,与此同时中苏关系出现严重裂痕,美借机开始考虑重塑中美俄三角关系,利用中国制衡苏联。由于中美战略利益出现趋同,美国开始调整对中国的身份认定和战略、安全观念,直接结果是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签署和发表,横亘于两国安全困境中心的台湾问题出现和平解决的曙光。这一时期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后调整工作重心、搭建经济基础的关键时期,美国放松了对中国的遏制,一定程度上对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建构周边地缘环境等战略性质的修正与调整给予默认,客观上对中国快速发展经济、恢复壮大国力起到助推作用。
第三阶段是冷战结束后至今(1991年至今)。这一阶段是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国力快速崛起的时期,伴随对这一现状的不同认知和判断,美国历届政府的对华战略观、安全观经历了多轮起落。克林顿政府早期,提出国家安全战略三个核心目标:增强美国安全、促进美国经济繁荣、促进海外民主与人权,强调继续在世界上发挥强有力的领导作用,在美国的核心利益地区确保和平稳定,扩大自由市场和民主板块范围。相应的,克林顿政府判断中国会跟随苏联出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崩解”,因此在执政之初对华主要考虑是“以压促变”,迫使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以经济市场化带动政治多元化,最终以西方民主和人权标准演变和改造中国。这一战略失败后,克林顿迅速将方向调整为“接触”,认为“如果我们同中国接触而不是自我孤立就可能影响中国选择的道路。”[8]在这一战略引导下,美国对中国突破经济封锁、融入国际市场体系给予支持,并在台湾问题上实施“模糊战略”,并不明确在中国台湾海峡两岸双方之间就安全问题选边站队。此时的美国坐享冷战胜利后的“历史假期”,对自身拥有绝对自信,尚未将中国界定为“挑战者”。
小布什执政后,美国新保守主义势力得势,国家安全观也相应调整。其根本判断在于,冷战后的世界依然是一个“没有结束危险和混乱的世界,是靠强权而非法律来治理的世界”。[9]美国对外政策由此前过度关注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取向问题,转向重新聚焦盟友体系和军事安全。在对中国的判断上,小布什一上台就埋葬了克林顿政府提出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将中国定义为“可与美国相匹敌的战略竞争者”,实行“预防性遏制”;与此同时,大力推动对台军售、宣布保护台湾地区,甚至把中国列为“潜在核打击对象”。但这一剧烈转向维系时间较短,在2001年九一一事件发生后被“锁进文件柜”。2002年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恐怖主义列为首要威胁,要求实施国防转型,积极发展军力,威慑和击败任何可能的对手和威胁,确保美国的全球利益和霸权地位。由此,小布什政府对中国的定位也调整为“利益攸关方”,逐步转向推动中国接受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要求中国“负责任”,作体系中的“现状国”而非“修正国”。
奥巴马时期,美国再次作出重大调整。201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次将全球共同危险置于地缘政治博弈之上,同时判定美国面对的恐怖主义威胁正在下降。此后,奥巴马政府在全球范围内实施“有限权势”和战略紧缩,明确推动减少海外驻军,同时将战略重心转向亚洲,推行“亚太再平衡”,并通过商签《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多项双边安全协定形成以经济、政治、安全、价值观为支柱的全体系性亚太战略,对中国的战略提防和限制在奥巴马第二任期大幅提升。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之后,“修昔底德陷阱”的提法开始在美国战略界流行,而中国同期提出的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议始终无法得到奥巴马政府充分认同。美方声称乐见中国发挥“负责任的领导作用”,但前提是中国必须与美国一道发挥作用,遵守各种国际规范,并与美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保持一致。可以说,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对守成大国美国的“权势冲击”已经开始引发美国政界、学界的忧思,并深刻影响了美国对华战略观、安全观和外交政策的发展演变。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政府先后发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和《核态势评估》报告等系列战略文件,自九一一事件以来首次把美国的战略目标从打击恐怖主义回调至聚焦大国竞争博弈,明确将中国和俄罗斯定义为“战略竞争者”和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大国”,位列美国三大类别战略挑战之首(后两类分别为伊朗、朝鲜等“流氓国家”和国际恐怖主义),而在“战略竞争者”当中,中国又排在俄罗斯之前,这就为美国从根本上调整对华战略提供了理念基础。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先后于2018年10月4日和2019年10月24日在位于华盛顿的哈德森研究所、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发表两篇对华政策演讲,称中国是美国的“战略和经济对手”,特朗普政府将在对华竞争方面坚持到底。依循白宫确立的基调和方向,美国各政府部门、强力机构和战略智库,纷纷出台针对中国的部门政策和报告,[10]逐渐形成“全政府的”战略竞争态势。美国国务院甚至直接研拟“X报告”并从文明冲突视角解读美国与中国的矛盾,说明美国官方已开始为对华战略调整搭建理论架构。[11]
在实际操作层面,以2018年初特朗普政府挑起的“贸易战”为先导,经贸摩擦被泛化,美方在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高新技术等领域对中国实施压制。强化对中资企业在美投资的审核检查,实施对中兴、华为等中国企业的制裁封锁,推动关键领域特别是国防产业对华“脱钩”,“技术冷战”事实展开。搭建并实化“印太战略”框架,以“离岸制衡”为核心理念大力优化在中国周边的直接战略和军事部署,以美、日、印、澳四国机制为轴心重整印太地区的盟友伙伴体系,以美国盟友版互联互通和数字经济合作对冲“一带一路”建设,以直接军事和政治介入搅浑南海、台海局势,由“战略模糊”向“战略清晰”转化,加紧酝酿更激烈的地缘政治较量。美国在香港、新疆问题上不断加强染指,反复挑战中国底线;重新渲染意识形态对立,污蔑中国为“技术威权主义”,“干预渗透”美国国内政治,“所构成的‘威胁’比俄罗斯更大”,[12]针对赴美访学中国学者和在美工作华裔精英进行专项调查。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等方面强化议题设置,绕开世界贸易组织搭建以美国为中心、奉行联盟价值标准、植入“毒丸条款”[13]以排斥中国利益的区域经济安排。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和一些行政部门内部的“鹰派”与盘踞在国会山上的右翼反华势力密切互动,更新或通过了《2019年国防授权法案》《台湾旅行法》《2018年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2019年台湾保证法》《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等一系列国会“立法”,不仅快速构筑着对华战略竞争的法律制度框架,也将遏华反华动员从精英层面延伸至普罗大众层面。
综上所述,冷战结束以来,美政军学界对中国的提防与怨念在不断累积,由于几届政府对华观念不断调整,恐怖主义、金融危机等突发事件接连发生,在全面遏制中国问题上始终缺乏战略层面的明确性、统一性和持续性。这种状况在特朗普执政后发生了变化,借助特朗普本人信奉“美国优先”和推动“公平贸易”的执念,涉华议题被各界“鹰派”成功泛化,形成从贸易公平、技术合作、产业发展到经济体制、国家安全的全方位收紧,目标直指中国“政治上的权威主义、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国际关系上的新扩张主义”,[14]初步完成了从战略犹豫向战略坚定的质变。
二 中美关系新态势的特点和趋势
围绕如何看待崛起中的中国,美国战略学界于2015年至2018年进行了大讨论,现已形成跨党派、跨阵营、跨领域的共识,即:过去若干年,美国历届政府始终致力于将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以推动中国确立市场化经济体制、进而实现政治变革,现在这项建设性接触的政策失败了,中国已经成为势不可挡、越来越具“进攻性”的异质力量、足以全方位“挑战”美国优势领先地位的竞争对手,美国的对华政策必须即刻调整,再不调整就来不及了。尽管对于如何调整,美国战略学界尚未形成一整套清晰思路,存在“有限接触”与“全面遏制”的分歧,但美国对华战略的定位已经全方位负面化,由“接触”向“规锁”转型,给正在形成的新战略注入“新遏制政策”的既成事实。[15]这种变化在中美之间搅起“行动-反应-再反应”的链条,深刻影响两国的情绪和判断,推动中美关系发生形态和性质上的转折。
美国对中国的心态和应对的变化引发了中国战略界的深深忧虑。一段时间来,中国战略界讨论的焦点是,美对华政策是否正在发生从建设性接触到全面遏制的转折,如果转折的确在发生,中国需要在战略上做何反应?自身改革发展方略须做怎样的调整?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美对华战略思维的转变是根本性的,处理中美关系长期依赖的“路径”发生了漂移。而在官方层面,处理对美关系更多强调斗争性已是既成事实。过去,双方承认两国间存在原则性分歧和结构性矛盾,但也尽量避免对抗冲突,而是强调共同利益大于彼此分歧、共同挑战多于相互威胁,合作是两国关系主流,所以每当双方发生重大现实摩擦和利害冲突,往往能通过对话沟通暂时化解和掩盖,两国关系中的积极面总体上能够压倒消极面。现在,足以维系两国合作面的共同利益诉求和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动力正在遭到消蚀,两国关系“新态势”的形成恐怕是双方乃至国际社会不得不接受的趋势。
现在看来,“新态势”的中心内容是,美国对华外交的本质蜕变为竞争性外交,中国的对美政策更加强调斗争,中美两国的竞争性明显上升,现阶段和今后特定时期内竞争大于合作。具体而言,“新态势”将在近中期内呈现以下特点:
(一)价值对立形成“锁定效应”
美国的政治和社会无论怎样分裂,各种势力仍具有基本共同的价值观,分权、制衡、民主、有限政府、自由企业和市场经济以及对专制和集权的恐惧仍是不可动摇的原则,并在对中国崛起的判断和应对上有充分表现。[16]美国不仅从权力转移和国家利益角度考虑对华政策,也认为中美在国际舞台上竞争的本质是西方民主政治圈与中俄“共同”领导的“威权国家阵营”之间的竞争,是两种价值体系的冲突;[17]政治制度不同是两国长期不信任的源头,“不会有美国领导人像中国政府希望的那样认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18]正是基于此种认识,加上特朗普政府在美国国内政治斗争中为抹黑民主党医改、环保等政策主张而将社会主义妖魔化的需要,意识形态话语正在美国国内政治中卷土重来并外溢到对外政策当中。[19]而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定维护基本制度,举国动员努力实现“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不可能拿核心利益做交易,中美双方思想意识层面结构性矛盾的发展将随中国崛起进程的深化而更加尖锐和复杂。
(二)经贸摩擦长期化与常态化
中美经贸摩擦在本质上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和战略问题;既源于美方对中美贸易不平衡导致自身利益流失的不满,也源于美方对中国改革方向不符合其预期的愤懑。中美经贸摩擦早期集中在货物贸易领域,现已扩散到金融、服务、投资、税收、知识产权、技术、能源等范畴,进入全方位摩擦时代。美国贸易“鹰派”挑起“贸易战”所要达到的,不仅是扩大自身经济利益,实现特朗普提高美国制造业与工人竞争力、使更多企业赴美或返美投资并“雇佣美国人”的竞选承诺,更聚焦中国所谓“国有企业补贴”“强制技术转让”及“一带一路”倡议造成的“掠夺性经济”等“结构性问题”,旨在改变中国的经济制度,削弱中国的竞争潜力。[20]即便中美达成贸易协议,未来中国在结构性变革方面也会面临更多压力,中美围绕协议的落实问题也会进行长期角力。[21]
(三)海上军事较量显性化
中国在核导、海洋、太空、网络等领域与美国的能力差距仍大,所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也决定了今后相关能力建设不可能比照美国的规模进行,目前仅能对美国构成非对称性制衡。但在西太平洋海上局部区域,双方有可能势均力敌。因此,未来中美战略竞争将带有很强的海权博弈色彩,结构性战略矛盾突出表现在海上,两军博弈焦点集中在西太平洋地区,特别是南海。自2009年起,美国战略界就已将中国视为最大的海上战略竞争对手并开始战术回应,连续推出“空海一体战”“联合进入与机动联合”“全域进入”等作战概念,近年加快推动海上战略转型,从“由海至陆”到“重返制海”。2019年4月,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CNAS)又相继发布报告,呼吁针对中俄的新一轮作战概念创新。[22]海上战略竞争态势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整体战略关系,中美海空力量对比的缩小将加剧海上战略竞争。中美海上战略竞争不同于历史上大国海上战略竞争可以快速进行海上决战决胜,大概率而言,这将是一场以双方舰机近距离接触和相互试探为主要表现形式的长期相持,在战争与和平之间有大面积“灰色地带”,使竞争变得更难管理,小规模、低烈度武装冲突的可能性无法排除。[23]
(四)以核军控和中导为主要内容的战略安全问题提上中美关系议程
美国退出《中导条约》,中国是其重要考量之一。美国军方认为,中国不受约束地大规模研制和部署中程和中短程弹道导弹,对美国部署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资源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美俄两国可能会就新的更广泛裁军条约进行谈判,美方坚持要求新条约必须包括中国。美国即将与俄罗斯展开《战略武器削减条约》续约谈判,也以“中国加入”为前提。这些动向表明,中美战略层级对话重心和博弈焦点即将发生变化,把中国拉入多边核军控体制已成为美国军控政策优先议程之一。美方意图是通过相关的军事透明及核查机制,了解中国的军事装备现状,同时规制中国在核导、网络、太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能力发展。今后,随着战略竞争的加剧,中国将会面临两方面压力:一是美方继续施压中国与美俄缔结新的军控条约,俄方的态度变得更加重要;二是美国将在关岛等西部太平洋地区的基地部署新的中程导弹,对中国的战略安全构成直接威胁。
(五)影响相互判断的情绪化因素更加显著
随着美国国内对华战略竞争动员向社会基层的深入,许多美国人把中国当做最有潜力取代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国家,习惯于根据中国不断增长的能力推测中国的意图,这就导致对中国的误判越来越深。盖洛普公司新近民调显示,2019年对中国持好感的美国民众比例仅有41%,创2012年以来新低(2017、2018年这一数据分别是50%、53%),46%的美国民众认为中国经济实力对美国构成“威胁”(2018年这一数据为40%)。[24]而在许多中国人眼里,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最大的战略威胁和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最主要外部阻力,美国对华压力向涉及政治体制和国家主权安全问题集中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中方受害心理和悲情意识,助推民族主义情绪,加剧不利于中美关系长期发展的公共舆论氛围,将不时冲击两国外交决策的理性框架。
(六)围绕国际秩序向何处去的影响力和塑造力角逐尖锐化
在美国政府和许多战略界人士眼中,中国发起“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就是要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之外“另起炉灶”,推行“去美国化”,“挑战”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在全球层面,美国与世界接触的意愿和能力都在减弱,正打着“美国优先”旗号挑起体系混乱,一方面甩掉一些其自认过重或不划算的包袱,另一方面拉住盟友重塑国际规则和标准,将中国排挤出去。而中国支持自由贸易、支持平等开放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与美国在理念上渐行渐远,利益对撞日趋严重。中国的民族伟大复兴与美国的“再度伟大”都需要在全球框架下运作,两个目标在实施空间、依托理念、驱动利益、指导价值上都存在冲突,竞争逐渐成为中美全球互动的主要方面。
从更长时间跨度看,未来中美关系的演变则有三种可能前景:
第一,贸易摩擦导致双边关系“压舱石”作用彻底失效,最终将演变成“新冷战”。经贸、科技、投资、教育和人才“脱钩”产生严重外溢效应,形成两个相对独立却又相互关联的经济体系,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市场随之分裂,一些国家依附美国市场,一些国家依附中国市场,绝大部分国家尽量两边同时下注。在白宫右翼势力看来,这一结局是两国结构性权势对抗的必然结果:曾任特朗普首席战略顾问的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认为,“美国对华经济战争已经打响,这场战争势必导致在25年到30年后,美中只有一方成为世界霸主”。[25]“历史终结论”提出者、斯坦福大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判断,“一场历史性的发展模式之争正在中国与美国、西方国家之间上演,会影响全球政治的未来”。[26]“进攻性现实主义”缔造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则坚信“美中必有一战”。[27]
第二,以贸易摩擦问题的妥善解决为经验借鉴,成功遏制双边对抗向其他领域蔓延,确立竞合关系状态。出于党派政治和选举考量,美国历届政府对华关系判断总会出现波峰波谷的交替转变,目前白宫对华战略的鹰派色彩也会随双边议题调整、特朗普竞选连任、白宫人事变动等有所变化。经过激烈交锋,中美关系有可能形成新的动态平衡和相对稳定,美国提供高科技、中国提供大市场,双方共同承载引领全球治理、提供公共产品义务,形成国际新秩序模板。
第三,结构性对抗保持在一定限度内,中美关系持续漂流。目前双方对未来都尚未确立针对对方的清晰和具体的目标,既有关系框架逐渐瓦解,新的框架一时还搭建不起来,两国关系继续漂流。但随着美方不断出招挑衅,中方不得已应战,“向下螺旋”继续起作用。
然而,历史演进从来不是单项选择题。今日美国已非冷战结束时的美国,虽正在进行自我调整和战略收缩,其霸权已开启盛极而衰的曲线,但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仍将在诸多领域保持优势。今日中国也大不同于1979年中美建交时的中国,从经济总量意义上看,在21世纪第三个十年初期,中国对美国实现赶超的前景日趋明朗;但从质量意义上看,中国的整体力量还不够全面,经济结构和科技研发上对美国等传统大国仍有较强倚重,且国内发展任务繁重,尚不具备取代和挑战美国的充分竞争条件。中美双方也都知道,两国各自体量过于巨大,长久积淀出来的利益交融过于深厚,彼此关系的变动影响深远,即使结构性矛盾无法调和,更高烈度、更广范畴的竞争不可避免,也不能发生过于激烈的全面对抗和正面冲突,必须对分歧进行管控,同时在可合作的领域尽量保持合作。在此情况下,对“底线”的强调和建设也将成为中美关系“新态势”的重要特点,两国强力部门特别是军方之间围绕战略稳定、接触规则的对话协商将更为频次化、专业化和正规化。但所有这一切并不能掩盖中美在多领域更频繁地进行正面博弈的趋势,也不能排除双方因某个或某几个问题发生中低烈度冲突的可能。今后相当长时间里,美国的调整与中国的上升如何相互作用,将构成影响国际格局变动的主线。未来的中美关系状态,更可能是在以上三种路径的综合体,并不存在单一、绝对选项。
三 中美关系的范式转变
“范式”(Paradigm)本是科学哲学概念,含义为范例、模型或基本模式,是指为开展科学研究、建立科学体系、运用科学思想提供基本坐标和参照系。这一概念被应用到国际关系领域后,原指现实主义、理性主义、革命主义三大理论体系层次,[28]后逐渐泛化,具体应用在国家间关系上,大概指主权行为体在彼此打交道时需共同遵从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在此基础上形成稳定可期的互动模式。[29]指导国家间关系的“范式”,具有明显的思想性、共识性、结构性、习惯性、规则性、底线性和示范性特征。在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研究中,“范式变化”是指国家间关系处理的基本方式、原则和目标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30]
随着美对华政策讨论的深入,“范式”一词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2018年11月,美前国务卿基辛格访华,在与中方学者交流时说,美中关系再也回不到从前了,需要重新定位;现在美中之间的根本问题并不只是要解决贸易争端这么简单,而是在一个更加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下如何共生共存;未来的美中关系既不会回到特朗普以前的状态,也不会变成“新冷战”的全面对抗关系,而是走向一种“新的范式”(New Paradigm)。[31]2019年11月,基辛格再次访华,在会见中国领导人时说,时代背景已发生变化,美中关系的重要性更加突出,认识和处理好美中关系需要宽广的思想和历史哲学的思辨,双方应该加强战略沟通,努力找到妥善解决分歧的办法,继续开展各领域交流与合作。[32]
基辛格没有解释“新范式”的具体含义,但从中国战略学界已做出的评论看,有观点将其理解为“新格局”,一般来讲包括三方面含义:权力结构、关系形态和各自主导两国关系发展的基本战略,同时又是物质和观念两方面发展演变的合成。[33]
中美关系基本格局的确在改变:从相对简单到异常复杂,协调合作宽泛存在,竞争摩擦全面展开;从经过痛苦的相互接纳形成利益紧密互嵌在同一全球经济体系内共舞的关系,到虽仍在同一全球经济体系内发挥作用,但彼此渐行渐远,双方供应链、销售链逐步剥离;从美国占据主导地位的关系,中国更多是从弱者地位出发与美国打交道,到从强强相对的大致平等角度开展博弈,中国自身的选择和主动作为也将产生较大影响,两大国进入同一个等级的关系,在双边、地区、全球层面同时交错互动。
无论是美国的对华战略、中国的对美政策,还是中美关系本身,都已呈现新的态势。有必要顺应中美力量对比和各自国际地位发生的重要变化,以中美关系的“新范式”应对中美关系的“新态势”。[34]而阻止“新态势”朝全面对抗与冲突方向演变,同样需要的是能够重新定位、处理和管控这一关系的“新范式”。[35]
“新范式”的建立无法脱离时代背景。当今世界最基本的“全球态势”有两个:一是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尽管面临“国家利益至上”及保护主义、极端主义、民粹主义的干扰和挑战,但大势难以逆转,世界已在全球产业和消费链的连接下结为一体,利益相互攸关,即便任何一方都有强烈的战略和利益驱使,但也无法做到与其他方全然“脱钩”。未来全球经济即便在中美各领一方、遵循不同标准的两个相对独立体系内运行,彼此也将是相互关联和存在共性的,不可能全然割裂,但中美难免在相当长时间内各自为维护相对独立体系的运行而付出巨大的战略、政治代价和经济成本。二是多极秩序的缓慢生成,在此之前世界格局有较大概率经过一段多强并立但中美两极相持的过渡期,协调合作的机遇与摩擦对撞的风险并存。正是因为这两大趋势的存在和延伸,中美作为未来全球最举足轻重的两个大国,需要把相当精力用在管理、谈判、协调上,两国互动除了互相塑造未来国家形态和民族心态之外,也将产生巨大的外溢影响,在治理方面促进新的“全球范式”形成。
需要关注的是,在特朗普及其团队操弄下,美国总统在对外政策方面的执政理念出现重大转变:从侧重多边重新转为倚靠单边或双边手段。准确地讲,特朗普政府正努力将美国的全球治理从多边模式调整到双边模式,在军备控制领域则以退出伊朗核协议和《中导条约》为标志转向单边主义。这样做的目的是压缩美国在国际合作中的让步空间,最大限度保全传统安全利益,继续掌控全球战略主导权。[36]如果特朗普在2020年大选中连任,世界格局将加速迈向多极秩序,大国的全球影响力空间将继续重新分配,中国在东南亚、南亚、非洲和中东等地区的综合影响力面临继续上升的机遇。即便特朗普败选,民主党总统在某种程度上重拾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因子,美国社会的保守化趋势一时也不会发生根本性扭转,在军控和战略安全领域的单边或双边主义倾向是美国跨政府任期的时代性选择。
“新范式”的建立需要正视心理建设问题,守成大国与上升大国须分别克服“斯巴达的恐惧”[37]和实力快速增长导致的自我膨胀。长期的热战冷战记忆、盎格鲁-撒克逊宗教文化和实力超群状态赋予的“例外主义”优越心理,使美国的战略文化难以走出结构性对抗的渊薮。这种渊薮是维护霸权的荣耀使命感和对现实、潜在竞争者的天然恐惧感的糅杂,决定了美国无法真正实现战略目标与战略手段的平衡,对中国崛起会继续加大防范、施压、遏制的力度。然而,经过在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的漫长摇摆与融合,美国战略文化形成了将国家利益中的安全、繁荣、价值、领导权等要素综合集成的逻辑闭环,构建起一整套精确、实用的战略管理机制,覆盖战略规划、战略实施和战略评估的方方面面,面对现实的调整能力仍是很强的。[38]中国则已进入大国崛起“行百里者半九十”的功成阶段,既面临国力加速累积、影响加速拓展的重大机遇,在维护自身利益和塑造国际秩序方面可以更加主动有为,也需要克服大国权力扩张的诱惑。未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将由在相对衰落轨道里调整的美国和在上升区间努力攀登的中国互动而成,相互试探和刺激固然无法完全避免,但只要情绪得到把控,美国得以进行战略自省,中国保持战略定力,就可以避免形成相互刺激的恶性循环。
“新范式”的建立,需在直接当事方持续不断的互动中逐渐形成相对稳定的机制架构。在中美关系范式的构建中,从20世纪90年代中方推动“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一度达成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关系”“互相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意向和美方推出“负责任利益攸关方”概念,再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方动议“共建新型大国关系”,每次重新界定两国关系范式的努力均未成功,根本原因就在于,尽管两国交流合作不断加深,但战略互疑不仅没有得到消解,反而还随着两国国力对比和各自国内政治条件等变化而深化,始终处于“漂流”状态。[39]美方内心既不情愿接纳意识形态迥异、发展潜力巨大的中国在所谓“伙伴”定位下获得与美盟友同等重要的地位,也不情愿在“相互尊重”原则下放弃干涉中国内政的机会并在国际体系中给予中国“平起平坐”的权利。[40]有鉴于中美关系的庞大体量和高度复杂性,要确立“新范式”,需在国际关系理论界公认的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点,同时吸纳中国传统战略文化中的和合思维,既在思想意识上扬弃双方历代领导人和战略界、舆论场、市民阶层总结归纳和共同接受的历史经验、文化沉淀和理想情怀,也植根于两国真实国力对比,在国内、双边、全球层面同时搭建能适应彼此关系新态势的对话管道、合作框架和分歧管控机制,在积极的互动中达致新的动态平衡,构建既竞争又合作的和平共存、共同进化关系。[41]2018年12月2日,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会晤时达成共识,同意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关系”。[42]这或许正是双方启动“新范式”探索所需要的高层信号。
在摩擦尤酣的经贸领域,尽管分歧巨大,甚至关涉中方核心利益,中美仍坚持沟通。2019年12月,经过13轮艰苦磋商,中美就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达成一致,协议文本包括序言、知识产权、技术转让、食品和农产品、金融服务、汇率和透明度、扩大贸易、双边评估和争端解决、最终条款九个章节。同时,双方达成一致,美方将履行分阶段取消对华产品加征关税的相关承诺,实现加征关税由升到降的转变。[43]这一进展说明,双方均已意识到经贸摩擦久拖不决只会导致双输局面,愿意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原则,以协调的办法解决争端,推进两国和世界经济“再平衡”。
四 全球安全治理中的中美关系“新范式”
冷战结束后,大规模军事集团对抗与战争风险消退,全球化及地区一体化并轨发展,关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政治、安全、环境、能源等共性问题得到国际社会更广泛关注,“全球治理”成为频繁使用的术语。“全球治理不仅意味着正式的制度和组织——国家机构、政府间合作等制定(或不制定)和维持管理世界秩序的规则和规范,而且意味着所有的其他组织和压力团体——从多国公司、跨国社会运动到众多的非政府组织,都追求对跨国规则和权威体系产生影响的目标和对象”。[44]
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拐点之上。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争取话语权和利益分配权的诉求随之增强,成为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变化,与陷入金融与债务危机困境的西方国家形成鲜明对照;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把世界各国利益和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近代以来列强通过“战争、殖民、划分势力范围”等方式争夺利益和霸权已逐步向各国以“制度规则”协调关系和利益的方式演进,建立国际机制、遵守国际规则、追求国际正义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45]
全球安全治理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冷战”后随“全球安全”“人类安全”“非传统安全”等问题的日益显现而被提出。马克·韦伯(Mark Webber)认为,全球安全治理是“规则的国际体系,有赖于多数受影响国家的接受,通过正式、非正式的规则机制驾驭跨越诸多安全以及与安全相关问题领域的行动”。[46]另有学者概括,“安全治理属于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环节……通过一个多边的形式,来解决这个世界面临的种种传统的以及非传统的安全问题”。[47]概括而言,就是主权国家、国际组织等从全球安全需求的视角出发,以超越传统国家政治界线的方式,为实现共需的安全与稳定、和平与发展,在世界范围内由各类行为体以合作协调的方式,寻求解决安全问题而采取的相关行动。它产生的前提是,当今世界相互关联、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同时全球性安全问题扩散加快,波及面扩大,冲击强度增加,成为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其逻辑起点则是国际社会在安全上形成相互依存与相互影响的观念及情势,合作共赢理念得到更大程度支持。
全球安全治理对于国际社会及其中的政府、民众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主因有三:第一,安全是实现生存质量与发展质量的关键。没有相对安全稳定的生存环境,国家间的权力斗争、零和竞争、武装冲突、军备竞赛等都易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调,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基本属性将更加彰显,国际社会就更难形成合作动力。至于个体,在不安全的状态下,最基本的自然、社会权利尤其是生存发展权利更难得到保障。第二,重大安全问题是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威胁。仅从近一个多世纪的历史看,两次世界大战是大国权力竞争失控的恶果;冷战时期,美苏核武库急速膨胀,能把地球毁灭数十次;冷战后爆发的地区冲突、国际恐怖主义袭击、核材料与核技术的扩散、日趋严峻的环境安全等,都让全球安全面临更复杂挑战,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第三,单一国家或集团应对全球性安全问题的缺陷明显。安全威胁来源具有全球性,既可能来自国家,也可能来自个人、组织,特别是恐怖主义组织、跨国犯罪组织和网络空间。[48]很多国家集团代表的集团利益与更大范围内的全球共性利益间存在明显的对立冲突。全球安全问题影响的是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必须也只能基于共识开展协调合作来加以应对。
尽管当今世界并不面临两次世界大战那样的紧迫战争威胁,但复杂化的安全挑战从方方面面渗入国家肌体,外部或内部的、军事或非军事的、经济或文化的、宗教或族群的……加剧了维护安全的难度,使得加强全球安全治理成为必然选择。但全球安全治理要想顺利展开,仍需克服重重障碍,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以西方强权政治思想、绝对安全理念为要核的安全治理观念。这套观念及以其为主导思维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在战后对全球进步作出了贡献,但也日益暴露出局限性,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政治和安全挑战日益碎片化的今天越来越难以提供全面、有效的解决方案。最典型的就是,美国把军事政治联盟作为维持霸权体系的支柱,惯用强制性的实力手段来推行对外政策,有时以最直接的暴力手段呈现,有时以其主导的国际法规或国际组织为掩护,奉行强权政治、霸权主义、“双重标准”,对国际政治民主化发展和人类寻求更加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努力造成干扰和威胁。
守成大国(体系)与新兴大国(体系)在权力竞争和过渡问题上的对抗风险,也会直接影响到全球安全治理的推进。当前,美国担心中俄会挑战它的世界权力和对国际事务的掌控,在军事安全领域对两国的排斥性尤其明显。美国的矛盾在于,它希望继续领导世界秩序、主导国际事务,但又不愿哪怕是部分地改变这个秩序当中的排他性属性。在这种思维的影响下,亚太安全秩序形成了“不对称的二元对立格局”并呈日益固化趋势。与此同时,中国在东亚的战略安排尽管享有地缘优势,并不断展现出积极有为的风格转变和布局调整,但仍不得不耗费相当精力应对美国的限制和围堵压力,自身在地区内亦不拥有美国式的同盟体系,在地区安全格局中仍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49]
中国和美国,一个是冉冉上升、影响力不断增强并积极提供新型国际公共产品的全球大国,一个是在现行国际体系中继续发挥主导作用但引领兴趣和影响力呈明显下降趋势的全球大国,两国的交互作用将决定今后包括全球安全治理在内的全球治理发展方向。一方面,两国在反恐、防扩散、打击跨国犯罪、传染病防治、应对气候变化、海洋环保等领域拥有共同利益,如能基于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广泛开展合作和协调,可对改革完善包括全球安全治理在内的全球治理形成带动、示范效应,包括全球安全治理在内的全球治理改革和发展也就好办得多。另一方面,两国安全观、秩序观、价值观严重对立:一个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的新型安全观,主张摒弃冷战思维,权利、机会、规则平等,强调开放为导向、合作为动力,反对搞针对性和排他性的安全安排;另一个维护霸权主导、坚持排他性的集体安全理念,同时又对全球责任分担斤斤计较,更对中国与美国“争地位”耿耿于怀;双方立场不兼容、政策难协调。现在,包括全球安全治理在内的全球治理平台已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外延,各种具体的防范限制举措正将全球体系推向大撕裂、大分化的危险境地,其他国家面临选边站队的压力。这种“分化”风险并非是单纯的经济全球化意义上的,也有战略和安全属性。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在2019年9月的第74届联合国大会开幕演讲中表达了忧虑:“一个新的风险正出现在地平线上,尽管还不算太大,但却是真实的。我担心大分裂的可能:世界分裂成两个,地球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制造出两个相互独立、彼此竞争的世界,每一个都有其各自主导性的货币、贸易和金融规则、单独的互联网以及人工智能技术,还有它们自己的零和地缘政治与军事战略。”[50]
未来中美建立彼此关系“新范式”的努力必须延及包括全球安全治理在内的全球治理领域,为“新范式”确立合理和宽阔的全球外延,协调中美利益、避免体系分化应是题中之意。在大的共处理念和治理原则一时还谈不拢、美官方也没有足够兴趣谈的情况下,双方在共同利益领域的功能性合作不应受到妨碍,并且涉及应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全球性挑战,处理兼具传统内涵和新兴意义的泛人类问题,在实际协商合作的过程中培育面向未来的相互了解与信任基础。将来如果美国民主党重新执政,其未必会扭转加强对华遏制的大方向,但应对全球性挑战这样的议程有望回归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位置,承担国际义务的道德和法律传统将会在某种程度上复活,两国企业界、知识界应保持沟通,尽量保留利益汇合点,这对未来中美在地区和全球层面的良性协调也有政策和工具储备意义。
不过也要看到,中美关系确立“新范式”有待解决的一大问题是,经贸合作作为两国关系“压舱石”的作用已经不稳,需要探索新的“压舱石”,包括全球安全治理在内的全球治理合作在此方面作用有限。既然未来中美关系的首要特点是战略竞争,最迫切的任务是管控风险,那么新的“压舱石”恐怕还是要适应这一特点,通过战略试探和博弈,如前所述建立某种相对稳定的机制架构,最终以大国权势平衡的方式来打造。
五 确立中美关系“新范式”的路径
新时代的中国外交是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形成并推进的,根本宗旨是服务于“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基本路径是着重建设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同美国探索关系“新范式”的努力当以此为宏观框架——一个合理的、均衡的全球安全治理框架,锁定协调、合作、稳定的基调,争取互动出新的平衡。这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愿望,也是全球安全治理健全发展的需要。
(一)明确“战略竞争”的概念和边界
美国对华战略调整的根本目的,是通过重拾战略竞争文化,激发美国自内而外的危机感和创新力,全方位压制对手竞争潜力增长,确保自身优势的持久性。这一调整虽有将中美关系引入美苏式冷战对抗轨道的危险,但是在控制其烈度方面并非全不自知,也非能为所欲为。特别是要把战略竞争和战略敌手的概念区分和界限辨析清楚。竞争是大国关系的常态,竞争未必导致敌对,竞争也不排除合作。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也提及:“竞争并不总是意味着敌对,也不是不可避免走向冲突,然而没有人能质疑我们捍卫利益的承诺。”[51]2019年10月24日,彭斯在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演讲表示,特朗普政府不寻求遏制中国的发展,不寻求与中国对抗,不寻求与中国“脱钩”,而是寻求“从根本上重组我们与中国关系的结构”。[52]
中国仍处于现代化进程当中,对美政策既要确立战略自信,发扬斗争精神,也需与自身实力相匹配,讲究斗争艺术。美国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仍将是在诸多领域拥有优势的世界强国,是中国不得不在战略上打交道的主要对手和在众多实际领域开展合作的重要对象。作为大国战略竞争的较弱一方,中国应当全面认识美国的战略考量,形成合理的应对策略,做出正确的时代选择。可通过努力控制战略竞争的边界,适当调整自身行为方式,推动美方与我们一道塑造自我克制、相互节制、共同进化的良性竞争文化。同时,不排除在某些领域存在对抗的可能,中国需要仔细评估这些对抗将两国拖入冲突的风险。[53]
中美有必要把价值分歧放在两国关系适当位置上,确立相互容忍而非谋求取代的价值共存模式。[54]同时理性规范、克制应用国内政治因素的驱动,避免双边关系被国内政治和情绪化民意绑架。
因此,中美有必要就各自利益关切进行“对表”,厘清哪些是共同、相通或相近的,哪些存在分歧但并非不可调和,哪些严重对立但可以做到相互理解和尊重,哪些根本对立无法调和必须严加管控,逐个解释说明,清晰表达各自战略意图和诉求,在此基础上列出“合作清单”“管控清单”“负面清单”,准备面向未来的政策“工具箱”。
(二)构建更完备的沟通、对话和协调平台
沟通和对话是中美关系重要传统。即便是在冷战期间最尖锐的对立状态中,中美也最低限度保持沟通,而20世纪70年代两国关系破冰过程中的高层交往堪称经典的战略对话。经过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积累,中美业已建立起较完整的沟通对话平台,尽管在特朗普执政时期部分实际停摆,但总体框架仍在、对话精神未泯。在战略竞争状态下,无论是出于加深相互了解的需要,还是为着管控分歧的目的,中美更应该健全沟通的机制、丰富交流的层级、充实对话的内容。
1.完善高层级对话沟通机制 建立与全球性大国关系重要性相匹配的互动管道
元首外交作用特殊不可替代,过去主要是为双边关系发展确立原则、提供指导,最后一刻确认共识,同时也有通过定期不定期的、正式和非正式的会晤安排抑制摩擦、管控分歧的功能。今后,继续发挥元首外交指导作用,有必要加强以对等方式为双边关系定议程、给两国矛盾“踩刹车”的作用,并使利于深谈的长时间小范围非正式会晤形成惯例,同时尽量避免领导人之间就重大疑难问题直接谈判。也要持续增加对美传统建制派精英的战略沟通。
2.重新激活功效濒于僵滞的战略对话机制 构建战略稳定框架[55]
美国的战略稳定政策要求美国对自身和对手的战略实力不断进行重新认识和评估,因此具有很强的动态性,在战略稳定关系上的决策并不追求取消核对抗与核威慑,而是希望通过占有优势的核对抗与核威慑最大限度达到所需战略效果,因而通常倾向于在技术和力量层面而非政治层面与对手讨论问题。[56]美国已把战略稳定的重要性置于“追求核优势地位”之后,且多次提及与中国保持战略稳定,中国正从美国战略稳定政策的边缘向中心部靠拢,这也是冷战后全球政治力量格局变化带来的新挑战。中美不仅要在观念上控制战略竞争的强度和烈度,在实力上形成核常兼备的战略威慑状态,还有必要在制度上达成双方共识的协调机制,防止敌化意识在各自内部不断发酵,并避免恶性军备竞赛。双方似有必要做出共同保证,以各自核武库的威慑能力降低常规危机或冲突升级为核对抗的危险。在此基础上,扩大中美之间战略稳定的概念、范畴、定义和适用范围,为2014年签署的《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机制》《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谅解备忘录等已有文件增加网络、太空及其他战略空间新附件。[57]从中长期看,如何在包括核导、网络安全在内的战略安全领域形成广泛共识,搭建战略稳定框架,实现“军备竞赛稳定性”[58]和“危机稳定性”,[59]为中美关系提供新“基石”,是双方需认真考虑的问题。[60]
两国外交和防务部门应进一步完善相关安全对话和危机管理机制,加强安全信任措施建设,可考虑将现有两国外交防务部门高官共同参与、迄今已举行两轮的中美外交安全对话实化为外交、防务“2+2”磋商机制。
3.加强中美两军机制性对话和专业交流
加强中美两军机制性对话和专业交流,继续巩固完善两军高层的战略对话平台,如国防部层级的工作会晤、高级将领互访等,适时考虑建立两国海空军及有关战区之间的热线。借助“香格里拉对话”“北京香山论坛”这样的多边多轨安全对话机制,向外界传递己方政治立场、战略考量及重大军事安全关切,并借此提高军事影响力和话语权。继续开展两军人道主义救援、海上相遇等领域的联合实操演练,适度引入东盟国家和澳大利亚等美国盟友参加,扩大共同安全利益的辐射面,塑造多元行为者互动协调的新平衡机制。推动两国两军安全研究智库、专家间的学术交流,通过建立专项论坛、合作研究等机制,既能促进两军进行专业性的研究交流,也联合开展针对性强的研究分析,为两军高层提供竞争管理和危机管控决策咨询。
4.抵制“脱钩”风潮 守护两国关系互利交融面
中美应坚持正常的经贸、科技、人文交流,抵制“脱钩”风潮,守护互利交融的一面。要借鉴历史经验,看到包括学术、民间在内的密切人文交往是中美关系重要维系因素、两国确保相互开放的重要因果保障,即便在总体关系非正常状态下也不能中断舍弃。总体来讲,美国国内企业界、教育界、学术界的大量人士并不认为“脱钩”是可取、可行的,也反感特朗普政府针对华人采取的有悖自由价值的监视、限制措施,同时也希望中方克制反应,不要搞成部门性“对等行为”的报复性螺旋升级。
(三)在全球安全层面理性博弈与有效合作
中国正在成长为全球性的大国,与美国的利益交叠日益向地区和全球层面延伸,双方处理彼此关系的平台不仅在双边,也是在地区和全球。美国虽有心分割世界,构建排斥中国利益和竞争力的新的体系标准,但经济全球化仍是大势所趋,世界很难分裂成两个,中美必须共同探索在同一国际体系内的新的和平共存模式。在此方面,中美两国各自的选择和彼此互动形成的效果固然起决定性作用,第三方力量的态度也会产生重要影响。
1.妥善管理海上战略竞争
在西太平洋海上、特别是南海正在成为中美面对面战略博弈的主场,也是两国进行战略试探和摸索寻找新的动态平衡的首要实践场。就大趋势而言,两国对彼此战略利益的冲突既做不到视而不见、避而不谈,也无法通过强力手段完全排斥对方,长期战略相持将成为常态化态势,这也促使双方在此消彼长中相互作出包容和妥协,以期摸索出新的互动模式。为此,双方都有必要跳出宣传功效引导下的话语冲突,克制单纯寻求建立压倒对方的海上力量优势和机制优势的冲动,转而尝试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开展海上战略对话,就海上军备发展进行军控对峙或相互限制,着重发展出一套在西太平洋地区共存共处的高水平的行为规范,最终就西太平洋地区权力分配和力量对比形成共识。[61]
值得注意的是,双方都需要提防局部事件诱发的决策失控和态势恶化,为此急需完善两军在敏感地区的突发事件应对机制,共建危机管控机制和安全沟通渠道,尤其应把关注点放在一线,探索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安全行为规范。近年来,两军建立区域安全管控机制的努力取得长足进展,[62]未来应针对南海等重点地区事态,着力建立处理突发事件的行为规范,尤其是标准化、可操作的反应流程。也可围绕“航行自由”行动、美军在争议海域的活动等重大问题,建立专门的双边磋商渠道。长远看,中国军事力量守护国家利益的平台既要聚焦海洋也要跳出海洋,以更广阔的战略视野来审视中美博弈,通过更高层级的战略性协调来降低在海洋领域的对抗冲突风险。
2.厘清共同利益点 保持正常合作基本态势
中美在广泛领域仍存在共同利益,在过去双方反复确认的应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挑战方面,合作性没有减少,包括攻克各类疾病提升人类健康水平、打击跨国犯罪、处理地区热点问题、应对气候变化、治理全球污染、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确保核安全、防范应对国际金融风险等。在一些新兴领域,双方竞争性关系的发展也不能完全掩盖协调合作的必要性,比如在网络安全、外太空治理、人工智能研发应用规则制定方面,美国拥有巨大技术优势,但中国也并非只是追随者,双方现阶段可从协商制定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的道德规范和发展原则入手,协商出一些惠及世界的共识性成果,为未来合作创造基础条件。这样的合作在补充双边关系基础的同时,更具宽广的人类福祉价值。
中美已在朝鲜半岛和阿富汗问题上积累了一定合作经验,前者是在多边对话与谈判中协调立场,严格执行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共守无核化基本方向;后者是在特定范围内共享信息,开展有利于阿富汗国内和平和解进程的项目合作。未来,随着两个热点问题形势的变化,双方可进一步突出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方面的共同利益,加强沟通协调。朝核、阿富汗问题运作好了,有条件成为中美在亚太建立安全新架构的缓冲带。
3.管理好第三方因素
中美在全球领域与其他国家都有密切联系,彼此关系也对其他国家利益产生深刻影响。中美应克制住纠集第三方力量对对方进行集团式封堵和抗衡的冲动,也不应逼迫第三方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那样的话效果将适得其反,同时也将给某些第三方从中美矛盾中渔利提供运作空间。要把第三方国家的角色尽量定义为中美共同的朋友而非敌人,越是当美国在全球性责任面前犹疑退让之时,中国越应与欧盟、东盟等第三方国家携手,在难民问题、反恐行动、气候变化、网络空间治理等安全议题上构建行动合力,推动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民间社会和个人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不断提升全球安全治理的整体性和协同性。通过强化第三方作用,有助于推动形成中美双方积极争取国际社会支持的良性局面,增强大国博弈的能力和弹性。
(四)立足亚太地区探索新型安全合作架构
亚太地区是中美战略利益最为集中交汇的地区,两国除双边渠道外,也需要在区域多边架构中合理互动,推动建立新型的地区安全治理机制。亚太地区尤需建立包容性的地区安全秩序和规则体系。当前亚太地区安全机制林林总总,最严格的是美国领导的排他性双边安全同盟体系,其问题在于不包容甚至针对中国。东盟地区论坛、亚信会议、东亚峰会等区域和次区域合作机制都在讨论安全问题,但缺乏处理矛盾和协调分歧的行动力。地区主要力量应携手推动建立一个管总、有效的安全机制,当务之急是就维护地区安全的共同原则展开研讨。
在此过程中,需要把握好四个关键问题。第一,地区安全治理机制不是对抗性的力量联合。不能成为类似美国主导的北约、西太平洋军事同盟那样为大国所操控、针对其他国家的对抗性组织。第二,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应有较大开放性。国际安全治理需要更多成员参与,封闭排他的机制最终必将缺乏代表性与公共性,利益视角的固化也将导致治理成效的弱化。第三,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应与区域经贸发展等制度紧密连接。大部分安全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发展的问题,安全又对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安全治理不能单纯将安全问题作为治理的全部,还应从安全的复合性特征入手,协同本地区在经济、环境、文化等领域的发展策略,更好地探寻安全矛盾的根源,削弱产生威胁的土壤环境。第四,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必须遵循主权独立和不干涉内政原则。侵犯他国主权,等于打开了动荡冲突的“潘多拉盒子”。美国惯于借助他国内部问题进行干涉,恶化地区安全稳定,也更深地破坏着两国间的合作。
美国正在推进富有地理和战略双重意义的“印太战略”。根据特朗普政府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定义,“印太”是指“从印度洋西海岸至美国东海岸的广大区域,这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63]2018年以来,特朗普政府加紧充实“印太战略”的具体内容,[64]相当程度上是为对冲、制衡“一带一路”倡议,从太平洋和印度洋东西两线遏阻亚欧大陆可能出现的“霸主”。“一带一路”建设已初具规模,尽管中方一再强调其经济倡议性质,美方也开始承认“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向全球提供新型公共产品的意义,无意采取针对性的反制措施,但仍对其背后的战略意图抱有疑虑,担心成为中国获取地缘政治影响力和全球领导作用的“工具”。中美双方均需慎重处理在亚欧大陆南缘自陆向海、由海向陆的战略交汇问题。中方需根据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更清晰地向世界展示“一带一路”是“谁的一带一路”,合理协调“中国的”与“世界的”两种属性的关系,把“一带一路”倡议真正做成中国引导全球治理变革、拓展开放合作的样板。美国等西方国家虽对“一带一路”倡议持反对或怀疑态度,但其大部分企业仍持开放态度,并渴望通过参与其中成为获利者。因此,可加快推动“一带一路”项目的第三方合作。立足长远,“一带一路”倡议与美“印太战略”和一些地区国家的“印太政策”都存在适当协调和合作共赢的空间,应尽量形成相互妥协容忍、即便对冲也不对撞的平稳关系。
六 结语
中美关系已经站在又一个关键的历史当口。美国调整对华战略,开启对华竞争,试图趁中国将强未强的“最后时机”压制、规锁中国,最好使中国未强先衰,抑或通过围堵和局部的权力交换,把中国的发展空间控制在有限范围内。无论今后是特朗普连任还是其他人上台,美国都不大可能重返过去对华接触合作的路线,中美关系都将呈现出竞争与合作并存、相当多时候竞争大于合作的新态势。大国战略竞争一旦开启,会步步深化、层层蔓延,成为一场全面的博弈,体现在中美关系上也不会例外。这场竞争和博弈是中国成长为世界强国过程中的必经洗礼。
面对美国发起的挑战,中国也要相应调整对美战略。中国所要做的是着眼长远,集中战略意念,保持战略定力,发扬斗争精神,积累博弈经验,以更强的主动性、灵活性和广泛性,在双边、地区、全球层面同时努力,积极充盈、综合调配政治、经贸、科技、军事、人文等方面以及多边框架下的政策工具,尽量稳定地推进中美关系的和平调整,争取与美方在竞争博弈中协调互动出新的合理关系范式,避免陷入美方鼓吹的“修昔底德陷阱”的渊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大势,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亦或自身行为深受中美关系走势影响的第三方力量,都有必要把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时间和空间,具备更多的人类的视角。
[1] [美] 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林华、曹爱菊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486页。
[2] Henry Kissinger, “Coming Conflict between US and China ‘Will be Worse than World Wars’,” November 15, 2019, https://summit.news/2019/11/15/kissinger-coming-conflict-between-u-s- and-china-will-be-worse-than-world-wars/.
[3] Paul Kenned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pp. xv.- xvi.
[4] 时殷弘、叶凤丽:《现实主义·理性主义·革命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传统及其当代典型表现》,载《欧洲研究》1995年第3期,第5页。
[5] 吴志成、王慧婷:《“修昔底德陷阱”对中美关系发展的非适用性分析》,载《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1期,第20页。
[6] Benjamin Frankeled,, London: Frank Cass, 1996, p. xviii.
[7][美]兰德尔·施韦勒:《应对大国的崛起:历史与理论》,载[美]阿拉斯泰尔·伊恩·约翰斯顿、[美]罗伯特·罗斯主编:《与中国接触——应对一个崛起的大国》,黎晓蕾、袁征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
[8], March 9, 2000, https://www.iatp.org/sites/ default/files/Full_Text_of_Clintons_Speech_on_China_Trade_Bi.htm.
[9]Sam Tangredi,,, Sacramento: University Press of the Pacific, p. 121.
[10]包括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发布污蔑中国在西方国家进行所谓“政治渗透”的《锐实力:上升的威权主义的影响》报告、亚洲协会的《中国影响力与美国利益:提高建设性警惕》等。
[11] Joel Gehrke,, Washington Examiner, https://www.washingtonexaminer.com/policy/defense-national-security/state-department- preparing-for-clash-of-civilizations-with-china.
[12] Tinatin Japaridze and Lincoln Mitchell, “On the Cyber Battlefield, China, Not Russia, Is the Biggest Threat to the U.S.,”, https://www.themoscowtimes.com/2019/02/25/in-the- cyber-battlefield-china-not-russia-is-the-biggest-threat-to-the-us-a64612; Carolyn Kenney, Max Bergmann and James Lamond, “Understanding and Combating Russian and Chinese Influence Operations,”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issues/security/reports/ 2019/02/28/466669/understanding-combating-russian-chinese-influence-operations/.
[13] 在原《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NAFTA)基础上重新谈成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SMCA)第32条规定:任何一方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议时,应允许其他各方在发出6个月的通知后终止本协议,并以它们之间的协议来取代之。
[14] 郑永年:《美国对中国的三大冷战判断》,全球化智库,http://www.ccg.org.cn/Expert/ View.aspx?Id=9321。
[15] Michael Mandelbaum, “Why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a New Containment Policy,”,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9-02-12/new-containment.
[16] 王缉思:《共同的利益,冲突的价值观》,全球化智库,http://www.ccg.org.cn/Expert/ View.aspx?Id=10691。
[17] “Vice President Mike Pence’s Remarks on the Administration’s Policy Towards China,” Hudson Institute, https://www.hudson.org/events/1610-vice-president-mike-pence-s-remarks-on-the- administration-s-policy-towards-china102018; “John S. McCain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2019,” Congress.gov,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5th-congress/house-bill/5515/ text; “China’s Influence & American Interests: Promoting Constructive Vigilance,” Hoover Institution, https://www.hoover.org/research/chinas-influence-american-interests-promoting-constructive- vigilance.
[18] 2018年10月30日,奥巴马时期美国国家安全理事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埃文·梅代罗斯(Evan Medeiros)在布鲁金斯学会举办的辩论会上发表此番言论。参见《美前官员:中国“核心利益”决定美中长期利益不可并存》,美国之音,https://www.voachinese.com/a/us-former-official- medeiros- china-core-interests-incompatible-with-us-long-term-interests-20181031/4637483.htm。
[19] “White House Issues Report Slamming ‘Socialism’ as Trump Blasts Democrats,” CNBC, https://www.cnbc.com/2018/10/23/white-house-issues-report-slamming-socialism-as-t-mp-blasts-democrats. html?&qsearchterm=opportunity%20cost%20of%20socialism.
[20] 杨文静:《美国对华贸易战的背后逻辑及其影响》,中美聚焦网,http://cn.chinausfocus.com/ finance-economy/20180619/29740.html。
[21] 2018年11月,美国前财长亨利·鲍尔森(Henry Paulson)在新加坡彭博经济论坛演讲时称,美中两国在贸易以外关键领域也存在利益分歧,即便双方达成贸易协议,两国之间紧张局势仍将持续。目前局面更应归咎于中国未能对外开放,而非仅是美国的对峙态度。美中若处理不好经贸争端,“经济铁幕”很快降临,世界也将因此分裂。参见“Remarks by Henry M. Paulson, Jr., 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t a Crossroads,” Paulson Institute, http://www.paulsoninstitute.org/news/ 2018/11/06/statement-by-henry-m-paulson-jr-on-the-united-states-and-china-at-a-crossroads/。
[22]Thomas G. Mahnken, Grace B. Kim, Adam Lemon, “Piercing the Fog of Peace Developing Innovative Operational Concepts for a New Era,”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 https://csbaonline.org/research/publications/piercing-the-fog-of-peace-developing-innovative-operational-concepts-for-a-/publication; Chris Dougherty, “Implementing the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Demands Operational Concepts for Defeating Chinese and Russian Aggression,”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https://www.cnas.org/publications/commentary/implementing-the-national-defense-strategy- demands-operational-concepts-for-defeating-chinese-and-russian-aggression.
[23]胡波:《美军海上战略转型:“由海向陆”到“重返制海”》,载《国际安全研究》2018年第5期,第73-97页。
[24] “Americans’ Favorable Views of China Take 12-Point Hit,” March 11, 2019, https://news. gallup.com/poll/247559/americans-favorable-views-china-point-hit.aspx.
[25] “Steve Bannon Called ‘American Prospect’ to Talk About Politics,” NPR, August 17, 2017, https://www.npr.org/2017/08/17/544105857/steve-bannon-called-american-prospect-to-talk-about-politics.
[26] Francis Fukuyama, “Exporting the Chinese Model,”, December 30, 2015, https://www.straitstimes.com/opinion/exporting-the-chinese-model.
[27]阎学通:《用“周边命运共同体”突破安全困境》,载《参考消息》2016年8月18日。
[28] 王传兴:《国际关系理论的范式及其命运》,载《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第92-98页。
[29] Cheng Li, Diana Liang, “Washington’s Search for a New Paradigm on China, Brookings,” November 19, 2018, https://www.brookings.edu/opinions/washingtons-search-for-a-new-paradigm- on-china/.
[30] “Texafornia Dreaming, America’s Future Will Be Written in the Two Mega-states,”, June 22, 2019, p. 7.
[31] 崔立如:《中美关系新格局下,加大有效风险管理》,载《文汇报》2018年12月6日,第4版,http://wenhui.news365.com.cn/html/2018-12/06/node64.html;《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接受凤凰卫视独家专访》,凤凰网,http://v.ifeng.com/201901/video_32542781.shtml。
[32]《习近平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中国外交部网站,2019年11月22日,https://www. fmprc.gov.cn/web/zyxw/t1718074.shtml;《王岐山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中国外交部网站,2019年11月23日,https://www.fmprc.gov.cn/web/zyxw/t1718324.shtml。
[33] 崔立如:《中美关系新格局下,加大有效风险管理》,载《文汇报》2018年12月6日,第4版,http://wenhui.news365.com.cn/html/2018-12/06/node64.html。
[34] 安刚:《以新范式迎接新常态》,载《世界知识》2019年第1期,第17页。
[35] 朱锋:《贸易战、科技战与中美关系的“范式变化”》,载《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9年第4期,第5页。
[36] 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2019-2024全球预测报告》,Игорь Иванов, Андрей Кортунов, Иван Тимофеев, Глобальныйпрогноз РСМД 2019-2024 [R] НПРСМД, 2019, http://russiancouncil. ru/activity/digest/longreads/globalnyy-prognoz-rsmd-2019-2024/?sphrase_id=26205805。
[37]修昔底德用“崛起”和“恐惧”来解释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以及因此诞生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概念,强调雅典的崛起所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参见晏绍祥:《雅典的崛起与斯巴达的“恐惧”:论“修昔底德陷阱”》,载《历史研究》2017年第6期,第109-125页。
[38] 参见顾伟、刘曙光:《试析美国战略文化的两面性》,载《美国问题研究》2016年第1期,第46-59页。
[39] 刘德斌:《管控中美关系“漂流状态”》,载《人民论坛》2013年第19期,第7页。
[40]小布什竞选总统期间,1999年11月19日在加利福尼亚州里根图书馆发表对外政策演讲时说的话最能反映美方这种心态:“我们必须把中国看清楚,而不是通过装腔作势和伙伴关系的透镜。所有这些事实都是我们必须正面加以面对的。中国是竞争者,而不是战略伙伴。我们必须不抱恶意地与中国打交道,但也必须不抱幻想。”参见Governor George W. Bush, “A Distinctly American Internationalism,” https://www.mtholyoke.edu/acad/intrel/bush/wspeech.htm。
[41]基辛格助手乔亚舒·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在2010年为《时代》周刊撰文中率先提出中美只有“共同进化”(Co-evolution)才能维护各自根本利益。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强调中美应“共同进化”,并且认为“共同进化”须处理好三层关系,一是大国正常交往过程中的问题,双边磋商结果大体能解决这一类问题;二是尝试把对常态性危机的讨论提升到更全面的框架,消除紧张状态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三是形成共同的区域政治概念,构造类似大西洋共同体的太平洋共同体,共同参与建设世界。王缉思等中国学者呼应了“共同进化”的设想,认为其要旨是在合作与竞争中促进各自利益,核心是两个国家秉持不同的价值和规则、追求不同的政治秩序,但均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内,只能根据自己的发展轨道平行前进,相互补充而非相互损害,能合作就合作,无法合作也不能对撞。参见Joshua Cooper Ramo, “Hu’s Visit: Finding a Way Forward on U.S.-China Relations,”, April 8, 2010, http://content.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 0,9171,1978756,00. html;[美]亨利·基辛格:《论中国》,胡利平、林华、杨韵琴、朱敬文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515-518页;王缉思:《“两个秩序”下,中美如何共同进化》,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http://www.iiss.pku.edu.cn/specialist/comment/2015/682.html。
[4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中国外交部网站,2018年12月2日,https://www. fmprc.gov.cn/web/zyxw/t1618093.shtml。
[43]《国新办举行中美经贸磋商有关进展情况新闻发布会》,中国商务部网站,2019年12月13日,http://www.scio.gov.cn/xwfbh/xwbfbh/wqfbh/39595/42254/index.htm。
[44] 刘伟、张辉主编:《全球治理:国际竞争与合作》,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页。
[45]《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 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15- 10/13/content_2946293.htm。
[46] [美] 詹姆斯·斯珀林:《21世纪的全球治理与安全》,侯尤玲译,载尹继武、李月军主编:《全球安全、冲突及治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年版,第202页。
[47] 欧阳康主编:《全球治理与国家责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41页。
[48] 尹继武、李月军主编:《全球安全、冲突及治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年版,第2页。
[49] 李开盛:《中美战略竞争管控的制度主义分析》,载《当代美国评论》2018年第4期,第2页。
[50] “Warning Against ‘Great Fracture’, Secretary-General Calls on General Assembly to Reconnect With Organization’s Values, Uphold Human Rights, Restore Trust,”https://www.un.org/ press/en/2019/ sgsm19760.doc.htm.
[51]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White House,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p. 3.
[52] “Remarks by Vice President Pence at the Frederic V. Malek Memorial Lecture,” The White House,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vice-president-pence-frederic-v-malek- memorial-lecture/; “A Conversation with Vice President Mike Pence,” Wilson Center, https://www. wilsoncenter.org/event/conversation-vice-president-mike-pence.
[53]左希迎:《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图景》,载《战略决策研究》2018年第2期,第86页。
[54] 王缉思认为,中美都在国内进行着引人注目的政治试验,其结果要到几十年后方能显现,长远看也许会发现彼此拥有更多相通的精神基础。参见王缉思:《共同的利益,冲突的价值观》,全球化智库,http://www.ccg.org.cn/Expert/View.aspx?Id=10691。
[55]根据传统定义,战略稳定是指敌对双方因持有决定性的核报复能力,而缺少先发制人的动力,形成的一种基于相互核威慑的稳定状态。这里阐述的是广义的战略稳定,即,互为竞争对手的双方均具有某种战略能力,使得对方首先采取任何重大战略举措均不能因此而获得其希望的益处,从而避免其首先采取这种战略举措的可能性。各自战略纵深、军力规模以及国家意志、作战概念、战斗经验等软性资源状况决定了两国在军事领域构建战略稳定并非没有可能。
[56] 葛腾飞:《美国战略稳定观:基于冷战进程的诠释》,载《当代美国评论》2018年第4期,第88页。
[57] 罗曦:《构建战略稳定:中美军事领域的重大课题》,载《世界知识》2019年第1期,第18-21页。
[58] 互为对手的一方采取军备发展的措施不会打破双方长久以来建立的“战略平衡”状态,不会导致其谋取战略优势的结果,也就不会引起另一方采取相应的发展军备措施,避免螺旋式军备竞赛的发生。
[59] 互为对手的双方在彼此关系发生危机时,能通过已建立的联系渠道控制、化解危机,使双边关系平复到危机前状态。
[60] 邹治波、刘玮:《构建中美核战略稳定性框架:非对称性战略平衡的视角》,载《国际安全研究》2019第1期,第40-59页。
[61] 胡波:《改善中美海上战略互动的路径在哪》,载《环球时报》2019年2月27日,第14版。
[62]2014年10月,中美两国国防部签署《中美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和《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谅解备忘录。2015年,中美重大军事相互通报机制新增“军事危机通报”附件,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新增“空中相遇”附件。此外,中美及西太平洋其他一些国家在2014年西太平洋海军论坛上通过了《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美方还提议与中方探讨建立防止危机冲突沟通框架。
[63]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White House,” December 18, 2017, pp. 45-46,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national-security-strategy-united-states-america.
[64] 美国的措施包括:经济上聚焦数字经济和网络安全、能源和基础设施发展等,先期投入1.13亿美元,以调动更多私人资本参与具体行动计划,加强美商业界扩展与印太地区的联系。安全领域聚焦“海上安全”、人道主义援助和减灾、维和能力提升、打击跨国犯罪,以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国为重点,并加大对孟加拉湾沿岸国的投入。2018年5月,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正式更名为印太司令部。逐步加大对民主与治理问题的关注,宣布推动耗资4亿美元的“印太透明倡议”,支持该地区的“负责任政府”并推动民主和法治,增强能力建设,提高它们“捍卫自身主权的能力”,避免落入“别国制造的债务陷阱”。政策协调架构方面,大力推动“美日印澳”四边机制(Quad)重启和升级,军方人士日后也或会直接参与。参见赵明昊:《美国怎样撬动“印太战略”》,澎湃新闻,2018年8月24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376978;赵明昊:《美国正赋予“印太战略”实质内容》,载《世界知识》2019年第5期,第55-57页。
安刚,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世界知识》杂志编辑(北京邮编:100020);王一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邮编:100872);胡欣,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战略与安全研究所副教授(南京邮编:210039)。
10.14093/j.cnki.cn10-1132/d.2020.02.002
D815.5;D822
A
2095-574X(2020)02-0023-26
2019-09-04】
2020-01-07】
*本文系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全球安全治理研究”项目成果。作者感谢《国际安全研究》编辑部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文中疏漏由作者自负。
【责任编辑:苏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