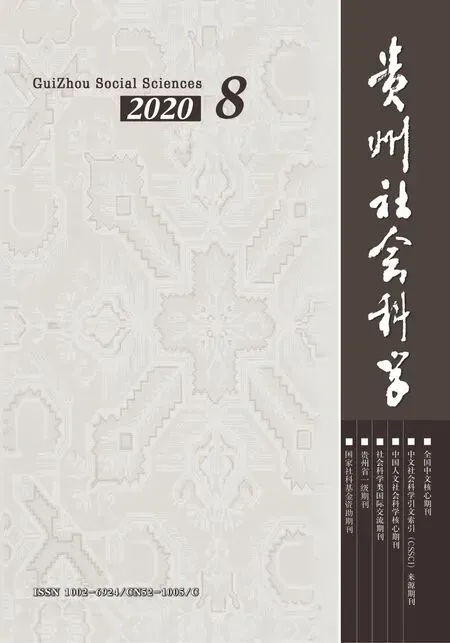中国现代语言变革中的文学本位观
张卫中 张 璐
(1.江苏师范大学,江苏 徐州 221100;2.中国地质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4)
近代以来,汉语书面语中的“文白之变”是中国语言变革的一个主要内容,这个变革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很多知识者参与其中;对待这场变革,他们或支持、或反对、或折衷,在文坛上也有过激烈的争论。但是此前,很多研究者大都将时人对文言与白话的态度归因于他们立场的趋新与守旧,而实际上,这个问题比人们的想象要复杂得多。语言文字是一种公共符号,社会不同阶层、不同领域对语言都有特殊的要求,而语言只有一种,因此社会不同阶层、不同领域的人都希望能对语言变革有所干预,让这个变革更符合自己的需要,更多惠及本阶层、本领域的使用者。这样,一种新式书面语的建构,就必然面临来自各个方面的争夺。一个知识者在文言与白话之间选边站队或许主要不是出于其立场的趋新或守旧,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站在哪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
在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诗歌在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在数千年的文学史中,文言也被打造成一种诗性的语言,那种要求文字与文采合二而一的观念在很多文人心目中根深蒂固。正是从这个立场出发,在晚清和“五四”,很多知识者明知白话文有利于日常实用和普及教育,但对文言还是有难以割舍之情;他们要么拒绝白话文,要么希望文言与白话并存。在“五四”前后关于文言与白话的论争中,这种语言的文学本位观虽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它很大程度上超越了趋新与守旧的界限,无论在所谓趋新派、守旧派还是折衷派中都能见到。这种以文学为本位的立场是当时语言论战中的重要一极,在文言白话争夺主导权,以及在现代白话文的建构中,它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折衷派的文学本位观
在今天看来,胡适、陈独秀当年提出废文言兴白话的主张也并非天经地义,事实上,文言与白话各有优点,除非放在时代变革的大局中,能够找到变文言为白话的必然依据,而仅就两种语言自身的优劣来比较,其实很难分出轩轾。在“五四”时期,当时的知识者很少能够像胡适、陈独秀那样站在时代的高度认识“文白之变”的意义,因而一些知识者对这个变革提出各种异见也是非常自然的。
1917年1月,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在《新青年》2卷5号上发表以后,很快就在文坛上产生了一些反响,最早对胡适语言变革主张做出回应的是持有“凡庸的折衷论”、后来被称为折衷派的一群知识者(郑振铎语)。这些知识者中既有像常乃德这样的在校学生,也有像朱经农、任鸿隽这样已经有一定声望、地位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对新文化的态度很难简单的用趋新与守旧来概括,他们更多是就事论事地从文言、白话的优点和缺点讨论变革的必要性。中国传统文人接受的教育其实一开始就包含了文学教育,在他们的观念中,文字之美本来就是学习、使用文字的必然要求,古人并不满足于正确地使用文字,而是希望通过文饰来美化文字。如林语堂所说:一篇文章只有“可颂可歌,可以一唱三叹,才叫文章。”[1]198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因此在胡适发起白话文运动后,很多人一方面部分支持白话文运动,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从文学的本位出发,认为白话文直白、简陋,不足以为文学所用,因而对胡适的白话文理论提出质疑。
在所谓折衷派的观点中,一个常见的主张是将应用之文与文学之文两分,他们认为,文学之文不同于应用之文,前者别有一种要求,像用典与对仗都是文学语言特有的修辞手段,并不能一概加以反对。他们肯定白话文的优点,但也认为白话确实有俚俗之弊,担心它短时间内不能满足文学之用。
事实上,早在《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之前,胡适在1916年10月寄陈独秀的一封信中(发表于《新青年》2卷2号)就概述了自己的文学变革思想,这篇文章中也已提到了改革文学的“八事”。而其后不久,在《新青年》2卷4号的“通信”栏中就刊出了常乃德给陈独秀的一封信,信中对胡适提出的“八事”有一个评说。他的基本观点就是,中国的“文”应当有“说理纪事之文”与“美术之文”的区别,而“文学之文”有自己特殊的要求。从这个观点出发,他认为“用典”与“对仗”都不应当废除。他说:“胡先生以古文之敝,而倡改革说,是也,若因改革之故,而并废骈体,及禁用古典,则期期以为不可。夫文体各别,其用不同,美术之文,虽无直接之用,然其陶铸高尚之理想,引起美感之兴趣,亦何可少者。”他说:“文学改良说理纪事之文,必当以白话行之,但不可施于美术之文耳。”他说:“为今之计,欲改革文学,莫若提倡文史分途,以文言表美术之文,以白话表实用之文,则可不致互相牵掣矣。且白话作文,亦可免吾国文言异致之弊,于通俗教育,大有关系。”[2]
其后不久,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后,余元濬在《新青年》3卷3号“读者论坛”栏目中发表的《读胡适先生<文学改良刍议>》,也对胡适提出的“八事”做了一番评说。他对胡适的“八事”多数表示赞同,但也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关于“不避俗语俗字”一条,他不完全同意胡适的观点。他指出:“末所谓‘不避俗语俗字’,此不能不于应用上规定其范围。盖文字之为物,本以适用为唯一之目的的。‘俗语俗字’虽有时可以达文理上之所不能达,然果用之太滥,则不免于繁琐。易言之,即用文理仅一二语即足以表出者,用‘俗语俗字’则觉连篇累牍,刺刺不能自休,且亦长易惹起人之厌恶,……”关于文言与白话的使用,余元濬还是沿袭了晚清学人的主张,认为白话适应于普及与应用,文言则可以用于文学与学术,它们在不同领域可以发挥不同的功能。[3]
“五四”时期在语言变革问题上出现的折衷派大都并不反对使用白话文,但是反对废弃文言文,而其理由主要还是考虑文言与文学、特别是与诗歌的特殊联系,认为要做出精美、高深的文学,不能单靠白话,至少应当兼取白话与文言。正是因为文学的需要,应当给文言留下一块保留地。1918年胡适的同乡黄觉僧在《折衷的文学革新论》中也指出:“文以通俗为主,不避俗字俗语,但不主张纯用白话。”他给出的理由是:“文学改革固当以一般社会为前提。然文之中有所谓应用的,美术的二种。即以欧人之文学言,亦复如是。是美术文之趋势如何,无讨论之必要。何者?研究美术文者,必文学程度已高,而欲考求各种问题真相之人,与一般社会无甚关系。愚意通俗的美术文(用于通俗教育者)与中国旧美术文可以并行,以间执反对者之口。旧美术文无废除之必要。”[4]黄觉僧的意思还是把文学视作一种高高在上的活动,这种活动应是由高高在上的人用高高在上的语言创造,因此创造文学不能纯用白话。
很多折衷派文人认为文言经过文人数千年的打磨、锤炼,有简约、典雅的特点,是典型的文学语言,而白话文一直偏居民间,是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有直白、简陋之弊,不适宜文学,特别不适宜诗歌之用。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他们多主张白话、文言并存,白话用之于普及教育与日常交际,文言则用之于文学。
二、守旧派的文学本位观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守旧派主要是指站在新文学阵营的对立面,反对新文学运动的一批人,包括了林纾、严复以及学衡派和甲寅派的人。但这些人的守旧,并不意味着他们整体否定中国现代化进程,他们更多地是眷恋传统文化与语言,反对文化与语言变革。他们反对白话文运动也更多地是立足文学的立场,认为文学对语言有特殊要求,普及教育与日常实用可以用白话,打造高雅的文学作品还是要依靠文言。
在守旧派中,最早站出来表达对胡适倡导白话文运动不满的是林纾。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在《新青年》刊出后,林纾紧接着就在上海的《民国日报》上发表《论古文之不宜废》,在陈述保存古文的理由时,他说:“方今新学始昌,即文如方、姚,亦复何济于用?然而天下讲艺术者仍留‘古文’一门,凡所谓载道者皆属空言,亦特如欧人之不废腊丁耳。知腊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有其不宜废者。”[5]在这段话中,林纾将“讲艺术者”与“仍留‘古文’一门”联系起来,意思还是将古文视为一种艺术语言,一种能为艺术所用的语言,言外之意在于文言因为是艺术语言而有保留的价值。
林纾之后,在学理上与新派文人有一番论争的是学衡派。20世纪20年代初出现在文坛上的学衡派与传统守旧派一个明显的不同,是他们并非单纯依托中国传统思想资源对抗启蒙新潮,他们更多地受到白璧德人文主义的影响,更多地是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中,依托人类多种文化传统对抗新文化运动。在学衡派诸人中,胡先骕是对文言、白话的优劣、废存问题关心最多的一个,他的观点在学衡派中也很具有代表性。早在《学衡》杂志创刊之前,胡先骕就已经对胡适的白话文理论提出质疑。他于1919年在《东方杂志》16卷3期上刊发的《中国文学改良论》(上)中,就认为文学对语言有特殊要求,文学语言是一种特殊语言,而就这一点说,文言明显优于白话,在他看来,这也是文言不宜废的主要理由。胡先骕指出:“文学自文学,文字自文字,文字仅取其达意,文学则必达意之外,有结构,有照应,有点缀。而字句之间,有修饰,有锻炼。凡曾习修辞学作文学者,咸能言之,非谓信笔所之,信口所说,便足称文学也。故文学与文字,迥然有别,今之言文学革命者,徒知趋于便易,乃昧于此理矣。”他认为,无论是戏剧还是小说,其语言都与日常语言有一定距离。“莎士比亚之戏曲,所用之字至万余,岂英人日用口语须用如此之多之字乎。”他说:“小说亦本以白话为本者也。今试读Charlotte Bronte之著作,则见其所用典雅之字极夥。其他若Dr.Johnson之喜用奇字者,更无论矣。”谈到“美术之韵文”时,他指出:“韵文者,以有声韵之辞句,传以清逸隽永之词藻,以感人美术,道德,宗教,之感想者也。故其功用不专在达意,而必有文采焉。而必能表情焉、写景焉。再上,则以能造境为归宿。氵弥尔敦但丁之独绝一世者,岂不以其魄力之伟大,非常人所能摹拟耶。我国陶谢李杜过人者,岂不以心境冲淡,奇气恣横,笔力雄沈,非后人所能望其肩背耶。不务于此,而以为白话作诗始能写实,能述意,初不知白话之适用与否为一事,诗之为诗与否又一事也。且诗家必不能尽用白话,征诸中外皆然……”[6]
在20世纪20年代,站在文化守成立场上反对白话文的还有甲寅派。作为代表人物的章士钊在论及白话不及文言时,主要也是从文学角度来谈论这个问题。他的一个观点是,创造美文只有天才能做到,后人只能揣摩而得。就这一点讲,文言有丰厚的传统,历史上有很多大师的文章可以师法,而白话缺少这样的传统,也没有足够的范例可以师法,因此要做白话又要使其美就难上加难。在《答适之》一文中,他一开始就拿美文说事。他说:“适之谓白话本身,能为美文,此语在逻辑为可能,但处今日文化运动之下,其的决不能达。”其原因是:“凡人类之心思,以何种方式,施于文字,使人见之而生美感,大是宇宙间之秘事,能得其秘,斯为文家。古今中外之大文家不多,足证此秘未尽宣泄。又人类为富于模仿性之动物,而语言文字,尤集此性所寄之大成,从古文豪,绝不由胎息之功而成名者乃至罕。……前人既有独得,后人自审无出于右,其揣摩乃不期然而然。由是而公美成,由是而文学有史,此普通论文之理也。至白话文学,则与此异趣。吾国语文,自始即不一致,以字为单音,入耳难辨,凡于义无取,徒便耳治之骈枝字。语言中为独多,以此骈枝字尽入于文,律之文章义法,殊无惬心贵当之道。古来除语录小说及词曲之一部外,无以白话为文者此也。今以白话为文,因古之人无行之者,胎息揣摩,举无所施,其事盖出于创,天下事之创者,惟天才能之,岂能望之人人。”所以,“今之白话文,差足为记米盐之代耳,勉阅至尽,雅不欲再,漠然无感美从何来。”因而他认为“文章大业非白话之力所胜。”[7]要做美文必须还要文言。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守旧派并不是他们先有了守旧的立场然后反对白话文,相反,他们立场上的守旧恰恰是因为他们对传统文化与语言的眷恋,后者应当是原因,并非单纯作为结果。而守旧派反对白话文的一个重要原因则是他们认为白话文不能胜任为文学、特别是为诗歌所用,他们是以文学的名义要求保留文言。
三、趋新派的文学本位观
与白话文相比,文言丰富、细腻、简练、含蓄,更适合文学、特别是适合为诗歌所用,对于这一点,新派作家也并非视而不见。但他们与折衷派、守旧派不同的是,他们更多地从社会大局出发认识白话的价值,他们即便看到了白话文在这方面的不足,也不会因此成为白话文的反对者。他们更多地是寻找变通的办法,解决在语言选择上面临的难题。当然他们提出的办法也不过是,或者让白话成为主流书面语,但不赞成马上废除文言;或者即便赞成以白话代文言,但也要求白话文能借鉴、吸收文言的成分,让其兼有文言的优点。非常有意思的是,他们提出的解决办法与折衷派、守旧派其实还是有很多相似之处。
在新派知识者中,最早提出在语言中分出应用与美术两种文字的是陈独秀。1916年10月胡适在寄陈独秀的信中提到了对文学改良“八事”的设想,陈独秀在回书中说:“除五八二项,其余六事,仆无不合十赞叹,以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在谈到第五项“须讲求文法之结构”时,他说:“仆意中国文字,非合音无语尾变化,强律以西洋之Gramma,未免画蛇添足……且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不同,上未可律以论理学,下未可律以普通文法,其必不可忽视者修辞学耳。”在谈到第八项:“须言之有物”时,他说:“若专求‘言之有物’,其流弊将毋同于‘文以载道’之说,以文学为手段为器械,必附他物以生存。窃以为文学之作品,与应用文字作用不同,其美感与伎俩,所谓文学美术自身独立存在之价值,是否可以轻轻抹杀?”[8]1916年底,陈独秀在回复常乃德的信中再次提到:“足下意在分别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作用不同,与鄙见相合。”[9]
在这个问题上,蔡元培的观点与陈独秀大致相似,他也认为语言应作应用文与美术文的划分,而且,应用文需用白话,美术文则用文言。1919年蔡元培在一次演讲中,一方面“断定白话派一定占优胜”,一方面又认为“文言是否绝对的被排斥,尚是一个问题。”他说:“照我的观察,将来应用文,一定全用白话。但美术文,或者有一部分仍用文言。”[10]
在语言文字的划分以及文言的废存问题上,刘半农的观点稍有不同。他认为,语言文字的界说当取法西文,“分一切作物为文字Language与文学Literature二类。”关于“文字”,他说:“西文释Language一字曰,‘Any means of conveying or communicating ideas’,是只取其传达意思,不必于传达意思之外,更用何等工夫也。”“至如Literature则界说中既明明规定为The class of writings distinguished for beauty of style,as poetry,essays,history,fictions,or belles-lettres自与普通仅为语言之代表之文字有别。”关于文言的废存问题,刘半农主张:“文言白话可暂处于对待的地位。”至于其中的原因,他说:“以二者各有所长、各有不相及处,未能偏废故。”然后他进一步解释说:他虽然对胡适、陈独秀的理论深信不疑,“但就平日译述之经验言之,往往同一语句,用文言则一语即明,用白语则二三句犹不能了解。”他说:“今既认定白话为文学之正宗与文章之进化,则将来之期望,非做到‘言文合一’或‘废文言而用白话’之地位不止。此种地位,既非一蹴可,几则吾辈目下应为之事,惟有列文言与白话于对待之地,而同时于两方面力求进行之策。”[11]
在文言废存问题上,新派作家除了通过将语言做“应用之文”与“文学之文”两分,从而以“文学之文”的名义保存文言,他们设想的另一种方法是让白话大量吸收文言的有益成分,在白话兼有文言的表意优势后,是否废除文言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傅斯年1918年发表于《新青年》4卷2号上的《文言合一草议》中就指出:“废文词而用白话,余深信而不疑也。虽然,废文词者,非举文词之用一括而尽之谓也。用白话者,非即以当今市语为已足,不加修饰,率尔用之也。”至于原因,他说:“文言分离之后,文词经二千年之进化,虽深芜丽杂,已成陈死,要不可谓所容不富。白话经二千年之退化,虽行于当世,恰合人情,要不可谓所蓄非贪。以白话为本,而取文词所特有者,补苴罅漏,以成统一之器,乃吾所谓用白话也。正其名实,与其谓‘废文词用白话’,毋宁谓‘文言合一’较为惬允。”傅斯年认为白话、文言各有优点缺点,“切合今世,语言之优点。其劣点,乃在用时有不足之感。富满充盈,文词之优点,其劣点,乃在已成过往。故取材于语言者,取其质,取其简,取其切合近世人情,取其活泼饶有生趣。取材于文词者,取其文,取其繁,取其名词剖析毫厘,取其静状充盈物量。”[12]
在实现以白话代文言之后,为什么要大量吸收文言成分,以及怎样吸收文言成分,关于这个问题,周作人做过详细的阐释。在《国语改造的意见》一文中他一方面主张使用国语,但另一方面,他又不主张“国语神圣”,因为在周作人看来,白话文要担负“国语”的责任,就有“改造的必要”。他说:“现在的国语运动却主张国民全体都用国语,因为国语的作用并不限于供给民众以浅近的教训与知识,还要以此为建设文化之用,当然非求完善不可,不能因陋就简的即为满足了。”周作人说:“现在的白话文诚然是不能满足,但其缺点乃是在于还未完善,还欠高深复杂,而并非过于高深复杂。”“久被蔑视的俗语,未经文艺上的运用,变缺乏细腻的表现力,以致变成那种幼稚的文体,而且将意思也连累了。”他认为,明清小说的语言“最大的缺点”是“文体的单调”,他说:“明清小说专是叙事的,即使在这一方面有了完全的成就,也还不能包括全体,我们于叙事以外还需要抒情与说理的文字,这便非是明清小说所能供给的了。其次,现代民间的言语当然是国语的基本,但也不能就此满足,必须更加以改造,才能适应现代的要求。”关于改造国语的方法,他提到的第一条就是“采纳古语”。他说:“现在的普通语虽然暂时可以勉强应用,但实际上言词还是很感缺乏,非竭力的使他丰富起来不可。”[13]
在中国古代,文字与文学之间并无明显界限,传统文人接受文字训练同时也是接受文学训练,他们的专长首先就是诗与文;很多文人,不管从事什么职业,首先都是“文学家”。即便到了“五四”以后,很多现代文人还是秉承了这个传统。因而在白话文运动兴起以后,他们首先就是从文学角度对这个运动做出评判,这个时期,很多拥有话语权的知识者都是站在文学的立场上发声,要求多方面照顾文学、特别是诗歌的特殊要求。他们的干预对现代文学语言的发展走向产生了很大影响,对现代文学语言的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