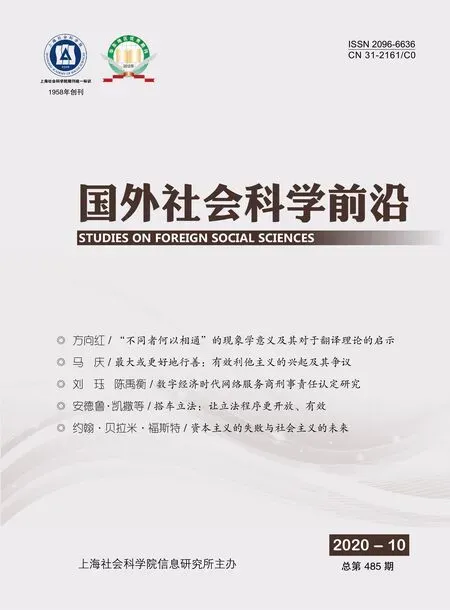斯图亚特·霍尔关于撒切尔主义的情势分析 *
李 开
内容提要| 20世纪70年代以来,斯图亚特·霍尔坚持从文化、话语和意识形态维度对撒切尔主义所主导的英国文化、社会情势进行分析,旨在阐明撒切尔主义在市民社会、文化以及公共领域获得话语权和文化领导权的内在机制,从而为英国左翼重建文化领导权提供有效策略。在欧美各国右翼崛起的当下,霍尔对撒切尔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的情势分析成为透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深层结构性变化的新视角。
20世纪70年代以来,战后英国社会经历了传统文化和社会民主共识意识形态逐渐瓦解的过程。作为英国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等人对战后英国青年亚文化的描述和解读表明,英国青年并没有在战后的“丰裕社会”(affluent society)中迷失方向,而是通过个性化、符号化、商品化的生活方式,进行仪式性的反叛或抵抗。在消费主义和新媒介兴起的战后时期,新兴的大众文化、青年亚文化以及来自英国前殖民地的少数族裔冲击着英国传统文化,从而引发了广泛的社会焦虑。这种文化冲击加上经济衰退,加剧了社会撕裂,引发了左翼的文化领导权危机。重建文化领导权和社会秩序已成为英国左翼政治的必然选择,但英国左翼当时没能及时做出相应调整。霍尔等人的合著《探察危机:行凶抢劫、国家、法律与秩序》(Policing the Crisis: Mugging, the State, and Law and Order,以下简称《探察危机》)已经预示了英国社会民主共识的危机,指出英国社会开始从共识社会向威权主义法制社会转变,直至撒切尔主义(Thatcherism)情势的历史性启幕。在霍尔看来,这种新兴历史情势表明英国政治、社会和文化开始被以“威权民粹主义”(authoritarian populism)为实质的撒切尔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所支配。
情势(conjuncture)这一概念可以追溯至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Joseph Bloch)的一封信中指出历史发展是“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05页。所造成的结果。法国年鉴派历史学家费尔南多·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为了满足研究漫长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提出了事件、情势和结构的历史时段划分方法,分别对应短时段(瞬间)、中时段和长时段。②[法]费尔南多·布罗代尔:《论历史》,刘北成、周立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0页。后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霍尔、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等有机知识分子坚持运用情势分析研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运动趋势,在知识实践中阐发、完善关于情势与情势分析的理论。综合上述思想家和理论家的界定,情势可被视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层面的种种历史力量博弈所形成的复杂变局,它是多种矛盾在同一历史时刻凝缩的场域,往往伴随有机危机——经济、政治、社会层面影响深远的结构性矛盾和变化。……情势分析是对特定情势的解读,探索的是各领域的深层结构性运动”。①李开:《矛盾、危机、聚变——论情势分析与文化研究》,《文化研究》2018年第35辑。作为新左翼知识分子,面对当代英国及全球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和新趋势,霍尔在知识实践中将对资本主义当下历史进行情势分析当作实现其历史使命的主要路径之一。
霍尔的兴趣在于理解特定的历史情势瞬间,并找到介入情势的方式,而不局限于寻找特定情势型构的某些看似普遍的逻辑。②Paul Bowman, Post-Marxism Versus Cultural Studies:Theory, Politics and Interventio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59.从20世纪70年代末“伟大的右转秀”(The Great Moving Right Show)开始,霍尔持续运用情势分析撰文批判撒切尔主义,直至2008年新自由主义出现危机,前后持续三十余年。起初,这些文章主要发表在《今日马克思主义》(Marxism Today)和《新社会主义者》(New Socialist)两份社会主义刊物上,后又结集出版为《撒切尔主义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Thatcherism)和《艰难的复兴之路:撒切尔主义与左翼危机》(The Hard Road to Renewal: Thatcher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Left),成为解读撒切尔主义意识形态运行机制的关键著述。引发霍尔关注撒切尔主义的主要因素是撒切尔主义在经济衰退时所建构的文化领导权。撒切尔主义批判是霍尔从文化、话语、意识形态的维度所进行的情势分析,有其具体的政治目标,即分析撒切尔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取得文化领导权的机制,为左翼政治提供反文化领导权的经验教训和战略对策,从而实现改变世界的愿景,这客观上也为撒切尔政府提供了执政镜鉴。
一、撒切尔主义的多重面向
撒切尔主义是霍尔在“伟大的右转秀”一文中首创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概念,主要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与撒切尔政府相关的意识形态趋势和主导文化社会思潮。撒切尔主义意识形态是英国右翼针对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危机和文化的全球性危机做出的回应,塑造了以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当代资本主义体系。在资本主义危机中,以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为代表的右翼成功抓住了英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机遇,而左翼则对当时的全球性变化置若罔闻,造成了自身发展的长期危机。撒切尔主义文化领导权计划处于全球化发展的加速阶段之初,其影响超出英国,波及全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版图。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的全球化情势中,这一转变过程“将经济生活、政治文化、公共制度、社会关系、媒体话语、态度及价值观用于满足全球化新阶段的迫切需要”。③Stuart Hall and Tony Jefferson(eds.), 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Youth Subcultures in Post-War Britain, 2nd, London:Routledge, 2003, p. xxx.撒切尔主义的崛起表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走向新自由主义情势。霍尔从情势分析的视角将撒切尔执政的十余年视为二战后英国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历史性转折,具有独一无二的历史特定性。
从经济角度看,撒切尔主义是新自由主义的集中表现,它推崇以自由市场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同时积极发挥国家的干预作用,力图解决英国在以福利国家为核心的社会民主共识之后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挽回大英帝国经济渐衰的趋势。从社会角度看,撒切尔主义旨在全面重组英国社会,恢复法律与秩序。从政治角度看,撒切尔主义对社会运动采取强制手段,致力于重构阶级与政党之间的关系,消弭国家与市民社会、公共与私有之间的边界。从文化角度看,撒切尔主义计划力图用“逆向式现代化”(regressive modernization)话语规训和教化社会,促进思想文化进步,其结果反倒是促使思想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的倒退。从话语角度看,撒切尔主义的实质可概括为威权民粹主义。威权民粹主义话语的成功之处在于它能够把“相互矛盾的话语在同一种意识形态内接合起来”,①Stuart Hall, The Hard Road to Renewal: Thatcher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Left, London: Verso, 1988, p. 10.因为这一概念本身就是包含悖论,它将不同的话语元素统一为一种治理哲学,涵盖了英国人引以为荣的保守传统、民族伟大的优越感、帝国衰退的失落感、更严格的社会管控、经济宽松和自由市场等方面的话语。同时,它能够表现“上层社会的恐惧和焦虑,并将其接合为右派共识”。②Nick Stevenson, Understanding Media Cultures: Social Theory and Mass Communication, 2nd,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2002, p. 38.从意识形态角度看,撒切尔主义是一种重建文化领导权的计划,力图在自由市场与保守主义之间铸就新的话语,在发挥自由话语作用的同时,从传统话语型构中重建大英帝国的民族性和民族文化,试图治愈帝国衰落所造成的民族心理创伤,应对文化身份危机。
在撒切尔夫人的第一届任期内(1979—1983),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4.2%,工业生产下降超过10%,制造业下降17%,失业率高达141%,失业人口超过三百多万。③James Procter, Stuart Hall, London: Routledge, 2004, p.97.但1983年撒切尔夫人第二次当选首相。霍尔认为,撒切尔主义获胜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其经济政策,而在于能在特定的历史情势中建构主导文化和意识形态话语的文化领导权。从第二届任期开始(1983—1987),英国经济开始出现复苏迹象,增长势头渐强,通胀率和抵押率已降至福利国家时期以来的最低水平,但是失业人口仍高居不下。尽管如此,保守党仍保住了撒切尔夫人的第三个任期,撒切夫人也成为二战以后英国最受欢迎的首相。撒切尔夫人为什么能够在经济状况不利的形势下取得连任,连续执政11年半,并享有持久的权威和影响力?以工党为代表的左翼人士对此大惑不解。霍尔指出,普通百姓之所以被撒切尔主义征服,不是因为他们都是傻瓜,或者被虚假意识所蒙蔽,而是因为“作为意识形态的撒切尔主义能够解决一个民族的恐慌、焦虑以及失去的身份等问题。它引导(英国人民)通过形象思考政治,能够应对(英国人民)的集体幻想,将英国视为想象的共同体,能够处理社会想象的问题”。④Stuart Hall, The Hard Road to Renewal: Thatcher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Left, London: Verso, 1988, p. 167.也可以说,撒切尔主义通过话语、形象将其政治和意识形态主张嵌入日常生活经验和常识,将英国普通百姓纳入“逆向式现代化”历史工程,成功建构了文化和道德上的领导权。霍尔之所以能够预测到撒切尔夫人的选举胜利,是因为他将日常生活中的话语变化视为社会变迁的指数,并从历史维度对这些社会文化现象进行情势分析,发现人们在公共领域中不再使用工党主义、福利国家、社会民主之类的话语,而开始使用成本效率、货币价值、选择、自由市场等话语。日常生活的话语转变意味着人们开始接受并使用另一套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话语系统。
1987年,依靠其稳固的文化领导权,撒切尔夫人第三次当选英国首相。工党在传统的就业、医疗、住房和教育方面的福利国家政策方面获得支持,总体表现超过预期,但最终再次落败。霍尔指出,获得选举胜利的关键并非具体的社会政策,而在于能够激发选民想象的政治形象,因为政治形象建构是一个关键的意识形态问题。霍尔断言:“撒切尔主义的胜利根源并不是任何临时支持的波动,而是重塑英国政治版图的深层运动和趋势。”①Stuart Hall, 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 The Great Moving Right Show and other Essays, Sally Davison, et al. (eds.), 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238.撒切尔主义不仅是改变经济运行方式的计划,而是一项旨在改变英国人思想意识的工程,有其深刻的文化根源。其实,自1979年以来,撒切尔主义运用意识形态的技术已几近完美,意识形态策略成为撒切尔主义的制胜法宝。与此不同,工党虽然努力吸取以往失败的教训,开始重视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但其所面临的问题是结构性的有机危机,找到合理的危机解决路径尚需时日。
二、撒切尔主义之前的英国文化与社会情势
霍尔首先从政治与社会维度描绘出英国战后至撒切尔夫人当选这一时期的历史情势,认为社会民主共识是这一时期英国政治的主要特征。英国社会出现新的不成文的社会契约,相互冲突的社会利益之间达成历史性的妥协一致。右翼舍弃反动政策以及自由市场,而勉强接受福利国家、综合素质教育、凯恩斯主义、全面就业作为劳资之间达成妥协的条件。作为交换,左翼接受了修正的资本主义,并愿意在西方集团的战略影响下与右翼保持一致,并暂时取得了文化领导权。在政治层面,除了偶尔发生的争议以及工人罢工之外,英国的政治局势整体呈现出全面共识或妥协的特征,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冲突暂时得到了解决或遏制。这就是霍尔所谓的社会民主共识情势。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这种社会民主共识的危机开始逐步显现出来。霍尔等人在《探察危机》中对此有过描述。时任英国首相、工党领袖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做出大胆的社会改革,主张社团主义国家,力图将不同社会部门的劳动者组成共同联盟或历史集团,并将之与新科技浪潮连接在一起。但威尔逊的改革最终以失败告终,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它没有像撒切尔夫人那样成功建构起文化领导权。
其实,英国二战后的社会民主共识稳定情势缺少充分条件,这也是导致其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英国当时受传统世界帝国中心身份的束缚,经济基础比较薄弱,整体工业结构落后,生产力低下,人们生活水平总体不高。20世纪60年代末,“英国病”迹象开始显现,因投资不足,英国既缺少维系资本积累所需的足够剩余,也无法为福利国家、工资增长以及贫困人口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到了70年代,随着世界经济衰退的持续加剧,作为世界资本主义链条上最古老的一环,英国社会开始出现了分裂,稳定的基础几乎被消耗殆尽。为了保卫资本主义制度,工党被迫对工人阶级进行越来越严厉的规训。早已蕴藏在社会民主共识中的内在矛盾开始显现,反对越南战争、反文化的新社会运动以及青年学生运动加剧了社会和政治动荡,最终导致了70年代末劳资之间的严重冲突。社会民主共识开始瓦解,其存在的合法性也荡然无存。不断的政治论战和社会恐慌伴随着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斗争,为新右翼的崛起创造了历史条件。
英国自由党在20世纪初退出历史舞台以后,工党取而代之成为执政党的反对党,为新右翼的崛起创造了历史条件。首先,自由党传统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话语元素,如自由企业、有私欲的个体、顽强竞争等被保守党发扬光大。保守党把这些元素与传统话语接合起来,形成具有高度矛盾性的现代保守主义。到了战后社会民主共识时期,保守党又完全抛弃了这些话语元素,并试图改造自身。但是,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话语是福利国家、社会救助、有限的国家干预、凯恩斯主义、工会谈判、社团主义、大国家大资本等构成的社会民主共识理念,致使这种改造难以完成。其次,在保守党领袖爱德华·西斯(Edward Heath)执政时期(1970—1974),英国经济已经出现了危机的迹象,致使保守党越来越倾向于新自由主义。在1970年的选举中,“法律与秩序”(law and order)、对社会中崛起的无政府主义的规训、反对黑人移民的种族主义等具有民粹主义特征的不稳定因素表现活跃。国家与工会之间的谈判一度中断,社团主义也被埋葬,产业激进分子与工会对抗不断。自由市场和自由竞争力量渐强,与国家资本主义脱钩成为英国工业的正常现象。同时,“英国病”加重:工业生产出现滞涨,企业破产增多,银行不良资产增加,房地产业失控,失业人数开始增多,劳资冲突加剧,社会动荡不安,英国工业不得不实行每周三天工作制。最终,西斯政府被矿工罢工击垮。此外,保守党议员伊诺克·鲍威尔(Enoch Powell)长期推行其鲍威尔主义,聚焦于种族、民族、自由市场、法治、优胜劣汰竞争机制等政治问题,代表着英国政治向右转的历史趋势,其部分理念被撒切尔主义所吸收。总体而言,撒切尔主义登上英国政治舞台之际正是以下三种历史趋势聚集的关键时刻,一是英国经济的结构性衰退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衰退同时发生;二是战后第三届工党政府的倒台导致战后以来所形成的社会民主共识危机的瓦解;三是冷战再次加剧,各国核武器竞赛加速。概括说来,英国经济实力下滑,但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情绪高涨,这些因素的“接合”(articulation)为撒切尔主义时代的到来提供了历史条件。
三、撒切尔主义的意识形态重塑
撒切尔主义首先对保守党进行意识形态改造,继而推动社会全面改革。撒切尔主义崛起之后,就革除掉前几届政府的“渐进社团主义”(creeping corporatism)。这场改革运动的首席意识形态家是当时著名的保守党人士基斯·约瑟夫(Keith Joseph),他甚至被视为是撒切尔夫人的思想导师。他们二人共同的思想导师则是主张自由主义的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在1974年的大选中落败之后,约瑟夫与撒切尔共同创办了“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Policy Studies)——研究新自由主义市场政策的智库。约瑟夫对货币主义经济理论非常感兴趣,并说服撒切尔支持这种经济理论。他们共同引领英国政治急速转向右翼,即霍尔所谓的“伟大的右转秀”。霍尔批评约瑟夫的高压政策疏远了部分关键选民,缺少民意支持,只有约瑟夫从保守党隐退,撒切尔夫人才有可能成为将货币主义与自由市场结合起来的最佳人选,撒切尔主义也才能够形成。
霍尔指出,尽管撒切尔主义继承了托利党(保守党前身)的主要传统,但是它仍是一种十分激进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力量,与战后以来主导保守党的传统有明显区别。撒切尔主义以全新方式将保守主义的各种元素组合起来,首要历史任务是击败保守主义遗老及其旧教条,改造人们对战后稳定情势的常识,而不是盲目认同战后的社会民主共识;其次,在经济政策方面,撒切尔主义要扭转国家补贴福利的趋势,缩减公共支出和公共部门的预算,恢复私有企业的活力,发挥自由市场作用,重建自由市场,加强国家干预,支持资本利润,约束工资增长,打击工会,压制工人阶级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中的地位;最后,在意识形态领域,撒切尔主义的任务是遏制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反资本主义浪潮,誓要打破福利国家的魔咒。因此,撒切尔主义需要另外重建一个以新自由主义、自由市场、有私欲的个体、管理至上等为理念的意识形态集团,改造凯恩斯主义国家背后的意识形态,瓦解社会权力集团,削弱不断增长的工人阶级力量,扭转权力失衡状况,恢复管理层以及资产阶级的特权。这些历史任务不局限于经济领域,也关乎社会和文化领域。撒切尔主义试图全面重建社会生活,回归传统价值观,如英国性、品行至上、男权主义、家庭至上等传统理念。撒切尔主义把意识形态当作不同话语元素接合形成的意义链,力图将自由市场的“哲学”(货币主义、自由市场、反集体主义、反国家主义等方面的话语)与保守主义的传统“哲学”(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国家主义、家庭至上、责任、权威、标准、自立等方面的话语)接合为一体。因此,撒切尔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将相互矛盾的话语、意义、价值观和实践用“强制力”或“赞同”(consent)的方式组合成一种表面上看似统一的意识形态整体。霍尔认为“自由市场+强大国家”这个悖论形象地抓住了撒切尔主义意识形态的实质。不过,霍尔并没有看到,正是撒切尔主义的矛盾性保证了其持久活力。实践证明,自由市场背后那只看不见手需要国家干预,保持这个矛盾的平衡发展才是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保障。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政府,在英国选举制度史上,也没有政治家能获得永久的胜利。根据多次选举结果看,撒切尔政府以微弱优势获得支持,也面临重重困难。虽然撒切尔政府在1982年取得马岛战争(Falklands War)的胜利,但并没有实现其预定目标。尤其是在1983年大选时,失业人数仍超过三百多万,撒切尔主义也没有扭转英国经济衰退的良方。尽管如此,撒切尔主义不仅在保守党内部取得领导权,并且成为全社会主导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力量,这主要归因于它的意识形态战略。撒切尔主义意识形态的目标是永远地改变英国的政治和社会格局,重塑英国人民的思维和言说方式。历史地看,撒切尔夫人的所作所为受到多种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驱动。通过对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简化式解读,她学会了如何只将个体当作经济人。在哈耶克那里,她认识到公共利益难以企及,市场是实现社会目标的最有效的途径。从货币主义者那里,撒切尔夫人学到了市场原教旨主义,把市场看作是自我调节的实体,具有神奇的力量,能够使所有人受益。
撒切尔主义全面逆转了英国战后的社会文化情势,尤其在意识形态方面获得巨大成功,最主要的表现是它有效地渗透到工党社会基础的核心地带。在前两次选举中,很多工党的支持者都转而支持撒切尔主义。这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衰退的紧要关头,十分重要。战后英国的各种社会趋势和潮流或者被消弭,或者被重新组合。撒切尔主义成为民粹主义政治力量的代表,在市民社会中赢得广泛赞同;同时,撒切尔首相在社会治理上实施更加严格的规训,由此形成了霍尔所谓的“威权民粹主义”。威权民粹主义是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形成的新右翼霸权政治的描述,它打破了国家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平衡,标志着英国国家和社会治理的重心已转向“威权主义”这一极。面对日益失控的英国社会,威权民粹主义力图自上而下实施新的社会规训和治理,其“民粹主义”这一极又把这种自上而下的社会治理形式建立在下层民众的恐惧和焦虑之上。最明显的表现是英国社会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转向“法律与秩序”。霍尔由此指出,威权民粹主义的意义在于其将工党和保守党之前所采取的危机治理与长期以来保持英国稳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共识元素接合起来,从而打破了英国当时的政治僵局,埋葬了新凯恩斯主义,瓦解了守旧的社团主义,有效反击了各种形式的社会民主和自由保守的国家主义。所以,撒切尔主义不是对旧体制以及阶级关系进行修修补补,而是彻底扭转英国社会阶级关系,全面转向右翼。
四、撒切尔主义之后的英国文化与社会情势
1990年,在撒切尔夫人下台之际,霍尔断言,尽管约翰·梅杰(John Major)政府(1990—1997)努力消除撒切尔主义的影响,但难以走出撒切尔主义的影子。不仅如此,撒切尔主义的影响波及全球,开启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情势,标志着全球资本主义发展进入新阶段——继冷战和福利国家之后全球资本主义的复兴。霍尔指出,自从社会民主共识情势终结之后,英国进入新自由主义情势阶段,新自由主义逐步在全世界攫取了文化和话语领导权。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伟大的右转秀”开始,到80年代持续的撒切尔主义批判,到80年代末的“新时代计划”(New Times)和90年代的“伟大的迷失秀”(The Great Moving No Where Show),再到21世纪初的“新自由主义革命”(The Neoliberal Revolution),霍尔的文化研究计划批判的是不同版本的新自由主义。霍尔的新自由主义情势分析是从撒切尔主义批判计划开始,之后又发起新时代计划宣言、新工党主义批判、布莱尔主义批判以及基尔本宣言。在这个过程中,霍尔对全球资本主义新变化的理解逐步深入,意识到撒切尔主义所产生的影响足以塑造新的文化与社会情势。
20世纪80年代末,西方知识界普遍意识到资本主义已开始步入“后现代”阶段。与此同时,霍尔联合一些左翼知识分子在《今日马克思主义》上发起了颇具争议的“新时代计划”知识实践,持续批判撒切尔主义,为英国左翼寻找一种替代性的政治议程,促使左翼与时俱进,应对资本主义在后福特主义时代、后现代阶段中发生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转型。此后,这些关于“新时代计划”的争论集结为《新时代:1990年代的政治变化》(New Times: The Changing Face of Politics in the 1990s),其中包括霍尔的“新时代的意义”(The Meaning of New Times)。揆其要旨,“新时代计划”从长时段的角度彰显出西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变革。在霍尔看来,撒切尔主义情势也只是“新时代计划”的一部分。具体而言,霍尔所谓的“新时代”指的是西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上发生深层变革①Stuart Hall, 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 The Great Moving Right Show and other Essays, Sally Davison, et al. (eds.), 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245.的阶段,这种变革进程在撒切尔主义时期加快了。他们的“新时代”话语暗含着西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各种面向,如后工业、后福特主义、主体革命、后现代、晚期资本主义等。但是这些面向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它们只是“解读现代性与资本主义之间被重启的关联的不同方式。……在20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获得了新活力,以横扫一切的力量,将所有社会和所有关系置于商品化和交换价值规律的麾下”。①Stuart Hall, 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 The Great Moving Right Show and other Essays, Sally Davison, et al. (eds.), 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245.这造成的结果是“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页。尤其表现为主体身份的革命和危机。随着社会群体主体身份(如阶级、民族、族群)的日益碎片化和多元化,个体主体的身份建构变得更加重要。个体主体不再是“中心化的、稳定的、完整的自我,也不再是自治的、理性的自我。自我更加碎片化,更加不完整,由多重身份组成,……是具有历史的、被生产出来的、在进行之中的事物”。③Stuart Hall, 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 The Great Moving Right Show and other Essays, Sally Davison, et al. (eds.), 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252.从霍尔的整体知识生涯来看,“新时代计划”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一方面,它表明霍尔已从撒切尔主义的批判开始转向更广阔的当下历史——现代性、全球化、文化身份等问题;另一方面,它也开启了霍尔对新自由主义情势的全面批判。
霍尔的撒切尔主义批判和“新时代计划”颇具争议,受到一些左翼知识分子的批评。例如,鲍勃·杰索普(Bob Jessop)等人认为霍尔的撒切尔主义批判和“新时代计划”过分强调撒切尔主义的意识形态维度,轻视撒切尔主义的经济维度,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霍尔在《艰难的复兴之路》中回应道,撒切尔主义的意识形态维度非常重要,但是左翼不但不懂得如何在意识形态层面展开斗争,而且还误读了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将之简化为经济问题。概而言之,霍尔声称自己坚持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即认为如果没有处于决定性地位的经济活动,对文化领导权问题的思考将是无源之水;未取得经济的核心地位,实现文化领导权也只是空中楼阁。实际上,霍尔重申了一种中间立场,既不否认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又坚持反对经济简化论。
1997年,新工党党魁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当选英国首相之后,开始实施“第三条道路”改革方案。霍尔在《今日马克思主义》特刊上发表了“伟大的迷失秀”一文。该文指出布莱尔主义只不过是撒切尔主义的变体,他的“第三条道路”没有明确改革方向,不是有效的复兴计划。此文与1979年的“伟大的右转秀”形成呼应,只是两篇文章发表的背景有很大不同。在后撒切尔主义时代以及新工党执政时期,霍尔仍然密切关注英国政府的政策,他在“新工党的双重洗牌”(New Labour’s Double-shuffle)中指出,自1997年赢得大选之后,新工党并未从根本上扭转撒切尔主义所形成的情势。新工党面临两种选择:要么找到替代撒切尔主义的方案,要么调整撒切尔主义。实际上,新工党选择了后者,将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共识结合起来。其中,新自由主义是新工党所采取的主导方案,而社会民主是辅助方案,后者取决于前者。可以说,新工党所奉行的政策本质上仍是新自由主义。对于英国左翼来说,想要有效地逆转新自由主义,必须建构新的可替代性政治计划。杰索普质疑霍尔在此文中所提出观点,认为霍尔对新工党的批判主要仍集中在意识形态和话语层面,而忽视了政治经济学层面。其实,政治经济学主要通过对资本运作机制的研究,揭示出资本主义制度剥削和压迫的根源。霍尔主要从文化、话语和意识形态这些方面揭露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不同方式,这与政治经济学层面的批判可谓殊途同归。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以霍尔为首的新左翼人士借助《探测》(Soundings)、《卫报》(The Guardian)等媒体平台组织发表了《新自由主义之后?基尔本宣言》(After neoliberalism? The Kilburn Manifesto)和《新自由主义危机》(The Neoliberal Crisis),全面清算新自由主义,力图找到新自由主义的替代性方案。霍尔等人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已在全球攫取霸权地位,为跨国公司、投资机构和风险资本家创造了巨额利润,但也酿成了恶果。不仅在一国之内,而且国家之间,收入差距愈来愈大。一方面,全球超级富豪的财富急剧增加;另一方面,贫穷人口的数量不断上升。全球范围内的不平衡发展造成民族对立,甚至引发极端民族主义。权力和资源大规模地流向私人,市场成为形塑社会关系的主导,交换价值变成了唯一的价值追求。这也引发了生态危机,西方各国无力应对环境危机、气候变化的威胁,只把这些问题推向市场。许多西方国家把金融危机看作巩固新自由主义的契机,纷纷采取了紧缩政策,以减少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富裕阶段产生的财政赤字。在英国,紧缩方案遏制了收入增长,设定利润上限,锐减公共部门就业,削弱地方政府的权威,弱势群体的生活水平和条件随之下降。危机所造成的后果逐渐转移到劳动人民、弱势群体和被边缘化群体身上。霍尔等人认为,除了引发惩罚性和逆向性的社会效应之外,这些紧缩措施注定要失败,因为它并不会大幅降低政府财政赤字,还要承担需求严重下降和税收崩溃的后果,从而加剧了经济螺旋下滑的趋势。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的新自由主义情势,代表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态势。在北大西洋世界,福利国家的安定局面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崩溃。冷战结束之后,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开启的新自由主义决定着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霍尔等人指出,这次金融危机意味着一个潜在的断裂时刻。新自由主义情势分析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弄清楚危机发生的原因及其性质。霍尔援引葛兰西的论断指出,新自由主义情势危机并非仅仅是经济危机,而是由于一些关键场域的矛盾汇聚在同一历史瞬间和政治空间而造成了断裂。在危机发生时期,各种力量凝缩形成新的社会型构,主要因素包括:阶级和其他社会利益、新的制度安排、私人公司对民主进程的过度影响、按新自由主义共识原则组建新工党政治进程、意识形态合法化的影响、对“看不见的手”的准宗教信仰以及市场的自我推崇。因此,霍尔将当下未能找到解决方案的情势性危机视为“新自由主义革命的长征”①Stuart Hall, 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 The Great Moving Right Show and other Essays, Sally Davison, et al. (eds.), 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317.。但是,将当下危机视为“新自由主义”主要出于政治需要,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这种做法将很多因素涵盖在新自由主义这个概念之下,但它掩盖了其内部的复杂性和地理历史特定性,忽视了新自由主义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的具体表现形式。
新自由主义批判弥补了文化研究在其发展初期时所缺失的政治经济学维度。通过援引葛兰西和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霍尔反复表达了对经济简化论的反对以及对多元决定论的坚持。霍尔强调,虽然经济是核心问题,但不能把危机简化为经济因素。其危机发生的原因十分复杂,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常识等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导致了情势性危机的爆发。这些场域虽然相对独立——它们都有自己的起源、不同的矛盾动力、按照自己的时间性演变,但在同一时刻可①Stuart Hall and Doreen Massey, Interpreting the Crisis,in Jonathan Rutherford and Sally Davison (eds.), The Neoliberal Crisis,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2012, p. 57.。霍尔指出,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之时,人们只看到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几乎失效,由此称其为经济危机。这种割裂经济与意识形态的做法貌似正确,但未能触及新自由主义情势的历史演变及其深层结构。
以聚集或凝缩而成“情势性危机”
霍尔坚持将意识形态话语看作理解新自由主义危机的关键。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话语已经被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净化”,结果是涉及公共利益、公共所有权、共同利益、平等、再分配正义、贫困等方面的话语几乎完全被“擦抹”。普罗大众的身份和主体性几乎全部被自由市场话语重新铸造,人人都变成了自由市场中的消费者或客户。从撒切尔主义开始,“社会”不复存在,只有市场、个人和家庭,所谓的公共利益也被个人私利取而代之。市场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个人私欲,但最终将无益于社会整体发展。最严重的后果是,新自由主义话语已经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常识和理念,追求个人私利和交换价值成为合情合理的诉求。在霍尔看来,当新自由主义话语成为常识,当人们把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看作世界的唯一标准,新自由主义就获取了文化领导权,而且,这种文化领导权主要是通过“赞同”而不是“强制力”来得以实现。“赞同”的实现主要借助于意识形态的“质询”功能,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被“惯常化”(naturalized),进入到无意识层面,成为无所不在的常识和文化,人们难以察觉意识形态的存在及其宰制作用。
五、情势分析:理解当代英国文化与社会的新视角
霍尔将特定社会形态的各个领域理解为相对独立,但又相互接合、共同发挥决定作用的偶然性“情况”(instances),并为任何历史特定情势的存在提供前提条件。在结构主义理论范式的影响下,霍尔认为,社会不再是有机的整体,而是由种种受制于偶发“情况”共同组合而成的结构。这些“情况”形成各种矛盾张力,最终将导致历史性的断裂(危机)和社会转型。但是,危机的结果并不能被事先决定,因为偶然性因素意味着支配与被支配要素之间的接合和再接合方式的决定总会出现某种斗争或对抗,而斗争和对抗的结果是难以预料的。所以,情势分析的精神旨归在于用具体的、历史的、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分析问题或危机。它能够建构分析具体问题的广阔视域,可以将多种要素纳入研究视野。从这个层面看,情势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超越庸俗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单向简化论和决定论。
作为一种文化研究的原则方法或范式,情势分析既是霍尔社会参与的主要进路,也是霍尔留给文化研究甚至社会科学各领域最重要的遗产之一。从新左翼时期分析消费资本主义造成的阶级消失假象开始,霍尔对当代资本主义在每一个历史瞬间的新变化的认识经历了长期的演变过程。《探察危机》和撒切尔主义批判是霍尔介入社会的知识实践和情势分析的主要成果。情势分析也是其长期知识实践的经验总结和方法论概括,它既满足了文化研究跨学科知识实践的需要,又代表了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之间交往对话的融合趋势。因为情势具有历史特定性,霍尔的情势分析没有固定不变的具体操作方法。情势分析的意义在于,一方面,提醒我们要抵抗理论简化论的诱惑,即认为只要掌握理论,就能够理解世界及其运行方式;另一方面,提醒我们要探察危机发生原因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是相对独立的,配置不同,组合方式不同,接合而成的情势也不相同,充满了不确定性,这也正是资本主义后现代境况的主要特征之一。
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和有机知识分子,霍尔认为自己有责任揭示撒切尔主义如何成功地将人民大众的信仰和价值观与新自由主义政策接合起来,剖析文化领导权的建构机制和形成过程,进而为左翼提出反文化领导权政治计划,确立反文化领导权的社会集团基础,以赢得道德和文化上的领导权。由于政治立场不同,霍尔并不十分关注撒切尔夫人大刀阔斧的改革在政治和经济上取得的巨大成功,以及撒切尔主义对以民主共识为基础的战后英国社会进行的彻底改造。实际上,英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撒切尔主义成功地逆转了英国在20世纪70年代急剧的经济衰落,并在一定程度上使英国跟上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撒切尔夫人所推行的货币主义、私有化、自由市场等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全球范围的影响依然巨大。2013年4月,在撒切尔夫人辞世之时,时任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甚至宣称人人都已经成为撒切尔主义者。不过,以“铁娘子”著称的撒切尔夫人的强硬社会政策使她难以与市民公众进行有效沟通,招致社会各界人士的批评。当前,欧美资本主义历史的钟摆再次向右偏转。2016年,撒切尔夫人当年提出的“让英国再次伟大”的口号被特朗普重新拾起。英国首相特蕾莎·梅(Theresa May)在内外政策上也颇具“铁娘子”风格,但因没能实现脱欧计划而被迫辞职。总体上,当下英国政治共识难以企及,社会撕裂的程度可见一斑。当前,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再次成为当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主导文化、社会思潮,资本主义历史情势及世界格局也已发生明显变化,情势分析不失为一种分析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深层结构性变化的有效工具或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