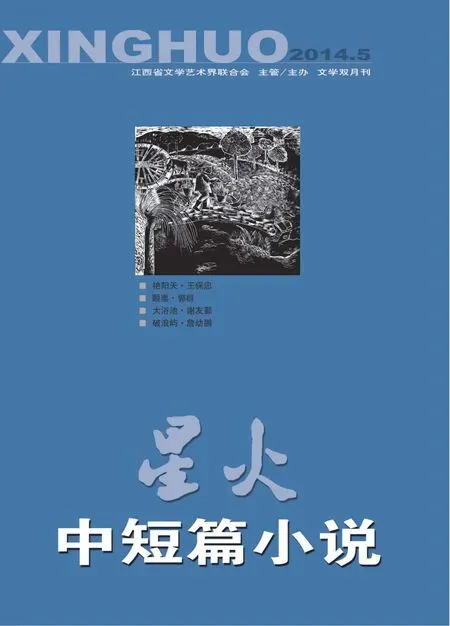譬如秋风
○陈纸
乡村的记忆在蜿蜒的梦境里曲折而行。我和乡村的事物站在高高的山岗,秋风在起伏不定的梯田上悠悠掠过,我的眉头紧锁,内心交织着某种困惑;我的眼睫毛像聒噪的门帘,忽闪忽闪。秋风劲扫,像在清理什么。乡村的某些地方越来越瘦,某些部位却越来越肥。
事物是乡村的拷贝,一挂上放映机,记忆的银幕便影像尽显。影像流淌故事,故事弥漫思想。思想经不住挽留,岁月远去,马蹄声碎,回应出一串串秋风叹息,引牵着我,向乡村深处逆流而上……
学 校
学校是小学的学校,在我们村一个叫“牛场”的地方。在宽广的蓝天下,学校操场的一排小青松跳跃着尖梢梢,偶尔有麻雀叽叽喳喳围着一两棵,欢快地叫着。操场上有篮球架,两只,相拥着中央一块平滑的泥地。印象中,泥地像一块硕大的、平滑的玻璃,谁也不敢(想)踩上去,仿似只作摆设的舞台,没人在上面表演。那时想:学校是不是没钱买篮球呢?
操场四周的跑道最热闹。有课上的日子,每天清晨,只要不下雨,就有一队队方阵在上面奔跑。冬天,有霜降,有雪飘,跑道被松软湿耷的冻土覆盖,沾粘我们陈旧的布鞋底,我们的脚步拖垮了速度。下课,课间操,或课间休息,跑道上填满了学生,我们或做动作,或追闹,广播里的音乐声、学生们的喊叫声,在跑道上奔涌。
跑道旁,有一大坑,大坑里铺着沙,细细薄薄,像永远吃不饱的我们,饿成了皮包骨。沙坑里,玩沙的比跳远的多;跳远的比跳高的多。跳高,只有在一个学期期末考试才有。跳高考试就像过一个节日,大家将跳坑围得密密实实,叫喊声、嬉笑声,就像雨点,没勇气、没本事的,会被淋得狼狈不堪。特别是女生,还没起跑,腿就发软。于是,喊声与笑声就变成了起哄,最后是体育老师的呵斥声来收场。
挨着沙坑外侧,是一条沟。沟是深沟,长满了浓密杂草,秋冬季节,枯枝败叶全躺在里面。沟很长,有四五十米,相当于“围墙”或“护城河”。人家的围墙往地面上撑,我们学校的“围墙”往地下长。深沟一头连着厕所,一头连着教室,呈南北走向。厕所只有一座,女厕所一侧连着深沟,男厕所一侧连着一条十几米长的石径。石径宽一米多一点,通往另一排教室。
深沟的外侧是树林,树林里掩映了十几座坟墓。坟墓有新有旧,坟头有高有矮,坟头草有浓有疏。上课时,冷不防地,能听到吹吹打打,由远及近,如浪波翻涌。大家没了心思,往窗外瞟,能看到一队人,有人抬棺,有人举幡,有人敲锣,有人打鼓……径直往离我们教室不足二十米外的树林里去。
五年级临近考试前两个月,我们在校寄宿,住在树林对面的教学楼二楼。没住几天,有女生向班主任反映说,她晚上看到了“鬼火”。班主任一听,竟然信了。第二天晚上,他还与我们坐在窗前,“欣赏”树林里闪烁的“鬼火”。也就是在那时,我知道,世界上有一种叫“磷”的东西,在我们死后的骨头里,遇到一定的温度,会自燃、发光。
教学楼,这里的意思是教职工大楼,是老师办公及住宿的地方,高两层。教学楼后门有三四棵梧桐树,集中长着,相同的年龄,像风雨共担的朋友。但朋友间也有不“平等”的地方,有一棵梧桐树上,挂着一口钟。钟是敲的,提示上课与下课。上课声敲得急促而密集,下课声敲得缓慢而疏朗。我不知道这钟声的“规格”是不是全国通用的,反正,在我们那时的那所小学里,就是铁律,就是指挥官最神圣、最严肃的声音。多少年后,我才知道,那口钟是从我堂叔拖拉机废弃的轮胎里拆下来的中圈,不知是铁的,还是钢的,反正,通体锃亮冷艳,声音清脆尖锐。
教学楼后门向着校园,面对后门,右边是老师的饭堂。对于我们农村走读的孩子们来说,那是一个神秘的地方,也是一个凛然不可侵犯的地方。我没敢涉足一次,哪怕进去喝一口水。我最多只是在当科代表送作业到老师办公室经过时斜眼看到某位老师端着碗筷出入那里。
教学楼左边是一条四五米宽的路,连着“牛场”上住着的七八户人家,是通往我们校园的路。我后来想,假如学校设校门,就应该在那里。但我们没有校门,哪怕立两根棍子,中央挑着弧形的顶棚都没有。所以,我们的学校没写校名,因为没地方挂。所以,我在那里读了五年书,直至毕业,都不晓得学校的准确校名。学校建在我们村,乡亲们以村唤名,习惯叫“舍陂小学”。现在想来,准确的全名应该是“江西省永丰县潭城乡舍陂村中心完小”吧?我也不知道。
这条路旁有两棵大松树,足足有唱片那么粗。两棵松树相距三四米,学校因势利用,在中间立了两根小孩子胳膊粗的竹竿,供我们爬玩。那时,爬竹竿比赛成为我们在学校的主要竞技活动之一。我瘦小敏捷,不输给一般对手,但手臂及腿脚不够有力,遇到高手,就甘拜下风啦。有一天,我两腿紧夹竹竿,往上爬或往下滑时,慢慢感到中间有一种无以言表的快意。我既慌乱,又兴奋,我知道:无羁的童年与懵懂的少年无缝对接了……
学校的教室,南边一排,北边一排,只一层,各三间,共六间。那时学生真多啊,教室空间只有那么大,容不下我们这般猖狂。我是好动的“话痨”,我的座位时常变换,通常前后左右都是女生,都不能“查封”我这张嘴。教室里,那时没空调,没电风扇,热来开窗冷来关,我们在大自然中顺应着天地的自然温度。夜来东风渡,教室纳余芳,经常不经意间,总有窗外的野花携香袭来,不觉就解颐了。这时,灵魂似乎也跟着游弋野外,没有目标,没有羁绊,只是,写的一些三四百的文字,悄悄染上了浪漫—我想,那该是我人生中关于文学最初的情怀吧?
直到最近,不知从哪本书上,读到一句话,大意是:任何人都有一颗上进的心。或许真的是我们疏忽了,或者是不相信。今天,在三十多年后,我再次走到这里,眼前的校园只有巴掌大,仿佛我一拍下去,它就会奄奄一息,瞬间双眼一闭。
实际上,它早在十几年前就寿终正寝了。村里的孩子越来越少,听说,由我们那时的六个班,逐渐减少到四个班、三个班……后来,四五年级划归到相邻的龙洲小学去了,这里,只有一、二年级合在一间教室里上课。再后来,干脆就不招生,废弃了。教室租给了村里一位养鸡专业户,当作了鸡舍。
操场上的青松,一棵也不见了,它们是死了还是长到成材后被砍了呢?深沟不知哪一年被填埋,而且砌起了围墙。围墙两侧皆是荒草萋萋,乱坟岗这侧,又添了十几座高大雄伟的新坟,坟墓中间,大树杂立,灌木丛生。我父亲的坟被乱枝缠绕、枯草掩埋,只能依稀见微微隆起的一小土堆。
此时,正是深秋,如果我端坐教室,窗,应该是或开或掩或半开半掩。探在窗外的叶子,应该黄成一片灿然。风一吹,贴了地的草,头更猛烈地撞在地上。
我本能地一摸额头,那里曾渗出过血—是数学老师碰的。我的成绩糟透了……
这会儿,我突然悟出,在这座学校里,我为何失去了信心。恍惚中,我在秋风中站成了那个小孩,浑身荒芜,还隐隐作痛……
土 窑
看远山横廓,苍青如黛;看河流如琴,土窑静卧。
土窑有三处。一处是新窑,专门烧砖的窑。这一处土窑是喧嚣而炽热的。我小时候见证过这座土窑的诞生—在山地上挖一个深坑,沿坑堆上圆弧的红土,夯紧,再用覆盖青草的土皮将顶部封起来。整个劳作的场面热火朝天,每个汗流浃背的人都是我熟悉的乡亲,他们都是“大队”的最小“细胞单位”。窑建成了,是“土窑”,可有人习惯称之为“砖窑”,“砖窑”是专指它的用途:烧制砖瓦的窑。
烧制砖瓦是一个复杂繁琐而又充满技术含量的冒险之旅。其过程纷繁漫长:要挖土、和泥、摔砖坯(或瓦坯)。挖土是力气活,和泥就有讲究了,要用铁锹搅和,不停地加水,每次加多加少,全看现场调度,边和边用脚踩,有时用人踩,有时牵牛在泥里,人与牛同时踩。踩了还要用铁杆打,打着打着,明水不见了,和到泥里,看不见了。泥里原来的颗粒不见了,瘫软细腻了。这时的泥不是当初的泥,这时的泥要倒到砖模(或瓦模)里去。打砖师傅将模压实了,用一根细细的铁丝,沿模具的平面快速一切,将高出的泥划去,然后,往撒了干沙的平地上轻扣,一块有模有样、平整厚实的砖坯便做成了。做瓦坯就复杂了,瓦模会转动,趁瓦横转动,将粘稠的和泥涂抹上去,用一块木板不停地刮磨,待一块瓦片大小的和泥呈微微弯曲状,附在瓦横上,便快速进行上下左右修整,将毛糙不齐的部分剔除,再在表面轻轻抹出几条“皱纹”,然后快速拿下来,放在照例铺了干燥薄细沙的地上,掀下,一块瓦坯也做成了。
做成的砖坯(或瓦坯)齐整摆好,之间要留缝隙,需通风、晾晒,让其干透。之后,才是土窑真正大显身手的时候。干透的砖坯(或瓦坯)要一担一担地挑进土窑,码好、堆好。接着,就是点窑了。点窑之后的几天几夜,便是高温的烧窑。将最干燥、最粗壮的木材往窑口塞。火势的控制也是颇有讲究的,一定是村里最有经验的乡亲,日夜守在窑边,把握着火候。
出窑时是乡亲们的节日,大半个村的人都在现场。大家挑着簸箕在土窑进进出出,如果砖瓦青青,而且没有烧废、烧残的,每个人脸上便都带着淡淡的笑意,传递着喜悦—近半年来的工夫和辛劳没白费啊。想想将用这些砖瓦盖新房,该是多么美的事啊。
时光催促,我们这些孩子一茬茬长大了,我们村里的那座土窑,也烧出了一茬一茬的砖来。终于有一天,现代化的制砖技术出现了,乡亲们到别的地方去买砖,还比自己烧制的砖便宜得多,土窑便开始发生危机了。再加上村里会制砖、烧砖、制瓦、烧瓦的人逐渐老去,他们挑不动、和不动、踩不动、转不动,眼花头晕,土窑便彻底没人照顾,废弃在村后的山坡上了。
风烛残年,土窑身躯佝偻。不知哪年,劲风漫雨,将拱形窑碹眼推进了淤泥里,土窑脚一软,腰一闪,彻底倒塌。
倒塌的是路思坪村的一座土窑,它就在路边,我们小时候放牛每天都要经过那里。我们避之唯恐不及,不敢探身去看看里面有多深。因为,关于这座窑,有一个传说:不知哪年,窑体突然坍塌,把正在里面劳作的窑工砸死了。至于砸死了几个,是男还是女,说法各异。后来,村里传出半夜去附近找牛的人看见窑里有几个飘忽的影子,在倒塌的土窑里点起了火,在里面烧红薯呢。还有村里的小伙伴说,有一次去里面解大便,见到一条大蛇,足有十几斤重。有小伙伴在旁插嘴说:何止一条,有一窝呢!
鬼与蛇纠缠、交织在一起,让那座土窑笼罩了一层令人望而生畏的神秘感,非胆大者不敢靠近也。
然而,童年的玩耍之地终究离不开土窑。我们村陈万全家旁的一座土窑成了我们的乐园。那座土窑位于马路边,是我们每天上学、放学的必经之地。土窑是废弃的土窑,苍老得找不到顶上的窑眼,也寻不着旁边的窑门。它全身甚至找不到一处空洞,我们真怀疑它曾经真的烧过砖瓦,它兴许徒有窑的体型,却从未发挥过窑的功用吧。但不管怎么说,它庞大的、松软的圆锥状体态爬满了我们的欢乐。
每次放学路过,我们都要紧跑几步,一口气冲向窑顶,抢先占领有利地形。恰好,窑顶类似一个盆地,我们刚好匍匐在地,仗着四周微微隆起的边线,充当天然的战壕。先冲上窑顶的小伙伴大多之前就备好了“弹药”:每人手中握着大小几颗土块,身子躺下,土块摆在眼前,“敌我”双方自然形成。在窑顶的,十有八九将自己认定为好人,而没来得及冲上窑顶的,就被充当了坏人。但往往他们不承认自己是敌人、是坏人。于是,争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的“战斗”打响了。“战斗”很少在两人之间进行,而是“大兵团”“集团军”作战。有时是同一个班级里分两派同学,将“战火”从学校蔓延到土窑;有时是两个村的同学,之前就是“敌我”双方,积怨很久,伺机寻找决一死战、分出胜负的战场。土窑的特殊地理位置激发了一方发动“战争”的欲望,他们仗着抢先占据了窑顶,向窑下的“敌人”掷出第一颗土块,“战争”在所难免,一触即发。于是,一时土块纷飞,“枪林弹雨”,由最初的“暗施冷箭”,到“明里放枪”,窑上窑下,交战激烈。
打得最多的仗,在我们舍陂村的学生与卢家村的学生之间。两个村的学生上学、放学都要经过那座土窑边,那里便成了咽喉要地和兵家必争之地。凡两个村学生有矛盾,战场就摆在那里。仗打了一场又一场,一年又一年。学生毕业了一届又一届,土窑见证了两个村庄学子的爱恨情仇。但要论谁输多谁赢多,谁吃亏多谁收益多,恐怕连土窑都分辨不出。
在一次与卢家村同学的“战斗”中,我被卢火根的“子弹”击中。他违反了战斗规矩,用的不是土块,而是石块。我的额头被他的石块击中,顿时鲜血直流。我捂着伤口回家向母亲哭诉,母亲将我拉到卢家村,找到卢火根家。卢火根的母亲当场扇了他两个耳光,他的哭声比我的哭声还大。
若干年后,我从南宁回家乡,在县城一家饭馆参加同学会。我在酒席上向卢火根提及此事,如今已长得五大三粗并已成为当地房地产开发公司老板的卢火根“嘿嘿”两声,说:我不记得了。然后,端起一杯啤酒,一饮而尽。
现在,再回到家乡,遍访那几处土窑,早已草木丛生、阴气森森。当年庞大体阔的土窑,早已成了隐没于旧土深处的小土包了。秋天,叶子飘落,发白的小草,在土窑的残垣上祭出一把把小旗……
世上恐怕已无土窑,此地早已颓败一片。曾经闪耀于此的“火的艺术”,燃烧在焦黑的泥土深处,秋风萧萧,无法吹熄。
祠 堂
据说,祠堂是姓氏宗族祭祀先祖的地方。可在我童年记忆中,祠堂却从未举办一场仪式,让我探探祖先的血脉及历史的体温。
小时候,我们倒是总喜欢在祠堂里玩耍。年少无知的我们,感受不到祠堂的庄严与肃穆。印象中,这座位于村子中央的建筑,古朴而厚重的木门永远敞开着,吸引着我们迈着轻快而杂碎的脚步,迈向其潮湿阴暗的深处。祠堂里的戏台、祠堂里的天井、祠堂里的雕花屏风、祠堂里上锁的左右两个房间……像高寿老人身上的一个个部件,是凝聚陈氏宗族力量的文化空间。
站在天井中央,抬头极目,若是晴朗,阳光普照,苔藓青瓦,绿得刺眼。俯视脚下,暗沟默然,暖气抚砖。更多时候,我们渴望雨天,雨天不必跟随大人去田里干活。如果又恰逢寒假则更妙,我们从晒场“移师”祠堂,在戏台上蹦跳,每个小伙伴都把自己当成主角,根本没有“配戏”意识。陈旧的木板,在我们的打闹中微微颤抖。祠堂里几根支撑的石柱子,表面的石灰已脱落,斑驳的躯体,任由我们稚嫩的手掌和脸庞在上面摩挲,柱子逼近地面两三尺的地方,全是我们无礼的脚印,我们将莽撞的历史记载在上面。
祠堂里最大的聚会是看电影时。偌大的祠堂也只有在此时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它消瘦的内脏仿佛要被四方八村赶来的人挤爆。记忆中,祠堂还演过一部戏,是我们县剧团的保留剧目《血衣冤》。第二天,据攀爬在祠堂窗户上看戏的别村人传话出来说:当晚,他感觉到戏台在吱吱呀呀地晃动……
小时候,祠堂里,唯一与聚餐有关的一次大活动,是村里陈接发失散了三十多年的弟弟陈接藤从台湾回来探亲。陈接藤可能是进我们村第一位穿西装、打领带的人。他带着妻子和女儿挨家挨户地走访,挨家挨户地道谢,挨家挨户地送上一团刷锅的铁丝。陈接藤这一新鲜的见面礼当时点燃了很多村民的心地,对我们村人用丝瓜络洗碗刷锅亦是一种颠覆。年纪大、认识或记得陈接藤的乡亲,都说陈接藤以前受苦了,现在有出息了;不认识、不晓得陈接藤的乡亲,现在知道了,都说陈接发有这么一个弟弟,接下来,真的要发达了……总之,都是好话,都是美好的祝福。陈接藤为了感谢全村人一直以来对他贫穷的哥哥的关照,除了献上薄礼,还宴请全村人在祠堂吃饭。
那是祠堂里真正全村人的大聚会。这样的场景,直到三十多年后的最近几年才得以重现。而此时的祠堂已旧貌换新颜,在原地得以重建,以前的老祠堂归位于陈氏家谱中,成了纸面上的汉字。新祠堂的正门上方,鲜红的油漆涂抹在六个凸起的大字上:舍陂村陈氏祠堂。
近些年来,不知刮的什么风,农村对清明祭祖聚餐特别看重。其实,说得准确一点是:清明祭祖一向看重,而祭完先祖、上完坟、踏完青,家族人员聚在一起大吃一餐渐成时尚。我们村也不例外,这几年,清明回老家扫墓,在村里聚餐成了新增内容。聚餐地点自然选在舍陂陈氏祠堂。第一年聚餐前,还举行了祭祖大典仪式,听说托另一村同是陈氏宗亲的关系,不知从何地弄来了一个大香炉,摆在祠堂正前方。正前方墙壁上,贴着一张红纸黑字的祭文。全村男子无论老少,齐齐下跪,倾听完祭文,围成几十桌,热闹非凡地大吃大喝起来。空旷简陋的祠堂里,弥漫着浓浓的菜味与酒气。
恍惚中,某个酒桌的位置,依稀记得,是在老祠堂的某个位置,那里曾经的模样,便映在眼前。农闲时分,除了小孩子们的追逐打闹,也是村里集中农具修修补补的时候。那时,我父亲是大队的副大队长,村里杂七杂八的事,都是他打理。他到处去请篾匠、木匠和铁匠,把他们领到祠堂来;指挥乡亲们将砍下的竹子、松树、杉树以及生锈的、用钝或折损的镰刀、锄头等搬到祠堂来。有时,篾匠、木匠和铁匠 “三匠”同时在祠堂里开工,“井水不犯河水”,“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村里的大人小孩各选其爱,择地旁观,一边看,一边聊天,家长里短、阴晴节气……说说笑笑,一天就这样不急不缓地流走了……现在,一闭上眼,那些铁花四溅、木屑纷飞、篾刀闪闪的场面仿佛就在昨天;那些前前后后走着、笑着,年轻着、老去了的乡亲,仿佛站在新祠堂的某个角落,冷眼旁观着这一桌桌丰盛的鱼肉呢。
清明节假期一过,我便匆匆告别母亲,离开村庄,回到了城里。很多跟我一样、常年奔波在外谋生的年轻人,也在这一次聚餐桌上,似曾相识地敬一杯酒后,回到了另外的城市。村里守着田地的乡亲们,在忙完春播、夏抢、秋收、冬藏后,便迎来了漫长的寒冬。
某一天,一个问候的电话打到家里,传来一个温暖的讯息:村干部为了照顾留守老人,在祠堂里燃起了柴火,将留守老人一一接来,一起烤火取暖,集中照顾……
但我还是不敢去看祠堂。我怕会看到清明被雨打湿的祠堂屋檐,一年都干不了;我怕听见老祠堂的人声回旋在新祠堂里,泛起往昔的记忆;我怕来去匆匆,像一阵秋风,裹挟着悲凉,却被乡亲们误读为满眼的期望……
大队部
大队部在舍陂村的西边村口,那时,舍陂村还是舍陂大队,所以,大队部叫舍陂大队部。那时,舍陂大队所辖,除自己村外,还有卢家村、江里村、江背村、路思坪村及官塘下村五个自然村。可以说,舍陂大队部是舍陂大队的“行政中心”。
彼时的“行政中心”,不像现在那么讲排场,但大队部也算是“五脏俱全”,六七个房间,左右前后依次排列,有公社蹲点干部的住房、大队会议室、蹲点干部的厨房、大队商店售货员的住房、商店电话间以及大队卫生所。
从大队部走出来的公社蹲点干部,是我那时见到的最大的“官”。他住在大队部,有时也在大队部做饭吃,但大多是在农民家里吃。挨家挨户排饭,一户人家排一天,蹲点干部吃完饭,走之前放下几张粮票和几张角票,从没白吃白喝的。
蹲点干部从公社派下来,不是来吃干饭的,除了在大队部主持召开各种会议外,大多数时间在田间地头调研、干活。每位蹲点干部都有一口田,播种、插秧、施肥、灌溉、收割,都要亲力亲为。蹲点干部手持斗笠或草帽,挽着裤脚来往田间及大队部的形象,在我头脑里至今仍很清晰。
大队部商店售货员长期由我们村陈素华及江里村的宋素清担任,她们分别是大队书记及大队会计的侄女。不知是因为她们自认为“不凡”有了信心后刻意打扮,还是本身确实长得高挑漂亮,我不得不承认,她俩是“唯二”配得上在大队部商店卖东西并且接听电话的姑娘。她俩在我童年的记忆里,被认为是“吃商品粮的人”。的确,她俩很少下田干活,身上永远新崭崭、光艳艳。一串大队部的钥匙轻扣在右手食指,走起路来,摆动的身姿,配合着“沙沙”的钥匙碰撞声,像一首浅唱低吟的乡村小曲飘荡耳边。有一次,我去商店买东西,从大队侧门进,没去商店的售货处,只攥着钱见开门的地方就乱闯,冷不防跑进了售货员住的房间。我看见江里村的宋素清与在大队小学当老师的陈广东拉着手坐在床沿,粉红色的蚊帐怔怔地分站两旁,静静看着他俩,吓得我差点被门槛绊住了逃出的脚步。
此后,有关宋素清与陈广东关系的传闻,时不时飘进我耳朵。但我可以对着摇摇摆摆踱过大队部门前的那一群大白鹅发誓:我绝不是那个绯闻的传播者。宋素清最后到底没能与陈广东走在一起,这不只让我们舍陂村与江里村的村民摇头叹息,也惹来了其他村里人在售货窗口的关心。他们的目的各异,但一致招来宋素清的喝斥。有时,连陈素华也受到牵连,皆因两人都有一“素”字,令一些村民分不清彼此,这让陈素华难堪不已。
宋素清、陈素华两人轮班休息的房间,除了一张床,和偶尔来坐坐的陈广东外,还有一张桌子。桌子像梳妆台,但其实除放了一面镜子、一把梳子和一两瓶雪花膏外,就是堆放报刊杂志和信件。桌子放在窗户下面,窗户对着马路。送往舍陂大队的报刊杂志和信件遇到大队部大门紧闭,邮递员就爬墙、抻身,丢在桌子上。从这个作用讲,这间房也成了大队的收发室,进出这里的人自然不少,但我等小孩是断不能随便闯入的。一则因为这是闺房,二则怕我们这帮小孩偷报刊杂志擦屁股或撕了折纸飞机……
大队部大门前有一块足球场大的空地,那里是村里放电影的好地方。那时候,不是每个自然村都有放电影的资格,只有称得上“大队”的,才能放电影,而且,是一个大队一个大队轮流着来,每一轮两部长片,一部“祖国新貌”或“新闻简报”之类的短片。
放电影,是大队部最热闹的时候。一是放电影的设备放在大队部,二是放电影的人住在大队部。设备一到,大队部就挤满了小孩,塞满了好奇的眼神。胆子大一点、读过几年书的年轻人,扛着锄头走进大队部,理直气壮地问电影放映员:今晚放什么电影?如果对方不吭声,他反正认识字,找放在发电机旁装电影拷贝的铁盒子看,上面用红油漆斑斑驳驳地写着呢。如果字迹实在太模糊,又要再一次厚着脸皮去问。有一个典型的段子是:放映员没好气地回答说“明天回答你!”听者不满意,非缠着对方说。我们在一旁听了,也急:就现在说呗,干吗要明天回答,明天回答还要你说吗,今晚放完我们个个晓得了,还用你明天回答?我们不就是想早点知道,然后马上去向家人、乡亲或其他小伙伴吹吹牛、显摆一下吗。放映员又说“明天回答你”。后来,我们才知道,那部片名就叫《明天回答你》。
如果运气好,说不定还能先睹为快呢。有时,放映员要试片,就是先放一遍,怕晚上出故障,被乡亲们骂,所以要“预演”一遍。地点就在大队部的会议室,一般是在下午,将窗帘一拉,只有少数几个人看,比如大队干部、公社蹲点干部和“赤脚医生”陈建国。有时不关门,如果小孩守规矩,不大喊大叫,不成群结队,便可以偷溜进去,过一把没有普通观众的“专场”瘾。
当时有一首歌;“赤脚医生向阳花,贫下中农人人夸,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千家。出诊愿翻千层岭,采药敢登万丈崖,迎着斗争风和雨,革命路上铺彩霞……”我觉得唱的就是陈建国。陈建国的乡村诊所就设在大队部,里面有一张桌子,桌子前一张凳子。桌子上放着处方笺、听诊器,还有一支钢笔。抽屉里有一些广谱消炎药和一只装着针头针管的铁盒。屋子的一面墙摆放着一个简易的药柜,药柜旁挂着他出诊的卫生箱,墙角放着两张短凳,一张给病人打针用,一张供带病人来的陪同人员坐。
不管有病没病,我们都喜欢到陈建国的卫生所去。有病时,能得到父母的重视和关心;没病时,我们去他那里拿用完药水的空盒子,我们用它作文具盒或养蚕的“暖房子”。
陈建国很喜欢我,爱逗我玩。不过,他有时开玩笑,拿我开涮,我却听不懂。还记得,我人生中买的第一本课外书,还拿给了陈建国看。那本课外书叫《一只红辣椒》,是一本小学生作文选。陈建国用钢笔在书上题了我的姓名,并且鼓励我好好学习语文。
此后,我读小学,升初中,考上了高中……陈建国比我父母还了解我的语文成绩。特别是我离开家乡到南宁,他知道我做了记者,而且成了作家。
若干年后,我回到村里,陈建国有意无意地,在我家附近的马路上闲逛,以制造与我的“巧遇”。他见了我,总是问我的职业情况和工作体会。他的问话很内行,这时,他是记者,我是被采访者。末了,他说:后生仔,我早就知道你会有出息,因为,你是我们村最爱看书的人,从小就爱,现在不知看了多少呢……
与我聊这些时,陈建国已经有六十多岁了。那时,大队部被拆除,已荡然无存。只有旁边的那丛竹林还在。奇怪的是,竹林里的竹子非但没有长高,反而好像更加瘦小低矮,只是密集了一些。
最近几年,回到家乡,再没见过陈建国。母亲说,他到城里帮他儿子带小孩去了。这时,我反而主动想见到陈建国。我会不由自主地逛到昔日大部队所在的地方,但那里的房子、那里的一砖一瓦,全没了,全没了……秋风悠然,竹林摇摆,只有一片片单薄的叶子,追着我的裤脚一路小走,间或,还有来往的农用拖拉机,轰鸣着自己的欢快,把我推到记忆以外,推到夕阳落山的那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