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特人的活跃:唐帝国兴衰的真正奥秘
郑渝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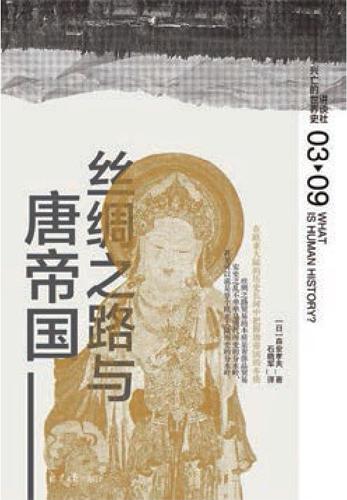
《丝绸之路与唐帝国》(日)森安孝夫著 译者:石晓军 理想国·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年1月
《丝绸之路与唐帝国》这本书有一大主角:粟特人。
在《丝绸之路与唐帝国》一书的序言中,长期致力于中央欧亚史研究的日本历史学家、大阪大学名誉教授森安孝夫批驳了日本在内东亚国家历史学界一些人的所谓“自虐史观”。日本保守右翼人士将反省日本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中期的对外扩张、侵略的历史学研究,贬低为“自虐史观”;但在森安孝夫看来,真正的“自虐史观”,其实是那种秉持了西方中心史观,毫无凭据和理由的贬低东亚、亚洲古代历史发展的成就,在探讨历史上的冲突、问题时不假思索地站在欧洲、西方的立场,将亚洲、东方视为敌对方的做法,而该做法在日本等东亚国家的历史学界颇具代表性。
当然,摆脱西方中心史观,不等于要陷入东亚、古代中国“唯一”、“独特”的反向偏狭。从蒙古高原东麓一直到西麓,跨越天山山脉、中亚、乌拉尔山脉,直抵里海、高加索山脉、黑海,都可称为所谓的中央欧亚地区。这一地区在巨大的山麓和山脉之间有许多辽阔的草原,没有涌现所谓的古代文明古国,而是成为了一次次冲击各大文明古国的游牧民族的策源地。《丝绸之路与唐帝国》书中指出,“从四大文明圈发展起来的农耕民与从中央欧亚发展起来的骑马游牧民之间的对立、抗争、协调、共生、融合等关系之中”,才孕育了包括东亚文明在内的古代文明。
4世纪至9世纪之间,我们今天所称的丝绸之路东段,粟特人是担纲贸易、文化往来的重要甚至主要角色。粟特语也成为当时的国际语言。粟特人在人种学上属于白色人种,粟特语是印欧语系伊朗语族的中古伊朗语的东支。粟特人离开伊朗故地后,向东发展,其文字传入突厥、回鹘,并在此基础上产生回鹘文字;13世纪,回鹘文字中产生了蒙古文字;17世纪,基于蒙古文字转化出了满文。
6世纪前后,粟特人中的精英开始在中国中原王朝(北方)中脱颖而出,涌现出不在少数的政治、外交、军事精英。粟特人精英在参与中国中原王朝的政治时,有意像之前汉朝、三国时期的汉族世家那样,对不同势力各自“下注”,以确保赢得权势对粟特人势力把控西域商路的支持。唐高祖进入长安后,凉州的粟特人首领安兴贵、安修仁兄弟发动政变,拘捕了当地军阀李轨,将凉州献给了唐朝;而安兴贵之子安元寿则成为了李世民的輔佐者,曾在玄武门之变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即调动粟特人兵马给予了李建成和李元吉一方较大的打击。
毫无疑问,隋唐两朝的皇族,以及作为朝廷柱石的关陇集团,其实都带有相当程度的鲜卑裔血统——从春秋战国时期到唐代,匈奴、鲜卑、氐、柔然、高车、突厥、铁勒、吐谷浑、葛逻禄、奚等族,都相当活跃,也逐步融合进入了之前狭义上的汉民族。而安史之乱爆发后,不仅宣告了盛唐时代的结束,而且也导致唐王朝从过去意义上的兼容、多元化帝国转为了更趋单一保守的传统王朝。安禄山和史思明在内的安史集团,多由粟特人、粟特裔突厥人、粟特裔汉人组成,并获得了粟特商业体系的资金支持。而唐王朝平息安史之乱,得益于回鹘的支援。突厥裔的回鹘在唐王朝由盛转衰过程中崛起,很快成为了与唐、吐蕃分庭抗礼,掌控西域和蒙古高原的新霸主。
书讯
《两栖爬行动物的神话与传说》
本书是一首关于蟾蜍和蛇、蝾螈和蜥蜴、鳄鱼和乌龟的颂歌。在这本书里,爬虫学家兼科普作家马蒂·克伦普探索了世界各地从古至今的民间传说。从创世神话到小道消息,从生育和重生到火灾和雨水,从两栖爬行动物在民间医药和魔法中的用途到它们在文学、视觉艺术、音乐和舞蹈中扮演的角色,克伦普揭示了我们为什么会对这些动物又爱又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