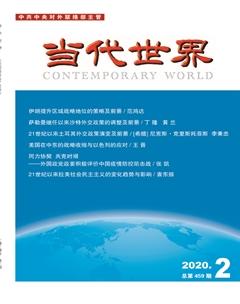萨勒曼继任以来沙特外交政策的调整及前景
丁隆 黄兰
【内容提要】2015年初萨勒曼继任沙特国王后,沙特外交政策开始由温和向激进转型,特别是在美国战略收缩背景下,沙特外交日趋强硬,倾向采取军事手段解决外交问题。沙特在寻求为沙美关系注入新内涵的同时,不断提高外交自主性,进一步加强与俄罗斯、中国的合作关系。发展和战略焦虑上升、国内政治出现不稳定、影响外交关键因素和领导人个人风格发生变化,是沙特外交政策出现激进化和自主性增强的主要影响因素。当前,由于激进化外交政策遇到挫折,沙特外交政策开始向温和务实方向回摆。
【关键词】沙特外交政策;美沙同盟;沙伊关系;特朗普中东政策;萨勒曼
【DOI】10.19422/j.cnki.ddsj.2020.02.002
2015年初,萨勒曼继任沙特国王。不同于以往历次沙特王位传承,此次王位继承给沙特内政和外交带来深远影响。内政方面,经过两次废黜王储,萨勒曼最终立其子穆罕默德为王储,改变了沙特建国以来“兄终弟及”的王位传承模式,沙特因此进入“萨勒曼王朝”。在穆罕默德王储的主持下,沙特推出“2030愿景”发展规划,启动经济、社会等全方位的深刻改革,触及沙特自建国以来延续至今的有关政教关系、妇女权利和经济模式等基本制度。外交方面,沙特一改传统温和的外交政策,日趋激进和强硬,趋向采取军事手段解决外交问题。在与大国关系方面,由于美国调整中东政策、减少地区投入,沙特需独自应对外交和安全挑战,以“石油换安全”为基础的沙美传统同盟关系有所松动。同时,面对国际能源市场的新变化,沙特需要与俄罗斯在能源政策上加强协调,与中国等亚洲国家在石油出口和经济转型发展上加强合作。因此,沙特外交自主性不断增强,其在设法继续维持与美国盟友关系的同时,也在多面下注,寻求合作伙伴多元化,以维护其经济利益和国际石油市场份额,对冲特朗普给沙美关系带来的不确定性。然而,沙特激进外交政策遭遇诸多挫折,如也门战争久拖不决、媒体人卡舒吉遇害引发国际关注、阿美石油公司油田设施遭袭等一系列问题,迫使沙特不得不审视其激进的外交和安全政策,重新确定自身的地区和国际角色。
推行以抗衡伊朗为中心的激进地区政策
特朗普上台后不断调整中东政策,总体思路是减少投入,降低外交和军事行动的经济成本,避免高风险军事行动,要求盟友承担更多财政义务,以期扮演“离岸平衡手”的角色。基于这一目标,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政策以遏制伊朗和巩固传统盟友关系为两大支柱。对于沙特而言,美国中东政策的调整使沙特与美国有了一个共同的战略敌手,这为双方联盟关系提供了有力支点,并且无论是遏制伊朗还是巩固盟友关系,都符合沙特的利益。
但是,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收缩导致地区出现权力真空,为伊朗等地区强国拓展势力范围提供了空间,引发沙特与伊朗新一轮地区主导权之争。伊朗力挺叙利亚巴沙尔政府,扶持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人民动员力量等什叶派武装。特别是伊拉克战争结束后,伊拉克国内政治生态发生巨变,什叶派上台执政,伊朗对伊拉克政局的影响力空前提升。近年来,伊朗在多个阿拉伯国家扶持什叶派民兵武装作为代理人,构建起“什叶之弧”,并采用“沙袋政策”筑起一道“防波堤”,将对美防线推至国境之外。伊朗借“阿拉伯之春”引发的地区动荡,不断扩大自身地缘政治空间,取得了对沙特等阿拉伯国家的相对战略优势。此外,伊朗的核计划也被沙特视为重大安全威胁,尤其是美国奥巴马政府选择与伊朗缓和关系,并推动国际社会与伊朗达成了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引发沙特强烈不满。
反观沙特,不仅未能遏制也门胡塞武装,反而深陷也门战争泥潭,本国领土还遭到胡塞武装攻击,大型油田设施等严重受损。同时,沙特在黎巴嫩等阿拉伯国家的势力和地区影响力正不断被伊朗蚕食。从表面看,沙特与伊朗的冲突缘自瓦哈比派与什叶派之间的教派冲突,但实质是两国围绕地区主导权的竞争,以及什叶派伊斯兰主义与阿拉伯君主制之间的制度竞争。以色列前外长索洛莫·本·阿米(Shlomo Ben Ami)指出:“伊朗欲改变地区权力格局,而实行君主制的沙特则是原有地区秩序的维护者。”[1]
沙特与伊朗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导致两国之间的安全困境,即随着伊朗国家实力和地区地位的提升,沙特的战略焦虑不断上升。面对伊朗日益坐大的势头,沙特在整个中东地区范围内与伊朗进行直接对抗。沙伊两国于2016年初断交,并在叙利亚、也门、黎巴嫩、伊拉克等国展开代理人战争或竞争。沙伊关系恶化推动沙特外交日益激进化,使其更迫切地采取對伊朗划线来维持地区事务主导权。2017年6月,沙特联手部分阿拉伯国家与卡塔尔断交,并对其实施制裁,而卡塔尔坚持与伊朗保持良好关系被视为此次断交危机的主因之一。

2019年10月1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时隔12年再次访问沙特。在与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会谈时,普京表示,俄罗斯与沙特加强协调对确保中东地区安全与稳定至关重要。图为在沙特首都利雅得,普京(左)与萨勒曼(右)出席欢迎仪式。
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收缩和伊朗的猛烈攻势迫使沙特对外政策激进性和自主性凸显。沙特牵头成立了具有地缘政治导向的联盟与区域合作机制,要求有关国家在沙特和伊朗之间选边站队,并组建反伊朗联盟,导致沙特与其他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然而,这些国家动机各异,从而导致沙特主导的联盟呈现松散性和功利性的特征。
一是深化与阿联酋合作,构建以沙特—阿联酋联盟为轴心的海湾新格局,弱化海湾合作委员会的作用。沙特与阿联酋脱离海合会另立联盟,并不是海合会分裂后的应激之举。2016年5月,沙特与阿联酋设立“沙特—阿联酋协调委员会”(Saudi-Emirati Coordination Council),并于2018年6月公布由44个战略合作计划组成的“决心计划”(The Strategy of Resolve),[2]以实现两国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一体化。沙特此举意在舍弃发生分裂的海合会,希望与阿联酋联手巩固地区领导地位,重塑海湾力量平衡。 此外,沙特与阿联酋结盟还有经济方面的考量。2018年两国经济总量达1万亿美元,相当于世界第十五大经济体。[3]两国石油储量占世界石油总储量的23%,产量占总产量的15%,两国经济整合可在国际原油市场上获得更强的谈判地位。同时,沙特将阿联酋作为效仿的榜样,学习以“经济繁荣、强势政府、世俗主义”为特征的“阿联酋模式”。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与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也建立了深厚的个人友谊,并将后者视为“导师”。
二是改善与以色列的关系。沙特发展与以色列的关系,是其基于自身利益转变采取的战略调整。随着伊朗地区影響力日益上升,伊朗已取代以色列成为沙特在地区内的头号敌手,中东和平进程等泛阿拉伯、伊斯兰问题也不再是沙特关心的首要议题。因此,与以色列联手抗衡伊朗,成为沙特的务实选择。在美国整合其中东盟友联合抗衡伊朗的背景下,通过改善与以色列关系,沙特可迎合美国的中东战略,进一步向美国靠拢。
2018年3月22日,沙特打破70年的禁令,首次向飞往以色列的商业航班开放领空,成为沙以关系升温的标志性事件。同年4月,沙特王储穆罕默德访美期间接受美国《大西洋月刊》主编戈德堡采访时表示,“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都有权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但须有一项和平协议保障”,“对于建立犹太国,并无宗教上的障碍”,“我们与以色列有很多共同利益,如果实现和平,以色列和海合会成员国之间将有许多共同利益”。上述表态被解读为沙特对以政策发生实质性变化,即沙特准备承认以色列,两国关系将向正常化方向发展。此外,为规避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的安全威胁,沙特正在与以色列谈判,计划修建通往以色列南部港口城市埃拉特的输气管道,未来还可能扩建为通往以色列海法的输油管道,成为沙特石油出口欧洲的通道。[4]同时,埃及决定将萨纳菲尔岛和蒂朗岛移交沙特后,沙以有了新的地理和战略上的联系。这两个岛屿都位于以色列进入红海的唯一通道——蒂朗海峡,未来可能成为沙以军事和经贸合作的重要区域。
三是牵头组建红海和亚丁湾沿岸国家理事会。2018年12月12日,沙特举办了红海和亚丁湾沿岸国家外长会议。2020年1月6日,红海和亚丁湾沿岸国家外长会议再度在沙特利雅得召开,外长会议讨论了该地区共同政治、安全和投资利益,海上航行安全和应对外国势力干涉等问题,同时签署了红海和亚丁湾沿岸国家理事会成立宪章。[5]该理事会成员包括红海和亚丁湾沿岸的沙特、埃及、苏丹、也门、约旦、厄立特里亚、吉布提和索马里8个阿拉伯和非洲国家。沙特组建该国际组织,旨在增强该地区国家应对危险和挑战的能力,保护红海和亚丁湾海域免受任何威胁,寻求与红海沿岸国家开展经贸合作,规划并建设符合自身利益的红海新区。更重要的是,沙特意图将红海区域纳入自身势力范围,将其作为新的战略支点,并排挤在此活跃的伊朗、土耳其和卡塔尔等国。
外交多元化与维护大国关系
大国关系是沙特外交的重中之重。近年来,美国实施战略收缩,不愿介入中东地区冲突。与此同时,美国实现能源独立导致沙美之间“石油换安全”的根基发生动摇。鉴于此,沙特一方面迎合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对外政策,采取一系列措施赋予沙美关系新内涵。另一方面,在中东地缘政治博弈“俄进美退”的背景下,沙特主动加强与俄罗斯的合作,以维持自身在国际原油市场的地位,摆脱外交困局。此外,为了推动经济发展,赢得更多国际支持,沙特开始“向东看”,越来越重视发展同中国的关系。
一、赋予沙美关系新内涵
与美国结盟是沙特建国以来一贯的立国之策。沙特缺乏安全感,若无外部安全保护,无法在动荡的中东生存。在沙特看来,只有美国能够为自身提供安全保护。因此,沙特把沙美联盟排在自身全球议程的首位。然而,自“9·11”事件以来,沙美关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两国关系的安全基础发生动摇,甚至在能源领域还转为竞争关系,并在“卡舒吉案”和也门战争上产生了尖锐矛盾。沙美对彼此的诉求在美国进行战略收缩的时期发生了错位,即美国欲淡出中东、重返亚太,而沙特欲倚重美国对抗伊朗。特别是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油田设施遭袭后,美国未做出反应,使依靠美国保障国土安全的有效性和沙美联盟关系的可靠性遭到沙特国内的普遍质疑。
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对外政策,使沙美联盟日趋呈现功利性和临时性的特征。沙特认为,即使在地区议题和军售协议上赢得了特朗普的支持,“在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也将面临不确定的投票结果”。[6] 2018年10月发生“卡舒吉案”后,美国国会不断要求对沙特实施制裁,限制美国对沙特军售规模。2019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反对美国为沙特联军在也门的军事活动提供支持。此外,美国已反超沙特成为最大的石油生产国,两国成为国际原油市场上的竞争者。更重要的是,美国由于战略收缩,不愿介入中东地区冲突。2019年5月以来,沙特、阿联酋多国油轮遇袭;6月,美国无人机被伊朗击落;9月,沙特石油设施遇袭,美国均未采取有效的反制措施。2019年12月,美军决定撤离叙利亚,使得沙特在叙利亚问题上借力美国遏制伊朗扩张的计划落空。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副总裁弗兰克·弗拉斯特罗(Frank Verrastro)指出:“美沙特殊关系已不复存在,并在一段时间以来持续恶化,如今的美沙关系不像从前那般牢固了。”[7]

2019年9月,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石油设施进行袭击,导致沙特石油一度减产50%。图为2019年9月14日的卫星照片,显示位于沙特布盖格的沙特阿美公司石油设施起火后冒出浓烟。
然而,沙特在安全上别无选择,仍然只能依靠美国。沙特将特朗普上台视为恢复沙美联盟关系的机遇,并采取以下三项措施赋予沙美关系新内涵。
第一,支持特朗普中东和平方案。为配合特朗普政府在巴以问题上推出的所谓“世纪交易”,沙特极力调整在巴以冲突问题上的立场。2019年6月,美国在巴林召开的“和平促繁荣”研讨会上公布了“世纪交易”的经济部分,即实际上是以经济利益诱使巴勒斯坦放弃大部分政治诉求,以偏袒以色列的方式解决巴以问题。对此,巴勒斯坦和广大阿拉伯国家并不接受,除主办方巴林外,只有沙特、阿联酋等少数几个阿拉伯国家参加会议。虽然沙特对协议内容并不完全赞同,但仍愿意配合特朗普政府,充当巴以和美巴之间的中间人。
第二,为沙美联盟构筑新基础。沙特试图以“军购换安全”替代“石油换安全”,为沙美关系注入新活力。“页岩油革命”使美國实现能源独立,不再依赖沙特石油,建立在“石油换安全”上的沙美盟友关系失去了重要根基。为维持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沙特试图以军购作为沙美关系的新基础。2017年5月,特朗普将上任后首次出访的首站放在沙特,双方签订总额超过1100亿美元的军售合同。[8] 2018年3月,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对美国进行空前的21天超长访问,期间与美方达成总额高达125亿美元的军购订单。
第三,为配合特朗普“美国优先”政策,加大对美投资力度。沙特试图通过扩大对美国的投资,实现对两国利益的捆绑。据美国大数据分析公司Quid统计,2014—2018年,沙特在美国直接参与了至少62亿美元的融资,[9]并成为硅谷最大的出资方。此外,沙特向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风险投资基金——软银愿景(Softbank Vision Fund)注资450亿美元,成为其最大股东,而该基金主要投资对象国便是美国。沙特王储穆罕默德访美期间,宣布对美国投资2000亿美元。军购和投资对于在外交上注重获取经济利益的特朗普尤其有效。“卡舒吉案”发生后,国际社会普遍谴责沙特,特朗普却态度暧昧,对外声称“不满意沙特的答复”,但又称自己“不想失去沙特在美国的投资,不想让美国失去100万个就业岗位” 。[10]
二、加强与俄罗斯的紧密合作
与沙美关系出现较大波动不同,沙特与俄罗斯关系迅速升温。2017年10月,沙特国王萨勒曼访问俄罗斯,成为首位访问俄罗斯的沙特国王。2018年6月,沙特王储穆罕默德访俄。2019年10月,俄罗斯总统普京时隔12年再次访问沙特,两国签署20余项合作协议,总额近100亿美元。
沙特与俄罗斯交好,一方面是为了联合俄罗斯共同调控国际油价。美国的“页岩油革命”使其在国际原油市场上的份额迅速提升,并开始与沙特主导的石油输出国组织(简称“欧佩克”)争夺国际油价话语权。因此,沙特选择联合同为石油出口大国的俄罗斯,对抗美国页岩油对国际原油市场格局的冲击。可以说,“美国页岩油拉近了沙特与俄罗斯的关系”。[11]
另一方面,在美国选择淡出中东之际,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却逐步上升,沙特已经接受了俄罗斯作为地区主要玩家的角色。近年来,沙特在与伊朗的较量中处于劣势,这不仅由于沙特军事实力相对较弱,也是中东地缘政治博弈中“俄进美退”的结果。因此,与俄罗斯保持良好关系,有利于沙特摆脱外交困局。沙特《中东报》前总编辑阿卜杜·拉赫曼·拉希德指出:“沙特与俄罗斯公开接近是两国共同利益驱动的务实之举。”[12] 例如,在叙利亚问题上,沙特支持的叙反对派大势已去,沙特只得将其目标调整为“避免叙利亚落入伊朗的完全掌控之中,遏制真主党民兵的扩散,以及阻止土耳其控制叙利亚的油田和地缘战略要地”。[13] 而沙特要想实现上述目标,离不开俄罗斯的支持与协助。而俄罗斯不希望叙利亚“伊朗化”“什叶化”[14],并且也有意遏制土耳其在叙利亚的势力扩张。
三、重视同中国发展全方位合作关系
随着中国成为沙特最大贸易伙伴和石油出口市场,沙特开始“向东看”,越来越重视发展同中国的关系。2016—2019年,沙特国王和王储三次访华,与中国签订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的合作协议,涉及从能源到太空的众多领域。沙特“向东看”具有伙伴多元化、经济多元化和市场多元化的多重考虑。
首先,沙特高度重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石油消费市场,并将其视为长期、稳定和可靠的能源出口市场。英国石油公司《2035年能源展望》预测,今后全球液体燃料的需求增长主要来自于新兴经济体,其中中国将占一半。[15] 2019年1—8月,沙特75%的出口原油销往亚洲。[16]2018年,中国每天从沙特进口原油高达160万桶,约占中国原油总进口量的15%。沙特石油对中国和印度等亚洲国家的能源安全至关重要。同时,在全球石油市场供大于求的局面下,沙特需要维护亚洲的石油“大买家”。沙特积极投资亚洲石化下游产业,2019年2月,沙特王储穆罕默德访问亚洲期间,分别与中国和巴基斯坦签订投资额达数百亿美元的石化项目合同,以扩大其在亚洲石化产品市场的份额。
其次,沙特希望拓展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中国与沙特具有很强的经济互补性,中国已是包括沙特在内的10个阿拉伯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2018年中沙贸易额达633亿美元,中国连续8年成为沙特最大贸易伙伴,沙特连续18年成为中国在西亚非洲地区第一大贸易伙伴。沙特积极开展与中国在多领域的合作,并致力于将自身“2030愿景”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对接。
最后,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沙特将中国视为“宝贵的政治支持资源”。[17]2016年,美国国会通过“制裁恐怖主义支持者法案”(又称“9·11法案”),允许“9·11”事件受害者和家属起诉沙特政府并向其索赔。中国对此持反对意见,并提出沙特政府应享有主权豁免。此外,“卡舒吉事件”发生后,沙特在国际上受到严重孤立,但中国仍接待了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来访,体现了对沙特的外交支持。
除了积极发展同大国的关系,沙特还高度重视多边外交,特别是以二十国集团为多边外交的主要平台。2019年12月1日,沙特开始担任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国,并将于2020年11月21—22日在利雅得举办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沙特将此次峰会视为改善国际形象、展示开放的新沙特的重要契机,现已投入巨资筹备会议。
沙特对外政策调整的动因
沙特外交转型有多重动因,其中发展和战略焦虑、国内政治不稳定、影响外交的关键因素发生变化以及领导人个人风格变化是主要因素。
首先,发展焦虑和战略焦虑促使沙特调整外交政策。2014年国际油价暴跌后,沙特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2019年,沙特石油收入约占其财政收入的66%,预计2020年将占62%,2020年沙特的财政赤字将达约500亿美元。[18] 同时,沙特认为自己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投资环境等方面,已比阿联酋等海湾邻国落后数十年。为此,沙特把经济外交放在优先位置,注重发展与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关系,深化与阿联酋的盟友关系,试图开拓外部经济和发展资源。战略焦虑则是由于美国中东政策调整和伊朗在地区的崛起,加剧了沙特的不安全感,使其更倾向于依靠自己,并以激进和强硬的方式应对外交和安全挑战。
其次,沙特外交政策调整是其国内政治变化的外部投射。“沙特进攻性的外交政策是其国内政治经济不稳定的反映。”[19]2015—2017年,沙特國内政局发生剧变,其外交政策也最为激进。萨勒曼国王继位后,经过二度易储并立其子穆罕默德为王储。为释放内部压力,沙特“通过升级与卡塔尔的冲突”转移国内注意力,“2015年入侵也门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20]
再次,宗教和教派因素不再是影响沙特外交的关键因素。沙特民族主义取代泛伊斯兰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成为沙特外交的意识形态基础,以利益和权力为核心的现实主义成为沙特外交的指导原则。对于沙特而言,现实政治中的安全和战略关切已超过宗教因素,瓦哈比主义越来越成为沙特的“负资产”,并不再被沙特当作拓展软实力的工具。例如,在处理与以色列的关系时,沙特不再被“阿拉伯和伊斯兰共同事业”束缚,而是从国家利益出发,作出改善与以色列关系的战略抉择。上述外交政策转变也与沙特国内“去瓦哈比化”和“世俗化”的改革形成同频共振。
最后,以穆罕默德王储为代表的新领导层的行事风格,推动了沙特外交激进化。穆罕默德王储放弃了王室内部集体决策和官僚体系参与决策,沙特国家决策呈现“去官僚化”的趋势。沙特内阁中的王室成员显著减少,内政和外交实权集中于以王储为核心的领导层,权力集中也使其可以做出更为果断也更为激进的一系列决策。
沙特外交温和性回摆及其前景
沙特激进的外交和安全政策遭受了系列挫折。沙特对伊朗的强硬政策,不仅未能遏制伊朗扩张,反而促使其采取更强硬政策予以回应。目前,伊朗已在也门、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取得明显优势。沙特原计划在数周内结束的也门战事,现已持续近五年,不仅加剧了沙特经济困境,还威胁到自身国内安全。2017年11月,胡塞武装开始对沙特本土发动导弹袭击,并造成平民伤亡。2019年9月,胡塞武装对沙特石油设施进行袭击,导致沙特石油一度减产50%。与此同时,伊朗公开对胡塞武装表示支持。2019年8月,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会见胡塞武装首席谈判代表穆罕默德·阿卜杜·萨拉姆,宣布伊朗支持该武装。[21]更重要的是,沙特在也门的军事行动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联合国称也门正在发生“世界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使得沙特国际形象严重受损。
面对诸多挫折,沙特外交政策不得不进行再调整,呈现去激进化的趋势。在也门问题上,沙特已开始为结束也门战事寻找政治解决方案。2019年11月5日,在沙特主持下,也门政府与南方过渡委员会(STC)签署了《利雅得协议》。[22]同月,在阿曼斡旋下,沙特与胡塞武装举行了间接和谈。[23]
沙特对伊朗的态度也出现了缓和迹象。2019年10月,沙特外交国务大臣朱拜尔对伊朗外长扎里夫关于恢复两国外交关系的表态作出回应,表示“随时准备与我们的邻国合作”。[24] 然而,2020年1月,在特朗普的授意下,美军利用无人机对伊朗高级军官苏莱曼尼实施了“定点清除”,美伊冲突升级增加沙伊关系缓和的不确定性。对此,沙特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防止事态升级。沙特的上述声明应被解读为真实诉求,而非外交辞令。虽然与伊朗长期对峙,但沙特无意与伊朗开战。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在也门内战中的立场分歧,沙特与阿联酋的盟友关系出现裂痕。沙特支持也门政府,阿联酋支持南方过渡委员会,两者在也门内部不断争夺势力范围,使沙特—阿联酋盟友关系受到考验。在此背景下,沙特或将改善与卡塔尔的关系,不排除将重新启动海合会合作机制。
总的来说,沙特外交屡屡受挫的根源是国家实力难以与其战略雄心相匹配,并且出现了国家安全接受者与地区安全提供者的角色错位。如今,沙特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于国内。在此背景下,沙特将更多聚焦国内改革和经济发展,其外交政策重回激进路线的可能性不大。近期,沙特王室资深亲王和官僚体系在外交决策中的作用又在增加,正是沙特外交重归温和的象征。
(第一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海湾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第二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
(责任编辑:苏童)
[1] 索洛莫·本·阿米:《宗教在中东政治上的衰落》,载《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第24期,第46页。
[2] “UAE, Saudi Arabia Announce Joint Vision, Strategic Partnership Across 44 Economic, Developmental, Military Projects”, https://uaecabinet.ae/en/details/news/uae-saudi-arabia-announce-joint-vision-strategic-partnership-across-44-economic-developmental-military-projects.
[3] Mohammad Al-Asoomi, “Saudi-UAE Alliance Can Be An Economic Behemoth”, https://gulfnews.com/business/analysis/saudi-uae-alliance-can-be-an-economic-behemoth-1.68245989.
[4] “Saudi Urges Self-Restraint Over U.S. Strike In Iraq”,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iraq-security-blast-saudi-idUSL8N2983BU.
[5] “Red Sea, Gulf of Aden Border Countries Form New Bloc To Tackle Challenges”, http://saudigazette.com.sa/article/586375/SAUDI-ARABIA/Red-Sea-Gulf-of-Aden-border-countries-form-new-bloc-to-tackle-challenges.
[6] Madawi Al-Rasheed, “King Salman and His Son: Winning the USA, Losing the Rest”, in Madawi Al-Rasheed ed., Salmans Legacy:The Dilemmas of a New Era in Saudi Arab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240.
[7] Alan Neuhauser, “Saudi Arabias Pivot to Asia”, https://www.usnews.com/news/the-report/articles/2019-08-23/saudi-arabia-longtime-us-ally-builds-ties-with-china.
[8]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Saudi Arabia: Background and U.S. Relations”, https://fas.org/sgp/crs/mideast/RL33533.pdf.
[9] Quid, “Quartz uses Quid to track Saudi investments in tech”, https://quid.com/feed/quartz-uses-quid-to-track-saudi-investments-in-tech.
[10] Conor Finnegan, “Trump‘Not Satisfied With Saudi Response to Khashoggi Killing, But Not Willing to Risk Arms Sales”, https://abcnews.go.com/Politics/trump-satisfied-saudi-response-khashoggi-killing-risk-arms/story?id=58670976.
[11] Abdul Rahman Al-Rashid, “Riyadh: Between Washington and Moscow”, https://www.arabnews.com/node/1569236.
[12] ??? ?????? ??????, “?????? ??? ????? ???????”, https://aawsat.com/home/article/1945686/???-??????-??????/??????-???-?????-???????.
[13] 同[12]。
[14] Clément Therme, “Iran and Russia in the Middle East: Toward a Regional Alliance?”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72, No. 4, Autumn 2018, p. 561.
[15] BP, “Energy Outlook 2035”, https://goo.gl/VNJnKi.
[16] 同[8]。
[17] Naser Al-Tamimi, “Chinas rise in the Gulf: A Saudi perspective”, in Madawi Al-Rasheed ed., Salmans Legacy:The Dilemmas of a New Era in Saudi Arab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266.
[18] Abdullah Al-Fozan,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Budget Report”, https://home.kpmg/content/dam/kpmg/sa/pdf/2019/kingdom-of-saudi-arabia-2020-budget-report-english.pdf.
[19] 同[6], p.250。
[20] Ayaan Hirsi Ali, “The Plot Behind Saudi Arabia s Fight With Qatar”,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4, 2017.
[21] Jonathan Fenton-Harvey, “How Saudi Arabias Foreign Policy is Backfiring”, https://insidearabia.com/how-saudi-arabias-foreign-policy-is-backfiring/.
[22] “Arab World Welcomes Signing of Riyadh Agreement on Yemen”, https://aawsat.com/english/home/article/1978416/arab-world-welcomes-signing-riyadh-agreement-yemen.
[23] Ramadan Al-Sherbini, “Oman: Saudis, Al-Houthis interested in deal”, https://gulfnews.com/world/gulf/yemen/oman-saudis-al-houthis-interested-in-deal-1.68090645.
[24] Mohammad S. Al-zoubi, “Iran and Saudi Arabia: Imagining a Path Towards Rapprochement”, https://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fikraforum/view/iran-and-saudi-arabia-imagining-a-path-towards-rapproch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