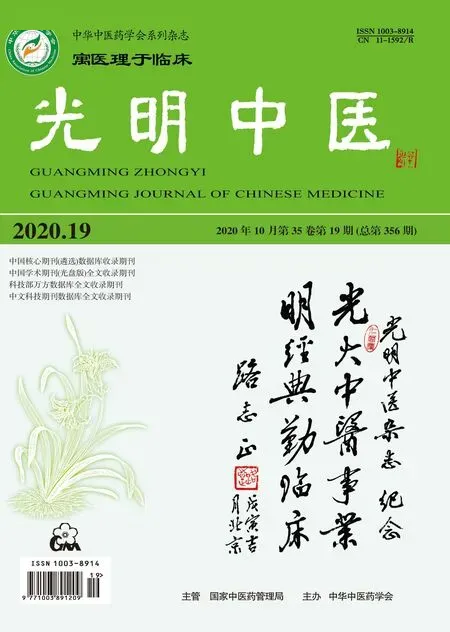栗锦迁教授辨治胸痹心痛临证撷萃*
陈 玲 李树茂△ 陈付艳 何 璇
栗锦迁是全国第3~6批名老中医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从事中医内科临床工作50余载,长于治疗脾胃病、心病及相关疑难病症,擅用经方,用药配伍精当。现将栗锦迁教授对于胸痹心痛在诊治上的经验总结如下。
1 四诊合参 见微知著
栗师常博览古典医籍,结合该病四诊的要点,归纳了一系列规律性的特色辨证。
1.1 辨疼痛在辨证之时,以胸痹疼痛的性质、频率、程度、时限、病程及兼证等方面进行鉴别。如疼痛每于活动时频频发作,伴有汗出,尤其是头汗出时,多为心气虚之证;若胸痹于恼怒后出现胀痛,走窜不定,时间较长,则多气滞导致心气不利之证;若胸痹遇寒加重,夜间痛重,手足发凉,精神萎靡不振,多为心阳不足之证;若胸口闷痛,背寒如掌大,疼痛缠绵,则多为痰饮内停之证。
1.2 辨气味在辨治过程中,与致病特点及病因病机结合,注重辨识患者口中气味。如口中苦者多为肝胃不和或心胆气虚;口中气味咸而润多为肾虚或寒湿上泛;口中清冷无味者亦多为脾胃气虚或寒象;口中甜腻多为湿热内蕴;口中甜而食少多为脾虚;口中酸腐可见于肝木乘脾,宿食停积;口中有臭味者多为有热之象。
1.3 辨舌象通过观察舌体、舌色、舌苔、舌下脉络以辨该病虚实。舌体瘀斑或瘀点为瘀血;舌面有竖行裂纹为气虚,有横行和竖行裂纹交错为伤阴;舌色偏淡为气虚,淡白为阳虚,淡黯为寒象更重;舌红嫩者为伤津之象;舌紫如润为寒凝或瘀血;苔白腻为寒湿;苔黄腻为湿热;苔腐为热偏重而夹湿;苔上两侧覆有黏液为饮邪内聚;舌下脉络迂曲紫黑者为瘀血阻络。
2 追本逐源 探求病机
栗锦迁教授深悟仲景在《金匮要略》中阐发的“阳微阴弦,即胸痹而痛”之意,系因正气不足(即“阳微”)、外感寒邪、饮食失节、情志不调、劳倦过度等因素致寒凝、痰湿、气滞、血瘀痹阻心脉(即“阴弦”),使气血运行不畅而致心脉痹阻,胸中阳气郁遏而痛。其病位在心,涉及肝脾肾,病机为本虚标实,常虚实夹杂为病。虚者多以气虚、阳虚为主,实者多为气滞、寒凝、痰浊、血瘀相兼而见。虚实两方面多互为因果,互相影响,常实中有虚,虚中存实,有以实证为主,有以虚证为主,较为复杂,故在治法上,应辨别标本缓急,分清主次。
3 尊崇经典 圆机活法
在辨证立法方面,根据胸痹心痛标本虚实变化的病因病机特点,以益气温阳,化痰宣痹、活血化瘀为大法,以求振奋阳气,通行血脉,并在此基础上执简驭繁,灵活变化。因此,结合治疗该病的治则治法特点,研究其用药规律,总结出的常用基础药物为:桂枝、生黄芪、陈皮、茯苓、赤芍、当归、川芎、桔梗、枳壳、党参、清半夏、五味子、白术[1],该方涵盖了桂枝甘草汤、四君子汤、血府逐瘀汤和二陈汤方,充分体现并验证了栗教授治疗胸痹心痛的理法特点,现分析如下。
首先重视温阳。阳气是一切生命的本源,在生命中居主导地位,人的生、老、病、死及一切生命活动依赖于阳气。血运行于脉中,无不依赖于阳气的推动及温煦作用。心居胸中,为阳中之太阳,为君火,阳气之主,与脾阳、肾阳关系密切。脾阳为后天阳气之本,升举及输布水谷精微至心肺,心肺得以濡养,则气血旺盛。肾为相火,为阳气之根,心阳得肾阳温养,则心肾交济,心阳振奋。此外,若心、脾、肾三脏阳虚,则寒凝、血瘀、痰湿痹阻,流连难去。在治法上,正如《类证治裁·卷之六·胸痹论治》云:“胸痹,胸中阳微不运……以《金匮》《千金》均以通阳主治也。”栗教授所云温阳包括通心阳、温脾阳、补肾阳,而当以通心阳为立法立方之根本。通心阳以桂枝为主,量多为10~25 g,常用方剂如桂枝甘草汤、桂枝加桂汤、桂枝加黄芪汤、苓桂术甘汤、枳实薤白桂枝汤等;温脾阳,常加干姜、炮姜、肉豆蔻、吴茱萸,补肾阳则常用淫羊藿、菟丝子、沙苑子、巴戟天,而温阳甚少用附片、人参、肉桂等其性大辛大热之品,是为防其悍利之性化燥伤阴,途生变证。
其次,栗师认为无论胸痹心痛之标本虚实,治疗应重视脾胃。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胸中之宗气,肾中之元气,脉中之营气,与气血行脉道,胸阳振奋息息相关,而三者无不依赖于脾胃化生精微的作用。同时,脾胃还是调节气机升降之枢纽,《四圣心源》云:“脾主上升,脾升则肾肝亦升,故水木不郁;胃主下行,胃降则心肺亦降,金火不滞……此外,脏腑之气的升降变化,亦根于中气。”由此可知,五脏之气,离不开脾之升清,胃之降浊。且心与脾胃关系密切,心主血,脾统血,血运脉中,心与脾共同维持。心属火,脾胃属土,两者为母子关系,心病可及脾胃,在临床上常发现患有冠心病者,合并有腹胀、痞满、便溏之脾胃病症。胸痹之病,痰湿停聚与脾胃相关,因脾为生痰之源,健脾运胃有助于祛痰化饮,若只用活血化痰,而不健运脾胃,则难治其根本。综上而论,治疗胸痹心痛与调运脾胃密不可分。
栗教授对于益气的理解,不仅包括补气,还包括理气、敛气3个方面,即调理气的功能多从脾胃入手。补气用生黄芪、党参、白术以益气健脾,依患者的病情轻重,特别是舌中间有纵裂纹者,黄芪可从30 g逐渐序贯加量至50 g,伴有扩展性心肌病或肥厚性心肌病者可增至100 g,方用四君子汤、当归补血汤等;调理气机用枳壳、桔梗、木香、陈皮、厚朴以健脾理气,常用方剂异功散、香砂六君子汤、枳术丸、逍遥散等;同时在健脾调气时,还常配五味子、酒萸肉勿忘敛心气、纳肾气,但此法需辨清虚实,以防关门留寇。
在临床中,栗教授发现胸痹患者多见舌苔偏腻,甚至水滑苔,或舌体两边有黏液,脉弦滑或滑数,即痰湿停聚之证,这和社会饮食结构变化、吸烟饮酒、过食肥甘厚味、运动减少、生活压力等因素有关,因此痰湿停聚符合现代胸痹致病特征的常见病机[2]。栗教授认为痰既是由阳气不足,水液停聚而成,但反之它又阻遏阳气温通,气机升降,正如戴思恭在《证治要决·卷三》所云:“故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气,气顺则一身之津液亦随气而顺矣”,故以温阳行气、益气健脾而除痰为先,这是治生痰之源,即“治痰先治气”。此外,还要除已成之痰。在治痰之法中,栗教授擅长运用燥化、温化和清化3种治法。燥化法常用二陈汤、橘枳姜汤,小半夏加茯苓汤;温化法常用二陈汤加桂枝、枳实薤白桂枝汤、瓜蒌薤白半夏汤、桂枝生姜枳实汤、苓桂术甘汤等;清化法常用温胆汤、黄连温胆汤、小陷胸汤;还有温清并用法以枳实消痞丸、半夏泻心汤为主。
再有,栗教授坚持以活血化瘀之法贯穿胸痹心痛病始终,皆因瘀阻心脉为本病的核心病机。以王清任《医林改错》之血府逐瘀汤中川芎、赤芍、当归、红花为活血化瘀的主药,有实验研究表明[3],其有效成分能明显降低血小板聚集,改善阿司匹林抵抗。凡瘀重者可加桃仁、三七粉以加强破血逐瘀,活血养血之功。同时,他还喜用红景天益气活血加强疗效,特别对于支架术后者,能有效改善血管内皮损伤[4]以及提高心肌细胞活性[5]。平时老师极少用虫类药活血通络及三棱、莪术破血逐瘀之品,皆因其易耗气伤气,损伤脾胃。
最后,他在整体治法上,还特别强调以下内容:①顺应时令变化,夏季伴暑湿者常配藿香、佩兰。②方中常酌加养阴之品,如玄参、生地黄、麦冬、石斛、女贞子、何首乌等,第一防止温阳药物化火伤阴,第二可防止化痰燥湿药物过燥伤阴,第三起到从阴引阳的效果,有助于温阳。③寒热错杂者,分清寒热轻重,调整温化和清化的药物比重;虚实错杂者,先祛实再补虚,避免补虚过早,余邪难去。特别是伤阴者,应注意是否有痰饮,化燥祛痰同时,勿忘养阴,燥湿药容易加重伤阴,而养阴同时又容易引起痰浊胶固,故宜用少量温阳药,从阳引阴,有助于化痰,且栗教授甚少用熟地黄这类滋腻补益之品,补阴效果强但又易使痰浊难去,避免出现如油裹面的局面。故在治疗中应通过辨证,权衡轻重缓急,配伍应用。④胸痹心痛非短期可痊愈,需待病情改善后,多以配制丸药来巩固疗效,长期服用效果理想。
4 验案举隅
患者男性,69岁。2018年1月2日初诊。主诉:胸痛间断性发作5年,加重2 d。患者数年前因琐事,自觉胸闷憋气心前区疼痛就诊于天津胸科医院,查心电图:窦性心律,心率:75次/min,T波低平;查冠脉造影:左前降支狭窄30%。诊为冠心病,不稳定心绞痛,心肌缺血。现劳累及情绪激动后反复发作,长期服用西药缓解不彻底。2日前,间断性出现前胸后背疼痛,发作较前频繁。症见:胸闷,气短,胸痛彻背,后背发凉,肩背沉重压痛,时有汗出,双下肢及足部时有寒凉感,大便干不易解,1~2 d一行,纳寐可,小便调,舌暗红中间有裂纹,舌下静脉暗紫,苔白微腻,左脉无力,右脉沉弦。中医诊断:胸痹心痛(心阳不振,痰瘀互结,水饮停聚);西医诊断: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肌缺血,不稳定型心绞痛。治宜益气温阳化饮,化痰祛瘀止痛。拟方以血府逐瘀汤、苓桂术甘汤合四逆散、二陈汤加减。处方:黄芪 30 g,当归 15 g,炒白术15 g,川芎20 g,茯苓 20 g,桔梗 15 g,陈皮 15 g,赤芍 20 g,枳壳15 g,柴胡20 g,清半夏15 g,木香 15 g,炙甘草 10 g,片姜黄 20 g,酒苁蓉 25 g,桂枝 20 g。每日1剂,水煎早晚温服,服用7 d。
2018年1月9日二诊:患者自觉胸闷气短较前缓解,肩背疼痛发作频率减轻,汗出大减,大便通畅,余同前。苔腻较前改善,左脉较前有力。原方去酒苁蓉,减桂枝至15 g,继前服用14 d。
2018年1月23日三诊:患者自觉胸闷气短较前缓解,无肩背疼痛及背寒之证,四肢不冷,舌暗红中间有裂纹,苔微黄腻,左脉较前有力,右脉弦。故原方去片姜黄,加香附15 g,继服7剂。
2018年1月30日四诊:诸症平稳,未见明显发作,减桂枝至10 g,守上方7料,配成水丸服用,每次6 g,早晚分服。
按:本病复杂,四诊合参,年老心气虚,心阳不振而致痰湿血瘀互相搏结,水饮停聚,阴寒之气内盛,上凌于心,心阳被抑,不能温通于背,而发为胸痹心痛之证,且伴有阳郁不达四末之证。栗教授曾在授课中提到《伤寒杂病论》中“夫心下有留饮,其人背寒如掌大”,故以温药和之。在治法上以益气温阳、化痰祛瘀为治疗大法。本方中用苓桂术甘汤以温阳化饮、健脾利湿,血府逐瘀汤以活血化瘀,二陈汤以燥湿化痰、健脾益气,四逆散以调和肝脾、理气解郁,加温性片姜黄,可行气活血止痛而治疗肩臂之痛,酒苁蓉以温阳通便。二诊汗出大减,心气得渐复,减量桂枝至15 g。三诊阳气达于四末,则不冷,苔微黄腻,左脉有力,提示体内阳气得复,但不应减桂枝,便于继续通阳、和营、化瘀、利水、祛痰,减片姜黄防止过燥过热,因右脉弦,故加香附以加强行气之功。四诊,诸症平稳,继前丸药,维持疗效。本案充分总结了栗教授在治疗胸痹上的独特见解,以益气温阳、化痰祛瘀为大法,尤重益气温阳,重视脾胃,勿忘化痰祛瘀是治疗本病的治疗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