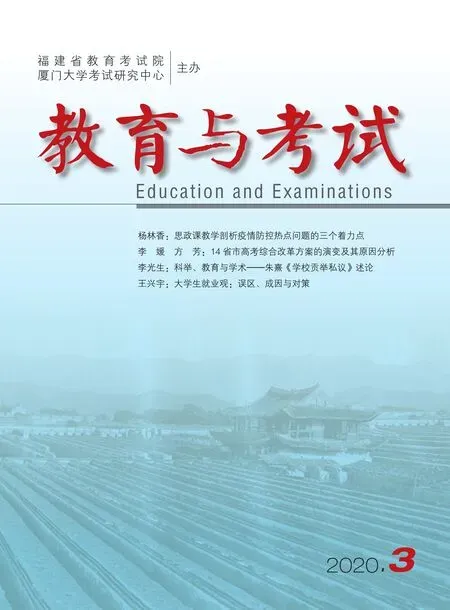科举、教育与学术*
——朱熹《学校贡举私议》述论
李光生
前言
《学校贡举私议》①(以下简称《私议》)乃朱熹晚年未及上呈的一份关于科举教育改革的奏议,束景南先生认为作于庆元元年(1195)。《朱子语类》载:“乙卯年,先生作《科举私议》一通,付(王)过看。大概欲于三年前晓示,下次科场,以某经、某子、某史试士人。如大义,每道只六百字,其余两场亦各不同。后次又预前以某年科场,别以某经、某子、某史试士人,盖欲其逐番精通也。过欲借录,不许。”[1]2698-2699据此,束氏考证道:“王过绍熙五年(1194)末来考亭问学,庆元元年(1195)上半年犹在考亭,故得见朱熹作《学校贡举私议》。盖朱熹在朝时,赵汝愚欲行三舍法,而陈傅良、叶适欲行混补,朱熹均反对,遂归而深思熟虑作《学校贡举私议》。”[2]《私议》被马端临收录于《文献通考》[3]之后俨成国人对待科举态度的定调之作,在中国科举史和教育史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然而,对于这样一个堪称经典的科举教育文本,虽说历代教育史尤其是宋代教育史著述多有涉及,但不免浮光掠影,令人遗憾②。迄今为止,学界仅李存山先生《朱子<学校贡举私议>述评》[4]一文,对《私议》做了较为深入的文本专题研究。李氏不仅剖析了朱熹完整的教育思想,认为其中之“明体达用之学”渊源于范仲淹、胡瑗等宋代新儒学先驱,而且把《私议》与中国近代学制改革相联系,突显其历史地位。见解精辟,尤具开拓之功。如果说李氏文主要着眼于从时间维度的纵向视角对《私议》进行研究,那么,本文主要从横向视角分析《私议》写作的真正动因及文化内涵,即朱熹在倡议科举改革、提出“德行道艺”的教育理想外,还有着针对永嘉学术的明显意图,其中也有朱熹对北宋以来学术传统在科举场域下获得支配性发展的质疑。
一
朱熹自幼立下学为“圣人”的宏愿,也把培养“圣人”看作教育的最终目的,所谓“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5]3873。然而,在科举文化已然成熟的宋代社会,大多数士人读书和受教育目的,往往直指科举功名而忽视了教育的道德意涵。朱熹《私议》针对当时科举制提出了尖锐批评:
今之为法不然,虽有乡举,而其取人之额不均,又设太学利诱之一涂,监试、漕试、附试诈冒之捷径,以启其奔趋流浪之意。其所以教者既不本于德行之实,而所谓艺者又皆无用之空言。至于甚弊,则其所谓空言者,又皆怪妄无稽而适足以败坏学者之心志。……而议者不知其病源之所在。反以程试文字之不工为患,而唱为混补之说,以益其弊。或者知其不可,又欲斟酌举行崇宁州县三舍之法,而使岁贡选士于太学。其说虽若贤于混补之云,然果行此,则士之求入乎州学者必众。[5]3633
朱熹认为解额不均和设立太学是科举制度的两大弊端,“足以败坏学者之心志”,尤其是太学,“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事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隽于场屋者耳。士之有志于义理者,既无所求于学,其奔趋辐凑而来者,不过为解额之滥、舍选之私而已。师生相视漠然,如行路之人。间相与言,亦未尝开之以德行道艺之实。而月书季考者,又只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无耻之心,殊非国家之所以立学教人之本意也”[5]3641。朱熹认为太学作为中央官学,只是“利诱之一涂”的“声利之场”,善为科举之文,失去了教人“德行道艺”的本意。
朱熹认为科举制度的弊端直接导致教育之失,因而倡议科举教育改革,《私议》接着说道:
莫若且均诸州之解额以定其志,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罢去词赋而分诸经子史时务之年以齐其业,又使治经者必守家法,命题者必依章句,答义者必通贯经文,条举众说而断以己意。学校则遴选实有道德之人,使专教导,以来实学之士。裁减解额舍选谬滥之恩,以塞利诱之涂。至於制科、词科、武举之属,亦皆究其利病而颇更其制。则有定志而无奔竞之风,有实行而无空言之弊,有实学而无不可用之材矣。[5]3634
在朱熹看来,“均诸州之解额”可以保证考试的公平公正,“立德行之科”可以兼顾考试的道德意义,“分诸经、子、史、时务”等科能培养学生通经致用之才。
关于立德行科,《私议》云:
故今莫若且以逐州新定解额之半而又折其半,以为德行之科。如解额百人则以二十五人为德行科,盖法行之初,恐考察未精,故且取其半而又减其半,其余五十人自依常法。……专委逐县令佐从实搜访,于省试后保明,津遣赴州。守倅审实,保明申部。于当年六月以前,以礼津遣,限本年内到部,拨入太学,于近上斋舍安排,而优其廪给,仍免课试。长贰以时延请询考,至次年终,以次差充大小职事。又次年终,择其尤异者特荐补官,余令特赴明年省试。比之余人,倍其取人分数,如余人二十取一,则此科十而取一,盖解额中已减其半矣。殿试各升一甲,其不中人,且令住学,以俟后举。其行义有亏、学术无取,举者亦当议罚。则士知实行之可贵,而不专事于空言矣。[5]3635-3636
朱熹建议从进士科中的地方考生解额中分出四分之一,以此额度来实行德行科的选拔。县令需要搜寻这样的人才,每次考试时把固定人数的德行科考生送至州府。如果他们可以通过州府级的考查,知州会将他们送往礼部,然后他们会有与进士科考生类似的安排。一旦到了京城,德行科考生会享受特殊待遇。他们会被送入太学,且不用参加学校里面的月书季考。太学第二年时,考生会去政府的各个部门实习,表现出色者会在第三年获得政府职位。剩下不能直接授官的学生则可以参加下一次省试。朱熹相信德行一旦成为科举的关键因素后就更容易推广,故德行科的创立和提倡会影响参与考试的所有人,也势必会导致教育的全面转型。为此,朱熹还主张任命有道德之人为学官,《私议》云:
其学校必选实有道德之人使为学官,以来实学之士。……择士之有道德、可为人师者以为学官而久其任,使之讲明道义,以教训其学者。而又痛减解额之滥以还诸州,罢去舍选之法,而使为之师者考察诸州所解德行之士与诸生之贤者而特命以官,则太学之教不为虚设,而彼怀利干进之流自无所为而至矣。[5]3640-3641
在朱熹看来,久任有德之人为学官,不仅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解额不均和太学虚设的问题,而且能保证德行教育得以较好的落实。
朱熹认识到天下之理不可能通过读书而“尽通”,所谓“天下之事皆学者所当知,而其理之载于经者,则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也”,故须在学校所设课程和教学内容上进行改革,“所以必分诸经、子、史、时务之年者”,即在诸科中还要分科,并分年考试。如诸经“故今欲以《易》《书》《诗》为一科,而子年、午年试之;《周礼》《仪礼》及二戴之礼为一科,而卯年试之;《春秋》及三传为一科,而酉年试之。年份皆以省试为界,义各二道。诸经皆兼《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义各一道论则分诸子为四科,而分年以附焉。”[5]3637朱熹主张在经书学习上要分配比重。《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在三年一次的科举中是必考科目,然后以每四次科举为一个循环,其他各种经书在这个循环中依次出现。经典被分为三类:第一年和第七年的两次科举考《易》《书》《诗》;第四年考《周礼》《礼记》《仪礼》;第十年考《春秋》及其注解。诸子、史和时务也以类似的方法在四次科举中考核。下一轮考试各科会涉及的书目和主题会在殿试之后马上宣布,这样考生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内可以专心研读数量有限的一些书籍。
治经持守家法,还必须改革科举考试的形式。首先要革除考官命题“附益裁剪”“穿凿新奇”之弊。考官命题“多为新奇,以求出于举子之所不意,于所当断而反连之,于所当连而反断之”,这致使考生“平居讲习,专务裁剪经文,巧为闘飣,以求合乎主司之意”,结果是“其为经学贼中之贼,文字妖中之妖,又不止于家法之不立而已也”。其次要改革考生经义答题的形式。“盖今日经学之难不在于治经,而难于作义。大抵不问题之小大长短,而必欲分为两段,仍作两句对偶破题,又须借用他语以暗贴题中之字,必极于工巧而后已。其后多者三二千言,别无他意,不过止是反复敷衍破题两句之说而已。如此不唯不成经学,亦复不成文字。……皆当有以正之,使治经术者通古今,议论者识原本,则庶乎其学之至矣”[5]3640。
在朱熹看来,通过改革科举制度、改变学校所设科目,促使士人学习儒家经典,不仅能“直论圣贤本意与其施用之实”、解决科举考试中道德与才能之间的矛盾,并终能“教明于上,俗美于下,先王之道得以复明于世,而其遗风余韵又将有以及于方来”“进于道德之归”,而这也是朱熹孜孜以求的教育理想。
二
事实上,《私议》所倡议的科举教育改革措施明显带有针对永嘉学术的党派倾向。众所周知,12世纪中后期的科举场域是永嘉学者的天下。在科举教育场域,由永嘉学者陈傅良、叶适等人编纂的几部策文选本如《待遇集》《进卷》最为流行,考生争相学习。吏部尚书叶翥在1196年的一份奏章云:“有叶适《进卷》、陈傅良《待遇集》,士人传诵其文。每用辄效。”[6]陈傅良、叶适等永嘉学者成为当时闻名遐迩的指导举业的教师。为了聆听陈傅良的举业课程,数百名学生聚集在温州府南门附近的茶院寺。[7]而永嘉士人在科场的卓越表现带给他们在中央政府任职的机会,如陈傅良先后担任多中书舍人、起居郎等职位,叶适担任过太学正和国子司业等职位。他们常担任科举考官之职。日本学者冈元司发现1142年至1199年间二十次省试里面,仅有两次考官中没有温州人,[8]这些都体现了永嘉学术在科举场域的巨大影响力。《私议》的党派倾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朱熹强烈反对混补法
《私议》云:“反以程试文字之不工为患,而唱为混补之说,以益其弊。或者知其不可,又欲斟酌举行崇宁州县三舍之法,而使岁贡选士於太学。其说虽若贤於混补之云,然果行此,则士之求入乎州学者必众。”[5]3633显然,朱熹既反对三舍法,也反对混补法,两者相较,三舍法要优于混补法。尤其是混补法与程试文字相关联,且由永嘉学者陈傅良、叶适等人倡议。《私议》对此说道:“所以今日倡为混补之说者,多是温、福、处、婺之人,而他州不与焉。非此数州之人独多躁竞而他州之人无不廉退也,乃其势驱之,有不得不然者耳。”[5]3634所谓“温、福、处、婺之人”,除“福(州)”多指浙东学者。南宋浙东学派林立,下分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等,其学术思想或有差异,然对待科举的功利态度上却并无二致,故科举场域的“永嘉”往往不限于永嘉地区,而是涵盖了整个浙东地区。朱熹反对混补法,实则是反对“永嘉”在科举场域的影响力。
(二)朱熹对科举中治《春秋》风气的极端不满
永嘉学者向来有治《春秋》的传统,永嘉学派在科举场域的崛起与永嘉学者专精《春秋》密切相关,如陈傅良和蔡幼学在太学以专治《春秋》知名,陈傅良有《春秋后传》一书存世。叶味道(1220年进士)来自温州府,他在1191年到1200年间跟随朱熹学习。[9]叶氏告诉朱熹他计划在下次考试时以《春秋》为专经,朱熹说道:“《春秋》为仙乡陈蔡诸公(按:陈傅良和蔡幼学)穿凿得尽。诸经时文愈巧愈凿,独《春秋》为尤甚,天下大抵皆为公乡里一变矣!”[1]2761朱熹对永嘉学者因专治《春秋》而占据科举场域优势地位且引领一时学风深怀忧虑乃至不满。《私议》云:
近年以来,习俗苟偷,学无宗主,治经者不复读其经之本文与夫先儒之传注,但取近时科举中选之文,讽诵摹仿,择取经中可为题目之句,以意扭捏,妄作主张,明知不是经意,但取便于行文,不暇恤也。盖诸经皆然,而《春秋》为尤甚。主司不惟不知其缪,乃反以为工而置之高等。习以成风,转相祖述,慢侮圣言,日以益甚。名为治经,而实为经学之贼;号为作文,而实为文字之妖。不可坐视而不之正也。[5]3638
朱熹着重突出时下治《春秋》之陋习,固然体现了《春秋》在科举场域的重要地位,却也反映出朱熹对永嘉学术的不满乃至敌视态度。
(三)强调道学注疏及“四书”的经典地位,排斥永嘉学者的注疏
朱熹主张治经必守家法,而要立家法,当以注疏为主。《私议》云:
如《易》则兼取胡瑗、石介、欧阳修、王安石、邵雍、程颐、张载、吕大临、杨时,《书》则兼取刘敞、王安石、苏轼、程颐、杨时、晁说之、叶梦得、吴棫、薛季宣、吕祖谦,《诗》则兼取欧阳修、苏轼、程颐、张载、王安石、吕大临、杨时、吕祖谦,《周礼》则刘敞、王安石、杨时,《仪礼》则刘敞,《二戴礼记》则刘敞、程颐、张载、吕大临,《春秋》则啖助、赵匡、陆淳、孙明复、刘敞、程颐、胡安国,《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则又皆有集解等书,而苏轼、王雱、吴棫、胡寅等说亦可采。[5]3638-3639
朱熹所列的这份注疏书目名单,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特别强调道学注疏的重要地位。道学人士的注疏被推崇为指导经书研读的最优选择。程颐被朱熹定为道学先贤,其各种注疏被列在所有经书之下,这在各家中是唯一一位。张载、杨时等其他被朱熹列入道学谱系的人物也常出现在这份名单中。第二,这份名单明显排斥了“永嘉”诸子的注疏。“永嘉”学者特别在《春秋》和《周礼》这两部经书的教育和注疏上享有盛誉,但朱熹对此不屑一顾。《朱子语类》载:
又问:“春秋如何说?”滕云:“君举(按:陈傅良的字)云:‘世人疑左丘明好恶不与圣人同,谓其所载事多与经异,此则有说。且如晋先蔑奔,人但谓先蔑奔秦耳。此乃先蔑立嗣不定,故书‘奔’以示贬。’”曰:“是何言语!先蔑实是奔秦,如何不书‘奔’?且书‘弃秦’,谓之‘示贬’;不书奔,则此事自不见,何以为褒?昨说与吾友,所谓专于博上求之,不反于约,乃谓此耳。是乃于穿凿上益加穿凿,疑误后学。”[1]2959
永嘉看文字,文字平白处都不看,偏要去注疏小字中,寻节目以为博。[1]2964
显然,朱熹对“永嘉”诸子在经书尤其是《春秋》注疏教学方面的影响颇为不满乃至愤怒,因为他认为这些人对经典的解读方法和他希望自己学生掌握的阅读方法背道而驰。从这份名单可见,朱熹希望限制学生对“永嘉”诸子的了解,仅列出了薛季宣的一部《尚书》注。
另一方面,为争取道学在科举场域的地位,朱熹选择一套核心科目以及为每一步经书指定相应的注解。如上文所述,在科举考试的经典科目中,《易》《书》《诗》《周礼》《礼记》《仪礼》《春秋》皆依次循环出现,只有《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在每次科举中必定会出现。这套《四书》首先由朱熹在1182年结集出版,成了正在定型中的道学经典的核心内容。这套书的第一部《大学》在12世纪中叶就已经成为道学运动的基础入门作品。朱熹一直认为《大学》一书包含了道学总纲,向学生介绍了修身步骤,即把个人、家国都整合进宇宙道德秩序之内。一旦学生理解了《大学》的中心思想,他们就可以在阅读清单上别的经典时应用这种思想。对朱熹而言,《四书》为辨别其他一切作品提供了标准。除了选编经典文本和强调其在阅读时的重要性,朱熹也对经典进行注疏。在《私议》倡议的教学内容中,其为《四书》所作注疏被列为理解核心经典的唯一选择。
(四)对时文的批评
南宋以来,科举时文(论体文)渐趋程式化、标准化。四库馆臣云:“其始尚不拘成格,如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自出。未赏屑屑于头项心腹腰尾之式。南渡以来讲求渐密程式渐严。试官执定格以待人。人亦循其定格以求合。于是双关三扇之说兴,而场屋之作遂别有轨度。虽有纵横奇伟之才,亦不得而越。其破题接题小讲大讲入题原题式实后来八比之滥觞。亦足以见制举之文源流所自出焉。”[10]“头项心腹腰尾之式”指的是12世纪后半叶程式化文章的段落名字。论体文包含六个顺序固定的段落,前三个相对较短。作者首先在破题中简明介绍主要论点。在此之后,用同样长度或者稍长点的文字列出几个分论点(“接题”或“承题”)。作者也可以选择在论体文的序论部分放入一段更详细的摘要,称之为“小讲”。以上这一段必备的文字包含了“破题”“承题”及“小讲”,构成了论体文的导言(“冒子”)。文章主干“讲题”之前通常有一个“原题”,确定题目在原引书中的出处,它也代表导言的结束和主体部分的开始。在立论中,对偶成为最主要的修辞手法。这样的标准也同样适用于经义考试。考官支持这样程式化、标准化的模式,因为这有利于提高阅卷效率;大多数考生也都遵循这种模式。占据12世纪中后期科举场域优势地位的永嘉学者对此自然也提倡有加。
朱熹注意到这种标准化考试文体结构对教学有负面影响,认为坚持某种特定格式会影响学生对文本的解读。现有的传统因此产生了一种特定的阅读方法。《私议》云:
大抵不问题之小大长短,而必欲分为两段,仍作两句对偶破题,又须借用他语以暗贴题中之字,必极于工巧而后已。其后多者三二千言,别无他意,不过止是反复敷衍破题两句之说而已。如此不唯不成经学,亦复不成文字。[5]3640
朱熹认为这种考试形式完全基于修辞考量,因而主张改变考试形式、改变评估标准。《私议》接着说道:
欲更其弊,当更写卷之式,明著问目之文而疏其上下文,通约三十字以上,次列所治之说而论其意,又次旁列他说而以己意反复辩析,以求至当之归。[5]3640
朱熹提议的经义文章形式包括三部分:先指出所引文章之上下文,再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注疏传统进行讨论,最后学生讨论自己对该段文字的理解。在朱熹看来,注疏在古典教育中的角色尽管关键,但还是次要的,原始文本才最为重要。学生使用注疏的方法反映了注疏的辅助性质,而注疏需要被批判性阅读。朱熹把对文本的个人理解定义为“直论圣贤本意与其施用之实”。这种对文本的个人理解,既不是提倡对原文进行批判性解读,也不是鼓励提出新颖的观点。阅读经书的目的是亲身经历且认同这些作品的意涵。而这些皆与永嘉学者的教学格格不入,甚至截然相反。
尤其是,朱熹对永嘉学者视作文修辞技巧为教学的中心地位甚为不满。在他看来,永嘉学者着迷于对科举文章进行修辞分析,这给历史和经学研究带来严重问题:
问:“今之学校,自麻沙时文册子之外,其他未尝过而问焉。”曰:“怪它不得,上之所以教者不过如此。然上之人曾不思量,时文一件,学子自是着急,何用更要你教!你设学校,却好教他理会本分事业。”[1]2700
朱熹对时文的批评不仅涉及时文结构的标准化问题,更涉及古文尤其是苏轼的文化遗产在士人文化中的权威地位。这一权威地位的形成在朱熹看来完全拜永嘉学者所赐。在朱熹眼中,永嘉学派的中坚人物陈傅良跟苏轼是同类人:“只是他稍理会得,便自要说,又说得不着。如东坡子由见得个道理,更不成道理,又却便开心见胆,说教人理会得。”[1]2960朱熹认为古文教学不仅仅是简单的技术问题,更是对道学的一种思想挑战。古文在科举场域中取得极高名气,一个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吕祖谦的教学活动。吕祖谦通过编纂古文选本及评点,对古文风格的议论范文进行结构和修辞分析,教导学生如何写作时文,所谓时文“以古文为法”。如其《古文关键》收录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苏洵、苏辙、曾巩和张耒八家之文,教学生“看”文字,分析整篇文章在语义和风格上的组织方法。《总论看文字法》云:
学文须熟看韩、柳、欧、苏。先见文字体式,然后遍考古人用意下句处。苏文当用其意,若用其文,恐易厌人,盖近世多读故也。[11]
吕祖谦认为韩、柳、欧、苏等古文经典作家作品代表了古文范式,指出文章须注重体式、用意和下句(即行文),并从“大概、主张”“文势、规模”“纲目、关键”“警策、句法”四个方面说明“看文字法”。客观上,吕祖谦的选文及教学活动有助于12世纪晚期和13世纪古文经典的形成。但朱熹对吕氏分析古文时所用的技术性和修辞方法提出了严厉批评:
因说伯恭所批文,曰:“文章流转变化无穷,岂可限以如此?”某因曰:“陆教授谓伯恭有个文字腔子,才作文字时,便将来入个腔子做,文字气脉不长。”先生曰:“他便是眼高,见得破。”[1]3321
吕祖谦写作各种文体文章所用的“腔子”来自他对古文尤其是韩、柳、欧、苏作品的研读。他以注释和解读来教导学生如何掌握古文名家作品的组织结构和修辞技法。朱熹认为时文结构的标准化以及12世纪晚期古文的权威地位都是士人重视修辞技巧的主要原因,是对道学及其教育的严重威胁。这其中,永嘉学者难辞其咎。
三
宋廷治国以儒家教化为本,表现得最彻底的就是对教育的重视实施及对科举考试的整顿。宋人清楚地认为,科举制之能实行,主要靠它的公正性。夏竦的说法颇具代表性:
伏以隋设进士之科,唐代特隆,其岁选登榜帖不过三十,贤俊之器、将相之具在其中,谅不虚语。然主司慎选,弊于回挠。豪右角逐之衢、是非锋起之场,进孤寒则道直而有愧,私权贵则道枉而无咎。[12]
就夏竦而言,唐代科举制度在实行时,不免常有私于权贵的现象,但由于它能给寒畯之士提供社会升迁的机会,因而应将它视为可以弥补社会之不公正和不公平的一种制度。夏竦的这一信念和宋人关于考试的看法基本一致。宋人相信科举考试的基本功能是选官,但儒家学说的最高信念是要以德行表现作为选举的唯一标准。一般说来,宋人大都相信科举制度必须兼顾选举的道德意义,但他们中不少人认为如此制度对实现选举的道德理想无能为力。在南宋,关于考试的道德目标以及教育如何同考试相关联的看法,通常倾向于认为只有教育才有希望为政府培养德行卓然的行政官员,而科举制度不可能真正实行以德行取士的理想,大多数人也放弃了那种考试能衡量一个考生道德水平和学术成就的简单信仰。叶梦得曾说道:“读书而不应举而已矣,读书而应举,应举而望登科,登科而仕,仕而以叙进,苟不违道与义皆不可。”[13]
朱熹提倡孔子的“为己之学”,明确批评科举取士,对科举制度的真正本质提出了质疑,并考察了它所存在的问题根源。《私议》为此提出改革,通过“均诸州之解额”的公平公正“以定其志”,同时立德行科以突显科举考试的道德意涵,以此达成教育理想。《私议》概括了当时科举制真正的和重要的基本问题,准确揭示了宋代士大夫在面对所谓“公正”考试问题上所遇到的主要困惑:保证了考试的公正性,就必须付出放弃以德行取士的儒家理想的代价。朱熹心里应该很明白,科举场域以德行取士只是一种美好而无法实现的愿景。朱熹自己也承认,上文提出的科举改革措施只是“如曰未暇”的下下之策,真正要达成所愿,“则必如明道先生熙宁之议,然后可以大正其本而尽革其末流之弊”。“明道先生熙宁之议”,即程颐《请修学校尊师儒取士劄子》。在朱熹看来,取士的公正性兼德行考察的实现只有在学校教育下才有可能达成。
借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科举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社会结构,政府、考官以及各样读书人都是主观上形塑这个科举场域的参与者。李弘祺先生认为,科举制是影响中国思想及文化最大的力量,宋代以后中国学术史很难说不是政府、考官与士人在科举场域争取主导权的发展史。[14]189-190换言之,科举是创立、传播和改变学术思想的重要场域。面对永嘉学术在12世纪中后期在科举场域咄咄逼人的声音,朱熹自然希望道学思想在科举场域能占有一席之地,《私议》极力倡议立德行科、确立《四书》及其注疏的经典地位、强调科举考试的道德意义,无疑是意欲其道学思想在科举场域获得发展的一次努力尝试。然而,北宋经学在科举场域的发展史表明,光是在科举场域里图谋发展一家学术是相当困难的。正如李弘祺先生所云:“科举考试在促成学风变革上,可能在王安石变法之后,变得不是那么明显。而同时,在科场上面相对缺乏影响力的北宋五子的道学思想只能通过其他途径发展他们的空间。”[14]198《私议》既然称为“私议”,表明它实际上只是朱熹与朋友之间的私下讨论与流传,在当时士人文化中并不算流行,然而,他将死时,其学术思想已经广为传播,这表明当时流传的科举时文并不能真的对学术产生完全支配性的作用。因而,学术思想的发展除了科举场域,应该还有另外一个场域——教育场域,《私议》标题事实上对此已有明确暗示。也就是说,对朱熹而言,无论是对于“德行道艺”“进于道德之归”教育理想的达成,还是道学思想的发展,学校教育场域可能比科举场域更值得信赖。
注释:
①本文所引《学校贡举私议》俱出自《朱熹集》(朱熹著,郭齐、尹波点校,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版)。
②较为著名的宋代教育史(包括书院史)著述如袁征《宋代教育——中国古代教育的历史性转折》(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李弘祺《宋代官学教育与科举》(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3年版);李兵《书院与科举关系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及苗春德、赵国权《南宋教育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皆有涉及,然多作征引文献之用,并未对文本本身的意涵有所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