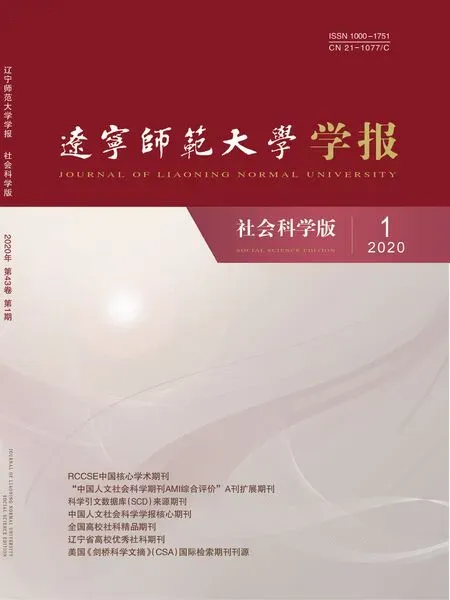遗山词研究40年
于东新, 姚立帅
(内蒙古民族大学 文学院,内蒙古 通辽 028043)
在中国文学史上,元好问(1190—1257),是备受关注的大家,是金元文坛的一代巨公,在各方面都有不凡的建树。在词文学上,其有词集《遗山乐府》传世,收词378首,不仅在数量上是金源词坛第一人,而且其艺术水平也可代表金词最高成就,即如清人陈廷焯《词坛丛话》所说:“元遗山词,为金人之冠。疏中有密,极风骚之趣,穷高迈之致,自不在玉田下。”(1)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全编:词坛丛话[M].北京:中华书局,2013:8.刘熙载也评判道:“金元遗山诗兼杜、韩、苏、黄之胜,俨有集大成者之意。以词而论,疏快之中,自饶深婉,亦可谓集两宋之大成者矣。”(2)刘熙载.艺概:卷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13.足见元好问在金词乃至整个词史上的重要地位。所以学界对遗山词多有关注和研究,尽管赶不上元氏文学理论、诗歌等方面的研究规模,但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对于金元明清时代包括遗山词在内的元好问研究情况的梳理,最为翔实的成果要数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张静的《元好问诗歌接受史》。该书对元好问在近700年间被接受、传播的历史过程做了系统的梳理,总结了元氏被文学史、文化史、词学史接受的情形,并探究了其深层的政治文化等原因,材料丰富,所论翔实,可参看。
迨20世纪前半期,由于受战乱等时局因素的影响,包括遗山词在内的元好问研究是比较萧条的。值得关注的成果,主要有况周颐《蕙风词话》与吴梅《词学通论》。作为晚清最重要的词家之一,况周颐(1859—1926)于1924年出版了《蕙风词话》《惜阴堂丛书》本,是书凡五卷,计325则。卷一论词之作法,卷二以下则以品评、纪事为主,其中卷二以宋词人居多,卷三以金、元词人为主,在讨论遗山词时,况氏结合元好问生平遭际与个性,认为:“遗山以丝竹中年,遭遇国变。崔立采望,勒授要职,非其意指。卒以抗节不仕,憔悴南冠二十余稔。神州陆沉之痛,铜驼荆棘之伤,往往寄托于词。《鹧鸪天》三十七阕,泰半晚年手笔。其赋隆德故宫及宫体八首、薄命妾辞诸作,蕃艳其外,醇之其内,极往复低回,掩抑零乱之致。而其苦衷之万不得已,大都流露于不自知。此等词宋名家如辛稼轩固尝有之,而犹不能若是其多也。”(3)况周颐.蕙风词话辑注:卷3[M].屈兴国,辑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131.进而指出,遗山词的特点“亦浑雅,亦博大,有骨干,有气象。”对遗山词做了较为系统的评判。1933年,吴梅(1884—1939)的《词学通论》《国学小丛书》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是书第8章集中讨论金词,共评述了16位金代词家,最后一位是元好问,其以元氏名作《迈坡塘·雁邱》为例推许遗山词的成绩:“余谓遗山竟是东坡后身,其高处酷似之,非稼轩所可及也。”并肯定金末覆亡之际元好问为保存金代文献上所体现出的文化担当,以为遗山词“多故国之思”,是词家心志的表现,并举例说:遗山《木兰花》“冰井犹残石甃,露盘已失金茎”;《石州慢》“生平王璨,而今憔悴登楼,江山信美非无土”;《鹧鸪天》“三山宫阙空银海,万里风埃暗绮罗”,又云:“旧时逆旅黄粱饭,今日田家白板扉。”又云“墓头不要征西字,元是中原一布衣”等,故曰:“可见其襟抱也。”(4)吴梅.词学通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95.总的来说,20世纪前半期遗山词研究是冷清的,缺乏现代的学术视野,还未在理论层面展开研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但由于受极左政治的影响,一直到1978年之前,30年间遗山词研究并未产生什么值得言说的成果,乏善可陈。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国家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思想禁锢渐次解除,学术的春天终于到来。在1978至2018年的40年间,遗山词研究呈现出繁荣的局面,获得了重要的发展,产生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具体以21世纪前后为界,分成前后两期予以观照。
一、1978—1999年的遗山词研究
最早探究遗山词的,是有“当代李清照”之称的著名词家沈祖棻,其有《读遗山乐府》(5)沈祖棻.词学研究论文集:读遗山乐府[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是文揭开了新时期遗山词研究的序幕。此期研究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赵兴勤王广超《元好问词艺术初探》(6)赵兴勤,王广超.元好问词艺术初探[J].徐州师院学报,1983(1):71-76.、金启华《金词论纲》、赵慧文《元遗山词概论》、赵兴勤《论元好问词创作的三个阶段》、张晶《论遗山词》、陈长义《遗山词辨微》、陈刚《遗山词简论》,以及王兆鹏、刘尊明《风云豪气,慷慨高歌——简说金词》等。上述成果往往侧重于遗山词的整体考察,比如关于遗山词的题材,金启华提出:“他的词,题材极为广阔,有登临抒怀、赠别感时、咏物寄兴、怀古伤今之作,长调小令无不精工。”(7)金启华.词学:第4辑[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32.赵慧文则将元氏词按题材分为咏怀词、言情词、咏物词、山水词、农村词,以及寄赠词等类别,并以此类别归纳了遗山词的风格特征,认为其咏怀词多与驰骋疆场、雪耻杀敌、国运危殆相关;其言情词表达了词家忠贞不渝的爱情观,真挚深沉,有时他还以爱情来隐喻家国身世之感怀;其咏物词曲笔抒怀,托物言志;山水词多状写北国雄伟壮丽的风物,从中可窥见词人崇高的主体精神;农村词既写恬静优美的农村风光,也表现农家之苦,反映了阶级压迫下民生之艰;此外,寄赠词则寄赠激励友人、抒写内心抱负。最后作者指出:“元词反映了金末广阔的社会生活,内容之丰富、深刻,词境之扩大,不愧为金词之冠。”(8)赵慧文.元遗山词概论[J].晋阳学刊,1990(5):69-76.关于遗山词题材内容的研究还有赵永源的《沉挚苍凉的时代悲歌——试论元好问金亡前后的词》(9)赵永源.沉挚苍凉的时代悲歌——试论元好问金亡前后的词[J].镇江师专学报,1991(2):29-33.等。
关于遗山词的创作分期,赵兴勤文认为,遗山词创作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泰和五年(1205)至元光二年(1223),这时期的词人,正值青春焕发之际,对国家振兴充满乐观信心,坚信收复失地指日可待,作品以劲词壮语,吐豪情壮志抒磊落情怀,有雄健浑朴之气,风格豪健、疏快。词人有时也言愁。此时之“愁”,大致有两方面的内容,即功名无成的感慨与盼望恢复的忧叹。正大元年(1224)至正大八年(1231)“赴召史馆”之后为遗山词的第二阶段,随着生活阅历的日趋丰富,其目光由山川风物,则逐渐转向较为广阔的社会生活。在词作题材的开掘上,也日见深广。多写广阔的社会生活,以旷达之言来掩饰其悲慨之怀。词中狂欢与深痛、旷达与幽愤、豪迈与辛酸相互交织,显出词人对国家、对人生充沛而丰富的情感。三是天兴元年(1232)至蒙古宪宗七年(1257),“癸巳之变”以后,国家倾覆,词人由金朝官吏沦落为蒙古统治者的阶下囚。作为一个生活在蒙古贵族铁骑之下的金朝旧臣,元好问不便直接吐露怀念故国之情,因而,往往借游赏山川、凭吊古迹来隐约传示。这便构成了他后期词作意旨深隐、蕴藉含蓄的艺术特征。其后期词作,格调更为悲凉、凄婉,含意也更加厚重幽邃。他的感时伤世之情,黍离麦秀之悲,坎坷遭际之叹,往往交并而出,以长歌代哭。黍离麦秀之感、坎坷遭际之叹,成为遗山此期创作的主题(10)赵兴勤.论元好问词创作的三个阶段[J].徐州师院学报,1991(3):54-58.。所论无疑是全面而深入的。
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张晶教授的《论遗山词》,站在词学史的高度,对遗山词进行了深入讨论。论文首先认可元遗山为“金代词人之冠”的观点,并胪列了理由:“元好问是金代词坛上最为高产的词人。从数量上看,遗山词便足以蔚为‘大国’。遗山词的题材非常广阔,有登临抒怀、赠别感时、咏物寄兴、怀古伤今之作,长调、小令都佳作迭出,词的风格多样丰富,或雄浑豪壮,或沉郁顿挫,或深婉缠绵。”故“遗山词代表了金词的最高成就,是金代词坛第一作手,同时,遗山词也为词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其次,论文拈出“‘亦浑雅、亦博大’的遗山壮词”(11)张晶.论遗山词[J].文学遗产,1996(3):73.,强调这是遗山词的主体类型,予以深入观照。指出“遗山壮词”“并非仅指词的豪放雄壮风格,而是指词人更多地继承了两宋以来以苏、辛为代表的豪放词传统的历史感与以崇高为主要审美因素的美学风貌。”尤其是作于晚期的遗山词,“将深沉浩茫的故国情思、黍离之悲,沉积于审美时空的品悟之中,……不再悲愤填膺,不再仰天长叹,而是将对历史兴亡的冷峻透视,沉积在时间的沧桑迁逝、空间的广远无涯上,这便是遗山壮词”。再次,论文还看到了遗山词风格的多样性,所谓“柔婉之至而又沉雄之至”,“遗山词中有些篇什从题材到手法都近于婉约家数,抒写词人细腻感受,写得柔婉幽峭”。如《迈陂塘·双莲》和同调的《雁丘词》,即为明证。最后张文还讨论了“遗山词在词史上的地位”,提出:“遗山词虽然承绪苏、辛豪放词的艺术传统,却自有其艺术个性,未可与苏、辛混一而论。遗山词一方面以豪健英杰之气充溢词中;另一方面,则十分讲究词的艺术表现。与辛词相较,遗山词更近于‘雅词’一路。”总的来看,“他在以豪气为词的同时,又以婉约笔法、浑雅风格使豪放词在经历了稼轩词之后再度与雅词合流。呈现出一种独特的风貌。这在词的发展史上有重要的意义。”(12)张晶.论遗山词[J].文学遗产,1996(3):74-77.(张教授相类的论述还有《漫说遗山词》(13)张晶.漫说遗山词[J].古典文学知识,1999(1):5-11.)与张文观点相近的,还有王兆鹏、刘尊明《风云豪气,慷慨高歌——简说金词》,其采用与两宋词相对比的方法来观照遗山词,认为遗山的山水词“展现了北方雄奇峻美的山川,是元好问在词中自然山水空间方面的拓展”,它有别于两宋词多描写南方山水,而很少涉及北方的高山大川;元氏爱情词也“不同于两宋爱情词的柔肠软泪、苦恋悲思,而独辟出另一种境界,即歌唱赞美那种感天动地、生死不渝、轰轰烈烈的忠贞爱情,他笔下那种不惜生命、海枯石烂情不改的爱情和柔情中带骨气的审美境界,是唐五代两宋词史上罕见的境界”。最后提出:“元好问是辛弃疾之后对词境开拓最多的词人。”(14)王兆鹏,刘尊明.风云豪气,慷慨高歌——简说金词[J].古典文学知识,1997(5):74-79.差不多与上述二文同时,陈刚的《遗山词简论》也提出,在内容上,“遗山词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真实地抒写了词人的人生之旅、动荡的时代、人民的悲欢苦乐”。在艺术上,“刚柔相济,豪婉兼备;疏密相间,离合有致;师法杜甫,兼得神韵,在13世纪的中国文坛别开生面。”(15)陈刚.遗山词简论[J].固原师专学报,1996(4):18-21.以上是整体研究的成果,是为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学界还有遗山词的分类研究,也有不小的成绩。
首先是遗山咏物词研究。元好问有咏物词24首,他也是词文学史上咏物词的名家。台湾辅仁大学教授包根弟作《元好问“咏物词”初探》长文,分上、下两篇,先后刊发于《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这是全面讨论遗山咏物词的专门文章。上篇从题材、内容、修辞等方面来讨论,即以题材观之,元好问咏物词之题材,大多为植物中花木一类,其所咏之花有梅、牡丹、莲、杳花、海棠、酴醾、芍药、樱桃、木犀、瑞香、玉簪、宜男等12种,共计22首。咏木者,则仅“烟中树”一首,咏物者仅《摸鱼儿·咏双雁》一首;以内容观之,遗山咏物词可分为纯咏物象以及咏物寄兴两大类;以修辞技巧而论,遗山咏物词绘形体物,使用了摹写、比喻、用典、类叠、拟人等修辞手法,论文还对这五种修辞进行了较深入的讨论分析(16)包根弟.元好问“咏物词”初探:上[J].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91(3):19-25.。论文下篇,从风格、思想、情感等三方面来探究遗山咏物词的艺术特色。认为,婉丽清雅,幽深蕴藉是遗山词之重要风格,遗山咏物词皆属此类风格。如“摸鱼儿”雁丘辞及双蕖怨二首,即为婉约风格之名作。在思想情感方面,遗山咏物词所表现之思想情感有:一是高雅之情趣,“其赏花之际,乃特重花高雅之格调”。二是感叹光阴飞逝,“身处金元易代之际的遗山,面对易落的花朵,(光阴易逝的)这种感触尤其深刻”。三是哀伤家国乱离。这种感情“亦寄寓咏莲咏梅、咏烟中树之作中”。四是颂扬真情真爱。此方面例证就是遗山词的代表作咏雁、咏双莲的《双蕖怨》和《雁丘词》(17)包根弟.元好问“咏物词”初探:下[J].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91(4):72-76.。
其次,关于遗山闺情词,学界也多有关注。刘怀荣《苏东坡、元遗山言情词比较论》(18)刘怀荣,苏东坡.元遗山言情词比较论[J].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91(3):83-88.、张进《论元遗山的闺情词》,以及赵永源《论元遗山言情词的创作因素》等都是此类成果。比如张进提出“遗山闺情词正是在抒情要雅正、用笔要和婉这两点上做到了较完美和谐的统一,因而尤符合言情词的审美特征。”并由此断曰:闺情词“代表了他的词的最高成就。”(19)张进论.元遗山的闺情词[J].唐都学刊,1995(1):51.显然,赵文从金元时期的词创作语境、元氏的个人经历以及元氏词学观念等方面,讨论遗山言情词的艺术特点,肯定了遗山此类词的成就(20)赵永源.论元遗山言情词的创作因素[J].中国韵文学刊,1999(1):40-45.。
再次,还有关于遗山词的代表作的分析研究。这种文本细读的研究,也能见出遗山词的艺术特色。比如对《水调歌头·赋三门津》的解读,重要的论文有如刘泽《骑鲸挝鼓过银山——读元好问〈水调歌头·赋三门津〉》(21)刘泽.骑鲸挝鼓过银山——读元好问《水调歌头·赋三门津》[J].名作欣赏,1990(3):108-110.,王兆鹏、刘尊明《神通之笔绘神奇之景——元好问〈水调歌头·赋三门津〉赏析》等。像后者就分析说:“元好问挟幽并豪侠之气,遨游于西北名山大川之中,用飞动的词笔,描绘出黄河三门峡的奇观。”词的开篇,便有尺幅千里之势。黄河仿佛从九天奔腾而下,一泻千里。其力度和气势堪与李白的名句“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相互辉映。“元好问此词则为中国词史增添了一道新颖奇特的风景线”,“就描写对象而言,在唐宋金元词史上,元好问此词是第一次发现并描绘三门峡奇观的词作;从词的情感基调来看,词人是豪气勃发,词中洋溢着乐观进取的豪迈气概,境界雄壮宏阔,意象雄奇飞动,绝无唐宋词中常见的那种忧患感伤的色彩”(22)王兆鹏,刘尊明.神通之笔绘神奇之景——元好问《水调歌头·赋三门津》赏析[J].古典文学知识,1998(2):36-38.。可见,论文高度肯定了元氏这首名词的艺术成就。
但此期也有不同的声音,在学界几乎一边倒地称誉遗山词的语境下,陈长义的《遗山词辨微》则显得不流时俗。其首先提出前人关于遗山词的评价中,有两人的观点值得重视:一是宋元之际的张炎。张炎在《词源》中说“元遗山极称稼轩词。及观遗山词,深于用事,精于炼句,有风流蕴藉处,不减周秦。”即张氏认为“遗山所追慕的方向与他取得的成功是相反的。同时将遗山词坛上的地位降到了与周秦同等。”二是清代的陈霆焯。陈氏《白雨斋词话》在肯定遗山词长处的同时,也道出了遗山词“刻意争奇求胜,亦有可观。然纵横超逸,既不能为苏、辛;骚雅清虚,复不能为姜、史,于此道可谓别调,非正声也”的不足,由此,论文认为:“应对遗山词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不能抑扬过当。”(23)陈长义.遗山词辨微[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1996(2):43.为此该文做了三方面的“辨析”,其一,备受人们称赞的遗山名词《迈陂塘·双莲》和同调的《雁丘词》并非完美无瑕,“都赞誉过甚”。具体的,《雁丘词》下片借用典故来深化感情,“但这些典故的内涵与作者所咏的事实并不十分贴切,而且这些典故一用,就将上片的直接抒情一下隔断了,对全词的情感意脉起了梗阻和分散作用。”(24)陈长义.遗山词辨微[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1996(2):44.《双莲词》也有同样的缺点。同时,“词人描述立场和角度的转移,影响了它们的艺术感染力”,作品的最后词人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向读者表达自己的看法,“俱是败笔”,提出:“从艺术创造的角度来审视,这两首词的雷同之处太明显。”(25)陈长义.遗山词辨微[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1996(2):45.再有,文章还分析了遗山《江城子》之“草堂潇洒淅江头”与“醉来长袖舞鸡鸣”,认为这才是遗山文质俱佳的上乘之作。其二,“古今一些论者还一直称道遗山的写景咏物词”,“但我以为遗山的写景咏物词达到上乘者不多,总体成就不算高。”(26)陈长义.遗山词辨微[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1996(2):46.比如《水调歌头·赋三门津》,与苏轼“大江东去”相比,“仍逊一筹”。至于《水调歌头·少室玉华谷月夕》,亦“称道过实”,它至少存在两处不足。再有就是遗山咏物词,有的是为咏物而咏物,“没有寄寓作者的情感,没有显出所咏之物的内在品格,发掘出它的美学内涵。”(27)陈长义.遗山词辨微[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1996(2):47.认为其中上乘的当属《鹧鸪天·莲》。其三,遗山词语言有些地方“刻意争奇不值得肯定”,例如《折丹桂》全词嵌入12个“秋”字,“似乎落入了文字游戏的恶道”(28)陈长义.遗山词辨微[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1996(2):48.。——这种不囿时见,有自己独立思考的研究还是值得关注的,这也说明此期遗山词研究的开放性。
此期,港、台学者的遗山词研究,也颇值得注意。重要的有钟屏兰《元好问评传》、张子良《金词研究》,以及黄兆汉《金元词史》等著作。钟著虽是元氏评传,但其专列一节讨论遗山词,它以“内涵境界的沉郁深广”“艺术技巧的浑成自然”“各种风格的兼具并存”等三方面来展开。提出“内涵境界的沉郁深广”有五方面的内涵:“情与世违的挫折寂寞”;“田园村居的闲适旷达”;“登临怀古的豪情悲慨”;“血泪交迸的身世伤叹”;“眷怀故国的沉痛苍凉”。而“艺术技巧的浑成自然”则主要包括“情景的交融”“托喻的手法”等表现形式。“各种风格的兼具并存”主要有四种风格:“奇绝排奡,浑雅博大”;“疏放自得,超旷俊逸”;“怨抑激楚,沉郁苍凉”;“清新浏亮,缠绵怨曲”等。并认为“遗山词映现金源一代风貌”“导元词发展之路”,在词史上具有重要影响(29)钟屏兰.元好问评传[M].台北:台湾文津出版社,1999:239-249.。钟氏曾在1991年完成了硕士论文《〈遗山乐府〉析论》,术业有专攻,故《评传》实为学位论文的精华。张子良的《金元词述评》出版的时间较早,其有感于“金元词自有独特精神气息在”,于是“汇集资料,考述事迹,列论存篇,撰成专文”。在体制上,全书“分列三章,首章绪言,乃就词之渊源、两宋以前传衍大势、金元词存篇之集录概况,作一简括说明,以为下文评述张本。二章述金词,三章述元词,略依时代先后为序。”(30)张子良.金元词述评[M].台北:台湾华正书局,1980:1-2.张氏评述金代词家凡49人,第二章第四节以《中州词宗元好问》为题评述遗山词,其以“先述词人事略,次举词,次论评”为序,首先称曰:(遗山)“词则踵武苏、辛,清雄掩抑之至。就金元词风论之,上承吴、蔡,下启藏春,实北方词派之巨擘。”其举《水调歌头·赋三门津》评曰:“此词奇伟壮阔,磊砟英多,纯然出自中州少年豪俊之口,其奇崛豪宕之势,似有过于坡公者。”(31)张子良.金元词述评[M].台北:台湾华正书局,1980:106.与之相类的词还有《水调歌头·汜水故城远眺》,“此词雄浑博大,有骨干,有气象,盖得北国风土之厚,下笔但觉威势逼人”(32)张子良.金元词述评[M].台北:台湾华正书局,1980:107.。张氏还以《雁丘词》《双蕖怨》来评析遗山至情之词。同时,以举例的方式来梳理遗山词的内容,或愤慨国事,有归林之思;或神州陆沉之痛,或铜驼荆棘之伤,或鼎镬余生之悲。丰富多样。最后作者评曰:“或谓遗山旷逸不逮坡公,然遗山以世家子而遇国变,鼎镬余生,栖迟零落者20余载,其视坡公生处盛世,虽偶为逐放之人,而终见天日者,焉可相提并论耶?生逢末运,遽遭亡国,若遗山者,不为长歌当哭,发为凄怆哀苦之音,已属强者,又安忍于旷,缘何而逸哉!故知人论世,谓其集两宋之大成,容或未逮,若以比东坡、稼轩鼎足而三,为金元词坛宗主者,舍遗山而外,孰能当之?”(33)张子良.金元词述评[M].台北:台湾华正书局,1980:112.其论知人论世,设身处地,颇为中肯。稍后面世的黄兆汉《金元词史》是一部全面探究金元词的专门史,该书分为四编,第一编总论,第二编金词,第三编元词,第四编道释、妇女外国华化词人。在第二编《金词》之第四章《金末六大词人》里,它集中讨论了赵秉文、完颜璹、李俊民、元好问、段克己、段成己等6位金末词家,在元好问部分,较细致地讨论遗山词多样化风格,认为“遗山一方面有东坡、稼轩风格的作品,同时亦有秦、晁、贺、晏风格的作品。”并且在一首词里“刚柔相济,达到‘刚健含婀娜’的境界”(34)黄兆汉.金元词史[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3:121-122.,比如《鹧鸪天》(玉立芙蓉镜里看)。此外他还有飘逸之作(如《人月圆·卜居外家东园》),也有质朴之词(如《清平乐·嘲儿子阿宁》),可谓体制完备。黄氏还归纳了遗山词的内容,即故国之思、饮酒酬唱、送别寄赠、爱情咏叹、写景状物,以及“效体”之作,等等,内容可谓丰富多彩。作者最后指出:“遗山的成功之处在乎把‘纵横超逸’或‘骚雅清虚’一炉共冶,形成一种‘刚健含婀娜’的崭新面目,而并不是单纯地追求‘纵横超逸’或‘骚雅清虚’。”(35)黄兆汉.金元词史[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3:129.所论是切合遗山词实际的。
总之,新时期的20年间,学界关于遗山词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既有整体观照,也有分类考察;既有以文学本位的视角,宏观梳理遗山词的词学史价值,也有从具体文本出发,微观探究遗山词的情采特点。与此同时,亦有不同的思考,深入遗山词的肌理深处,提出遗山词存在的不足,见出研究的细致深化。但此期研究,总的来看,还是一种囿于文学史、文学本位的研究,视野有待拓展,方法有待创新,并且,尚未关注到元好问的民族身份、遗山词的地域特色等,这些多元、多维、多视角的研究,只能寄希望于新世纪的到来。
二、2000—2018年遗山词研究
进入新世纪,随着文化语境的开放与多元,新理论、新思维的不断引入,以及信息化技术的巨大冲击,遗山词研究呈现出许多可喜的变化,宏观视野与微观考察、现象描述与价值判断、内部探究与外部观照、文本细读与新批评理论的流行等等,使得研究的学术性与研究主体的个性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重要的成果有赵维江《论金元北宗词学的理论建构》(36)赵维江.论金元北宗词学的理论建构[J].文艺理论研究,2010(4):116-122.《论元好问以传奇为词现象》《效体·辨体·破体——论元好问的词体革新》、刘扬忠《元好问对辛弃疾其人其词的接受和学习》、胡传志《稼轩词的北归及其走向——兼论元好问在其中的作用》,以及周秀荣《论金词与宋词间的关系》(37)周秀荣.论金词与宋词间的关系[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2(4):39-43.,等等。
其中,赵维江教授对金词研究用力颇多,贡献也最突出。其与夏令伟合写的《论元好问以传奇为词现象》,提出了元好问创立了词之“传奇体”的新见,认为元好问在东坡“以诗为词”和稼轩“以文为词”的道路上继续开拓,其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以传奇为词,在词里不避险怪,述奇事、记奇人、写奇景,即创立一种“传奇体”。该文并未满足一种现象的描述,它重点讨论“传奇体”产生的原因:“当是唐宋以来词体形式及其观念不断演化的结果。”具体就是词序篇幅及功能的进一步扩展,遗山词中传奇故事的主要载体是词序,而“转踏、鼓子词等民间通俗文艺的说唱形式,稼轩以文为词的创作范式,为传奇体词的创作提供了可操作的平台和取材、结构、语言等方面的启发与借鉴。”并且,遗山以传奇为词的写法是有着文化背景与土壤的原因:“仙道思想及好奇尚异的审美观,小说的志怪传奇传统及诗歌的好奇风尚,以词存史的词学观念。”(38)赵维江,夏令伟.论元好问以传奇为词现象[J].文学遗产,2011(2):91.对于“传奇体”的形成都有着程度不同的影响。而《效体·辨体·破体——论元好问的词体革新》则从词体为本位,探究遗山词的贡献:首先,元氏通过“效体”,比如“效花间体”“效东坡体”“效俳体”“效闲闲公体”等方式,从前代各种不同的词体形式中汲取营养,使其词具备“集两宋之大成”的品格。其次,元氏“以明确的‘辨体’意识和实践,为苏、辛体‘正名’,其雄浑沉厚的词风秉承苏、辛而别具风貌”,词体中的北方/中州文化的因子得以强化和壮大,所谓“宗苏辛以自树”。再次,元氏“沿着辛弃疾‘以文为词’的道路继续开拓,‘破体’为词”,即将传奇故事和传奇笔法引入词中,为词体注入了新的活力(39)赵维江.效体·辨体·破体——论元好问的词体革新[J].文艺研究,2012(1):57-62.。上述这些讨论视野开阔,即有传统文学的思维,更有文学地理学、民族学的视角,看到了元氏作为北方/中州词家的地域特点和民族身份,因而夺人眼目。
关于遗山词及金词的渊源,学界多有讨论。其中有名的学者是刘扬忠和胡传志等。刘扬忠先生虽然关于元好问的成果不多,但他的思考是有见地的,比如《元好问对辛弃疾其人其词的接受和学习》,立足于华夏文化大的格局来谈元氏是如何学习、接受辛弃疾的。首先他认为元好问是认同辛弃疾其人的,因为“二人有共同的文化基质和相近的政治理想,他们都认同华夏文化,都反对民族分裂,赞同国家重新统一”,这是元氏学习辛词的思想基础。其次,表现在词学上,“元辛二人有共同的词学基础与艺术追求”,二人都学东坡词风,都崇尚北方豪雄之风,加之有相似的人生际遇和时代背景,所以元好问认同辛词。再次,元好问主张词学要“有阳刚之气和英雄之志”,这种词学理念使得他的词无论是题材内容,还是风格情调,抑或遣词用语和意象的使用,都效仿辛词(40)刘扬忠.元好问对辛弃疾其人其词的接受和学习[J].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12(3):1-3.。胡传志教授的《稼轩词的北归及其走向——兼论元好问在其中的作用》也是此方面的重要成果,尽管该文关注的重点是辛弃疾,它梳理了稼轩词北传的过程,但在这个过程中,元好问的认同作用是不能忽视的。论文指出,辛弃疾壮岁满怀理想,由济南率众南下,投奔南宋,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家乡,但他的词作还是回到了北方故乡。“稼轩在世期间,南北双方交往不断,当时稼轩词就可能通过私下途径(人员携带、榷场交易等)传入北方。”金代后期,部分稼轩词作,被元好问推举为北方词坛的新高标。元氏对稼轩词的接受是有选择的,身为金朝臣民,他不可能接受稼轩抗金救国的政治倾向,但可以继承其爱国精神和昂扬斗志。“元好问侧重继承的是稼轩以诗为词、借词流连光景、感慨时事等取向,并未继承和看重稼轩的豪放词风以及抗金倾向。”(41)胡传志.稼轩词的北归及其走向——兼论元好问在其中的作用[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7(5):5.
此外,关于遗山与稼轩的渊源承继,刘玉华的学位论文《论宋金背景之下的元好问词与辛弃疾词》与李姣的学位论文《论元好问容受稼轩词的特征》也是此方面的成果。前者将元、辛两家词置于宋金文化背景之下进行考查,重点讨论了元好问对稼轩词的继承和元词出现的新变(42)刘玉华.论宋金背景之下的元好问词与辛弃疾词[D].太原:山西大学,2012.。尤其是后者,别有意味,其打破了朝代和民族的界限,从文学接受的角度来讨论元好问对稼轩词的容受问题。论文从“元好问对稼轩词的接受早在金亡之前”(43)李姣.论元好问容受稼轩词的特征[D].长春:吉林大学,2012.“‘东坡以来便到稼轩’的词史体派论”(44)李姣.论元好问容受稼轩词的特征[D].长春:吉林大学,2012.以及“元好问基于‘文化中国意识’对容受稼轩词的‘前理解’”等方面,梳理了元好问接受稼轩词的情况,尤其提出元好问“对稼轩词的接受不存在古代版‘民族意识’与‘爱国主义’的‘前理解’”(45)李姣.论元好问容受稼轩词的特征[D].长春:吉林大学,2012.,这种观点是切合实际的。论文还用较大篇幅探讨了元好问容受稼轩词的历史背景,说明为什么金代“夷夏之辨”会“消解”而不构成金人接受之“前理解”。论文的核心观点是:“真正促使金代以正统王朝的姿态跻身于中国历史序列,获取政权合法性地位的,归功于其对中原核心文化区的成功改造,并在这种改造中发展了其正统观念,从而在理论层面上消解了传统的夷夏之大防。”(46)李姣.论元好问容受稼轩词的特征[D].长春:吉林大学,2012.上述都是圆融宏通的见解。再有,周秀荣的《论金词与宋词间的关系》,讨论的是包括遗山词在内的金词渊源,辨析了金词与宋词间存在—种既相通又相异的关系。提出:金词主要学习的是宋词主流以外的即苏轼所开创的抒写主体性情、雄迈刚健的豪放词风,同时也接受了—定的婉约词风的影响。而辛弃疾的南渡,又在金词与宋词间架起了一道相沟通的桥梁。这种将元好问置于宋金词影响、发展的视野下的观照,角度虽正,倒也言之成理。关于遗山词对苏词承继的研究,由于是个老问题,新见不多。
关于遗山词的渊源,黄春梅的《遗山乐府与宋词关系研究》也做了较全面的探究。其认为元好问词“从词学观念、创作艺术和风格影响等方面系统地继承和发扬了两宋词的传统。”“他在词创作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不是对宋词某一家、某一派的学习,而是他能在学习苏、辛之外还善于容纳其他宋代词人的格调,并能熔铸成自己所特有的词品、词格。以吟咏性情为主,注重词的固有特质的词学主张,体制兼备的圆通的创作态度。”(47)黄春梅.遗山乐府与宋词关系研究[D].广州:暨南大学,2008.论文的结论是:“‘深于用事,精于炼句’的创作手法,融豪放与婉约于一体的艺术风格,在宋词基础之上的继承和创新,使元好问成为集金词之大成的大家。”
至于胡梅仙《论元遗山词对大定、明昌词的继承和创新》、于新《浅析元好问的词》、黄春梅《论元好问词炼句的技巧》,以及毕宇甜的《金元之际词的新变——以元好问、白朴为中心的考察》等论文,探究的重点是遗山词具体的艺术机制。胡文提出:“遗山词是在既有金词的土壤上多方承继和创新的丰硕成果,其不仅与金的特定时代、地理环境有关,更与金文化中传统主流思潮儒家文化的失重及多元文化空间的形成有关;而金中期词表现出的旷逸、恬淡、清新、朴质的多重风格无疑是遗山词最直接的丰厚土壤。”(48)胡梅仙.论元遗山词对大定、明昌词的继承和创新[J].阴山学刊,2005(2):22.因此,其结论是“遗山词率真尚情的主观抒发是对于金词主情观念高扬的承继;山水田园在遗山词中的境界变得更为阔大;遗山词具有盛唐胸怀。”于新的论文认为遗山词“常以比喻、用典、想象等多种手法表达其经世之志、丧国之悲、身世之恨、悯民之情等多种人间挚情,体现了诗人悲天悯人的情怀。”(49)于新.浅析元好问的词[J].长沙铁道学院学报,2009(4):62.黄春梅文探讨了遗山词的写作技巧,认为其“在炼句方面的技巧主要是化用前人成句入词、锤炼字句。”究其原因,这是元氏“追求诗歌语言凝练含蓄的方式之一”,其化用之自然妥帖,用语之形象生动,体现了其诗歌语言“豪华落尽见真淳”的美学要求,并且也是其词能避免辛派后学“粗豪叫嚣”而达到“风流蕴藉”境界的原因(50)黄春梅.论元好问词炼句的技巧[J].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09(4):129.。而毕宇甜的《金元之际词的新变——以元好问、白朴为中心的考察》看到了随着散曲的崛起以及杂剧、小说等通俗文学的兴起,词出现了曲化、传奇化的倾向,并演变成一种风气,而引领这种风气的则是元好问与白朴,论文于是首先梳理了元、白词的曲化特点,即在用字、用韵、体式、巧体、语言、修辞等6个方面所现出的曲化特点,以及内容上的谐谑之意、调谑之情、淡泊之情等曲化倾向。其次,从题序和传奇志怪典故的使用等方面考察了元好问词中的传奇化现象(51)毕宇甜.金元之际词的新变——以元好问、白朴为中心的考察[D].太原:山西大学,2016.。此类论文,还有牛敏洁的《论〈遗山乐府〉的艺术风格》,其将遗山词风格划分为豪放刚健、婉约含蓄、平淡自然与沉郁顿挫等四类,并就具体内涵分别予以梳理,虽无新的开拓,但有细致的分析,还是有所贡献的(52)牛敏洁.论《遗山乐府》的艺术风格[D].太原:山西师范大学,2012.。而刘杰峰《士人的痛苦旅程——从遗山词看元好问的悲剧心理》则从文化心理的角度探究遗山词的情感内容,提出“遗山词是词人悲剧心理的一种再现,即向往山林却放不下仕途与国家;渴望建功立业,却又无所适从”“其悲剧的一生中,无时不在表现这样的一种传统士人的无以摆脱的宿命轨迹。”(53)刘杰峰.士人的痛苦旅程——从遗山词看元好问的悲剧心理[J].沙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3):18.
此期,最值得关注的研究,就是将元好问置于金元民族文化大融合的语境,以地域的、文化的视角,观照遗山词,往往得出新的结论。这种研究肇端于刘扬忠、张晶、赵维江等学者,而后学界时有相类的成果问世,如王菊艳的《遗山词的北方民族文化特质》就看到:遗山词在内容上常写奇险壮美的北国风光与狩猎战争,并敢于写真情、至情,较少受封建道德规范的束缚,艺术上,不少词充满了英风壮气,雄健质朴,出语新奇,凡此均表现了不同于汉族词人的北方民族文化特质。之所以如此,最重要的是因为“融汇汉文化传统与北方民族文化为一炉”,这就是元好问文学成就所达到的制高点所在。“元好问与萨都剌、耶律楚材、纳兰性德等北方民族作家一道,以其风格独具的诗词纠正了汉族作家创作的某些流弊,为中国古典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54)王菊艳.遗山词的北方民族文化特质[J].北方论丛,2003(2):63.再如于东新、张丽红的《对宋词“有偏斜度的超越”:从遗山词看金词》认为“作为金词之集大成,遗山词继承了宋词之言情传统,然又不为宋词所囿,其抒情豪迈苍凉,慷慨率直,情辞恳切,具有元氏自我面目。在体制上,元好问推尊‘东坡体’而成金词之‘正体’,改造‘宫体’而为新体宫词。在风格上,元氏既有本于苏、辛的‘遗山壮词’,又‘不尽为苏氏余波’。”该文的重点是对这种词艺成因的探讨,提出“多民族文化融合不仅是金词发生的背景,更是其发展的动力,遗山词充分体现了金词对宋词‘有偏斜度的超越’。”(55)于东新,张丽红.对宋词“有偏斜度的超越”:从遗山词看金词[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3(6):95.
总之,上述研究,均为整体正面的观照,与前时期相比,打破了文学史本位的局限,以多学科、多视角来考察遗山词渊源承继,深入探究遗山词艺特点,显出此期研究的开阔与融通。
此期还有关于遗山词分类研究的成果。主要有单梅森的《元好问山水词新探》、黄春梅《吴文英与元好问爱情词之比较》、陈磊《元好问遗民诗词创作心态考证》、陈巍的《元好问归隐时期词作研究》,以及华东方《遗山词研究三题》等。单梅森文认为元好问山水词不多,共20多首,但却是遗山词之代表性的类别,它主要体现了词人在自然山水中怡然自得、吟啸山林的志趣,以及由此引发的隐逸之想。在艺术上,论文认为其山水词有三种形式:其一,为纯粹的山水词,通篇是山水景物的描写,末句书写自己的情感,类似于赋的手法;其二,以山水景物开篇,下文言及它事以抒别情,类似于兴;其三,景语在词的中间部分,是为总结上文或引起下文。指出:元好问不断吸取前辈的经验当作自己艺术的基石,化用前人的诗句信手拈来,比如他化用苏东坡、辛弃疾、李白等大家的诗句;在词作中使用了拟人与对比的修辞手法,运用典故恰到好处,使词作清新活泼,内涵丰富。再者,在风格上,更多地表现了雄放杰出、超脱旷逸的风格特征(56)单梅森.元好问山水词新探[J].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10(1):80-81.。而黄春梅文将元好问与吴文英作比,从而梳理出元氏爱情词的特点:一是情词由“共我”的、普泛化的表现转向自我表现,词人感情由“应歌”转向深挚。二是虽然吴文英与元好问在爱情词的主体情感抒发上都是“缘情而发”,但其所抒情感的类型却不相同。吴描写的是自我个人的情事,而元遗山从叙述者的角度把爱情悲剧当作一种社会现象予以关注,尤其是遗山早期的言情词呈现出浓重的尊情倾向,不仅肯定情的价值,而且对违礼的私情予以了深情的歌颂,这在词史乃至文学史上的意义不可低估。三是在词的章法结构上,吴与元的爱情词都不约而同地打破了宋词上阕写景、下阕写情的通常写法,显得腾挪跌宕而又各有特色。四是吴文英与元好问在语言形式上也体现出两种不同的风格。“梦窗深得清真之妙,其失在用事下语太晦处,人不可晓。”而“元遗山极称稼轩词,乃观遗山词,深于用事,精于炼句,有风流蕴藉处不减周、秦。”上述吴文英与元好问的同与不同,究其原因,论文以为其一是两者的审美追求和词学观念不同。吴文英远祖温庭筠,近师周邦彦,而元好问在词学上极赞苏轼和辛弃疾。其二是与两者所处的文化环境有关。南方和北方产生了相对独立发展的两个词坛,南北两个词坛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创作风貌(57)黄春梅.吴文英与元好问爱情词之比较[J].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5):102-103.。而陈磊文则将观测点落实到元好问作为遗民词家身份的创作:“元好问作为金代诗词创作的高峰与方家,其遗民诗词风格形成与其身世与遭际志节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58)陈磊.元好问遗民诗词创作心态考证[J].科教文汇,2007(9):191.元氏遗民词怀溯故国而境界发越,体现出多重矛盾的士人心态与彷徨伤痛的思想感情。“元好问词与修治《金史》的举动相映衬,体现出气节的操持与心理变化的历程,于金元诗词文史间具有重要的词学价值。”华东方的论文是一篇硕士学位论文,提出:“遗山隐逸词写出了对高隐名士的倾慕和赞颂、寄情山水田园的适意欢乐、对功名利禄和人生态度的反思以及对道教仙家的倾慕。其隐逸词表现出自然天成的艺术特色。”(59)华东方.遗山词研究三题[D].桂林:广西师范学院,2010.并看到:“遗山词在选材、抒情方式等方面具有不同于传统唐宋词的‘北国情味’,其北方地域文化特点明显。”同是学位论文,陈巍的《元好问归隐时期词作研究》则将元氏归隐生活划分为或仕或隐的矛盾归隐时期和晚年遗民归隐时期,梳理了两个不同时期爱情词、山水词、怀古词、咏物词和寄赠词的创作情况,并分析不同时期词风的转变,认为或仕或隐矛盾归隐时期词风豪放中带有凄凉之感,晚年遗民归隐时期词风则是婉转中蕴涵豪放(60)陈巍.元好问归隐时期词作研究[D].吉林:延边大学,2008.。但这种前后分期其实是很难操作的,如何界定“仕或隐的矛盾归隐时期”?而最重要的,元氏归隐时期的作品与整体遗山词是一个什么关系,论文几乎没有涉及,不免遗憾。
再有,就是关于遗山爱情词的研究成果,比如关于《雁丘》词专题的讨论。主要有孟繁仁《元好问的〈雁邱〉词与“秋林渡燕青射雁”》、张沫、赵维江《情是何物——读元好问、李治、杨果的〈雁丘〉唱和词》以及梁俊仙《健笔写柔情,生死常相许——元好问〈摸鱼儿·雁丘〉〈摸鱼儿·双莲〉解读》(61)梁俊仙.健笔写柔情,生死常相许——元好问《摸鱼儿·雁丘》《摸鱼儿·双莲》解读[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2005(2):14-16.等,都是围绕《雁丘》展开的,或赏析、或辨析、或拓展研究。其中,孟繁仁文认为“燕青秋林渡射雁”情节在《水浒全传》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以此暗示作品中的部分情节构思,与金、元之际元好问的诗词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通过这一富有诗意的情节,比喻、暗示以宋江为首的“梁山弟兄”最后将面临四分五散、惨遭迫害的悲剧结局。论文借元氏《雁丘》谈的其实是小说《水浒传》的问题(62)孟繁仁.元好问的《雁邱》词与“秋林渡燕青射雁”[J].东南大学学报,2003(5):116-118.。而张沫、赵维江文谈的要以元好问《摸鱼儿》双雁凄美故事所展开的唱和,从而透露出金代词坛的某些情形。论文指出,元好问、李治、杨果的《雁丘》同调同题,然其构思立意,各有所重;造句行文,也风格有殊;就其艺术造诣而言,各有不同,但三词匠心各运,犹如松、竹、梅三友,皆有妙处,也可谓异曲同工(63)张沫,赵维江.情是何物——读元好问、李治、杨果的《雁丘》唱和词[J].名作欣赏,2004(6):75-78.。也有学者从这首《雁丘词》中见出元好问“神州陆沉之痛,铜驼荆棘之伤”(况周颐语),见出他人生的种种“草蛇灰线”,其“出乎世,入乎世”的矛盾心理和复杂人生。这就是陈为人《〈雁丘辞〉沧桑元好问》的主要观点(64)陈为人.《雁丘辞》沧桑元好问[J].社会科学论坛,2011(10):153.,见出一定的新意。此外,还有观照遗山爱情词其他作品的,如刘玉《流落的男游别都,耽阁的女怨深闺——元好问〈江梅引〉析读》。《江梅引》也是元氏非常有名的爱情词,该文认为上阕是铺陈金娘之怨,也对男子的失约隐隐有所指摘,在词人看来这正是导致一出爱情悲剧的根源。下阕是词人自我抒情。失去杨白花的胡太后尚能借《杨白花歌》传达哀思,而失去情郎的金娘却只能将满腹的幽怨带入坟墓,一个妙龄女子玉殒香销更让人感伤。论文最后指出:“元好问写词‘吟咏性情’,对金娘的悲剧表达深切的同情,同时也对她的忠贞不渝表达肯定和赞美。从这个角度来说,元氏此类作品对爱情的颂扬实际上开启了后代至情文学的先河。”(65)刘玉.流落的男游别都,耽阁的女怨深闺——元好问《江梅引》析读[J].文学界,2010(10):61.
此期还有对遗山涉梦词的成果。遗山涉梦词多达81首,占其词总量的1/5,是十分重要的作品。较早的论文是邓昭祺《遗山词中的“梦”》,其认为遗山涉梦词题材广泛,“包括咏怀、爱情、吊古、丧乱、游览、送别、寄赠、咏物等”,“这些词中所写的梦境,大概可以知道词人最关心的是哪些问题。可以把遗山梦词的内容分为渴望归隐、忧时伤国、悼念亡妻、怀念朋友和人生如梦等五大类”(66)邓昭祺.遗山词中的“梦”[J].民族文学研究,2009(4):143.,并分别做了讨论。陆凤星的《遗山涉梦词研究》是完成于2014年的一篇学位论文,在前贤的基础上,其以题材为标准,将遗山涉梦词归纳为“归隐梦”“伤国梦”“人生喟叹梦”“男女相思梦”“亡妻梦”“思友梦”“思乡梦”“游仙梦”以及“咏物梦”等九类,并通过主客观两方面,分析了涉梦词的成因,认为其“对梦幻世界的青睐是客观环境与主体世界不断进行交融与碰撞的结果”(67)陆凤星.遗山涉梦词研究[D].昆明:云南大学,2014.。最后还讨论了遗山涉梦词对唐宋涉梦词的拓展,认为有两方面:“一是题材的创新。遗山在具体梦境的描绘中增添了许多细节刻画,并且增添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元素;二是技法的开拓。遗山涉梦词具有典型的‘以传奇为词’的特征和巧妙地运用以男女之情喻家国之感的寄托手法。”这种梳理使得遗山涉梦词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此期还出现了一些专门的研究。如赵永源《论元好问〈鹧鸪天〉词的创作》,认为《鹧鸪天》是元好问使用得最多的一个词调,共37阕,多半为其晚年手笔。这些作品其实是一个整体,词人特殊的人生经历使这些词作显得沉郁顿挫,意蕴深厚,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其中蕴藏着作者深厚的功名意识、故国之思、身世之感等,而且它往往与隐逸情思紧密联系在一起。论文的结论是:“元好问《鹧鸪天》系念故国、感怀身世的思绪浓重而又强烈,这种运用某一特定词调来抒发特有的情感内容,并深入开掘和拓展这一词调的艺术实践,在金词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68)赵永源.论元好问《鹧鸪天》词的创作[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7):63.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此期还有学者关注遗山词的词序问题。词前有序,一般认为始自苏轼,其从无到有、由简入繁,艺术水平越来越高,审美功能也日趋多样化,而其中遗山词序是继苏轼、辛弃疾、姜夔之后最值得关注的作品。颜余庆《元好问与词序的进化》就是考察遗山词序的成果,它主要讨论了元好问对于词序的创新,认为是表现在更加复杂多样的功能上,如“交代写作的语境,记载有关文献史料,提供必要的词语、典故的训释,以及指明拟古的性质和对象”(69)颜余庆.元好问与词序的进化[J].兰州学刊,2009(4):1.“在他笔下,词序与正文之间有时形成叙事与抒情相应相生的关系,就像说唱文学中宾白相生、韵散结合的结构一样。”所以它的结论是,“元好问在词序的进化过程中是重要的一环”(70)颜余庆.元好问与词序的进化[J].兰州学刊,2009(4):209.。这是学界第一篇讨论遗山词序的论文,值得注意。而后,又有张博《元好问词序、词题论三则》,该文并非讨论遗山词序艺术机制,而是就遗山词序、词体中所包含的词学理论进行解读,从中见其词体创作的完备、“以词存史”理论主张的实现、“诗词一体”观的自觉实践等方面内涵。比如其中所包蕴的元氏词体观念。一是遗山词体类众多,创作完备,并且不以体之庄谐而取舍有偏,即如徐世隆所言“体制最备,又能用俗为雅,得前辈不传之妙”。二是遗山词在仿效众体的同时,又能不受选体本身的优劣束缚,而是将个人的情感体验并入其中,从而使得其词在整体风格上殊异于所效之体,即所谓“变故作新”之意(71)张博.元好问词序、词题论三则[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1):76-80.。可以说,此类研究还是有一得之见的。
此期,还出现了专门关于元好问词学理论的研究。按时间顺序主要有邓昭祺《元好问词味说初探》、王昊《雅正与尊情:元好问词学思想的内在张力及其意蕴》、黄春梅《元好问的宋词观》,以及于东新《元好问的文化立场及词学思想》等成果。邓昭祺文提出“以味论词,始于元好问”。元氏在《遗山自题乐府》中以黄庭坚《渔父词》、陈与义《临江仙》二首为例,来分析词之有味,最后该文认为元氏所谓的词味,实际是指“含蓄委婉地包含在词中的深层意思”(72)邓昭祺.元好问词味说初探[J].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7(4):4.。王昊文则从元氏对苏轼《沁园春》(孤馆灯青)一词的误读说起,指出,其“误读背后体现的是元好问词学思想观念具有鲜明的崇雅意识和儒学背景,其词美理想正是其士大夫精英意识的集中体现。”具体的,一是“雅正与尊情”。金源与南宋之世,“尊体”成为南北词学共同目标。元好问的“尊体意识”一以贯之内化于“以诗衡词”中,即他是以诗学观念来观照阐释词体这一后起的音乐样式的。他对词体“吟咏情性”的要求是情感的中节与导范,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所谓“倡‘雅正’也主‘真情’”。二是“以诚为本”。元好问的词学思想颇为复杂,“雅正”与“尊情”的张力结构是具有连续性的。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矛盾,元好问晚年提出了“以诚为本”的诗学命题。论文认为,“雅正”与“尊情”这一张力矛盾的理想状态的完全消解只能是哲学层面上(73)王昊.雅正与尊情:元好问词学思想的内在张力及其意蕴[J].社会科学战线,2009(9):151-153.。关于元好问如何看待宋词,黄春梅的《元好问的宋词观》进行了讨论,认为在如何继承宋词的问题上,元好问表现出的“是一种兼收并蓄、勇于超越的胸襟和气魄”(74)黄春梅.元好问的宋词观[J].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9(2):141.。正是这种胸襟和气度,使元好问在词体的本质、功能以及风格、流派等一系列词学基本问题上提出了许多颇有新见的主张,比如他的性情说,对“东坡体”和“宫体”体式特征及价值的认识,这些都对后世词学理论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于东新文则提出“元好问是站在华夏文化守护者和传承人的立场上,在金元鼎革之际,救世活人,存文保道,积极促进了蒙元政权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显示出一种了不起的器识和境界。”(75)于东新.元好问的文化立场及词学思想[J].社会科学辑刊,2014(3):182.正是这种“文化大于种族”的立场,使得元氏词学思想兼容百家,包蕴古今,“无论是其词主‘情性’的创作主体论,渊雅深厚的艺术风格论,还是‘言外’与‘滋味’的欣赏接受论,以及以词传史的审美功能论,都显示出元氏词论的开放和圆通的多元文化特色”。
值得注意的是,此期江苏大学的赵永源教授是一位集中研究遗山词的专门家。他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关注遗山词,先后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代表性的有《遗山词集版本考略》(76)赵永源,秦冬梅.遗山词集版本考略[J].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4):21-27.《论遗山词的词史地位及其独特性》(77)赵永源.论遗山词的词史地位及其独特性[J].江苏大学学报,2006(5):65-70.《试论宋金元间词体创作的雅俗之变——以山谷词与遗山词为例》(78)赵永源.试论宋金元间词体创作的雅俗之变——以山谷词与遗山词为例[J].江西社会科学,2007(4):84-88.《词中的“杜陵嫡派”——析论杜甫诗歌对遗山词风的影响》(79)赵永源.词中的“杜陵嫡派”——析论杜甫诗歌对遗山词风的影响[J].江苏大学学报,2007(4):48-53.《再论杜甫诗歌对遗山词风的影响》(80)赵永源.再论杜甫诗歌对遗山词风的影响[J].江苏大学学报,2009(2):37-41.《融合传播接受——评议宋金元明清时的遗山词》,以及与蔡晓伟共同完成的《论遗山词在民国词坛的接受》(81)蔡晓伟,赵永源.论遗山词在民国词坛的接受[J].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18(6):26-31.等,学术专著有《遗山乐府校注》(82)赵永源.遗山乐府校注[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遗山词研究》(83)赵永源.遗山词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等。
元好问词集名《遗山乐府》,又名《遗山先生新乐府》,其版本主要有一卷本、三卷本、五卷本等不同的系统,在词篇数目、词作编序、词前小序、部分文字等方面,都有差异,现出不同的特点。赵氏编撰《遗山乐府》历十余年,广采博收,钩稽考辨,终于校注完成这部当下较为完备的遗山词别集。其体例仿唐圭璋先生《全金元词》录遗山词例,前三卷以《疆村丛书》本《遗山乐府》为底本,余则以《石莲庵汇刻本》为底本,并参之八千卷楼藏明钞本、吴讷《唐宋名贤百家词》本、陶湘刻景明弘治高丽晋州本、阳泉山庄刻《遗山先生新乐府》本、读书山房刻《遗山先生新乐府》本、鉏月山房校本、清钞本、丁氏迟云楼抄本等达11种之多,间以吴重熹石莲庵汇刻《九金人集》本校勘,力求精善。具体词篇的校注,即所谓“词篇之有本事者,则详加笺释。词中之事典、语典、人名、地名等亦详注之”,具体体例形式是先出“校记”,次出“笺注”,最后为“附录”。关于“校记”,编者解释说:“《疆村丛书》本《遗山乐府》附有《校勘记》,鉏月本《遗山先生新乐府》卷末附《订误》一卷,于校勘有参考价值者,则在《校记》中酌加转引。”(84)赵永源.遗山乐府校注[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3-4.而《笺注》中多引吴庠、缪钺之《遗山乐府编年小笺》、狄宝心《元好问年谱新编》等文献。同时,将历代品评遗山词之言论,“尽目力所及,细大不捐,多所钩稽”,以“附录”形式缀于相关词篇之后。并在全书之末,又集有六大“附录”,分别是附录一《遗山词补遗》、附录二《遗山词集版本考》、附录三《历代书目所录〈遗山乐府〉版本及题跋》、附录四《〈遗山乐府〉序跋》、附录五《遗山词总评》、附录六为《历代方志所见遗山传记资料》,可见编者寻绎勾连,上下求索,可谓详赡矣。《遗山词研究》是赵永源教授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出版的一部系统研究遗山词的专书,集中体现了其关于遗山词研究的基本观点。上篇为“考证篇”,梳理遗山词集的版本、考证遗山词的作年,将词学研究建立在厚实的文献基础上。下篇为“论述篇”,有《遗山的词学理论及其词词作》《宗唐风气下的遗山词》《遗山词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等章次,赵氏详细梳理了遗山词与唐人尤其是杜甫的承继关系,所论令人信服。他指出:“金元词坛宗唐之风炽盛,金元词人从用字、用句、用意等不同角度全面学唐。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等大诗人尤得喜好,特别是杜甫备受尊崇,在金元词人的作品中尊杜用杜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与宋代词人周邦彦檃括唐诗后的浑厚和雅交相辉映。当然,遗山词宗唐最为成功的地方表现在他对杜甫诗歌的接受和融化。饱经沧桑的人生经历、独特系统的杜诗学理论,使得遗山把杜甫作为自己诗词创作时规模、取法的对象。遗山不仅诗可称‘杜陵嗣响’,其词亦堪称‘杜陵嫡派’”(85)赵永源.遗山词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6.。
综上所论,作为“金人之冠”的遗山词,自1978至2018年40年来取得了非凡的成绩。既有宏观、正面的整体观照,也有具体词类、微观作品的文本细读;既有词集版本的文献整理,也有立足实证的诠释性分析;既有文学史、文学本位的专业研究,也有立足文化史、民族学、文学地理学等跨学科的多元考察,视野开阔,成果丰硕,值得肯定。但也有不足,比如多学科、多维度的研究还是显得薄弱,那种立足于“构建多元一体中华文学史”广阔视野的研究还有很大开拓的空间。期待学界未来10年或40年,包括遗山词研究在内的元好问研究取得更大的成绩,为繁荣我国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