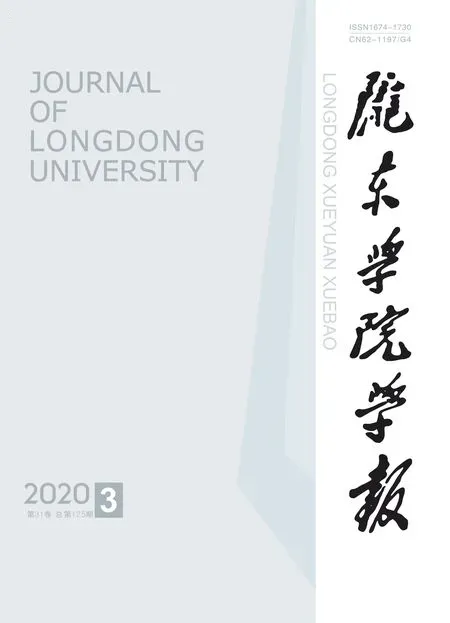陇东地域特色写意人物画创作研究
——基于环县道情皮影美术的写意人物画创作
邵维聪,李 娜
(1.陇东学院 美术学院,甘肃 庆阳 745000;2.河连湾小学,甘肃 环县 745000)
环县道情皮影作为陇东地区的璀璨明珠,受到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关注。道情皮影美术在诸多方面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充分体现了陇东地区民间美术的特征。在中国画发展多元化的当下,研究并将其运用于写意人物画创作,对于拓宽写意人物画创作途径,传扬陇东民间美术,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一、环县道情皮影美术的艺术特征
环县道情皮影相传产生于宋代,是融合民间音乐,美术和口传文学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深受道教的影响,为使说教形象化,生动化,从而以皮影戏曲的形式展开,形成了独特的道情皮影艺术。在清代末期,经过皮影大师们的革新,使得道情皮影艺术逐渐成熟并定型[1]。与陇东人民生活、生产、风俗习惯密切联系,环县道情皮影具有独特的地域特色,生动地展现了陇东人物风情。其通俗易懂的艺术形式受到劳动人民的喜爱,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与众不同的造型观和色彩观。
环县道情皮影注重工艺变化与图案装饰,造型方面即生动概括,又极为丰富精美。在制作上融入了陇东剪纸等民间艺术的造型元素,形成了独具一格的造型语言风格。在人物造型上,运用直线和曲线相结合的方式使人物形象变得简练、概括,线条的组织上长短穿插错落有致,气韵生动。善于运用线条的长短粗细以及疏密变化来展现形体的透视变化。皮影内部的造型比较复杂,在服饰的边沿等部位使用装饰性的图案符号排列装饰,首尾呼应,使画面平而不板,呈现出和谐统一的艺术效果。人物按戏曲的生,旦,净,丑行当设计,一般为黑忠,红烈,白奸,空正,实丑,体现出头大身小,上窄下宽,手臂过膝的造型特点,线条流畅,人物形象鲜明。其他殿堂,帅帐,鬼怪,奇禽异兽,花草树木等道具,构思巧妙,形态多样,彰显出中国民间美术夸张写意的特征[1]。
色彩方面,道情皮影用色对比强烈,光洁透亮,艺人们在长期的观察与感受中,形成了一套象征化的设色理念,充分体现了陇东地区的民间审美习惯。在人物面部的设色上,运用了象征的表现手法来表现人物特征。不采用现实生活中眼睛所观看到的自然颜色,而是经过主观分析,选用最能体现人物形象特征的色彩进行赋色,使人物的形象特征与设色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此外,艺人们吸收借鉴了环县社火脸谱,地方戏剧脸谱的色彩搭配程式,尤以净角的花脸呈现的特征最为明显,不同色块组合的隔色渲染描绘,配合变化有致的镂空线条,形成角色各异的脸谱程式。自古以来,色彩一直被人们赋予丰富的内涵。环县道情皮影赋色上以黑、白、红、绿为主,反映出环县人民个性鲜明,感情强烈的特征。红、绿作为最具有乡土气息的色彩,受到陇东当地人的喜爱,因为那是生命力的象征。黑、白作为最具有象征性的色彩,是实与虚的写照,也是人们伦理道德观念中善恶的象征,这种设色方法具有很鲜明的地域特征和强烈的装饰性。
二、环县道情皮影美术与写意人物画的共通性
基于共同的文化,绘画历史渊源,环县道情皮影美术与写意人物画之间有着许多共通性。这种共通性基本体现在造型,色彩,表现手法,透视法则以及文化内涵五个方面。
(一)意象的造型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作为中国画最基本的造型原则,贯穿于中国画千百年来的发展历史[2]。受其影响,环县道情皮影的造型表现也具有这一特征,二者的造型理念都与西方绘画造型理念不同。虽然所表现的客观对象包罗万象,但环县道情皮影与写意人物画的造型理念都是以意象造型为主。这种造型观念确定了画家对客观物象的表现是一种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的结果。即通过观察,对客观对象以“意”取“象”,以描绘者所要表现的主观精神的需要来规定艺术形象与客观物象形貌之间“形似”程度[3]。换句话说,即是以己之意,塑彼之象,传己之情。写意人物画在创作过程中始终以这一标准来造型。道情皮影在制作过程中,为使人物形象生动,个性特征鲜明,也遵循这样的造型理念。因而,从这方面来讲,环县道情皮影的造型理念与传统写意人物画的“写意”造型理念一致。
(二)色彩的夸张运用
道情皮影的用色,以红绿为主色调,黑色调和,隔色平涂,逐层烘染,加上牛皮的黄色,镂空处呈现的白色,共有五色[4],是民间传统五行五色观的包罗万象、简化归类的运用体现。在环县道情皮影中,神仙、天官、仙姑、童子等神话形象及想象创作的奇灵异兽,赋色主观,夸张浪漫,不拘泥于客观对象本身[2]。与传统中国画中所倡导的“随类赋彩”用色手法相似,写意人物画用色概括,依附于人物的结构变化,讲究笔触美感,色墨混用,制造对比,但又于对比中寻求色调的和谐与协调。其中小写意作品,人物面部设色细腻,在赋色上强调赋色的主观意识。
另外,黑色作为二者所经常使用的重要颜色,具有特殊的表征。传统中国哲学认为,人文观念的审美意识强调性情内敛,含蓄内蕴,所以多以墨色代之。所以黑色(即墨色)被赋予了特殊的内涵,并大量运用于造型过程当中,这在二者的造型中都有体现。
(三)相似的表现手法
道情皮影人物的设色与造型手法较为夸张,但这种夸张的表现手法在中国画中很容易见到。采用这种手法能够强化物象特征,突出情感的表达,从而使艺人们在创作中摆脱原有形和色彩的束缚,大胆地对色彩和形加以夸张运用,以达到“妙超自然”的境界。
另外,不管是道情皮影还是中国画,其发源都来自传统中国美术。在设色手法上,多为分染、平染和罩染,且二者的部分作品在表现手法和人物动态形象特征的处理上相差无几,绘画符号具有共通性。这也使得二者在写意人物画创作方面的结合成为可能。
(四)共同的透视法则
中国画将透视称之为“远近法”,它基于庄禅哲学的引导,以意象思维来完成,是一门建立在深厚人文基础上的、超越了自然视觉感受的科学观察方法。它重视自然万物的本相,但又不是视觉直观,是一种以线造型的平面经营形式。平面造型的图像被安置在同样平面的空间上,使中国画的造型特点与优势得以发挥,达到造物在我,造境在我的创作自由。在创作中,画家可以根据自己创作的主观想法,不受束缚于物象的客观存在状态,灵活安置它们的位置关系。
道情皮影美术同样讲求作品二维平面的视域特征,讲究构图的完美,自由灵活,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5]。源自画家对作品表现的需要,画中人物,物体放置“随意”,视野宽广、辽阔且具有变化,具有典型的散点透视方法。所以二者在透视方法上相同。
(五)共同的文化内涵与美学思想
无论是道情皮影美术还是写意人物画,都是随着时代的步伐,以中国传统文化,美学思想为前提的。文化是民族发展,存在的根基,是道情皮影美术和写意人物画发展的文化积淀和永恒定力。道情皮影和中国画之所以能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而不被覆盖,归结原因,它们的支撑点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积累。从这一方面来讲,道情皮影与写意人物画的文化内涵是相同的,这也是许多学习中国画和传统中国民间美术的外国学者只得其技法却不能得其精神气质的根本原因。
《庄子·田子方》中记载:“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笔和墨,在外半者。有一史后至者,儃儃然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视之,则解衣般裸。君曰:‘可矣,是真画者也[6]18。’”庄子的这段话充分传达了中国画创作的审美观念。创作是一种自我意识、精神意识的自然抒发,当画家在达到精妒八极,心游万仞之时,其作品将必然会是饱含生命力和冲破束缚的张力的。“用情笔墨之中,放怀笔墨之外”[6]19,将个人的主观情感发挥到极致,其作品也将自然地会自由生动,打动人心。与此同时,将“自我”进行自由伸张,进入“非自我”的状态,实现中国画“返璞归真”的最高境界,这在写意人物画中体现得最为突出。道情皮影作为以道家思想衍生的一门艺术,其美学思想与写意人物画大致相同。
三、寻求基于道情皮影美术基础上的写意人物画表现新途径
纵观写意人物画的发展历史,实际上是一部写意人物画技法、样式、风格不断发展变迁的历史。继承并发展写意人物画是当代画家的使命,许多人做出了大量尝试,取得了一定成绩。这其中,有画家成功吸收并运用传统民间美术,突破写意人物画原有模式,创作出了新的视觉样式,成为当代写意人物画坛的杰出画家。比如画家周京新及其《水浒》系列人物画作品,画家张立柱和他笔下的陕北农村题材作品。此二者将中国民间美术与写意人物画创作进行有机结合,均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有的画家只是单纯地借助其他材料或模仿其他画种如:油画,版画,水彩画等技法,作品不尽如人意,不管是从作品的效果或是中国画的本质语言而言都是失败的。这其中的主要问题便是油画,版画等画种的审美标准以及文化渊源与中国画的差异。这要求我们须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重新审视,寻求适用于自己的写意人物画法。道情皮影美术则不同,源于中国传统美术,与写意人物画有着诸多共通性,具有与写意人物画创作相结合的可行性。依据本人在该研究上所做的创作实践经验,有以下途径可有效实现二者的结合:
(一)人物形象表现的意象夸张
“意象”作为写意人物画的主旨精神,贯穿着整个写意人物画发展史。不受客观形象束缚,迁想妙得的意象造型,写立于胸怀的心象,形成了其独有的图形样式。石鲁在《画学录》中对此说道:“偏于主观者以形象为符号,偏于客观者以形象为拜偶,皆不足取也。余谓当取于客观,形成于主观,归复于客观,故造型之过程乃为客观—主观—客观之式也[2]。”此说法非常精辟地阐述了传统中国画意象造型的方法和要求。回顾历史以及当代名家的作品,均是结合一定的笔墨变化,以意象造型的风格不同为突破方向而进行创作的,使其作品具有独特性,占据了美术史的一席之地。因而,写意人物画要寻求发展、突破,离不开意象造型的创新。与之相比,道情皮影美术中的意象造型存在差异。后者为使人物动态在表演中更加形象生动,在造型方面进行了简化,夸张。此造型手法对于创新写意人物画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在创作中,可借鉴道情皮影美术对人物造型的表现手法,风格特征,进行加工整合,以此来创作出风格独特的作品来。这方面的探索已有成功案例,比如著名画家张立柱笔下的写意人物画作品就是将剪纸艺术的造型方法在写意人物画中成功运用的例证。作为陕西地区最具有代表性的写意人物画家之一,张国柱的绘画作品多表现的是农村生活题材。作品中奔跑玩耍的孩童,推着手推车运送东西的农民等。画家在绘制这些人物形象时都将剪纸艺术的造型特点运用于其中,以典型的剪影式的平面造型塑造,人物动态生动,活泼,生活气息浓厚,更好地对这一题材进行了表现。另一方面,因为将剪纸美术的造型元素运用其中的缘故,使得其作品中人物形象的绘画语言具有很好的符号性,视觉样式独特,具有吸引力。道情皮影美术虽与剪纸的造型特点存在一定差异,但其造型体系相似,如能很好地将道情皮影美术的造型特点成功运用到写意人物画创作过程中去,势必会取得一定的优秀成果。
(二)笔墨语言的概括、装饰化处理
写意人物画作为一种独有的绘画形式,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有着较为稳定的内在结构和完整的语言体系。深受我国传统美学思想的影响,其绘画主体语言是笔墨。植根于历史文化大背景和现实生活土壤之中,笔墨包容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独特的哲学思想、人文观念和思维特点[3]。发展写意人物画,须秉持这一基本的语言特征。创作中,借鉴道情皮影美术对于人物形象的概括造型和装饰化处理方法,对写意人物画笔墨技法进行革新,可以使写意人物画形成浓郁的地域风格和独特的视觉效果。
在创作中,要实现笔墨语言的概括,在笔法上可以使用没骨法对人物形象进行塑造,减少双勾画法的应用。落笔要干脆利落,笔法灵活而不乱,做到用笔高度概括,准确地表现人物的结构特征,使人物形象呈现剪影式的表现效果。与此同时,注重墨法的运用,使笔法与墨法相辅相成,让画面产生水墨淋漓的美感。这可使作品中人物形象概括的同时,不失写意人物画的笔墨韵味和其特有的笔墨符号,创作出一种新的写意人物画作品样式。在设色上,与笔墨互为表里,以色助墨光,以墨显色彩,共同构成一个整体。在当代中国画的发展中,墨与色的同构及其艺术规律的演绎与展示,已成为传统中国画与现代中国画的艺术通道,为中国画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另外,在绘制人物形象和服饰时,适时采用图案化的处理方式,对构成人物形象局部结构的笔墨,色彩进行图案化处理。如周京新在其《水浒人物》系列作品中对于笔墨、色彩的构成处理就具有很好的示范性。画家在作画过程中,对人物服饰,道具,动物等对象,在笔墨上进行了“有序”的排列组合,使画面中的每一笔墨色都具有构成意味和装饰性。在人物服饰上采用了民间年画的设色样式,进行了图案化处理,以此来实现整幅作品的装饰性效果,因而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三)突出创作主题
“化景物为情思,万趣融其情思”“真境逼而神境生”[6]18。观看历代中国画,唐代以后,在绘画活动中人的主观能动性日益处于主宰地位。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写意人物画的发展趋于多元化。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科技的发展使绘画材料不断丰富,众多画家在材料的使用上大胆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与此同时,许多画家陷入了研究各种技法的“技”的层面的困境而不能自拔。忽视了绘画作品更重要的主观性与人文关怀,使自己的创作步入末路,这样的现状令人担忧。道情皮影在此方面具有很好的启示意义,其每件皮影作品都是为表现某一特定主题而创作的,并最终回归到人文关怀,使其更容易被大众所接受。因此可借鉴此类经验,让写意人物画创作出具有社会价值的作品。
但写意人物画作品与道情皮影美术的主题表达又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体现为写意人物画创作更突出画家的个性发挥,且以突出学术性特征为主,表现画家本人的思想、人文关怀,观众多为专业人士。画家唐勇力就是典型,他的敦煌系列作品,借助于哈粉等特殊技法材料,使作品主题内涵鲜明;画家刘庆和使用皮纸作画,利用皮纸渗透慢的特性时将没骨画法推到一种新境界,使之与人物形象有机结合,准确表现出了画家对于当代人心理状态的理解,感人肺腑。道情皮影则程式化突出,主题性明确,感情色彩浓烈,有歌颂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取得的发展成绩,也有表现乡村爱情或神话故事等农民群众所乐道的话题,其观众多为普通农民群众,其中众多话题具有大众化特点,被大众接受,认可。在创作中,要灵活运组织画面的主题,处理好这一关系。
总之,环县道情皮影美术与写意人物画在诸多方面有着共通性。因此,将二者结合,创作出具有陇东地域特色、新的写意人物画作品样式具有很好的可行性,需要画家进行大量的创作实践研究。这将对传扬陇东民间美术,拓宽写意人物画的创作途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蓝田上许村道情演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