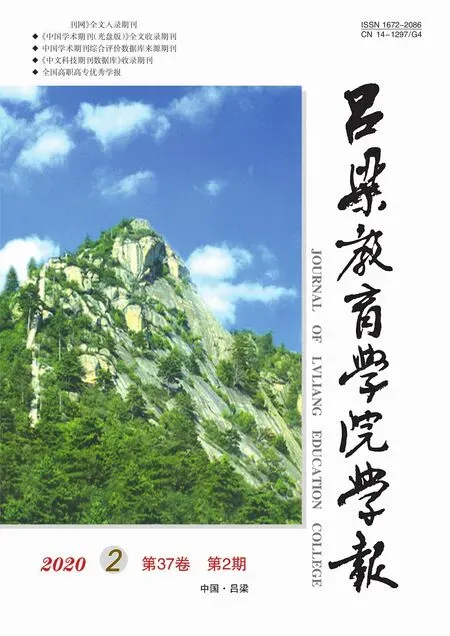中国高师院校女教师职业发展环境研究述评
许 英
(山西师范大学 临汾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0)
“妇女/女性”和“环境”这两个曾经完全独立的概念,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1995,北京)之后密切联系起来, 高校/高师院校女教师和发展环境问题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界。近二十年来研究者基于不同的环境视角聚焦于高校女教师的职业/专业发展困境(禹旭才,2012;穆岚、李宝华2012;艾晶、张洪阳,2013;周亮梅,2011;黎钰林,2016)、职业倦怠(苟亚春,2008;李悦池、姚小玲,2017)、职业生涯规划和发展(罗青,2006;姚冬梅,2008;程芳,2011)、工作-家庭冲突(李明勇,2009)方面对高校女教师发展环境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师范院校职业环境本身对不断增加的高师院校女教师群体的影响在高校环境中淡化了师范性的特色存在。学界在开始不断认识师范教育发展中人才的重要性的关键口,女教师职业发展环境的重要性就推到了研究的高度。故本研究旨在对高师院校女教师发展环境进行梳理,从女教师职业环境的现状、女教师对生活的环境体验、女教师期待的环境、优化环境的对策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探索地方高师院校女教师职业发展环境理论视角和方法的迫切性。
一、高师院校女教师职业发展环境因素分析
影响人才发展因素多种多样,既包括硬环境,也包括软环境;既包括物质环境,也包括精神环境;既包括宏观环境,也包括微观环境。涉及内容也非常广泛(政治、经济、文化、人文、科技、教育)。影响方式也不同(有单向影响,也有多向影响,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有深层影响,也有浅层影响)。软环境是近年来学术界高校环境建设关注的因素。高校软环境蕴含了“大学的内在品质。”本质体现的是高校文化氛围和文化熏陶,突显出高校的特质所在,深远地影响着高校对外辐射的力量。在完善学校软环境的研究里,内涵式发展生长为高校发展新的增长点,学术界在内涵式发展要求下对高校人才队伍建设进行思考,在论述内涵式建设与学术权力回归的必然联系的基础上,呼唤学术权力回归。关注了高校内涵式发展的制度环境,将教育效能感、工作投入等变量纳入到高校软环境建设与教师职业发展的关系探讨中。有的在关注政策环境对高校教师影响的同时,共同融合校园环境和社会环境建设。
综合来看,学术界近几年关注高校职业发展环境因素呈现出几个特点:(1)由注重硬环境建设到关注软环境建设;(2)由侧重宏观环境研究到微观环境研究;(3)由重视外在环境因素研究到内涵式环境研究。(4)从间接环境因素到直接环境因素研究。研究趋势也朝向软环境的建设中走出内涵式发展道路。共同融合社会环境、学校环境、家庭环境、个人环境来认识高师院校女教师的成长(潘慧春,2008)[1]。
二、高师院校女教师职业发展环境的现状
高校专任女教师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从1999年37.35%,到2015年达到了48.62%。毋庸置疑,女性发展的机会和空间日益扩大。蒋玉梅(2011)[2]把高校教师的职业发展置于社会性别权力机制中加以审视,发现高校女教师边缘的群体,是游离在男权中心的高等教育体制之外的。生云龙(2009)[3]则通过男女教师的职务、年龄、学历及其学科结构等角度的研究,显现出男女专任教师职业发展的性别差距,看到高校女教师的职业发展环境身处于“玻璃天花板”隔离。禹旭才(2011)[4]在研究中指出我国高校女教师队伍日益壮大并不一定意味着 “男中心女边际”环境格局的打破。赵叶珠(2007)[5]放眼国际定位我国女教师职业队伍建设,研究中同样看到女教师比例虽然较高,但在整个教育领域顶级学术职位上,男性仍然占有相当的优势。祝平燕(2004)[6]呼吁地方要建立一个有利的高校女教师发展的性别文化和社会环境。高师院校女教师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界定自己的职业身份或性别身份呢?学界研究者主要聚焦两个方面予以了关注——师范院校是综合性大学还是师范性大学?女教师是性别身份还是职业身份?
高师院校随着一些综合性大学的介入走向了开放(宋争辉,2018)[7]。随之而来的师范学校/大学逐渐被取消、合并和转型,“师范院校”的特色——“师范性”渐渐淡出了研究者的视域,“师范性”呈现出了弱化的趋势。面对教师群体应对教育变革的各类回应,研究者们更多地追问教师的负向情绪,试图为教师提供应对改革的各类支持、反思改革过程中存有的不适以及在调整变革推动改革方面寻找路径。但在实践运行中,高师院校的改革积极性普遍倾向于在学科建设与专业设置上向综合性大学靠拢,改革的力度也较大,但在教师教育改革方面甚至可以说缺乏改革力度,改革的思路不够明晰,仍在按惯性运转而已。教师又不可避免地处于被动状态,教师的决策权并没有明显体现,缺乏为其合法性辩护的可能。教师教育培训、师范教育院校资源条件等等环境建设没有及时跟进,教师倍感压力。实际上一些师范院校的教师教育并没有被加强,反而被削弱了(郑师渠2004,孙彩霞2017)。[8-9]史晖(2009)[10]以叙事研究方法通过“我”的视角,“我”的经历,“我”的体验和思考站在高师院校学科教学论教师的角度追问“出路”“我在哪里?”“我是什么身份?”。(杨跃,2011;崔藏金,2018)[11-12]丁瑜(2014)放眼高校的具体情境中发现,女教师只是跟随者,满足于安身立命,男性通常被视为规则的制定者[13]。在以男权为中心的职业环境中,师范教师身份问题在女性教师群体当中体现得更加明显和突出。性别身份与职业身份之间的博弈是女教师生存环境的主要现状,是研究者绕不开的课题。在生活、工作情景中女教师精神世界面临着双重困扰:扮演好独立自主的人时,是被社会排斥出正常女人的行列,扮演好好妻子、好母亲、好女儿角色时,又远离了独立自主的队伍。高校女教师的角色冲突似乎不复存在,事实上它不过是一个破灭了的“神话”(张李玺,2005)[14]。“教师职业是女性职业”,但“无形中女教师又游离在权利中心外围,产生了性别隔离现象”(蒋玉梅,2011)[2]。虽然有些男性已经开始认识到家庭对他们的重要,并会偶尔主动帮助做家务和照顾小孩,但是社会大环境的认同不足,对于男性的参与没有给予适度的肯定与正面的支持,潜在的社会性别意识形态仍难摆脱家庭性别分工的影响(周新霞,2007)[15]。我们不难看出高校女教师的身份特征自我建构中透露出的困惑和迷惘、压力与压抑,她们的生命选择与发展道路受到各种外来环境因素的影响,致使潜力无法挖掘出来,主体地位不能凸显,她们在生活选择中所做的各种努力、调适与抗争多被隐没在问题中了(丁瑜,2014)[13]。所以,在参与高等教育的进程以及在高等教育中拥有的资源、权力和发展机会是必然存在不平等现象的(于桂敏,2017)[16]。
综合而言,研究者认为“边缘化危机”与“性别迷思”仍然是当下高师院校女教师职业发展的两大主要环境困境(禹旭才,2011)[4]。呼吁在研究中不仅要关注女教师“话语权、发展权、社会声望和资源分享等方面,而且要关注女教师精神上、心理上的体验。
三、高师院校女教师职业发展环境的感知与体验
环境是相对某个中心事物的外部世界。中心事物不同,环境概念也随之改变。高师院校女教师对环境的体验是理解和促进环境发展的关键。对环境的体验和感知,目前学界取向于行为主义和人本主义两种角度。行为主义关注脱离情境的人的心理。人本主义强调情境中的主体经验和人与环境的交互。在两个取向下目前学术界分别从心理体验和社会生活体验展开研究。心理体验更倾向于幸福感体验、职业成功感、工作/生活满意度等方面的研究。社会生活体验关注的是“生活世界”的整体感受和体验(顾佩娅2016;丁瑜,2014)[13,17]。幸福感、职业成就感、工作/生活满意度作为积极心理学的一个重要指标,越来越受到诸多研究者的关注。姜淑梅以吉林省高等院校女教师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和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对其主观幸福感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并从人口学相关的各因素考查了可能对高校女教师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因素。研究发现,地区间的差异、不同院校类型、不同职称、不同学历等因素都会影响到女教师的主观幸福感。研究中对学校这个大环境建设的意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学校不仅肩负着为祖国培养实用性人才之使命,同时也承载着为社会培养有能力创造幸福感、职业成就感、工作/生活满意度的未来人才的义务(姜淑梅,2016)[18]。在此意义上,高师院校女教师职业使命感和未来人才的幸福感具有了统一性。同时,研究者看到高校女教师的工作-家庭平衡与主观感知和体验到的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喻轲,2017)[19],且工作-家庭平衡是有效预测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由此可见,工作-家庭环境是会影响到女教师主观幸福感受的。近年来,研究的生态学转向 (宋改敏2009)[20]就是女教师主体对环境感知、体验和回应的强调。女教师职业发展环境就是她们生活世界的重要组成,换句话说女教师感知和体验到的生活世界就是女教师职业生活和成长环境。是将“人-境”互动与发展放到更完整、更复杂的动态环境系统中去考察,努力建构“人-环境”复杂关系的生态本质(顾佩娅2016)[17]。朱依娜(2014)[21]研究发现女性在家庭中投入的时间通常多于男性,日均家务劳动时间女性为2.7小时,男性则为1.4小时,而在科研时间投入方面,女性教师投人科研的时间为2.7小时/日,显著少于男性教师的3.4小时,家务劳动时间对科研时间无形中产生一种挤占效应。女教师渴望在工作-家庭之间更好地调整和平衡,但有限的精力使平衡两者间关系变得如此的艰难,这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她们体验到的幸福感。因此,研究者指出每一项学术工作,都需要学者两种品质:很长时间和专心致志。无论是教学还是科研,无论是知识的传播抑或创造,都是一种高强度的脑力劳动,这种脑力劳动不仅对时间的跨度要求高,而且对时间的纯度要求也相当高(王俊,2011)[22]。时间这种资源在工作、家庭争夺中变的如黄金般稀缺。也有研究者发现女教师“一方面在证明自己的才能智慧,按照市场公平竞争的原则接受社会的挑战,与男性一样进行职业生存竞争的同时。另一方面,迎接高于传统的现代女性家庭角色标准的挑战,做丈夫的好妻子、孩子的好母亲、好朋友、好教师(杨小燕(2009),刘齐(2017))[23-24]。脑力劳动者双重角色冲突在现实环境中凸显了出来。女教师在“第一班”“第二班”“第三班”的工作中不得不成为“跷跷板上的女人”(佟新,2012;禹旭才,2012)。[4,25]
由此看来,研究者对关注女教师“生活世界”带来的整体感受和体验,平衡工作-家庭中女教师双重角色研究趋势愈见明朗。
四、高师院校女教师职业发展环境的期望
我们希望建构什么样的环境呢?学界也在不断追寻着路径。大多数研究者认为社会支持是缓解高校女教师工作家庭冲突的重要变量。社会支持在工作-高校教师-家庭冲突间与职业倦怠中发挥着缓解的作用(刘玲,2013;汤舒俊,2010)[26-27]。吴雅文在分析社会支持系统时侧重客观的社会支持系统和主观的社会支持系统两个方面的综合考虑。客观的社会支持系统主要来自外在的社会资源。主观社会支持主要是一种体验、可利用可获得的社会支持。同时研究者重视话语权的环境建设。认为话语是个人身份建构的来源,高校女教师代表着特殊的知识精英群体,她们的现实生活处境映射出的是一代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可向往的境遇,她们发出的“声音”如涟漪的水波,一圈一圈画出去。狄凌芳(2010)[28]从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初期,1990年代中期以来三个时期认识到高校女教师主体性从隐身和屏蔽的状态——一定程度的觉醒和凸现——建构的状态。但觉醒的同时在具体实践活动中仍不能摆脱充满父权制色彩的国家话语;在建构自己主体性在场的同时又充满着种种矛盾,无法完全摆脱男权话语束缚的困境。
这样看来,研究者聚焦社会支持这个重要的变量,但又感到力不从心。所以把研究视角转向女教师本身的“觉醒”,希望朝着在国家有力的社会支持体系下为自己赢得更具主动性而有力的话语权而努力的。
五、改善高师院校女教师职业发展环境对策
环境现状和环境适应之间的问题以及环境现状和环境期待之间的问题是学术界改善环境聚焦的关键点。研究者发现核心的问题是改善工作-家庭问题和消除社会性别隔离问题。
如何来改善工作-家庭问题,有“冲突论”“适应论”“平衡论”之说。在全球化压力下,工作和家庭的平衡成为全球性问题。佟新(2012)[25]相信工作的满足感和家庭生活的满足感来自于工作和家庭的平衡发展。喻轲(2017)[19]用滚雪球的抽样结合网络调查法,运用层次回归和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探讨工作家庭平衡、主观幸福感和留职意向之间的关系,同样发现高校女教师工作家庭平衡、主观幸福感和留职意愿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在平衡工作-家庭关系中学术界在做着各种各样的努力,从“家庭友好型政策”、“关怀理论”、提升妇女地位和权力等等方面研究。目前有一股新的趋势,研究者把研究的目光投向了男性。对“什么样的男人做家务”进行发问(刘爱玉,2015)[29]。推动男性家庭角色的改变(张亮,2014)[30]。让“男性和男孩促进性别公正”(方刚,2015)[31]。
综上,目前学界取向于行为主义和人本主义两种角度,对高校及其高师院校女教师环境发展现状、环境感受和体验、改善环境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但在此基础上,我们发现对于高师院校女教师环境因素的建构、环境理论研究视角、环境研究主题等方面研究存在不足。
第一,社会文化理论视角下建构心理体验和生活体验。人才工作环境绝不囿于人才本身,而是关注人才的活动范围。因此,高师院校女教师职业发展环境研究应该聚焦在宏观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影响下,从教师主体及其发展的社会性和交互性出发审视环境。将高师院校女教师与环境放在特定的情境中,在情境中理解高师院校女教师为全人的综合素质的心理关注。不仅能使我们重新审视传统的妇女与环境的静态探讨,描述地方高师院校的权力运作,还可以使我们更准确地理解“妇女/女性”“环境”和“发展”的相容性。
第二,同心圆结构中建构环境空间。家庭、学校与自我之间的多重关系是高师院校女教师生活的核心。她们在家庭、婚姻经验中交织着职业、教学、科研等的影响,承载着来源于家庭、婚姻、自我、性别方面千丝万缕的感悟。女教师在家庭和学校两个空间中的经验是互相联系、相互影响的。在家庭生活、教研工作中,在对他人与对自己的关怀、反思中发展的。环境的内涵深深地镶嵌在一组多个层级内嵌相连的同心圆结构中,以“我”为中心交织而成的个人环境、学校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如何在环境中建构出这种交织相容的环境?周新霞[15]研究发现工作-自我-家庭冲突主要基于时间和精神上的,并不受其行为的影响。这个研究提醒研究者在社会文化视角下来看高师院校女教师体验环境回应的意愿指向,从而指导在行为意愿的时间和情感上的冲突。这样高师院校女教师在工作时间上的投入不足并不能简单归咎于婚姻家庭的拖累(朱依娜,2014)[32]。不能总是把婚姻家庭当作负面因素与女性的职业联系在一起。需要我们重新回归高师院校女教师的日常生活,重新思考它所蕴含的文化能量,让生活品味出最真实的味道,在细细体验中收获愉悦的认可和享受的经验,成为教育革命的可能(丁瑜,2014)[13]。把高师院校女教师“我”生活体验,得以“内在而知”“内在而化”。
第三,双向互动建构环境主题目标。人是环境的一部分,环境和人是相容相生的。高师院校女教师与环境的互动及环境改善实践研究已经开始涌现,虽然女教师与环境的双向互动过程研究还没有形成研究的主流,但禹旭才(2010),顾佩娅(2017)等研究者已经在进一步加强、改善环境为目标的探索性实践中开辟出一条道路。
总之,高师院校女教师职业发展环境研究亟需深入发展。基于对已有文献研究前沿与动态的把握的基础上,生态女性主义视角是未来女教师研究的重要视角。保护与践行女教师解放与男女平等的运动。实践着一种新时代人文关怀的教师队伍整体发展的愿景,绘制着高师院校女教师职业发展环境研究的真正蓝图[33]。
——以大四公费师范生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