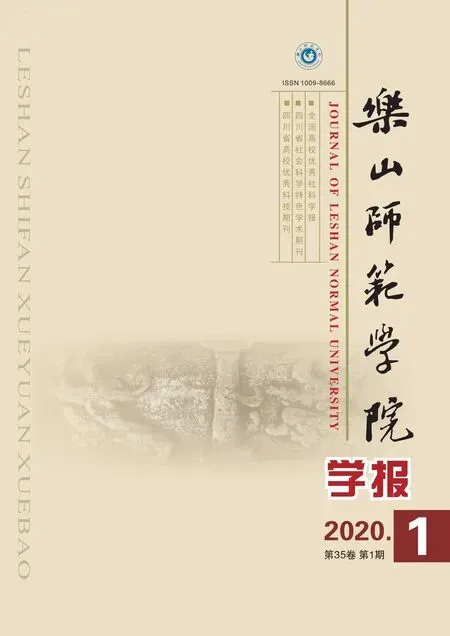论狄金森诗歌中独特的叙事视点
刘保安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基础教育学院 广东 广州 510507)
叙事视点(又称叙事视角或聚焦)是由美国现代小说家亨利·詹姆斯在他的《<淑女画像>序言》中提出的,是詹姆斯对其小说创作实践的高度概括和总结。詹姆斯追求小说的真实性, 他曾这样强调小说真实性的重要性:“予人以真实之感(细节刻画的翔实牢靠)是一部小说的至高无上的品质。”[1]15为了达到真实性,詹姆斯反对传统的第三人称全知叙事模式和第一人称回顾性叙事,主张作家隐退,提出要“最大限度地降低作家的叙事声音”[2]115。在传统小说中,小说家不仅是故事的讲述者,而且他们还会向读者详细地交代每一个细节。詹姆斯认为,为了降低小说家的叙述声音,增强小说的戏剧性,必须使“故事”自我上演。
“为此,詹姆斯主张小说家应该尽量采用小说人物的眼光,客观地展示处于人物‘观察下的现实’,使事物在人物意识屏幕上得到最丰富的投射。”[2]119唯有如此,小说家叙述的故事才具有真实性和客观性,才能有效地避免作家的介入。詹姆斯在小说创作实践中,经常采用人物有限叙事角度,创造了“意识中心”的叙事模式,即故事中的叙事者是故事中的一个人物。詹姆斯的叙事理论不仅颠覆了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而且为研究小说的叙事视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詹姆斯的叙事理论有效地助推了小说领域的叙事视点研究,然而,以詹姆斯的叙事理论研究诗歌叙事的成果则不多见。由于小说和诗歌都是文学表现形式,又由于19世纪美国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的许多诗具有小说的元素,如时间、背景、人物、故事情节、叙事者等,这为我们研究她的诗歌叙事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依据。同时,狄金森善于以弱势群体作为视点人物讲述故事,以此实现作家的成功隐退。这恰恰符合詹姆斯所倡导的降低作家的叙事声音,让故事中的人物讲述故事。我们知道,现代诗具有“去个人化”倾向。[3]22-24因为现代诗歌“往往离弃了诗人个人的自我”[3]3。狄金森在其诗歌中的隐退恰恰与现代诗歌吻合,因此,她的诗歌具有明显的现代性特征。狄金森的诗歌在很多方面都具有现代性,叙事手法仅仅是其诗歌现代性的一个方面,而詹姆斯的小说叙事理论则标志着现代小说叙事学的开始。笔者在此拟以詹姆斯的叙事视点理论为切入点探究狄金森诗歌中独特的叙事视点,旨在拓展狄金森诗歌叙事艺术研究的内涵。
非连续性文本短小精悍,带给我们获取信息、处理信息、评价信息的无限可能性。非连续性文本资源的开发,是学生阅读方式的崭新途径。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虽以连续性文本为主,但可充分利用教材中隐藏的非连续性资源进行适度开发,使之发挥语文教学更大的功效。
第一部分是评估函数,确定局部最优情况,最终确定的评估函数算法有两种:一是局部进行评分的算法,在此称为局部最优得分算法;一是尽量贴近最优情况阵型的算法,称为局部最优矩阵算法。
一、儿童视点
狄金森诗第45首、185首、186首、215首、285首、288首、413首、613首等都是以儿童作为视点人物。狄金森善于以儿童作为视点人物,描写宗教对人的压抑(J.215;J.413),展现父权重压之下的小女孩的心境(J.613),展现儿童独特的认知(J.45)等。詹姆斯强调小说存在的理由是表现生活:“一部小说之所以存在,其唯一的理由是就是它确实试图表现生活。”[1]5狄金森诗歌的强有力的存在也依赖对(儿童)生活的展现。诗第45首就是以儿童视点叙事,展现儿童与成年人认知的不同。因为诗中的叙述者“我”年幼无知,所以“我”以为躺在房间里的孩子是在沉睡,事实上,这个孩子早已经死去。在孩子的认识范围内,没有死亡的概念,仅有睡觉的概念。因此,“我”对成年人在房间内营造出的简单而又庄重(simple gravity)的氛围根本无法理解。诗第251首中的小女孩眼巴巴地望着篱笆那边甜蜜的草莓,却不敢翻越篱笆去采摘草莓,因为她怕受到上帝的责骂。诗人以小女孩为视点揭露了宗教对人的压抑。狄金森以儿童视角对代表基督教的上帝予以批判,不会引起主流社会的关注。某种意义上,以儿童视点叙事是诗人一种“自保”的艺术策略。诗第413首以小女孩的口吻直接呈现出对天堂和上帝的厌倦,而且这种表述是以现实主义的笔法呈现出来的。狄金森以小女孩的口吻,批判象征基督教的上帝对人类言行的束缚和压抑,展现诗人对自由的渴望和追求。人类一直处在上帝的监控之下,宗教对人的压抑令人窒息,人们似乎永远难以躲开上帝的视线,即使他出门访友或是午睡都在监视着人类的行为。即便是人们躲开他,最终也躲不开“末日审判”。诗人将批评的锋芒直指天堂和上帝:“在下界,我从不感到自在——/在富丽堂皇的天上——/我知道,也不会觉得舒畅——/我,并不喜欢天堂——//因为那里永远是礼拜的日子——/假期,永不来到——/伊甸园一定像清朗的星期三下午——/那样寂寞、无聊//如果上帝能够出门访友——/或是午睡一个时辰——/以至看不见我们,但是据说/他自己就是望远镜——//我们长年在他眼底——/我宁愿逃得很远很远/躲开他,躲开圣灵和一切——/但是,还有‘末日审判’的一天!”(J.413)[4]122-123
二、女性视点
狄金森以女性视点真实地展现了19世纪的历史文化语境,这恰恰符合詹姆斯所说的“小说就是历史”[1]6。詹姆斯“将小说与历史并举,与其说是为了申述小说的‘真实性’,倒不如说是为了强调小说与历史在表述行为上有异曲同工之妙。从这个角度看,詹姆斯探讨的问题就远远不只是小说与生活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是在探讨一种叙事技巧,它能够使虚构的艺术世界与客观世界形成一种张力,使杂乱无章的现实在井然有序的艺术面前显现出某种程度的妥协。”[2]105可见,詹姆斯试图将生活与艺术(小说)融为一体,以确立小说的真实性,即将小说艺术提高到生活的层面,以此达到小说所展现的内容的真实性。既然小说就是历史,具有真实性,那么,诗歌也是历史,也具有真实性。
诗692首对于死者的眼睛的描述是从临终人的视角讲述的。人之将死,其视觉功能正在逐渐丧失。尽管诗中人看到太阳一直在不断地下落,但是却怎么也看不到午后的色彩;尽管诗中人看到暮色不断地降临,但是怎么也看不到草叶上的露珠。他的视线是如此有限,最后他看到的仅仅是光线的消失,不过他很快意识正在消失的不是光线,而是自我。狄金森以临终人的视点讲述故事,对将死之人的状况进行了细致入微而且十分生动的描述:“太阳不断下落,下落,却仍然/不见午后的色彩——/从村落的光景我知道,/是中午移动在屋脊之间——//暮色不断滴落,滴落,却仍然/不见草叶上有露珠——/只是停在我的额头/沿着脸颊流注——//双脚不断困倦,困倦,却仍然/有我的手指清醒——/可是为什么由内心向外/奏不出什么声音——//我以往对光何等熟知——/我现在还能看到——/它正在死去,我也一样,但是/我并不害怕知道——”(J.692)[4]205-206
狄金森的一些诗歌以女性作为叙事视点。狄金森常常以女性的口吻展现女性初为人妻的狂喜、不安、焦虑、怀疑等复杂心情,描绘女性对爱情的渴望和忠贞,对幸福婚姻的向往,呈现女性的孤独、恐惧、痛苦、压抑等,揭露男尊女卑的社会现实,展现女性在男性面前的羞怯和卑微,再现自己对自由的向往和男女平等的思想等。狄金森以女性为视点的诗歌向读者展现了女性的复杂的内心世界。诗第493首就是如此:“世界——对我——显得——更加庄严——/从我跟他结婚的时候——算起——/一种谦虚适合灵魂/却具有另一个人的——名字——/一种怀疑——是不是戴上那完美的——珍珠——/就确实——美丽——/男人——跟女人——结合——/永远——要抱紧她的灵魂——/一声祈祷,愿它证明——更具天使品质——/一种更加洁白的礼物——在心里头里——/送给那种慷慨,因为选择了——/这么一个不事修饰的——王后——/一种感谢——是那样真实——/它早以为梦寐——/太美丽——形状难以证实——/姿态——无法赎回!”(No.493)[5]353-354这首诗展现的是初为人妻的“她”对婚姻的严肃思考。结婚对于女性是极其庄严的,诗中使用“五个名词总结了她的反应:‘谦虚’‘疑惑’‘祈祷’‘礼物’和‘感激’,说明她为美梦成真感到惊喜和激动,同时认为自己有责任做一个称职的妻子。”[6]50由于19世纪美国的大多数女性在经济上不能独立,因此,她们婚前依赖父母,婚后依靠丈夫。故而,婚姻成了女性的追求和寄托。当她们迈进婚姻的殿堂时,她们自然是又惊又喜。诗人将名词天使(angel)化为形容词有助于将祈祷(a prayer)与诗中所突出的其他几个名词谦虚(a modesty)、疑惑(a doubt)、礼物(a gift)、感激(a gratitude)构成并列,并有效地集中突出“她”成为妻子时复杂的内心世界。谦虚指即将成为人妻的“她”认为,只有自己具有谦卑的品德才能配得上丈夫的姓氏,疑惑指诗中的妻子怀疑自己是否值得丈夫如此深爱。祈祷指对幸福婚姻生活的祈祷,也可以指婚礼上庄严的祈祷仪式。礼物指诗中的“她”发誓努力做一个合格的妻子以配得上丈夫给自己如此厚重的礼物,感激指诗中的“她”感激丈夫选择自己做妻子。
三、死者的视点
狄金森诗第280首以死者为叙事视点,展现了诗中人对葬礼的体认和感受。诗人以死者(诗中人)和生者(准备葬礼和参加葬礼的人)对葬礼不同的认知形成鲜明的对照。死者躺在棺材中,听见人们为他举行葬礼仪式,听到人们为他送行,最后把他的棺材放入墓穴里。死者认为,葬礼是对死者的折磨和煎熬,生者不应该强加给死者这样的葬礼,生者应该让死者的灵魂得到安息。而活着的人则认为,隆重的葬礼既凸显了死者的身份和高贵,又能体现生者对死者的敬意。事实上,诗人间接地提出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善待生者?作为生者,我们应该如何幸福地生活?人死后,无论葬礼多么隆重、显赫也是毫无价值和意义的。与其说葬礼是为死者举行的,还不如说是为生者或者是为了做给生者看而已。诗人这样写道:“我觉得一场葬礼,在我的脑海举行,/吊丧的人来来往往/不停地踩踏——踩踏——最后/好像感觉在突围一样——//人们统统落座之后,/仪式,犹如一面鼓——/不停地敲击——敲击——直到/我觉得神志就要麻木——//然后我听见他们抬起一个盒子/嘎吱嘎吱穿过我的灵魂/又用的是同样的铅靴,/然后空中——响起了钟声,//如果九重天是一口钟,/生命,只不过是一只耳朵,/我,沉默,则是奇族异种/在这里,落难,寂寞——//然后一块木板在理性中,断裂,/我就向下坠落,坠落——/每一个,撞击一个世界,/然后——知觉覆没——”(J.280)[5]193-194
诗第461首以女性的视点叙述自己将由少女成为人妻的感受。诗中人将自己即将成为妻子描绘为向胜利的挺进,这充分展现出诗中人将婚姻视为快乐的心境。诗第303首展现的是女性对爱情的忠贞,一旦“她”选定自己的心上人,她的心扉将对包括王公贵族在内的所有人关闭。诗第246首以女性的视点叙述女子仅仅是男性的一部分和女性对男性的绝对服从。女性只有承受生活中悲伤的义务,没有享受欢乐的权利;而在面对欢乐时,女性则把所有的快乐都让给男性去享受。诗第723首写女性婚后作为妻子要迎合丈夫的需求不得不牺牲自己的一切。她应该遵循的规矩到底有多少,她自己也全然不知晓。诗第24首写在没有男性的世界里,女性可以尽情享受欢乐,与大自然为伍,让美丽的时光常驻。此诗再现了诗人对自由的向往之情。诗第576首以女性的口吻讲述自己还是个小女孩时被逼做祈祷的情景。第106首揭露男权社会之下女性对男性的依附,没有男性女性简直无法生存。
四、失败者的视点
狄金森诗第639首以战败士兵的视点展现他对战争的感受。战败的士兵认为,他们战败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运气不好,是命中注定的。这个士兵坚信,嘹亮的凯歌和隆隆的战鼓不属于失败者,而属于胜利者。“今天——我的命数就是失败——/一种运气比胜利还要苍白——/更微弱的凯歌——更稀少的钟声——/战败并不敲着鼓点——把我追随——/失败——一种更加缓慢的现象——含义/比炮弹更加有劲——”[5]120-121这首诗的第二诗节以战败士兵的视点呈现出残酷的战争场面:士兵的鲜血在地上流淌,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瞬间化为灰烬,随处可见战死的士兵的尸体,到处可以听见受伤士兵的呻吟声、叹息声、祈祷声,还有那些年轻的士兵茫然的神色。诗人借战败士兵的口吻展现出自己对战争的憎恶,对和平的向往。这首诗的第二诗节这样写道:“这里到处是骨头和污点——/战士们太直,腰不能再弯,/还要一堆堆硬实的哀怨——/还有一片片茫然——表现在稚气的眼里——/还有支离破碎的祈祷——/以及死亡的惊奇,/在石头里——打下的印记可见——”[5]121狄金森一生笔耕不缀,尽管关于她有生之年仅发表过若干首诗的原因有多种说法,甚至有人说她不愿发表自己的作品,但是无论如何她也曾渴望过发表,追求过功名。但是,她最终在世时候也没有取得任何功名。因此,作为失败者,她曾经希望自己的作品得到出版;作为失败者,她对成功的渴望和描述是真切的。这是狄金森对生活的真切印象:这恰恰符合詹姆斯所说的:“一部小说是一种个人的、直接的对生活的印象”。[1]10狄金森以一个战败士兵作为叙事视点,远比以作者的口吻叙事可信度高,而且更具有说服力。这一叙事视点不仅赋予故事真实性,而且使故事具有客观性。
五、饱受痛苦者的视点
狄金森是最权威的痛苦阐释者。她因隐居生活和终生未嫁饱受孤独之苦,又因失败爱情的打击和反对权威反对宗教她还必须默默地承受着极大的精神压力,内心充满无限的忧伤和痛苦。她别出匠心地将痛苦赋予诗中人,以饱受痛苦者的视角阐释对痛苦的感受,对痛苦的诠释具有真实性和客观性,这恰恰符合詹姆斯所说的:“除非你具有真实的感觉,否则你就不会写出一部好小说来。”[1]13狄金森对极度痛苦的阐释入木三分:“我爱看痛苦的表情,/因为我知道它真实——/人们不能佯作剧痛/也不能,假装惊厥——//目光一旦呆滞,就是死——/人们无法伪造出/由衷的痛苦在额头/串起的一颗颗汗珠。”(J.241)[4]67狄金森对痛苦有着深切的体验。她认为,痛苦给人的感觉是惊厥、目光呆滞和额头上的一颗颗汗珠。因为痛苦是真实的,所以人们无法佯装。诗第708首的叙事者坦言,当巨大的痛苦把人折磨到极点使人难以忍受时,当厄运一直缠绕着,当黑暗似乎永远没有尽头时,一时就会有轻生的念头,直接想到天堂去品尝快乐的滋味。诗第768首展现的是“我”对过去的回忆。“我”回想起:当“我”内心充满希望时,在寒冷的天气里丝毫感受不到严寒,“冻雨不能把我刺伤——/严霜无法让我寒冷——/正是希望使我保持温暖——/而不是美利奴羊毛披巾——”(J.768)[5]209;当“我”处于恐惧之中时,即使是阳光普照也感到全身发冷:“我灵魂上的冰柱/刺得人又紫又冷——/鸟儿到处飞翔赞扬——/只有我——动不动”(J.768)[5]209-210;而绝望的折磨给“我”的感觉恰似落山的太阳,黑暗遮蔽了白昼的脸庞,挡住了她的视线;世界处于一片黑暗之中,黑夜笼罩着大地上的每一个角落。诗中人这样讲述绝望的折磨:“那是夜晚/太阳已经沉没——/黑暗横亘她的脸庞——/并且罩住了她的视线——/大自然迟疑不决——在/记忆和我面前——”(J.768)[5]210诗人以“我”为视点,通过“我”将希望与绝望的对比,强调了希望与绝望的极大差异,有效地展现了痛苦对“我”的折磨。狄金森通过描写痛苦展现了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和追求,并以此唤起读者对美好生活的热爱。
溃疡程度评价方法:0分为无缺损;1分为溃疡面积最长直径<2 mm;2分为最长直径2~5 mm;3分为最长直径6~8 mm;4分为最长直径>9 mm;5分为溃疡穿孔。
狄金森在19世纪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开创了诗歌独特的叙事方式。她所创造的独特人物视点是她对诗歌艺术不懈追求的结晶。狄金森以被边缘化的人物作为叙事视点既完成了作者的成功隐退,又展现了自己对社会、人生、宗教、男权社会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思考。实际上,她特意选择的这些弱势群体中的人物作为视点人物为自己的诗歌披上了面纱。弱势群体属于非主流群体,这些人处于社会的边缘地带,他们的言行常常被主流群体或主流社会所忽视。因此,狄金森把这些人物作为视点的中心人物便于她自由地、无所顾忌地挑战传统、习俗和主流文化。同时,狄金森把这些人物作为视点人物,以唤起主流社会对他们的关注。从这个意义上讲,狄金森诗歌展现的是对人类生存状况和人类前途命运的关切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