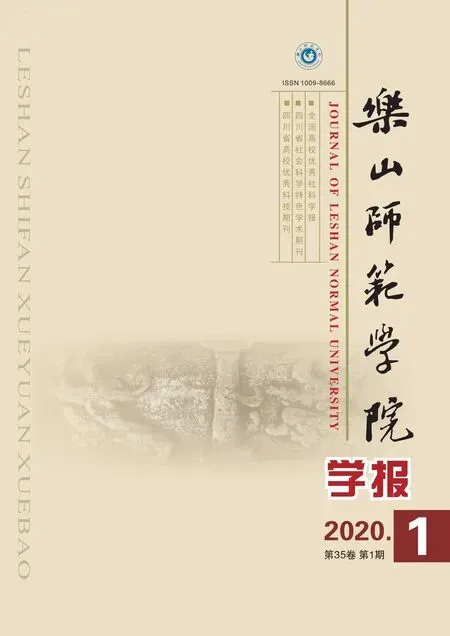苏轼笔记对高丽朝李奎报散文创作的影响
金 欢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清代姚鼐在《古文辞类纂》中将散文分为论辩、奏议、诏令、传状、杂记、书说等十三类,苏轼、李奎报散文也涵盖上述内容。鉴于研究需要,笔者以苏轼散文中相对短小精悍、具有杂谈琐语性质的随笔体为主进行探讨。李奎报《东国李相国集》中近乎一半属于奏议、诏令、传状等公牍类散文,与苏轼笔记的相关性不强,笔者除个别篇章外,不作详细阐释,而主要以论辩、杂记、书说等为依据,并结合诗话作品《白云小说》来探究李奎报散文对苏轼笔记的接受。
一、苏轼与李奎报相关研究综述
李奎报(1168—1241),字春卿,号白云居士,高丽朝中后期文学家,著有《东国李相国集》四十一卷、《东国李相国后集》十二卷,以及被誉为高丽四部诗话之一的《白云小说》。
关于苏轼与韩国文学的研究,樊葵《论同源文化间传播的选择性——以高丽对中国文学的受容为例》[1]指出,对高丽初中期文学影响最大的中国文人中就包含了苏轼,其圆融达观的人生态度成为高丽文人向往的典范。崔雄权的《苏轼与韩国汉诗风的转换与诗学价值选择》[2]一文表示,苏轼及其诗歌的东传改变了新罗末、高丽前期晚唐诗风的统治地位,带来了韩国汉诗风的“变革”。
除了对苏轼与整个韩国文学宏观把握外,李红燕《高丽中期苏东坡热与陶渊明文学的接受——以李仁老、陈华、李奎报为中心》[3]将其与具体文人李奎报联系起来。韩国学者柳基荣较早关注了苏轼词与韩国词作的关系,并详细论述了李奎报对苏轼词形式要素的承传。
综上,研究者们已关注了苏轼与韩国文学、苏轼与李奎报的联系,但就诗话而言,鲜有对二人作探讨,而是倾向于研究欧阳修诗话、笔记对韩国诗话的影响。马金科《<六一诗话>与高丽诗话<破闲集>之比较》[4]认为,李仁老的《破闲集》能动地接受了欧阳修诗歌“用韵”、知人论诗的批评方法,但也提出了符合朝鲜政治、文化环境的主张。李银珍在《宋代笔记研究》[5]一文中以崔滋、徐居正所引《归田录》为例,考察了韩国笔记接受宋代笔记的痕迹。李奎报在其文集中多次提及苏轼,《全州牧新雕东坡文跋尾》言:“每个时期无数个文集问世,各有崇尚之作,但自古以来盛行的上乘之作就属《东坡集》。”[6]358-360
在此基础上,本文拟对苏轼笔记与李奎报散文予以探讨。然而,目前把李奎报散文与中国文学相结合的研究不多,对苏轼笔记与高丽文学进行影响研究的也寥寥可数,这使得笔者在整理资料时,可学习和借鉴的思路比较有限。因此,本文的立意、论证存在一定的不足,希望有更多的研究者将笔记与高丽诗话予以结合,对研究宋代笔记有所裨益。
二、苏轼笔记对李奎报诗话创作的影响
高丽诗话作为高丽文学的代表,与宋诗话的艺术形态和写作范式呈现出一定的关联性。李奎报的《白云小说》作为高丽四部诗话之一,在一定程度上也接受了宋诗话、笔记的影响。
(一)宋诗话、笔记和高丽“稗说体”的关联性
“诗话”一词首次出现,见于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其给予“诗话”的含义是“以资闲谈”,即寓诗论于闲谈述事之中,不仅对诗人、诗派进行评论,还对典故等展开论述,进而形成一种“闲谈”的随笔体式。宋代除了诗话,还有一种常见的散文文体,即笔记体,它也是一种随笔而录,杂谈琐语性质的散文,“其特点是内容广泛,遇有可写,随笔而书,可长可短,不拘形式。”[7]462宋代诗话、笔记作为杂谈性质的随笔,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郭绍虞就曾指出,论诗的风气之所以如此流行,最大的原因就是诗话逐渐笔记化。
高丽中期以后,出现了一种被历来文学家称之为“稗说体”的论诗之作,即高丽诗话。因为是“稗说体”,所以并不专注论诗,而重在记述文人感兴趣的一切琐事、传闻以及故事等,进而形成了一种“杂录文学”。高丽诗话取名为小说、破闲、补闲等,直接继承了欧阳修所开创的宋诗话“以资闲谈”的特点,形成了一种“闲谈”的随笔体式。因此,与其说高丽诗话是诗话专集,倒不如说是杂著更为准确一些。
《白云小说》作为高丽四部诗话之一,也明显地体现出杂著化的特点。“小说者流,盖出于稗官。”[8]24“小说”二字对文体作了更准确的诠释。这里的“稗官”是为统治阶级搜集街巷细碎之语的“小官”。李奎报将其诗话取名为《白云小说》,可见其内容何其冗杂。
(二)李奎报对苏轼诗论的接受
苏轼评论古代先贤的诗作,在押韵、炼字及表情达意上有自己的标准,期望达到一种语、意完美融合的艺术境界。他在《仇池笔记·记游庐山》中评价李白《望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不仅展现了庐山瀑布宏伟的气象,而且炼字精准,对其极力称赞;与此形成对比,评价徐凝的《庐山瀑布》诗,“飞流溅沫知多少,不与徐凝洗恶诗”[9]8。在苏轼的审美体验下,徐凝诗用词直白,只状写瀑布之形态,未道出瀑布之神韵,境界不开阔,因此称其为“恶”。
李奎报在《白云小说》第十五则中对徐凝写诗,苏轼论诗也进行了评述。他认为:“徐凝《瀑布》诗歌‘一条界破清山色’则余拟其佳句,然东坡以为恶诗。由此观之,余辈之知诗,其不及古人远矣。”[6]53李奎报基本沿袭了苏轼的诗论理念,他对徐凝《庐山瀑布》诗的理解也由此而来。
在新罗末,随着崔致远的归国,给高丽带来了浓厚的晚唐诗风。当然,这种时代气息也笼罩着宋初诗坛,“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王黄洲学白乐天,杨文公、刘中山学李商隐,盛文肃学韦苏州,欧阳公学韩退之古诗,梅尧臣学唐人平淡处。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亦”。[10]181严羽认为,宋诗坛学唐之风随着苏轼的“自出己意为诗”而得以改变。由此推之,苏轼对于高丽诗坛的影响之深、之广。有学者认为,苏轼及其诗歌的东传,“带来了韩国汉诗风的第一次‘变革’,形成了苏轼在韩国古代文人与汉诗中的独特地位,其影响持续到朝鲜朝前期”。[2]142同时,李奎报也深感自己才学尚浅,在评论古人诗作时与大文豪苏轼差距尚远。在李奎报看来,欲学苏轼诗风,必先读其书籍,后得以仿之。“语意得双美,含蓄意苟深,咀嚼味愈粹”。[6]89李奎报在创作诗歌时强调“语”和“意”的双美,在论诗时,也坚持这一原则,提倡表达的含蓄性,并认为只有达到此境界,才能使意深而味粹。
“帝遣银河一派垂,古来惟有谪仙辞。”[9]8苏轼高度赞扬李白诗所描绘的壮丽气势,称其为“谪仙辞”。
李奎报在《读李白诗》中也言:
呼作谪仙人,狂客贺知章。降从天来得见否?贺老此语类荒唐。及看诗中语,岂是出自人喉吭。名若不书绛药阙,口若未吸丹霞浆。千磨百錬虽欲仿,其体,安可吐出翰林锦绣之肝肠?皇唐富文士,角攫各专场。前有子昂后韩柳,又有孟郊、张籍喧蜩螗。岂无语宏肆?岂无词倔强?岂无体夺春葩丽?岂无深到江流汪?如此飘然格外语,非白谁能当?虽不见乘銮驾鹤,去来三清态,已似寥廓凌云翔。所以呼谪仙,贺老非真狂。[6]53-54
“谪仙”的字面意思是被贬谪的仙人。起先李白在《玉壶吟》中称汉文学家东方朔为“谪仙”。贺知章在读完《蜀道难》后称李白为“谪仙人”。对此,李奎报认为“狂客贺知章”“此语类荒唐”,但品读完李白诗,不禁感叹其“语宏肆”,“词倔强”,是陈子昂、韩柳等文人所不能及的。因此,李奎报赞叹贺老“非真狂”,他对李白其人、其诗的评价是可信的。苏轼称李白诗为“谪仙辞”,李奎报也赞李白是被贬谪的仙人,二人在李白的评价问题上具有了一致性。
三、苏轼笔记对李奎报史论创作的影响
一般情况下,评定史论主要根据历史事实。然而,苏轼《东坡志林》中的十三篇史论,均先引用或转述史实,然后以“苏子曰”展开议论。可以说,苏轼并不是完全依靠冷静客观的思考,而是凭借一时的感受作史评,所以主观色彩浓厚。面对内政腐朽、外患频繁的时代,李奎报在一定程度上也借鉴了苏轼善于抒发自身独到见解的这一特点。
(一)天意之难违
《东坡志林》史论第一篇为《武王非圣人》。苏轼对周武王攻打殷商,诛杀纣王,篡夺江山的行为作出了批判。即使纣王暴虐无道,殷商统治天下六百年,先代明君的遗风并没有退去,因此,武王的篡位违背了天意。
笔者了解到,多数学者认为,苏轼对于武王标新立异的见解,在某种程度上有些无中生有,并没有按照史家严谨务实的标准去衡量,所以很难欣然接受。南宋朱熹说:“苏氏用三五百字骂武王非,则非矣。”[11]910但也有学者予以称赞,金圣叹评点“武王非圣人也”一句,“劈空落大笔,发怪论,不怕天雷,不怕王法。妙,妙。”[12]
虽然苏轼、李奎报所生活的朝代不同,但二人对历史的深刻反思是一致的。另一方面,李奎报与苏轼一样,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史学家,他在评价中国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时,难免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
对于秦始皇“焚书坑儒”,我们很大程度上会认为其凶狠残暴,但李奎报“秦始皇坑儒生焚诗书,而以周易为卜巫之书,独不焚之。予以为此天下之意也,非秦皇之意也……易者,生于天者也。始皇如果焚烧,就是灭天地之道”[6]543-545却认为《易》是天地所赐,汲取天地的精华,比五经更加地有智慧,所以只能坑儒生、焚诗书以顺应天意。
(二)君主之无能
君臣关系作为维护统治的重要武器,自古以来受到了历代君王的格外重视。然而,和谐友好的君臣关系,不仅仅是臣子单方面的遵守君臣之纲,还要求君主给予臣子足够的信任。倘若,君主不听逆耳忠言,一味猜疑,甚至动了杀人的欲望,其统治的国家也是难以长久发展的。苏轼在《东坡志林·七德八戒》中认为唐朝的衰败并不仅仅因为安禄山,还在于唐明皇错用了李林甫和杨国忠等奸臣。因此,安禄山即使有罪过,也罪不至死。接着,苏轼又从反面论证,列举了汉景帝“以鞅鞅而杀周亚夫”、曹操“以名重而杀孔融”等历史事实,批判这些君主或生性怯弱,或听信谗言,进而杀害无辜忠良。
李奎报也创作了《屈原不宜死论》《为晁错雪冤论》等为忠良鸣不平的作品。在《屈原不宜死论》中,李奎报先以比干谏言,反被纣王诛杀而称其“杀身成仁”,又以武王伐纣,伯夷、叔齐谏言失败,耻居首阳山而称其“杀身成节”;并进一步展开议论,纣王早已被众人深恶痛绝,比干之死并不能加重其罪行;武王称王有功于天下,这种恩惠不会因伯夷、叔齐的被杀有所减少。“若楚之屈原,举异于是,死不得其所,只已显君之恶耳。”[6]387-390屈原与比干、孤竹二子之死,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前者加重了楚怀王的罪行。《史记·屈原传赞》中评论说,楚怀王不识忠臣,被内外的郑袖和张仪所蒙骗,疏远屈原,听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最终不仅亡国,还葬身秦地,被天下人所耻笑。李奎报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屈原的怜爱,对上官大夫尹子兰、楚襄王等佞人奸臣的痛恨。
(三)史官之不公
除了评论“天意之难违”“君主之无能”,苏轼也对史官修书进行了评价。在《东坡志林·司马迁二大罪》中,苏轼严厉地批评了司马迁,认为其有两大罪过:一是“先黄老后六经,退处士进奸雄”;二是“论商鞅、桑弘羊之功也”。[9]171秦国的富强不能归功于商鞅的变法,反而后来的暴政是由其造成的。司马迁对商鞅的歌功颂德,苏轼是极为不赞同的,秦朝的灭亡到底应该归罪于谁?“仁义不施而攻守至势异也。”尽管也有专家认为贾谊的这番评价“文字甚妙,但非至当之论”[14]77,但起码我们也能得到一个启示,秦国的灭亡并不如苏轼所言,是区区一个商鞅能完全左右的。
“班固之笔,疑有不公焉。”[6]376-379李奎报在审视中国历史时,也尝试着对史官评史进行深入的思考。班固认为韩信“诈力成功”;李奎报则称韩信献策为奇计,并非“诈”。司马迁在《史记·淮阴侯列传》中引韩信所言,汉王有恩于他,待其不薄。韩信作为汉王的臣子,对于汉王的赏赐是心怀感恩的,不忍违背,待其被斩,才悔恨当初,未听献计,惨遭被骗。李奎报的这番辩驳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阐述了班固评史的不公,表达了对韩信的同情,值得我们深思。
(四)夷狄之难防
苏轼《东坡志林》卷三中有一个主题是“夷狄”,有两篇为《高丽》《高丽公案》。在《高丽》中,苏轼将东夷、南蛮等夷狄称之为胡孙,叙述高丽将大宋朝的赠礼视作赝品,当场拆分……苏轼在塑造高丽人时,并没有完全再现镜子般的他者形象,而是加入了自身的思想情感,从而意识到凭借高丽来牵制北虏的愿望恐怕会受到影响。
朝鲜半岛,山河锦绣,物产丰富,自古即为外族异邦所凯觑,所以高丽被夷狄欺压,需要朝贡。“且小国动事大邦,犹恐不尽其诚……以献大国之心乎。然物之有无丰瘠,係子风土。我国本介居山谷间……虽有所产,例皆粗品,殊不合上国之用。”[6]55-56李奎报诚挚地解释了本国的实际情况,委婉地表达了歉意。在《蒙古兵马大元帅幕送酒果书》中,他又一次为国家遭受契丹侵扰,十分惶恐,所以真诚上书蒙古元帅,希望得到援助。文中,李奎报将蒙古兵马大元帅尊称为元帅“阁下”,将高丽称为“小邦”,而将入侵者贬低为“贼寇”“倭寇”,认为蒙古国大义凛然,其“邦扶弱恤隣之义”是高丽小国万世难遇的幸运。
四、苏轼笔记对李奎报游记创作的影响
苏轼贬官期间,非常喜欢陶潜,创作了大量的“和陶诗”;李奎报也说:“善爱陶渊明,达语淡而粹。常捉无弦琴,其诗一如此。读诗想见人,千载仰高义。”[1]64-65可以看出,他们有着积极豁达的胸怀,十分向往无所牵挂、自由自在的生活。与陶渊明不同的是,二人作为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的士大夫,起初身列高官,议论国政,后遭小人陷害被贬,不能立身朝廷辅佐君王。尽管如此,他们对儒家的出仕仍然有着强烈的愿望。
(一)“经世济民”的出仕抱负
“结发事文史,俯仰六十余。老马不耐放,长鸣思服舆。”[14]2281在苏轼的仕宦生涯中,始终贯穿儒家的理想和“经世济民”的出仕抱负,即使后来被贬惠州,赴任途中,他也是“所在撰书、易、论语,皆以自随”。他有着文人与士人的双重身份,心忧天下,一直在努力实践一个儒士的社会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
李奎报从九岁起就阅读中国儒家经典,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作一生的抱负,晚年的他更是忧国而彻夜不眠。他的作品风格慷慨悲壮,激越豪放,始终饱含着爱国爱民的思想感情。《白云小说》第九则,李奎报批评了以李仁老为中心的“海左七贤”,认为这些人或是政治上的失意者,多次科举而落榜,或是榜上有名而官位较低,但无论哪种,都往往自命清高而无所作为。通过批判这些人,李奎报进一步表明自己出仕的强烈愿望。他对做官表示肯定和赞赏,甚至认为“官”是实现“道”的工具,只有身居一定的官职,才能发现利国利民的真正的“道”。
(二)“随遇而安”的处世态度
经历了宦海浮沉,苏轼晚年能豁达地看待人生得失了。这种处世态度在《记游松风亭》一文中有所体现:“余尝寓居惠州嘉佑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林止息……由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9]9试想,诗人何尝不是忽得解脱的“挂钩之鱼”?又如《儋耳夜书》:“己卯上元,余在儋耳……步城西,入僧舍……归舍已三鼓矣。舍中掩关熟寝,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为得失?……然亦笑韩退之钓鱼,无得,更欲远去,不知钓者未必得大鱼也。”[9]10诗人用韩愈钓鱼不懂随缘自适的典故反衬自己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这无疑让我们感慨,人生的很多事情都无恒定的得失标准,所谓钓得大鱼之乐未必就优于钓得小鱼之乐。
李奎报自号为“白云”,并且详细描述了白云的形态:“不滞于山,不系于天,飘飘乎东西,形迹无所拘也。变化于顷刻,端倪莫可涯也;油然而舒,君子之出也;敛然而卷,高人之隐也。”[6]311-314
苏轼自比为忽得解脱的“挂钩之鱼”,李奎报用形迹无拘束的白云来表达摆脱牵制得以超脱的自由心境,二者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李奎报由苏轼的诗文进而了解和学习他的为人,并从中寻找磨砺自身诗文和思想的动力。因此,苏轼笔记不仅对李奎报诗评、史论、游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还作为一面镜子,透过它,可以窥探二者的人生遭际、理想抱负,甚至可以映射出二者所生活的时代背景。
苏轼与李奎报的人生经历恰好是那个时代文人命运的共同写照。我们透过个体,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对宋以及高丽的社会背景予以对比分析,这为研究中国与朝鲜半岛的文化交流起到了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