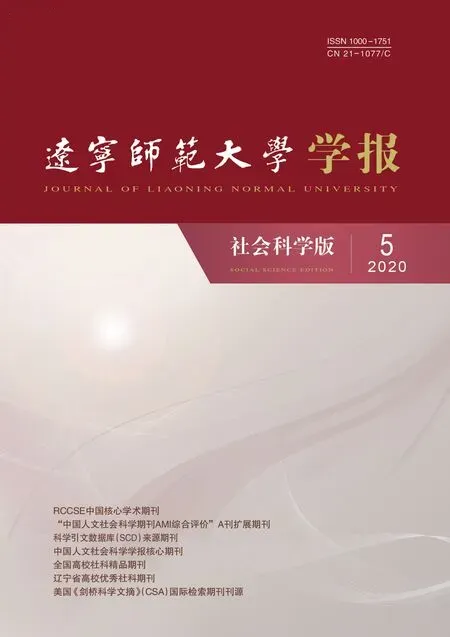“五四”作家许地山“异域性”的诗意书写
宁 芳
(辽宁师范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9)
在文学的视域里,“异域”总是给人无限遐想。异域空间的风光旖旎,热情奔放,如梦如幻,浪漫神秘……语言难以穷极。诚然,不同的历史和时代,异域所形成的想象空间,也有着不一样的心理体验。从某种程度上说,作品中的“异域”折射着现实、历史和文化的影子,也兼容并蓄地呈现着生活和生命相互交融的意蕴和诗性活力。同时,不同时期的作品,“异域”所对应的地理空间,也有不同的倾向性,充满了个性的风貌。“五四”初期,由于当时很多知识分子从欧美、日本留学归来,所以,他们创作中的“异域”书写更多的是表现在东洋和西洋的主题上。许地山则是中国现代作家中最早写东南亚风情的作家,他的小说《命命鸟》被称为“新文学第一篇充满异域情调的作品”。其后,他又接连创作出《商人妇》《缀网劳蛛》《海角底孤星》《醍醐天女》等东南亚风情浓郁的作品。这种“异域色彩”“异域情调”,已经成为许地山有别于其他一些现代作家创作的独特之处,成为具有“许地山印记和色彩”的想象文本。但是,许地山真正的与众不同,更多的则在于他对“异域”题材的处理方式、富于个性化的审美方式,以及他对异域文化的吸收和运用。在充满“异域”性的感受中,许地山舒展开个人和生命的精神肌理,唤醒了其间意味深长、耐人寻味的现实沉寂,呈现出深厚的情感隐喻和人生底蕴,并赋予了异域以真实的情境和迥异的意象。
异域文化对于个人的影响会有很多方式,大致可以分为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从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被迫打开之后,外国的文化就源源不断地输入,不论是西方国家强性地殖化,还是中国自己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动接纳,近代中国的文化、教育、生活都受到了“西洋”“东洋”文化的影响。许地山的出生和成长正值中国这一段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所有这些文化也就必然会对他产生深刻的影响。加之,他出生在台湾岛,不到一周岁就因为战争的原因,举家搬迁至广东省。由于广东独特的地理环境,许地山从小就接触到很多东南亚的文化,所以,对于许地山而言,“异域”并不局限于“东洋”“西洋”或者“南洋”中的单一方向,这里面包含了综合性的文化符号,当然这些都只能算是间接的影响。真正直接对许地山产生影响的是他在缅甸工作两年及去印度学习梵文、研究佛经的那些生活体验。因为许地山个人的经验,对异域之地风俗文化、自然样貌的切身感受,他的空间感和精神维度都获得了再生性的变化,所以,他在创作过程中把南洋的文化、风情都融入作品之中,形成新的诗意的空间,使其无法摆脱文化的渗透和浸润,书写出超越空间和时间、超越历史与文化、超越文明与人性的传奇。
细读小说《命命鸟》我们就会发现,许地山在这里不仅为读者描绘了一段凄美的爱情,也用不同的色调描绘出一幅幅美丽的画面,这样的画面,明显受到地域的熏染和异质性元素的催化。这种画面感使得人物的气质和脾性都生成与众不同的品质。作品的一开头敏明的出场,就是在一片金黄的色泽中展开的:“她的席在东边的窗下,早晨的日光射在她脸上,照得她的身体全然变成黄金的颜色。”(1)许地山.命命鸟[M]∥许地山经典全集.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6:72.仅仅是照在脸上的阳光,就把通体映成了黄金的颜色,不难想象敏明的周身都会散发着温暖的神性的光。而加陵的出现则显得明快很多,“一个十五六岁的美男子从车上跳下来,他的头上包着一条苹果绿的丝巾,上身穿着一件雪白的短褂,下身围着一条紫色的丝裙,脚下踏着一双芒鞋,俨然是一位缅甸的世家子弟”(2)许地山.命命鸟[M]∥许地山经典全集.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6:73.。“苹果绿”“雪白”明亮而鲜艳的色彩刚好衬托出“十五六岁的美男子”青春纯洁的天性,而“紫色”的高贵彰显加陵贵族的身份。敏明和加陵,恰值大好年华,一个温暖恬静,一个活泼欢快,一出场就宣告了他们是天生的一对,而后面所有的景色似乎都是在为这一对的“天生”做铺垫。我们惊异于许地山对生活、情感和人性的细部的呈现,只有用心地铺展开生活的细部,从细部进入生活,进入存在世界,进入环境,人与环境的关系和地域、文化因素,才会在人物的内心发酵,这是最见作家创作功力和个人情怀的所在。
那么,在许地山的小说里,诗意究竟是如何呈现的?地域和风情之于许地山,之于许地山小说中的主人公,又蕴藉着怎样的力量和元素,呈示出怎样一个具有时代特征和精神引导的别样的世界?同时,主人公的情感和命运,又是怎样与这个生态环境息息相关的?诗性和诗意,又是如何在人性的维度上展开的?《命命鸟》中的“绿绮湖”是故事的重要环境背景。绿绮湖是仰光最大最好的公园,“湖边满是热带植物。那些树木的颜色、形态,都是很美丽,很奇异。湖西远远望见瑞大光,那塔的金色光衬着湖边的椰树、蒲葵,直像王后站在水边,后面有几个宫女持着羽葆随着她一样。此外好的景致,随处都是”(3)许地山.命命鸟[M]∥许地山经典全集.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6:75.。绿绮湖一出场就环绕在瑞大光的光环之中,它有着王后一般的高贵,又高举着超凡的神圣,它具有让人消除内心烦恼和忧郁的魔力。但就是这样的绿绮湖,却成了加陵和敏明一对璧人香消玉殒的地方。可见,在这里,景致和环境已然不是具体的风景,而是凸显人物命运的风情和重要参照系。“他们走入水里,好像新婚的男女携手入洞房那般自在,毫无一点畏缩。”加陵说:“咱们是生命的旅客,现在要到那个新世界,实在叫我快乐得很。”(4)许地山.命命鸟[M]∥许地山经典全集.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6:85.绿绮湖如同一条在此岸和彼岸之间摆渡的船,负责把人们从此岸渡到彼岸。每个人都是生命的过客,都有旅程结束的那一天,只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乘上“绿绮湖”这叶扁舟成功地到达彼岸。加陵和敏明,如同没经历过任何痛苦一般,仿佛走入湖中的他们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另一种生命的延续,是一段新的旅程即将开启,快乐的不仅是加陵,仿佛整个绿绮湖都在欢送这对“新人”。“那时的月光更是明亮,树林里萤火无千无万地闪来闪去,好像那世界的人物来赴他们的喜筵一样。”(5)许地山.命命鸟[M]∥许地山经典全集.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6:85.月光为他们照亮前行的路,不再迷茫不再犹豫,树林里的萤火虫一闪一闪的,仿佛是婚礼上闪烁的烛光,宾客盈门,高堂满座,都在欢庆有情人的终成眷属。拉着手的他们,坚定地向前走,这对此岸的命命鸟再也不会“呆立”原地,他们也要如同其他的鸟儿一样吟唱,唱出最美妙的声音。许地山把一段“殉情”、一次死亡,竟然写得如此诗情画意。曼妙而动人的场面,会让人忽略两个年轻的生命就要结束,因为忘我地融入情境之中,人们既会感觉到莫名的悲伤,又会幻觉一样地认为他们真的是去了新的世界,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毫无疑问,这样的幻觉,是由于异域的环境所造成的错觉,更主要的原因是许地山所营造的诗意空间,延展了人物的命运和伤怀之意。无论是生命的结束,还是生命的延续,生命都将以诗意的方式呈现,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会觉得这段爱情的美好,尽管是以悲剧来给故事结尾,却丝毫不能削减美的成分,反而幻化出这一切被浓厚的美感所包围。“现在他们去了!月光还是照着他们所走的路;瑞大光远远送一点鼓乐的声音来;动物园的野兽也都为他们唱很雄壮的欢送歌;唯有那不懂人情的水,不愿意替他们守这旅行秘密,要找机会把他们的躯壳送回来。”(6)许地山.命命鸟[M]∥许地山经典全集.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6:85.
我一直觉得《命命鸟》是许地山小说中写得最美的一篇,爱情是凄凉真挚的美,绿绮湖是净化通透的美,瑞大光是神圣辽远的美,而敏明产生的幻境更具有神秘未知的美。“两边的树罗列成行,开着很好看的花。红的、白的、紫的、黄的,各色齐备。树上有些鸟声,唱得很好听。走路时,有些微风慢慢吹来,吹得各色的花瓣纷纷掉下:有些落在人的身上;有些落在地上;有些还在空中飞来飞去。敏明的头上和肩膀上也被花瓣贴满,遍体熏得很香。”(7)许地山.命命鸟[M]∥许地山经典全集.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6:80.另一个世界都是奇花异草,有很多水鸟都是敏明未曾见过的,流水的声音如同奏乐一般;对岸的景色更加奇妙,男子和女子的形态各异,他们身上都落满了叫作“情尘”的花瓣,他们一直重复着一样的对话,一样的表情。如此奇异的景象已经远远超出了现世的范围,它的美不仅仅是因为景色的与众不同,更在于它隐隐地透着那种神秘朦胧的气息。在这个独特的想象空间里,如同寓言一般,不仅把加陵和敏明比喻为命命鸟,喻示他们是命中注定的天生一对,不会分离,而且也预示着故事的结局。在敏明刚进入这个空间的时候,有人在她耳边说:“好啊,你回来啦。”在这里,“回来”一词自然宣告了这才是敏明原本存在的地方,而空间之外的敏明不过是走了那么一遭,旅行一般,走到了尽头自然得折回,敏明最后在绿绮湖的祈祷如同开启“回来”的钥匙,绿绮湖为她开通了“回来”的路。当我们读懂了这些之后,就会觉得故事的结局早已注定,如此纯洁美好的两个人并不属于那个污浊的俗世,他们终究要回到自己本来的世界,最后湖水送回来的只不过是他们在俗世的皮囊罢了。
《命命鸟》的故事是根据一个真实事件改写而成的,原本说的是一对缅甸的青年男女为了追求自由的爱情而一起投湖自尽,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框架,许地山却用他的文字搭建出了空灵、神秘、浪漫且充满别样情韵的想象空间,丰盈了这个故事的同时也诗化了生命的奥义。我们常说许地山是中国现代文学独特的存在,他为何如此独特?《命命鸟》是为许地山的“独特”打响的第一枪,那么《命命鸟》的“独特”又在何处呢?许地山是如何让它成为独特的呢?显而易见,“异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命命鸟》中的“异域”感让一切都变得自然而然,那些瑰丽的景色,在异域的空间里可以自由盛放,那些离奇的情节,异域空间可以尽情地延展。也就是说,“异域”的想象空间,不仅对于创作者而言可以自由书写,更是深深地嵌入和满足了读者的阅读空间。但许地山的“异域”,决然不同于其他作家的异域,许地山的“南洋”亦不是别人的南洋。
“中国作家到过南洋的实在不少,但写过实在的南洋色彩的作品的应当不多,老舍的《小坡的生日》,只有平面的描画。至于停留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与印尼多年的郁达夫,只留给我们几篇游记,都浮光掠影,连平面描画亦谈不上,反而在缅甸住过两年的许地山,倒写过有真正南洋色彩的小说。”(8)黄傲云.中国作家与南洋[M].香港:科华图书出版公司,1985:15.这是香港学者黄傲云对许地山写作中异域性的充分肯定,也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关于“南洋色彩”非常中肯的描述。以绿绮湖的描写为例,艾芜在《我在仰光的时候》一文中这样描述绿绮湖:“离这里不远,就是树林茂密,水波浩渺的绿绮湖。并且在湖的那边,耸立着大金塔,在蓝色的天幕里,经常现出璀璨的金色的巨影。”(9)艾芜.我在仰光的时候[M]∥艾芜全集.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4:344.艾芜的“绿绮湖”与许地山的“绿绮湖”,好像并不是一个地方,前者所描写的“绿绮湖”无法承载起一个想象的空间,让人很难与一段凄美的爱情联想在一起,神圣与净化的属性,更是难以连接。通常作家都会在小说中选择一个地方作为故事背景,但是,要把这个背景处理得与众不同并不容易。所谓的“异域”,是指在我们所熟悉的地方之外的领域,它有着自己独特的个性,包括人物、语言、风景、习俗、历史和思想等,虽然我们可以从书本或者图片中获得一些信息,但是文学和艺术重在体会和感受,想要自己的作品能更深入地走入读者的内心,这就要靠亲身的体会,深入的观察和情感的投入。“若果人物生动,历史正确,用语贴切,写景配合,至多给读者一个平面的描画;若果加上风土人情,与思想背景,那么画面便有立体感;若果再有情调的渗透呢?那么作品便有了灵魂了。有了灵魂,文学才可成为艺术。”(10)黄傲云.中国作家与南洋[M].香港:科华图书出版公司,1985:14-15.许地山更注重通过“异域”建立和保持一种情调,情节和人物都被控制在这种情调和效果之下,成为某种意志的投射,而这个意志是他的生活经验,是对社会现实的感知,也是对特定历史做出的回应;而作品的灵魂除了这种“情调”的渗透之外,在于许地山的“真”与“美”。正所谓一片风景就是一种心理状态,许地山结合自己对现实的思考和对生命的感悟,倾注自己的情感色彩,以一种熟悉又陌生的感觉打造了专属许地山的异域空间。而这些感觉、情感、心理状态甚至是思考和感悟,都离不开许地山那深入骨子里的诗意,这也是许地山独特的原因之二。
再如,诗人徐志摩有一篇带有浓重南洋风情的小说——《浓得化不开》,其间我们看到,南洋特有的热带氛围、异国情调,深深地感染着徐志摩。他眼中的芭蕉是“‘红心蕉’,多美的字面,红得浓得好。要红,要热,要烈,就得浓,浓得化不开,树胶似的才有意思”;暴雨过后的小草是“漏着喜色哪,绿得发亮,绿得生油,绿得放光”;“这风可真凉爽,皮肤上,毛孔里,哪儿都受用,像是在最温柔的水波里游泳。做鱼的快乐。气流似乎密一点,显得沉。一只疏荡的胳膊压在你的心窝上……却是有肉糜的气息,浓得化不开”。徐志摩所感受到的热带自然“更显得浓厚,更显得猖狂,更显得淫,夜晚的星都显得玲珑些”。而热带的女人,“最初的感觉是一球大红,像是火焰,其次是一片乌黑,墨晶似的浓,可又花须似的轻柔;再次是一流蜜,金漾漾的一泻,再次是朱古律(Chocolate),饱和着奶油最可口的朱古律。这些色彩感,因为浓初来显得凌乱,但瞬息间线条和轮廓的辨认,笼住了色彩的蓬勃的波流。”徐志摩眼里的热带女郎万种风情,情之所浓只有用“流蜜”“一泻”“蓬勃”“波流”这样的词语,好像换作任何其他的词语,那些重彩就会立刻稀释开来。应该说,徐志摩笔下的“异域”色彩也十分鲜明,赤裸裸的视觉冲击效果,丝毫不加遮掩,热带的风情感染了徐志摩,而徐志摩的热情和激情,也被“异域”在文学叙述和抒情中点燃。但是,我们只要细细品读就会发现,徐志摩的“浓”都浮于表面,“浓得化不开”的只是字面上的色彩。而同样以“异域”为背景创作的许地山,他的“浓”是深入灵魂,不只是视线所及的事物,而是需要用心去体会、感受,是“浓得化不开”的“情”(11)徐志摩.翡冷翠山居闲话[M]∥徐志摩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5:111-117.。这样的“情”,其中暗藏着“境”,许地山越过了无数的精神和情感的废墟,常常是出其不意地让一种异域的感怀,融会贯通在字里行间,成为叙述和人物挣脱不掉的意绪和幻想,在文本中传递着一种情怀的嬗变,聚焦生活和生命的感怀和千姿百态,文本的美学意义方才愈益浮现出来。在许地山其他的以异域为背景的小说中,更是通过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和意象的运用,特别是通过那种宗教式的神性的光芒来突显一种神秘的诗性力量。
《海角底孤星》中,那对新婚夫妇的结局虽然让人感到哀伤,但是他们的爱情却让人感动。“他在船上哪里像个新郎,简直是妻的奴隶!”他没有什么朋友,也不愿意认识什么朋友,因为他觉得船上的任何人都不配与他成为朋友,他的眼中只有他的妻子。船在向着赤道的方向前进,越靠近赤道两个人的感情愈加浓厚、热烈;赤道下的阳光又送了他们许多热情、热觉、热血汗。他们更觉得身外无人。”两个人的眼中只有彼此,丈夫对着妻子说:“我愿意和你永远住在这里。”“树胶要把我们的身体粘得非常牢固,至于分不开。”这样的情才是真正的“浓得化不开”。但是,到了岛上的第二年妻子就去世了,丈夫因思念成疾,在妻子离去后不到一年也去世了,妻子被葬在了万绿丛中,而丈夫却葬在了深蓝的大海里,他将永远都是“海角底孤星”。“日落了,蔚蓝的天多半被淡薄的晚云涂成灰白色。在云缝中,隐约露出一两颗星星。金星从东边的海涯升起来,由薄云里射出它的光辉。”(12)徐迺翔,徐明旭.海角底孤星[M]∥许地山选集.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107.东边升起的金星,仿佛就是去世的丈夫的化身,在另一个世界找寻他的妻子,也在天上一直守护自己的小女儿,此处的隐喻透满诗意。
《醍醐天女》写的是一对夫妻共患难而不离不弃的故事。一对恩爱的夫妻到森林里玩耍,丈夫不小心被毒刺扎伤,因流血过多而昏厥。尽管自己也身处险境,但妻子没有丢下奄奄一息的丈夫,而是在充满危险的漆黑森林里四处奔走求救。胆小的妻子为了丈夫的生命已然忘记了害怕,即使累到不能再多走一步仍然没有忘记哀求他人救助自己的丈夫,所幸丈夫最终得到了救治。夫妻感情之深只是这篇小说的表意之一,另一个意象则是“人”与“神”属性的互通性。小说的名字叫作“醍醐天女”,并且开头以“乐斯迷”的传说作为引入,传说乐斯迷是爱神的母亲,是保护世间的大神卫世奴的妻子,她是从醍醐海升起来的,印度人一谈到她,都会发出非比寻常的钦赞之声。但是“我”却一直有个奇怪的疑问,“我生在世间的年纪也不算少了,怎样老见不着她的影儿?”这个疑问看似无奇,但是却隐藏着一个很深的伏笔,“乐斯迷”究竟是神还是人?是人,为何“我”从未见过;是神,为何人们又会觉得她是世间存在的呢?两个印度朋友笑“我”不是没有道理,他们的玩笑话却是很有智性的——“在这有情世间活着,还不能辨出人和神的性格来”。“情”成为人类最神圣的情感,因为有情人才能称之为人,也因为“情”的真挚纯洁,人也可以是神。《醍醐天女》中,准陀罗的母亲因为那无私的真情,而被儿子奉为“乐斯迷”。《海角底孤星》的结尾,“我”反对印度人的话语让人听着心都融化了:“女人是悲哀的萌蘖,可是我们宁愿悲哀和她同来,也不能不要她。我们宁愿她嫁了才死,虽然使她丈夫悲哀至于死亡,也是好的。要知道丧妻的悲哀是极神圣的悲哀。”神圣的“情”不应该简单地局限于男女之间的私密情感,当人性上升为神性的时候,“情”就大而化之为普度的伟大。
《商人妇》中惜官的人生似乎在不断地反转,每当觉得幸福马上就要到来的时候,就会有更大的灾难和痛苦等着她。她以为丈夫去了南洋必然会让自己过上好日子,但是却一等再等,始终没有丈夫的音信;她以为去南洋寻找丈夫,丈夫也会如她般欣喜,但相见的场面却异常冷淡;她以为既然与丈夫相认,从此就会夫妻恩爱共同经营生活,但是丈夫却把她卖给了印度商人做了小妾;她以为在印度的生活也算平淡无忧,从此儿女绕膝简单快乐,但是商人阿户耶的去世再一次让她无处容身,不得不踏上逃亡之路;她以为丈夫会念及曾经的夫妻情分再次接纳她,但丈夫一家却早已搬至别处。故事的结尾,惜官选择继续寻访丈夫的下落以期待再回到印度的可能,惜官未来的生活将如何我们不得而知,我们能做的只有为这个可怜的女人默默地祈祷,希望一直围堵她的人生之墙能够訇然中开,闪出一道希望之光。
命运多舛的惜官不可谓不可怜,如果从现代以来一直倡导的妇女独立自主的角度来看,惜官之所以可怜,是因为她完全依附于男人,她的命运完全受控于男权的力量,女权主义者可能会对此嗤之以鼻。人们常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而读过《商人妇》后,谁都无法对她产生恨意,都希望她的生活可以好转起来。就像荷尔德林所说:“只要良善/和纯真尚与人心相伴,他就会欣喜地拿神性/来度测自己”,这就是惜官,不论命运如何待她,她的纯真和善良始终是内心的底色,如同启明星一般光明,是“夜界最光明的星”——“凡光明的事物都不能迷惑人,在诸星之中,我最先出来,告诉你们黑暗快到了;我最后回去,为的是领你们紧接受着太阳的光亮”,她的纯洁和善良才是最光明,最使人警醒的。这应该就是荷尔德林所指的“神性”,“神性乃是人借以度量他在大地之上、天空之下的栖居的‘尺度’”(13)海德格尔.人,诗意地栖居[M]∥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471.,按照海德格尔的解释,当人开始拿神性来度量自己的时候,说明他已经栖居在他生活的那片土地上了,只有这样的状态下,人才会拥有把天地作为边界来衡量自己的心胸。当《商人妇》中的惜官开始与“神性”相接时,她应该已经找了栖居的入口,在她经历了无数磨难的前半生,似乎很难寻觅“诗意”的踪影,但是她乐观的天性又何尝不是老天赐予她的“诗意”呢?既然她已经找到了栖居的入口,加上她始终如一的善良纯真,谁又会怀疑她下半生不会在某片土地上诗意地生活下去呢?
从某个角度来看,“神性”就是超越普通伦理道德的精神追求,而当这种精神追求上升到一定程度,就会被称作“神明”的形象,在许地山的作品中,能称得上“神明”的形象的必然是《缀网劳蛛》中的尚洁。尚洁被丈夫长孙可望误解刺伤,并背负着莫大屈辱,她没有为自己喊冤叫屈,不做任何辩解,默默地承受长孙可望的诬陷:“我的行为本不求人知道,也不是为要得人家的怜悯和赞美;人家怎样待我,我就怎样受,从来是不计较的。别人伤害我,我还饶恕,何况是他呢?”(14)许地山.缀网劳蛛[M]∥许地山经典全集.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6:69.尚洁饶恕的不只是长孙可望,她是宽恕了整个世界。可以说,在很大的程度上,尚洁对于长孙可望无理取闹所采取的态度,以及对事件的处理方式,已经超越了普通人的正常范围,如同普度众生的神明,可以包容世间的一切罪恶,原谅人们的所有过错,接纳所有阶层的人,她以超越常人的宽容,和对人生透彻的领悟去度化身边的凡人,提高他们的精神境界,净化他们的灵魂,她的纯洁似乎不沾染任何凡尘。所有的苦难她都承受,但是她却仍然以一种很诗意的方式安居在这个世界里。这样的生存状态,不仅仅关乎她的修为,渗入她的生命体验,更加本质的是“诗意”背后的人所具有的“真”与“善”,以及最终归之于“美”的范畴,这是人的最高“尺规”。这里所谓的“诗”已经远远超越了语言艺术门类的范畴,它代表的是一种生命的本真状态,是通往真理的无限接近。
纵观《商人妇》《缀网劳蛛》《醍醐天女》《海角底孤星》等几篇小说,我们发现其间的异域风情,已经远远弱于《命命鸟》。《商人妇》中最明显的应该是惜官辗转的几个地方,新加坡、印度,以及马来妇人、阿户耶、阿噶利马、伊斯兰教这些标签性的名词撑起了所谓的“异域”,相对于《命命鸟》那样细致的描写已然消失;《缀网劳蛛》中只有“土华”这个异域的地名;《海角底孤星》中“赤道”“槟榔屿”“椰子”“棕枣”“树胶”这些略带南洋风情的地名和物种,以及船上的印度人,其他描述似乎很难有“异域”的感觉;而《醍醐天女》除了船上的印度人,周围的印度洋,印度的传说,我们也很难找出关于“异域”的其他描写。其实,“异域”对于许地山而言不是猎奇的手段,不是吸睛的噱头,他从没有刻意去渲染“异域”的“异”,更多的是利用这个“域”让故事可以更真切地传达出他期许的意蕴。“异域”对于许地山的创作不应该局限于“南洋”或者某个固定的地理范围,“异域”这个词背后的意义应该更加宽广,它代表的是许地山的思想中对多元文化的吸纳,也是空间的隔离,眼前的现实过于乌糟邋遢,许地山那神圣而纯洁的“情”,浓得化不开的“诗”,需要有一个不一样的空间才能安放,而许地山的“异域”与其说是南洋,不如说是他用自己的想象虚构了另一个真善美的空间而披上了“南洋”的外衣。
近一个世纪以来,对许地山创作的研究一直集中于宗教、异域、人生等几大方面,但是我们还需要做的是透过这几个维度去寻找他思想中最根本的内核,不论是多么崇高的信仰还是多么深奥的生命哲学,“人”永远是这一切的基点,人要如何活着是许地山创作所有棱面的基线,而许地山追求的终点就是“人,诗意的栖居”——这才是许地山思想的真正内核,是他所希望的人的最理想的生命形态。
小说《海世间》是许地山的自我对话,文鳐对“他”说:“是谁给你分别的?什么叫人造人间,什么叫自然人间?只有你心里妄生差别便了。我们只有海世间和陆世间的分别,陆世间想你是经历惯的;至于海世间,你只能从想象中理会一点。”(15)许地山.海世间[M]∥花香雾气中的梦.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5:68.“他”把人间区分为“人造人间”和“自然人间”,所谓的“人造人间”就是文鳐说的“陆世间”,是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充满了“社会律的桎梏”;而“自然人间”究竟在哪里,“他”也说不清,一直在寻找。其实对于人来说,“自然人存在的受、想、行、识”这些沉重的东西,脱掉日常伪装的“外衣”,还原人性最原本的真善美,自由自在地生活。而这样的生活“只有在想象或淡梦中能够实现罢了”。文鳐和“他”是许地山思想中的理想版和现实版,二者的对话象征着许地山思想的转换和提升,在现实和理想中穿梭,既要直面现实又必须要给现实插上一双翅膀,向更美好的未来世界努力飞翔。
从文学的角度讲,许地山首先是个诗人,作为诗人的许地山用他最饱满的诗意倾注到他的诗歌当中,然后又投入到了他毕生的精力和经历,用他的诗学来灌溉他整个的文学创作以及更广泛而融合的文化意蕴,引导人们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安居,无论多少困苦永远不缺少“良善”和“纯真”,真挚的情感让诗意自由弥漫,隐匿的哲性成为做人最大的“尺规”,这就是许地山的诗学世界,也是他的灵魂所在,这同样也是我们“阅读”许地山必须要攀登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