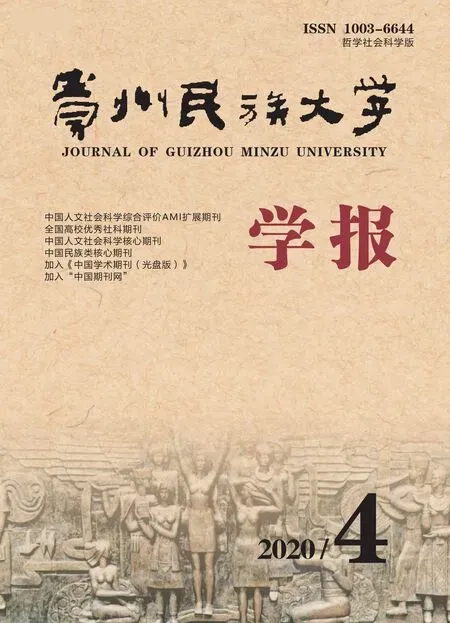援用还是创译
——西方逻辑第二次传入的术语问题
刘 永 强,翟 锦 程
一、问题的提出
术语体系的建设是任何一门学科的基础,完善的术语体系对于学科的进步与发展至关重要。术语以其基础作用,成为了解和掌握一门学科的重要途径,恰如周有光所言:“大千世界,经纬广布;科学发展,术语是纲;抓住术语,纲举目张。”[1]2中国学者对西方逻辑学的认知亦是从术语开始。西方逻辑学术语体系在中国的构建是伴随两次西学东渐而进行的,是一个不断中国化的过程,其历程曲折而复杂。
在明末清初的第一次西学东渐中,来华西方人是西方文化传播主力。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年),字复初,1543年生于意大利中南部的斯品纳佐拉(Spinazzola)城,获得两个博士学位。1579年7月,到达澳门,并开始学习中文,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1583年在澳门写出《天主实录》,该书为“欧罗巴人最初用华语写成之教义纲领”。1584年刊印,1640年傅汎际(Francois Furtado,1587-1653年)修订后改称为《天主圣教实录》。其后,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年)、高一志((Alfonso Vagnoni,1566-1640年)、艾儒略(Jules Aleni,1582-1649 年)、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年)等西方人在部分士大夫的协助下,采取合作翻译、编写图书等方式介绍了有关西方传统逻辑的内容,包括《几何原本》《西学》《西学凡》《名理探》和《穷理学》等。这些图书介绍了西方传统逻辑的部分术语,比较初步地介绍了亚里士多德逻辑的部分内容,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尽管译者们在译介过程中综合运用了音译和意译的方法,但由于译者多为士大夫,而非逻辑学家,他们对于逻辑学的理解较为粗浅,使得所翻译的术语生涩难懂,不利于流传。例如,利玛窦和李之藻在翻译《名理探》时,将三段论音译为“细録世斯模”,将亚里士多德的十范畴译为充满儒家意味的“十伦”。前者的意义令人费解,后者的译成虽适应了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儒家,但终究未能还原其本意。总之,由于第一次传入主体是非逻辑学家,他们的目的是其他而非传学,因而作为整个传播内容一部分的逻辑学术语系统性不足,且翻译质量不高,不利于其普及与流传。
通过比较,西方传统逻辑第二次传入在术语体系的建构上远远超过了第一次。与第一次传入不同,第二次传入是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大背景下进行的,传播主力是以救亡图存为目的的知识分子,而日本也与西方一样成为逻辑著作引进的重要来源地。当时,严复、胡茂如、王国维等学者积极向国内译介西方传统逻辑,何兆清、章士钊、王章焕等则自行编写逻辑教材,共同推进逻辑学在国内的普及。日本是中国近代译介逻辑著作的主要来源地之一,而经过明治维新后的日语中存在大量的以汉字为基础的“和制汉语”,例如哲学、主观、客观、归纳、演绎等。这就给当时的译者在具体翻译中提供了有别于第一次传入时两种译法的方法——直接沿袭日语翻译,使用“和制汉语”。因此,诸如张之洞、梁启超、王国维等有识之士便主张在翻译过程中可以借鉴乃至使用日语翻译,以此加快中国社会与科学的发展进程。另一方面,在翻译西方逻辑学著作时,严复坚持自己提出的“信达雅”翻译原则,从中国古代寻找与西方传统逻辑类似的概念进行翻译,或者依照自己理解创造出大量逻辑术语。前者是援用,后者是创译,在两者并行使用下,西方传统逻辑术语在中国逐渐普及开来。但这个过程中存在一个问题:两种方法产生了不同的术语系统,在日常使用中难以统一,如何对二者进行取舍?
二、和制汉语与援用
和制汉语是指以汉字为基础,由日本人创造的汉语词汇。和制汉语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至日本奈良时期。近代以来,和制汉语深深地影响了现代汉语的发展。据崔崟统计,传入中国的和制汉语共计889个,涉及中国社会各个领域。[2]22-26这种影响正如萨丕尔(Edward Sapir,1884-1939年)所指出:“语言与文化一样,对自身很少是充足的。基于交流的需要,单一语言使用者总会直接或间接地接触与其相邻或文化占主导地位的语言。这种交流或者是友善的,或者是敌意的。……然而,不管与邻近民族接触的程度或者性质如何,通常都足以引起语言的交互影响。”[3]159
被誉为日本哲学之父的西周对和制汉语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他在《百学连环》中利用汉字创译出大量的西方学术名词和哲学范畴,涵盖哲学、逻辑学、心理学等各领域。日本学者森冈健二认为西周使用过1410个译语(其中863个与中国典籍存在联系,可以在古籍中找到出典),独创的译语有787个。[4]232在这些译语中,与哲学、逻辑学、心理学有关的词汇占绝大多数,其中与逻辑相关的有分类、外延、概括、概念、命题、全称、特称、归纳等。[4]232-234其后,井上哲次郎、和田垣谦三、国府寺新作、有贺长雄搜集西周等学者创制的译语,加上他们自己的一些译语,整理汇编为《哲学字汇》,并多次再版。如哲人、自然哲学等皆出自于《哲学字汇》及其后续版本。[4]237-238日本学者大规模地使用和制汉语翻译西方科学术语,为近代中国学者援用其翻译提供了基础。
另一方面,近代日本与中国在西方船坚炮利下,几乎同时发起了向西方学习的运动。但是,相较于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国力迅速提高,清政府的改革运动却远远不及,最终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给国人以极大震撼。因此,有人主张向西方学习的同时,也应向日本学习。洋务大臣张之洞直言:“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二、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5]9738基于这种认知,张之洞提出“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的翻译主张。[5]9744留日学者接触到和制汉语后,敏锐地发现借助和制汉语能省却大量翻译劳动。康有为指出:“日本文字犹吾文字也……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费不千万金,而要书毕集矣。”[6]585-586梁启超认为:“日本与我为同文之国,自昔行用汉文。……日本自维新以后,锐意西学,所翻彼中之书,要者略备,其本国新著之书,亦多可观。今诚能习日文以译日书,用力甚鲜,而获益甚巨。……以此视西文,抑又事半功倍也。”[7]50
和制汉语的发展为中国学者直接援用提供可能,清政府官员与知名学者的提倡则进一步推动了日文书籍翻译的进行。本文所论之逻辑学相关术语便是在这种环境下得到引入,而引入也存在着三种方式:一是直接翻译日本逻辑学教科书,成体系引入逻辑学术语;二是利用和制汉语翻译西方逻辑著作;三是中国逻辑思想研究。
直接翻译的日本逻辑教科书有田吴炤的《论理学纲要》、胡茂如的《论理学》、蒋维乔的《论理学讲义》等。本文主要介绍《论理学》中的术语。《论理学》为日本学者大西祝所著,是东京专门学校(即早稻田大学——笔者注)逻辑学课程用书。该书分为三编,第一编、第二编主要谈论西方传统逻辑。其中,主要术语为论理学、推理、命题、主语、客语、系辞、定言命题、选言命题、假言命题、全称命题、单称命题、特称命题、肯定命题、否定命题、对当、反对对当、矛盾对当、换质、换位、外延、内包、矛盾律、排中律、自同律、三段论、前提、断案、大项、小项、大前提、小前提、格、式、省略三段论、复杂三段论、假言三段论、选言三段论、归纳法、类推法、类同法、差异法、类同差异并用法以及相变法。[8]对比明治36年由警醒社出版的《大西博士全集·论理学》中和制汉语表示的逻辑术语,胡茂如直接援用了论理学、推理、命题、外延、内包、矛盾律、排中律、自同律、归纳等和制汉语。这些和制汉语表示的逻辑术语基本涵盖了西方传统逻辑内容,与现今标准术语也相差无几。
利用和制汉语翻译西方逻辑著作的学者是王国维。王国维本人在谈及日本学者翻译西方术语时指出:“且日人之定名,亦非苟焉而已,经专门数十家之考究,数十年之改正,以有今日者也。”[9]42他认为由于“日本人多用双字,其不能通者,则更用四字以表之。中国则习用单字,精密不精密之分,全在于此”,并且学习、使用日语有“因袭之易”而无“扞格之虞”,是故“何嫌何疑而不用哉”。[9]42-43所以,尽管他在翻译耶方斯《逻辑基础教程:演绎和归纳》(ElementaryLessonsinLogic:DeductiveandInductive)时没有采纳日本的“论理学”,而是以“辨学”翻译“logic”,但其内容却大量地援用了和制汉语。例如,推理、名辞、命题、同一、矛盾、大前提、小前提、归纳等皆是和制汉语。
一些中国学者在中国逻辑思想研究过程中引进并使用和制汉语中的逻辑术语。近代中国逻辑思想研究的启蒙者孙诒让在给梁启超的信中就使用了当时国内尚未出现的逻辑术语:“尝谓《墨经》楬举精理,引而不发,为周名家言之宗,窃疑其必有微言大例,如欧士论理家雅里大得勒(即亚里士多德——笔者注)之演绎法,培根之归纳法,及佛氏之因明论者。”[10]382有学者认为,由于信中“演绎”“归纳”在当时国内尚未出现,所以孙诒让在这里很可能借鉴了日语翻译,直接使用和制汉语。[11]刘师培在《攘书·正名》中表示,欧洲论理学就是中国的名学,是“真理之要法,所谓科学之科学也”,有归纳和演绎两种方法。[12]108他认为这两种方法即是荀子所谓的“大共”与“大别”。[13]10梁启超在“logic”定名上主张援用日语翻译,而其他逻辑术语“则东译严译,择善而从”,但“采东译为多”,因为他认为“吾中国将来之学界,必与日本学界有密切之关系,故今毋宁多采之,免使与方来之译本生参差也”。[7]3186以此为基础,他将《墨经》的术语与西方逻辑术语一一对应,开启了近代中国逻辑思想的比附研究。
总之,和制汉语以其与汉字之间的独特联系,加之当时赴日留学生规模庞大,又有清政府与知名学者的倡议,使得国内学者在翻译或编写逻辑著作时大量援用日语翻译中的术语。当然,日语翻译相对于中文翻译也并非全占优势,例如日语翻译中将“distribution”译为“周延”,相对于严复译词“尽物”,前者在直观方面略显不足,单凭字面无法理解。[14]而严复关于“尽物”的翻译则是当时介绍逻辑学术语的另一种主流方法——创译。
三、创译及“Logic”定名
创译是不同语种翻译转换的一种方法,关于它的描述与定位有很多。一般来说,它指“在目的语系统中,对源文本进行编辑、重组、创造性重写、创意性重构等的转述方式,实现目标话语的表达性与目的性的文本,其方式可以为单模态或多模态”。[15]它表现为语词和作品篇章两方面,而关于语词的创译则是指“词语(术语、概念)翻译过程中,利用汉字本有的形音义来创造汉语中没有的新词,并对应原语的相关词”,具有首创性、创造性、形音义皆备、既科学又艺术、恰切性的特点。[16]本文主要指术语的创译,就其实现的路径而言,可分为音译和意译。
与当时直接援用日语翻译相比,一些学者更多地倾向于使用这种创译的方法,尤其是在部分关键术语上,严复、章士钊等是其中的代表。
严复是近代著名翻译家。他提出“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以此译介了多部西方学术著作。其中,有关逻辑的是《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严复在接触到西方逻辑后,发觉中国古代也存在类似西方逻辑的内容。他指出司马迁所说的《易》的“本隐之以显”是归纳法,而《春秋》的“推见之隐”就是演绎法,只是“后人不知广而用之者,未尝事其事,则亦未尝咨其术而已矣”。[17]1320这种中西逻辑间的共通性为他能够采用部分中国古代逻辑术语翻译《穆勒名学》奠定了基础。
严复翻译《穆勒名学》以及《名学浅说》时,国内已经引进了日本的逻辑教科书,即前文所说的《论理学》等。因此,他在译介过程中可以接触到大量关于逻辑的和制汉语。但是,他认为这些翻译并不恰当,不符合其“信达雅”标准,“西名东译,失者固多,独此天成,殆无以易(指和制汉语‘自由’——笔者注)”[17]132。他尤为反对将“logic”译为“论理学”,认为其“已极浅陋,……窃以为不及吾译”。[18]57所以,他很少借鉴和制汉语中的逻辑术语,而是采取意译与音译的方法创译逻辑术语。例如,他将“logic”译为“名学”就是根据其对“logic”的理解,并结合中国古代逻辑术语翻译而成。事实上,在严复之前就有关于“logic”的译名,如明末清初李之藻译成的“名理探”,近代艾约瑟译成的“辨学”。但他认为名学是“一切学之学,一切法之法”,其学“精神广大”,而这些翻译过于陋俗,不足与逻辑“深广相副”,只有名学“奥衍精博,与逻各斯字差相若,而学问思辨,皆所以求诚、正名之事,不得舍其全而用偏也”[19]2。除“名学”外,严复翻译的逻辑术语还包括逻辑、内籀、外籀、天然公例、端、缀系、词、联珠、公名、专名、察名、玄名、正名、负名、外举、内函、有涵之名、不涵之名、德、寓德、常德、界说、句主、缀系、所谓、正词、负词、申词、有待之词、析取之词、统举之词、偏及之词、调换词头之法、简捷转头、限制转头、例、案、判、大端、中介、小端、察观、试验、设覆、印证、前事、后事、推概之法、比拟、眢词等。能够发现,这些术语与今天通行的逻辑术语体系大相径庭。
章士钊与严复相似,也提出了关于翻译的一些观点。他认为作为创译的两种路径的音译与意译都有缺陷,但相较而言,音译要优于意译。因此,“自非译音万不可通,而义译又予吾以艰窘,吾即当诉至此法”[20]454。将“logic”定名为“逻辑”便是这种方法的生动体现。当时流行的关于“logic”的译名有论理学、名学以及辨学,章士钊认为此三者皆不妥,并一一批驳。关于“论理学”,章士钊指出它是由“science of reasoning”所得,为“日教科书中肤浅之定义”,它使得逻辑泛化,并且“论”一字的词性变化会使其本身意义不定,所以“论理二字,义既泛浮,词复暧昧,无足道也”。[21]296严复翻译的名学虽然可以涵盖亚里士多德逻辑,但“未能尽倍根(即培根——笔者注)以后之逻辑也”,所以也不适用。[20]449至于辨学,章士钊虽认为其较名学要优,但其终究只能“范围吾国形名诸家,究之吾形名之实质,与西方逻辑有殊”,以致“本体佳绝,而亦复不中程者此也”。[21]298所以,章士钊主张“以音译之,可以省却无数葛藤。吾国字体,与细纹系统迥殊,无法输用他国字汇,增殖文义。以音译名,即所以弥补此憾也”。[21]298并且,逻辑一词,“实大声宏,颠扑不破,为仁智之所同见,江汉之所同归,乃崭焉无复质疑者也”。[21]575由此,“逻辑”之名逐渐为社会所接受,直到1949年后被确定下来。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章士钊在“logic”定名问题上与严复相左,但他十分推崇严复的其他术语翻译。在编写《逻辑指要》时,章士钊多借鉴严氏术语,他说:“为国人开示逻辑途径,侯官严氏允称巨子。本编译名泰半宗之,译文间亦有取,表示景仰前贤之意。”[21]295这些术语包括内籀、外籀、内涵、端词、公名、玄名、察名、正名、负名、有涵之名、无涵之名、全称之辞、偏称之辞、浑称之辞、独称之辞、辞之对待、辞之变换等等。
此外,当时关于逻辑的译名还有孙中山的“理则学”。孙中山认为论理学、辨学和名学皆为不当翻译,因为“推论者乃逻辑之一部分,而辨者,又不过推论之一段,而其范围尤小,更不足以概括逻辑矣。至于严又陵氏所翻之名学,则更为辽东白豕也”。[22]33因此,孙中山主张逻辑是“诸学诸事之规则,为思想云为之门径也”,因而翻译为“理则学”比较恰当。[22]34这种译法在当时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综上可以发现,严复、章士钊乃至孙中山在创译逻辑术语时,都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了中西逻辑的比较研究,对中国古代辨学、名学与西方逻辑的内涵及外延进行考察,并在一些关键术语上直接沿用中国古代术语。就此而言,他们关于逻辑术语的创译启发推动了中国逻辑思想的研究。但正如前文所指,这些著作在当时虽具有一定影响,但其中的术语却并未得到继承与发展。
四、援用还是创译
应当知道,前文中的援用与创译是近代中国构建西方逻辑学术语体系的两种主要路径。这两种路径在逻辑学研究和普及方面都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只有援用的和制汉语中的逻辑术语体系流传至今,而以严复为代表的创译者们所创译的逻辑术语大多被遗忘。那么,是何种原因造成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笔者以为可从以下几点进行分析。
其一,和制汉语中的逻辑术语较为通俗易懂,阅读门槛低于创译术语。一般来说,术语的翻译必须既具有专业性,又有可读性。前者体现术语翻译的精确性,后者体现术语翻译的可普及性。严复是当时逻辑术语的主要创译者,他认为写作文笔对于真理的表达十分重要,因而“理之精者不能载以粗犷之词,而情之正者不可达以鄙倍之气”。[17]516基于这种看法,严复创译逻辑术语时多用古语。这直接提高了阅读门槛,译语“非今日普通人所易解”[23]。当时参与校对《穆勒名学》的包天笑就说:“坦白说一句,我是校对过《穆勒名学》一书的人,我也仍似渊明所说的不求甚解。”[24]229而且当时其他学者也直接批评了严复的译语,如张君励所言:“特其立言之际,务求刻肖古人。往往以古今习用之说,译西方科学中之义理。故文学虽美,而义转歧。……总之,严氏译文,好以中国旧观念,译西洋新思想,故失科学家字义明确之精神。”[25]但严复认为若译语过于陋俗,反而不利于学术研究,况且其译书的读者应为“多读中国古书之人”,而非“目未睹中国之古书,而欲稗贩吾译者”,是故“过在读者,而译者不任受责也”。[17]516-517这表明,严复已经意识到自己译语较为复杂,不利于在普通人群中普及,但却固执己见,未做改变。与之相比,和制汉语中的逻辑术语却相对简易,易于普及。两相比较,不难理解和制汉语的逻辑术语何以能流传至今。
其二,援用和制汉语中逻辑术语的书籍量多,且影响范围广。近代日本在西方文化引进道路上相较同时期的中国走得更远、更快,其文化建设与辐射力高于中国。加之教育部门为节省人力物力和加快教育发展,提倡“先取日本译成西学普通各书,转译中文,颁发肄习,俾其易于通晓,易于成就”,[26]581给引进日文教科书和援用日语翻译提供了可行性。当时,以和制汉语中逻辑术语为标准的书籍主要是翻译的日本教科书,以及国人自行编写的教科书。这二者数目庞大,有近百种,且多为政府规定的教科书,涵盖了高中、师范以及大学。如王振瑄编纂的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中的《论理学》,由高岛平三郎讲述、江苏师范生使用的《论理学教科书》,魏先朴、杨昌济编著的、大学使用的《论理学教科书》等,这些教科书影响了一大批学生。作为比较,以创译为主的《辨学启蒙》《穆勒名学》《名学浅说》等虽在特定时间也充当过教科书,但时间较短,且使用范围较小,影响人数相对较少。如此,使用和制汉语中逻辑术语人更多,使得援用的逻辑术语更加流行,进而影响更多的人,形成马太效应,最终从影响上超过了以严氏术语为代表的创译术语体系。
其三,中国逻辑思想研究对逻辑术语选择的影响。孙诒让训诂《墨经》时,发觉其中有类似西方逻辑的内容,并在寄给梁启超的信中谈及了此事。信中所用的逻辑术语便是和制汉语中的“归纳”和“演绎”,而这是二词在国内的首次出现。与此同时,日本学界也在进行中国逻辑思想的研究与考察。日本明治时期,服部宇之吉、西周、松本文三郎、蟹江义丸以及桑木严翼等日本学者对中国古代有无逻辑的问题展开讨论,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古代逻辑的义理问题进行考察。[27]283-289这些研究对近代诸如梁启超、王国维及刘师培等中国学者研究中国逻辑产生了直接影响,例如王国维直接翻译了桑木严翼于1900年出版的《哲学概论》附录中的《荀子的论理学》,题为《荀子之名学说》。[11]他们在日本学者的影响下,援用和制汉语中的逻辑术语进行中国古代逻辑的研究,加速了这些术语的普及。相比之下,严复等创译的逻辑术语却鲜有人使用,除逻辑、名学等寥寥几个外,大多被当时学者摒弃。近代是中国逻辑思想研究发生、发展的重要时期,相关研究中的术语选择对后续进一步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这使得当时援用的逻辑术语在普及程度上远远高过了创译术语,并影响至今。
概言之,援用的和制汉语中的逻辑术语通俗易懂,使用这些术语书籍规模大,加之中国逻辑思想研究对和制汉语的选择,这三者共同推动了和制汉语中逻辑术语在中国的标准化进程。笔者认为透过上述分析,能够启发当前的逻辑术语体系建设、逻辑研究乃至文化发展。
第一, 新术语的翻译是一个不断中国化的过程,应援用与创译并举,意译与音译共行,而不拘泥于某一种方法。术语的翻译是不同语种间的形式转化,就中国的术语翻译而言,实质上就是将其他国家语言转换为汉语。而和制汉语是中国汉语的一种衍生,天然的与汉语相亲。因此,日本学者利用汉字翻译西方术语所创造出的和制汉语与严复创译术语一样,都是为西方术语的汉化而努力。同时,如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等前人所言,借助和制汉语能省却国内学者的翻译劳动,也不会带来理解上的困难,可以加快外来文化的学习、消化过程。加之前文业已指出无论是援用的和制汉语,还是严复等人创译的术语,二者都非尽善尽美,存在一定弊端。所以,有必要综合运用援用与创译的方法,共同加快外来术语译介进程。
第二,中国逻辑思想的研究可以在对比参照中借鉴西方逻辑,但不能依赖比附。在中国逻辑思想研究早期,利用西方逻辑术语对中国古代逻辑进行比附研究,发掘中国逻辑思想,普及逻辑术语,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逻辑思想的发展。但是,比附只见其同,不见其异,有碍于中国逻辑思想的深入研究,不能进一步还原中国逻辑思想的本貌。因此,中国逻辑思想的研究必须抛弃比附的观点,将中国古代逻辑作为世界三大逻辑传统之一,从逻辑的观点出发,与西方传统逻辑和印度因明进行比较研究。换言之,在研究过程中,既注重中国古代逻辑所具有的逻辑的一般特性,又能看到其作为中国古代逻辑的民族性。以此为基础,推动中国逻辑思想研究进入更深层次。
第三,应当加快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设,增强学术话语权。近代中国的社会整体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大规模向西方学习是中国自救的途径之一。由于日本是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的“优等生”,国内知识分子便主张经由日本向西方学习。这种背景下,国内除逻辑学一科,诸如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也都大量引入了和制汉语。然而无论是学习西方抑或是学习日本,本质上都是中国学术水平落后的反映。就此而言,当今时代应加快逻辑学包含在内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设,增强学术话语权,提高汉语的国际学术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