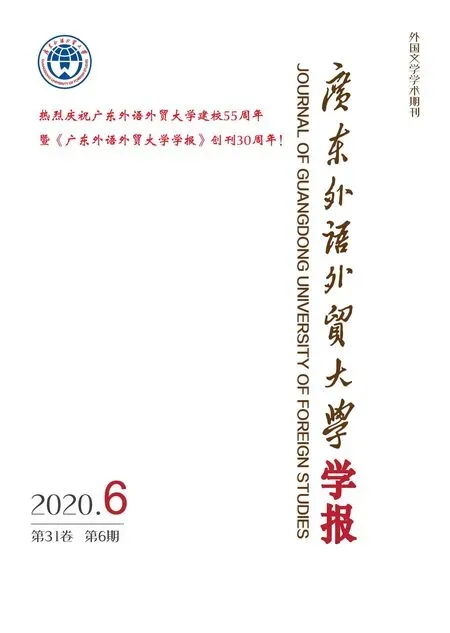《大都会》中的双重物质叙事
唐建南
引 言
《大都会》(Cosmopolis, 2003)是著名美国后现代作家唐·德里罗(Don Delillo, 1936-)于二十一世纪出版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讲述了二十八岁的青年股市大鳄埃里克·帕克(Eric Packer)坐着豪华加长轿车穿越城市理发的荒诞故事,一天的经历记录了这位跨国资本家从富可敌国到债台高筑的沦落。目前为止,《大都会》的多数文学评论集中批判该书映射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和技术崇拜,其中不乏对物件或商品的剖析。张琦(2017)与伊恩·戴维森(Ian Davidson,2012)都聚焦小说中无所不在的汽车,前者指出埃里克的豪车是“冷漠无情的庞然大物、虚拟/虚幻的封闭空间、‘车轮上的国家’的隐喻 ”;后者探讨汽车在话语空间中自由、权力与财富的象征意义,并剖析“全球化生产与消费链中的物品所带来的影响”。朱荣华(2011)以“物时间”为切入点,指出小说中物品更新换代的节奏指向未来,远远超出承载历史的“身体时间”,以此批判发展至上的跨国资本主义,肯定回归身体时间所实现的精神升华。可以看出,对《大都会》中物品/商品的研究主要聚焦其映射的象征意义或物质的话语性,并未从物质叙事的角度比较全面地探讨物质是物质性(material)与话语性(discursive)的融合,是物质本身(本体)和社会话语建构(喻体或符号)的结合体。这种缺失的一大原因是物质叙事还是一个崭新话题,二十一世纪兴起的新物质主义推动了物质生态批评中的物质叙事研究,而国内尚处于介绍该成果的初级阶段。
物质生态批评扎根于二十一世纪初兴起的新物质主义,这种“物质转向”是对持续三十年的“文化转向”的纠正。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西方“偏重语言、话语、文化与价值观的文化转向”导致了“物质主义的终结”(Coole、Frost, 2000: 3)。后现代主义就是该文化转向中的重要思潮,它反对所有西方传统中根深蒂固的二元论,但是唯独默认了语言/现实的二元对立关系,认为语言构建了物质世界,人们“热情激昂地抛弃现代主义的物质根基时,却走向了话语的另一极端,认为话语是建构自然、社会与现实的唯一来源”,从而导致了“物质性的缺失”(loss of the material)(Alaimo、Hekman, 2008: 2, 6)。受自然科学新发现的推动,也为反思导致全球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物质主义于二十一世纪初开始了复兴之路,以此推动新物质主义的盛行。它主张不仅要继续从传统物质主义中汲取精华,还应该从笛卡尔的精神高于物质的二元偏见中解放出来,将传统推向新方向、新领域,认识到物质不仅仅是物品(object),它是“积极主动、自我创新和难以预测的,它是力量,是活力,它相互联系又各不相同”(Coole、Frost, 2000: 9)。这种主张在广泛的社会科学领域得到积极回应,从新物质主义中萌芽的物质生态批评不仅认同所有人类与非人类物质都具有施事能力,而且认为所有物质的叙事能力就是其施事能力的重要表现。
意大利教授赛仁娜拉·伊奥凡诺(Serenella Iovino)与土耳其教授瑟普尔·奥伯曼(Serpil Oppermann)是奠基物质生态批评的两大学者,她们认为所有物质都是“有故事的物质”(storied matter),物质之间的内在互动(intra-action)推动了世界的构成与变化,这种互动过程或物质化过程(materialization)既是物质的物理结构和化学构成的变化过程,也是与人类互动中意义不断生成的过程,后者是社会话语对物质的解读,也就是一种物质的“符号化力量”(signifying forces)的再现(Iovino、Oppermann, 2014:1-2)。物质生态批评旨在解读“文本中的物质”(matter in texts)和“物质文本”(matter as a text), 将“自然-文化之间的互动解读为物质叙事(material narrative)”,追踪“物质生成过程隐含的文本性”(Iovino、Oppermann, 2014:6-7)。换而言之,分析物质叙事就是聚焦物质性和话语性于一体(material/discursive)的物质其动态变化过程和社会话语的解读过程。任何文学作品都不仅仅是作者个人施事能力的产物,而是作者与非人类自然物质通过内在互动产生的,“人类施事能力与物质的叙事施事能力半路相遇,产生了以文学和其他文化产物为形式的物质-话语现象”(Iovino、Oppermann, 2014,11)。
从物质生态批评角度分析德里罗的《大都会》,可以发现小说凸显的物质符号化或物质话语性的解读导致人们认为物质性是缺失的,但是深究物质叙事的隐形进程,发现物质性其实一直隐藏在叙事暗流中。对小说双重物质叙事的解读证明人类永远无法超越物质生存,物质的物质性和话语性也是互相交融、难以分离的。
物质的符号化:后现代世界中物质性的缺失
后现代主义遭人诟病为“物质性的缺失”,从物质生态批评的角度分析《大都会》,可以看出后现代文学采用的语言游戏致力于揭露复杂的社会现实,凸显社会话语对物质的符号化解读,以至于被人认为存在物质性缺失的不足(Alaimo、Hekman, 2008: 6)。究其原因,物质在信息化、消费主义和全球化的共同冲击下导致能指与所指出现“断裂”,“个体与物品抛弃了后现代现实中相应的参照实体,只能以符号的形式存在”,在后现代的语言游戏中,受社会话语建构而幻变成符号的物品脱离了现实中真实的存在(Harma, 2014)。
小说开篇就是物质符号化的真实再现:“他身边空无一物,只有头脑中的嘈杂之音和时间概念”,操纵着物欲横流社会的主人公尽享世界的奢华物品,却感到空无一物,徒留社会话语建构留下的意义或符号,其中时间就是话语建构的产物(德里罗,2003: 4)①。在消费主义时代,人们用货币兑换商品,难以看到商品作为物质的生产过程和空间移动,就像埃里克即使不惜巨款买下罗思科教堂,作为商人的他永远难以理解画家是如何与其他物质进行内在互动而创作,而画作本身作为物质又可以通过与人的内在互动引起心灵冲击,唤醒内心中“更深邃、更美妙的生命”(27)。在全球化时代,商品经过跨国运输和销售,人们更难以超越空间的限制思考物质在全球的生产与运动,就像埃里克触摸着豪车内意大利卡拉拉的大理石地板,他在乎的是地板出自五百年前米开朗基罗站过的采石场而体现的商品价值,而无法感知其内在的物质性。在信息化高度发达的社会,物质符号化达到了最高境界。随时随地可以进入的虚拟空间将人与其他物质的实质接触降到最低,人们在信息流中误以为可以操纵整个物质世界,其实面对的却是物质符号化的图表、数据、文字等等,在这里,信息成为物质的符号,人们在网络虚拟社会操纵的不再是可以看见触摸的实物,而是物质的概念。
《大都会》中,技术发展至上的理念加速了物质信息化的过程,相比德里罗《白噪音》中的电视拟像,连接世界、无孔不入的网络信息时代将物质符号化推到了极致。在小说中,屏幕作为信息的载体随处可见,埃里克的手表、掌中宝、豪车内的电脑电视、街道上的电子屏幕,推送着让人目不暇接的货币行情、新闻报道、股票动态等等。埃里克的豪车是他的信息处理办公室,所有物质转化成屏幕上“流动的符号、高山形图表和跳动的数字”,埃里克每天处理无数的信息,对他而言,信息就是“最爱和生命之光”(10-11)。生物圈(biosphere)也不再是人类与非人类自然物质互动而构成的集合体,而是由奔流不息的数据组成的世界,或者说让位于超现代(hypermodernity)的“技术圈”(technosphere)(Spretnak, 1999: 114)。在这个技术圈,身体可以超越物质性,转换成一组组信息。世界也变成了数字符号支配生命的地方,因为“在电子表格和由0和1构成的电脑世界中数字指令决定每一个行星上亿万生命体的呼吸”(21)。数字本是代表物质的符号,却在信息建构的世界中超越了物质,人们为数字所代表的信息疲于奔命,埃里克所代表的跨国资本家可以在信息流中叱咤风云,建立自己的金融帝国,莱文所代表的自由资本主义受害者也可以因为跟不上信息流的瞬息万变而倾家荡产、流落街头。
信息远离物质或者能指脱离所指也是物质符号化世界自我毁灭的重要原因。在信息化支撑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资产失去了“重量和形状”,数目就代表了资产的价值,老鼠变成了货币表明代表物质的老鼠也变成了货币符号,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可以操纵数据的人就可以忽视物质世界的约束而毁坏市场的正常运作(70)。掌握全球资本的埃里克自以为可以超越物质、凌驾于信息化世界,没想到最终卷入信息化旋涡:他大量购进日元,最终导致市场紊乱崩溃,个人破产,遭到莱文的追杀。物质的信息化也是个人身份危机的根源。埃里克“融入信息流”,像永不停息的信息流一样日夜不寐,他阅读大量科学文章和诗句以治疗失眠,但是这只是用传统信息的载体代替了网络信息流,他在无尽的信息流中远离了真实世界,试图挣脱身体的束缚,化变为操纵信息的理智(92)。进行体检时,埃里克看着屏幕上的心脏不确定是“心脏在电脑中的映射,还是心脏本身的影像”,与其相信心脏是自己肉身物质的一部分,他更被心脏的影像化符号而吸引(40)。对他而言,心脏是超越物质、超越肉身的存在,它让自己虚幻地认为“他的生命正以影像的形式在他身外轰鸣”(40)。这种超越身体、超越物质的妄想使他认为即使死亡,他的生命也不会终止,他可以“超越他的肉身,超越他的骨头上面的软组织,还有肌肉和脂肪”,他将“活在芯片上,活在光盘上,像数据一样活在旋转中”(189)。在德里罗的后现代世界中,埃里克作为人类物质的代表终究成为一个信息符号,这是其身份危机的重要原因,他活在德里罗书写的信息载体——小说中,他是技术发展至上的符号、是跨国资本主义的符号、是莱文将要书写的符号,更是德里罗本人向这个疯狂世界发出警告的符号。正是这些符号驱动了小说的显性叙事进程,从开头的“身无一物”到结尾超越肉身的“量子灰尘”,读者在符号化世界中目睹了埃里克人生的起伏,透视人类企图通过高科技与跨国资本经营超越物质的狂妄。由于物质的符号性已有学者探讨(朱荣华,2011;Davidson, 2012; 张琦,2017),也是后现代主义文化转向的突出特征,以下将重点探讨容易受到忽视的物质性叙事暗流。
物质叙事的暗流(上):物质自我的唤醒
尽管以《大都会》为代表的后现代文学被认为存在“物质性缺失”的缺陷,但是细读该作品,可以发现物质性更是一种消隐,而不是缺失。国内学者申丹(2013)指出,批评家往往聚焦情节的单一叙事运动,容易忽略叙事的隐性进程,“它与情节发展呈现出不同甚至相反的走向,在主题意义上与情节发展形成一种补充性或颠覆性的关系”。从《大都会》的开篇到结尾,也存在一股物质叙事暗流,它隐藏在物质符号化的叙事运动中,颠覆了情节中物质沦落为被社会话语建构的消极被动的物品、商品或符号的显像意义,这股暗流叙述着物质的本体性,即物质性,它与物质的话语性形成互补关系,反讽了人类超越物质、主导世界的狂妄。
全书分为两部分,以埃里克见证自焚、股市开始崩溃为分水岭,第一部的最后一句话“现在他可以开始生活了”是两部分的过渡句(95),这句话标志着埃里克从信息化跨国资本主义世界的呼风唤雨走向股市帝国崩溃后的自我毁灭,从“赌场资本主义”的大起大落到“精神家园”的回归(黄向辉,2012)。这句话也是物质叙事暗流的起伏标志,如果说这股暗流在小说的第一部还只是流淌在埃里克意识中的细流,最后一句话象征着埃里克“物质自我”(material self)的唤醒,那么这股细流在第二部变成汹涌的暗河,叙述着信息帝国的崩溃和物质欲望的毁灭,也讲述着物质自我的最终回归(Alaimo,2010: 20)。物质欲望是物质主义至上理念影响下对物质的占有欲,这里的“物质”是消极被动的物品或商品,而物质自我是对身体与其他物质本体性或物质性的肯定,是对“与广阔环境内在相连的自我”的认同(Alaimo,2010: 20)。通过认识到身体的物质性,埃里克在死亡的痛苦中拥抱了物质自我。
在第一部中,隐性进程中的物质性叙事只是细流暗现,体现于对非人类自然的感知和物质身体的回归,而这也是主人公的物质自我的觉醒过程。埃里克对自然物质的感触着墨极少,往往是稍纵即逝的意象。无眠之夜,他看到远方大烟囱上摇曳的“灰蒙蒙的烟雾”,漫不经心的一句话却隐藏着对环境污染的担忧(4)。即使埃里克并未明确表达远处的毒物污染与自己的联系,但在广阔的城市夜景中这幅画面的捕捉却渗透了“互相联系物质性”的理念,毒物将作用于人类身体和其他物质,对人类健康与城市环境造成巨大威胁(Oppermann, 2013)。对他而言,最华美的景色并非信息流中的数据和图表,而是“喷薄而出的太阳”,这说明埃里克并未完全将自己投入信息流的旋涡,因为自然的物质存在也不允许他忽视自然的物质性,富有生命力的太阳是自然万物生命力的来源,是人类与非人类自然物质具有施事能力的强大驱动(4)。当埃里克注视着“千百只海鸥追逐着顺流而下摇摆着的驳船”,他与自然物质也建立起共同拥有“又大又强壮的心”的联系,转瞬即逝的想法暗指埃里克要在全球资本帝国大开杀戒的雄心,但是也表明他无法忽视自己与海鸥为了生存共有的物质性(4)。不可否认的是,这些物质性的意识还只是物质世界被社会话语建构的主流下的暗流,就像埃里克在思索时眼前闪过的植物。他想起树木的植物学名字才“知道自己是谁了”:自我存在的参照物并非植物本身,而是植物的符号(29)。
除了对物质世界的感知,物质自我觉醒的关键是对物质身体的认同。在西方传统中,理智/身体是二元对立关系,理智优越身体,埃里克就是西方理智思维的化身,他是资本帝国的主宰者、信息技术的掌控者,即使健身锻炼,其目的也是为了“摆脱他的身体”(44)。物质生态批评认为有必要将“身体从话语的领域中解救出来,关注身体的经验与实践”(Iovino & Oppermann, 2012)。我们不仅要关注社会话语如何建构身体,也要注重身体的物质性,比如身体由各种物质构成,遵循万物新陈代谢、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与自然界其他物质存在物质交换(如空气、水、食物、毒物等等),并通过感官感知其他物质。
在第一部中,埃里克非常在意身体的健康,每天进行体检,对自己的前列腺不对称耿耿于怀,因为他潜意识中知道肉身和其他物质一样难逃衰老病死的自然规律,因为害怕肉身死亡,他竭尽全力想超越物质性的身体,实现自我在芯片中的永生,但是身体对痛苦、对死亡、对自然物质的感受和体验却将他一再拉回到身体物质性的现实之中。前列腺检查引起的疼痛通过神经在其全身蔓延,他不得不承认“他活在前列腺的疼痛之中,活在灼热的生理事实中”(46)。如果说这种疼痛只是让埃里克局限于对自我肉身的物质性感知中,那么对自焚者的痛苦感同身受却让其超越了小我,感受到所有肉身经历的痛苦。德里罗这里的描写层层递进,像镜头一样先用广角拍到整个画面,看到大家对自焚的反应,然后聚焦自焚者本身,看到他的皮肤烧成油泡,闻到空气中烧焦的肉味,进而让埃里克进入自焚者的内心,想象着他给亲人打电话、买火柴、内心挣扎,“想象着此人的痛苦、他的选择、他那可怕的意志力”(88)。这种艺术性写法将埃里克对身体物质性的感知扩大到对所有身体物质性的觉醒,淋着大雨的他将其感官向整个物质世界张开,“雨水拍打着他的脸庞,他感觉很好。对轿车上残留的尿液发出的酸臭味,他感觉也很好”(95)。大卫·艾布拉姆(David Abram,1996:ix)认为,技术的发展往往麻痹了身体的感知,我们需要走出技术的封闭空间感受身体的物质性,口眼鼻舌和皮肤是“身体接受他者滋养的门户”,物质身体是我们拥抱世界上无数物质“他者”的媒介,促使我们认识到与非人类自然物质共存相依的紧密联系。艾布拉姆提到的感性认知就是发现自我与其他物质相互联系的重要方式,埃里克在大雨中实现了物质自我的洗礼,拥抱了其他的物质“他者”,开始了新的人生。
物质叙事的暗流(下):物质自我的回归
小说的第二部是埃里克的死亡之旅,追求时速与利益的自由资本主义导致像莱文一样的底层人士家破人亡,他的复仇即是埃里克的毁灭。但是,隐性进程也见证了埃里克物质自我的回归,他在第一部的物质自我唤醒之后不得不面对物质的本体性,并最终在死亡中实现了物质自我的毁灭或回归。
这一部分记录了埃里克远离信息流、回归物质自我的旅程。在显性叙事进程中,他疯狂地网购日元,掀起的金融紊乱风暴最终导致破产,这种君临信息帝国带来的“自由”或“强大、自豪、愚蠢和优越”表面上象征着人类超越物质的狂妄自大,但在隐性进程中却是一种虚拟世界“理智”自我的毁灭(103-104)。埃里克“厌烦”了屏幕推送的拟像或虚拟世界,将车内屏幕推进车壁的内柜中,感受到“视线不受阻碍”,这是主人公远离高科技建构的虚拟世界的顿悟,是拒绝继续通过图表、数据、影像等符号观察或主导物质世界的开始(127-128)。这也促使他进一步接受身体的物质性。他“感到他的免疫系统正在酝酿一个喷嚏”,思考喷嚏是人体“对鼻腔黏膜的一种保护性反应,为了排出入侵的物质”,对身体的感知将他与自然中的其他物质联系起来:埃里克不再是孤立的自我,而是与环境中其他物质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自我(128)。他参与电影的裸体场景拍摄,感受到地面上黏着车辆碾压过的口香糖,“闻到了地面上的烟气味,泄露的汽油味,轮胎磨餐烤焦的沥青路面留下的气味”,“感受到周围所有肉体的存在,感受到它们的呼吸、热量、流动着的血液”(157-158)。一方面,埃里克的物质自我通过感官真实感受到与其他物质的紧密联系,即使令人不快的口香糖和汽油味也是真实物质世界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剥去人类文明的外衣,人类肉体和其他生命一样本质上都具有物质性,需要空气、能量和水分维持其生存。
埃里克物质自我的回归还包括对痛苦、对死亡的进一步认知。西蒙·埃斯托克(Simon Estok,2014: 130)认为,痛苦是人类本体研究的基础,解读物质叙事有必要理解“痛苦、物质和环境”之间的关系。身体是物质之间进行交换、互相作用的场所,痛苦是身体叙述这种物质之间内在互动引起不适的重要方式。痛苦可以“消解边界”,让痛苦者认识到身体像任何物质一样遵循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而其他物质的“物质性施事能力”可以给身体带来痛苦的体验,而最大的痛苦就是对身体死亡的恐惧(Estok,2014:134)。痛苦让我们认识到“身体的物质现实”,即人类并非居住于真空或虚拟世界中,物质性存在是人类身体经验的一部分,是人类“嵌入世界”的真实体现(Estok,2014:135,137)。如果说小说的前半部分埃里克被动地感受体检的痛苦和自焚者的痛苦,那么后半部分他将主动体验痛苦、认知死亡,并最终在巨大的痛苦中主动迎接死亡。
首先,埃里克主动体验痛苦。他命令女保镖用电枪击打他,他想体会强大电压下电击引起的身体痉挛和疼痛的“感觉”,这种受虐方式在显性进程中是埃里克在网络上击垮金融界带来自由快感的外在映射,但在隐性进程中也是他寻求物质身体回归的重要方式(103)。其次,埃里克主动认知死亡和体验死亡。在第一部中,埃里克对国际货币基金会总裁和俄罗斯媒体大亨的死亡幸灾乐祸,对无名自焚者的死亡萌发同情之心,而在第二部中,埃里克在说唱歌手费斯的葬礼上开始真正意义上认知死亡,并在自己的死亡痛苦中实现物质自我的回归。费斯的自然死亡表明身体作为物质始终遵循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就像其歌词,死亡是“回归本我”的方式,“虽已不在但还活着”象征着费斯的精神永存,但在物质叙事的暗流中却表明死亡是身体物质分解的开始,是肉体转换成其他物质形式存在的过渡(126)。死亡宛如物质的旋转之舞,它“溶成了液体状态,变成旋转液体,变成一圈圈的水和雾,最终消失在空气中”,死亡的肉体将通过其他物质形式而存在,从而进一步证明了身体的物质性(126)。埃里克为死者、为他人、也“为自己哭泣”,因为对死亡是万物必然规律的认知使其充满对肉体衰竭的恐惧(127)。在符号化的物质世界,他可以操纵信息流,可是,死亡将其推向“失去施事能力的恐惧”深渊,因为这种死亡痛苦是不可控制、不可避免的(Estok, 2014: 134)。如果说人类掌控万物是“自创神话”(self-mythologizing),那么痛苦和死亡就将人类从虚幻的神话中拉到了包括身体在内的万物拒绝人类操纵的残酷现实之中(Estok,2014:135)。
埃里克主动接受死亡是物质自我毁灭和回归的终极体现。他朝自己的左手手心开枪,忍受着烈火焚烧般的疼痛,“闻到上百万个坏死细胞的气味”(181)。疼痛消解了边界,他感觉自己被黑暗包围,又在黑暗的外面,“觉得自己同时处在包围圈的内外两边,感觉到自己,同时又看得见自己”,这是生与死的交界,也是身体与外在物质边界的消融,是肉体与世间万物融为一体的觉知(184)。唤醒的身体记忆穿越一生,回望到冬日身体的不适和失眠的夜晚,感受到大腿上的小瘤子,闻到香皂的杏仁味,听到膝盖疼痛的弯曲响声,这是物质自我在时间维度上刻下的本体性记忆。他曾想超越肉身化变为永不腐朽的量子灰尘,活在高科技芯片上,可是“疼痛却在阻碍他的不朽”,疼痛与“生命息息相关”,只要以生命的物质形式存在,他就无法逃避疼痛和死亡(189)。即使通过手表屏幕观看自己的死亡和头顶上甲虫的爬行,埃里克终将回到现实物质世界,看到“甲虫顺着垂悬的电线往下爬”,忍受着“全部生命的疼痛——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疼痛”(190-191)。埃里克的死亡象征着物质自我的毁灭,人体和其他万物一样最终通过新陈代谢实现不同物质形式的转化,因为物质是“内在互动的变化过程”,死亡就是这一转化的过渡,是“自我”与“他者”边界的消解,是物质自我投向物质世界的回归(Barad, 2008: 146)。
结 语
物质性的暗流与显性的话语性叙事在全书中此消彼长,随着埃里克的跨国资本与信息帝国逐渐崩溃瓦解,话语性叙事的主导性逐渐减弱,而物质性的叙事暗流愈加凸显,但是,二者总是互相纠缠,相互推动,形成了全书的双重物质叙事进程。根据物质生态批评理论,物质的物质性和话语性永远不可分割,当埃里克用自然规律阐释股票或货币的波动和市场周期时,其话语建构实际上植根于物质世界。同样,他也不能忽视前列腺不对称也映射着社会话语解释世界时需要考虑的不平衡、不规则。世界由无数具有施事能力的物质组成,物质之间的内在互动推进了世界的改变,埃里克的行为引起周围世界的连锁反应。德里罗通过莱文对埃里克的控诉,表达了对物质世界的人文关怀,只有认识到物质之间的内在互动,我们才能从物质自我的小我关注辐射到万千世界的大我关怀。从这层意义上讲,小说在语言游戏中用符号阐释这个世界如何用社会话语建构自身。同时,这种话语建构下面流淌着物质叙事的暗流,叙述着自我永远无法超脱的物质性,反讽了人类超越物质、掌控世界的狂妄。这种双重物质叙事不是揭示物质性和话语性之间界限分明,相反,符号化叙事与物质性叙事永远互相交融、互动互补。而小说本身就是德里罗与物质世界半路相遇、与有叙说功能的物质通过内在互动共同书写的产物。作品反思了跨国资本主义和技术发展至上对物质世界产生的摧毁性效应,用语言建构了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就在我们身边,像故事中的甲虫一样真实存在,展现着话语空间中的文化叙说和物质空间中“细致的美丽”(187)。
注释:
①小说《大都市》引文均出自: 唐·德里罗. 2003.大都会[M].韩忠华,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随文标明页码不再详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