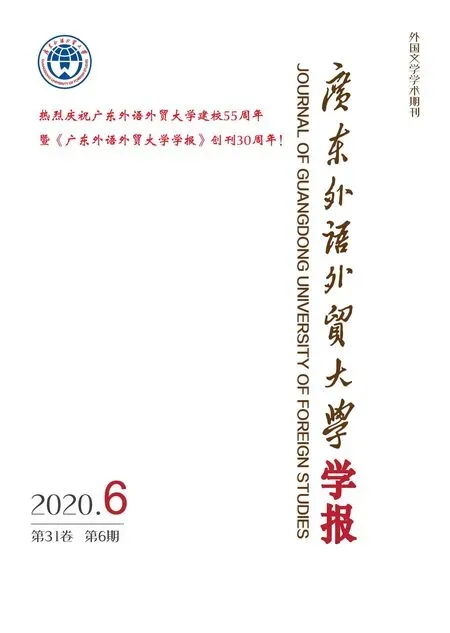努鲁丁·法拉赫《地图》中的身份认同危机
杨建玫 常雪梅
引 言
努鲁丁· 法拉赫(Nuruddin Farah 1945-)是索马里当代著名作家,第二代非洲作家中的领军人物。他享有较高的国际声誉,曾获得美国、英国的文学奖,包括享有“美国的诺贝尔奖”盛誉的纽斯塔国际文学奖(The Neustadt International Prize for Literature)。迄今为止他已创作十部长篇小说、一部剧作和一部论文集。法拉赫生长在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两国交界的欧加登地区,这里因领土争端而战乱不断,他也因此长期流亡国外。然而,他却始终忠于自己的祖国,“是典型的异邦流散作家”(朱振武,2019:143)。作为“一位关注政治与社会的作家”(林晓妍,等,2018:115),他认为自己“不但有伦理责任,而且有道德、伦理和哲学责任见证索马里的变化”(Farah,1986:284),并书写索马里在过去五十年间的独裁统治、内战和海外流亡者回到索马里的生活状况。
殖民历史造成的身份敏感是非洲作家写作的一个重要特征。“身份焦虑和身份认同是身份问题的两个方面。身份焦虑是身份问题的最初表征”(杨柳,2018:38)。对于难民来说,身份是其永恒的追寻目标,也是法拉赫四十年创作生涯中的一个主题,但他的独特性在于探索人物在流亡中的身份焦虑以及这种焦虑与索马里局势的紧密联系。他在小说《地图》(Maps, 1986)中,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之间发生的欧加登战争为背景,展现了索马里孤儿阿斯卡尔的身份焦虑及其身份认同危机与索马里民族、历史、国家和政治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法拉赫的身份书写动因、《地图》中阿斯卡尔的身份焦虑及其对索马里国家身份的追寻,探讨小说的身份认同危机主题。
法拉赫的身份书写动因
法拉赫的身份书写动因与索马里历史遗留的分裂及动荡局势和他长期在国外的流亡生活息息相关。身份是一个人在社会中存在的标识,如果一个人没有明确的国家身份定位,那么他就不会有归属感。作为索马里人,在法拉赫海外漂泊了大半生的时间里,面对空间错置和时代变迁,无根的他将注意力聚焦于人物的身份,而索马里的动荡局势使他更为关注身份,在小说中进行身份书写。
法拉赫的身份书写源于索马里——他的出生地的动荡局势,这是殖民侵略埋下的祸根。法拉赫一九四五年出生在意属索马里,成长于曾被英国和埃塞俄比亚先后控制的欧加登地区。由于西方殖民国家的侵占,欧加登的领土归属权长期存在争议。索马里在十九世纪因被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瓜分而四分五裂,索马里人不得不分别居住在周边几个国家,其中面积达三十八万平方公里的欧加登地区在一八九七年被划归到意属埃塞俄比亚。二战时英国盟军占领了意属索马里和欧加登地区,并在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四年与俄塞俄比亚签订协议,承认埃塞俄比亚对欧加登地区的主权。一九四九年联合国将意属索马里交意大利托管,此后意大利和埃塞俄比亚的边界谈判未能达成协议。一九六○年由英属索马里和意属索马里组成的索马里共和国宣布独立,索埃的边界争端便延续了下来。索马里独立后将欧加登地区划入版图,从此索埃在这一地区的武装冲突不断,一九六四年爆发了欧加登战争。虽然在战争初期索马里在苏联帮助下收复了欧加登,然而,随着两国关系破裂,欧加登重新被埃塞俄比亚占有。随后两国不断发生冲突,在一九七七年和二○○六年又爆发了战争 (刘易斯,2013:89-92)。
因战争所迫,法拉赫逃离了欧加登,后又因当局迫害不得不离开祖国。一九七七年,当欧加登战争又一次爆发后,法拉赫逃难到了摩加迪沙。但是,这一年他因小说《裸针》影射索马里当局的腐败、独裁和暴力而被通缉,从此他不得不流落异国他乡。他长期在美国、西德、意大利和印度及一些非洲国家任教,直到一九九六年巴雷政权倒台后,离开故土近二十年的他才第一次回到祖国。如今他主要在南非的开普敦和美国明尼苏达州大学任教。
长期的流亡生活使法拉赫不知该如何定义自己的身份。如果一个国家没有清晰的身份,那么它的人民也注定不得不去流亡。法拉赫生长在战乱不断且有边界之争的索马里,这也注定了他的国家身份不会明朗,他会产生身份焦虑感。在《地图》中,他意欲通过阿斯卡尔探寻自己的个人身份和索马里的国家身份。就像阿斯卡尔尝试通过与养母的亲密关系去追寻身份一样,法拉赫将自己与索马里联系起来去追寻身份,但是他并未在分崩离析的索马里找到答案。
面对分裂的索马里,法拉赫难以有归属感和国家身份感。在外流亡多年,法拉赫不知该如何面对这个破碎的国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尽管独裁者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最终下台,但是索马里却陷入更加悲惨的无政府境地,整个国家处于无序状态,百姓流离失所,索马里没有自己的国家身份,法拉赫对索马里的国家身份感也被残酷的现实破坏。霍米·巴巴(Bhabha,2015:26)认为,“被压制的人完全可以对占主导地位的殖民文化进行‘改写’……这是使自己的边缘生活方式、话语方式不至于过分恶化的重要前提”。这样就使后殖民的文化研究不再是单纯的政治斗争,而是一种文本领域的话语革命(王岳川,2001:66)。法拉赫作为被殖民者为索马里发声,是在通过创作进行话语革命。他无法在现实中实现国家身份认同,便试图通过阿斯卡尔的形象与国家历史的联结实现国家身份认同的目标。
索马里是法拉赫的精神支柱和创作的灵感来源。他的所有作品背景都立足于索马里本土,从一九七九年出版《酸甜牛奶》伊始,他创作的三部曲《非洲独裁统治主题变奏曲》《太阳里的血》和《回归索马里》均以索马里为背景,关注索马里的政治与社会。即使处于流亡之中,法拉赫的创作焦点仍旧是索马里的“个人、族群和国家的身份”(颜治强,2011),他书写非洲的独裁统治、索马里前独裁者巴雷的政权和内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法拉赫因其流亡的经历而不再属于索马里这个国家,因此他没有明确的个人身份。虽然被祖国“驱逐”,无法在世界上找到容身之处,但他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索马里人(Niemi,2015:331),也从来没有试图与祖国分离,加入他国国籍。在国外多年,他仍然心系祖国。面对动乱的索马里和流离失所的索马里人,他尽己所能以笔做武器为他们书写,为索马里发声,那是因为在他的心中有一个索马里梦。
阿斯卡尔的身份焦虑
作为流散作家,法拉赫的创作充满了身份不确定性危机。他通过流散文学创作对流亡情境下的个人身份进行思考,他笔下的人物因个人身份认同的缺失而焦虑。“作为一种自身的主观定位,认同是一种对所谓‘归属’的情感……认同在人文科学领域所寻求的是某种群体的归属意识的形成过程”(范可,2008: 5)。换言之,身份认同是“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陶家俊,2004:37),也就是一个人的文化和社会归属问题。法拉赫在《地图》中体现了一种本质主义身份认同观,即“身份是一种常驻不变的‘人格状态’”,是赖以确定人们权利和行为能力的基准,人们一旦从社会获得了某种身份,就意味着他获得了各种与这种身份相适应的权利,体现了整体、稳定、核心身份、归属感和同质性的本质主义身份观(杨柳,2018: 38)。阿斯卡尔内心深处的本质主义国家身份认同危机是他产生身份焦虑的根源。《地图》围绕阿斯卡尔的身份展开,展现了他的身份认同危机与索马里的历史、民族、国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阿斯卡尔的身份焦虑源于小说题目“地图”的意象。“地图”在作品中多次出现,隐含了小说的核心问题,那就是索埃两国在欧加登地区的领土之争,这一地区也是阿斯卡尔童年的生活地。虽然法拉赫是一位爱国作家,但并非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在书写这一战争时并未简单地判定某一方的对错。索埃的边界之争是因同一个索马里民族分布在不同国家引起的,这种跨界民族问题更为复杂。索马里在独立后与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的关系因跨界民族引起的边界问题日益恶化,它对埃塞俄比亚提出的领土要求主要涉及索马里族生活的地方,也包括索马里族为寻找牧区足迹所至的地方。李安山(2004:184)认为,“这种要求实质上是以立足于宗教和文化因素之上的民族主义为基础的”。法拉赫(1986:332)对于索埃冲突的观点是:“没有什么是绝对的泾渭分明,但是总是有‘临界地带’”。这显示出法拉赫并未一味地维护和促进本国族的自身利益,而是能够在创作中客观地反映史实。
由于阿斯卡尔出生的土地充满争端,他无法确定自己的个人身份。“我是谁?”成为阿斯卡尔从小就不断追问的问题,由此他开始了个人身份的追寻。“身份问题的核心是自我形象问题,自我形象的定位决定着发言立场和价值判断标准”(高文惠,2015:95)。小说开端以第二人称叙事视角描述了阿斯卡尔对此的思考和困惑:“你对你自己来说一直是个问题”(Farah,1986:2)。阿斯卡尔通过养母米斯拉讲述获知自己的出生状况,小说多次出现米索拉向他提及他出生时的场景:在他出生之前父亲已经去世,而母亲也在他出生时去世。这导致他一出生就没有身份,所以他总是在质疑自己的存在:“你有时怀疑你是否存在于你的思想之外,存在于你的头脑以及你的养母米斯拉之外。你似乎是头脑中的概念所诞生的产物”(Farah,1986:3)。这种第二人称的自我言说方式揭示出阿斯卡尔分裂的内心以及他对自身生命起源的困惑,身份成为萦绕在他头脑里挥之不去的阴影。
一个作家“为谁言说和从何种角度去言说却在所说内容的意义框架中起着关键作用”(高文惠,2015:95)。法拉赫采用复杂的叙事结构,将阿斯卡尔的身份危机突显出来。各章分别从单数第一人称、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的叙事视角依次展开:第一人称叙述者是阿斯卡尔虚构的自我,“我”表达了试图重建索马里历史的民族主义梦想,也暗含着“我”内心对养母米斯拉的依恋情感和“我”通过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对身份的追寻;第二人称视角是阿斯卡尔的内心独白,表现了他内心分裂的自我,象征着他与米斯拉之间亲密的依恋关系;第三人称是全知全能的视角,以线性顺序客观书写与索马里国家身份相关的政治事件,并对阿斯卡尔的梦境进行描述。这种后现代叙事手法凸显了法拉赫对人物身份的关注和阿斯卡尔对身份的敏感度。
阿斯卡尔因父母双亡而身世不明,便努力找寻自己的个人身份。他首先通过自己与米斯拉的亲密关系来定义个人身份。弗洛伊德(2016:132)曾用身份认同来解释一个人对于他人的归属感,所以这就不难解释阿斯卡尔也有归属于父母双亲的需求。在米斯拉的关心和爱护下,阿斯卡尔渐渐通过她来找寻自己的身份。他作为一个孤儿得到了这个埃塞俄比亚女人的爱,成为她的儿子,这种母子间的亲情纽带有助于阿斯卡尔来定义自己的个人身份。他将米斯拉视为他的宇宙,感到“我是她投射的影子的一部分,我是她延伸的自我,是围绕着她的地理空间”(Farah,1986:75)。法拉赫模糊了阿斯卡尔与米斯拉的身体界限和性别界限,“两人达到了心灵的沟通和交融”(Kazan,1993:257)。阿斯卡尔有寻求归属感的本能需求,所以他选择通过米斯拉的存在和他对米斯拉的爱来建构个人身份。
然而,米斯拉的埃塞俄比亚身份成为阿斯卡尔身份焦虑的另一个原因。随着阿斯卡尔逐渐长大,他通过米斯拉建构的身份随着欧加登战争的爆发开始动摇。米斯拉作为来自敌对国的异族,处于危险的生存境地。当人们怀疑她是间谍时,她的身份变得更加可疑,阿斯卡尔的身份也随之不确定,这导致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份。他逃往摩加迪沙,并在舅舅希拉尔的帮助下成为索马里公民。然而,他对米斯拉的情感使他又陷入了困惑:她可能是背叛索马里的叛徒,这使他不知该如何面对她。阿斯卡尔日益上涨的爱国情感使他逐渐与米斯拉疏远。“如果一个人不具备明确的身份定位,那么他生存在世界上就没有归属感,也就无法拥有正常人的权利和自由”(张其学,2017:39)。阿斯卡尔因身份迷失而没有归属感,他对自己的身份充满了困惑和焦虑。
一个孩子长大成人后会将归属于父母的需求转化为归属于更大群体的需求。身份是“一个人(群体、阶级、民族、国家等)所具有的独特性、关联性和一致性的某种标志和资质,这种标志和资质既使他的身份与其他身份区别开来,又使他的身份可以归属到一个更大的群体身份中”(张其学,2017:114)。在摩加迪沙,少年阿斯卡尔将视野转向更为广阔的天地,他试图将自己归属到索马里的群体身份中。他的家庭教师卡斯曼不断提醒他,他是来自欧加登的孤儿,他的使命是肩负起解放欧加登的责任,这使阿斯卡尔获得了生存的意义和价值。然而,随着欧加登的局势日趋紧张,他又面临人生重大抉择:他是应该去上大学,还是加入西索马里解放阵线,为欧加登的解放而战?然而,索马里人最终失败了,阿斯卡尔也被告知他的养母是背叛了索马里战士的叛徒。身为米斯拉的儿子以及索马里人的双重身份使他陷入了理智与情感的较量之中,他的心理危机围绕米斯拉是否是叛徒得以呈现,他不知究竟该如何确定自己的身份。在情感上阿斯卡尔热爱给予他幸福童年的母亲,感到应该为她报仇,但是在理智上他认识到自己应该为索马里的统一而战。最终米斯拉被杀,阿斯卡尔的精神世界也随之崩溃。他的复杂身份使他的内心自我分裂了。
小说中多次出现阿斯卡尔的奇幻梦境,这也反射出他对个人身份的困惑和焦虑。第三人称叙事视角是法拉赫展现阿斯卡尔梦境的手段。第三章阿斯卡尔在一个花园里漫无目的地奔跑,沿途他看到很多人用刺青来标明他们的名字、民族和归属地,当他想与这些人沟通时,他们突然消失不见了。阿斯卡尔感到莫名的空虚,他开始质疑人类存在的意义。后来他遇见了一条象征血脉纽带的蛇,也遇见了米斯拉,但她突然也消失了。于是他开始质疑米斯拉的存在,甚至怀疑他自己的存在。阿斯卡尔的梦中花园代表着人类起源的伊甸园,而花园也隐含了他不明的身份起源(Husband,2010:80)。阿斯卡尔的梦境显示出他希望有一个身份的梦想。
阿斯卡尔追寻身份的曲折过程显示他的身份焦虑不可避免。“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自己在社会中的身份,这样才能实现自己的独特价值”(Taylor,1992:275)。如果一个人知道他是谁,那么他就会知道他身在何处。阿斯卡尔曾尝试通过切断他与米斯拉的亲密联系来将自己定义为忠诚的索马里人,然而,米斯拉的死使他意识到米斯拉是他的宇宙,他的身份也随之破碎。最终阿斯卡尔不仅没有获得情感自由,也失去了自己的身份。阿斯卡尔复杂且多变的身份使他不知道生活的意义何在,而他将会终其一生去追寻身份。
阿斯卡尔对索马里国家身份的追寻
《地图》不仅表现了阿斯卡尔的身份焦虑和追寻,还展现了他对索马里国家身份的追寻。本尼迪克·安德森提出,国家是一个自然概念和文化概念,作为联结某一社群成员关系的国家身份包含着许多假想和虚构的文化和政治因素(Anderson,1991:7)。索马里的国家身份建构过程处于英国殖民历史的话语范畴之内,是西方殖民历史的产物。小说题目“地图”突出强调了索马里的国家身份是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也吸引着读者关注欧加登地区的领土之争。
确切地说,殖民国家对索马里领土的争夺使欧加登地区的归属权不断变更,这导致索马里的国家身份模糊不清,这也是阿斯卡尔从追寻个人身份转向追寻索马里国家身份的原因。法拉赫曾说,他童年时生活在欧加登的卡拉福,那是一个“有说索马里语的平民人口,一个从事商业活动的大型阿拉伯社区,以及说阿姆哈拉语的士兵……招募自埃塞俄比亚帝国的所有民族的士兵”(Farah,1986:332)。这不仅显示出欧加登人员混杂、民族众多的特征,而且其归属权也模糊不清,这些因素导致索马里的国家身份不明。
生活在这样一个有着复杂局势的地区,阿斯卡尔开始利用地图追寻索马里的国家身份。他从希拉尔那里得到一张地图后,便试图通过识别索马里的具体领土范围来确定他的索马里身份。欧加登战争爆发后,这张地图成为凝聚索马里人力量的有力工具。许多邻居来到阿斯卡尔家,用阿斯卡尔的那张地图来定位索马里军队将会收复的土地。他们渴望索马里统一,地图增强了他们同为索马里人的认同感。然而,米斯拉总是不合时宜地担心索马里军队是否会胜利,而这对于索马里人来说无疑是对索马里军队的不信任。阿斯卡尔由此意识到米斯拉和他们不一样,感到她站在了索马里人的对立面,便开始疏远她。阿斯卡尔与米斯拉的亲密关系被他的国家身份感破坏。
事实上,世界上有争端的地区是因西方殖民者绘制出边界模糊的地图而人为制造的产物,是殖民国家遗留给第三世界国家的祸根。斯图亚特·霍尔认为,“国家身份的形成是表征、符号等结合的复合过程。在国家身份的建构过程中,叙事作为一种媒介起到建构社群的共同认知的作用,而话语掌控者经常选择对国家本质最具表现作用的素材加以发挥利用,这种利用往往会导致对历史真实的背离”(Hall,1996:4)。英国殖民者作为话语掌控者,为了自身利益才绘制出所谓“官方认可的”欧加登地区的地图。英国不顾索马里人曾拥有欧加登地区的史实,强加给索马里边界界限不明的地图,才导致索埃两国的领土之争不断。这与印度和巴基斯坦争夺克什米尔地区一样,是英国殖民者的殖民压迫和强权统治遗留下了后来的战争恶果。
对于英国殖民者划定的地图所具有的所谓“历史真相”,法拉赫通过希拉尔之口进行批判。希拉尔曾这样给阿斯卡尔解释制图师工作的政治内涵和帝国主义者的意图:“地图上有真相:欧加登作为索马里的一部分是真相,但是对于埃塞俄比亚的制图师而言,这不是真相”(Farah,1986:125)。作为索马里人,希拉尔拒绝承认西方殖民国家划定的边界,在他看来,索马里本应是个统一国家,如今却被分解到肯尼亚、吉布提和欧加登,而欧加登本应属于索马里。虽然索马里在战争中失去了欧加登,但是希拉尔认为,地图上划定的欧加登的边界并非真相。受希拉尔的启发,阿斯卡尔重新审视地图,把它看作是两国边界的标记。在重新了解了索马里的地理政治后,他认识到,“我涂画的不是欧加登,而是西索马里。在某种意义上,这就使欧加登失去了其特殊身份”(Farah,1986:217)。在此阿斯卡尔接受了关于地图的事实:地图作为边界标记,在人为干涉的政治和军事行动后很容易被扭曲,所以地图永远是统治者的统治工具。“对于被殖民者来说,地图如同一个剧场,他们必须在这个剧场里把自己的界限内化”(Ngaboh-Smart,2001:96)。法拉赫借此指出,地图上的边界是英国殖民者人为划定的,它歪曲了历史真相。这隐含了他对英国殖民者把欧加登从索马里划分出去的霸权行径的谴责。正是因为英国殖民者绘制的欧加登地图边界模糊,才开启了索埃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领土之争。由于索马里的国家身份模糊不清,导致其战乱不断,给索马里人带来了流离失所的痛苦生活和身份问题。
法拉赫(1986:168)通过地图这一意象表达了他对西方殖民者书写的“大写”历史的不满。他借希拉尔之口指出,所谓的“历史真相”就是“那些能接触到书写系统的人书写历史后,把它强加给那些无法接触到书写系统的人”。他以此解构了西方殖民强权政治的宏大叙事,对西方殖民列强侵占剥削非洲国家予以谴责。如同法拉赫一样,近年来,一些后殖民国家的作家在作品中挑战西方的种族中心主义殖民话语,书写西方强权国家地图上忽视的空间,颂扬前殖民地被殖民文化的多样性和多民族特征,这些文化以前被殖民文化所忽视。法拉赫在谈到非洲的殖民地图时说,“我们应该根据我们的经济、心理和社会需要重新绘制,而不是接受从我们的区域划分出来的荒谬的边界”(Wright,1992:34)。这是法拉赫对西方列强强加给索马里人的所谓边界的否定,他解构了西方殖民者的宏大叙事,否定了殖民历史遗留的地图所划定的边界的真实性。
阿斯卡尔不断增长的国家意识促使他借助地图在内心重新绘制索马里的边界,索马里的国家身份也变得清晰具体。他像个制图工一样在地图上绘制出被索马里人收复的领土,并重新画出讲索马里语的大索马里地区,以此来发现并记住自己的国家身份。阿斯卡尔通过这张地图了解索埃战争的进程,以此来定义自己的索马里身份,因而地图又成为国家身份的隐喻。
然而,随着战争以索马里的失败告终,阿斯卡尔对索马里国家身份的追寻也陷入了困境。欧加登被埃塞俄比亚统治,索马里的文化生存权随之面临巨大挑战。当地的索马里人不得不接受埃塞俄比亚的文化殖民统治。索马里语被取代,失去了管理自己人民的权力和发声的权力,也失去了生存的权利和土壤。“对于前殖民地国家的人民来说,殖民话语对他们最大的文化伤害是自我的被贬损、被压抑、被剥夺。自我的被迫丧失导致前殖民地人不停地追问‘我是谁’的问题”(Linnes,2007:56)。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索马里。索马里人失去了与索马里文化的联系,使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面临消亡的命运,其国家身份也不复存在。阿斯卡尔为此深感悲哀。
战争是索马里失去国家身份的直接原因。小说也是有关战争和战争的灾难性影响的故事, 法拉赫曾将这场战争与毕加索的著名画作《格尔尼卡》(Guernica)联系起来,认为它们都表现了相似的战争主题(Wright,1992:37)。《格尔尼卡》采用碎片化的表现形式生动展现了德国纳粹残酷杀害无辜犹太人的场景,勾勒出战争给百姓带来的无尽伤痛,而小说也有类似的意象。在小说结尾,阿斯卡尔的几个监护人都失去了身体的某部分器官,这些意象预示着欧加登地区的进一步分裂。在小说结尾,那些逃离了欧加登战争的人无家可归,成为难民。索马里就这样被瓜分,欧加登人失去了家园,不得不流落到异国他乡。如果把米斯拉看作母性象征的话,那么她最后被肢解也代表了索马里人对祖国统一梦想的终结和一个统一的国家身份的瓦解。
对于整部作品回荡的阿斯卡尔的问题 “索马里到底在哪里?”,也许从福柯对权力话语的知识谱系学分析中可以找到回答,那就是英国殖民者“通过战略和战术对领土的移置、分裂、分配、控制……就构成了某种地理政治学”(王岳川,2001:38)。如果一个人无法识别祖国的边界,那他又如何定义自己的身份? 在索马里失去欧加登之时,阿斯卡尔重病以及米斯拉的失踪和死亡都象征着索马里人在国家统一进程中遭受的挫折和痛苦。从此索马里仍然处于分裂状态,其国家身份仍旧模糊不清。
结 语
索马里的战乱以及法拉赫长期在外流亡的无根状态成为他在《地图》中关注阿斯卡尔的身份认同危机和索马里国家身份追寻的出发点。阿斯卡尔对个人身份的焦虑和索马里国家身份的追寻反映了法拉赫本人的身份追寻。他试图通过探索人类的生存本质明确自己的个人身份,他的流亡经历使他的身份主题书写意义深远。
身份是一个流动的过程,它从来不是完整的,而是一直处于建构中,并派生于个体在阶级、种族、性别、族群、宗教等方面(任宏智,2020)。《地图》把阿斯卡尔的身份、索马里的国家身份与索马里的局势联系到一起,他的身份焦虑和他对索马里国家身份的追寻与索马里和欧加登地区复杂的民族历史、国家、政治状况息息相关。阿斯卡尔试图寻求“一个独特的索马里身份”,但他养母的异族身份和他的出生地欧加登地区四分五裂的状况打破了他想要获得“真正的”索马里身份的梦想。当整个国家的命运被他国掌控时,索马里的国家身份也变得更加不明朗。在索马里这个分裂国家的背景下,阿斯卡尔的身份追寻注定会失败。
法拉赫通过阿斯卡尔反映了他本人对个人身份和索马里国家身份的追寻和渴望,他以此表达了对动荡不安的索马里局势的担忧。然而,像其他后现代作家一样,法拉赫绝非只是为了展现索马里的混乱局势而书写,也并非仅仅为了表现阿斯卡尔对索马里局势的困惑而写作。四十年来,尽管法拉赫一直在国外流亡,但他却始终围绕索马里的局势持续进行书写,他的小说只专注于索马里人的生活和命运(Riggan,1998:701)。身份成为法拉赫心中的一个结,但是他在书写索马里的混乱和他的困惑背后,仍旧对祖国的统一和未来怀有希望。他希望以自己的书写引起国际社会对索马里问题的关注,同时也树立索马里的文化威信,让世界认识到索马里并非只有海盗、战乱、贫穷,还有灿烂的文化。虽然在《地图》的结尾阿斯卡尔前途未卜,但是法拉赫是在“无望”和“无序”中寻找“希望”和“有序”,在混沌中寻找光明,他是在以这种方式激发索马里的民族凝聚力,表达他对祖国美好未来的期盼,这反映了他对索马里的统一、稳定昌盛以及索马里人能够拥有身份归属感和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