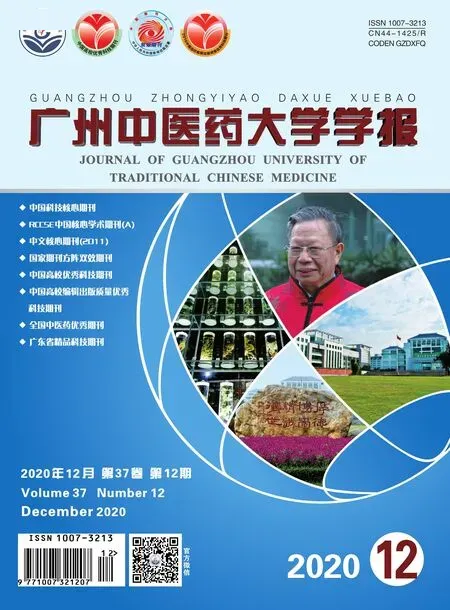唾液代谢组学技术在中医脾肾证候与疾病研究中的应用探讨
郑欢, 秦书敏, 吴皓萌, 黄马养, 黄绍刚, 李建华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广东广州 510006)
唾液是由口腔内的多个腺体分泌的混合物液体,具有辅助消化、清洁口腔中食物残渣、保持口腔清洁和濡润作用。唾液的成分复杂,不仅包含水分,同时包含血浆中的各种蛋白成分[1]。现代研究发现,唾液成分的改变与多种疾病的发生密切相关[2]。“脾在液为涎,肾在液为唾” 是中医脏象理论的重要内容,从唾液角度来研究中医脾肾脏象的内涵,或开展脾肾相关疾病唾液的微观客观指标和生物学标志物的研究,对于发展中医特色的微观辨证学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脾肾证候的诊断和预后中具有现实的应用价值[3]。以下采用唾液代谢组学方法探讨开展基于中医理论 “脾在液为涎,肾在液为唾” 研究脾肾证候与疾病的依据和优势。
1 唾液代谢组学
代谢组学又称代谢物组学,是研究集体代谢产物谱变化的一种方法。代谢组学借助高通量、高灵敏度与高精确度的现代分析技术,动态跟踪细胞、有机体分泌出来的体液中的代谢物的整体组成,以寻找代谢物与生理病理变化的相对关系[4]。随着系统生物学的发展,唾液代谢组学的研究展现出了巨大的优势:(1)唾液作为机体代谢物的一种,含有一系列具有重要生物学功能的物质,血清中的很多成分在唾液中也有一定的反映;(2)唾液具有取材非侵袭性、安全、易获取及廉价的优势;(3)唾液代谢组学具有整体、动态的优势,与中医的整体观、辨证论治不谋而合。
2 唾液可反映脾肾的生理与病理
《素问·宣明五气篇》 曰:“五脏化液:心为汗,肺为涕,肝为泪,脾为涎,肾为唾”。“涎” 和 “唾” 均为口腔分泌物。《辞源》 载 “涎为口液”“唾为唾沫”,认为质地清稀、流动性大、流出口腔者为涎;质地黏稠、流动性小、需吐而出者为唾。但由于二者都分泌于口,临床上很难截然分开,因此人们习称为 “唾液”。
2. 1唾液与脾脏“脾在液为涎” 始载于《黄帝内经》。中医学认为,涎乃脾之液,由脾脏所主,液入于脾为涎,涎出于脾而溢于胃[5]。
脾在液为涎,一方面因为脾主运化水谷与水湿精微。“脾为胃行其津液”,口中之涎液倚仗脾之化生和制约,既不溢于口外酿成滞颐(口角流涎),也不会少涎干涸而致口咽干燥。另一方面因与经络循行有关。足太阴脾经,起于足大趾内侧端,上行挟咽连舌本,散舌下。从唾液腺所在的解剖位置及其开口部位来看,正属于足太阴脾经的循行所在,此提示 “涎即为唾液”,唾液与脾的生理功能直接有关。另外,脾主升清,能将水谷精微及津液上输肺与头目,其功能正常,则津液上注于口而为涎,以辅助脾胃的运化功能,且不溢出口外;若脾胃不和,则导致涎液分泌异常,如口干或滞颐,甚则出现口中味觉异常等。
2. 2唾液与肾脏肾在液为唾,是因口中唾液是由肾精灌注舌窍而成。肾精能上注于舌,乃因“肾足少阴之脉……循喉咙,挟舌本”(《灵枢·经脉》),“唾生于舌下,足少阴肾脉循喉咙挟舌本也”(《类经·疾病类》),“少阴根于涌泉,结于廉泉”(《灵枢·根结》)。可见肾中藏纳之精,通过肾之经脉,由足上行至舌根,而舌下之廉泉,又是足少阴肾经的经气流注归结之处。肾之阴液由经脉上行,自廉泉出于舌之端而为唾。若肾之精气充盛,则可蒸化摄纳津液,上承于口,使其津常润,致口中和合,食饮甘味,且可灌注脏腑,润泽肢体肌肤;若肾之精气不足,温煦、蒸化、摄纳、封藏失常,则可出现多唾、久唾或少唾、无唾等唾液泌泄失常之病证。
因此,脾肾功能与唾液的生成、分泌、组成及质地均具有密切的关系;脾肾功能异常均能导致唾液的变化。
3 唾液代谢组学技术在中医脾肾证候与疾病研究中的应用
上文已述唾液在中医理论中与脾肾二脏关系密切,而唾液由脾肾所主,唾液的生化输布离不开脾肾二脏,此二脏的功能及物理变化会反映在唾液中。“见微知著”“司外揣内” 是中医诊治疾病的主要思维方式与研究方式。相应地,唾液的细微变化也可反映内在脾肾的功能情况。
目前关于 “脾在液为涎,肾在液为唾” 理论的研究,仍无统一的研究方法,但大多数以唾液为基本研究物质,或从实验模型动物出发,研究脾虚、肾虚动物的唾液指标的变化,或从临床疾病出发,研究患病人群脾肾相关证型的唾液变化或与正常人群唾液对比的差异性研究。
3. 1唾液代谢组学技术在肾虚证候研究中的应用研究表明,唾液的分泌量、蛋白含量、流动速度、免疫功能的强弱、重要细菌的检出率和组成比均受肾阴肾阳的调控[6-8]。Chen M J 等[9]基于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GC/MS),以氢化可的松构建肾阳虚模型,结果显示肾阳虚模型组动物尿液的代谢物谱与对照组比较具有明显的差异,在代谢图上反映出有规律的分布,且予以温肾阳中药肉苁蓉干预后,肾阳虚动物的代谢物谱又与模型组动物出现差异,其在代谢图上的分布与模型组动物不同,更接近正常组动物。同时,巩振东、孙理君等[10-11]研究发现肾虚证大鼠的白细胞介素6(IL-6)、唾液溶菌酶升高,分泌型免疫球蛋白A(SIgA)降低,揭示了大鼠肾虚证与唾液免疫有一定的关系;予以补肾阳方剂右归饮干预后,模型组紊乱的免疫功能恢复正常,萎缩及破坏的唾液腺得到恢复。另外,该课题组以 “正常体质-肾虚体质-肾虚证候” 动态演变过程为出发点设计动物实验,发现与正常体质对照组大鼠比较,肾虚证候模型组大鼠唾液中二十碳五烯酸、二高γ-亚麻酸、苯丙氨酸、牛磺酸、6-甲基腺嘌呤含量下降[10]。
3. 2唾液代谢组学技术在脾虚证候研究中的应用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脾为后天之本。脾气虚弱必然影响到多脏器的功能活动和物质代谢过程,并最终在代谢产物中体现出来,引起 “涎(即唾液)” 的代谢物变化。赵晓山等[12]采用病证结合的方法,以核磁共振仪(NMR)测定住院及门诊患者唾液中的代谢物,发现与正常健康者比较,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病以及亚健康状态等脾气虚证患者唾液中的成分比率发生了变化,脾气虚证组唾液中主要含谷氨酰胺、蔗糖、乳酸盐、苯丙氨酸等物质,且含量相对较高。郑丽红、孙理君等[12-13]以脾虚大鼠模型作为研究对象,发现其IL-6、唾液溶菌酶水平升高,SIgA 水平降低,提示大鼠脾虚证与唾液免疫有一定的关系;且予以健脾方四君子汤干预后,模型组紊乱的免疫功能恢复正常,萎缩及破坏的唾液腺较前恢复。有研究[14]指出,唾液流速在健康对照组、脾阴虚组、肾阴虚组3 组中呈递减趋势(P <0.05);单位时间内唾液中的唾液溶菌酶含量脾阴虚组、肾阴虚组较均健康对照相降低(P <0.05),而脾阴虚组与肾阴虚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另有研究[15]表明,与正常健康者比较,安静状态下脾虚患者唾液淀粉酶活性升高,酶活性比位小于1。这些证据均支撑了 “脾主涎” 理论的科学内涵。
3. 3唾液代谢组学技术在疾病研究中的应用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代谢组学对生物流体(如尿液、血浆)的分析已经产生了大量且不断增加的研究成果。目前有关唾液这一最容易获得的人类生物流体的代谢组学分析已经滞后,但唾液代谢物作为诊断生物标志物的潜力是巨大的。
3. 3. 1 在口腔疾病研究中的应用 通过唾液代谢组学技术检测发现,唾液代谢物的变化与口腔癌、口腔白斑、牙周疾病、龋齿有关[16-17]。Sugimoto M等[18]运用毛细管电泳飞行时间质谱法对健康人和口腔癌患者的唾液进行代谢分析,发现口腔癌患者唾液中的丙氨酸、牛磺酸、亮氨酸/异亮氨酸、组氨酸、缬氨酸、色氨酸、谷氨酸、苏氨酸、肉碱、胡椒酸水平均升高,且鉴别出不同于健康受试者的胆碱、甜菜碱、派可林酸和肉毒碱比率。在牙周炎研究方面,有报道指出牙周炎患者唾液里的溶血脂类水平、单酰甘油水平、脂肪酸水平、甘油磷脂产物水平、三酰甘油降解水平均升高,可能与牙周炎患者的脂肪酶上调有关,其或可作为牙周炎代谢物标志。龋病的发生与变形链球菌有关,发展与乳酸杆菌相关,成人龋患者唾液中的乳酸杆菌检出率高达90.2%[19]。
3. 3. 2 在肿瘤疾病研究中的应用 Sugimoto M等[18]对前列腺癌患者的唾液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前列腺癌患者唾液中的丙氨酸、亮氨酸/异亮氨酸、组氨酸、缬氨酸、色氨酸、谷氨酸、苏氨酸、肉碱水平升高,牛磺酸水平降低。尽管该课题组的系列研究遵循了大致相似的方法,试图找出患病个体与健康对照者之间的差异,但样本收集和制备方法、所使用的分析平台和所使用的统计方法却存在很大差异,且缺乏多中心试验进行系统评价,因此目前在临床上作为生物标记物的诊断价值不大,需要通过更系统与严谨的深入研究验证后,其结果才能用于临床。
3. 3. 3 在其他疾病研究中的应用 唾液代谢组学技术现已拓展应用至原发性干燥综合征、阿尔茨海默氏病、帕金森氏病、艾滋病、乙肝、肥胖等,有望为这些疾病的研究提供潜在生物学标志物。
综上,依据中医 “脾在液为涎,肾在液为唾” 的理论,唾液的质与量的变化可反映脾肾二脏功能的变化。应用唾液诊断技术研究脾肾二脏的相关证候与疾病(包括但不限于临床表现、内在实质及其临床诊断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临床意义。但目前关于脾肾与唾液的相关研究,主要停留在简单的理化指标检测水平,研究内容相对单一,研究深度及广度尚浅。故目前研究只能解释某一现象,无法从整体上系统、动态地揭示脾肾与唾液关系的内在机制及唾液对脾肾二脏相关疾病与证候的临床诊断价值。 今后的研究应从中医学整体观念出发,应用代谢组学技术,基于唾液与脾肾之间的相关性,通过大数据分析进一步挖掘唾液与脾肾二脏的关系,寻找脾肾二脏证候与疾病的唾液标志物,开展脾肾脏象相关证候与疾病唾液微观辨证客观指标和生物学标志的研究。这将既有助于全面阐释中医 “脾在液为涎,肾在液为唾” 理论的科学内涵,也为临床开展脾肾二脏疾病与证候的无创诊断技术和微观辨证研究奠定基础。代谢组学技术与唾液诊断技术相结合,可为中医脾肾证候及疾病的诊治提供客观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