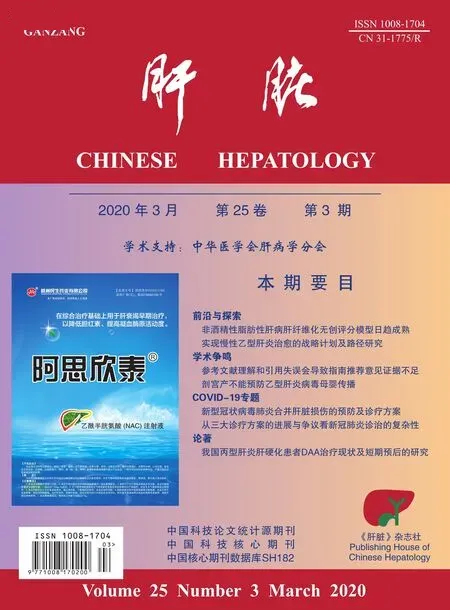对《中国乙型肝炎病毒母婴传播防治指南(2019年版)》的若干探讨意见
徐陈瑜 陈廷美
近期,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发表了《中国乙型肝炎病毒母婴传播防治指南(2019年版)》(简称《指南》)[1],并引发了学术讨论[2-3]。针对《指南》某些推荐意见,结合自身从事预防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阳性母亲的乙型肝炎病毒(HBV)母婴传播的经验和查阅的资料,将若干认识整理如下,与作者作一探讨。
一、《指南》推荐意见 1:婴儿在7~12月龄检测项目问题
《指南》推荐意见 1建议“婴儿7~12月龄静脉血检测HBsAg和(或)HBV DNA”,而没有建议检测乙型肝炎表面抗体(抗-HBs)[1],而在回复中解释“任何一部指南都不可能回答所有的临床问题,只能优选当前最重要、紧迫和需要的”[3],我们认为这不是遗漏抗-HBs检测的理由。指南确实不可能包罗万象,但也不能缺少重要内容。HBsAg阳性母亲的婴儿在7~12月龄检测抗-HBs,是预防母婴传播的重要环节,其中1%~3%婴儿对乙型肝炎疫苗无应答(接种第3针疫苗后1~5个月抗-HBs<10 mIU/mL),他们是感染高危人群,需要及时再次接种3针疫苗,这是重要内容。因此,7~12月龄除了检测HBsAg外,还需要检测抗-HBs。
《指南》建议婴儿在7~12月龄检测“HBsAg和(或)HBV DNA”,其中HBV DNA检测缺乏根据。HBsAg阳性母亲的婴儿,经正规联合免疫预防后,总体感染率仅1%~3%。检测HBsAg和抗-HBs,足以明确有无感染和免疫力,无需通过检测HBV DNA诊断或排除感染。试图通过检测HBV DNA而确定婴儿隐匿性HBV感染,缺乏循证医学证据[4]。报道的婴儿隐匿性HBV感染,几乎为检测过程污染所致[5]。即使是HBsAg阳性婴儿,定量检测HBV DNA也并非必须。
而且,以笔者所在妇幼保健院系统,我国大部分妇幼保健院和基层医院不开展 HBV DNA检测。如果让这些婴儿再到综合医院或传染病院进行不必要的HBV DNA检测,是浪费资源,给家长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增加婴儿院内其他感染风险。因此,婴儿随访时,不应该提出检测HBV DNA这一建议,既无必要,也不符合国情。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产科学组制订的指南和欧美国家的指南,均没有建议婴儿在7~12月龄检测HBV DNA[6-8]。
二、《指南》推荐意见 1:脐血检测问题
《指南》引用会议摘要(《指南》参考文献6)描述“婴儿出生24 h内静脉血或脐带血HBsAg和(或)HBV DNA阳性率显著高于6月龄、7月龄或12月龄静脉血检测结果”,这让读者无法理解是否需要检测脐血。我国许多医院(包括我院)曾一度广泛开展脐血或出生后24 h内检测HBV标志物,错误地将阳性结果误认为宫内感染,浪费医疗资源,导致恐慌,而没有任何临床价值。我国产科学组制订的指南明确指出“不建议在6月龄前检测HBV血清标志物”(包括脐带血或新生儿出生数日内)[6],笔者所在医院不再检测脐血HBV标志物,其他医院这类不合理的医疗行为也越来越少。新生儿的脐带血或生后24 h内HBsAg和/或HBV DNA阳性,只能说明存在暴露,不能确定婴儿感染[9-10],而6~12月龄检测阳性,可以确定感染,将2种不同意义的阳性结果进行比较,缺乏科学性。
三、《指南》推荐意见2 :孕妇抗病毒治疗的HBV DNA阈值问题
《指南》推荐意见2:“HBV DNA≥2×105IU/mL的孕妇,推荐口服抗病毒药物以阻断母婴传播(1B),1×104IU/mL ≤HBV DNA<2×105IU/mL时,可与患者充分沟通后决定是否干预(2C)”。高病毒水平孕期需要抗病毒治疗的阈值,相应文章已进行了讨论[2-3]。对“1×104IU/mL ≤HBV DNA<2×105IU/mL时,可与患者充分沟通后决定是否干预” 这一推荐意见,我们认为“与患者充分沟通”很模糊,缺乏可操作性。孕妇必然希望其子女不感染HBV,但她们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是否服用抗病毒药物进行预防,最终还是取决于医生的观点。如果医生倾向于用抗病毒药物,模糊地说“有一定母婴传播风险”,而没有具体的数据,患者会选择抗病毒药物预防。临床上经常存在因“万一”而导致过度诊疗的行为。如果医生明确告知患者,这样的病毒水平,婴儿经联合免疫预防后,母婴传播发生率几乎为0或者<0.1%(实际情况如此),几乎没有孕妇选择抗病毒预防。因此,“与患者充分沟通”,实际上取决于医生的倾向。
临床指南的目的,是在有充分证据的前提下,尽可能提供明确的、可操作的具体建议,实现统一合理的医疗行为。孕期HBV DNA≤2×105IU/mL,其子女几乎不再感染,这已有大量的研究证据,但《指南》仍建议抗病毒治疗预防母婴传播,这不符合循证医学原则,也与国际主流指南和我国其他指南推荐的HBV DNA>2×105IU/mL进行抗病毒治疗的意见不符[7-8,11]。
四、《指南》推荐意见 4:抗病毒治疗开始孕周的问题
《指南》推荐意见4建议孕24~28周开始服用抗病毒药以阻断母婴传播。根据之一是会议论文摘要(《指南》参考文献21),其内容为“妊娠28 周以前进行干预与 28周及以后进行干预相比,前者母婴传播风险明显降低(RR=0.019)”,因该摘要没有获得结论的过程,也无全文参考,故无法判断其结论是否可靠。但根据笔者阅读的大量文献显示,孕28~32周开始抗病毒治疗,同时新生儿联合免疫预防,几乎能完全阻断母婴传播[12-14],即使从孕30~32周开始服药,也不发生母婴传播[15],在孕中期开始使用抗病毒药,并没有增加保护率[16]。因此,根据现有的证据,没有必要从孕24周就开始抗病毒治疗。尽管欧洲肝病学会指南提出从孕24~28周开始抗病毒治疗[7],美国肝病学会提出的从孕28~32周开始治疗更为合理[8]。
研究显示,经正规免疫预防,HBsAg阳性/HBeAg阴性母亲的子女几乎无母婴传播;HBeAg阳性母亲的子女感染率<10%,HBeAg阳性或高病毒水平孕妇孕28~32周开始抗病毒治疗后,其子女几乎无感染[12-15]。这提示HBV宫内传播非常罕见,因为免疫预防对宫内感染无效。孕晚期抗病毒治疗,仅能降低母体的病毒水平,而且需要经过2~4周才能发挥作用,在分娩时母体的病毒水平,大致相当于HBeAg阴性母亲的病毒水平,同时新生儿联合免疫预防,从而几乎完全阻断母婴传播。因此,抗病毒治疗减少母婴传播的机制是降低母体的病毒载量,使分娩时新生儿暴露的病毒明显减少,而不是减少宫内传播。因此,无论从经济还是安全的角度,都无需在28周前开始使用抗病毒药物。
此外,《指南》推荐意见2以“HBV DNA≥2×105IU/mL”为抗病毒治疗的阈值,证据级别是(1B)。而在推荐意见4中,同样为“HBV DNA≥2×105IU/mL”,仅添加了“妊娠 24~28周期间”,证据级别降为(2C)。笔者无法理解其原因,是因为“妊娠 24~28周期间”让证据级别降低了,还是证据定级存在随意性。
五、《指南》推荐意见 9:羊膜腔穿刺术的问题
《指南》推荐意见 9,认为孕妇HBV DNA≥1×106IU/mL时,羊膜腔穿刺术会增加胎儿发生宫内感染的风险,其根据是美国肝病学会的指南和一篇中文meta分析。但美国指南明确指出尚不清楚(Whether invasive procedures during pregnancy, such as amniocentesis, increase the risk of HBV infection in the infants is unclear),同时根据北京的一篇报道结果,指出高病毒载量时需要考虑相关风险[8]。该北京报道指出HBV DNA≥107IU/mL时,羊膜腔穿刺后母婴传播发生率高达50%[17],但仅纳入6例孕妇,难以排除抽样偏倚。最近广州报道羊膜腔穿刺能增加母婴传播,但该研究中未穿刺组HBeAg阳性母亲的子女母婴传播率仅1.6%(3/188)[18],明显低于同一研究组此前报道的 4.44%(21/473)[19],而穿刺组49例HBeAg阳性母亲的母婴传播率仅8.2%[18],即使孕妇HBV DNA≥107IU/mL时,羊膜腔穿刺后母婴传播率仅10.8%(4/37)[18],与其他报道的母亲没有羊膜腔穿刺的母婴传播率相似,而与北京报道的穿刺后50%的母婴传播率差异极大。浙江报道92例HBeAg阳性母亲羊膜腔穿刺后,仅6例(6.5%)发生母婴传播,不增加母婴传播率[20]。因此,我们认为根据这些数据,对高病毒水平或HBeAg阳性母亲,羊膜腔穿刺是否能增加母婴传播,尚不能定论。
《指南》引用的中文meta分析(《指南》参考文献49)中,只有2篇论文(包括上述北京的一篇报道),涉及HBV DNA≥107IU/mL、羊膜腔穿刺的孕妇总例数仅10例,这样的meta分析不可能得出可靠的结论,该文发表在与乙型肝炎基本无关的《分子影像学杂志》。《指南》作者引用此类文献作为证据,而不引用上述浙江报道(HBeAg阳性母亲多达92例,结论是羊膜腔穿刺不增加母婴传播)的文献[20],这明显与引言中声称的 “基于当前最佳证据” 不符。
总之,根据现有证据,对孕妇HBeAg阳性或高病毒载量,羊膜腔穿刺术是否增加HBV母婴传播,尚不能提出明确建议,有待进一步研究。而HBeAg阴性孕妇羊膜腔穿刺不增加母婴传播,研究结果较为一致[17-18,20-21],因此,有羊膜腔穿刺指征时,不必担心HBV母婴传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