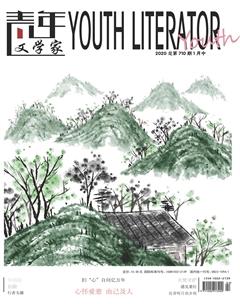李白与威廉·华兹华斯山水诗比较研究
基金项目:本成果受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李白文化研究中心课题李白与华兹华斯山水诗平行研究(项目编号:LB17-B05)资助。
摘 要:李白与威廉·华兹华斯是中英两国文学史上具有独特地位的伟大诗人。以二者山水诗为研究对象,通过文本细读和比较研究,探讨山水景观在诗中的作用,以及体现的山水观。二者在诗中皆表达了山水生态思想,李白体现了“人性化”的山水观,华兹华斯体现了“神性化”的山水观。在当代生态环境面临挑战的情况下,探究二者的山水诗能够深化对山水的认识,重新审视人与山水自然的关系,最终提出构建人类与自然共同体的理念。
关键词:李白;威廉·华兹华斯;山水诗;山水观
作者简介:何新(1989.4-,女,汉族,四川德阳人,硕士,成都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02-0-03
李白与威廉·华兹华斯在中英文学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李白是中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其诗歌通过描写山水自然体现了豪迈洒脱的个性;华兹华斯是英国浪漫主义运动的先驱,提倡回归自然和诗歌抒发强烈的主观情感。虽然在二者之前两国皆有诗人书写浪漫主义诗歌,但正是李白和华兹华斯让中英两国浪漫主义思潮达到了高峰。即使所在国家,生活朝代和时间不同,但时代政治经济背景,个人生活经历,诗歌艺术创作特征有许多相似点。①所以,二者具有不可置换的可比性。在传统的关于二者诗歌的平行研究中,大多比较二者诗歌艺术创作特征。而本文通过文本细读和比较研究的方法,旨在探讨二者创作山水诗的缘由,山水景观在诗中所起的作用,从而全面了解二者的山水观,以此深化认识二者的山水诗并重新思考人与山水自然的关系。
一、山水诗的定义
中国的山水诗早在先秦时期的《诗经》、《楚辞》中就有了创作萌芽,从第三世纪后半期开始逐渐出现在诗人的作品中,而于南朝的刘宋时代正式确立其为‘文类的地位,在唐朝成型。对于什么是山水诗,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界定。王国璎在其书《中国山水诗研究》中指出:“所谓‘山水诗,是指描写山水风景的诗。虽然诗中不一定纯写山水,亦可有其他的辅助母体,但是呈现耳目所及的山水之美,则必须为诗人创作的主要目的。在一首山水诗中,并非山和水都得同时出现,有的只写山景,有的却以水景为主。”[1]通过分析汉语言家朱光潜、伍蠡甫、林文月、李文初等人对于山水诗的定义,朱德发在其《新探与界说:中国山水诗》中认为诸家定义中有三个相通点:一是将自然山水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以自然山水为描写题材;二是表现出诗人对于自然山水的审美体验和审美情趣;三是承认山水诗是诗歌的一种类型。所以朱认为山水诗是“自然山水美与主体审美心灵相融合的艺术载体”。[2]83 杨志在《论古今山水诗的衰变》中也谈到了山水诗的定义:“人与山水相遇,主客体交融、互动,最后在人的意识中形成为 诗。因此,山水诗并不是摹写客观物象的诗歌,而是人与山水联系的形成品,是对人与山水相遇的联系的一种表现,因而具有主客观交融的特点。”[3]45 巩宏昱在其硕士论文《李白山水诗研究》认为“‘山水诗一词,‘山水作为定语,决定了其首先是以描写‘山水为主的诗歌,换言之山水应是该首诗歌的主要表现对象,是主题而不是附庸,陪衬。”[4]2
综上所述,从80年代到现代学者,对山水诗的界定有以下几点:首先,山水诗应主要是围绕“山”和(或)“水”的客观存在的自然景物描写,山水景观描写是主体而不是附庸;其次,山水诗中可以有辅助的其他主题,这种主题既可以是表达对于自然的赞美之情,也可以是借景抒发内心其他感受。根据这一界定,李白的诗歌中有大量的山水诗,如《清溪行》,《秋浦歌》,《送友人寻越中山水》,《望天门山》,《登峨眉山》等。
中国的“山水诗”在西方没有直接对应的诗的种类,但可归类于“natural poem”,并根据含义可翻译为“landscape poem”。“书写自然的诗歌在英国文学史上可谓源远流长,最早描写自然的诗作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但描写自然的诗歌只有到了华兹华斯时期(浪漫主义时期),才真正地向着纵深发展,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5]55 所以是华兹华斯把英国诗歌对自然的崇拜推向了高潮。西方的诗歌并没有像中国古典诗歌那样把描写自然的诗歌细分为山水诗,但根据中国山水诗的定义去界定华兹华斯的诗歌,发现诗人很多诗都属于山水诗的范畴,如《阳春三月作》,《延滕寺》,《永生的信息》,《早春命笔》,《鹿跳泉》等。
二、山水描写
李白和华兹华斯的山水诗中对于山水的描写一方面都再现山水美景画面,能让读者获得美感体验;另一方面能够间接烘托出诗人想要表达的内心情感。但是二者描写山水的艺术手法和借助山水表达的情感有所不同。
由李白的山水诗看出,诗人创作时全身心沉浸在其中,几乎达到了忘我的境界。由于没有“我”的干扰,故可以对山水的本来面貌做出最真实的写照,最直接的欣赏。如:“清溪清我心,水色异诸水。”“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 (《清溪行》)诗人在描写山水时,更多的使用夸张和比喻的表现手法,给讀者展现一幅气壮山河,旷阔澎湃的画面。如《望天门山》: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
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诗人用寥寥数笔勾画出了天门山的雄奇壮观和江水浩荡奔流的气势。碧水,青山,孤帆,日,诗中意象勾画出了一幅层次分明,颜色饱满的画面,让读者仿佛置身其中,心旷神怡。在《望庐山瀑布》(其二)中,“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诗人用夸张和比喻把庐山瀑布的磅礴气势展现得的淋漓尽致 ,给读者以美学感受。
而华兹华斯在描写山水时,常见拟人的修辞手法,展现出一幅静谧祥和的山水图。如《延滕寺》(杨德豫译):
如今,我再次听到\这里的清流,以内河的喁喁低语\从山泉奔注而下。我再次看到\两岸高俊峥嵘的危崖峭壁\把地面景物连接于静穆天穹\给这片遗世独立的风光,增添了\更为深远的遗世独立的意味。
虽然诗人在诗中运用了“奔注”,“高俊峥嵘”,“危”,“峭”修饰山水,但“低语”,“静穆”,“遗世独立”让整幅画面 变得祥和平静起来,能让读者在纷杂的世界中找到内心的平静。“她(缪斯)凝眸观赏晶莹明镜的河川——水清见底,只因它缓缓流荡;”清澈见底的河水缓缓流淌,让人的内心能跟着河水的流淌慢下来。
综上所述,李白和华兹华斯山水诗中对山水的描写虽都能用寥寥几笔再现山水风景图,给读者提供生动的视觉美感体验,让人赏心悦目,但二者对山水的选择和描绘不尽相同。李白偏向描绘山的雄峻气势,水的激昂奔腾,给读者一种热血澎湃的感受;而华兹华斯偏向描绘山的静穆,水的细流,让读者一种祥和的体验。
三、山水观
在山水诗中,对山水的观照不仅可以再现美景,也可以反映出诗人的生态山水观。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李白把自己和山水融入一体,进入“虚静无我”的状态,对于山水的描写,即也是对自己内心感受的刻画,仿佛山水能够读懂诗人。同样,在华兹华斯看来,在山水中他能找到真实的更好的自我,自然山水具有很好的净化和治愈作用。
道家哲学强调的是“人与外物之间超功利的无为关系,其最终旨標 是令人要无我两忘,乃至物我同一,达到绝对自由,逍遥无侍的心灵境界”。[1]12 《齐物论》中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唯一”,即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是由同一基础而生,人与山水自然在宇宙中有同样的地位,人与自然山水要“天人合一”。这里“天”的概念在道家思想中并不是指神,而是包含了“自然”的特征。“庄子生态美学所强调的人与自然密切联系的观点,从审美认识层面阐释了宇宙联系中蕴含着的生态智慧”。[6]17李白诗中的山水仿佛是他的一部分,一个反映,他把自己山水化,把山水自己化了。山的孤寂,仿佛也是李白政治抱负不能实现的孤寂。如:“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独坐敬亭山》)诗人没有采用传统人类对山水的视角,而是把敬亭山当作像自己一样有生命情感的了,只有彼此才能读懂对方,才能明白对方的寂寞与抱负。李白把山水看成与自己一样是宇宙的一员,已把山水自己化,把自己山水化,所以山水自然也能体会他的各种情感,在他的众多山水诗中,描写山水美景的同时也抒发了内心的各种情感。李白漂泊在外离家多年,难免会有思乡之情,在山水中诗人流露出了思乡的感伤。如“清溪清我心,水色异诸水。借问新安江,见底何如此。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向晚猩猩啼,空悲远游子。”(《清溪行》)此诗写于李白在公元753年第二次漫游中游安徽池州时所作。此时距他离开家乡已经有大约28年了。这28年中,李白漫游中国,看透了当时的政局,但又无法回到家乡,心中难免有思乡之情。所以在诗中觉得山中猩猩的啼叫都是在为自己感到忧伤。又如“惜彼落日暮,爱此寒泉清。西辉逐流水,荡漾游子情。”(《游南阳清冷泉》)看见流水,诗人的乡愁油然而生。李白一生都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可惜唐王朝腐朽堕落,诗人即使不能实现政治抱负也不向权贵屈服,这样不屈的精神以及愤恨的情感在李白的诗中仿佛山水也能读懂。《梦游天姥吟留别》中,诗人首先刻画出天姥峰宏伟的气势:“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诗的末尾提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诗人把天姥峰自比,有着气壮山河的气势,不向任何人屈服。
李白把自己融入山水,把山水“人性化”,认为山水同人类一样也是宇宙中的一员,能够深刻体会感受到人类的感情,人类也能通过山水传达自己的情感。在他的山水诗中,“写景就是写人,写人也是写景,物我合一,彼此难分,展示出‘天人合一的美学意境”。[7]107道家“与天合者谓之天乐”的生态美学思想让李白与自然山水合二为一,体现出诗人“山水自然人论”。
华兹华斯的山水诗也体现出了他返璞归真的愿望,寻找自我和山水的契合,“华兹华斯将山水视为灵感的源泉,山水美景能给人力量和愉悦,具有疗效作用,使人的心灵净化和升华。” [5]57 换言之,与李白认为山水可以与他感同身受不同,深受自然神论影响的华兹华斯更多的认为山水自然是一个具有治愈作用的神性场所, 置身山水美景中便能使他忘记人类社会的纷争与喧嚣,扔掉悲伤烦恼的负面情绪,找到内心的平静。在自然神论上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斯宾诺莎认为“上帝完全被整个自然所取代,或者说自然本身就是神,神已经泛化为自然万物”。[8]69在华兹华斯的自然山水诗歌中,无处不见自然山水神性的思想。在《廷滕寺》中,诗人开篇描写了山泉,峭壁等山水美景,后来不惜几次抒发自己在山水中的感受:
我同样深信,是这些自然景物\给了我另一份更其崇高的厚礼——\一种欣幸的、入目天恩的心境\在此心境里,人生之谜的负重\幽晦难明的尘世的如盘重压\都趋于轻缓 (杨德豫 译)
不难看出,不同于传统诗歌中认为人类可以主导自然的一切,诗人反而认为山水自然给他(人类)带来“天恩”,在山水中,人类所有尘世的重压都能减缓。诗中还提到“惟有 自然(山水),主宰着我的全部身心。”在诗人看来,不是人类主宰山水自然,反而是山水自然主宰着人类命运,把山水“神性化”,彻底颠覆了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18世纪后半叶英国如火如荼地进行工业革命,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并且自启蒙运动以后,人们热忱地推崇理性主义,“伴随着神的消亡和理性的增长,人的主体性得到明显增强”。[8]62 人们扔掉基督教义对于人服务于上帝,人的命运由上帝掌握的思想,开始自己把握命运,体现自我主体性,认为人类才是宇宙万物的中心,对自然开始疯狂的占有和征服,想更多的从 自然世界中榨取資源和利益,以满足人类的自我享受。在等到自然开始对人类的宰割进行强烈的抱负时,人们才意识到人类与自然应该和谐相处。而华兹华斯的山水诗不仅体现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还体现了其“神性化”的山水观。我国学者王佐良认为“华兹华斯的诗歌已经不属于一般的山水诗范围,诗人认为自然界最最平凡最卑微的事物都有灵魂,而且他们是同整个宇宙的大灵魂合二为一的。就诗人自己来说,同自然的接触,不仅能使他从人世的创伤中恢复过来,使他纯洁,恬静,使他逐渐看清事物的内在生命,而且使他成为一个更善良,更富于同情心的人。”[9]79 由此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华兹华斯的自然山水被诗人赋予了同神,同人一样的灵魂,具有治愈和改善作用,已不仅仅只是客观物质对象,而是神性山水。
这样的山水观在华兹华斯的其他许多山水诗中也有体现,如《永生的信息》中感叹道“哦! 流泉,丛树,绿野,青山! 我们之间的情谊永不会中断!你们的伟力深入我心灵的中心;”又如诗人在《转折》中赞叹树林山野的作用:“春天树林的律动,胜过一切圣贤的教导,它能指引你识别善恶,点拨你做人之道。”华兹华斯在英国工业革命中认识到了人类对自然山水的破坏造成的严重危机,不仅仅是物质上自然山水的抱负带来的损失,精神上人们也日渐异化失去自我。所以诗人回归自然山水中,隐居湖区,认为山水能够启迪人们的心灵和智慧,能保持自己的尊严和纯洁,置身山水自然中才能与日益利益熏心 ,压迫个性的工业社会分庭抗礼。
综上所述,李白和华兹华斯的山水诗都体现了他们摒弃 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敬畏山水的山水自然观。略有区别的是,李白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认为宇宙万物皆有“道”,把自己与山水融于一体,把山水“人性化”,认为山水也能感受到他政治上的失意,感受到他蔑视权贵不向封建社会屈服的反抗精神。华兹华斯则更进一步地把山水“神性化”了,认为山水自然可以启迪人们的心灵,人们在山水中可以回归到原初本真的状态。
四、结语
李白与威廉·华兹华斯作为中英两国最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在各自的文学史上有他人不可替代的位置,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无论从二者的一生历经,生活的政治背景,所属的文学流派而言,都极具不可替换的可比性。在二者山水诗中,诗人都用简单易懂的文笔,高超的艺术手法,描绘了山水美景,给读者以审美感官上的享受;并且从二者的山水诗中都体现了诗人热爱山水,敬畏山水的生态思想。不同的是,深受中国道家“天人合一”的美学思想,李白把自己融入自然山水中,并把山水“人性化”,把山水和人类的地位放到宇宙中同等高度,仿佛山水能够感受到人类的情感;而华兹华斯深信自然神论,更是把山水“神性化”,认为自然山水万物皆是神的化身,具有治愈作用,可以凈化人们的心灵,让人们成为更好的自我。
从二者的山水诗中不难看出,无论是在8世纪的唐朝封建社会,还是在19世纪的欧洲工业社会,山水自然都能给人类心灵给予启迪和慰藉。二者的山水诗,让我们在环境被日益破坏的现代社会,重新审视和思考人类与山水自然的关系,最终构建人类与山水自然共同体。
注释:
①李白与华兹华斯可比性论述具体见作者发表于《北方文学》2018年第九期的论文“李白与威廉·华兹华斯可比性浅析”。
参考文献:
[1]王国璎, 中国山水诗研究[M].北京:聊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6:一12。
[2]朱德发, 新探与界说:中国山水诗[J].山东社会科学, 1994(5): 83。
[3]杨志, 论古今山水诗的衰变[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1(4): 45。
[4]巩宏昱, 李白山水诗研究[D .山西师范大学, 2009: 2。
[5]范丽娟, 影响与接受:中英浪漫主义诗学的发生与比较[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55-57。
[6]钱同舟, “万物并作”与“天人合一”:先秦生态美学思想及启示[J].学术交流, 2010(9):17。
[7]赵丽梅, 李白的诗与道家思想[J].学术探索, 2011(12):107。
[8]鲁春芳, 神性自然: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生态伦理思想[M].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9:62-69。
[9]王佐良, 英国文学论集[M].北京: 外国文学出版社, 198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