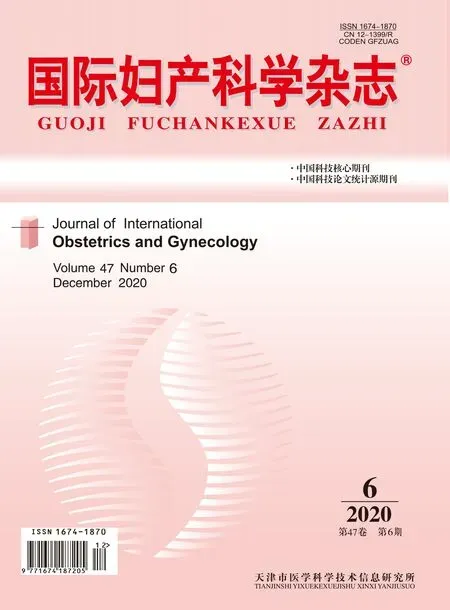雌激素及炎症因子与绝经后骨质疏松症相关研究进展
陈怡洁,金雪静,王雪,杜旖旎,盛祝梅,张治芬
骨质疏松症是一种以骨量低、骨组织微结构损坏,导致骨脆性增加,易发生骨折为特征的全身性骨病,多见于绝经后妇女。许多慢性炎症性疾病,如骨关节炎、慢性阻塞性肺病、牙周炎等都伴随着明显的骨丢失,提示炎症可能与骨质疏松症有密切联系。绝经后女性由于体内雌激素水平骤然下降,导致骨重建失衡,同时由于年龄的增长,绝经后女性的生理机能和免疫功能下降,长期处于慢性炎症状态,因此绝经后骨质疏松症(postmenopausal osteoporosis,PMO)同样被认为是一种慢性炎症性疾病。雌激素及雌激素受体(estrogen receptor,ER)信号通路参与许多生物学过程,通过多种方式调控骨重建的进程和炎症的发生发展[1]。过去的研究忽略了更广泛的生物学复杂性,通常单独研究雌激素或炎症与骨质疏松症的关系,目前已有证据表明这两种机制是相互关联的,雌激素缺乏可能通过影响炎症水平而导致骨质疏松[2]。本文将从绝经后骨质疏松和雌激素的变化,雌激素与炎症因子的关系,及雌激素下降如何影响炎症因子从而进一步导致PMO这3个方面进行综述。
1 PMO的发生和绝经后雌激素的变化
骨质疏松症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两种类型,其中原发性骨质疏松症包括Ⅰ型PMO、Ⅱ型老年骨质疏松症和特发性骨质疏松症,与年龄、性别、种族等因素密切相关[3]。值得注意的是,骨质疏松症最常见的危险因素,如肥胖、糖尿病、吸烟等,与绝经期危险因素相似[4]。据估计,美国50岁以上的人口中约54%患有骨质疏松症或骨量减少,约40%的女性可能会发生髋关节、脊柱或前臂骨折[5]。长期分泌炎症因子会诱发慢性炎症性疾病,在诸如类风湿性关节炎、脊椎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炎性肠病和慢性阻塞性肺病等慢性炎性疾病中,已经有大量研究表明其与骨质疏松相关。这些患者接受长期糖皮质激素治疗,首先糖皮质激素治疗可通过抑制成骨细胞的增殖和分化,增加成骨细胞的凋亡等多种机制引起骨丢失[6]。其次,炎症因子与免疫系统、骨骼重塑之间的相互作用,慢性炎症本身导致骨质下降[7]。已有研究证明持续的慢性炎症为进行性骨丢失的诱因,慢性炎症因子在抑制骨形成的同时促进了骨吸收,这种不平衡导致骨密度(bone mineral density,BMD)下降,骨质流失以及骨折风险的增加[8]。女性随着年龄增长,卵巢功能逐渐减退,绝经后卵巢极少分泌雌激素,少量循环雌激素主要来自肾上腺皮质。绝经后雌激素水平下降,破骨细胞的骨吸收大于成骨细胞的骨形成。雌激素与破骨细胞、成骨细胞、软骨细胞和部分炎症因子关系密切,可通过作用于骨组织细胞ER进而调控靶基因的转录翻译。ER主要包括ERα、ERβ和ERγ等,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谱系中存在ER的差异性表达,ERα在骨皮质中高度表达,而ERβ则在骨小梁有较高表达,这表明其在骨组织中可能有不同的功能[9]。激素替代疗法是防治PMO的有效措施,可通过抑制破骨细胞活动和降低骨转化以减缓绝经后女性骨量丢失,绝经前后启动激素替代疗法的妇女可获得骨质疏松性骨折一级预防的好处[10]。
2 雌激素水平与炎性因子的关系
炎症是许多疾病的发生、发展中重要的生物学过程,但这些疾病在不同性别中的发生情况却不同。自身免疫性疾病(例如硬皮病、多发性硬化症、类风湿性关节炎)和某些炎症性疾病(例如哮喘)等在女性中多发。但是,部分炎症疾病(如败血症、手术后感染和痛风等)却在男性群体中的发病率和严重程度较高[11]。女性雌激素在慢性炎性疾病的发生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其中月经周期、妊娠和绝经状态是其重要影响因素,阐明雌激素对炎症反应的作用机制有助于了解绝经后妇女的病理状态,并且可以进一步探索绝经后妇女易患骨质疏松症、类风湿关节炎、阿尔茨海默病等慢性炎症疾病的病因[12-13]。一方面,在几种慢性炎症动物模型中,雌激素具有抑制骨吸收和抑制炎症的作用,可降低炎症介导的疼痛反应并减少神经炎性疾病发生,但其作用机制尚不明确[14]。另一方面,雌激素在创伤、脓毒血症中具有免疫支持作用,在人类某些慢性自身免疫性疾病中具有促进炎症作用[15],本文要强调雌激素既有抑制又有促进炎症的双重作用,在炎症性疾病中不能仅阐述其单一作用。如在福尔马林炎症疼痛试验中,补充雌激素可显著减少去卵巢(ovariectomy,OVX)大鼠伤害感受行为和c-Fos表达[16]。在紫杉醇诱发神经性炎症疼痛大鼠模型中,OVX大鼠雌激素及ER表达减少,炎症因子如白细胞介素 1β(Interleukin-1,IL-1β)、IL-6 和肿瘤坏死因子 α(tumor necrosis factor α,TNF-α)的表达增加[17]。在进行辅助生殖助孕、处于卵巢控制刺激过程的女性中,通过流式细胞仪分析其血清雌二醇(E2)浓度对女性血循环白细胞组成及其体外极化/激活状态的影响,发现血清E2水平升高,并且其血循环中嗜中性粒细胞、单核细胞、辅助性T细胞数量增加,而细胞毒性T细胞减少,这些实验数据支持证明雌激素可能调节免疫系统并具有抗炎作用[18]。一项纳入155例健康绝经后妇女的横断面研究发现,内源性E2水平与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纤溶酶原激活蛋白-1(plasminogen activator protein-1,PAI-1)、IL-6呈正相关,与血清淀粉样蛋白 A(serum amyloid A,SAA)、脂联素呈负相关[19]。另一项研究发现,在绝经后健康女性中,血清CRP水平与雌酮、总E2和游离E2与CRP呈正相关,与性激素结合球蛋白(sex hormone-binding globulin,SHBG)呈负相关[20]。有研究表明,人CRP与骨髓瘤细胞上的CD32/FcγRⅡ结合,通过由有丝分裂激活的p38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p38MAPK)和转录因子Twist激活下游信号传导,并促进骨髓瘤细胞产生细胞因子,从而增强骨髓瘤细胞介导的破骨细胞分化和骨吸收[21]。
3 雌激素缺乏导致的炎性因子改变在PMO中的作用
PMO与雌激素缺乏引起的细胞衰老和炎症密切相关,以破骨细胞分化和骨吸收为主要特征。细胞因子通过免疫系统影响破骨细胞的形成,失调可导致病理性骨病。细胞因子是低分子质量可溶性蛋白质,具有调节固有免疫和适应性免疫,细胞生长以及损伤组织修复等多种功能。细胞因子可被分为IL、干扰素、TNF超家族、集落刺激因子等。炎性细胞因子的释放会引起免疫细胞的活化以及产生其他炎性细胞因子的释放,在维持骨稳态中起关键作用,其中核因 子 κB (the nuclear factor-κB,NF-κB) 配体(RANKL)和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macrophage 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M-CSF)在破骨细胞分化中发挥核心作用[22]。炎症细胞因子损害DNA修复并导致细胞衰老以及生物衰老[2]。有研究指出,慢性炎症影响BMD的机制可能是炎性细胞因子作用于间充质干细胞和破骨细胞前体,增加破骨细胞介导的骨吸收,使RANKL和M-CSF受体激活剂的产生增加,骨保护素(osteoprotegerin,OPG)的激活减少。OPG是一种TNF受体超家族成员,主要通过与RANKL结合并阻碍RANKL-RANK的相互作用从而负调节破骨细胞生成。炎症细胞因子可通过这些作用提高破骨细胞的活性。在绝经后妇女中,慢性炎症与雌激素水平的下降相结合,导致骨吸收增加[23]。Cline-Smith等[24]发现E2通过诱导Fas配体(FasL)和树突细胞的凋亡来调节IL-7和IL-15的表达。E2水平下降,树突细胞寿命增长,导致IL-7和IL-15水平升高,激活慢性炎症状态,促进了OVX小鼠骨质流失。另一项研究发现,在1型糖尿病OVX小鼠模型中,低雌激素水平和高血糖会促进炎症而增强TNF-α的表达,小鼠成骨细胞数量和活性及骨小梁体积分数明显降低[25]。有证据表明在绝经后女性及OVX大鼠模型中,雌激素可能通过NLRP3/caspase-1/IL-1β通路加重根尖性牙周炎,进而导致骨质流失[26]。PMO相关的动物研究显示,在骨折愈合前期,雌激素下降,受损骨组织间充质干细胞水平降低,血管生成减少,骨质愈合时间延长;在骨折愈合后期,雌激素缺乏会使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数量减少,生物力学性能降低[27]。此外,最近有研究发现雌激素水平下降不仅会影响骨折中晚期的愈合,还会影响损伤后的炎症阶段,在骨折第3天,OVX小鼠与假手术组小鼠相比,受损骨组织发育愈合和皮质桥接较差,促炎性细胞因子中期因子和IL-6表达增加[28]。在因骨关节炎行全髋或全膝关节置换术的189例老年人(平均年龄65~66岁)中发现,骨关节炎的疼痛反应与全身性炎症相关,其中在老年女性中高水平CRP与关节疼痛评分相关[29]。另外,有研究提出骨质的丢失可能是对于急性短期炎症的适应性机制,由免疫系统介导机体为其他组织提供钙离子,而持续性的炎症刺激可能造成骨量持续下降,加快骨质疏松的进程[30]。
4 结语和展望
老年女性常处于无症状持续性慢性轻微炎症状态,与骨质疏松发生发展关系密切。PMO是老年女性常见的疾病,更需要普及健康教育,做到早期筛查与识别。绝经后女性接受恰当的健康指导和药物干预,可极大程度上减少骨质疏松和骨折的发生。雌激素可以影响免疫系统和炎症状态。与男性相比,女性免疫性疾病发病率上升且部分慢性炎症疾病随月经周期、妊娠和绝经期状态变化而变化。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雌激素可通过炎性因子直接或间接地影响骨代谢,了解雌激素调节炎性因子的途径可能对治疗骨质疏松症提供新的理论依据,以便早期预防骨质疏松症的发生,延缓其相关疾病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