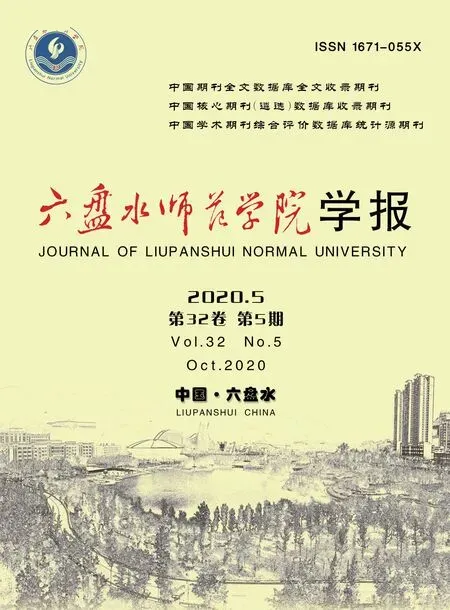论耶律楚材诗中的“苏轼情结”
唐樱艳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贵州贵阳550025)
耶律楚材为一代重臣。《元史》载:“以学行事金世宗,特见亲任,终尚书右丞……博极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下笔为文,若宿构者,金制宰相。”[1]耶律楚材博学多才,泽民救世,为官清廉,政治贡献显赫。如清末芳郭无名人氏在《湛然居士文集后序二》评其云:“扞圉边庭,国威遐震,草创法度,功在庙社。谏革初制之苛猛,苏息民物之疮痍,丰功伟烈,衣被天下,非刘秉忠诸人所能望。”[2]13观其诗之特色,四库馆臣云:“今观其诗,语皆本色,惟意自如,不以研炼为工。”[2]382王鄰亦云:“中书湛然性禀英明,有天然之才,或吟哦数句,或挥扫百张,皆信手拈来,非积习而成之……味其言言语语,其温雅平淡,文以润金石,其飘逸雄淡,又以薄云天,如宝鉴无尘,寒水绝翳,其照物也莹然。”[2]4由此可知湛然诗温纯绚烂,显达酣畅。现今,学界对耶律楚材的研究,多从其诗歌特质着手,如郭亚宾《耶律楚材诗歌特质论》[3]、孙玉峰《耶律楚材及诗歌简论》[4]等;又有从耶律家族的文学特色入手分析耶律楚材作品的文学性,如和谈《论耶律家族文学的艺术特色》[5]、贾秀云《耶律楚材家族与苏学的关联》[6];还有学者从耶律楚材的诗歌倾向入手,如傅秋爽《耶律楚材诗中的陶渊明情结》[7]、陈苗《论耶律楚材诗歌中的白居易情结》[8]等,这些文章都提及耶律楚材诗歌中含有苏诗的倾向,然关涉不足。故而重新梳理湛然诗作,以期得湛然诗中的“苏轼情结”。
一、耶律楚材慕苏情结之诗学背景
(一)苏学行于北的文化氛围
在北方诗坛中,苏轼诗文广泛流传并影响深远。《事实类苑》中记载张舜民使辽时所见:“张芸叟奉使大辽,宿幽州馆中,有题子瞻《老人行》于壁间。子瞻名重当代,外至夷虏,亦爱服如此。芸叟题其后曰:‘谁传佳句到幽都?逢着胡儿问大苏。’”[9]苏轼本人也曾在《记虏使诵诗》中自述道:“昔余与北使刘霄会食,霄诵仆诗云:‘痛饮从今有几日,西轩月色夜来新。’公岂不解饮者耶?虏亦喜吾诗,可怪也。”[10]又赵翼《瓯北诗话》卷一二云:“宋南渡后,北宋人著述有流播在金源者,苏东坡、黄山谷为盛。南宋人诗文,则罕见传至中原者,疆域所限,故不能及时流通。”[11]清代四库馆臣亦有“宋自南渡以后,议论多而事功少,道学盛而文章衰,中原文献,实并入于金”[12]。在中原文献流至北方过程中,苏轼的作品占主要部分,并且深刻地影响了金元诗人的文学创作。
处于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元代初期的北方文坛,几乎没有人不以苏轼为文坛宗主。翁方纲于《石洲诗话》云:“程学盛于南,苏学盛于北,如蔡松年、赵秉文之属,盖皆苏氏之支流余裔。遗山崛起党、赵之后,器识超拔,始不尽为苏氏余波沾沾一得,是以开启百年后文士之脉。”[13]又如袁桷在《书程君贞诗后》中谈到“苏公以其词超于情,嗒然以为正,颓然以为近,后之言诗者争慕之”[14]。亦如顾嗣立所言“北方之学变于元初……苏门以理学探本,一时才俊之士,肆意文章,如初阳始升、春卉花苗,宜其风尚之日趣于盛也”[15]。由是可见,苏轼的作品和思想对金元诗人的影响深远。
(二)家学的浸染
耶律楚材瞻仰苏轼不仅是受时代的影响,还与其耶律家族文学的传统有紧密的关联。耶律楚材的曾祖父耶律内剌为耶律倍的六世孙,耶律倍热爱中原文化,并积极寻觅和搜集中原文人的作品,“令人赉金宝私入幽州市书,载以自随,凡数万卷,置书堂于医巫闾山上,扁曰望海堂”[16]。这种家学渊源世代传承,形成稳定独特的家族文化。耶律内剌为辽朝定远大将军,位高权贵,对苏轼的威望和影响也是了如指掌的。《程史》记载:“承平时,国家与辽欢盟,文禁甚宽,辂客者往来,率以诙谑诗文相娱乐。元祐间,东坡实膺是选,辽使素闻其名。”[17]身逢其时的耶律内剌也会是深感兴趣,并尽力搜罗和保存其作品。耶律内剌之子,耶律楚材之父耶律履在这样崇苏的家庭文化熏陶下,学苏慕苏亦在情理之中。
在《元好问全集》中就记载到耶律履仰苏之事:
世宗尝问宋名臣孰为优,公以端明殿学士苏轼对。世宗曰:“吾闻苏轼与驸马都尉王诜交甚款,至作歌曲,戏及帝女,非礼之甚!其人何足数耶?”公曰:“小说传闻,未必可信,就令有之,戏笑之间,亦何须深责?岂得并其人而废之?世徒知轼之诗文人为不可及,臣观其论天下事,实经济之良材,求之古人,陆贽而下未见其比。陛下无信小说传闻而忽贤臣之言。”明日,录轼奏议上之。诏国子监刊行[18]。
从上述对话中得知,耶律履为苏轼“戏及帝女”一事进行辩护,并且称赞苏轼是宋朝最卓越的大臣,钦佩苏轼的文学成就和肯定其经济政治才能。另外此事还促使国子监刊行苏轼奏议,引起了金代大臣对苏轼经济才能的关注,推动了苏轼著作的传播。如《思益堂日札》中载道:“东坡先生性既和易,好谐谑,随笔作小词,各说部多载其逸事,不必真实,乃传入敌国,几遭诋斥。使非履道奏白,身后斗山之望减矣!”[19]虽不免有溢美之言,但不得不承认耶律履在传播苏轼著作上所做的贡献,以及其对苏轼的推崇。
另外从其现存为数不多的诗词中,亦可发现他对苏轼的仰慕。一方面,直接引用苏诗中的语词,直取珠肌。如《和德秀道济李仲茂自得斋诗韵二首》(其一):“骨相癯儒真可人,飘然野鹤出清晨。”[20]中的“可人”取自东坡的《广陵后园题申公扇子》“闲吟绕屋扶疏句,须信渊明是可人”[21]1282;其“问学不图攀月桂,孤高那与比霜筠”(同上)中的“霜筠”源自苏轼《渼陂鱼》“霜筠细破为双掩,中有长鱼如卧剑”[21]213;“我为物囿劳机算,愿策驽顽袭后尘”(同上)中的“驽顽”见于苏轼《书韩干<牧马图>诗》“奇姿逸得隐驽顽,碧眼胡儿手足鲜”[21]722。另一方面,其现存的3首词作词风豪放,境界开阔,善于议论,语言飘逸,与苏轼相近。耶律履不仅学苏,还以苏自比“东坡疑是前身,赤蛇宵吼”[22]。如前所述,耶律履不仅在政治方面推崇苏轼,在文学方面也多次化用东坡诗句,还自比苏轼,足以证明其对东坡的推崇和痴迷。
言而总之,耶律楚材诗学创作植根于民族融合的历史土壤,又受到苏学北行风气的熏陶及家学的浸染,其自然会仰慕苏轼,深为苏轼所影响。
二、耶律楚材慕苏情结之思想表现
耶律楚材的苏轼情结指埋藏在诗人内心深处对苏轼的赞美、仰慕、认同的情感倾向。这一倾向会潜移默化地影响诗人的思维和情感方式,形成与之相关的特殊的感情。如其诗云:“既慕东坡才,当如东坡志。君才如东坡,其志未相似。诗似东坡诗,字如东坡字。胡不学东坡,且学长不死。”[2]256(《勉景贤》),不仅羡慕苏轼的才气,称赞苏轼的志向,还要学习苏轼诗文,更要学苏轼字,不然不罢休,足以看出耶律楚材对苏轼的仰慕。正是这种情感的深刻认同,影响了二者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的接近。
(一)佛理濡染下的“空观”
佛教认为世界的本源即是“空无虚妄”,如《金刚经·应化非真分》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23]《维摩诘经·方便品》亦云:“是身如芭蕉,中无有坚。是身如幻,从颠倒起。是身如梦,为虚妄见。”[24]而贯穿耶律楚材、苏轼一生的佛理是诸法皆空,人生如梦。
苏轼很早就开始学佛理,早年就有诗云:“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21]96言说人生如白驹过隙,来去匆匆,无迹可寻。而第一次直接提出“空观”观念的是其《吉祥寺僧求阁名》:“过眼荣枯电与风,久长哪得似花红。上人宴坐观空阁,观色观空色即空。”[21]331由当下的花繁叶茂联系到人的荣辱沉浮,应景而抒发佛理。那么随着苏轼人生阅历的积累、宦海沉浮的波折,他对于“人生如梦”的般若空观又有了进一步的体会:“当年帷幄几人在,回首觚棱一梦中。”[21]1476“生前富贵草头露,身后风流陌上花。”[26]973经历乌台诗案后,对人生的虚幻更有了深刻的体会。如:“已将世界等微尘,空里浮花梦里身。”[21]393“旧事真成一梦过,高谭为洗五年忙。”[21]942被贬岭南时,人生变幻无常的主题更是反复出现:“生世本哲寓,此身念念非。”[21]2250“梦幻去来,谁少谁多?弹指太息,浮云几何?”[21]2269贬谪生活苦不堪言,但大风大浪之后,苏轼早已看淡人生无常之事。
与苏轼相类似,人生如梦的般若空观也为耶律楚材所深刻认同。耶律楚材早年跟随万松行秀学习佛法“肤浅未臻其奥”[2]4但对人生空无观已有了自己的看法:“但能死生荣辱哀乐不能羁,存亡进退尽是无生路。”[2]9“不信西天三步远,焉知东海一杯深。”[2]41中都城攻破之后,耶律楚材深受打击,其修齐治世的理想完全破灭,内心的苦闷使得他对人生虚无观有了独特的体会:“生死与涅槃,都如昨梦耳。”[2]170“回首五年如一梦,梦中不觉过流沙。”[2]48(《寄移剌国宝》)“生死既知皆是幻,功名犹恋岂能贤?”[2]116(《西域和王君诗二十首其十五》)。国都破灭,他选择了出仕蒙古,但对故国并不是毫无感情,这种情感的矛盾使耶律楚材备受痛苦:“旧山盟约已愆期,一梦十年尽觉非。”[2]21(《和移剌继先韵二首》其一)、“三年沙塞吟魂遁,一夜氊穹客梦清。”[2]21(《过阴山和人韵》其四)。出仕之后,并未能如其所愿修平治国,内心苦闷,以如梦如幻之空观对待人生功名:“一入空门我畅哉,浮云名利已忘怀。”[2]147(《过天山和人韵二绝》其二)、“蛮触功名未足夸,掀髯一笑付南华。他年击破疑团后,始见从来尽眼花。”[2]218(《和非熊韵》)。到了晚年,耶律楚材人生世事无常的观念上升到了王朝的幻灭以及人生行迹的梦幻。如“千古兴亡同一梦,梦中多少未归人”[2]149(《又用韵和王巨川》其二)、“因而识破人间梦,始信空门一著奇”[2]262(《示忘忧》)。“静思二十年间事,聚散悲欢一梦同。”[2]64(十二《过燕京题披云楼和诸士大夫韵》)、“聚散悲欢灯影里,兴亡成败梦魂间”[2]231(《寄妹夫人》)。
从苏轼、耶律楚材对佛学的整体把握来看,二人皆运用佛教理论,超越现实苦难,慰解人生。两者均追求了空观念,以梦幻泡影的态度看待自我坎坷的人生,彰显出了很大程度的一致性。
(二)超然旷达的人生智慧
苏轼与耶律楚材皆认同佛学梦幻虚妄的主题,同时苏轼达观豁然的人生态度亦深深影响了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号湛然居士。关于其称号中的“湛然”一词的来源,孟广耀认为取自苏辙为苏轼写的《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吾生不恶,死不必坠填,无哭泣怛化。’问以后世不答,湛然而逝。”[25]“湛然”一词在苏轼诗中也多次出现,如“遂令冷看世间人,照我湛然心不起”[21]862(《中秋见月和子由》)中指月光皎洁,如同我心波澜不兴,清澈亮堂;如“湛然如古井,终岁不复澜”[21]928,形容古井清澄深净;又如《真一酒歌》“湛然寂照非楚狂,终身不入无功乡”[21]2359指清虚淡泊,寡欲疏狂;结合苏轼的一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21]2641。一生坎坷,宦海沉浮,但苏轼都能调整好心态,以随遇而安、洒脱澹远的态度看待人生忧患苦难。如苏轼的“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26]356就表达了这种随缘自适的情怀。而耶律楚材正是以东坡旷达超然的心态蔑视种种痛苦。他以苏轼“诗意”人生为号,体现了苏轼坦然达观的生存智慧对耶律楚材产生的影响。
在其诗中,可以体会到诗人经历大风大浪、人生浮萍之后,以超然物外、洒脱自适的人生智慧处世。耶律楚材胸怀抱负,“泽民济世学英雄”[2]26,辅佐成吉思汗时,希望能够“扈从銮驾三万里,谟谋凤阙九重城”[2]40。一番大济苍生的壮志却在现实中一次次被消磨打击,在这种夙愿未酬、佞臣排挤夹缝生存中,沉痛哀叹的耶律楚材选择了另一种处世哲学,即归隐林泉、笑傲江湖,如“他年共纳林泉下,茅屋松窗品正音”[2]81“他年收拾琴书去,笑傲林泉我与君”[2]21“百事湛然都不念,祗知渴饮与饥餐”[2]66。到了晚年,耶律楚材已能以苏轼的“此心安处是吾乡”[26]579的人生智慧洞彻人生的真谛,在极度困厄之际亦能闲适旷达、自处湛然,如“但得胸中空洒洒,天涯何处不安生”[2]142“南北东西总是家”[2]151“舍生从此乐余生”[2]144“心与孤云自在闲”[2]48;为此耶律楚材还以书为伴,以琴为友:“聊句弦歌清夜乐,人生适意亦何忧。”[2]150
苏轼和耶律楚材在深刻认同佛教梦幻泡影的同时,耶律楚材也被苏轼旷达超然的人格魅力所影响,并以此心态作为看待外部世界的方式,力图在苦楚虚幻之现实中寻求解脱。
三、耶律楚材慕苏情结之文学表现
耶律楚材不仅在思想上亲近苏轼,在创作上也学习苏轼。他运用自己的妙笔生花,形成了富有内涵的文学表现。在其文集中,其羡苏情结的文学表现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学苏之以议论为诗;二是尚苏之清新雄壮之风。
(一)善于议论
以议论为诗是苏诗的本色,苏轼在诗中爱发议论,且能够将议论、抒情、叙事和描写融为一体,创造出融议论、意象、情感于一体的诗篇。如赵翼曾说:“坡诗不尚雄杰一派,其绝人处在乎议论英爽,笔锋精锐,举重若轻,读之似不甚用力,而力已透十分,此天才也。”[27]苏轼的议论不是枯燥苍白,生硬乏味的,而是妙趣横生,飘逸隽永。例如:“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21]339诗人将议论与自然的景象结合,将天气的变化比喻仕途风雨和人生苦难都是短暂的,一切终究会归于平静,表现了一种随缘自适的旷达。纪昀评其云“阴阳变化开阖于俄顷之间,气雄语壮,人不能及也”[28]。
将议论融入自然景物方面,耶律楚材对苏轼也多加继承。如《西域河中十咏》其六:
寂寞河中府,西流绿水倾。
冲风磨旧麦,悬碓杵新粳。
春月花浑谢,冬天草再生。
优游聊卒岁,更不望归程[2]113。
此诗作于金宣宗元光元年(1222),为耶律楚材随成吉思汗西征第三年。在此期间以卜筮为主,其致主泽民之志未酬,内心苦闷,故在西征期间,游历山川,借此消遣。诗歌前四联绘写溪水轻流,暖风和煦,小麦新长,极写边塞之春色。此诗看似写景,实则借景抒情,故而有“春月花浑谢,冬天草再生”二句。花谢草长本是自然普遍规律,而诗人以己之情移至草木的生长,寄寓着人生的希望。诗人由眼前实景引发议论,由自然芳草的变化悟出人生之期盼,末言归之适意而安。
苏轼性喜山水,常于山水之间融入独特的感悟与洞见。但当诗人之主观情感难以找到合适的物象来抒发时,诗人以论为诗,直吐胸怀,兴到意随,如:
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2]1049
此诗虽言简语短,纯是理宗,却也逸态横生。苏轼以健笔驱遣,以琴寓理,巧妙地阐释了琴声潜于指尖,指尖弹于琴弦,二者紧密结合、密不可分的琴诣。诗歌与耶律楚材的《赠万松老人琴谱诗一首》亦有异曲同工之妙:
良夜沉沉人未眠,桐君横膝叩朱弦。千山皓月和烟静,一曲悲风对谱传。
故纸且教遮具眼,声尘何碍污幽禅。元来底许真消息,不在弦边与指边[2]80。
此诗写诗人良夜未眠,横膝叩弦,奏弹悲风,物我两忘,至臻其奥。“声尘”为佛教语,意言六根清净。耶律楚材痴于奏琴且重于大音希声的意境,故而才有“不在弦边与指边”的体悟。此诗兴到神会,没有指定的意象与诗韵,由琴声的悠扬通透系之绝尘超俗之境。耶律楚材此诗虽不如苏诗来得自然圆融,但也能景中见情,由情寓理,情景理三者相融。
宋诗以理著称,但于理中亦能融情,即议论兼以情韵并行。如《说诗晬语》卷上云:“事难显陈,理难言罄,每托物连类以行之。郁情欲抒,天机随触,每借物引怀以抒之。……倘质直敷陈,绝无蕴蓄,以无情之语而欲动人之情,难矣。”[29]又“议论须带情韵以行,勿近伧父面目耳。”[30]沈德潜认为陈事理言须做到动人之情与诗韵兼行。情感为艺术之生命力,诗韵是哲理诗之灵魂,哲理抽象晦涩,唯有化理为情、由情渗理,诗什才深邃又不失隽永。苏轼的议论诗正是如此,“有情思的向度……并非仅仅以诗‘精言名理’”[31]又“苏诗造理之深、言理之妙……是一种感动,即以一种独特而深刻的个人情感和经验作为依托”[31]111。
耶律楚材在诗中亦好言理,但此“理”是发个人之情,感人生之叹,充沛着真挚饱满的人生体验。如“旦洒生前一腔血,管他身后荣与辱”[32](《峄山书怀》)、“翠竹无心甘晚节,黄花有意助年芳”[2]159(《和武善夫韵二首》其二)、“枝横碧玉天然瘦,蕾破黄金分外香”[2]83(《腊梅二首》其一)。有时为了强调议论,会将议论置于首句,如“人生都几何,半被功名役”[2]29(《和裴子法见寄》)、“学道宗儒难两全,湛然深许国华贤。”[2]66(《再用韵赠国华》)、“人生一瞬息,日月如玑璇”[2]233(《和冯扬善韵》)。
耶律楚材诗的议论虽不及苏轼那般理趣盎然,甚至部分表达有些生硬,但是多数也是将抽象、一般的哲理融于具体、特殊的景象中,将议论融入诗中,饱含情韵地表达出来。
(二)清雄旷放之风
“清雄旷放”是苏轼诗独创的艺术风格,既不同于李白的飘逸豪侠,也异于杜甫的沉郁顿挫。“清”指古雅淳朴,“雄”指清刚劲健,“旷”指达观恣意,“放”指奔放雄豪。苏轼一改唐诗张扬与富腴的韵致,创作出自然洒脱、笔力遒劲的作品,他的诗歌平淡中有韵味,豪情中有风骨,其清丽旷放、文质彬彬的艺术风格得到了耶律楚材的认可,在湛然诗作中,这种清雄之质得以充分展现。
苏轼曾在《答谢民师书》中说:“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33]创作要天工自然,如行云流水,自然圆融,反对刻意雕琢。耶律楚材作诗,秉承了苏轼诗快意自得的审美情趣以及隽永俊逸之风神,特别是一些清丽自然的山水诗作。譬如他的“渔矶旧隐荻花深,尘世宁忘昔日心;两岸清风单舸稳,满江明月一钩沈”[2]72(《和抟霄韵代水陆疏文因其韵为诗十首》其十),自然逸飞,清新旷意,使人忆起“自庇一身青箬笠,相随到处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26]370(《浣溪沙·渔父》);他的“山接青霄水浸空,山光滟滟水溶溶。风回一镜揉蓝浅,雨过千峰泼黛浓”[2]161(《过济源登裴公亭用闲闲老人韵》),动静相宜,色彩清秀,令人想起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21]430(《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二)、“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21]339(《望湖楼醉书》)。一方面,耶律楚材继承苏诗自然浑融、情景合一的境界,透过山水表达对自然的热爱及对人生的慨叹。苏轼有“野桃含笑竹篱短,溪柳自摇沙水清”[21]436(《新城道中二首》其一)的轻快,耶律楚材就有“含笑山桃还似识,相亲水鸟自忘情”[2]95(《壬午西域河中游春十首》其五);苏轼有“夜深风露满中庭,惟有孤萤自开阖”[21]1219(《自兴国往筠宿石田驿南二十五里野人舍》)的独傲,耶律楚材就有“劲挺松柏操,磊落英雄姿”[2]226(《和谢召先韵》)的坚忍不拔。另一方面,耶律楚材吸取了苏诗神性兼备、随物赋形的艺术手法。其“小桃嫌铺翠云叶,疏杏惊看碧玉枝”[2]223(《红梅二首》其一),由苏轼的“认桃无绿叶,辨杏有青枝”[21]1106润饰成之,采用拟人的手法,比之原作精巧生动;又如“酒晕半潮妃子醉,胭脂初试寿阳妆”[21]1106(《红梅二首》其二)以比喻手法传神地表现红梅的娇艳,贴切新奇,神气盎然。
苏轼诗歌行云流水,有清旷之意,更具有雄放之风。同样地,在湛然诗作中,不仅包容“金山前畔水西流,一片晴山万里秋”[2]21(《过金山和人韵三绝》其二)的自然清丽,还纵情倾吐“千里旌旗翻锦浪,一声金鼓振寒波”[2]22(《过天德和王辅之四首》其二)的雄豪刚健;时而清新流丽,时而掣鲸碧海,笔力遒健又不失丰厚余韵。元代王邻在《湛然居士文集序二》中评其诗云:“飘逸雄谈,又义薄云天。”[2]4清人顾嗣立评价说:“雄篇秀句,散落人间,为一代词臣倡始,非偶然也。”[34]元人虞集亦说:“中州隔绝,困于戎马,风声气习多有得于苏氏之遗,其为文亦曼衍而浩博矣。”[35]其诗雄丽洒脱,摒弃浮艳颓靡。如“插天绝壁喷晴月,擎海层峦吸翠霞”[2]21(《过阴山和人韵》其三)、“千岩竞秀清人思,万壑争流壮我观。山腹云开岚色润,松巅风起雨声乾”[2]7(《过金山用人韵》)等奔腾直泻,一气呵成,酣畅淋漓,深得东坡豪放之风。
四、余论
耶律楚材博采众长、转益多师。如冰岩老人云:“向之所言贾、马丽则之赋,李、杜光焰之诗,词藻苏、黄,歌词吴、蔡,兼而有之,可谓得其全矣。”[2]4而在众多诗人中,于耶律楚材影响最显者为陶渊明、白居易、李白、苏轼四位大家。经过统计,慕陶学白分别有13处和20处,钦李羡苏即是11处与12处[3]。虽慕苏未是突出之处,然湛然诗作中的以议论入诗与诗中之达观超然确是师从苏轼。此与时风文潮及家学与个人境遇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