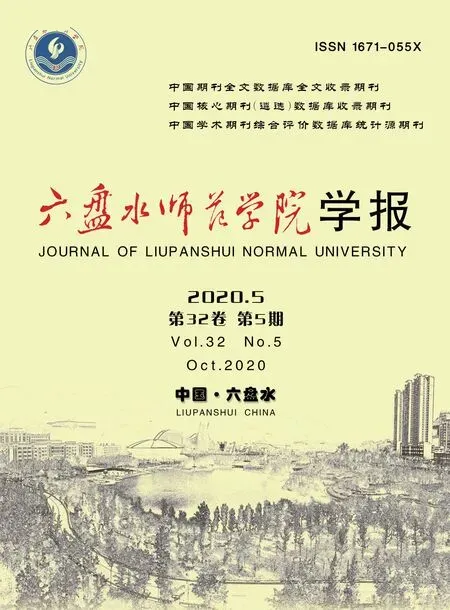湖湘文化与宋代寓湘词人关系刍论
祝文蕊
(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吉首416000)
湖湘文化积淀极为深厚,随着宋代湖湘地区流寓词人的增多,湖湘地域文化的发展也更加繁盛。目前学界关于湖湘文化的研究成果颇丰,但这些研究主要侧重于探究湖湘学派及湖南地域的书院,从文化与作家关系角度来探究湖湘文化与宋代寓湘词人之间微妙关系的研究数量不多且不够全面,笔者以此入手,一方面探究湖湘文化对宋代寓湘词人生活及文学创作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探寻宋代寓湘词人对湖湘文化发展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力求把握宋代湖湘文化发展的脉络及寓湘词人的生存状况、文学创作及历史贡献,以期能深化对此的认知和理解。
一、湖湘文化概况与宋代寓湘词人的生存状况
“湖湘文化”的含义复杂且外延广阔,主要是因为“文化”的含义广泛,广义的文化包括人类所创造的一切劳动成果,狭义的文化主要包含文学、艺术、宗教等精神方面的内容,并带有一定的时代性与地域性,笔者侧重于探讨狭义的文化内涵。“湖湘”一词则带有鲜明的地域色彩,自唐代有“湖湘”专属称谓之后,其地域范围的界定也更加清晰,区别于“荆汉”地区,主要包括以湖南省为主的湘、资、沅、澧四水系及洞庭湖在内的广阔地域。基于此,“湖湘文化”的内涵可归纳为湖湘地域本土及外来人物所生产出的文学、艺术、宗教等精神产品总和,是一种既含独特地域属性又含鲜明时间属性的地域文化。
这种文化的形成与积淀,受到多重因素影响,从自然环境方面来看,湖湘地区“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迭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1]1。绵延的山脉限制了这一地区陆路交通的发展,但湖湘地区并非“水少”之地,与之相反的是此地水系丰富,有湘江、资江、沅江、澧水四条主要水系,又有洞庭湖“浩浩汤汤,横无际涯”[2]966,水路交通便利。水多则会影响人们的生存状态和心理,如刘师培所说,南方“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3]162。这奠定了湖湘地区人们的文学、艺术等心理基础与观念。再从历史发展来看,湖湘地区崇巫、尚巫,先秦时期,除了《九歌》中对山鬼、东皇等神带有歌颂以及神化性质的描写,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中更以写实的方式详细地记述了湖湘地区的巫俗习惯,正月初一,人们“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恶鬼。贴画鸡,或斫镂五采及土鸡于户上。造桃板著户,谓之仙木。绘二神贴户左右,左神荼,右郁垒,俗谓之门神”[4]2-5,新年伊始,楚地人民没有先拜访亲友,而是先放爆竹辟鬼。这些宗教习俗不仅成为湖湘文化的一部分,也奠定了湖湘地区宗教、文学等的基础与底调。
唐宋之前,湖湘文化以楚文化为基础逐步发展,但较为缓慢。唐宋以来,随着中央对地方统治的加强、地方贬谪人群的增多、战争避难人群的涌入等原因,湖湘文化发展开始走向繁荣,诚如范仲淹所说“迁客骚人,多会于此”[2]966,湖湘地区成为词人墨客的栖息地。按照《全宋词》中收录的词人进行不完全统计,除去湖湘地区本土词人,宋代因迁谪、隐居、避难于此的词人多达七十余位,其中不乏词作大家,代表性的如黄庭坚、秦观、陈与义、辛弃疾、姜夔等。
湖湘之地虽水路交通便利,风景秀丽,但阴湿多雨、山路崎岖的自然环境并不适合人类的生存,因为过错遭到贬谪的词人,内心多因贬谪而痛苦、愤懑,触目所见,虽山水秀丽,却人烟荒凉,不如京都繁华,离开繁华京都的落差及贬谪的愤懑汇而为一,更加深了词人内心的痛苦和对环境的不满,如王禹偁就曾说他身处“六百里之穷山,唯毒蛇与贙虎”[5]7。词作大家黄庭坚则更甚,他在绍圣元年(1094)初遭到贬谪,认为自己被“屏弃不毛之乡,以御魑魅。耳目昏塞,旧学废忘,直是黔中一老农耳”[6]1377,将自己比作农夫。当他从京城至黔州时又言其“万里投荒,一身吊影,成何欢意。尽道黔南,去天尺五,望极神州,万重烟水”[7]387,刚离开汴京城繁华之地的词人,面对着阴雨连绵、瘴气横行的环境,他不仅内心受到折磨,身体上也多病多灾,并且生计艰难,亲人生离死别者众多,他在《与唐彦道书》中说他生计困顿“到黔中来,得破寺堧地,自经营筑室以居,岁余拮据,乃蔽风雨,又稍葺数口饱暖之资,买地畦菜,二年始息肩”[6]1769-1770,又在《与吕晋父帖》中说起他病痛缠身“哀苦穷困,多病婴缠,日力不自给”[6]1679。其他如秦观等贬谪的寓湘词人的生存状况也多相似。
因避祸而寓居湖湘者,他们的生活状况较之因为过错遭受贬谪的词人更加窘迫危险,他们不仅要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还有因国家动荡、城阙残缺对自身安全的威胁以及对未来的茫然,如陈与义,按其年谱所载,靖康元年(1126)“正月,北虏入寇,复丁外艰。自陈留寻避地”[8]995。离开汴京,一路流亡,至建炎二年(1128)八月到岳阳,却在随后的一两年间辗转于郢州、长沙、洞庭等湖湘多地,年谱中载其“建炎三年(1129)留岳阳……四月,差知郢州……五月,避贵寇入洞庭,过君山,泊宋田港,复从华容道还……九月,别巴丘,由南洋抵湘潭……建炎四年(1130)自衡岳历金潭,下甘泉,至邵阳……至秋被召”[8]996。因游历而寓居湖湘者,他们没有官职俸禄,生活上也多有拮据之感,如姜夔,在游历湖湘之地时结识萧德藻,给予了他资助。
这些寓湘词人在湖湘之时,目之所及的山川秀水、历史文化,身之所经历的风俗习惯都对词人的内心情感产生了震撼,受到湖湘文化的影响,他们在文学作品中也带有了湖湘文化的气息,而他们自身的学识也为湖湘文化的发展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湖湘文化对宋代寓湘词人的影响
湖湘文化中所包含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山水胜景、神话传说、巫术习俗、节日庆典等元素在潜移默化中浸染着这些寓湘词人的审美情趣与风格,影响他们作品的主题与内容,也为他们提供丰富多彩的创作素材。
(一)提供创作素材
湖湘文化的地域色彩十分鲜明,除了与北方迥异的山水风景,即便是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都与北方有明显差异,词人更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1]1,流寓至此的词人们初到此地时就被这奇妙的山水风景、独特的风俗习惯、诡谲浪漫的神话传说所吸引,他们在创作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湖湘地区的文化元素。
首先是洞庭湖、岳阳楼等湖湘山水意象的使用,湖湘地区奇妙的山水风景能在短期内对词人造成最直观的视觉冲击与心灵震撼,即便只是途经湖湘地区,也可将所见所闻作为写作素材,化入诗词创作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洞庭湖意象,如张孝祥在乾道二年(1166)罢静江府北归,途经洞庭湖时以洞庭湖为主要意象,即兴创作了《念奴娇·过洞庭》一词:
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玉鉴琼田三万顷,著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应念岭海经年,孤光自照,肝肺皆冰雪。短发萧骚襟袖冷,稳泛沧浪空阔。尽吸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扣舷独笑,不知今夕何夕[7]1690。
全词从湖湘地区特有的景象洞庭湖青草开始写起,以下次第写湖光山景与湖上明月,将作者眼中之景呈现于读者眼前,整首词读起来“飘飘有凌云之气”,若非是张孝祥目之所及,他也定不能写出这样一首“在集中最为杰特”的词作了。另外,寓居于长沙的李曾伯有《水调歌头·洞庭千古月》一词,词以洞庭湖意象为主体,描写了词人中秋夜与友人共赏洞庭湖美景,词写“洞庭千古月,湘水一天秋。凉宵将傍三五,玩事若为酬。人立梧桐影下,身在桂花香里,疑是玉为州。宇宙大圆镜,沆瀣际空浮。傍谯城,瞻岳麓,有巍楼。不妨举酒,相与一笑作遨头。人已星星华发,月只团团素魄,几对老蟾羞。回首海天阔,心与水东流”[7]2827,词中洞庭月色、岳麓巍楼、沅湘草木,非湖湘地域难以见到、非亲身经历难以感受、非目之所及难以描摹。
另者便是湖湘地区的历史文化与宗教风俗元素的运用。屈原、贾谊等历史人物,湘妃、渔父、山鬼等神话传说,《离骚》《九歌》等文学作品以及湖湘独特的风俗习惯都是湖湘文化的深厚积淀。寓居于此地的词人在这种异于中原文化的氛围下,往往更易将之写入作品中,如湖湘地区七夕节时的“人家妇女结彩缕,穿七孔针,或以金、银、石为针,陈几筵、酒、脯、瓜果、菜于庭中,以乞巧”[3]55。张孝祥知潭州时,恰逢七夕,作《二郎神·七夕》一词,词中描写湖湘地区七夕景象为“南国。都会繁盛,依然似昔。聚翠羽明珠三市满,楼观涌、参差金碧。乞巧处、家家追乐事,争要做、丰年七夕”[7]1692,将湖湘地区的民风习俗作为素材写入词中。其他如陈与义的《除夕》、秦观的《阮郎归》中都有对湖湘地域节日习俗的描写。
虽然宋词中洞庭、岳阳楼等意象的运用以及湖湘地区风俗的描写十分常见,但若非亲身所处、亲眼所见,词中景致只能是兀自想象,缺了生动与情致。
(二)影响作品主题与内容
湖湘地域迁谪流寓历史十分悠久,可上溯至屈原,他两遭贬谪,足迹遍及沅湘,他在流放期间所创作的《离骚》《渔父》等作品更成为湖湘迁谪文学的奠基。此后百年,汉代贾谊也被贬谪至此,触景感怀而写了《吊屈原赋》,贾谊以屈原所遭遇自喻,赋作极尽哀婉缠绵,确立了湖湘贬谪文学的基调。宋代贬谪流寓至湖湘地区的词人众多,他们内心大多郁郁不得志,借由屈贾来暗喻自己内心情感,因此他们的作品主题多是山水隐逸与咏史羁旅,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秦观与陈与义。
秦观在绍圣三年(1096)因为元祐党争被削秩徙郴州,直到元符年间才离开。在秦观尚未被贬谪到郴州前,他的词作内容多是一些游玩、登临、唱酬之作,如作于元丰三年(1080)的《望海潮·星分斗牛》,词中描摹了州郡的雄壮、人物的豪骏、居所的华丽,虽然下片有怀古描写,但只是感叹,情感不深,据《秦观词年表》所载,此词是秦观“日以文史自娱”,兴之所至,泛舟观赏而赋。当秦观被贬谪至郴州时,他即吟“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7]460,黄苏的《蓼园词选》评其“少游坐党籍,安置郴州。首一阙是写在郴,望想玉堂天上,如桃源不可寻,而自己意绪无聊也。次阙言书难达意,自己如同郴水绕郴山,不能下潇湘以向北流也;语意凄切,亦自蕴藉,玩味不尽”[9]712。秦观寓居湖湘期间,内心因为贬谪而深觉痛苦,身处桃源典故的发生地,受到桃源隐逸思想的影响,开始频繁在作品中描写这一主题与内容,他的另外两首词《阮郎归》(潇湘门外水平铺)与《临江仙》(千里潇湘兰浦)两词的主题与内容也与上词有异曲同工之妙。
陈与义也在湖湘辗转流寓很长一段时间,但他与秦观的贬谪不同,他是为逃避灾难南下至岳州,后来又经过长沙、衡阳等地。《全宋词》中收录陈与义词18首,有5首词是在寓居湖湘期间所作,这几首词在主题与内容上一致,多借用湖湘特有的山水风物来表达自己的羁旅之意,与剩下的13首词并不一样,如他在建炎三年(1129)所写的《临江仙》及《虞美人》二词中先后说明他“高咏楚辞酬午日”[7]1068“满载一船离恨、向衡州”[7]1068,词中借吟咏楚辞来表现内心羁旅的愁苦之意。另外13首词中,除去3首《法驾道引》的仙曲之外,剩下10首词,多表现的是追忆往昔之意,如他的《虞美人·十年花底承朝露》《虞美人·扁舟三日秋塘路》《临江仙·忆昔午桥桥上次》等词,所表现的主题都是追忆往昔。
(三)陶染审美情趣与风格
我国地域辽阔,南北地理环境差异巨大,《隋书·文学传序》中就注意到这一问题,指出“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10]2122,自然环境的差异也影响到了词人的气质和风格。湖湘地处我国南方,气候适宜、山川秀美,按汪辟疆所言湖湘地区“襟江带湖,五溪盘亘,洞庭云梦,荡漾其间。兼以俗尚鬼神,沙岸丛祠,遍于州郡;人富幽渺之思,文有绵远之韵”[11]20-21。再者,湖湘地区是屈原、贾谊等人的贬谪之所,《楚辞》《吊屈原赋》等作品奠定了湖湘文学去国离家、忧谗畏讥的幽怨基调,在这种地理环境及人文环境的影响下,本土文人的审美情感及风格倾向于凄婉浪漫,而途经及长期流寓此地词人的审美情感及风格也受其影响,代表性的词人有姜夔及张舜民。
姜夔,在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曾客居湖南并作有7首词,按《姜白石词编年笺校》来看,这7首词的编年在姜夔词作创作时间上十分靠前,仅次于淳熙三年(1176)的《扬州慢》。姜夔词风本就倾向于清空雅正,而在他寓居湖湘期间,受其山水滋养,身处二妃及屈贾故事的发源地,对此的感受也更深,所写之词的风格及情感上也更加清空凄婉。如他的《小重山令·赋潭州红梅》及《一萼红》都是在寓居长沙期间所作,皆为描写红梅,这两首词感怀吊古、托兴深远,哪怕是借用二妃之事也能忧思缠绵,而姜夔寓居苏州时所写《暗香》《疏影》两词,虽同样是写梅花,却在审美风格上有所不同,前两词在情感表达上加入了湖湘地域特色,借用二妃典故,在风格上更加凄婉缠绵,后者则借杜诗、寿阳公主及昭君事,风格上更倾向于清空潇洒。
张舜民,宋元丰六年(1083),张舜民因写作《西征回途中》一诗,获罪遭贬至郴州,《全宋词》中收录张舜民词4首,其词风如其诗文风格,豪重且有理致,但在他贬谪途经岳阳楼时所做的两首《卖花声》中,词风一改其前,偏于凄婉幽怨,词曰:
木叶下君山。空水漫漫。十分斟酒敛芳颜。不是渭城西去客,休唱阳关。醉袖抚危栏。天淡云闲。何人此路得生还。回首夕阳红尽处,应是长安。(其一)
楼上久踟躇。地远身孤。拟将憔悴吊三闾。自是长安日下影,流落江湖。烂醉且消除。不醉何如。又看暝色满平芜。试问寒沙新到雁,应有来书。(其二)[7]265
岳阳楼风景开阔,极目眺望则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按其一贯风格来看,本应豪迈潇洒,但却在登上岳阳楼时踯躅惆怅,周煇在《清波杂志》逐客一条中评价这两首词曰:“放臣逐客,一旦弃置远外,其忧悲憔悴之叹,发于诗什,特为酸楚,极有不能自遣者。”[12]138对于迁谪的芸叟而言,湖湘的自然山水与历史人文给了他精神慰藉,他将耳目所见、内心所感与自己内心的忧思踌躇合二为一倾注笔端,更增其幽怨哀婉。
湖湘文化“造于鬻熊”,历史悠久,地域特色鲜明,寓居于此的词人深受其熏染陶冶,于词作题材上更加多样,于审美风格上更加多元,于词作内容上更加丰富,于情感诉求上更加饱满。
三、宋代寓湘词人对湖湘文化的推动与贡献
湖湘文化在萌芽期就与流寓文人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第一位诗人屈原就来自于湖湘地区,其创作是在湖湘这一地域空间内进行的,此后的贾谊、李白、刘禹锡等人皆有寓湘的经历,并在寓湘期间创作了大量具有湖湘特色的作品,湖湘文化发展至宋代,更是与张孝祥、陈与义、朱熹、张栻等寓湘词人密不可分。
(一)湖湘学派的发展及文人培育
湖湘地区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寓湘词人之间关系十分紧密,他们一方面推动了湖湘理学的发展和繁荣,另一方面也成为湖湘文化发展的主力军,并主动承担起这一区域内文人学者培育的重担,自觉成了湖湘文化的学习传播者与继承创造者。
首先,湖湘学派的发展与繁荣得益于这些寓湘词人。湖湘文化发展至宋代,尽管已经较为繁荣,但并未能形成自己的学术流派。与北方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学派林立的局面相比,南方的湖湘地区在学术发展上就稍显贫乏了,但自张栻、朱熹进入湖湘大地之后,逐步改变了这种局面。湖湘理学虽起源于周敦颐,但其传播与推动者中贡献最大的则非张栻、朱熹莫属。南宋年间,张栻受聘于岳麓书院,在岳麓书院聚众讲学,当时来听学的有千人之多,一时蔚为壮观。乾道三年(1167),朱熹也从福建来到湖南,在岳麓书院中与张栻进行论学,即闻名于世的“朱张会讲”,这次论学,使得湖湘理学闻名于当时,对湖湘理学理论的形成和成熟都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也改变了湖湘地区学术发展弱势的局面。紧随其后的魏了翁在靖州为官期间,广泛吸收了湖湘理学的相关理论,开办“鹤山书院”,让湖湘学派的理论逐步走向全国。而湖湘理学作为湖湘文化的一部分,它的蓬勃发展也促进了湖湘地区整体的文化发展。
其次便是文人的培育与文化的传播。寓湘词人在迁寓至湖湘地区时,其自身就属于文化知识阶层,本身就携带了大量的外来文化,在他们寓湘期间又广泛地接触到湖湘地区的本土文化,因此他们在传播外来文化的同时,又会融合湖湘地区的本土文化,如真德秀,他在潭州为官时,就提倡教化,而这种教化不仅有中原文化,还有湖湘本土的巫觋文化。文化传播最强有力的媒介就是书院,宋代湖湘地区的书院发展更离不开这些寓湘词人的建设和推动。书院自唐代开始便已经存在,发展至宋代已经相对成熟,南宋时期,湖湘地区大批流寓文人的涌入,书院的发展更加繁荣,闻名于世的四大书院中,衡阳石鼓书院及长沙岳麓书院都在湖湘地区。宋代流寓于此的词人通常聚集于书院讨论书中疑难之处,彼此探讨学术,朱熹在《衡州石鼓书院记》中说:“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13]3783这里他指出了宋代书院的基本情况。同时他自己也是书院建设的推动者,绍熙四年(1193)他知潭州兼荆湖南路安抚期间,就重新改建了岳麓书院,给岳麓书院注入了新鲜血液。书院的发展为湖湘地区培育了大量的文人,一时之间,“湖湘江浙之士,不远千里负书从学”[14]1335。
(二)山水胜景推广
湖湘地区自然景观众多,它们之所以为人们所熟知,也得益于宋代寓湘词人的探访和吟咏。
湖湘地区的山水胜景中,有些在宋代时已经为大众所熟知,而那些本来就已经家喻户晓的自然及人文景观也因词人的反复吟唱而更加有名,甚至成为地域文化标志。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洞庭湖、岳阳楼。如张孝祥从乾道元年(1165)至乾道五年(1169),五年之中三次寓湘,在此期间,有多首词写洞庭湖和岳阳楼,上文中所提及的《念奴娇·过洞庭》在描写洞庭湖景色中最为有名,另外还有《浣溪沙·洞庭》,词中描写星夜下的洞庭湖“红蓼一湾纹缬乱,白鱼双尾玉刀明”[7]1703,动静结合,场面虽不阔达,却别有一番风味。此外还有《水调歌头·过岳阳楼作》,反复吟咏了岳阳楼景致。
湖湘地区还有一些少为人知的优美景色,但由于古代地理交通不够发达,且并非是像汴京、临安那样的大都市,因此许多地方景致虽好,却人迹罕至。流寓在湖湘地区的词人们往往喜欢拜访、参观名胜古迹,于山水之中寻找乐趣,兴之所至便借由词作抒发情感,词作中所出现的自然及人文景观在历史长河中渐为人们所熟知。其中包括岳州明山、南岳铨德观、长沙橘子洲等,这些地方在寓湘词人的词作中皆有写到。岳州明山,《嘉庆一统志》中载“在平江县南五十里,一名奉国山。高七十余丈,周回三十余里。三面峭绝,惟一径可通”[9]1603。陈与义在岳州时有《忆秦娥》一词,注为五日移舟明山下作,词中不仅写了潇湘之景,还写了明山之雨,清新自然。铨德观则在衡山紫霄峰顶,若非香客,甚少有人到访,乾道二年(1166),张孝祥东归经湖南时,曾到此一游,写有《望江南》一词,词曰“朝元去,深殿扣瑶钟。天近月明黄道冷,参回斗转碧霄空。身在九光中。风露下,环佩响丁东。玉案烧香萦翠凤,松坛移影动苍龙。归路海霞红”[7]1705,将观中烟火鼎盛的场面写得飘飘若神仙之境。这些山水胜景的描写,让湖湘地区的美景为更多人所熟知,让其成为著名的旅游胜地。
四、结语
综上所述,湖湘文化与宋代寓湘词人之间的关系绝不是一方单方面的影响另一方,而是呈现一种双向互动的特点,并且在这种互动中,湖湘文化与寓湘词人之间互相依存,湖湘文化为寓湘词人提供创作灵感及源泉,也为他们的精神寻找契合栖息地,而寓湘词人也报之以琼玉,毫不吝啬对湖湘大地的讴歌与赞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