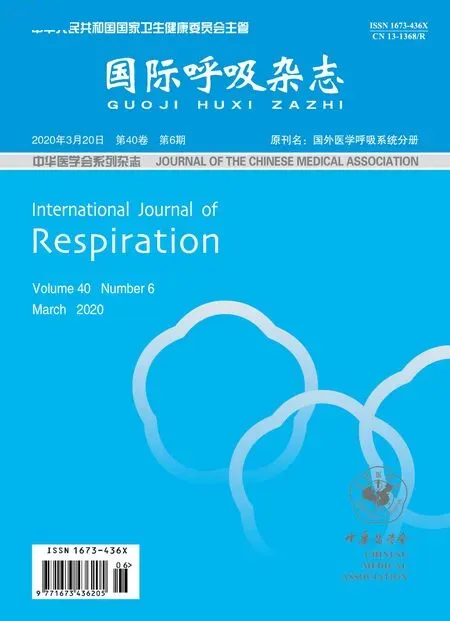肺泡巨噬细胞在肺部稳态及感染中的作用研究进展
沈阳 冯旰珠
1南京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 210011;2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呼吸科210011
呼吸系统疾病是全球人类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肺部感染、肺癌和COPD每年造成数百万人死亡[1]。人体呼吸道大致分为上呼吸道和下呼吸道。上呼吸道由鼻子、咽部和喉部组成。下呼吸道为树状组织,从气管分支到支气管、细支气管,最后是肺泡。肺泡下方是密集的毛细血管网络,生命必需的氧气和二氧化碳交换便在肺泡上皮和肺泡周围的毛细血管内皮之间进行,二者仅由厚度为0.2~0.5μm的融合基底膜分开。人体每天吸入近11 000 L空气,其中包含了许多危险的或无害的颗粒、毒素、过敏原和感染因子,肺泡脆弱的屏障不断暴露于这些潜在的危险环境,需要有效的肺部免疫系统进行密切监测。肺泡巨噬细胞(alveolar macrophages,AMs)位于肺泡的腔侧,是呼吸树的第一个哨兵,也是机体固有免疫重要的组成部分,稳态下AMs占肺泡内90%~95%的细胞组成。AMs受到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进化出相应的功能,履行着维持肺内稳态和第一线防御的作用[2-3]。
1 AMs的起源和极化
“吞噬”的概念来自古希腊,是19世纪80年代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Elie Metchnikoff定义的,用来形容巨噬细胞吞噬异物的一种防御机制。曾经的主流观点认为大多数组织巨噬细胞来源于循环和骨髓中的单核细胞前体。最近的深入研究表明,肺泡驻留巨噬细胞源自胚胎衍生的胎儿单核细胞,并在出生后形成高度依赖于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的自我复制,可持续整个生命,并在大多数情况下 (稳态时)独立于血液单核细胞的输入[4-5]。在发生感染、代谢紊乱时,可通过募集骨髓来源的血液单核细胞以补充肺泡驻留巨噬细胞。AMs群体在不同状态下存在高度动态调节,炎症可以增强肺泡驻留巨噬细胞的低水平增殖能力,而循环的单核细胞也可以长期替换原始的AMs。AMs的不同来源造就了其异质性,使AMs在不同的机体状态下能够发挥及时的应对策略。
巨噬细胞极化是巨噬细胞对微环境产生特定功能反应的过程[6]。目前以 “M1/M2”来命名2种不同的极化状态。M1型巨噬细胞又称 “经典活化巨噬细胞”,可由干扰素γ、肿瘤坏死因子α、脂多糖等诱导,表达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Ⅱ(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Ⅱ,MHCⅡ)、CD68、CD80及CD86共刺激分子等;M2型巨噬细胞即 “替代活化巨噬细胞”,可由IL-4、IL-13、IL-10等诱导,表达高水平的CD163和CD206[7]。M2型巨噬细胞根据刺激因子不同又可进一步分为M2a、M2b、M2c和M2d[8-9]。M1/M2巨噬细胞在分泌促炎/抗炎细胞因子、诱导Th1/Th2细胞免疫反应、无氧糖酵解代谢/氧化代谢、螯合/释放铁代谢等方面均有不同[10-11]。总体来讲,M1巨噬细胞具有促炎、抗微生物、抗肿瘤活性,但同时也介导了组织损伤、损伤组织再生和伤口愈合;而M2巨噬细胞对于碎片和凋亡细胞具有强大的吞噬能力,能促进组织修复和伤口愈合,促进血管生成、纤维化、肿瘤形成和进展,参与寄生虫的清除等[12]。在病原体感染时,巨噬细胞在相应刺激诱导下形成M1型巨噬细胞,产生多种促炎细胞因子,以消灭病原体;而一旦感染得到控制,免疫系统则通过产生更多的M2型巨噬细胞来中和M1型巨噬细胞的作用[13]。
与概念上简单的双峰极化相比,在体内实际上存在更复杂的表型谱,尤其是在体内多种因素作用下[14]。此外,完全分化的巨噬细胞在暴露于新的组织环境时可能保留改变其基因表达谱的能力[15]。这突出了巨噬细胞在分化后进行重编程的潜在能力,可以作为未来潜在的治疗方法。目前,不同极化巨噬细胞的新标记也在不断发现、更新,如M1(CD38、Gpr18和Fpr2)和M2(Myc和Egr2)。而除环境因素外,细胞信号在巨噬细胞极化中的重要作用也正被研究者们所揭示。目前研究较多的有信号转导与转录激活因子 (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STAT)、干扰素调节因子、过氧化物酶增殖物激活受体γ、细胞核转录因子κB和激活蛋白[6,16]。其中,巨噬细胞极化受STAT1和STAT3/STAT6的细胞信号传导事件之间的平衡密切控制。以操纵信号通路调节M1/M2巨噬细胞的表达来控制疾病是可行的。
2 稳态下的AMs
稳态下的AMs在面对组织碎片、无害刺激时整体处于免疫耐受状态,以减轻不必要的肺组织损伤。AMs一方面可以通过分泌抗炎因子如转化生长因子β、一氧化氮、IL-10和前列腺素等,趋向于抑制对吸入抗原的免疫应答[17];另一方面,AMs表达一组抑制性表面受体,如转化生长因子β受体、信号调节蛋白α及其配体表面活性蛋白A和D、IL-10受体、CD200受体,组成性地减少AMs活化,以维持肺部稳态[18-20]。
稳态下AMs另一个重要的功能是吞噬和分解代谢肺表面活性剂。肺表面活性剂是脂质 (90%)和蛋白质 (10%)的复杂混合物,由Ⅱ型肺泡上皮细胞合成、分泌和再循环,具有促进最佳气体交换、防止呼吸不全或肺泡萎陷的功能。AMs介导很大一部分的表面活性物质脂质代谢,当AMs减少或吞噬功能发生障碍时,会导致肺泡蛋白沉积症和呼吸衰竭[21]。其中,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受体-过氧化物酶增殖物激活受体γ轴是AMs对表面活性剂分解代谢的关键分子途径[22]。
3 肺部感染中的AMs
3.1 免疫应答初期 肺泡腔中的AMs固着于肺泡上皮细胞,并且对肺泡液体流中输送的微生物进行监测。AMs通过识别、吞噬、消化、抗原递呈等对病原微生物进行有效免疫应答。AMs利用其模式识别受体来识别病原体相关分子模式和危险相关分子模式,如果微生物表面被抗体或补体C3b片段所包被,巨噬细胞还可通过表面的Fc受体或C3b受体与上述分子分别结合,激活防御途径[23]。一旦识别,巨噬细胞会引发促炎细胞因子的产生,如肿瘤坏死因子α、IL-6、IL-12和IL-1β,释放趋化因子IL-8,诱导邻近的巨噬细胞向感染部位聚集,以及从血液中招募中性粒细胞、单核细胞和其他效应细胞[24]。随后,巨噬细胞对病原微生物进行吞噬,这是由精细调控的细胞骨架蛋白重塑来驱动实现的。肌动蛋白骨架的重排促使巨噬细胞游向并附着于吞噬物,细胞局部凹陷,形成富含F-actin的膜结构(如丝状伪足、板状伪足和吞噬杯等),包绕病原体并吞入细胞内[25-26]。肌动蛋白细胞骨架作为维持细胞形态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巨噬细胞吞噬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巨噬细胞对吞噬体内的病原体通过形成酸性环境、与溶酶体形成吞噬溶酶体、生成多种毒性物质等多种手段进行酸化、消化,发挥杀菌作用[27]。病原体的消化产物通过胞吐作用被清除至细胞外,而具有免疫原性的肽类物质则与MHCⅡ类分子结合形成肽-MHCⅡ复合物,表达于细胞表面,向T细胞迁移并提呈给不同的T细胞亚群[28],启动特异性免疫应答。
3.2 免疫应答后期
3.2.1 控制组织损伤 炎症反应在消灭病原体的同时,也会造成组织的损伤,AMs需要及时控制炎症反应以避免组织损伤。在免疫应答后期,活化的免疫细胞通过线粒体凋亡通路和受体介导的凋亡通路发生凋亡,表达 “发现我”、“吃我”信号,巨噬细胞的一些受体 (如磷脂酰丝氨酸受体、清道夫受体)与凋亡细胞表面这些信号分子结合,介导吞噬[29]。AMs对凋亡细胞的吞噬减少了炎症期招募来的细胞,防止垂死细胞释放促炎和有毒物质进入环境,释放了抗炎和修复因子,并抑制了促炎性细胞因子、趋化因子和白三烯C4等的分泌[30-31]。AMs还可通过与肺泡上皮细胞的相互作用来调节免疫,如分泌细胞因子信号传导抑制剂来抑制肺泡上皮细胞STAT的激活、通过二者之间的间隙连接和钙波的传播来抑制免疫等[32-33]。此外,AMs还能通过促进调节性T细胞反应来抑制炎症[34]。AMs通过上述几种机制调控免疫反应以控制炎症、减少组织损伤。
3.2.2 病原体持续存在 然而,控制组织损伤可能会利于病原体的持续存在。在军团病、结核病、胞内寄生虫、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中均发现病原菌在AMs中持续存在和复制[35]。Roquilly等[36]最近的一项研究也表明,在严重感染消退后肺部树突状细胞和巨噬细胞获得免疫耐受,导致持续免疫抑制和易受继发感染。
导致病原体持续存在的因素是多样的。其中,AMs的免疫抑制可能是导致免疫逃避的关键[37]。例如,在控制组织损伤的介质中,具有抗炎作用的前列腺素E2可以通过增加细胞环腺苷一磷酸来抑制自然杀伤细胞活性、下调树突状细胞上的MHCⅡ类表达以降低抗原呈递、抑制NADPH氧化酶以抑制对细菌的杀伤。另外,AMs对凋亡细胞的摄取也会抑制它们吞噬和杀死细菌的能力[38]。还有,AMs的极化也是病原体持续存在的重要因素之一[39]。与M1巨噬细胞的葡萄糖依赖性代谢相比,M2巨噬细胞的抗微生物活性降低、氧化代谢增加,可导致宿主中病原体持久存在;M2巨噬细胞还表现出对病原体有益的铁代谢[11]。这些因素使病原体能长期存在于体内,因此,组织开始修复的时机对结果至关重要,过早解决炎症反应可能会延长微生物感染。
4 存在的一些问题
虽然目前对于AMs的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比如:(1)实验方法中常规使用的肺泡灌洗液中获得的AMs部分是否代表肺中的整个AMs群体?以支气管肺泡灌洗获取AMs,虽然不存在使用酶、诱导剂等导致表型和功能改变,然而,支气管肺泡灌洗仅能获得小鼠气道腔中总AMs的约10%,还有一些AMs与上皮紧密结合,未被灌洗获取。有研究[33]表明,这些固着巨噬细胞明显不同于支气管肺泡灌洗可以获取的巨噬细胞。(2)在清洁条件下饲养的实验小鼠中的观察结果是否也适用于从早期生活中就暴露于反复感染和炎症的人类?(3)不同年龄、不同状态 (稳态、肺部感染、感染恢复后)的AMs组成有何种变化?这些变化是否会导致其他相关的肺部疾病,如继发肺炎、肺纤维化、肿瘤等?(4)对于体内AMs的表型和功能、组成的动态变化等仍需要借助于新的技术手段,在群体和单细胞水平上同时进行大量的研究和比较。
5 结论和展望
AMs因其不同来源和潜在的可塑性,能够对周围环境多样的刺激产生相应的影响,包括分泌多种促炎或抑炎免疫介质、改变吞噬和抗菌活性等。充分认识到AMs在肺部免疫应答不同阶段的表型变化和功能作用,对于维持肺部稳态、控制肺部感染至关重要。在未来的临床应用上,可以形成以AMs为中心,通过表观遗传修饰因子[40]、非编码RNA[41]、活性氧[42]等不同手段来操纵 M1/M2表型的平衡,选择性增强抗微生物防御或抑制有害炎症等,形成抗感染、控制组织损伤、减少胞内病原菌持续存在等一系列有效的治疗方案。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