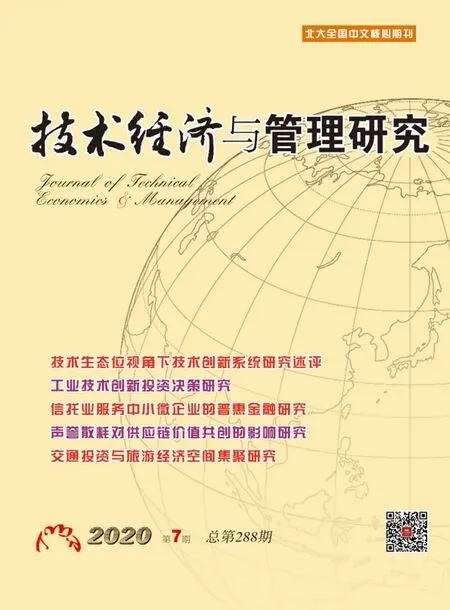科普传播著述须用心甄别重要概念语义之转变
——以力学与形而上学等概念寓意之沿革为例
卫 青,厚宇德
(1.山西省地质调查院,山西 太原 030006;2.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所,山西 太原 030006)
有些优秀科普著述(如竺可桢、茅以升等人的若干科普作品)[1,20],常在特定的学科发展史或相关历史文化背景下展开叙事。这种做法有一个妙处,即能够较为自然地诠释与特定科学知识相关联的文化背景,以及特定文化背景对这些科学知识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在科学史家萨顿看来,科学史是衔接科学与文化并创造更高尚文化的最重要的坚实桥梁[3]。因此,在科学史背景或在更广义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撰写科普作品,除了有利于普及科学知识外,往往还可以一举多得,所成就的作品本身也富有浓郁的文化氛围。
阅读科学与人文学养深厚的前辈们(如竺可桢、茅以升等等) 的这类科普作品,让人感觉到在娓娓道来之中,一条条历史与文化例证信手拈来,十分轻松、自然。事实上,以这种方式与风格撰写出的科普作品,对作者的素养要求极高,是一种严苛的考验。如果学有不逮或稍微马虎粗心,就可能酿成错误而贻笑大方。文章以英文“mechanics”(力学或机械学,也蕴有“技巧”之意) 与“physics”(物理学) 以及“metaphysics”(形而上学) 等词汇在不同历史时期寓意之差异以及人们对其相应的心态变迁为例,对此理予以说明。
一、西方文化中“力学”与“物理学”语义的演变
在西方文化中,从字面上看,由古希腊到中世纪,再到文艺复兴直至今天,“力学”与“物理学”这两个词汇一直存在。然而在西方学术史上,在不同时期与不同学派学者的思想认识中,“力学”与“物理学”的含义一直演变,其含义与今天的力学和物理学寓意大相径庭。如对此缺乏了解,撰写著述时望文生义而不根据不同历史时期对其含义做些分辨,就无法避免大错特错甚至浑然不觉。
由于在工程技术等领域的特殊贡献,今天的力学已经成为独立的一级学科。但从学理上看,毫无疑问力学是物理学知识体系中最早完善的一个重要分支。然而德国学者、物理学家赫尔曼(Armin Hermann) 曾指出:“从亚里士多德到伽利略时代,力学与物理学是对立物。”[4]在有的古代西方学者,比如在柏拉图(Plato) 看来,物理学研究的是地球上人类周围的物理现象。而人类靠观察变动无居的自然界,是根本不能认识到世界本质的。因此,物理学算不上一门能够与天文学、数学相提并论的科学。柏拉图认为与物理学的做法相反,只有研究永恒不变的、与现象世界相对的理念世界,才能获得真理。
那么在伽利略之前的西方学者看来,力学究竟与物理学有什么区别呢?赫尔曼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十分出色:那时的“人们把物理学视为关于自然物的科学,而把力学看成反自然的行动:用小的力举起巨大的重物,用阿基米德水车把水反其自然地抽到高处,这都是人们用来欺骗自然的伎俩。当时有一位比萨大学的数学家,名为吉多巴尔多·德尔·蒙特,他把机器的应用看成不可思议的事情,并认为人们可用这种手段来智胜大自然。”[4]这就是说,在伽利略之前的多数西方学者看来,物理学是关于自然的知识系统,而力学是借助特殊人类智慧使“自然界”发生有悖常理现象的技巧。这就是力学(mechanics) 一词蕴含“技巧”之意的根本原因所在。
人称伽利略(Galileo Galilei) 为西方近代科学之父。除了因其在物理学、天文学等领域做出的那些具体的科学贡献外,伽利略还是彻底纠正西方人对于力学的错误认识的人:“在1593 年,青年时期的伽利略写成的一部著作中强调说,当人们应用机器时,只是借助自然来行事;人不能欺骗自然,不能战胜自然、不能超越自然。例如用杠杆获得了轻便,这正是消耗了路程、时间和速度的结果。伽利略说:‘这将在所有已经思考出来的工具中和将被思考出来的工具中发生。’这就是说,仪器和机械的应用不是反自然的东西,测量仪器也是符合自然的东西……[4]”如同后来人们逐渐认识到制造永动机的梦想永远无法实现一样。伽利略经过研究,已经明确指出:依靠“力学”实现“投机取巧”的愿望是无法实现的。与热现象、光现象等等相并列,力学研究的现象,只是物理学研究的诸多现象中的一小部分。
伽利略的这一思想,实现了力学与物理学的统一,而“仪器和机械的应用不是反自然的东西,测量仪器也符合自然的东西”这一推论性理念,也是当时的伽利略所迫切需要的,惟有这一认识得以牢固树立,人们才会相信借助他的望远镜观察到的天文现象是真实可靠的。遗憾的是在很多著述里、在很多学者的意识中,都忽视了“力学”在早期具有与后来截然不同含义的事实。从而错误地认为力学作为物理学最基本的分支,早已有之并逐渐发展成熟,在其演变过程中,变化的只是具体的力学知识,而“力学”一词本身的含义并未发生变迁。此认识违背史实。
二、“形而上学”一词含义的变迁
17 世纪诞生了牛顿力学,18 世纪牛顿力学的思想普遍融入西方文化并成为其核心内容,基于这一理论诞生了哲学范畴的决定论。决定论认为一切现象皆源自物质的位置变化,现在与未来皆由先前(初始位置、初始速度与受力情况) 所决定,即明确知道现在,既可反推过去,又可预言未来。正如恩格斯所说,力学大厦的缔造者牛顿曾发出这样的警告:“物理学,当心形而上学呵!”[5]牛顿所说的形而上学,可以称为古典形而上学。中国古语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由今天“器物”两字并列的构词所指不难理解,“器”属于现在人所言的物质范畴,而“道”是凌驾于“器”之上的非物质的存在。“当心形而上学”的警示要揭示的思想方法是:在牛顿看来,物理现象是认识的源头,而实验则是认识现象与事物的最可靠方法。“当心形而上学”,就是告诫研究者不要偏离这一研究纲领:“探求事物属性的准确方法是从实验中把它们推导出来。……我之所以相信我所提出的理论是对的,不是由于它来自这样一种推论——因为它不能别样而只能这样,也就是说,不是仅仅由于驳倒了与它相反的假设,而是因为它是从得出肯定而直接的结论的一些实验中推导出来的。”[6]与牛顿奠定的近现代物理学基本纲领相反,中国古代文化总体说来更加崇尚“形而上学”。中国古人认为,道是高于器(由气构成)的存在,所以他们在思想意识上恰恰是重道不重器的。
牛顿彻底完善的肇始于伽利略的力学新体系,相比于充满古典形而上学理念的亚里士多德时期以及中世纪的物理学,都是一个巨大的革命性进步。在今天的航天与工程技术等诸多领域,牛顿力学仍在发挥积极作用。然而正如恩格斯所说,基于牛顿力学这一革命性的科学理论,却无法避免地推演出一个新的形而上学的世界,即机械唯物主义世界:基于牛顿力学,不管自然界本身是怎样产生的,只要它一旦存在,那么在它存在的时候它始终就是这样。
行星及其卫星,一旦由于神秘的‘第一推动’而运动起来,它们便依照预定的椭圆轨道继续不断地旋转下去,或者无论如何也旋转到一切事物的末日。恒星永远固定不动地停留在自己的位置上,凭借‘万有引力’而相互保持这种位置。地球亘古以来或者从它被创造的那天起(不管哪一种情况) 就毫无改变地保持原来的样子。
现在的‘五大洲’始终存在着,它们始终有同样的山岭、河谷和河流,同样的气候,同样的植物区系和动物区系,而这些植物区系和动物区系只有经过人手才发生变化和移植。植物和动物的种,一旦形成便永远确定下来,相同的东西总是产生相同的东西……开始时那样革命的自然科学,突然站在一个彻头彻尾保守的自然界面前,在这个自然界中,今天的一切都和一开始的时候一样,而且直到世界末日或万古永世,一切都将和一开始的时候一样[5]。
基于对牛顿力学推论出的新的自然观(而不是牛顿力学本身) 本质特征的深刻认识,恩格斯明确断言它非但不是进步的,而是巨大的倒退:“十八世纪上半叶的自然科学在知识上,甚至在材料的整理上是这样地高于希腊时代,它在观念地掌握这些材料方面,在一般的自然观上却是这样地低于希腊时代。在希腊哲学家看来,世界在本质上是某种从浑沌中产生出来的东西,是某种发展起来的东西、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5]。
20 世纪著名理论物理学家马克斯·玻恩(Max Born) 曾将牛顿呈现的物理世界描写为“僵冻的、死的世界”,并指出:“歌德就讨厌过这种不动的世界。他认为牛顿乃是对自然界持有敌意看法的典型人物[7]”。玻恩的学生,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海森伯(W.Heisenberg) 把牛顿理论对世界的描述与其前人的做法的不同做了三点概括:“在三个标志性特征方面,牛顿理论和旧的描述有所不同,这三个特征是:它以定量的陈述代替了定性的陈述;它把不同类型的现象追溯到同一个起源;它放弃了去提‘这是为什么’的问题。正是由于这种放弃,所以例如浪漫时期的科学家就对牛顿的学说表示不满;而像洛伦兹·奥铿那样的学者就企图用一种‘比较有生气的’理论来代替它。奥铿曾经写道:‘你们不应该用冲冲撞撞和敲敲打打,而应该用生气来创造世界。如果行星是死的,那么它就不能为太阳所吸引[8]。’”
歌德与奥铿等持老派思想学者的反对,间接反映了牛顿理论的创新与革命性;而从玻恩与海森伯的言辞不难看出19 世纪的恩格斯与20 世纪的玻恩及海森伯对牛顿力学所隐含的自然观的认识与评价是高度一致的。基于牛顿力学而产生的新的自然观,所揭示的即今天哲学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概念,在它与机械唯物主义之间,是可以划等号的。
那么在科学性上高于古希腊以及中世纪力学的牛顿力学,为什么会导致这种新而落后的形而上学自然观呢?恩格斯认为这是由牛顿力学本身的局限性,以及将牛顿力学视为整个自然科学理论基础的观念所决定的必然。
从牛顿力学本身的局限性来看,“它用位置变化来说明一切变化,用量的差异来说明一切质的差异,而且忽视了质和量的关系是相互的,忽视了如同量可以转变为质的那样,质也可以转变为量,忽视了所发生的恰好是相互作用。如果质的一切差异和变化都可以归结为量的差异和变化,归结为机械的位置变化,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得出这个命题:所有的物质都是由同一的最小的粒子所组成,而物质的化学元素的一切质的差异都是由量的差异,即由这些最小的粒子结合成原子时数量上和在空间上排列的差异所引起的[5]。”这无疑十分接近古希腊的原子论。
20 世纪物理学的发展表明,物质世界并不存在构成一切的同一的最小粒子,目前已经发现数百个种类的基本粒子,以大的类别分,也有夸克、轻子和传播子三大类;而机械运动也远远无法囊括和完备解释化学运动、生物运动、社会运动、原子以及原子核内部的量子现象等所蕴含的特殊运动方式。
在恩格斯的著作中已经出现与此近似的认识:“不论就广义或狭义而论,力学上只知道量,它所计算的是速度和质量,最多再加上个体积。……但是,在物理学中,尤其是在化学中,不仅有量变所引起连续的质变,即量到质的转化,而且要考察怎样为量变所制约还没有证实的那许许多多的质变。……一切运动都包含着机械运动……但是这些机械运动并没有穷尽所有的运动。运动不仅仅是位置变化,在高于力学的领域中它也是质的变化[5]。”在哲学意义上,恩格斯的思想完成了对牛顿力学机械自然观的突破。
如果一部科普作品要触及西方文化中的诸如“力学”、“物理学”或“形而上学”等相关概念,以上所述是首先必须清晰认识的内容。否则在古典历史文献中看到“力学”与“物理学”的字样即以今天的语义去理解和诠释,那么势必导致彻底的“辉格”化,演一出别具风味的科学概念之“张冠李戴”,也难以避免会出现“关公战秦琼”的景象。类似的情形不胜枚举,中国古籍中的“物理”、“天文”、“地理”等词语,与今天自然科学体系里的同名概念在所指内容上都存在较大的不同。
三、早期道家文化中“机械”观
中国古代在机械与工具制造方面有很多重要的发明,中国古人对待工具(以力学机械为主) 使用的思想态度,今天看来是较为有趣的。一个现象是在中国古人看来“哲人贤者固为智能之士,能工巧匠也是得道之人”[9],这可以称为一种典型的“工具主义”;另一方面却有人明确而坚决地反对“工具主义”。泛道家(包括道教) 的机械与工具观及其转变,尤其值得辨析和玩味。
道家最著名的著作《道德经》鲜明而充分地表达了早期道家对于机械或工具使用的原则性立场与态度:“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10]显而易见,在老子向往的理想社会里,老百姓要放弃使用可以省力十倍、百倍的工具或机械设备,有车有船不用,放弃有好的铠甲和兵器,最后让老百姓回到结绳记事的生产力最低下的社会状态。
道家的另外一部经典著作《庄子》中有一则故事[11],再次形象而具体地展示了早期道家对待“机械”(泛指工具) 的鲜明态度: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滑滑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为圃者仰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泆汤,其名为槔。”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
子贡是儒家孔门十哲之一,在这则故事中是作为儒家代表而现身。而这“为圃者”即农人,则是位“得道高人”,他宁肯费力受累而不用省力轻便的农具,而他这样做的理由则是用机械则必有机心,有机心则将导致“道之不载”。胡化凯先生对于《庄子》中的这则故事,以及道家的思想观念有深刻的剖析。他指出:“‘机心’即机巧、机变之心,或投机取巧心理。浇田老人的话,代表了道家对于机械技术的态度。机械可以使人‘用力甚寡而见功多’但道家反对运用它,因为他们认为,‘功利机巧必忘夫人之心’,‘有机事必有机心’,使用机械技术会使人产生投机取巧的心理[12]。”这则故事把早期道家对这一话题的基本主张表达得淋漓尽致。
《庄子》中的另外一段话,更深入地诠释了弃用工具的理由:“夫弓弩毕弋机变之知多,则鸟乱于上矣。钩饵罔罟罾笱之知多,则鱼乱于水矣。削格罗落罝罘之知多,则兽乱于泽矣[11]。”早期道家学派认为,放任与过度使用捕鸟、捕鱼、捉兽的工具,将直接导致鸟患、鱼患与兽患。而使用工具所导致天下大乱的深层根源,则在于知识的应用与智慧的运用:“故天下每每大乱,罪在于好智(知)[11]。”庄子的这一主张,与其前辈老子的思想可以说是一脉相承。老子认为,只有“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才能“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10]。
总之,在早期道家看来,机心即取巧之心,有机心才有机械;使用机械就是投机取巧而使人心失道不纯。使用力学机械属于投机取巧,早期道家人物的这一认识,与古希腊及中世纪时期,西方人认为力学(即机械学) 是欺骗大自然的技巧的观念,不无相通之处。
四、葛洪、谭峭等中期道家文化中知识与机械观念的异化
早期道家所追求的基本思想是,通过弃智、弃义、弃利并无为,祛除机巧心理,从而恢复并保持少私寡欲如孩提般的纯正赤子之心。
弃智的重要方式就是拒绝制造和使用力学机械或其他工具。而其后追求长寿以至于成仙逐渐地成为了道家理论与实践上的主要追求目标。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即是炼制丹药(外丹)。一旦有了明确的追求目标,而且要实现这一目标需借助特殊的手段并依赖器具(丹炉等) 和药材等身外之物,那么“无为”、“弃智”都必然成为无法再遵循的空话。
正因为这一缘故,葛洪立于道派,继承老庄的基本主张,却有这样的心声:“道成之后,略无所为也;未成之间,无不为也。采掘草木之药,劬劳山泽之中;煎饵治作,皆用筋力;登危涉险,夙夜不怠。非有至志,不能久也。及欲金丹成而升天,然其大药物皆用钱直,不可卒办。当复由于耕、牧、商、贩以索资,累年积勤,然后课合[13]。”要实现得道与长寿的目标,必须绞尽脑汁去筹集资金、持之以恒劳神费力采药炼丹,真是“无不为也”(此无不为说的是人,与老子所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丝毫无关,不能混淆);既然“无不为”,就无法避免用“机械”、有“机心”。这不是早期道家思想走向死亡,而可以看做道门思想的一种自然发展。
时至五代,道家代表谭峭等人明确表示,不再“弃智(知)”、不再摒弃机械,相反他们坚信,只要掌握天地的核心知识(道纲),则可以改变命数,甚至改天换地,可谓无所不能:“转万斛之舟者,由一寻之木;发千钧之弩者,由一寸之机。一目可以观大天,一人可以君兆民。太虚茫茫而有涯,太上浩浩而有象。得天地之纲,知阴阳之房,见精神之藏,则数可以夺,命可以活,天地可以反复。”[14]由此可见,谭峭的思想把修道要“有为”,掌握关键知识和技能即可“人定胜天”的观念推论到了极致。
道家著作包含很多与中国古代生物、化学、物理等等有关的知识与观念,因此是研究中国古代科技文化不能忽视的重要文献。在介绍道家及其思想时,如果对这些经典著述缺乏较为全面的认识,局限在某个特定时期即做普遍结论,难免片面与偏颇,这种做法不符合辩证史观。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今天很多人仍然对待历史、对待古人思想、对待教派宗旨采取粗暴、简单而浅显的态度,而不是做深入细致的辨析。对待道家的态度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几乎无一例外,将道家复杂的思想体系简单地等同于无为与顺应自然。笔者曾指出道家强调“道法自然”中的“自然”二字与大自然中的“自然”二字,所指有根本区别;道法自然中的“自然”,“指的是道本身或道自己的样子[15]”。
五、结语
民国时期很多学者二三十岁留洋归来,即开宗立派、著书立说,成为学界各领域之巨擘。当时曾有清醒者指出,如此作为、如此急功近利,难免学术浮华而名不符实。逝者如斯,百年之数又过七十,今天的中国学术界诸多领域(尤其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鲜有超乎民国那些颇具大家气象之上者,但似乎更加浮躁、更加急功近利。而一入浮躁之境即无法为学精深,就难以将学术做扎实、细致,于是很多常识性错误,就往往难以避免。
了解科学知识发展的源流,深刻理解并能辨析一些重要科学名词或概念在不同时代的异同,应成为科普作者一项基本功课。彭桓武院士曾说:“我很害怕搞科普,因为科普搞不好,一些人就会抓住一些名词胡闹[16]。”彭院士这话的侧重点与文章不同,但是不要轻视科普创作,不要以为科普易为,这一认识是永远不错的。正因为科普作品面向绝大多数读者,就尤其更需要仔细推敲、斟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