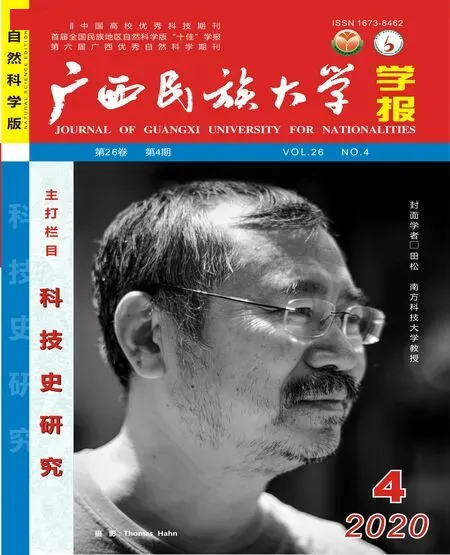刘慎谔历史植物地理学思想的形成及其特征*
伍小东,姚 远
(西北大学 科学史高等研究院,陕西 西安 710127)
刘慎谔(1897-1975),著名的植物分类学家和植物地理学家,中国近代植物学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与胡先骕同享“南胡北刘”的崇高地位.他留学法国有十年之久,被誉为“第一个研究法国植被的中国人”.[1]901929年,刘慎谔回国后创办国立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并主持工作长达20年.1934年,他发表的《中国北部及西部植物地理概论》以独特的视角填补了中国植物地理学研究的空白.[2]在抗战全面爆发之际,他率领植物学研究所西迁武功与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组成立中国西北植物调查所.随后又前往昆明筹备建所并积极开展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他再次奔赴植物学研究的处女地——东北开展植物学研究.直至20世纪60年代,他结合自身丰富的科考经历和中国植被的分布情况、发展历史,对原有的相关理论进行了发展和创新,为中国创建了两门闪烁着辩证法光辉的分支学科——动态地植物学和历史植物地理学,从而成为国内研究植被演替、植物地理、植物区系成分和植物区划等方面的重要理论基础.刘慎谔去世后,以他的研究理论为支撑的“森林采伐更新理论的研究”和“西北沙漠地区修筑铁路设计施工”两项成果,获得了1978年的国家重大科学技术成果奖,这是国家和社会对其一生工作的最大认可.
目前,国内对刘慎谔的研究十分有限,仅有的十余篇文章中,多数是在其逝世十周年和诞辰百周年时的一些纪念性文章,集中于生平事迹的概述和梳理.另有两篇关于学术思想的研究文章,[3-4]也是对其学术贡献的总结,缺乏宏观分析和探讨.文章从刘慎谔植物地理学形成的历史经过谈起,以辩证法的视角分析其中所蕴含的关于植被的永恒发展观、植被与环境的辩证统一的科学思想.以期更为深入、全面地理解这位科学家的科学思想及其学术贡献.
1 刘慎谔历史植物地理学思想的形成
1.1 刘慎谔历史植物地理学思想的基础
刘慎谔出生于山东省牟平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幼年曾就读于私塾、烟台模范小学和济南第一中学.1918年考入保定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学习,1920年起便开始了长达10年的法国留学生活.他先后在郎西大学农学院(1920-1923)、蒙彼利埃农业专科学校(1923-1924)、克来孟大学理学院(1924-1925)、里昂大学理学院(1925-1926)和巴黎大学理学院(1926-1929)学习.他留法学习期间的一个重要工作是结合其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内容,对高斯山地区的植被分布情况进行考察,其间采集植物标本25000余号,解决了地植物学家布瑙-布朗喀(BraunBlanguet)教授提出的地中海植被是怎样向中央山区过渡、高斯山有哪些植物群落、这些植物群落有哪些区系特征和生态特征等问题.1929年,他完成了博士论文《法国高斯山植物地理的研究》,并获得法国国授理学博士学位.刘慎谔对法国植物的熟悉情况曾被导师勒诺瓦尔赞誉到:“法国学生也没有像他那样清楚地掌握法国的高低等植物”.[5]30在研究之余,刘慎谔还积极关注和推动中国生物学事业的发展,他先后参加了“新中国农会”“中国生物科学学会”等组织,与林榕、刘厚等人共同编辑《中国植物文献汇编》,广泛收集整理有关中国植物研究的著作、论文和杂志,推动中国植物学的发展.
关于刘慎谔学术思想形成的起源,首先要从其留学期间完成的博士论文——《法国高斯山植物地理的研究》谈起.这是刘慎谔植物地理学学术思想形成的奠基之作.全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地质、气候、地文、植被及其经济意义四个方面介绍了高斯山区的基本情况;第二部分共有四章介绍了高斯山区的植物群落分布情况;第三部分指出高斯山地区的植物区系有六种成分,发展情况也各不相同,其中地中海成分是该地区植被的基础,地中海—低山成分与地中海成分混生,中欧成分为森林群丛的组成成分且分布于阴坡,大西洋成分仅局限于矽(化学元素“硅”的旧称)质土上,北方成分是极少数的近代引进的种,最后一种萨马第(东欧)成分主要分布于白山岩风化砂土上.总体来看,高斯山既是一个植物种类向外扩散的中心,又是一个植物种类发生的中心.刘慎谔在法国期间跟随导师勒诺瓦尔的学习经历,正是其思想的学理来源,他采用的方法基本上是法国地植物学家布瑙-布朗喀和巴维亚尔(J.Pavillard)在其所著的《植物社会学词汇》中提出的方法,同时还吸取了美国考尔斯(Cowles)和克莱门茨(Clements)动态植物地理的概念.植物群落成分分析和植被地理的区划是其学术研究中的核心概念,正是以此为出发点,刘慎谔开始了长达50年的植物地理学研究工作.
1.2 刘慎谔历史植物地理学思想的形成
经历过晚清民初时期社会动荡的科学家,“科学救国”始终是他们心中难以割舍的情节和动力.1929年,刘慎谔怀着发展中国人自己的植物学科的雄心壮志,带着在法国采集的植物标本和书籍资料,以及十年间形成的先进科学理念回到了祖国,并执掌国立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面对国内植物学研究“一穷二白”的现实,特别是在缺乏中国本土的研究材料的情况下,在他到所的第二天就和同事外出采集植物标本.1931年,他参加了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察范围涉及内蒙古、新疆、甘肃以及青藏高原,后经印度返回上海,采集植物2000 余号.翌年,他再入天山、昆仑、喜马拉雅山脉,采得2500余号标本,对中国华北、西北地区的植物区系有了初步认识.1936年,国立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西迁合组成立中国西北植物调查所,刘慎谔随之西迁来到陕西.随后他遍历秦岭山脉、秦巴盆地、关中平原等地,采集了大量的西北植物标本.1941年,他再次赴昆明开展西南地区的植物调查.新中国成立后,1950 年他又应邀前往东北,开展了长白山、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和内蒙古大草原等地的标本采集和调查研究工作.这种自欧洲西部,到东北亚、中亚、西亚、南亚的大范围宏观考察,目睹了植物区系丰富多彩的多样性变化,是其植物地理学思想产生的直观基础.刘慎谔在这种大区域植物学考察基础上相继完成的《中国北部及西部植物地理概论》《中国南部及西南部植物地理概要》《陕西植物分布概要》《太白山森林植物之分带》《中国西北之植物地理》《云南植物地理》《关于中国植被区划的若干原则问题》等论文是他这一思想不断成熟和完善的表现.在东北完成的《动态地植物学——基本理论的探讨及其应用》(1963年)和《历史植物地理学》(1964年)便是这一思想的系统总结和阐述,从而形成了结合中国实际的完整的植物地理学思想.由此在中国开创了这两门新兴的植物学分支学科.
总体而言,在法国区域植物分布考察的基础上,回国后又进行大范围考察是刘慎谔植物地理学思想形成的重要过程.虽然考察地点不同,但其野外标本采集、分类和研究方法都几乎相同,即:从地质、气候、地文、植被及其经济意义五个宏观角度切入,再对植物群落(比如钙质土上的根茎短柄草、冲击土上的短柄草、矽质土上的曲芒发草)做微观考察,最后得到植物区系发生演变的规律.直到晚年,刘慎谔仍把这种方法运用于对中国历史植物区系发展演化规律的研究,并以东北、华北、西北、西南的分区考察为支撑,完成了其动态地植物学和历史植物地理学的重要研究成果,并展现了他一系列重要的科学思想.这清晰地反映了其法国植物学流派的学源,以及根据中国实际将这种思想中国化的发展历程.
2 植物区系绝非一成不变的动态演变思想
植物区系的成分分析和植物区系的划分是刘慎谔学术思想的重要基础,也是其科学思想的核心概念.不论是在《动态地植物学》中强调一个地区的植被成分在不断地发生动态的演替,还是在《历史植物地理学》中从一个大尺度的宏观历史角度,来强调整个地球表面的植被区系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他始终要阐述的一个核心就是植被的成分和区系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不断地发生运动、变化和演替.因而,必须用动态的观点来认识和研究植被.
关于植被的动态变化,刘慎谔先从单个的植物种的演变开始研究.刘慎谔回国后面对中国植物学研究刚刚起步,植物分类学被外国人所垄断的实际情况,从植物地理学转而从事植物分类学的研究,开展了真菌、地衣、苔藓、蕨类及种子植物的分类学研究.他结合大量的研究基础和分类工作中遇到的变种等实际问题,创造性地将发生学的观点引入植物分类研究中.他主张在植物分类研究中一定要考虑种的分布,从哪里来的? 什么时候来的? 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做好分类工作.对此,他明确指出,植物种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且长期在地理环境与大气候等自然条件不断变化的影响下,在移动之中动态地、系统地发生和演化所形成的.[6]用发生分类学的思想来观察和研究植物分类过程中的形态变异规律、等级划分及系统位置,是刘慎谔不同于同时代其他植物学家分类思想的重要方面,也是其植物地理学研究的思想基础.
单个植物的种是在运动中产生、发展、衰亡,那么,由不同植物组成的植物群落也处在不断的演替过程中.[4]35刘慎谔强调必须从动态的观点来认识植被,在分析现在植被的基础上,还要了解过去植被的特点和将来的发展方向,才能为植物区系的划分提供翔实的依据.[7]因而,在植物区系的研究过程中,他在区分单元顶级和多元顶级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地带性顶级和非地带性顶级的概念,以及前顶级、后顶级、偏途顶级和转换顶级,更是对以克列门茨(Clements)和坦斯黎(Tansley)为代表的动态学派的延伸和创新.正是基于这种植物群落不是静止的,而是伴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思想,刘慎谔开始了对自然植被的改造和人工植被的建立两方面的研究.这也最终发展成东北红松林的伐育和沙漠治理两方面的实际工作的指导思想,并为新中国的建设产生了重大的经济效益.
同样,这种植被动态变化的思想在植物区系的划分中也有所体现,在《历史植物地理学》中,刘慎谔以地质学与植物学交叉融汇的大尺度历史演变观论述了世界植物区系形成的历史原因、植物区系起源、植物区系成分分析及其分布.随后,又从极地摆动、大陆漂移和海陆陆桥等角度详细分析了中国植物区系的形成和发展历史,将地形因子、气候因子和人为因子等纳入植物区系的划分和成分的分析中,阐明了影响中国植被历史演变过程中的重要因素,以及各种因素的影响过程和改变方式.[8]229他强调,历史植物地理学的任务并非静止地描述植物的分布,而是要将他作为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来描述.[9]地球植被和中国植被目前所展现出来的形态,是在地形、气候和人为等因素的影响下不断形成的,而且这种影响也将持续下去.因而植被的成分和区系的划分也将持续改变,只是这种动态的改变很难在较短的时间内被感知.在使用动态的观点研究历史植物地理过程中,刘慎谔进一步强调,同时还要结合静态的思想,否则就只有方向而无法确定具体的内容.[8]231这种动态和静态相结合的科学研究思想成为刘慎谔留给后人研究植物学的珍贵的思想资源.他的学生和助手王云章、王战等人正是在此思想的长期熏陶下,成长为中国著名的菌类学家和林学家.
从单个植物种的发生,到一个地区的植物群落的演替,进而到一个国家甚至地球表面植被区系的划分,刘慎谔在对这些理论的阐述中,始终围绕着动态变化的核心思想,从而构成了其历史植物地理学的基本理念.在强调从动态的和历史的观点来认识和研究自然植被时,刘慎谔更加着眼于如何通过这种动态变化来建立人工植被,进而解决中国社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为解决生产问题、制定生产决策和规划提出科学的理论依据,展现出这一代科学家将论文写在中华大地上的豪迈与坚守,而这一思想也是他后期指导防沙治沙和森林伐育工作的重要理论基础.
3 植物区系是地球历史集中表现的辩证统一思想
如果说植被的动态演变是刘慎谔学术思想的基础,那么,他提出的植被与环境的辩证统一就是其学术思想的集中体现.地球表面的植被状态由其生存环境塑造,反之,对当前植被和过去植被状态的综合分析就能推断出环境的变化过程,进而展现地球历史的发展概貌.这种辩证思维是刘慎谔从植物学研究中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首先,这种植被与环境辩证统一的思想体现在刘慎谔植被顶级概念的阐述中.“顶级”一词最早由瑞士学者盖姆斯(H.Gams)于1918年提出,但是刘慎谔根据中国植被分布和发展的实际对这一概念做了延伸和创新,提出了地带性顶极和非地带性顶级,使其成为不同于国外地植物学研究的标志性特点.所谓顶级,是指在一个地区内,由于受大气候条件的控制,植被演替的方向或早或晚终将向着相同的终点发展.刘慎谔把这种受大气候控制的顶级称为地带性顶级.比如,由大气候决定的地球表面不同纬度的国家和地区,以及中国东北、华北及长江以南地区,就分别生长着不同的植被.因而,通过对前顶极、后顶极和现在植被关系的分析就“可以为大气候的变迁提供历史资料”.[10]145具体而言,古气候和古植被可以成为判定现在气候和未来气候的依据,分析现在的植被也可以了解过去气候的发展特点,并且也可据此了解未来的发展方向.这是刘慎谔基于地带性顶级对二者关系的最初表述.
以大气候为基础的地带性顶级只是从地理分布和植被区划上划分植被的大类型时成立,但是当研究一个具体地区的植被类型时,则要考虑由局部环境条件所形成的非地带性顶级.植物区系的形成是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之前存在过的历史条件.[11]气候因素、地形因素的变迁以及人为因素的变动都会影响到植物种类在形态上的变化,进而影响植物区系的划分和植物地理的分布.因而,刘慎谔指出“现存植物区系的组成是过去各种历史环境条件逐渐变化乃至反复变化集中反映的结果”.[8]232基于此,刘慎谔指出“地球历史是历史植物地理学的必要条件,反过来,历史植物地理学又是地球历史的集中表现”.[8]231这就是说,地球表面植被的形成和发展是气候、地形、人为等多种历史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同时期植被状态的形成几乎涉及了整个古代地球历史的全部资料.那么,通过研究和分析不同时期植被的演变规律就可以展现出地球历史的发展过程,通过这种反向推断给重建地球的历史做出重要贡献.因此,历史植物地理学也被苏联著名植物学家E.B.吴鲁夫形象地描述为“一把了解地球历史的钥匙”.[12]1这种植被与环境的辩证统一思想,是刘慎谔对学生和同事一直强调的一个观点,也是指导自己从事科学研究和实际生产工作的基本理念.[13]
当把这种辩证关系应用到具体的实际工作时,刘慎谔进一步强调,在分析植被的影响因素时还要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和实际情况来寻找主导因子和次要因子.[14]181主导因子是造成目前植被分布类型的主要影响因素,同时,还要仔细辨认影响植被分布的次要因子.此外,还要注意在不同的情况下,主导因子和次要因子也会根据环境的变化而转变,光线、水分、土壤、地形和气候等因素会同时作用于植被,但既可以是主导因子,也可以是次要因子.他以东北小兴安岭带岭地区凉水沟的植被变化情况来说明这一点,此地有一片落叶松林,原来长得整齐有序,但随后发现落叶松林边缘的红松、红皮云杉、臭冷杉等不断向落叶松林入侵.落叶松原本是湿生系列,而红松、红皮云杉等是旱生系列,为何会发生这种入侵的情形呢? 刘慎谔认为是湿生系列的落叶松地下水位的下降而引起的,原本地下水位是主要因子,而土壤的水分变化相对持平后,主导因子就由水分转变成了光线,因而出现了边缘高大的红松、红皮云杉等向低矮的落叶松入侵的趋势.[14]182由于这种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转化,在分析和讨论植被的变化历史时,一定要仔细辨认,一旦影响因素找错了,那么基于此而构建的地表环境的发展变化规律也将无从谈起.这是刘慎谔对这一关系的一次详细注解.
总之,刘慎谔提出地带性顶级和非地带性顶级概念,有效地解决了植物学家长期以来关于单元顶级和多元顶级之间的争论,进而以整体和局部、主导因子和次要因子等概念入手,在国内创新性的发展了植物地理学的理论架构.在他的理论分析中所蕴藏的这种辩证统一观,更能引发人们关于植物与环境之间的思考,这也为植物生态学的发展提供了一定借鉴.
4 刘慎谔历史植物地理学思想的现实意义
刘慎谔学术思想的形成不是局限在书本和实验室中,而是在接受欧洲先进的生物学学术训练后,在大范围的实地考察基础上逐渐凝练和清晰起来,是西方近代生物学在中国的拓展和创新.中国知名的植物分类学家王战曾明确指出:“《动态地植物学》和《历史植物地理学》两部著作的显著特点就是能够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理论和指导实践,具体表现在:一是在原有理论和学说的基础上有新的发展,提出了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独创见解和观点;二是理论结合实际,他所解释和说明的问题,不是在教科书上多年沿用的国外经典例子,而是能够解决中国实实在在的现象和存在的问题.”[15]28因而,理论源于实践,进而用于指导生产建设,使其学术思想具有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新中国成立前,迫于植物学研究刚刚起步的现实和社会环境的不断滋扰,刘慎谔将更多的精力用于植物学的考察和研究中.新中国成立后,在一个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氛围中,新中国的建设也需要多方面的发展.刘慎谔秉持“文章不但要写在纸面上,而且要写在地面上”[3]43的理念,将其研究成果应用到解决森林采伐和治沙等实际问题中去,为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提供了科学依据.在森林植被的保护方面,他坚决反对苏联专家提出的对东北地区红松林的大面积皆伐,而极力主张采育结合的采伐方式,在他的一再坚持下最终得到了当时政府的肯定并得以推广.1974年,时任伊春林业管理局副局长的宫殿臣夸赞道:“刘慎谔老先生最关心林业生产,能理论联系实际,是一位有真才实学的受林区职工尊敬和爱戴的老一辈科学家”.[10]141在治沙方面,刘慎谔主张草、灌、乔相结合的人工植被类型的治沙措施,为包兰铁路腾格里沙漠路段的修建做出了重要贡献,被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的李鸣冈称赞为“我国治沙研究工作的创始人”.[16]1他这两项成果在新中国建设过程中具有突出贡献,因此获得国家重大科学技术奖,也进一步显示出刘慎谔学术思想的重大现实指导意义.
如果从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角度来审视刘慎谔的研究和实践工作,则可以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展现其学术思想的现实意义.这一概念虽然在刘慎谔所处的时代没有使用和推广,但是其所开展的一系列研究和生产实践却具有重要的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意义.无论是最早在辽宁西部创建的章古台治沙定位试验站,还是采用伐育兼顾的东北红松林择伐,或是包兰铁路修建过程中的人工植被固沙,都包含着强烈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意味.刘慎谔强调森林的砍伐要遵循林木的生态特点和天然更新规律,治沙中人工植被的建立也要符合自然植被的发展规律,这些观念的提出和应用,对于当代的生态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5 结语
刘慎谔这种从亚洲到欧洲,从中国华北到西北、从西南到东北的大尺度、大范围的宏观考察和微观思考,奠定了植物地理学方面丰富的研究基础,形成和建立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历史植物地理学理论,实现了国外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本土化发展之路.同时,在这一理论中也蕴藏着植被动态演变以及植被与环境相统一的辩证思想,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挖掘和阐述的科学思想,也是刘慎谔留给当代人宝贵的精神财富.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又将这些重要理论发现运用到中国东北森林的伐育和西北包兰铁路的治沙过程中,从而实现了科学源于实践,再用于指导实践的正确途径.其宏观考察与微观观察并行、野外工作与实验室工作相结合、中西融汇、善于多学科交汇、重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特别是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的作风,无疑给我们以重要启迪,也是我们今天实现科教兴国、民族复兴的重要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