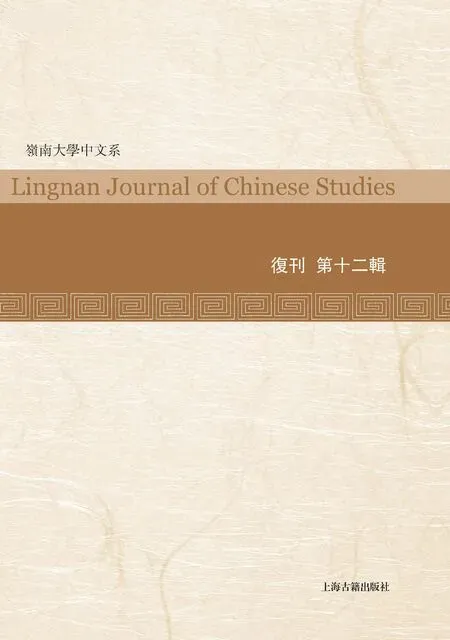獨抒性情與文本互涉的辯證
——袁宏道的詩論與詩歌
蔡振念
一、叙論:獨創還是摹擬
文學作品的載體是語言與文字,而語文是文化的底藴和最大公約數,因此語文是一種人人能懂的符號。近代結構主義研究語言文字,把語文作為一種符號,區分為符徵(signifier)與符旨(signified)①首先提出符徵與符旨(或譯意符與意指)是語言學家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於1916年出版的《通用語言學》(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又譯《普通語言學教程》)首先提出的,該書是由索緒爾的學生們將他在日内瓦大學上課的筆記編輯成書,被視為引領歐美語言學蓬勃發展的關鍵之作。語言學中,符徵和符旨的關係通常是約定俗成的,也就是没有任何實質關聯的——純粹是達成了一群人的共識。參見Ferdinand de Saussure,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Roy Norris,London:Bloombury,1983,rpt.2013.,文學作為文化的一環,其在當世的傳播或者後世的流傳勢必要依賴口語或文字,語文作為一種符徵,是傳播者的工具,藉此傳達當事者心中之符旨。近代傳播理論則以叙述者(narrator)和受述者(narratee)來指稱傳播兩端的當事者,而語文是其中之媒介。因為傳播的需要,語文有其特性,即是其符徵必需是約定俗成的,纔能為接受者所理解。因此語文有其慣性,語文慣性最基本的表現應該是文法,説話或書寫而無文法,勢必不為他人所理解。但受述者或讀者並非被動的接受文字符號,而是以自己先存既有的知識結構(forestructure),來看出叙述者或作者所未見的意義②先存結構是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1889—1976)的概念,見Robert Maglioa,Phenomenology and Literature:An Introduction,West Lafaette,Indiana:Predue UP,1977,pp.174-191.,因此閲讀前人文本,既是對前人文本的理解闡釋,也是一種創造新義行為。作者以自己的文字符號來編成符碼(encode),讀者則以自己的知識脉絡(context)來解讀符碼(decode),也即詮釋文本(text)。在這種閲讀活動中,過去的符碼被後來者用現下的符碼知識加以詮譯,而現下的符碼因我們對過去符碼的知識而得以深化、衍義、擴大,因而形成了作品互相指涉的交感③Edward Stankiewicz,“Structural Poetics and Linguistics,”in Current Trends in Linguistics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Cambridge,Mass:Harvard UP,1980,pp.14780;Jonathan Culler,The Pursuit of Signs:Semiotics,Literature,Deconstruction,Ithaca:Cornell UP,1981,pp.105-119.。
但文學作品是作家個性、心靈與情感的表現,因此表現作品的文字自然講求獨特性,纔能突顯作家之一空依傍,露才呈性,其次,文學中各種文類也有其傳統,作家不可能自外於文學傳統,作家作品必須放在文學傳統中纔能評估其作品的價值與個人才性④T.S.Eliot,“Tradition and Individual Talent,”in Selected Essays:19171932,New York:Harcourt Brace,1932,pp.311,中譯參見艾略特(T.S.Eliot,1888—1965)著,卞之琳、李賦寧譯《傳統與個人才能:艾略特文集論文》(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年版)書中《傳統與個人才能》一文,該文中譯又見杜國清譯《艾略特文學評論選集》,臺北:田園出版社1969年版,頁1—20。。這就為作家帶來一個兩難處境(dilemma),一方面作家要獨抒性情,一方面又要兼顧繼承傳統,如何可能?我們從文學史的角度來看,文學的發展無非是傳承與新變的辯證①有關文學的傳承與新變可參看張高評《宋詩之傳承與開拓》(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版)與《宋詩之新變與代雄》(臺北:洪業文化公司1995年版)二書。。因此作家常在傳統與獨創之間依違折衝,有時甚至表現出理想與現實的妥協,或者理論主張與實際創作的悖反。這種現象史不絶書,歷代文人多有,但明代公安派詩人袁宏道(1568—1610,穆宗隆慶元年至神宗萬曆三十八年)可能是這種現象中最值的探討的詩人之一,他生在明代前後七子的擬古與復古的文學風氣之後,不滿於前七子李夢陽(1473—1530)、何景明(1483—1521)等與後七子李攀龍(1514—1570)、王世貞(1526—1590)等“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之詩文理論,於是提出“獨抒性情”之説。前後七子復古的詩文理論主要是在明初成祖至英宗間館閣重臣楊士奇(1364—1444)、楊榮(1371—1440)、楊溥(1372—1446)及李東陽(1447—1516)為首的茶陵派文學風氣下提出的。臺閣重臣的詩作,大多屬應制頌聖、題贈之章,以歌詠昇平為主要内容,風格雍容閑雅,欠缺真實性情。在臺閣體盛行詩壇之後,李東陽出而矯之,以擬古樂府著稱,推崇李白(701—762)、杜甫(712—770),主張詩要寫真情實意。李東陽主盟當時文壇,追隨者衆。但以李東陽為首的茶陵派並未完全擺脱臺閣氣息,因此為前後七子的宗唐復古肇立了近因②參考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臺北:五南圖書公司1994年版,頁312—319。。等到前後七子一出,反抗臺閣體與八股文,以擬古及復古為職志,但這種回到漢唐傳統的風格,等於拾古人遺唾,缺乏文學作品應有的個性,等到公安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袁中道(1570—1626)兄弟登上文壇,由於他們性喜自由,嘉樂山水,自然不願受傳統桎梏,於是有了獨抒性情的主張。袁宗道世壽不永,且大半時間都在做官,留下的詩歌僅近二百首,文則多為應酬文章③參見袁宗道:《白蘇齋類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袁中道則到萬曆四十四年(1616)纔舉進士,此時離他去世不過七年,他一生大半時間多在旅游山水,結交詩友,對詩歌理論並没有太多的主張④參見袁中道著,錢伯城點校:《珂雪齋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因此三袁中唯袁宏道個性最明顯,留下的詩歌及論詩文章最多,對前後七子之復古反抗力道也最大。問題是前後七子主張“文必秦漢,詩必盛唐”,漢唐詩文確實是傳統中的經典,袁宏道真的能一空依傍,字字從心中湧出,篇篇都是獨抒性情嗎?
近代文論有所謂影響的焦慮,美國學者布魯姆(Harold Bloom,1930— )在《影響的焦慮》書中提出,任何文學家,均負荷著前人對自己影響的焦慮,在此種弗洛伊德之戀父又弒父的心理衝突的情況下,尋求突圍。後來者必須對早先的作品重新運用、翻案,以便發展出本身的創意①Harold Bloom,The Anxiety of Influence,New York:Oxford UP,1973.。此外,在他的另一部作品《誤讀的地圖》中,他更提出,世上所有偉大的文學創作,均乃是對於前輩作家的一種誤讀,後來者必須將誤讀作為新解,每個人的寫作、思考、閲讀,都無法避免模仿,但詩人又以修正前人的方式去逃避模仿②Harold Bloom,A Mapof Misreading,New York:Oxford UP,1975.布魯姆也在A Map of Misreading中提出不存在獨創的文本,只有文本之間的交互關係之説,參見該書頁3。。法籍學者克莉斯蒂娃(Julia Kristeva,1941— )更提出了文本互涉(intertextuality,或譯互文性,在本文中兩個譯名將交互使用)的概念,認為所有的文本或文學作品都和他人之作形成互涉,不存在一空作傍的文本,任何文本都是從其他文本中汲取或建構的,文本彼此互相聯繫的現象廣泛存在,旁徵博引和典故繁複的史書固然頗富互文性,即使是號稱獨創的文學作品,同樣依靠互文性來建構其内涵。互文性還指出歷史的、社會的因素與環境同樣和文學作品形成互文,讀者先前的閲讀經驗、文學知識也和作品形成至關緊要的互文③Julia Kristeva,La Révolution Du Langage Poétique:L'avant-GardeÀLa Fin Du Xixe Siècle,Lautréamont Et Mallarmé,Paris:Éditions du Seuil,1974,English translation: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1984,按本書為克莉斯蒂娃博士論文的出版。。在《符號學》一書中,她更強調,每一個作品都是從其他作品引用文句、拼嵌成形,既吸收其他作品,又加以變化④Julia Kristeva,Séméiôtiké:recherches pour une sémanalyse,Paris:Edition du Seuil,1969.English translation:Desire in Language:A Semiotic Approach to Literature and Art,Oxford:Blackwell,1980,p.146.。克莉斯蒂娃的觀念來自俄國學者巴赫汀(Mikhai Mikhaliovich Bakhtin,1895—1975),他認為語言作為表達的符號,只能在人與人之間的領域產生,因此語言或符號其實是一種社會活動,其意義來自對話(dialogue)場合,從而語言便是社會活動的產物,其意義在互相交會中生生不息。他人的文本和自己的文本不斷地交涉,後來者對前行者或者翻案(interior polemic),或者諧擬(parody),或者風格模仿(stylizing),或者是刻意的重複、引用,使得文本意義成為知識的總合⑤V.N.Voloshinov,Freudianism:A Marist Critique,New York:Academic,1976,p.85;Julia Kristeva,Desire in Language:A Semiotic Approach to Literature and Art,trans.Thomas Gora et al,New York:Columbia UP,1980,pp.65-73.。法國結構主義學者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和德希達(Jacques Derrida,1930—2004)也都景從克莉斯蒂娃的説法,巴特認為任何一個文本都是一個互文本,其他文本都以某種形式存在於這一文本之中,每一個文本都是對另一個文本的吸收和改造,作品因此是彼此之間的對話、諧擬、翻案之關係的交匯①Roland Barthes,S/Z,trans.Riehard Miller,New York:Hill and Wang,1974,p.4.。德希達則以為寫作是在叙述者和受述者(或者説訊息的發出者和接收者)兩者缺席(absent)的情況下發生的,僅憑前行文本的被引用(citationality)開創新本文的生命,因此,世界上没有純粹獨創的現存符號或文本,只有不斷延異(deferred)、有待解讀的符號或文本②Jacques Derrida,“Signature Event Context,”Glyph,1,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7,pp.172197.。俄國另一位形式主義學家什克洛夫斯基(Victor Shklovsky,1893—1984)也有相同的看法,他説:“藝術作品的形式決定於它與該作品之前已存在過的形式之間的關係,不單是諧擬作品,任何一部藝術作品都是作為某一前行作品的類比和對照而創作的。”③Victor Shklosky,Theory of Prose,trans.Benjamin Sher,London:Balkey Archive Press,1991,p.35.現代文本理論雖出自西文學界,但文學理論之成立,在於它為文學現象提出了一個普遍而行諸四海皆準且古今通用的律則。因此,我們不難找到在中國文論文相對應的説法。
在中國傳統文論中,劉勰(約465—520)的《文心雕龍》可能最早注意到文本的互涉,在《宗經篇》中他指出了後人作品對經典的繼承,其言曰:“若禀經以製式,酌雅以富言,是仰山而鑄銅,煮海而鹽也。”④劉勰:《文心雕龍》,臺北:啟業書局1976年版,頁23。另對中國文學中作品互相指涉的問題,可參見葉維廉:《中國現代文學批評選集·序》,臺北:聯經文化事業公司1976年版,頁1—14;Chou Ying Hsiung(周英雄),“Intertextuality between Han China Proverbs and Historiography,”Asian Culture,9.3 and 4(1981),pp.67-78,60-72;另鄭樹森《結構主義與中國文學研究》(載於《中外文學》1982年第10卷第10期,頁26—27)也提到對前人作品成句的引用是中國文學的特色,構成了作品之間互為指涉的關係。唐皎然(730—799)《詩式》也提到復古之中需有變化,也就是模仿中有新創,其言云:“作者須知復變之道,反古曰復,不滯曰變,若惟不變,則陷於相似之格。”⑤釋皎然《詩式》卷五“復古通變條”,收入張伯偉編:《全唐五代詩格校考》,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頁307。後來韓愈(768—824)知道獨創之難,所以在《答李翊書》中説:“惟陳言之務去,戞戞乎其難哉!”因此他要李翊“游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絶其源”⑥韓愈著,屈守元編:《韓愈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頁1454。,换句話説,就是要從《詩》、《書》中取材,所以他在《進學解》中乾脆承認自己“窺陳編以盜竊”①韓愈著,屈守元編:《韓愈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頁1911。,又在《南陽樊紹述墓誌銘》中説詩文:“必出於已,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惟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②同上注,頁2641。這是説後人雖指責前人之作公然相襲,但從漢到唐其實人人難免,只是久而未覺自己之作和古人有相連屬而已,韓愈言下之意,當然是説獨創實難,所以後學要能變化古人為自己所用,承襲中要有創意,並不是真的鼓勵抄襲。北宋黃庭堅(1045—1105)也曾就對前人文本的推陳出新,提出點鐵成金之説,在《答洪駒父書》中云:
自作語最難,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③黃庭堅:《豫章黃先生文集》,臺北: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四部叢刊》正編第49册,卷九。又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臺北:新興書局,1983年版,前集卷九引。
又惠洪《冷齋夜話》引黃庭堅奪胎换骨之説云:
詩意無窮而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淵明、少陵不得工,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换骨法,規摹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法。④吴文治編:《宋詩話全編》,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頁2429。
劉若愚以為换骨指使用不同字句模仿前人意境,奪胎指模仿前人字句以表現不同的意境⑤劉若愚之説見James J.Y.Liu,The Art of Chinese Poetr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2,p.78.,李又安(Adel A.Rickett)則以為奪胎意指使用前人的詩句來表達深一層或與原詩不同的意思,换骨則指用不同的語詞表達相同的意思⑥見其“The Poetics of Huang Ting-chian,”in Adele A.Rickett,ed.Chinese Approached to Literature from Confucius to Liang Ch'i-chiao,Princeton:Princeton UP,1978,中譯見莫礪鋒:《法則和直覺:黃庭堅的詩論》,原載《文藝理論研究》1983年第2期,收入莫礪鋒:《神女的追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頁271—285。。奪胎换骨除了模仿前人字句,使用句典之外,也是事典的使用,錢鍾書論宋詩,以為宋代詩人貴用事在點鐵成金的黃庭堅詩裏達到了登峰造極,宋人有了唐詩作榜樣,“就放縱了摹仿和依賴的惰性”①錢鍾書:《宋詩選注·序》,臺北:書林書店1990年版,頁17;宋人善摹仿的相關研究另可參見徐復觀:《宋詩特徵試論》,載於《中國文學論集·續編》,臺北:學生書局1981年版,頁23—68。。錢鍾書對文學傳統於後來者的意義也有很適切的評論,他説:“前代詩歌的造詣不但是傳給後人的產業,而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説向後人挑釁,挑他們來比賽,試試他們能不能後來居上,打破紀録,或者異曲同工,别開生面。”②錢鍾書:《宋詩選注·序》,頁16。中國文論在用詞上雖和現代西方文論不同,但對詩歌中摹仿和文本互涉現象以及在摹仿之際如何創新的辯難是一致的。
無論中西文論,都指出詩歌的獨創戛戛其難,文本都是前有所承的。因此,公安派袁宏道主張獨抒性情是可以成立的嗎?還是他其實是在傳統的影響下反傳統,在文本的獨創中其實和前行詩人而形成文本互涉?詩歌的創作中不免用典、挪用前人詩句、唱和他人作品、借古諷今、諧擬等,在今天文學理論看來,這些都是互文性,是互文便無獨創,而是和古人或今人作品形成秘響旁通③葉維廉:《秘響旁通——文意的派生與交相引發》,載於《歷史傳釋與美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局1988年版,頁89—113。葉維廉在此文中對文學母題(motif)如何在不同詩文中反復出現有很好的闡釋,文學既是許多母題的不斷重復,便不可能有真正的獨創。,如此一來,袁宏道在詩歌創作中還能説是字字由己出嗎?還是他其實在不自覺的表現出了理論與作品間的辯證或者甚至是悖反?這是本文的問題意識,也是本文希望透過袁宏道文學理論與詩歌的檢驗,來討論文學創作中傳承與新變之間的關係。
二、獨抒性情理論的提出
前文提到,袁宏道的詩學主張是極其具有針對性的,他看不慣前後七子詩必盛唐的復古詩觀,所以主張獨抒性情。但復古詩派有其時代意義,宋佩韋指出:“明代士大夫經過了長期的八股訓練,已不知不覺地養成了模仿的根性,復古派盡以救衰起蔽為己任,盡怎樣地高唱文必秦漢,卻終逃不出模仿古人的圈套。”④宋佩韋:《明代文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頁5。宋氏這段話其實也説明了一個文學史上普遍的現象,那就是模仿前人往往是不可避免的學習過程,只是有些作家在模仿之後能出以己意,點鐵成金,奪胎换骨,如黃庭堅,這是高明的模仿,如姜白石所言:“不求與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與古人異而不能不異。”①姜夔:《白石道人詩集·序》,《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頁2。但有些作家字擬句隨,容易為人看破,成了拙劣的模仿。但不論那一種模仿,都是不同程度的文本互涉。吉川幸次郎(1904—1980)其實極肯定明代復古派摹古的史識,只是他認為問題就在摹古派“作品無法擺脱窠臼,變成了古人的奴隸,難免止於單純的模仿,毫無推陳出新,獨出心裁的創造性。”②吉川幸次郎著,鄭清茂譯:《元明詩概説》,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2年版,頁223。可見問題不在模仿,模仿是文學的常態。杜甫在唐詩中之創體無可置疑,但他《宗武生日》詩中仍告誡兒子要熟讀《文選》,杜甫自己的作品,更是多從六朝詩人而來③杜甫詩對六朝詩人的繼承,可參見吕正惠:《杜甫與六朝詩人》,臺北:大安出版社1989年版。。蓋模仿形成了和他人文本的互涉,仿佛佛經中所説的帝網明珠,互相映照,彼此相融。因此,前後七子的問題不在於學習盛唐詩,而在於不能辨證性的從盛唐傳統中“轉化”出新意④這裏借用林毓生對五四時期知識份子反中國文化傳統有些保留,他認為傳統不是要捨棄或反對,而是要能轉化。參見林毓生:《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北京:三聯書店1988年版。。李夢陽和何景明的友人陸深(1477—1544)就曾批評二人的作品“似落人格套,雖謂之擬作可也”⑤陸深:《儼山外集》,《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卷一五,頁122。。
袁宏道在當時詩壇摹古聲中登場,不滿於當時詩風,這當然和他個性喜自由,不喜格套有關,但也是當時千篇一律的模仿詩風,已到了不得不變的時勢使然。因此他拈出獨抒性情的詩學主張,便得到了不少迴應⑥時代稍後的錢謙益(1582—1664)評袁宏道云:“中郎之論出,王、李之雲霧一掃,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靈,搜剔慧性,以蕩滌摹擬塗澤之病,其功偉矣。”見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哈佛大學: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丁集,袁稽勳宏道條下。網址: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44010&page=2。,影響深遠⑦有關袁宏道文學對後世的影響,參見田素蘭:《袁中郎文學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2年版,第七章,頁209—227;韋仲公:《袁中郎學記》,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年版,後跋,中郎總論,頁125—130。。但是他的詩學主張,雖然有洞見(insight),也有其不見(blindness)⑧洞見與不見是美國耶魯大學學者德曼(Paul de Man,1919—1983)提出的術語,認為任何批評家都有其洞見,也有其盲點,見Paul de Man,Blindness and Insight,Minneapolis:Minnesota Press,1983,pp.102-103.,我們必須將其放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來看纔不致先入為主。其洞見之處當然在於他提出獨抒性情,語語自胸臆中流出之説,合於文學作品應有創意及個性的原則。其不見則在創意難得,追步模仿前人不可免,大詩人尚且如此,何況其他。完全出自個人胸臆,不僅使詩歌脱離傳統脉絡,無所繼承,也將使詩歌成為個人囈語,難為他人所理解。袁宏道在理論上雖力倡獨抒性情,但在實際作品中實不能不與古人相唱和,追步前人,也許折衷之道在於從古人作品中作創造性轉化,此種轉化近於西方文論的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手法,所謂陌生化,意謂當一種藝術手法或修辭成為陳套,不能再引起新鮮感受,後來者於是用新奇和阻拒手段,擴大對事物感知的困難,使熟悉的經驗有了新鮮的效果①陌生化理論參見Victor Shlovsky,“Art as Techque,”in Lee T.Lemon and Marion J.Reis,ed.Russian Formalist Criticism:Four Essays,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65,pp.525.,换言之,也就是在前人基礎上推陳出新,或宋人所謂的奪胎换骨。無論如何,袁宏道處在摹古風氣極盛之後,其抨擊摹古,提倡獨抒性情,自有其時代意義與詩學上的重要性。我們必須檢視他對摹古的一些批評,纔能理解他理論的時空背景,首先來看袁宏道在序弟弟中道的詩集時對當時摹古風氣的不滿:
蓋詩文至近代而卑極矣,文則必欲準於秦、漢,詩則必欲準於盛唐,剿襲摹擬,影響步趨,見人有一語不相肖者,則共指以為野狐外道。曾不知文準秦、漢矣,秦、漢人曷嘗字字學六經歟?詩準盛唐矣,盛唐人何嘗字字學漢、魏歟?秦、漢而學六經,豈復有秦、漢之文?盛唐而學漢、魏,豈復有盛唐之詩?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所以可貴,原不可以優劣論也。②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叙小修詩》,頁187。
另外他提倡宋詩,也是為了對抗當時“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無謂③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張幼于》,尺牘,頁501—502。:
至於詩,則不肖聊戲筆耳。信心而出,信口而談。世人喜唐,僕則曰唐無詩,世人喜秦、漢,僕則曰秦、漢無文,世人卑宋黜元,僕則曰詩文在宋、元諸大家。
這是為了矯枉不得不然的言論,唐代是詩歌極盛的時代,近體詩的五七言律絶都在唐代完成格律和體製,古詩和古樂府也在唐代完成律化,使得唐代不管五七言古詩或樂府都和兩漢及魏晋六朝不同,宋、元、明代起,至少在聲調格律上都無法超越唐人訂下的形式,其它諸如李、杜、王、孟等在詩歌題材上的開創就不用説了。而袁宏道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説“唐無詩”,實有其時代背景及為反擬古不得不然的一番苦心。細檢袁宏道文集,可以發現他不僅常提到盛唐李、杜詩,更時時閲讀杜詩,在給李贄的信中曾説:“至李、杜而詩道始大。”①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與李龍湖》,尺牘,頁734。他的好友曾可前(1560—1611)在序其《瓶花集》時説:“石公(袁宏道號)居嘗語友人,文必摹秦漢,詩必襲杜陵,此自世之大病……斯言出,疑信參半,其信者遂謂石公自為文若詩焉耳。余獨謂石公之文從秦漢出,石公之詩善學老杜者。”②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附録》,頁1694。曾可前被視為公安派詩人,正因他和袁氏兄弟往來密切,知之最深,他道出了盛唐李、杜詩,是橫在後學前面的一座巨山,不可能被忽視,後學者唯有高屋建瓴,踏在巨人的肩上繼續前進。我們也許可以説,在前人影響的焦慮下,袁宏道提出了獨抒性情之説,但獨創不可能一無依傍,不以前人作品為參照,就像物理學所説,我們能夠感受到物體的運動,是因為有兩種物體互為參照,在萬里無雲的天空中,乘客幾乎感受不到飛機的快速前進,也像心理學的鏡像理論,人對自我的了解,是來自他者做為參照纔有可能。文學也是如此,没有前行者作品的參照,就無所謂獨創,獨創也必需放在傳統中來觀察,因此詩人可能自覺是獨創,但在無意識中其實已經汲取了社會、文化、歷史、傳統文學等等中的元素與養分,甚至模仿了前人作品而不自知,因此獨創也者,乃是對傳統的創造性轉化。杜甫號稱大家,但只要細檢仇兆鰲《杜詩詳注》,不難看出杜詩有多少詩句是變化前人而來,有多少使事用典,皆出六朝以前文化的積淀,皆出先秦兩漢以至六朝的文史著作。在這樣的脈絡下,袁宏道一方面倡言唐無詩,一方面又推尊李、杜,也就無足怪了。甚至中晚唐如李賀也是他喜愛的詩人,他的朋友甚至視他為“今之長吉”③袁宏道好友江盈科(1553—1605)在序袁宏道《解脱集》時説:“中郎論詩,最恥臨摹,其於長吉詩非必有心學之,第余觀其突兀怪特之處,不可謂非今之長吉。”見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附録》,頁1690。。
雖然曾可前以為袁宏道學老杜,但袁宏道自己則一再強調今人應該為今人之文,不必摹古,他在給友人張幼于的尺牘中説到:
古之不能為今者也,勢也。……辟如《周書·大誥》、《多方》等篇,古之告示也,今尚可作告示不?《毛詩·鄭》、《衛》等風,古之淫詞媟語也,今人所唱《銀柳絲》、《掛鍼兒》之類,可一字相襲不?世道既變,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也,亦勢也。……若使今日執筆,機軸尤為不同。何也?人事物態,有時而更,鄉語方言,有時而易,事今日之事,則亦文今日之文而已矣!①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江進之》,尺牘,頁515—516。文中之盧楠,字少楩,大名濬縣(河南省淇縣東北)人,國學生,明代廣五子之一,詩文為王世貞(1526—1590)贊賞,萬恭(1515—1591)稱其詩作有先秦策士之風。為人恃才傲物,好使酒駡座。嘉靖二十一年因得罪縣令而下獄,謝榛(1495—1575)至京師為其稱冤,時平湖陸光祖代縣令,冤案始得昭雪。嘉靖三十年出獄後,到彰德拜謝謝榛。隆慶三年(1569)因嗜酒而死。有《蠛蠓集》等。參《明史·謝榛盧楠傳》卷二八七。
袁宏道在上文中説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古不能為今,今也不必摹古,這當然是正確的,但他又推尊蘇軾、歐陽修,以及民歌俗曲如《銀柳絲》之類,更在自己作品中大量追模白居易(772—846)、蘇軾(1037—1101)及民歌,這就呈現了理論和創作之間的背離了。摹擬漢唐是摹擬,摹擬宋詩、民歌當然也是摹擬,袁宏道有此矛盾,可能是為了對抗詩必盛唐的復古派,於是拈出宋詩及歐、蘇、民歌,但這種矛盾,我們必須放在時代背景下去理解。錢謙益在《列朝詩集小傳》中適切地指出萬曆中期的詩風及袁氏推尊宋詩之由:
萬曆中年,王、李之學盛行……中郎以通明之資,學禪於李龍湖,讀書論詩,橫説豎説,心眼明而膽力放,於是乃昌言擊排,大放厥辭,以為唐自有詩,不必選體也,初、盛、中、晚皆有詩,不必初、盛也。歐、蘇、陳、黃各有詩,不必唐也。②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哈佛大學: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資料庫),丁集,袁稽勳宏道條下。網址: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44010&page=2。
袁宏道則在序弟弟袁中道的詩集時稱其所作詩文大都獨抒性靈,從自己胸臆中出,甚至以為即使有若干瑕疵,也都是本色獨造,既使作品看似佳處,只要落入蹈襲,便有遺憾。他甚至以為當時詩文,值得流傳的,只有民歌,因為只有民歌出自胸臆,是真性情:
弟小修……泛舟西陵,走馬塞上,窮覽燕、趙、齊、魯、吴、越之地,足跡所至,幾半天下,而詩文亦因之以日進。大都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有時情與境會,頃刻千言,如水東注,令人奪魄。其間有佳處,亦有疵處,佳處自不必言,即疵處亦多本色獨造語。然予則極喜其疵處,而所謂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飾蹈襲為恨,以為未能盡脱近代文人氣習故也。……且夫天下之物,孤行則必不可無,必不可無,雖欲廢焉而不能,雷同則可以不有,可以不有,則雖欲存焉而不能。故吾謂今之詩文不傳矣。其萬一傳者,或今閭閻婦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類,猶是無聞無識真人所作,故多真聲,不效顰於漢、魏,不學步於盛唐,任性而發,尚能通於人之喜怒哀樂嗜好情欲,是可喜也。①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叙小修詩》,頁187。
又在序曾可前詩集時,強調他和曾可前之所以同調,厥在氣味相投,詩文皆有真性情:
余文信腕直寄而已。以余詩文視退如,百未當一,而退如過引,若以為同調者,此其氣味必有合也。昔人謂茶與墨有三反,而德實同,余與退如所同者真而已。其為詩異甘苦,其直寫性情則一。②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叙曾太史集》,頁1106。
在給好友張獻翼(1550—1636,字幼于)的信中提到書籍之所以流傳,在於不依傍古人,詩文若是剽襲他人,便無足觀,他自己最得意之詩,正是那些他人所不取而不似唐人的作品:
昔老子欲死聖人,莊生譏毀孔子,然至今其書不廢,荀卿言性惡,亦得與孟子同傳。何者?見從己出,不曾依傍半箇古人,所以他頂天立地。今人雖譏訕得,却是廢他不得。不然,糞裏嚼查,順口接屁,倚勢欺良,如今蘇州投靠家人一般。記得幾個爛熟故事,使曰博議,用得幾個見成字眼,亦曰騷人。計騙杜工部,囤紮李空同,一個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以是言詩,安在而不詩哉?不肖惡之深,所以立言亦自有矯枉之過。公謂僕詩亦似唐人,此言極是。然要之幼于所取者,皆僕似唐之詩,非僕得意詩也。夫其似唐者見取,則其不取者斷斷乎非唐詩可知。既非唐詩,安得不謂中郎自有之詩,又安得以幼于之不取,保中郎之不自得意耶?僕求自得而己,他則何敢知。近日湖上諸作,尤覺穢雜,去唐愈遠,然愈自得意。①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張幼于》,尺牘,頁501—502。
在給友人梅蕃祚(字子馬,生卒年不詳)的《王程稿》作序時,他説自己論詩的主張多與時人不合,又無借梅蕃祚的話道出自己心聲:
余論詩多異時軌,世未有好之者,獨宣城梅子與余論合。凡余所擯斥抵毀,俱一時名公鉅匠,或梅子舊師友也,梅子的然以為是。……梅子嘗語余曰:“詩道之穢,未有如今日者。其高者為格套所縛,如被殺翮之鳥,欲飛不得,而其卑者,剽竊影響,若老嫗之傅粉,其能獨抒己見,信心而言,寄口於腕者,余所見蓋無幾也。”②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叙梅子馬王程稿》,頁699。
在給自己同年進士江盈科(字進之,1553—1605)的詩集寫序時,他再次抨擊復古之詩學及不敢呈一己之才以摹擬為務的作品:
近代文人,始為復古之説以勝之。夫復古是已,然至以剿襲為復古,句比字擬,務為牽合,棄目前之景,摭腐濫之辭,有才者詘於法,而不敢自伸其才,無之者,拾一二浮泛之語,幫湊成詩。智者牽於習,而愚者樂其易,一唱億和,優人騶子,皆談雅道。吁,詩至此,抑可羞哉!③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雪濤閣集序》,頁710。
在給自己的舉人座主馮琦(字用韞,號琢菴,1558—1603)的信中,他又強調自己詩作皆獨出己見,絶不摹古:
宏實不才,無能供役作者。獨謬謂古人詩文,各出己見,決不肯從人脚根轉,以故寧今寧俗,不肯拾人一字。④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馮琢菴師》,尺牘,頁781—782。
獨抒性情當然是袁宏道在前後七子摹古的時代環境中不得不然的主張,但我們從他友人曾可前的文章中可看出,在旁人眼中,袁宏道詩文還是有所承襲,在詩歌方面,他不可能無視於唐詩的成就,他標舉宋詩,主要是針對當時“詩必盛唐”的剽襲之風而發,盡管他在詩學主張上一再強調獨創,但在實際創作中他又多方借用前人詩句、使事用典、和唐宋人韻、推尊白居易和蘇軾,尤其是對白、蘇的推尊,詩文中處處可見,但筆者翻檢中國期刊全文資料庫、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中國碩博士論文網、臺灣碩博士論文加值系統及書目資訊網,竟發現僅少數論文淺論袁宏道對蘇軾的推尊①賀玉:《淺論袁宏道在詩歌理論及創作上對蘇軾的推崇》,《金田》2015年第10期,頁14—15。作者為四川省自貢市自流井區自貢一中高中部教師。張志傑:《論交際語境下的“袁宏道為蘇軾後身”説》,《新國學》2017年第1期。,可見學界對此一議題尚未有深入之探討。以下筆者便從袁宏道對白、蘇的推尊、模仿、和詩,來論袁宏道在拈出獨抒性情的詩學和實際創作上的辨證與轉化,也就是説袁宏道一方面強調詩歌的獨創性,另方面其實也不能擺脱前人影響的焦慮,不自覺中作品也呈顯了對前行詩人的摹擬以及文本互涉的現象。
三、對白、蘇的摹擬:獨創還是互文
袁宏道對白居易與蘇軾的推尊,和其老師李卓吾有一定的關係。但也是受到其大哥袁宗道的影響,朱彝尊在《靜志居詩話》評袁小修時説:
自袁伯修出,服習香山、眉山之結撰,首以白蘇名齋,既導其源,中郎、小修繼之,益揚其波,由是公安派盛行。②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版,卷一六,“袁中道”條下,頁465。
按袁宗道長宏道八歲,長中道十歲,仕宦在二人之前,朱彝尊之説應可信,袁宏道自己在《識伯修遺墨後》文中也説:
伯修酷愛白、蘇二公,而嗜長公(蘇軾)尤甚。每下直,輒焚香靜坐,命小奴伸紙,書二公閒適詩,或小文,或詩餘一二幅,倦則手一編而臥,皆山林會心語,近懶近放者也。余每過抱甕亭,即笑之曰:“兄與長公,真是一種氣味。”伯修曰:“何故?”余曰:“長公能言,吾兄能嗜,然長公垂老玉局,吾兄直東華,事業方始,其不能行一也。”伯修大笑,且曰:“吾年只是東坡守高密時,已約寅年入山,彼時纔得四十三歲,去坡翁玉局尚二十餘年,未可謂不能行也。昔樂天七十致仕,尚自以為達,故其詩云‘達哉遠哉白樂天’,此猶白頭老寡婦,以貞驕人,吾不學也。”因相與大笑。①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識伯修遺墨後》,頁1111。
三弟袁中道也在記大哥袁宗道書齋時提到:
伯修賦性整潔,所之必葺一室,掃地焚香宴坐,而所居之室,必以白蘇名,去年買一宅長安,堦上竹柏森疎,香藤怪石,大有幽意,乃於抱甕亭後,潔治靜室,室雖易,而其名不改,尚友樂天、子瞻之意,固有不能一刻忘者。②袁中道:《珂雪齋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卷一二,《白蘇齋記》,頁533。
可見袁氏兄弟對白居易的推尊喜愛,肇自大哥袁宗道,只是袁宏道變本加厲,甚至以白、蘇二公為大菩薩,在給蜀人黃輝(1559—1612)的信中,他説:
詩文是吾輩一件正事,去此無可度日者,窮工極變,舍兄不極力造就,誰人可與此道者?如白、蘇二公,豈非大菩薩?然詩文之工,決非以草率得者,望兄勿以信手為近道也。③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黃平倩》,尺牘,頁1259。
一般認為袁宏道是追求精神自由的人,性喜山林,不屑為官④劉大杰:《袁中郎的詩文觀》,附見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附録三》,頁1743。,但其實他對白居易和蘇東坡的推尊,除了詩文之外,還在於二人能做到儒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處世態度,以出世情懷為入世事業,在給友人的信中,他説:
陶石簣近字,道其宦情灰冷。弟曰:“吾儒説立達,禪宗説度一切,皆賴些子煖氣流行宇宙間,若直恁冷將去,恐釋氏亦無此公案。”蘇玉局、白香山非彼法中人乎?今讀二公集,其一副愛世心腸,何等緊切。①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與劉雲嶠祭酒》,尺牘,頁1595。
陶石簣即陶望齡(1562—1609)②陶望齡,字周望,號石簣,會稽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終官國子祭酒,見《明史》卷二一六陶傳。望齡與弟奭齡同為袁氏兄弟至交。,蘇玉局即蘇軾,蘇軾晚年自儋州貶所赦回,授朝奉郎提舉成都玉局觀,實未至任所,而是任其在外州居任,但後人仍以其最後官職名之。在上信中,袁宏道提到自己以好友陶望齡倦宦,而以白、蘇入世情懷相勉。
前文提到,詩文中的互文性,不僅在字隨句仿,模其精神,也在典故史實的拈出。袁宏道對白居易、蘇軾的推尊,便以這種方式來形成互文性。在給徐州知府夏崇謙的信中,他説:
往見燕子樓甚頽落,即子房山上祠,亦僅蔽風日耳。仁兄游刃之暇,能一改創之乎?蘇子瞻有祠否?《黃樓賦》有佳搨,幸見寄一本。③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與夏徐州》,尺牘,頁1605。按夏徐州即夏崇謙,京山人,萬曆十六年舉人。
按白居易有《燕子樓詩三首并序》④白居易著,朱金城校箋:《白居易集校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卷一五。,序中提到他為校書郎時游徐州,張尚書宴請,席中見到張尚書愛妾關眄眄(或作盼盼),12年後友人張仲素示其《燕子樓詩三首》,其時張尚書已逝,關眄眄則居於燕子樓而不嫁,白居易感其事,因和詩三首。白居易《燕子樓》三首如下:
滿窗明月滿簾霜,被冷燈殘拂臥牀。燕子樓中霜月夜,秋來只為一人長。
鈿暈羅衫色似煙,幾回欲著即潸然。自從不舞霓裳曲,疊在空箱十一年。
今春有客洛陽回,曾到尚書墓上來。見説白楊堪作柱,爭教紅粉不成灰?據黃啟方考證,白居易《燕子樓詩三首並序》應是寫於元和六年四月居母喪之前①黃啟方:《黃樓如何燕子樓》,載於《東坡的心靈世界》,臺北:學生書局2002年版,頁63。。清代汪立名編《白香山詩長慶集》在《燕子樓詩三首》下引明萬曆年間蔣一葵在其《堯山堂外紀》之説,以為關眄眄接到白居易詩後,因白居易責其不能死節,竟不食旬日而死。至於白詩中的尚書,究竟是張建封或其子張愔,則衆説紛紜,宋代以來已多指尚書為張愔②相關考證見日人福本雅一著,李寅生譯:《燕子樓與張尚書》,載《河池學院學報》第6期(2007年12月),頁15—23。。
至於黃樓,據蘇轍《黃樓賦》所記,乃熙寧十年(1077)秋,黃河決於澶淵,水及彭城下,時任徐州太守的蘇軾使民具畚鍤,畜土石,以為水備。後又請增築徐州城,事畢於城之東門為築大樓,堊以黃土,因名黃樓,可覽觀山川,弔水之遺跡。可知黃樓是蘇軾在彭城治水的紀功樓,蘇轍在序文中説,因其兄治水得宜,官民日親,後來秦觀也作了《黃樓賦》。《黃樓賦》雖非蘇軾之作,但卻是記其事功。東坡自己在徐州詩詞不少,最著名的當然是寫於元豐元年(1078)之《永遇樂·明月如霜》③全詞云:“明月如霜,好風如水,清景無限。曲港跳魚,圓荷瀉露,寂寞無人見。紞如三鼓,鏗然一葉,黯黯夢雲驚斷。夜茫茫、重尋無處,覺來小園行遍。 天涯倦客,山中歸路,望斷故園心眼。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古今如夢,何曾夢覺,但有舊歡新怨。異時對、黃樓夜景,為余浩嘆。”,其時為東坡改守徐州的次年,東坡這詞有序云:“彭城夜宿燕子樓,夢盼盼,因作此詞。”詞末云:“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
上文袁宏道給友人夏崇謙的尺牘為我們提供的文本相涉的最好範例,讓我們清楚看到白居易、蘇軾、袁宏道異世而共鳴的現象,三個文本共同指向了同一歷史事件或者説文學母題,白居易在曾經宴請他的徐州太守友故去後,到過洛陽張尚書墓,感慨尚書故去而佳人獨存,白詩末句寫時空變易,紅粉終有成灰之日,未必是責佳人不能死節,只是言者無心,聽者有意,一首詩竟讓佳人斷魂,恐怕是白傅始料未及的。三百年後東坡到徐州,寫詞用燕子樓事典,等於也回應了白居易對物事人非、時逝人去的感慨。事過八百年,袁宏道異世再寫,宛如刮去再寫的羊皮紙(palimpsest),新的文本上,舊跡猶存,具現了歴史叙事永遠是漫涣重疊與反覆改寫的。袁宏道《燕子樓》寫白居易和愛姬楊柳之事,全詩云:
空窗晝掩紅紗隔,一夕温風長葵麥。秋去春來雙燕兒,年年銜粉扮粧額。芍藥死枝不死根,焉知黃土不青春。幽魂異日逢楊柳,應悔生前别舍人。①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燕子樓》,頁573。
這是袁宏道於萬曆二十六年入京途中,經徐州燕子樓而作。詩中的楊柳,即白居易愛姬樊素,按《舊唐書·白居易傳》:“家妓樊素、蠻子者,能歌善舞。”②宋祁等:《舊唐書·白居易傳》,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卷一一六,頁4354。晚唐孟棨(乾符二年進士,875年)《本事詩·事感》:“白尚書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蠻善舞,嘗為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年既高邁,而小蠻方豐艷,因為《楊柳枝詞》以託意。”③孟棨:《本事詩》,《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頁12。葛培嶺引蔡顯《紅蕉詩話》認為樊素、小蠻指的是同一人。香山詩集中並無“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兩句,白居易姬樊素,又名柳枝、樊蠻,不見有小蠻名④見葛培嶺:《白居易》,臺北:知書房出版社2001年版,頁413,注3。蔡顯,字景真,號閒漁,江蘇華亭(今屬上海市)人,清朝文人。雍正七年(1729)中舉。在家開館授徒為業。乾隆三十二年(1767)三月《閒漁閒閒録》刻成後,分送其門人和親朋。書中語涉狂悖,且多訐發他人陰私之處,被處死。。按白居易《晚春酒醒尋夢得》詩云:“還携小蠻去,試覓老劉看。”⑤彭定求等編:《全唐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卷四五六。自注云:“小蠻,酒榼也。”是白居易詩中的小蠻乃是酒榼名。白居易應只有姬人樊素,别名柳枝者,案白居易《宴後題府中水堂贈盧尹中丞》詩,其中有“莫言楊柳枝空老”句,白居易自注:“府妓有歌楊柳枝曲者,因以名焉。”⑥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卷四五九。白居易晚年得風濕病,因遺名馬及柳枝,有《病中詩》十五首,其中有一首《别柳枝》:“兩枝楊柳小樓中,嫋娜多年伴醉翁。明日放歸歸去後,世間應不要春風。”又有《對酒有懷寄李十九郎中》詩云:“往年江外拋桃葉,去歲樓中别柳枝。”又有《不能忘情吟》詩,序中説:“妓有樊素者,年二十餘,綽綽有歌舞態,善唱柳枝,人多以曲名之。”詩云:“駱駱爾勿嘶,素素爾勿啼;駱反廄,素返閨。吾疾雖作,年雖頽,幸未及項籍之將死,何必一日之内棄騅兮而别虞姬!乃目素曰:素兮素兮!為我歌《楊柳枝》。我姑酌彼金罍,我與爾歸醉鄉去來。”⑦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卷四六一。樊素離去後,一次酒宴散後,正值暮春三月,春盡花殘,白居易想起了樊素,寫了《春盡日宴罷感事獨吟,開成五年三月三十日作》:“五年三月今朝盡,客散筵空獨掩扉。病共樂天相伴住,春隨樊子一時歸。閒聽鶯語移時立,思逐楊花觸處飛。金帶縋腰衫委地,年年衰瘦不勝衣。”①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卷四五八。後來東坡詩《次京師韻送表弟程懿赴夔州運判》中有“我甚似樂天,但無素與蠻”之句,應是沿襲《本事詩》之誤,以樊蠻、樊素為二人。
袁宏道在上引詩作中,把關盼盼和樊素的故事作聯想,設想她們幽魂若相逢,則楊柳應後悔生前輕别白居易舍人。在此我們又看到了一個文本互涉的典範,白居易當年寫關盼盼,感嘆初見張尚書時,兩人猶恩愛逾恒,但十一年後,隨著張尚書故去,人事變遷,時光易老,紅粉也難免紅顔不再。袁宏道再寫燕子樓,則嘲諷了白居易的輕遺愛姬。同樣是離别,生離與死别,也許生離更令人難堪。袁宏道巧妙的應用典故,形成了有趣的文本互涉。下面一首《遣姬》詩,袁宏道又再度用楊柳典故:
蠶懶無心更作絲,樂天未老别楊枝。陽臺不是嫌雲雨,圖得生離勝死離。②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遣姬》,頁613。
萬曆三十二年(1604),袁宏道三十七歲,閒居公安,在《甲辰初度》詩中,我們又看到了他用楊柳母題:
閒花閒石伴疏慵,鏡掃湖光屋幾重。勸我為官知未穩,便令遺世亦難從。樂天可學無楊柳,元亮差同有菊松。一盞春芽融雪水,坐聽游衲數青峯。③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甲辰初度》,頁1052。
所謂“樂天可學無楊柳”,也是蘇軾《次京師韻送表弟程懿赴夔州運判》詩中“我甚似樂天,但無素與蠻”的回響,再一次,白居易、東坡、袁宏道形成了織錦式的互文。袁宏道多次在詩中表示對樂天的追慕,在《偶成》中説:“擬與樂天為近舍,借他歌板佐歌聲。”④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偶成》,頁992。在另一首詩中,又用到歌姬典故:“寒節逢人少,新詩説酒多。小蠻持管笑,呵墨寫長蛾。”⑤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冬日雜興其四》,頁613。
在互文性理論中,和詩也是文本互涉的一種方式,關於和詩,宋劉攽(1023—1089)《中山詩話》將唐人和詩分為三種:“唐人賡和詩,有次韻,先後無易;有依韻,同在一韻;有用韻,用彼韻不必次,吏部和皇甫《陸渾山火》是也,今人多不曉。”①吴文治編:《宋詩話全編》,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頁445。吏部指韓愈(768—824),皇甫指皇甫湜(777—835)。又吴喬《答萬季埜詩問》:“和詩之體不一,意如答問而不同韻者,謂之和詩;同其韻而不同其字者,謂之和韻;用其韻而次第不同者,謂之用韻;依其次第者,謂之步韻(亦稱次韻)。步韻最困人,如相毆而自縶手足也。蓋心思為韻所束,而命意佈局,最難照顧。”②郭紹虞編:《清詩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頁25。换言之,和韻、用韻、同韻三者實質相同,都是指同韻部而韻字之順序不同,而次韻也稱步韻,最為嚴格,韻字先後順序必須相同③有關和詩的詳細研究,可參看陳鍾琇:《唐代和詩研究》,臺北:秀威科技公司2008年版。。和詩既然必須和原詩之意,又在用字用韻上必須步步相隨,則當然就是一種模仿,不管是和古人之作或和時人、朋友之作,都形成了文本之間密切的關聯,而不可能是完全的獨創。在袁宏道詩歌中,正有不少是和白居易和蘇軾的同題之作,如他模仿白居易作《白香山三十四歲作感時詩余今正其時矣仍次其韻》詩云:
少年沐新髮,鬱若青莎地。一朝盆水中,霜縷忽三四。辟如百里塗,行行半將至。視老猶壯容,比少已憔悴。是身如肉郵,皮毛聊客寄。微官復寄身,寄與寄第二。浮雲畸太空,種種非作意。鱗鬣及鬘鬟,散時等一氣。為樂供朱顔,及時勿回避。青山好景光,花木饒情致。我有戰老策,勝之以無累。胸中貯活春,不糟自然醉。虚舟蕩遠波,從天作升墜。④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白香山三十四歲作感時詩余今正其時矣仍次其韻》,頁899。
白居易《感時》詩云:
朝見日上天,暮見日入地。不覺明鏡中,忽年三十四。勿言身未老,冉冉行將至。白髮雖未生,朱顔已先悴。人生詎幾何,在世猶如寄。雖有七十期,十人無一二。今我猶未悟,往往不適意。胡為方寸間,不貯浩然氣。貧賤非不惡,道在何足避。富貴非不愛,時來當自致。所以達人心,外物不能累。唯當飲美酒,終日陶陶醉。斯言勝金玉,佩服無失墜。①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卷四二八。仔細對比,可以發現袁宏道這首追和白居易之作,用了吴喬所説最困難的步韻,“蓋心思為韻所束,而命意佈局,最難照顧”。但袁宏道巧妙的在模仿之外,作了翻案文章,推陳出新。白居易詩首先感慨青春易逝,人命不永,世事不盡如人意,接著道出無奈中的應對之道,厥在通達人情世故,使外物不能累,最後以及時行樂的思想總結全詩。袁宏道詩首言人生行半,忽已中年,感慨時間易逝、人生如寄的情緒和白居易是相同的,但他接著便道出自己不同於白居易的處世哲學,便是游山水以遺老,自然任運,醉春而不需醉酒。兩人之作,同又不相,相同的是感時的母題,不同的是應世的心態。如此一來,袁宏道在模仿古人中又有自己的創意,唯雖説是創意,又不脱唱和前人之作,在用字和用韻上步步相隨,印證了互文理論中所説的,没有文本是獨一無二的,所有文本都是其它文本的迴響。
袁宏道另有《放言》五首,也是追和白居易的同題之作,詩如下:
掉頭誰擬作公卿,只合林間樹下行。臧是穀非憑耳過,元輕白俗任詩成。有身祇作他人看,無事休將造物爭。夜踏芒鞋深雪裏,自呼東郭冷先生。
賢愚富貴且憑他,山上髻鬟柳上娥。鐵網試撈穿海月,漁舟任截過頭波。齊肩大士辭葷久,秃髮中書感事多。船芎老郎江口女,咿啞容易得成歌。
鸞靴寧説上場難,衫袖郎當且自看。世路兩平三仄嶺,人情八折九迴灘。胸中毛女霞千片,石上王喬藥一丸。夢去幾番登岳頂,扶桑清水浴赬盤。
高人竊欲比無功,間把心情托去鴻。《易》象有時輪瓦卜,《騷》材兼不廢媱風。謀生拙似啣冰鶴,觸事剛如蝕木蟲。莫放大鵬天上去,恐遮白日駭愚蒙。
抹却濃嵐作羽衫,撫松終日坐枯巖。盜悲老氏折衡斗,馬謝莊生脱轡銜。青鳯下來傳古字,白雲飛去護仙緘。芝田數畝那耕得,收拾山中木柄欃。①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放言效白》,頁900—901。
白居易《放言》五首原詩如下:
朝真暮偽何人辨,古往今來底事無。但愛臧生能詐聖,可知甯子解佯愚。草螢有耀終非火,荷露雖團豈是珠。不取燔柴兼照乘,可憐光彩亦何殊。
世途倚伏都無定,塵網牽纏卒未休。禍福回還車轉轂,榮枯反復手藏鈎。龜靈未免刳腸患,馬失應無折足憂。不信君看弈棋者,輸贏須待局終頭。
贈君一法決狐疑,不用鑽龜與祝蓍。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材須待七年期。周公恐懼流言後,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
誰家第宅成還破,何處親賓哭復歌。昨日屋頭堪炙手,今朝門外好張羅。北邙未省留閑地,東海何曾有定波。莫笑賤貧誇富貴,共成枯骨兩如何。
泰山不要欺毫末,顔子無心羨老彭。松樹千年終是朽,槿花一日自為榮。何須戀世常憂死,亦莫嫌身漫厭生。生去死來都是幻,幻人哀樂繫何情。②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卷四三八。
白居易《放言》五首詩序云:“元九在江陵時,有放言長句詩五首,韻高而體律,意古而詞新。予每詠之,甚覺有味,雖前輩深於詩者未有此作。唯李頎有云:濟水自清河自濁,周公大聖接輿狂,斯句近之矣。予出佐潯陽,未届所任,舟中多暇,江上獨吟,因綴五篇以續其意耳。”唐憲宗元和五年(810),元稹因得罪了權貴,被貶為江陵士曹參軍,元稹在江陵期間,寫了五首《放言》詩抒發心情。元和十年,白居易因上書急請追捕刺殺宰相武元衡的兇手,遭當權者忌恨,當年六月,被貶為江州司馬,途中寫下了和元稹《放言》組詩。可知白居易的詩原是追和元稹的,而袁宏道詩又是追和白居易的。
白居易第一首詩中的臧生指武仲臧孫氏,名紇,官為司寇,據《論語·憲問》載:“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防是武仲的封地,孔子是説武仲憑藉其封地防來要脅魯君,《左傳·襄公二十二年》杜氏注:“武仲多知,時人謂之聖。”甯子指甯武子,《論語·公冶長》載:“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照乘則為明珠名。《史記·田敬仲完世家》載齊威王:“與魏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梁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為萬乘之國而無寶乎?”①司馬遷:《史記·田敬仲完世家》,臺北:文馨出版社,影印武英殿版,頁749。白居易這首詩旨在表達人情事物的真偽難辨。
第二首詩用了莊子典故,《莊子·外物》:“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窺阿門……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仲尼曰:神龜……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策,不能避刳腸之患。”②郭慶藩輯:《莊子集釋》,臺北:河洛出版社1974年版,頁933。“馬失”句用塞翁失馬事,見《淮南子·人間訓》③劉安編,高誘注:《淮南子》,臺北:世界書局1984年版,頁311。。
第三首中,“辨材”句下作者亦自注云:“豫章木生七年而後知。”按《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楩楠豫章。”《正義》:“豫今之枕木也;樟今之樟木也。二木生至七年,枕樟乃可分别。”④司馬遷:《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臺北:文馨出版社,影印武英殿版,卷一一七,頁1229。《漢書·王莽傳》:“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散輿馬衣裘,振施賓客,家無所餘。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衆。……欲令名譽過前人,遂克己不倦。”後獨攬朝政,殺平帝,篡位自立①班固著,王先謙補注:《漢書·王莽列傳》,臺北:藝文印書館,無出版日期,卷九九,頁1711—1759。。北邙,山名,亦作北芒,即邙山,在今河南省洛陽市北,為東漢及北魏的王侯公卿墓地。這一首詩也在表現人情真偽難辨。
第四首中,“張羅”句用典,形容門庭冷落,《史記·汲鄭列傳》:“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衆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②司馬遷:《史記·汲黯列傳》,臺北:文馨出版社,影印武英殿版,卷一二〇,頁1271。這首詩表達了人生死的窮通蹇達之别,但死亡撫平了人世間的一切不平等。
第五首中,顔子是早死的孔子學生顔回,老彭則是據説活了八百歲的彭祖,其父名陸終,彭祖名籛,彭城人。全詩大意在説榮枯有時,生死無常的夢幻感。
袁宏道的《放言》第一首中,用了兩個典故,第一個出自《莊子·駢拇》,原文云:“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游。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蹠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蹠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蹠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③郭慶藩輯:《莊子集釋》,頁323。莊子意謂事情也許表相不同,人物也許行事不同,但自殘生損性的本質來看,其實是相同的。
第二個典故出自《列子·天瑞》,原文云:“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為盜。始吾為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穰。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為盜之言,而不喻其為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贓獲罪,没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己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為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為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鱉,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鱉,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亡殃。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向氏大惑,以為國氏之重罔己也,遇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非盜哉?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仞而有之,皆惑也。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有公私者,亦盜也;亡公私者,亦盜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知天地之德者,孰為盜邪?孰為不盜邪?”①列御寇:《莊子集釋》,哈佛大學: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卷一。列子的故事寓意和莊子相同,也在説明人事或事物也許行徑、外相不同,但自本質而言,其實不二。袁宏道借用莊子典故,在這首詩中表達了溟汩是非的人生觀。
第二首鐵網典故出自宋王禹偁《仲咸借予海魚圖觀罷有詩因和》,詩云:“偶費霜縑與綵毫,海魚圖畫滿波濤。搘床難死慙龜殻,把酒狂歌憶蟹螯。䗉蚱腳多垂似帶,鋸鯊齒密利如刀。何當一一窮真偽,須把千尋鐵網撈。”②王禹偁:《小畜外集》,《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卷七,頁5。原意是指畫中的海魚栩栩如生,唯有用鐵網撈起真魚方可一探真假,袁詩借來指海中水月與真月真假不分,又有何關係。齊肩大士是袁宏道自喻,袁宏道自二十餘歲與李贄學佛,便斷葷食,至萬曆三十年作此詩,不食葷已久,但並未落髮。秃髮中書則指白居易,蓋白居易於長慶元年(821)任中書舍人。這首詩表現了袁宏道思想中無賢愚窮達的老莊齊物觀。
第三首中的毛女用《列仙傳》典故,原文云:“毛女者,字玉姜,在華陰山中,獵師世世見之。形體生毛,自言秦始皇宫人也,秦壞,流亡入山避難,遇道士谷春,教食松葉,遂不饑寒,身輕如飛,百七十餘年。所止巖中有鼓琴聲云。婉孌玉姜,與時遁逸。真人授方,餐松秀實。因敗獲成,延命深吉。得意巖岫,寄歡琴瑟。”③劉向:《列仙傳》,《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卷下,頁30。王喬也是神仙人物,《列仙傳》卷上:“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凰鳴。游伊洛之間,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求之於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巔。至時,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④劉向:《列仙傳》,《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卷上,頁316。這首詩中,袁宏道詠歎世路人情的崎嶇不平,以及出世自外人間的思想。
第四首中無功用《莊子·逍遥遊》典故:“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⑤郭慶藩輯:《莊子集釋》,頁17。瓦卜即古代之瓦兆,唐杜甫《戲作俳諧體遣悶》詩之二:“瓦卜傳神語,畬田費火耕。”①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卷二三一。仇兆鰲注引王洙曰:“巫俗擊瓦,觀其文理分析,以卜吉凶。”宋史繩祖《學齋呫嗶·瓦卜》:“今之瓦卜,蓋有取於周太卜之瓦兆。②史繩祖:《學齋呫嗶》,《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卷三,頁90。”另大鵬之喻,當然也可以是《莊子·逍遥遊》中摶扶摇而上九霄的神鳥。全詩主旨在説自己拙於謀生,但其實有若大鵬,志在九霄,不在巢枝。
第五首中第三句用《莊子·胠篋》典故:“故絶聖棄知,大盜乃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③郭慶藩輯:《莊子集釋》,頁353。袁氏云老氏,恐怕是誤記。第四句用《莊子·馬蹄》:“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闉扼鷙曼,詭銜竊轡。”成玄英疏:“竊轡,即盜脱籠頭。”陸德明釋文:“嚙轡也。”④郭慶藩輯:《莊子集釋》,頁339—340。袁宏道在這首詩中企慕老莊,甚至仙家,但以仙路難求,終以無奈之情作收。仙家也許只是袁宏道對世情或宦情厭離的隱喻,畢竟詩人念佛多年,出離之心必然不淺。
白居易五首放言是在被貶時所作,故充滿了等是非、齊生死的釋老思想。袁宏道詩則作於萬曆三十年(1602)居公安時,這時大哥宗道和祖母已在萬曆二十八年去逝,他宦情冷落,自北京辭官回家,在心情上和白居易有些相似,因此詩中表達的思想也追步白舍人,然韻字並不相同,用典也不相同,但表達對世情的無奈和厭離是相同的,應是和意而不和韻之作。
除了白居易外,袁宏道最推尊的詩人是蘇軾。袁宏道對蘇軾的推崇,可能受到李贄(1527—1602)的影響。李贄生平服膺蘇軾,曾有詩文之選。《復焦弱侯》:“蘇長公何如人,故其文章自然驚天動地,世人不知,祗以文章稱之,不知文章直彼餘事耳,世未有其人不能卓立而能文章垂不朽者。弟子全刻抄出作四册,俱世人所未嘗取者。”⑤李贄:《李温陵集》,《續修四庫全書》本,卷四,第1352册頁54。又《寄京友書》:“坡仙集我有披削旁注在内,每開看便自懽喜,是我一件快心却疾之書。”⑥李贄:《李温陵集》,《續修四庫全書》本,卷五,第1352册頁77。焦弱侯即焦竑(1540—1620)⑦焦竑,字弱侯,號澹園,又號漪園,南京人。十六歲選為京兆學生員,二十五歲中舉。神宗萬曆十七年會試北京,得中一甲第一名進士(狀元),授翰林院修撰,二十二年任太子講官。萬曆二十五年任鄉試主考官,將落榜之徐光啟提拔第一。由於個性耿介疏直,被曹大咸、楊廷蘭等彈劾,貶為福寧州同知。萬曆二十六年赴福建福寧州任,一年後移官太僕寺丞,辭官,歸家不出。焦竑篤信卓吾之學。他與李贄相率而為狂禪,贄至於詆孔子,而竑亦至崇揚墨。,袁石浦即袁宗道。袁宏道兄弟結識李贄在萬曆十八年(1590),時李贄漫游至公安,住於寺廟,相談傾倒,袁中道輯其問答為《柞林紀譚》①袁中道著,錢伯城點校:《珂雪齋集》,附録。,那年袁宏道23歲,而李贄已64歲。萬曆十三年,李贄在湖北麻城龍湖隱居,萬曆十八年初見李贄後,便時相往來,對李贄詩文大為拜服。萬曆二十年第二次到龍湖訪李贄,次年再訪,臨别作《别龍湖師》八首。袁宏道在寫於萬曆二十一年的《懷龍湖》詩中,將李贄比為老子李耳,詩云:“漢陽江雨昔曾過,歲月驚心感逝波。老子本將龍作性,楚人元以鳯為歌。”②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頁68。袁中道在《中郎先生行狀》中也説宏道:“既見龍湖,始知一向掇拾陳言,株守俗見,死於古人語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至是……能轉古人,不為古轉,發為語言,一一從胸襟流出。”③袁中道著,錢伯城點校:《珂雪齋集》,頁755—756。小修這段文字,已可見中郎文學主張之所由自,其對東坡的喜愛,應該也是受李卓吾的影響。他甚至認同李卓吾為東坡後身的説法,在題李贄《枕中書》時云:
人有言曰:胸中無萬卷書,不得雌黃人物。……吾於楊升菴、李卓吾見之。或説卓秃翁……為蘇子瞻後身,以卓吾生平歷履,大約與坡老暗符。④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附録》,袁宏道書李贄《枕中書》卷首,頁1634。
袁宏道又選有東坡詩,今國家圖書館藏其《東坡詩選》12卷,線裝6册,卷首題“公安袁宏道中郎閲選,景陵譚元春友夏增删”,為明天啟元年刊本。選詩當然也是讀者接受的一種方式,選詩必擇其精華,在揀擇過程中,必已精讀其詩。既精讀其詩,不可能不受影響,在讀者接受理論中,讀者對特定本文的接受經常表現為選詩、摘句、讚頌、和詩、同題競作、挪用字句、引用典故等現象,這些都已是文本互涉理論中所謂任何文本都是其它文本的編織物了。
袁宏道在給李贄的一封信中,甚至以蘇軾為詩神:
近日最得意,無如批點歐、蘇二公文集。……蘇公詩高古不如老杜,而超脱變怪過之,有天地來,一人而已。僕嘗謂六朝無詩,陶公有詩趣,謝公有詩料,餘子碌碌,無足觀者。至李、杜而詩道始大。韓、柳、元、白、歐,詩之聖也,蘇,詩之神也。①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與李龍湖》,尺牘,頁750。
在給梅國楨(字客生,1542—1605)的信中,袁宏道又以蘇軾的詩卓絶千古,戛戛獨創,出自性情:
蘇公詩無一字不佳者,青蓮能虚,工部能實,青蓮唯一於虚,故目前每有遺景,工部唯一於實,故其詩能人而不能天,能大能化而不能神。蘇公之詩,出世入世,粗言細語,總歸玄奥,怳惚變怪,無非情實。蓋其才力既高,而學問識見,又迥出二公之上,故宜卓絶千古。至其遒不如社,逸不如李,此自氣運使然,非才之過也。②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答梅客生開府》,尺牘,頁734。
又在《夜坐讀少陵詩偶成》詩中,認為蘇軾是唯一可以和杜甫異代相比的詩人。詩云:
嘗聞工書人,見書長一倍。每讀少陵詩,輒欲洗肝肺。體格備六經,古雅凌三代,武庫森戈戟,廟堂老冠佩。變幻風雲新,妖韶兒女黛。古鬼哭幽塚,羈遊感絶塞。古人道不及,公也補其廢。化工有遺巧,代之以覆載。僅僅蘇和仲,異世可相配。剪葉及綴花,諸餘多瑣碎。紛紛學杜兒,伺響任鳴吠。入山不見瑶,何用拾瓊塊。③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夜坐讀少陵詩偶成》,頁1049。
此詩中的蘇和仲,是蘇軾的字,較少為人所知。此詩首先稱美杜甫詩具六經之完備,超越前人,有如武庫中無所不有,詩風又如風雲變化無端,道古人之所未道,而有化工之巧,蘇軾步武杜甫,異世同標,能補杜詩之不足,不像時人,僅拾人牙慧餘唾,入寶山而不見瓊瑶。詩中稱美蘇軾善學杜,旨在帶出袁宏道對明代復古派一味學杜而又無所新創④有關明代復古派學杜之弊,參見陳英傑《明代復古派杜詩學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8年版),尤其是第二章至第六章論李夢陽、何景明、謝榛、王世貞、胡應麟、許學夷部分。。
山居無事,讀蘇詩也帶給袁宏道無限傷感:
飽食長腰米,高撐過頂枝。閒尋施藥地,細剖訟花辭。霧眼添燈暈,雲瓢挂癭師。山齋通夜雨,腸斷子瞻詩。①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和王以明山居韻》其四,頁849。
除了在書信中屢屢提到蘇軾外,他也在許多詩中,歌詠蘇軾。萬曆三十六年(1608),袁宏道赴京途中過中山、定州,所寫的詩中有三首都提到東坡,第一首寫開元寺塔:
孤塔三千級,俯身見鳥過。但知天闊遠,未許岫嵯峨。鈴語聞沙塞,燈光射虜河。昔賢誰眺此,韓宋與東坡。②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登定州開元寺塔》,頁1386。有關開元寺塔,明朝徐昌祚:《新刻徐比部燕山叢録》(臺南:莊嚴出版社1995年版,《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248册)云:“定州開元寺有塔名料敵塔,宋築以望契丹者。高十三級,廣六十四步。旁施鐵幢。中貫數抱大木,登上級可瞰百里,仰視行雲,勢若摇動。宋失燕、雲,以定州為邊境,故潛備甚密。”雍正《定州志》、清《畿輔通志》、民國版《定縣誌》略同。宋祁另有《登塔》詩寫登塔眺望云:“窣堵緣霄雁勢聯,憑闌清眺俯三川。春華已遍燃燈地,日氣猶烘噀雨天。游蓋結陰塵不動,飲籌催釂客爭傳。須知四級題名處,要記浮生六十年。”開元寺的前身是建於北魏太和十六年(492)的七帝寺。七帝是指從北魏開國到寺院興建時的七位帝王,建七帝寺意在為帝王祈福。隋開皇十六年(596),七帝寺更名為正解寺。到了唐開元二十六年(738),正解寺改以開元為額。北宋咸平四年(1001),真宗下詔建塔,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成,歷時55年。參見賈敏峰、賈寶峰:《定州開元寺沿革考》,載於《文物春秋》2006年第3期,頁11—28。
末句的韓宋是指韓琦(1008—1075)與宋祁(998—1061),韓琦知定州在宋仁宗慶曆八年(1045)四月辛卯③見畢沅《續資治通鑑》卷五〇宋紀,仁宗慶曆八年四月辛卯。,一直到皇祐四年(1052),未見存詩。宋祁知定州在皇祐五年二月(1053)④見胡應麟《玉海》,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據《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卷三,《皇祐御敵論》。,曾登開元寺塔,並題詩紀游⑤宋祁《宋景文公集·開元寺塔偶成十韻》,板橋:藝文印書館1966年版,卷二〇。詩云:“集福仁祠舊,雄成寶塔新。經營一甲子,高下幾由旬。屹立通無礙,支持固有神。雲妨垂處翼,月礙過時輪。頂日珠先現,絛風鐸自振。沙分千界遠,花散四天春。億載如如地,三休上上人。堆螺俯常碣,繚带視河津。陶甓勤爭運,園金施未貧。誰紆簡棲筆,為我誌琳珉。”。蘇軾知州在元祐八年(1093)⑥蘇軾知定州日期,按其元祐八年《九月十四雨中示子由》詩云:“去年秋雨時,我自廬山歸。今年中山去,白首歸無期。”蓋蘇軾元祐八年六月,以端明殿翰林侍讀二學士除知定州,九月尚留京師,行禮部事。冬十月,到定州。見孔凡禮:《蘇軾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版,元祐八年下。又王水照:《蘇軾研究》,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頁397。,在定州半年,留有詩作二十九首,今定州開元寺塔三四樓間梯道猶有東坡題刻留字。
袁宏道第二首詩《過中山見諸名蹟題清風店壁》云:“東坡瘦墨如健鷹”,第三首則是《中山觀長公雪浪石》,詩云:
銀釣錯落繞盆唇,遭時燬禁石僅存。峨嵋積雪裹玄雲,坐令靈璧羞季昆。黑山夜渡蛟波翻,飛濤挂壁天迷昏。漩流入眼風生痕,一洗河北印版紋,石中應有道子魂。①袁宏道著,錢伯城箋:《袁宏道集箋校·登定州開元寺塔》,頁1386。
詩題中的長公即東坡,因為東坡排行長子,時人尊稱為長公。按宋杜綰《雲林石譜》載東坡雪浪石云:“中山府土中出石,灰黑,燥而無聲,温然成質,其紋多白脈籠絡,如披麻旋繞委曲之勢。東坡常往中山,採一石置於燕處,目之為雪浪石。”②杜綰:《雲林石譜》,《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下卷,頁47。中山府即今定州,《輿地廣記》卷一一:“中山府……戰國初為中山國,後為魏所并……大唐改為定州。”③歐陽忞:《輿地廣記》,《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卷一一,頁174—175。蘇軾在定州得到雪浪石,愛不釋手,築雪浪齋以佇之,其《雪浪齋銘引》云:“予於中山後圃得黑石,白脈,如蜀孫位、孫知微所畫石間奔流,盡水之變。又得白石曲陽,為大盆以盛之,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齋云。”銘云:“盡水之變蜀兩孫,與不傳者歸九原。異哉駁石雪浪翻,石中乃有此理存。玉井芙容丈八盆。伏流飛空漱其根。東坡作銘豈多言,四月辛酉紹聖元。”④蘇軾:《蘇東坡全集》,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年版,後集,卷八,頁551。又有《次韻滕大夫三首·雪浪石》詩寫此奇石之由來云:
太行西來萬馬屯,勢與岱岳爭雄尊。飛狐上黨天下脊,半掩落日先黃昏。削成山東二百郡,氣壓代北三家村。千峰石卷矗牙帳,崩崖鑿斷開土門。朅來城下作飛石,一炮驚落天驕魂。承平百年烽燧冷,此物僵臥枯榆根。畫師爭摹雪浪勢,天工不見雷斧痕。離堆四面繞江水,坐無蜀士誰與論?老翁兒戲作飛雨,把酒坐看珠跳盆。此身自幻孰非夢,故國山水聊心存。⑤蘇軾著,王文誥輯:《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9年版,卷三七。又見清馮應榴(1741—1801)輯:《蘇軾詩集合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卷三七,頁1888。袁宏道推尊蘇軾,喜其所喜,東坡珍愛的雪浪石、墨寶,一再出現在他詩中。他對東坡的推尊,也表現在和詩上,萬曆二十八年(1600),袁宏道將將游廬山,過赤壁,有懷東坡,因作《赤壁懷子瞻》,詩云:
夜深清拍嫋楊枝,驚起澄江白鷺鷥。過客爭澆赤壁酒,幾人曾和雪堂詩,山民自種元修菜,石榻剛存乳母碑。見欲鑄金範老子,柳浪湖上拜新祠。①袁宏道著,錢伯城箋:《袁宏道集箋校·赤壁懷子瞻》,頁857。雪堂為蘇軾貶黃州時在東坡於大雪中所築之堂,因名雪堂。東坡更作《黃州雪堂記》誌其築堂始末。詩中元修菜者,據東坡《元修菜》詩并序,應是產於四川東坡家鄉的一種豆科蔬菜②蘇軾《元修菜詩并序》云:“菜之美者,有吾鄉之巢,故人巢元修嗜之,余亦嗜之。元修云:使孔北海見,當復云吾家菜耶?因謂之元修菜。余去鄉十有五年,思而不可得。元修適自蜀來,見余於黃,乃作是詩,使歸致其子,而種之東坡之下云。”詩云:“彼美君家菜,鋪田綠茸茸。豆莢圓且小,槐芽細而豐。種之秋雨餘,擢秀繁霜中。欲花而未萼,一一如青蟲。是時青裙女,採擷何匆匆。烝之復湘之,香色蔚其饛。點酒下鹽豉,縷橙芼薑葱。那知雞與豚,但恐放箸空。春盡苗葉老,耕翻煙雨叢。潤隨甘澤化,暖作青泥融。始終不我負,力與糞壤同。我老忘家舍,楚音變兒童。此物獨嫵媚,終年繫余胸。君歸致其子,囊盛勿函封。張騫移苜蓿,適用如葵菘。馬援載薏苡,羅生等蒿蓬。懸知東坡下,塉鹵化千鍾。長使齊安人,指此説兩翁。”見蘇軾著,王文誥輯:《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二二。另清馮應榴輯注:《蘇軾詩集合注》,卷二二注引趙景和《雲麓漫抄》以為趙以巢菜為豌豆苗,非是,見頁1113。。乳母碑則是指《乳母任氏墓志銘》宋神宗元豐三年(1080)十月,替乳母任采蓮所撰之墓誌③碑文云:“趙郡蘇軾子瞻之乳母任氏,名采蓮,眉之眉山人。父遂,母李氏。事先夫人三十有五年,工巧勤儉,至老不衰。乳亡姊八娘與軾,養視軾之子邁、迨、過,皆有恩勞。從軾官於杭、密、徐、湖,謫於黃。元豐三年八月壬寅,卒於黃之臨臯亭,享年七十有二。十月壬午,葬於黃之東阜黃岡縣之北。銘曰:生有以養之,不必其子也。死有以葬之,不必其里也。我祭其從與享之,其魂氣無不之也。”蘇軾:《蘇東坡全集》,前集,卷三九,頁453。。柳浪湖在今公安孟家溪鎮東,袁宏道曾在湖堤之西築柳浪館閑居,與詩友唱和。
萬曆三十年(1602),袁宏道閑居公安,在二月十二日花朝曾作《花朝和坡公韻》詩云:
絲絲新柳颺堤門,早晚南村又北村。風信暖寒觀樹色,藥苗深淺記竿痕。行來潮覺姑羢重,靜裹頻將姹火温。是物逢春皆作語,子規
未必是啼魂。①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花朝和坡公韻》,頁912。
詩中的姑羢,是一種羊毛衣,由蘭州所產羊毛製成②據民國楊鍾羲《雪橋詩話餘集》,雕龍中日古籍全文資料庫電子書,卷三引《蘭臬載筆》,蘭州所產羊毛尤細者稱姑羢,頁164。。姹火是煉丹之灶火,道家稱水銀為姹女,煉丹需用水銀,故云姹火③姹火一詞少見於古籍,除袁宏道此處使用外,筆者僅檢索到明鄧士亮《心月軒稿》,雕龍中日古籍全文資料庫電子書,卷三有《壽左文郊先生八十先生嗜仙》詩云:“幾尋靈藥到仙源,黍米丹成姹火温。”頁84。詩中黍米原為一植物果實,可作中藥,但在道書中被用來比喻人出生後先天的一點靈氣,稱之為黍米丹,見孔德:《道家内丹丹法要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5年版,附録,丹經譬喻。,按袁宏道未曾行丹道,這裏應該只是升火取暖。子規又名杜鵑,子規啼魂用揚雄《華陽國志》蜀帝典故。全詩寫早春風物,因春寒料峭,故猶未脱冬衣。末以萬物逢春皆自喜作結。東坡原詩題是《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余於女王城東禪莊院》,詩如下:
十日春寒不出門,不知江柳已摇村。稍聞決決流冰谷,盡放青青没燒痕。數畝荒園留我住,半瓶濁酒待君温。去年今日關山路,細雨梅花正斷魂。④見蘇軾著,清王文誥輯注:《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二一。又見清馮應榴輯注:《蘇軾詩集合注》,卷二一,頁1038。
按此詩作於元豐四年,題下王次公注引《東坡志林》云:“黃州城東十五里有永安城,俗謂之女王城。”可知東坡詩作於黃州,原是一首留别詩,詩末所謂“去年今日關山路,細雨梅花正斷魂”者,即指元豐三年過關山時,作有《梅花》詩二首⑤見清馮應榴輯注:《蘇軾詩集合注》,卷二一,頁1038,句下引王次公注。。袁宏道之和詩是和韻而未和題,情境也不同,但就早春情懷之母題及步韻而言乃可謂和東坡詩形成文本互涉。另萬曆三十年(1602)二月,袁宏道在公安有和東坡的梅花詩三首:
世人鬪豐不鬪槁,瘦而能立勝肥倒。世人相喜不相愁,濁快豈若清煩惱。寒花遒逸花典刑,不與夭喬論繁早。根株虬曲榦橫斜,總令無花格也好。山茶肥膩蠻腮紅,蒲柳輕微娼黛掃。孤清妁月婢春雲,白石蒼盡相對老。只將黃髮領芳菲,忍令高姿伴花草。山中夜逢萼綠華,騎著幺鳯上青昊。
花神一夜色枯槁,主人入門愁絶倒。夜深花嘆似人言,主人百事重花惱。一者庸工剪束繁,二者醜女折戴早。三者頭上寧著老鴉啼,不願俗子相憐好。晒褌遺矢主不知,花落青苔任箒掃。算緍立券坐花前,無酒無詩送花老。孤山事我若仙姝,君之視臣如芥草。主人百拜謝花神,過不即芟如春昊。
主人被謔如催槁,空庭百匝愁顛倒。抗顔也作花忠臣,摘葉披技恐花惱。貯君玉照金谷之堂,山驕石佞君開早。貺君和羹驛使之辭,調卑格弱君言好。我無紅碧為君妍,莎臺莓榭躬除掃,宋硯蜀紙李廷珪,折枝貎得花韻老。榮枯開落等一觀,自覺與花非草草。月沉風止兩無言,一方積雪照冥昊。①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和東坡梅花詩韻今年雪多梅開不甚暢為花解嘲復以自解云耳同惟長先生作》,頁914—915。
第一首詩旨在寫梅花的孤標傲世,不以濃膩肥艷媚俗,寒冬中著花,不與高大的花樹競早,是花中典型②典刑一辭和前人寫梅花形成互文,如元胡助《隱趣園八詠》之八“歲寒亭”:“松竹如佳士,梅花更典刑。”,既使不開花,瘦骨枝幹也具高格。而梅花又生長山中崖邊,不求人知,猶如高士,直可與仙人同歸。末聯中萼綠華是仙女名,據《太平廣記·女仙二》引《真誥》云:“萼綠華者,女仙也。年可二十許,上下青衣,顔色絶整。以晉穆帝昇平三年己未十一月十日夜降於羊權家。自云是南山人,不知何仙也。自此一月輒六過其家。權字道學,即晉簡文黃門郎羊欣祖也。權及欣,皆潛修道要,耽玄味真。”③李昉輯:《太平廣記》,《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卷五七,頁103。後來羊權竟和萼綠花同登仙界。
第二首寫俗人不知賞梅花,令主人和花神同愁,或者工人胡亂剪裁,或者醜女折花戴頭,或者枝上烏鴉啼鳴,而人們忙於算錢謀生俗務,竟無詩無酒伴花老去。想孤山隱士林和靖(名逋,967—1028)以梅為妻,而今人視梅如草介,最後主人以春天也不芟除梅花告謝花神。
第三首中主人欲將梅花貯之名園,以免為俗子所欺,並願以筆墨圖畫梅花,使花貌永不老。詩中玉照者,玉照堂也,在杭州。袁宏道萬曆二十五年辭吴縣令後首次游西湖,有雜記16篇記游,其中《晚游六朝待月記》云:“石簣數為余言傅金吾園中梅,張功甫玉照堂故物也,急往觀之。”石簣者,陶望齡;張功甫即張鎡,南宋將領張俊之孫,官奉議郎,職祕閣,能詩善畫。張氏嘗闢地十畝,種植古梅,並築室以賞梅,名曰“玉照堂”,時有梅四百株。金谷園為晋石崇宅第,在洛陽,杜甫《至後》詩有“青袍白馬有何意,金谷銅駝非故鄉。梅花欲開不自覺,棣萼一别永相望”①彭定求等:《全唐詩》,卷二二八。之句。驛使一詞用南朝宋陸凱《贈范曄》詩:“折梅逢驛史,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②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宋詩,卷五,頁1204。李廷珪者,原姓奚,河北易縣人,祖父奚鼐為晚唐製墨名家,以松煙為墨,稱奚鼐墨而聞名。唐末戰亂,奚氏為避亂至歙州,因當地多松,仍以製墨為生,為徽墨之始祖。後廷珪為後主李煜賞識,賜姓李,改名廷珪。所制之墨堅如玉,且有犀紋,時與澄心堂紙、龍尾石硯並稱三寶③參見李遠杰:《河北名人小傳》,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頁169。。袁宏道引用不少事典及句典,和前人形成互文,杜甫和陸凱寫梅花詩久為人所知,讀者在接受時不難索解,也容易引起對前行文本的回溯,在這裏,因為互文的關係,讀者和作者的期待視野(horizon)因而融合為一④有關接受美學、讀者反應理論及期待視野等理論,參見Wolfgang Iser,The Act of Reading(Baltimore:The John Hopkins UP,1974);Jane Tompkins,ed.Reader-Response Criticism(Baltimore:The John Hopkins UP,1980);Hans Robert Jauss,Toward an Aesthetic of Reception.trans.Timothy Bahti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2).。
袁宏道這三首詩和蘇軾的《和秦太虚梅花》,而蘇軾又是和秦觀(1049—1100)《和黃法曹憶建溪梅花同參寥賦》的,秦觀詩又是和黃法曹的⑤黃法曹即黃子理,福建浦城人,時為海陵(今江蘇泰州)司法參軍。,同時和黃法曹詩的還有參寥子。這就使袁宏道的詩和前人之作形成繁複的文本互涉,除了諸人之作如帝網明珠互相映照,諸詩也都韻字相同,詩意複叠。袁宏道追步之作在取法古人之外也有獨創。我們先看蘇軾的《和秦太虚梅花》,詩寫於元豐六年(1083),詩云:
西湖處士骨應槁,只有此詩君壓倒。東坡先生心已灰,為愛君詩被花惱。多情立馬待黃昏,殘雪消遲月出早。江頭千樹春欲暗,竹外一枝斜更好。孤山山下醉眠處,點綴裙腰紛不掃。萬里春隨逐客來,十年花送佳人老。去年花開我已病,今年對花還草草。不如風雨卷春歸,收拾餘香還畀昊。①見蘇軾著,王文誥輯注:《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二二。又見清馮應榴輯注:《蘇軾詩集合注》卷二一,頁1137。
西湖處士指林和靖,袁宏道在第二首詩中也提到。蘇詩“江頭千樹春欲暗,竹外一枝斜更好”。更令人想到林和靖的《山園小梅》中的“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②林逋:《和靖詩集》,《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卷二,頁36。《山園小梅》全詩如下:“衆芳摇落獨暄妍,占盡風情向小園。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斷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須檀板共金樽。”。“被花惱”一句也是杜甫《絶句》“江上被花惱不徹”的互文。“萬里逐客”兩句,蓋蘇軾自熙寧四年(1071)因和王安石不和出判杭州,再責黃州,十年之間從杭州、密州、徐州再到黃州,輾轉薄宦,故自比逐客,更言心已成灰,想來只有梅花稍可安慰情懷。末句用《詩·小雅·巷伯》:“投畀有昊”之典,謂將梅花餘香投向昊天也。
再看秦觀《和黃法曹憶建溪梅花同參寥賦》,詩云:
海陵參軍不枯槁,醉憶梅花愁絶倒。為憐一枝傍寒溪,花水多情自相惱。清淚斑斑知有恨,恨春相逢苦不早。甘心結子待君來,洗雨梳風為誰好?誰云廣平心似鐵,不惜珠璣與揮掃。月没參橫畫角哀,暗香銷盡令人老。天分四時不相貸,孤芳轉盼同衰草。要須健步遠移歸,亂插繁華向晴昊。③秦觀:《淮海集》,《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卷三,頁52。
海陵參軍即黃子理,“誰云廣平心似鐵”一句,廣平者,宋璟(663—737)字也。宋璟有《梅花賦》,其序云:“垂拱三年,余春秋二十有五,戰藝再北,隨從父之東川,授館官舍。時病連月,顧瞻圯牆,有梅一本,敷蘤於榛莽中,喟然歎曰:斯梅托非其所,出群之姿,何以别乎?若其貞心不改,是則可取也已。感而成興,遂作賦。”④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版,卷二〇七。後來皮日休倣宋璟作《梅花賦》,有《梅花賦序》云:“余嘗慕宋廣平之為相,貞姿勁質,剛態毅狀。疑其鐵腸石心,不解吐婉媚辭。然睹其文而有《梅花賦》,清便富豔,得南朝徐庾體,殊不類其為人也。”①皮日休:《皮子文藪》,《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卷一,頁23。秦觀此句承自皮日休,皮日休寫梅花又承自宋璟,下文我們可以看到,袁宏道《和東坡聚星堂韻》詩又再次用了廣平心如鐵的典故。中國古典詩中很多詩都可探本溯源,也可以説前有所承,戛戛獨創之中不免有沿襲。秦觀此詩也是如此,心如鐵、暗香等都是用典,已和古人之作為互文,又因是和詩和韻,又和今人梅花之作為互文,諸人之作等於古往今來,時空交錯中的一幅織錦。
再看參寥的詩,參寥即釋道潛(1043—1106),參寥和詩《次韻少游和子理梅花》,全詩如下:
朔風蕭蕭方振槁,雪壓茅齋欲欹倒。門前誰送一枝梅,問訊山僧少病惱。強將筆力為摹寫,麗句已輸何遜早。碧桃丹杏空自妍,嚼蘂嗅香無此好。先生攜酒傍玉叢,醉裏雄辭驚電掃。東溪不見謫仙人,江路還逢少陵老。我雖不飲為詩牽,不惜山衣同借草。要看陶令插花歸,醉臥清風軼軒昊。②釋道潛:《參寥集》,哈佛大學: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卷三。按南朝梁何遜有《詠早梅揚州法曹梅花盛開》詩云:“兔園標物序,驚時最是梅。銜霜當路發,映雪擬寒開。枝橫卻月觀,花繞凌風臺。朝灑長門泣,夕駐臨邛杯。應知早飄落,故逐上春來。”③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梁詩,卷九,頁1699。後來杜甫有《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詩云:“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此時對雪遥相憶,送客逢春可自由。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為看去亂鄉愁。江邊一樹垂垂發,朝夕催人自白頭。”④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卷二二六。李白則有《送友人遊梅湖》,有句:“送君游梅湖,應見梅花發。有使寄我來,無令紅芳歇。”⑤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卷一七五。李白詩和杜甫詩都用了陸凱詩折梅的典故。參寥的詩在何遜、杜甫、李白的基礎上,寫自己雖不如飲酒,但愛花愛詩和陶淵明並無不同。詩末表達了願如陶淵明般做個醉臥清風超軼軒轅、少昊的羲皇上人。
袁宏道追步蘇軾,在蘇軾及其詩友的梅花詩上踵事增華,鋪衍為三首,形成和前人作品互相映襯。袁詩和蘇試中都用到西湖處士林和靖在孤山梅妻鶴子的典故,也都寄託了花落人老的感慨。但袁宏道後出轉精之處在他詩歌語言較東坡活潑及口語化,第二首且以雜言代替齊言,另一方面,袁詩用了更多典故,諸如梅花詩中常見的陸凱詩折梅贈驛使以及較少見的萼綠華及李廷珪之典。我們看到,袁詩在唱和蘇詩的同時,又有自己的獨創性,在文本互涉中既有前文本,又刮去前文本,在羊皮紙上傳達了新訊息。
袁宏道另一首《和東坡聚星堂韻》則云:
凍鳥無語僵寒葉,曉起漫堦五尺雪。穿簾撲幔綴斜風,楯碧紗紅景幽絶。罏膏乍澀紫絨生,研冷煤枯霜穎折。千梢擺壓鳳翅垂,萬瓦齊鋪烏鱗滅。近牆老鵠不知人,却立氋氃如被掣。月團三百沸温瓶,盈碗漚花瀉文纈。高禪滿坐氍毹床,佳言衝口栴檀屑。楊岐偈子再三題,龐老機鋒時一瞥。東坡先生寫雪真,不用煩言與喻説。杜老梅花詩亦然,廣平空有心如鐵。①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和東坡聚星堂韻》,頁1051。
東坡《聚星堂雪並引》云:
元祐六年(1091)十一月一日,禱雨張龍公,得小雪,與客會飲聚星堂。忽憶歐陽文忠作守時,雪中約客賦詩,禁體物語,於艱難中特出奇麗,爾來四十餘年莫有繼者。僕以老門生繼公後,雖不足追配先生,而賓客之美殆不減當時,公之二子又適在郡,故輒舉前令,各賦一篇。
窗前暗響鳴枯葉,龍公試手行初雪。映空先集疑有無,作態斜飛正愁絶。衆賓起舞風竹亂,老守先醉霜松折。恨無翠袖點橫斜,只有微燈照明滅。歸來尚喜更鼓永,晨起不待鈴索掣。未嫌長夜作衣稜,卻怕初陽生眼纈。欲浮大白追餘賞,幸有回飆驚落屑。模糊檜頂獨多時,歷亂瓦溝裁一瞥。汝南先賢有故事,醉翁詩話誰續説。當時號令君聽取,白戰不計持寸鐵。②見蘇軾著,王文誥輯注:《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三四。又見清馮應榴輯注:《蘇軾詩集合注》卷三四,頁1723。
袁宏道詩中用了許多典故,楊岐指楊岐方會禪師(992—約1049),因方會住袁州楊岐山普明禪院,故名。他師事臨濟宗門下之石霜楚圓禪師(986—1039),自成楊岐派,世稱楊岐禪師。龐老指龐居士,字道玄,生歿年代不詳,《祖堂集》卷一五記載他生於湖南衡陽,見到馬祖道一大師,便問:不與萬法為侣者是什麽人?馬師回説:待居士一口吸盡西江水,我則為你説。居士便於言下大悟,遂不變儒服,心游象外,混跡人間,初住湖北的襄陽東巖,後居郭西小舍,唯將一女服侍,製造竹簍,令女市貨,以維生計。另梅雪典故,除了東坡聚星堂詩外,還用了杜甫《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之典,在詩體上則全詩學步歐陽脩、蘇軾等的禁體物語,寫梅花、雪而不用常語,初看全不似寫雪、梅。從各方面看,袁宏道此詩都是唐、宋諸人之作的模仿。
再看蘇軾原詩,序文中之張龍公為傳説中人物,能致雨,蓋蘇軾在元祐六年自杭州召回,出守潁州,十月在潁州有《祈雨張龍公祝文》、《禱雨張龍公既應劉景文有詩次韻》,序文中汝南也即潁州。另所謂“禁體物語”,也就是詠某物不得用某物常見之慣用語①如五代僧神彧《詩格》論破題《直致》,引崔補闕《詠邊庭雪》“萬里一點白,長空鳥不飛”,謂“此用白一字,傷其雪體,故云直致”,已開詠雪禁體之例。唯歐陽脩《六一詩話》謂此體創始於宋初進士許洞之賦詩約禁,歐陽脩在潁州撰《雪》詩,自我設限,所謂“禁體物語”詩之範式,於焉提出。嘉祐三年(1058),歐陽脩《與梅聖俞》書簡曾言:“前承惠《白兔》詩,偶尋不見,欲别求一本。兼為諸君所作,皆以常娥月宫為説,頗願吾兄以他意别作一篇,庶幾高出群類,然非老筆不可。”是歐公之願望於梅堯臣者,不止於“禁語”,更添加“禁意”,所謂“以他意别作一篇”者是。其後,傳梅堯臣著之《續金針詩格》,楬櫫“詩有七不得”,所謂“説見不得言見,説聞不得言聞,説靜不得言靜,説樂不得言樂”云云,著重“不犯正位”之描述,已略述禁體之詩法。參見張高評:《白戰體與宋詩之創意造語:禁體物詠雪詩及其因難見巧》,載於《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49期(2009年5月),頁173—212。,蘇軾《聚星堂雪》一詩,特提“汝南先賢有故事,白戰不許持寸鐵”,故“禁體物語”又稱“白戰體”,強調白描手法,以及無所依傍。所謂汝南故事即當年歐陽脩在潁州因雪會客作詩時,相約禁用“玉、月、梨、梅、練、絮、白、舞、鵝、鶴、銀”等寫雪之常用語。其後蘇軾繼作,除《聚星堂雪》外,尚有《江上值雪》、《雪後書北臺壁二首》諸詩,踵事增華,於艱難中特出奇麗,標榜自鑄偉詞,不傍前人,以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的手法創新出奇。
蘇軾、袁宏道二人詩相同之處都在用歐陽脩創發的禁體物語,寫雪而不用雪的平常形容詞,於是專用旁敲側擊的方式,兩詩中都用了許多和雪相關的典故,但都不是直接讓人容易想到是雪。袁詩就其用白戰體和次韻而言,當然是不出東坡原詩,但在尊蘇學蘇的前題下,他又自創了許多新辭,用了許多罕見典故、偏僻詞語,可謂有傳承,也有代變,和前人文本互涉而又自有新意,這是袁詩獨抒性情的創造性。
除了和詩之外,袁宏道也在許多詩中歌詠蘇軾軼事,如《石公解嘲》詩云:
於是石公乃攘袂而起,撫手按節而為之歌。歌曰昔者汝陽王,道逢麯車口流涎,醉鄉之日月不加延。後來蘇子瞻,望酒盞而醉,醉鄉之日月不加逝。又歌曰信美此土兮,樂而忘死。①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石公解嘲詩》,頁552。東坡不善飲酒,曾自言少年時望酒盞而醉,成年後則僅能飲三蕉葉②見蘇軾《題子明詩後》,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卷八。按此篇題跋宋程俠刻本、今河洛出版《蘇東坡全集》失收。東坡不善飲相關論述見黃啟方《我雖不解飲,把盞歡意足——東坡酒量淺論》,載於《東坡的心靈世界》,臺北:學生書局2002年版,頁5—12。。袁宏道在詩中引用了飲酒的典故,汝陽王一典,出自杜甫《飲中八仙歌》:“汝陽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車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③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卷二一六。汝陽王李璡(?—750)是唐朝讓皇帝李憲的長子,獲封為汝陽王。官至太僕卿,善飲,又得到釀王的封號。信美此土一句出自王粲《登樓賦》:“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
又在《贈黃平倩編修》詩云:
窗前獨種菴婆羅,石火風燈不浪過。緗帙夜繙塵牘少,客衣春晒衲頭多。亳端漭漭書巴水,枕上巉巉夢小峩。詩有餘師禪有友,前希李白後東坡。④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贈黃平倩編修》,頁623。
此詩中更是以蘇軾為詩歌上的老師,尚友古人。前文曾提及,典故、徵引詩句、讚辭、佚事等的入詩,都是讀者接受的一種表現,也是互文的一種現象,後來者不僅在和詩中對前賢致意,也有競作逞才之心,因此這些詩作,雖説是追步前作,但模仿之餘也有後來者的獨創之處,這也是袁宏道詩論雖主張獨抒性情,但在他的實際創作上,卻不免時時模仿前人,和前人之作文本互涉,這種現象在他追和白居易、蘇軾的詩作時尤為明顯,當然這也是因為白、蘇是他最推尊的詩人之故。
四、結 論
文學作品是作家個性與心靈的表現,因此講求獨特性,作家因之可以露才呈性,但文學也有其傳統,作家不可能自外於文學傳統,作家文學作品必須放在傳統中才能評估其作品的價值與個人才性。這是作家的兩難處境,一方面作家要獨抒性情,一方面又要兼顧傳統,如何可能?其次,近代文論有所謂影響的焦慮,任何作家,均負荷著前人對自己影響的焦慮,後來者必須對早先的作品重新運用、翻案,以便發展出本身的創意。世上所有偉大的文學創作,均乃是對於前輩作家的一種誤讀,後來者必須將誤讀作為新解,每個人的寫作、思考、閲讀,都無法避免模仿,模仿是一種文本互涉,所有的文本或文學作品都和他人之作形成互涉,文本彼此互相聯繫的現象廣泛存在,旁徵博引和典故應用都是互文性,他人的文本和自己的文本不斷地交涉,後來者對前行者或者翻案,或者諧擬,或者風格模仿,或者是刻意的重複、引用,使得文本意義更加豐富,任何一部藝術作品都是作為某一前行作品的類比和對照而創作的。互文便無獨創,但袁宏道的詩歌理論又提出了獨抒性情的主張,這是可能且可行的嗎?在文本互涉的語境中,詩歌創作中還能説是字字由己出嗎?還是袁宏道其實在不自覺中表現出了理論與作品間的辨證或者甚至是悖反?這是本文的問題意識,也是本文希望透過袁宏道文學理論與詩歌的檢驗,來討論文學創作中傳承與新變之間的關係。
如同上文的論述,我們得出,袁宏道的詩學,雖主張獨創,但在實際創作中,尤其是追步前人的和詩和擬作,仍不免通過使用典故、徵引詩句、讚辭、佚事等的入詩,和前行詩人形成文本互涉。文本互涉是讀者反應和接受的一種表現,後來者的和詩擬作,不僅是對前賢致意,也有競作逞才之心,這些詩作在模仿之餘也有其獨創之處,這也是袁宏道詩論雖主張獨抒性情,但在他的實際創作上,卻不免時時模仿前人,這種現象在他追和白居易、蘇軾的詩作時尤為明顯,當然這也是因為白、蘇是他最推尊的詩人之故。
經由文學理論的實際操作,也許我們可以對文本互涉提出若干修正,文本互涉理論指出所有文本都是前行文本的翻案、諧擬、風格模仿等,固然有其真實性。但我們也能看出,文學創作者的個性以及創新的文學本質,使得作家必得在前人影響的焦慮中推陳出新,因此文本互涉和袁宏道的獨抒其實是一種辨證的關係,作者在前人作品的巨大影子下,以其獨特的性情,走出影子,創造出自己的一片光彩,袁宏道追和白居易和蘇東坡的詩作給了我們最好的例證。